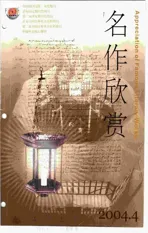拆碎七宝楼台与探秘珠宫贝阙
——与李天飞道长《西游》论妙
2017-07-13辽宁梁归智
辽宁 梁归智
拆碎七宝楼台与探秘珠宫贝阙——与李天飞道长《西游》论妙
辽宁 梁归智
李天飞道长的“抽丝剥茧”“分出层”,就是把《西游记》这座“七宝楼台”一片片拆下来,“择出来”,显示出每一段楼台的原始真相。李道长的考证,与本文作者悟证和论证彼此参照,互相生发,于《西游记》“思想”“艺术”“文化”“历史”等奥妙的显示发扬,各有其作用功能。
李天飞 《西游记》 考证知识
华夏古历,丙申是猴年,而《西游记》的第一主角,乃一只猴子,英文版《西游记》书名,就是“Monkey”,直接翻译成“猴子”。李天飞先生“识时务者为俊杰”,于2016年2月18日,也就是华夏历丙申年元旦之日起,在自家的微信公众号“仙儿”上开讲西游,每日一讲,玉兔走金乌飞,转眼之间,到了2016年5月18日——丙申年四月十二日,已经完成了一百讲。李先生真不愧“天飞”神将也!
李先生在西游讲座中以“贫道”自呼,出于对仗,笔者就自诩“老僧”,后面行文,也就称李先生为李道长了,呵呵。话说老僧后知后觉,在李道长已经“天飞”了十几讲之后,才得知这一消息。从此“追踪蹑迹”阅读,并补阅了前面的十几讲。如此热衷,因缘是老僧也算一个《西游记》的研究者。早在1996年,写过一篇《自由的隐喻——〈西游记〉的一种解读》,后来被收入梅新林和崔小敬主编的《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成了所谓《西游记》主题“自由说”的代表作。2012年11月,三晋出版社出版了老僧的评批本《西游记》。2015年和2016年,《名作欣赏》上旬刊陆续发表了鉴赏《西游记》的几篇“经典探秘”文章。
有了以上背景,对李天飞道长的“讲西游”,自然就生起了“惺惺相惜”而欲“华山论剑”的兴趣。先谈初步的印象,李道长的“讲西游”,最大的佳胜之处,是文献的广泛搜检和深入发掘。李道长是出身名校古典文献专业的高材生,供职于高端出版社,早已做过校注《西游记》的大功课,中华书局2014年10月出版的“中华经典小说注释系列”之《西游记》,堪称超越此前各家注本之最详尽深入的校注本。有了这种雄厚的“资本”和“优势”,李道长讲起《西游记》来,自然是蓄势待发、厚积薄发而任意抒发,日做一讲却无匆促窘迫之态,优游裕如地寻根问源而说得头头是道。李道长在其校注本《西游记》“前言”中如是说:
对于《西游记》注释的困难,在于它的知识体系极为广泛,不像文人诗词那么精致,基本从传世文献中就能找到答案。《西游记》涉及的知识,虽然每个部类都不深,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及佛道二藏,甚至还得翻检宝卷、法律文书、建筑、壁画、雕塑等文献。通过注释,恰可以还原《西游记》的知识体系,同时也就是此书作者或作者群的知识面貌,从而把《西游记》还原到历史的一环去,尽可能反映出一个生动的明代社会。
旨哉斯言!老僧有评批、研讨《西游记》的经历,对此也颇有体会。虽然有了网络时代查寻资料的便捷途径,老僧知道李道长注解《西游记》,恐怕还是下了不少排沙简金的“笨”功夫,“三更灯火五更鸡”地熬过夜吧。即便有电脑检索的方便,但“上穷碧落下黄泉”,也得知道往哪里去寻觅啊(看到第一百讲,才知道校注《西游记》,李道长花费了九年的时光!)还有,李道长交代得明白,他的注解吸收了相当广泛的前人研究成果,而“《西游记》的研究成果,到今天已蔚然可观”,要采择拣选“拿来”,其实也得做一番投入。
于是我们看到,李道长对《西游记》中的角色、情节、细节,甚至某个词语,都一一做了“还原”,娓娓道来而有根有据。
比如他说在《西游记》的早期故事中,其实沙和尚是二师兄,而猪八戒是三师弟,所以那一副沉重的取经担子,才会由最小的师弟担负到西天;比如昔日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记录的一部元代《西游记》,唐僧三个徒弟的排序,猪八戒就排在沙和尚后面。再说取经故事的演变中,沙和尚本来就出现得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已经有了猴行者和深沙神,却没有猪八戒的影子,要到元明时期的《西游记》杂剧,猪八戒才出了茅庐。明代定本《西游记》中猪八戒上升为二师兄,沙僧成了三师弟,但挑担子的角色却延续了历史情况。当然后来的连环画和电视剧中,是沙僧挑担子,但那是不符合小说文本描写的现代人改编。
更进一步,李道长考证,说猪八戒在浮屠山云栈洞时期入赘高老庄当上门女婿前,曾有个前妻卵二姐,其实应该是卯二姐,卵是卯的传抄之误。因为干支里面卯属兔,而猪属亥,这是根据星命术数,十二地支互有冲犯和合,其中亥、卯、未合五行金木水火土中的木。给亥猪骚八戒用干支配对,所以是卯二姐。
又比如第九十二讲,题目叫“玄奘法师一定要背个大登山包?”说的是我们在语文课本和电视片《大唐玄奘》中看到的玄奘的标准造型——像个驴友背着类似登山包的唐三藏,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的误传误认。首先,唐玄奘法师去印度,其实像《西游记》里一样,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有马骑坐的,没有辛苦到自己背负登山包。其次,误传来自玄奘背负登山包的一幅流传久远的图像,其底本藏在日本东京的国立博物馆,而这幅图像其实只是画的一个僧人,并非唐玄奘!李道长旁征博引,出示了孙英刚《三藏法师像初探——一件珍贵的图像文献》,陆宗润《玄奘法师像非玄奘》、李翎《玄奘画像解读——特别关注其密教图像元素》等论文考证成果和各种文物图像,不局限于学术圈而是在广泛的社会层面澄清了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功德一件。
能在一个细节里剥茧抽丝而扯出多多的学问,让读者眼前一亮道一声“原来如此”,这就是文献学的功夫了。但文献学素来有枯燥乏味的名声,到了李道长的笔下,却变得趣味盎然,这是李道长讲《西游记》的另一个贡献,是真本事。李道长可不是死钻进文献里出不来的传统意义上的老学究,而是一位红颜绿鬓风华正茂的新潮青年才俊,甚至称得上是个倜傥风流的才子,不仅擅长书法丹青,而且能做美丽的诗词。如此这般的李道长,写文章遣词造句,就没有搞文献专业者常见的枯窘呆板横秋老气状,不仅文通字顺,通俗易懂,而且颇能与时俱进,衔接上网络时代的“地气”而自如自在。看看他“讲西游”的题目:
装逼和牛逼——第一讲;好囧的弼马温——第四讲;哪吒你还能穿得再少点吗——第七讲;二郎神你为啥这么小鲜肉——第十讲;做营销,你未必做得过四海龙王——第五十七讲;老鼠姑娘要出嫁,来了和尚就嫁给他——第八十四讲……
过去说言之无文则行而不远,但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在相当程度上可讲究言之不俗则行而不远。只有俗——通俗易懂到生动甚至有点“下贱”,才能博得广泛的受众青睐和赢得众多的粉丝。李道长深谙此理,把文(文献学问)和俗(通俗表达)相当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偏僻古奥的文献知识在活泼调侃的语言表述中,轻轻松松地楔入到众多读者的“脑洞”中了。
李道长“讲西游”中有不少篇幅,属于考证知识的普及。大体上是这样几类:关于道教和佛教以及民间信仰等传说在《西游记》中错综交缠情况的解析,比如第十六讲《玉帝的名字和太上老君的住处》,第二十五讲《轮回居然是这样的,佛祖你知道吗?》,第六十一讲《一张图告诉你什么叫“犯天条”》,第九十九讲中关于“5048”这个神秘数字中“潜藏的丹道知识”;有《西游记》成书过程中角色故事原型不断变迁演进的考察缕述,如第八讲《老娘才不想嫁给你》,第三十九讲《石槃陀,你在寻思什么?》,第四十三讲《起底镇元大仙》;有历史上各朝代特别是《西游记》成书的明代社会之时代背景知识的说明,如第九十讲《玉华州的明代经济史》,第九十四讲《一个吃货眼中的〈西游记〉》,第九十五讲《〈西游记〉里是怎样出警抓人的?》等。
这些讲述不仅普及了历史文化知识,还经常和当代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互相联系、映照,更增加了可读性。比如第八十一讲《盘丝洞的那点事》,在追溯了“盘丝洞是个永恒的故事”,即“偷窥洗澡”乃源远流长的人性表现后,最后落实到了“恋爱那点事”:“初心很重要,有些情侣是真心的,有些只是为了玩玩,有些贪图某种利益在一起……这些初始条件就完全不一样,不要小看这个初始条件,它决定了感情的基本走向;但是即便在一起了,也有许多边界条件,例如,能够忍受多久的异地恋,能够忍受多久的繁忙工作,手里的积蓄有多少等。感情需要各种条件,并不是说只要一片真心就一定不出问题。然而,作为初始条件的真心是最重要的!”曲终奏雅,归结到“正能量”,漂亮!
李道长的“讲西游”,澄清了一些网络上的“西游乱弹”。可能《西游记》的普泛性太强了,可能大家接触到的第一本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这本书,它又是神魔小说,留出来的口子大,所以现在网上对《西游记》的“信口开河”几乎已经泛滥,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乱象。李道长讲西游,对某些胡诌乱侃的无根游谈具有正本清源的矫正作用。突出的例子是第六十七讲《别上当了,孙悟空根本就没死在取经途中!》,网上有一种奇葩的说法,即所谓真假猴王故事中,被打死的那个,是真孙悟空,此后跟着唐僧到西天取经的那个,是六耳猕猴,这些都是如来的阴谋,是为了搞倒他的对手菩提祖师云云。李道长紧扣小说文本,条分缕析,逐条反驳“网上一些不靠谱的证据”,最后说:“网上说‘孙悟空其实已经死在取经途中’的梗,一是编造谣言,二是偷天换日,三是断章取义,连蒙带猜带造谣地骗人。骗的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既不读原著,也不读《封神演义》,只看电视剧的人。当然贫道相信,这个说法的本意只是娱乐,可是拿着这件事当真相,那就实在是太轻信别人了!”
但李道长对“真假猴王”却给出了这样的结论:“贫道负责任地说,真假孙悟空去的那个西天雷音寺都是假的!或者说,那个如来都是假的,真的如来已经死了或被软禁了,现在这个如来是菩提祖师变的!”
李道长这样说的理路是:真假猴王打到西天时,如来佛正在讲经,讲到这一段:“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空即是空,色即是色。色无定色,色即是空。空无定空,空即是色。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而这段经文,“翻遍整个大藏经,一点影也找不到”,因为这一段根本就不是佛经,而出自道教经典《太上洞玄灵宝升玄消灾护命妙经》,是元始天尊说的。那么只有孙悟空的第一个师父菩提祖师贯通三教,佛理道法皆精,所谓“妙演三乘教,精微万法全。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西游记》第二回),那么,推理的结果是:“两位孙悟空打到西天的时候,那个宝座上的如来,恐怕就是菩提祖师变的!要不就是雷音寺被元始天尊占领了!”
当然,李道长颇会写文章,很快就声明这只是根据网上的奇葩逻辑也“戏说”一下,增加文章的趣味性。但这种戏说,也反映李道长一个根本的学术立场,即“《西游记》并不一定是扬佛抑道的”,而《西游记》的作者,其实对道教的经典比对佛教的经典更熟悉。应该说,李道长对《西游记》文本许多细节的考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但从这一认知基点,又“逗漏”出李道长进一层的学术认知和治学路向,老僧却要和李道长商榷切磋一番了。
在《西游记》校注本前言中,李道长交代了对《西游记》研究已有各种说法的认同,其中提到采纳了蔡铁鹰先生的“孙悟空”“齐天大圣”为两个形象说。在一百篇“讲西游”中,更突出表现李道长认为《西游记》乃一部由两套故事系统“在元代的时候硬拧巴到一起去的”(第五讲:孙大圣和孙行者:我大闹天宫,你却到处被打爆)作品。在这一讲的结尾,李道长说:
孙悟空前后本领不一,完全是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观众出于不同的目的,加在他身上的命运。今天的《西游记》故事,就像一块一层层浇上的奶油蛋糕,它在几百年的流传中,至少叠加了三层:第一层,是最古老的,是一些宣扬佛教的故事;第二层,是后来全真教道士们为了讲内丹加入的;第三层,是另一些和民间信仰有关的人士加入的。其实还可能有第四层……贫道这一百天为大家连载解读西游,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抽丝剥茧的方法,把这些层化掉的奶油,重新分出层来。把叠加在《西游记》里的这些层次,一个一个地择出来。还给大家一部清晰透彻的《西游记》。
应该说,李道长的许多考证做得不错,这也就是老僧为本文所拟标题“拆碎七宝楼台”所意指的。李道长的“抽丝剥茧”“分出层”,就是把《西游记》这座七宝楼台一片片拆下来,“择出来”,显示出每一段楼台的原始真相。“拆碎七宝楼台”的说法,来自南宋词人张炎在《词源》中评同代词人吴文英词:“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老僧用此典,是想说,李道长把《西游记》的“七宝楼台”拆碎的结果,有时就难以避免“不成片段”(用当代的说法,就是“一地鸡毛”)的尴尬。
一个显著的因果,是李道长否认了《西游记》具有“一个中心思想”的认知。在校注本《西游记》的前言中,李道长夫子自道:“笔者既不强作解人,也不勉为折衷,而是本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先做文本上的解读。这样,虽然提不出一套像样的理论,但是至少会使读者理解《西游记》时,不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出现偏差。我们知道,一部伟大的著作,总会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心中产生不同的回响;但自来也不曾听说,哪部经典一定就能被人轻易概括出了无可移易而类似标准答案的‘中心思想’。”
这里面有两个层面的吊诡。第一个吊诡来自西方文艺理论,即所谓“接受美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会对同一部作品产生不同的“读者接受反应”。既然时代的差异、个体的差异,将使作品的“主旨”或者“中心思想”不断发生变化,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第二个吊诡,则特别是像《西游记》这样经历了好几百年时代累积型演变的古代小说,作者无法确定,那个最终的写定者的身份角色不明朗,就更容易因“妾身未分明”而被李道长这样的研究者“分层”袪魅了。
这是老僧不能苟同李道长的两个关键之点。
关于接受美学,老僧早在研讨《红楼梦》的论著中就说过,需要一点辩证法,而不能过于绝对化。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作者的“原意”、原著的“本旨”,还是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可以“还原”和追索,不能把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弄成绝对的相对主义。作者固然不是上帝,读者也同样不能独尊,而要兼顾两方面。把相对主义绝对化,同样捉襟见肘。也就是说,不管各朝各代的读者如何受自己那个时代的思潮和自己独特个性的影响,而对《西游记》有各自的角度和创见,《西游记》文本仍然存在一种原始的基本的“中心思想”,客观的读者和研究者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予以“还原”。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对作品之“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深度揭示。
《西游记》有漫长的成书演变过程,从玄奘口述辩机记录的《大唐西域记》,以及慧立、彦悰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到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再到元代人《西游记平话》(明初《永乐大典》与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各存一段)、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人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此二种仅见著录,文本已佚,吴昌龄剧本有残文)、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一路演变丰富发展,到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乃最后横空出世。这些也就是李道长深入其间而“择出来”“分出层”的最基本材料。当然李道长的内功更加深厚,还从宝卷、法律文书、建筑、壁画、雕塑等文献中旁搜广觅,集腋成裘,而完成其拆碎七宝楼台“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
但李道长似乎过于沉迷“拆碎”和“还原历史”的过程,似乎忽略了最后的定本百回本《西游记》,其实是有一位大才子做了创造性的“整合”工作。可以这样说,尽管可能的确有全真教道士和民间信仰人士给西游故事添过砖加过瓦,但有一位大才子的匠心独运才是最后成书的。从这种意义上,这位大才子完全可以说是《西游记》的作者。
至于这位大才子是谁,在这一点上,老僧和多数《西游记》研究者取相同立场,他并不一定是吴承恩,现在只能说是一位无名氏。
但这位无名氏的工作具有原创意义,基本上决定和规范了《西游记》的“中心思想”和“艺术特质”。
老僧的这种认知立场,就和李道长大异其趣了。老僧的评批本《西游记》和“经典探秘”那几篇文章,其主体内容就是揭示这位《西游记》最后写定者的灵心慧性,以及他所赋予《西游记》的“中心思想”和“艺术特质”。在这种视野下,之前为取经故事添加砖瓦的全真道人和民间信仰人士们,只是为这位写定者准备了某些原料而已。是这位兼有李道长才气和老僧灵感的天才作家利用了前人提供的“片段”材料,发挥大智慧施展大本领,创建起辉煌的七宝楼台——珠宫贝阙。定本《西游记》,完全是这位无名大才士的原创性贡献!
这位大才士,这位《西游记》的写定者,更值得我们仰视赞叹,他所创建的七宝楼台——珠宫贝阙定本《西游记》,其间有无限的神秘瑰丽,更值得我们去探索、去研究。也就是说《西游记》其实含蕴着深刻的中心思想和卓越的艺术特质,更值得关注和研讨。
由此引申,还可以深入一点理论视野的思考。就是“四大奇书”和后来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甚至包括之前的《封神演义》,其实是不能与其他明清通俗小说等量齐观的。这几部书,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明清通俗小说,而是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了经典,就在于其中已经蕴涵了深刻的文化、思想,具有自觉的高超艺术,而之所以达到如此水平,乃在于这几部书,都有某位天才级别的大才士对之做了决定性的“升华”,大才士完全可以说是书的作者。尽管撰写这几部经典的大才士作者姓甚名谁,除了吴敬梓,其他都充满了争议而不能十分确定。但是,这几部小说已经上升为具有“哲学”和“艺术”质量的高级结晶体,则是确定无疑的,因而对于其“时代累积型演变”原始形态的“还原”就要把握分寸,过了头,就成了“毁玉挝珠”和“焚花散麝”。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先生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出版),就比较深入地探索了“四大奇书”的金质玉相。多年以前,周汝昌先生就曾撰文,对浦安迪提出“奇书文体”这一理论概念大加赞扬,认为这样就把几大经典名著与一般的明清通俗小说严格区别开来。
明人不说暗话,老僧不敢苟同有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不能认同“孙悟空”“齐天大圣”为两个形象的说法,不能认同《西游记》乃一部由两套故事系统“在元代的时候硬拧巴到一起去的”说法。即使这个阶段在早期的取经故事演变中确实一度存在过,也是“弱弱的”,经过了天才写定者的整合创作,孙悟空和齐天大圣已经完全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并无矛盾而是充满了哲理内涵和审美意蕴的不朽艺术形象了。“两个故事系统”“两个孙悟空”早已契合(不是“拧巴”)圆融,无论情节逻辑、性格逻辑、审美逻辑,都实现了质的飞跃,成了美轮美奂的艺术珍品,绝非粗枝大叶拼合因而自相矛盾的积木毛坯。
老僧所写《孙悟空本领的大小之谜——〈西游记〉经典探秘之一》(《名作欣赏》上旬刊2015年第7期,其微信公众号题目为“取经路上,孙悟空的本领变小了吗”)就揭示了孙悟空从石猴到美猴王到弼马温到齐天大圣到孙行者到斗战胜佛变迁过程的思想密码和艺术密码。把老僧这篇文章和李道长的《孙大圣和孙行者:我大闹天宫,你却到处被打爆》对照阅读,其间的“张力”不是满满的吗?
老僧所写的《天路历程之谜——〈西游记〉经典探秘之二》(《名作欣赏》上旬刊2015年第9期,其微信公众号题目为“通天河:作为取经路中点的意义”)、《心路历程之谜——〈西游记〉经典探秘之三》(《名作欣赏》上旬刊2015年第10期,其微信公众号题目为“《西游记》探秘:孙悟空心路历程之谜”)、《女妖怪的隐喻——〈西游记〉经典探秘之四》(《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2期,其微信公众号题目为“《西游记》经典探秘:女妖怪的隐喻”)、《草蛇灰线,一击两鸣——〈西游记〉经典探秘之五》(《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3期,其微信公众号题目为“《西游记》里‘桃子’和‘诗词’的隐喻”),这些揭示定本《西游记》思想和艺术奥秘的文章,和李道长对取经故事“择出来”“分出层”的各集“讲西游”对照阅读,也将产生分外生动的“碰撞”而又“磨合”之美。
举一个例子。李道长在第四十五讲《白骨精的罗生门》中,回顾了一打白骨精、二打白骨精、三打白骨精的情节描写后,以“怎样对待证据”“火眼金睛并没有被证实过”“唐僧何时成了人妖不分的代名词”“束缚暴力的紧箍咒”为小标题做了讨论,最后说:“到底是谁更有破坏的力量,到底是谁更应该受到约束?到底是谁更应该多被苛责?但是,可不可以把孙悟空赶走?赶走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故事,太深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听惯了对紧箍咒的批判,听惯了对唐僧的丑化。我们一定要清楚,谁是唐僧?谁是孙悟空?谁是主人公,谁是伺候主人公的徒弟?紧箍咒是给谁用的?谁掌握着任意杀人的武力?谁掌握着把孙悟空赶走还是留下的权力?另外,谁承担把孙悟空赶走的后果?有许多朋友在这些定位上,恰恰是颠倒的(这个问题,明清的评点家们,认识得比今天的人清楚多了)!所以,还在为孙悟空抱屈么!贫道担心的是,假如这种批判、丑化、定位的颠倒,成为我们大众共识的时候,假如我们还觉得自己是被紧箍咒束缚了的时候,那就是离取经失败不远了!”
如果把老僧考论三打白骨精其实是“斩三尸”的隐喻,紧箍咒其实是“定心真言”,以及郭沫若和毛泽东唱和“三打白骨精”七律诗其间隐藏的历史烟云揭秘等(分别见老僧几篇“经典探秘”文章及评批本《西游记》),与李道长的讲论和感慨联系对照阅读,是不是会激发出读者更深层次的思考,而进一步对《西游记》生出高山仰止之心意呢?
又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道长对“真假猴王”故事的“八”(网络语言,即“扒”——分析),如果参照阅读老僧关于“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到“二心搅乱大乾坤”的一系列解析,关于菩提祖师乃“心”的象征而非须菩提,更与道教偷抢了佛教位置无关,而正体现《西游记》写定者融会贯通儒、佛、道三教义理和智慧,“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审美大情怀大境界,是不是对读者更有启发呢?
此外,如李道长第三十七讲《虎先锋:你看我的脸》,与老僧对唐僧初上取经路途即接二连三遭遇几次“虎难”的分析;李道长第六十五讲《金刚琢到底是什么》,与老僧对取经路途后一半一开始即遭遇老君青牛精作怪,金刚琢的“圈子”隐喻之分析;李道长第七十六讲《四位树精,诗写成这样就别出来混了》,与老僧对“木仙庵谈诗”“小西天”两个故事乃“文字障”和“学术障”之隐喻的分析;特别是李道长第八十六讲《瞌睡虫和豹子精的秘密》,与老僧有关“分瓣梅花计”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等的分析,皆有参照对照阅读而互相映照之妙趣,或对读者能产生启沃提撕(此四字乃老话,即今所谓“启发”)更上层楼之功效。
我们还需要深入体会《西游记》写定者的审美气质和艺术匠心,特别是那种自由和自娱的创作心态,也就是明清评点家经常提到的“趣”字。如果对此缺乏感觉,就会把作家有意为之的调侃幽默妙趣横生用表面的形式逻辑切割“挑错”,而发现一些“不合理”并归之于“成书过程”的痕迹,实际上却是一种“误读”。李道长“讲西游”中,对此似乎注意不够。如说“孙悟空火眼金睛辨识率还没及格”(第四十六讲),比较孙悟空和妖道谁更能招来龙王降雨(第六十讲),褒贬木仙庵的树妖们写的诗是否真有水平(第七十六讲)等,就未免太较真了,神魔小说的游戏笔墨是不能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来规范的。而且,表面上的“不合理”,往往隐藏着“大道理”,如孙悟空火眼金睛的辨识率问题,其实隐喻着“心猿”与“心灵”之“一念之间,仙凡自异”的微妙作意。当然,李道长追根溯源旁征博引的许多“八”,是趣味满满的,大大娱乐了读者,这里也不过是求全责备而已。
《西游记》第八十七回开头有云:“大道幽深,如何消息,说破鬼神惊骇。”给读者一个建议:把李道长的注解本《西游记》与老僧的评批本《西游记》并置案头,把李道长的“西游百讲”与老僧的“经典探秘”一体同观,或可节省些性命精力而曲径通幽有所收获。说到底,李道长的考证,与老僧的悟证和论证,彼此参照,互相生发,于《西游记》“思想”“艺术”“文化”“历史”等奥妙的显示发扬,各有其作用功能,老僧与李道长僧道携手,或可彰显这部伟大文学名著几分清明否?
考证、论证、悟证,也就是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文献、思想、艺术,也就是史、哲、文,也就是真、善、美。一切概念名相,不过是为了心灵的澄明。《西游记》从“心猿意马”到“猿熟马驯”的故事,西天取经十万八千里九九八十一难,说到底,是对因果纠结生死流转的求解,是自由的悖论,青春的悖论,人生的悖论,人性的悖论,历史的悖论,文化的悖论,儒佛道的悖论,存在的悖论,宇宙的悖论,也是史、哲、文和真、善、美的悖论。悖论晃晃身,其实就是互补。
李道长的“讲西游”,有两段特别让老僧感动。一段是第二讲“真的能长生不老吗”,其中说:
宗教家们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多少伟岸的偶像,多少富丽的寺院,这偶像、这寺院,是为了培养人们的坚信——这项人类的专属福利的。他们一直为人类谋求着一种救拔之道。企图在人类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在生时避免烦恼的困扰,在临终摆脱死亡的折磨。我们实在不应该咒骂他们为骗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我们当然有权利不接受这一派或那一派的教义,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报之以深沉的敬意!
另一段是第九十六讲“灵山上都有什么”,其中说:
我们看《西游记》,如果抱着斗争的成见去看,肯定处处看到的都是斗争。但是如果抱着平等、合作的眼光去看,其实反倒更多能看出佛道的融合。因为这种仙佛同源、佛道合一的思想,正是明代人所特别崇尚的。明代民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激烈的佛道斗争,反倒是大家都认为:修仙和修佛其实是一回事。其实这种思想,凡是通达的人物都能意识到。
就凭这两段,老僧就与李道长谬托忘年交的知己了。正是:
西游论妙慕天飞,大悟大玩怀大悲。渺渺茫茫僧道去,傲来国仰月新眉。
作 者:
梁归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红楼梦探佚》《红楼梦诗词韵语新赏》《大家精要·苏轼》,评点本《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红莓与白桦:俄罗斯游学记》等。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