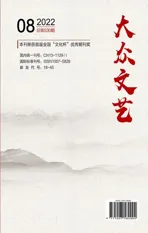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影像语言的隐喻表达
2017-07-12辽宁大学110036
郭 荣 (辽宁大学 110036)
陈文耀 (浙江传媒学院 310000)
侯孝贤电影《悲情城市》影像语言的隐喻表达
郭 荣 (辽宁大学 110036)
陈文耀 (浙江传媒学院 310000)
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在威尼斯影展上获奖,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中重要的里程碑。影片展现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台湾民众的生活缩影,独特的影像语言隐喻式地显示出导演对历史的客观记录与理性反思。史诗形态的素材、绵延的历史创痕、章节式的叙事框架,视听语言“陈述”观念、文字语言隐喻表达、无声语言静默压抑、国别语言杂糅交汇,影片对影像语言的丰富运用,促成了多义性、隐喻化的主题建构和表达。
《悲情城市》;影像语言;隐喻
影片《悲情城市》溯源历史长河,重新摭拾台湾政治神话的症结,独特的影像语言表达方式,使得这部影片成为台湾新浪潮电影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侯孝贤导演“作者电影”轮廓逐渐形成的标志。对于影片《悲情城市》,侯孝贤曾说他拍的不是历史,但观众却看到了禁忌的历史。这是台湾影史空前大突破,也是一种沉寂的史诗大作。影片独特的语言风格促成其特有的叙事格局,既葆有中国的民族性,又不缺时代的创新性,堪称传统与现代交汇的电影作品。影片对历史影像的客观陈述、对文字语言的隐喻表达、借助无声语言的静默力量、以及融合不同国别语言的表达方式,都隐喻着台湾社会在寻求一种“身份认同”。
一、视听语言“陈述”观念
影片《悲情城市》中,历史的沧桑感和使命感透过对白、音乐、文字和静默无力的神情构成多重叙事。透过不同形式的影像语言,客观陈述特定历史时期台湾民众的生活境况及生存观念。历史本身也是一种透过语言(文字)的叙事,多少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和文学类型。影片中“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一个历史大背景,而真正的议题依然纠结于台湾民众的“身份认同”问题。
台湾,这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若干认同危机和矛盾。《悲情城市》以苍凉的影像语言,用多重视角叙述的方式,表现新旧政治势力交替过程中,知识分子对祖国的憧憬和浪漫的幻想逐渐演变成破碎、绝望、压抑的梦魇。陈述成为创作者用来承载和表现喻意的方式。
二、文字语言隐喻表达
善于使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或交待事情的发展进程,是侯孝贤电影的特色之一。书信、念白、歌词、字幕、叠印等文字语言的形式,形成了《悲情城市》这部影片独特的叙事方式。片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脱离日本统治五十一年”及片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大陆易守,国民政府迁台,定临时首都于台北”。这种冷静又略显呆滞的文字,将事件背景、发展和刻意的目的性表现得极为深刻,它像烙印般刻在观众心上。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中,文字插入也是常用手法,目的就是疏离投入的认同情感,增加电影化与文学性的辩证关系。这种文字语言的运用,对于《悲情城市》这部影片来说,则是有意促动被客观影像疏离之后的心理认同。
影片中,文字语言的叙述没有冗杂琐碎,却贯穿始终有意营造若隐若现的影像氛围。“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统治者的交换更替,人们内心深处渴望释放的压抑,文字中隐藏着语言的张力,预示着主人公未来的命运,也是整个台湾民众的悲情写照。
三、无声语言静默压抑
《悲情城市》中的主人公文清是一个口不能言、耳不能听的聋哑人,无声的世界是对台湾民众静默压抑的一种隐喻表达。无声语言使影片基调颇为沉重,历史遗留的落寞和沉重需要观众在静默中去品味和反思。在聋哑人群中,由于他们无法正常使用有声语言,只能够使用无声语言进行全部的交流活动,无声语言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影片中文清这一聋哑角色的设置,正是隐喻当时社会境况下台湾民众的压抑状态。先天不足的文清是一名专业照相师,用照片记录下美好瞬间。导演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静默状态下对历史的审视与内省。片尾文清全家福的自摄照片,在繁花、壁炉、沙发等点缀下,隐藏着一种与虚拟场景相反的现实凄苦。文清死前的血书“父亲无罪”,也是对生死、对社会现状的有力挣扎和呐喊。
《悲情城市》使用无声语言辅助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影像语言的象征性和喻义性。影片对话并不多,多是需要观众主动地寻找讯息发出点,自我建构影像喻意。导演赋予了影片中的人物角色以复杂情感和沉重意味。
四、国别语言杂糅交汇
在影片《悲情城市》中,台语、国语、日语、上海话、广东话五种语言,带有分歧又客观真实地存在着。言语带来的文化差异隐喻着台湾这座岛屿的漂泊无依。影片中林家大哥文雄与上海帮之间的对话,是影片颇具意味的一个场景。两个人的谈话经过四种语言转换,一种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的距离充满着矛盾。语言神圣也神奇,它可以投射出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内涵和风土人情。不同国别的语言杂糅交汇,也是一座小岛积郁的悲情。
影片中除了对台湾本土人生活的描绘,更是不回避对日本人的直接摄入。日本人小川校长及女儿静子,对情谊的坚持和珍视,对台湾这片土地的不舍和依恋,都超越了国别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差异。虽然国籍及政治观念存在诸多不同,但看似矛盾对立的关系在影片中被很妥洽地融合在一起,影像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国别的界限。不同国别的人物角色,不同语言的对白交汇,诉说着那个特定时代,人的迷茫、无措和无归依感。
五、结语
影片《悲情城市》把敏感历史事件直白、客观地予以展现,用静默的影像语言沉寂着一个民族寻找“心理认同”的期冀。诸多个性化的影像语言,客观冷静的悲情叙事,隐喻着历史境遇下心灵家园的缺失和悲哀。视听语言“陈述”观念、文字语言隐喻表达、无声语言静默压抑、国别语言杂糅交汇,这些客观化而又带着主观性的表现技巧,促成了影片多义性、隐喻化的主题建构和表达。
[1]黄仁.新台湾电影——台语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252.
[2][3]焦雄屏.台港电影中的作者与类型[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52-54.
[4]张矣.论无声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J].咸宁学院学报,2009(05):102.
[5]黄仁.新台湾电影——台语电影文化的演变与创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3.
[6]余乐.最好的时光——从《悲情城市》看侯孝贤[J].电影评介,2008(20).
[7]张矣.论无声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J].咸宁学院学报,2009(5).
郭荣(1993-),女,汉族,山东青岛人,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影视美学。
陈文耀(1987-),男,汉族,山东枣庄人,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影视文学、影视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