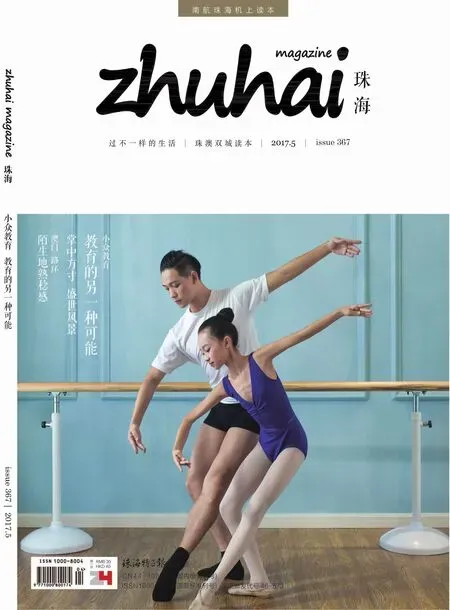历史到底有无意义
2017-07-07吴越春秋
历史到底有无意义

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文化学者。近年来一直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化,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散文、随笔和诗歌作品。本文是他的系列随笔《历史九问》其中一篇。
在人类浩如烟海、茫然无绪的历史中,尤其是人类尚未发明文字、对于以往的历史无法记述的阶段,多少历史事实和真相都已被厚厚的烟尘所掩埋,被重重的迷雾所纷扰,或者只在口口相传的神话和传说中若隐若现。即使是有了文字的记述,记述者或者授意记述者的态度也直接决定着对历史事件的取舍、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因为历史终究是人写的,而人又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生命的动物,即使如史官那样具备应有的客观与公正和职业道德,也难免笔端带有感情色彩,更何况在后来的封建专制时代,统治者的专横暴虐主宰着一切,包括对于历史,尤其是对自己亲历的历史的记述。因此,他们甚至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编历史、歪曲历史、捏造历史,对敌人极尽丑化、妖魔化之能事,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为自己抹粉涂脂,绘彩贴金,美化、神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我们会质疑,这样的历史可信吗?有意思吗?有意义吗?
太史公司马迁是公认的“史圣”,他的《史记》也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但即使是像他这样不畏强暴、蔑视权贵、秉笔直书,甚至敢把当朝开国皇帝刘邦一副流氓无赖的嘴脸和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任人唯亲的行径都刻画、暴露无遗的史家,也有被后人所诟病的硬伤:一是他对三皇五帝等神话传说的处理,把这些都当作实有的历史加以撰述,使得中国史前历史缺乏现代史学和考古学的科学依据,变得荒诞无稽。当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他,毕竟他活在两千多年前,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于那个时代;二是他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中,过多地甚至过度地运用了文学手法,一方面固然使得历史的可读性大大增强了,令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体验,但另一方面也使历史的真实性有所削弱,换句话说,历史似乎是被“演绎”了,被文学化了,被有意识地处理过了。它更像是小说、评书、话本,而不像是历史,譬如在描写鸿门宴时,项羽垓下被围虞姬自刎时,仿佛太史公自己就在现场,所有人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他的视野之中。此外如宫闱之中的暗室密谋,他似乎都亲眼目睹亲耳所闻,内容之确凿,甚至语气之真切,动作之细微,都让人心生疑窦。因此我们一样会质疑,《史记》这样一部史书之鼻祖、之正宗、之绝唱,难道就是真实的吗?
况且,中国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某种东西一旦被捧为经典奉为正宗,那么它就是无可质疑难以撼动的,而且也成为后世的法则。后人只能因循,而不得擅改,只能遵从,而不得违逆,否则就是离经叛道,数典忘祖。孔子删定的“六经”便是如此,其中的《春秋》这部史书,则确立了一种“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也为后世所常用。而孔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不也夹杂着他个人的思想感情吗?这种态度,必然影响着后人对历史的态度,因此才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和效果。孔子自己也深知这点,故而也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感叹。
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就可以说,历史还是有意义的,是有着大意义的。不绝于史书的众多历史人物,尤其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除了少有的几个昏君糊涂蛋,大多还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名声和历史地位(形象)的,即使他篡改历史,其初衷也还是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不能流芳百世,至少也不愿遗臭万年。对于那些乱臣贼子,历史还是有它一定的警戒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