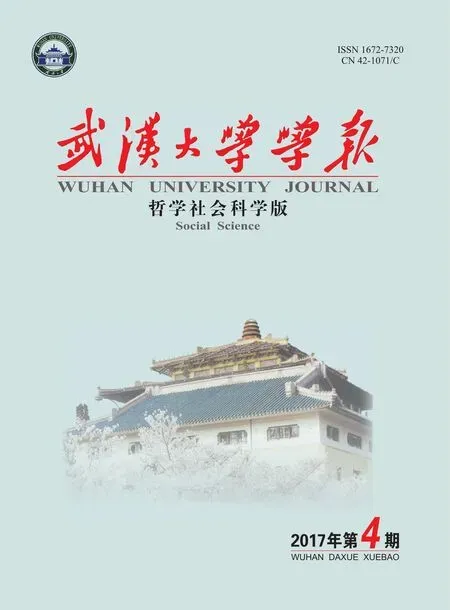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与参与意愿
——转型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2017-07-05麻宝斌于丽春
麻宝斌 于丽春 杜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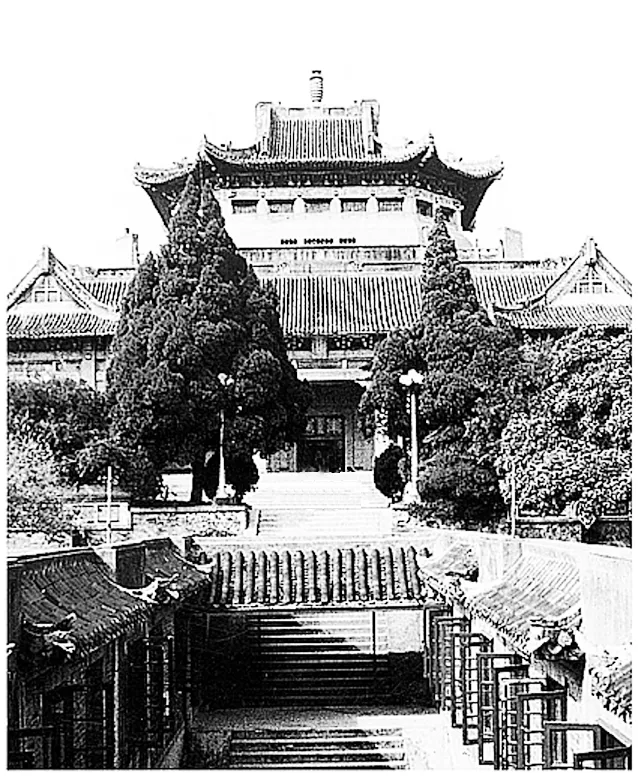
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与参与意愿
——转型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麻宝斌 于丽春 杜 平
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公众对于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也会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立足社会转型的背景,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从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参与意愿等几个维度对公众所在社区和工作单位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政治参与意愿对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并不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所在社区和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所在社区和单位相关事务的管理中,但是现居住地对公众相关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不明显;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所在单位事务的管理中。这些研究发现对于提升公众政治参与的能力与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
政治参与机会认知; 参与意愿; 政治社会化; 收入水平
一、 问题的提出
“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亨廷顿、纳尔逊,1989:1)。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公众的参与机会越来越多,这必然会要求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不断增强。而政治参与意愿是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政治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阿尔蒙德将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归纳为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以及参与者政治文化等三种类型,并且每种类型的政治文化都对应着不同的政治结构(阿尔蒙德,2008:16-20)。其中,参与者政治文化与现代的政治结构相适应。从政治现代化的视角来看,“除非人民的态度和能力同其他形式的发展步调一致,否则国家建设和制度的建立只是徒劳无益的行动”(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3)。相应地,对公众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多,已有研究围绕政治参与(Verba & Nie,1972:9-21)、政治态度(阿尔蒙德,2008:213-216)以及政治效能感(Campbell et al.,1954:3-9)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并且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
建国以来,中国逐步健全和完善了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组成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为广大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民主制度的完善必然要求公众增强政治参与的意愿,换一个视角来看,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也有助于在最大程度上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在多种的政治参与形式(亨廷顿、纳尔逊,1989:13-15)中,公众更倾向于哪种政治参与形式?是否具有积极的参与意愿?又是否认为自己的参与行为影响到了政策的制定?公众的参与行为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研究表明,公众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参与形式偏好(Shi,1997:15-21),而且近年来公众的政治参与形式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分化特点(肖唐镖、易申波,2016:97-111),公众的自治参与、选举参与和政策参与等行为会受到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多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王丽萍、方然,2010:95-108;房宁,2015:1-40);此外,由于信息技术发展而引发的政治机会结构变化也在影响着政治参与行为(臧雷振,2015:164-165)。还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参与状况的研究不能忽视“事实上能够参与的知觉”(阿尔蒙德,2008:170),也就是公众是否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的问题。综合来看,已有公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问题上(范柏乃、徐巍,2014:25-30;胡荣、沈珊,2015:23-33)。在内容上,政治参与不仅包括选举,还包括公共事务的管理等。比较而言,已有研究对后者的关注还不是很充分。将公共事务管理和参与机会认知两个维度的内容结合起来,就会发现,还有如下问题需要理论研究来回答:在现实生活中,公众是否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不同层次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又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我们之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要明显高于政治参与意愿,呈现出明显的“机会不等于意愿”(麻宝斌等,2016:136-140)的特征。在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参与意愿也呈现出明显的传统和现代并存的特征,有研究表明社会的参与意愿确实有了很大提高(周晓虹等,2017:341-352),也有研究认为公众在社区选举参与中的参与意愿较低(熊易寒,2008:180-204),对民主的理解呈现出较强的传统特征(张明澍,2013:279-283)等。但是,并没有将政治参与意愿作为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试图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立足社会转型的背景,着力回答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问题。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是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社会化以及收入水平等维度来分析转型时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问题。
(一) 政治参与意愿与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
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文化前提(Nathan & Shi,1993:95-123),而公众政治参与意愿的不断增强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传统社会,中国公众普遍遵循的是实质正义观念,更关心分配结果的合理性,而不是分配过程的合理性,因而政治参与意愿并不强(杜平,2016:59)。近年来,随着社会总体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价值观念也逐渐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社会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也逐渐向现代转化,越来越重视分配过程的合理性,并且这种变化有可能会影响到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比较而言,政治参与意愿越强的公众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基于以上分析,论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政治参与意愿越强,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就会越强,也就是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
(二) 收入水平与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
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也具有重要影响。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维持基本的生存已经不是最关心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可能转移注意力重心,越来越关注政治参与等问题,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例如,英格尔哈特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关注重心会逐渐从安全向参与等转变(英格尔哈特,2013:71-75)。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经济社会地位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意愿就有可能会越强烈(蒲岛郁夫,1989:13)。相应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政治参与认知上表现为传统公民向现代公民的转变。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个人的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就越强,具体来看,在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方面,收入水平高的群体认为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管理。
(三) 政治社会化与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
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公众的参与意愿会呈现出较强的现代化特征,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政治社会化。具体来看,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主要包括学校、工作组织等。也正是由于这些媒介的作用,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公众的政治参与认知才会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首先,城市化对于政治参与意愿现代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已经为诸多研究所证实。从城市化的影响来看,城市的生活经历有效“提升了农村人口的意识形态现代化和个体的效能感,增强了他们社会参与的内在动机和主体意识”(李培林等,2013:173)。此外,与城市化相伴生的工业化也会对公众的政治参与认知产生影响,因为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工厂可以说是培养现代性的学校,工厂的工作经历是一项可以促成现代化的独立因素(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229)。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深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镇化率有了大幅的提升。同时,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近年来已经超过两亿人。这些都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公众从农村走向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生活经历的洗礼,相应地,公众的政治参与认知可能会呈现出更明显的现代特征。这就可能会导致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具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同时,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常住人口中出现了“户居分离”的现象,因此,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高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进一步来看,这又导致了城市常住人口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差异,比较而言,当地人口比外来人口更加能够参与到相关事务的管理中,其政治参与机会认知应该会更高一些。基于此,我们就城市化对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相比于农村居民和农村户籍人口,城镇居民和城镇户籍人口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具体来看,在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方面,城镇居民和城镇户籍人口认为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管理。此外,城镇居民内部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当地人口比外来人口具有更强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
工作组织也会对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经济成分日益多元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与之相适应,“体制外”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有了快速的增长,逐渐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相应地,职业类型就成为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从事不同类型的职业会有不同的工作经历,这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政治参与认知。有研究从理性选择理论、学习社会化理论、社会交往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等视角来解释体制内群体为什么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卢春龙,2011:88-94)。此外,相关研究表明,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群体在社会参与的意识上要明显强于其他社会群体。根据这种思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可能要比农民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更强一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相比于农民,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要更强一些。具体来看,在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方面,与农民相比,国有和民营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有更多机会参与不同层次公共事务的管理。
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通过接受更多的教育,使得在社会中寻找更适合自己的位置,综合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也使他们具备更多的技能和资质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闵学勤,2004:173)。此外,英克尔斯和史密斯对个人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同样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就会越多(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209)。建国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快速的发展,社会整体的受教育程度都明显提高。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越有可能关注政治参与问题,也就越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意愿。反映在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上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管理中。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越强,也就是说,在政治参与机会认知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管理。
综上所述,从参与意愿、政治社会化以及收入水平等几个维度来分析中国转型时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状况的影响因素就成了本文的研究内容。
三、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6-8月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现状测评与改善对策研究”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调查”。此次调查的抽样是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采用分层分阶段法实施的。首先将全国分为直辖市、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地区。其次,以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初级抽样单位(不包括新疆、西藏、青海);以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市所辖区)、县(包括县级市)为二级抽样单位;以街道、乡镇为三级抽样单位;以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为四级抽样单位;在居委会或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并通过生日法在家庭住户中选择一个生日(公历)与7月20日(公历)最接近的18周岁以上成年常住人口为最终抽样单位。最后共抽取北京、上海、山东、广东、河南、湖南、内蒙古、陕西等8个省级单位,19个区县级单位,32个街道或乡镇级单位,96个居委会或村级单位。共发放问卷26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25份,回收率为93.3%。
(二) 研究设计
1.因变量
本文以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状况为因变量。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状况变量通过“我能够参与社区的管理”“我能够参与所在单位的管理”等问题进行测量。在调查过程中,由受访对象根据自身实际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其作二分变量处理,将“非常同意、同意”的选择编码为1,表示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相关事务的管理过程中;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和说不清楚”的选择编码为0,表示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没有机会参与到相关事务的管理过程中。
2.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其中,主观层面的变量是公众政治参与意愿,该变量通过“只要决策是合理的,我参不参与决策过程不重要”这一问题来测量。在调查过程中,由受访者根据自身实际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说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其作为定序变量进行了处理,将选择非常不同意的编码为1,将选择不同意的编码为2,将选择不清楚的编码为3,将选择同意的编码为4,将选择非常同意的编码为5,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的政治参与意愿越不强,也就是更加不愿意参与到不同层次公共事务的管理中。
与政治社会化相关的变量有受教育程度、职业、户籍类型、现居住地等。按照受教育程度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含中专和技校)、大学、研究生,分别编码为1、2、3、4,数字越大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按照工作部门性质差异,将全部样本分为农民、民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分别编码为0、1、2。按照户籍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分别编码为1、0。按照现居住地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编码为1、0。此外,按照个人年收入差别,将全部样本分为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中高收入者、高收入者,分别编码为1、2、3、4、5,数字越大表示收入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男、女)、政治面貌(是否中共党员)、年龄(1949年之前出生、20世纪50年代出生、60年代出生、70年代出生、80年代出生、90年代出生)、宗教信仰(是否信仰宗教)、所在区域等。其中,年龄变量作为定序变量,1949年之前出生编码为1,20世纪50年代出生编码为2,20世纪60年代出生编码为3,20世纪70年代出生编码为4,20世纪80年代出生编码为5,20世纪90年代出生编码为6,数字越大表示调查对象的年龄越小。其余的控制变量都作为分类变量处理。在性别变量中,男性编码为1,女性编码为0;在政治面貌变量中,中共党员编码为1,不是中共党员的编码为0;在宗教信仰变量中,信仰宗教的编码为1,不信仰宗教的编码为0;按照所在区域不同,将全部样本分为西部地区(陕西、内蒙古)、中部地区(湖南、河南)、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广东、山东),分别编码为0、1、2。
按照上述设计,我们对相关变量的具体构成情况进行了统计(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四、 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两个因变量都是二分变量,而自变量既有分类变量,也有定序变量,所以我们根据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方法对转型时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一) 公众社区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
基层自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那么,这些变化是否影响了公众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变化呢?本文从受教育程度等几个方面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见表2)。
在表2中,模型1只放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政治面貌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比较而言,中共党员对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的程度较高,也就是说,中共党员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参与基层自治事务管理。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党组织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所在区域变量也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与西部地区公众相比,中部地区公众认为自己参与到所在社区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机会要低一些。但其余的控制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放入了政治社会化、收入水平等客观层面的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政治面貌变量依然能够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在相关的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之间显著正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基层自治事务中,这与研究假设是一致的。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市户籍人口认为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基层自治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但是,居住地区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并不一致,而且两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而没有更多途径参与所居住社区相关事务的管理,因而才认为自己缺乏参与基层自治事务管理的机会。本文其他的研究假设并未得到有效验证,说明个人年收入水平、工作部门性质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在模型3中,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放入了政治参与意愿变量,结果表明,政治参与意愿对因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模型4中,我们放入了全部自变量,结果表明,只有受教育程度和户籍变量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等政治社会化的相关因素能够对公众基层自治事务管理参与机会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已有研究发现了政治社会化的经历能够对公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形成较好的补充。

表2 公众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参照群体。
(二) 公众工作单位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
接下来,本文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社会化和收入水平等三个维度分析影响公众工作单位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的相关因素(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模型5只是放入了相关的控制变量,在这些变量中,年龄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年龄越小,人们对工作单位参与机会认知的程度越低,更不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工作单位相关事务的管理过程;比较而言,中共党员对工作单位参与机会认知的程度更高;与西部地区居民相比,中部地区公众认为自己参与机会较少。模型6又放入了政治社会化相关的自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年龄、政治面貌变量依然能够影响因变量。在政治社会化的相关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所在工作单位的管理;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市户籍人口认为自己在工作单位中相关事务的参与机会较多,但是城镇居民的参与机会认知并不明显,后者与研究假设不一致,这与城镇居民对基层自治参与机会的认知类似,在实质上所反映的也都属于同一个问题。此外,工作部门性质也能够显著影响到因变量,和农民相比,民营部门工作人员对工作单位参与机会认知的程度更高,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工作单位的管理,但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的机会认知并不显著,后者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其中的原因还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在模型7中,我们在模型5的基础上放入了参与意愿变量,结果表明参与意愿对机会认知的影响并不明显。在模型8中,我们放入了全部自变量,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城市化、工作部门性质等变量都能够对因变量产生明显影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与公众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影响因素不同,个人收入水平能够对工作组织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产生明显影响。这一结论反映出,在现实中,收入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可能会更多参与工作单位的事务。

表3 公众工作单位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参照群体。
五、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相关制度的逐渐完善必然会要求公众政治参与意愿的增强,因此,公众的政治参与认知状况及其影响因素问题逐渐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就中国公众政治参与认知问题来看,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了政治参与形式偏好、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等相关问题上,比较而言,对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很多。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双重”转型时期,在此过程中,相关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在持续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通过系统的研究来有效回答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状况及影响因素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这种认识,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一项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围绕公众参与基层社区事务管理和工作单位事务管理等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与参与意愿等几个维度入手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因素问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和工作单位事务管理参与机会认知的具体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具体来看,在对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上,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类型等都能对因变量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市户籍人口会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参与到基层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但是城镇居民的基层自治参与机会认知并不明显,后者与研究假设是相反的。在对工作单位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上,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户籍类型以及工作部门性质等变量都能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过程中;收入水平越高,就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与农村户籍人口相比,城镇户籍人口更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但城市居民的相关机会认知并不明显;与农民相比,民营部门工作人员认为自己更有机会参与到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但国有部门工作人员的相关机会认知并不明显。综合来看,本文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政治社会化对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得到了较好的验证,但是参与意愿对参与机会认知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有效验证。从上述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等政治社会化因素的确能够影响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考虑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化对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行为等的影响上,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看作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一个较好的补充。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带来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收入水平越高越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中?为什么民营部门的工作人员更认为自己有机会参与到工作单位事务的管理中?我们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这些问题。
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的提高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根据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如下促进公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转型的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关注政治参与等问题。相应地,当社会总体的收入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之后,公众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也会有明显的增强。由此来看,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促进政治现代化进程需要提高社会总体的收入水平。第二,积极发展教育事业,不断提升社会总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水平。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不仅可以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意愿,也可以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增强社会总体的受教育程度显然可以有效增强公众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第三,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但是当前“城乡分立”的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机会认知,因此,有必要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逐渐把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一些权利从中“剥离”出来,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机会。第四,进一步落实相关的民主制度,保障公众在参与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管理中获得充分的效能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增强其政治参与意愿,提高政治参与机会的认知,进而促进现代公民的成长,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奠定坚实基础。
[1] 阿尔蒙德(2008).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
[2] 杜 平(2016).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民众正义观念变迁.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3] 范柏乃、徐 巍(2014).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浙江社会科学,11.
[4] 房 宁(2015).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亨廷顿、纳尔逊(1989).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6] 胡 荣、沈 珊(2015).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和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东南学术,3.
[7] 李培林等(2013).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卢春龙(2011).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9] 麻宝斌等(2016).机会不等于意愿:中国转型时期民众政治参与认知状况分析.理论探讨,2.
[10] 闵学勤(2004).城市人的理性化与现代化——一项关于城市人行为与观念变迁的实证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1] 蒲岛郁夫(1989).政治参与.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2] 王丽萍、方 然(2010).参与还是不参与: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心理分析.政治学研究,2.
[13] 肖唐镖、易申波(2016).当前我国大陆公民政治参与的变迁与类型学特点——基于2002与2011年两波全国抽样调查的分析.政治学研究,5.
[14] 熊易寒(2008).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社会,3.
[15] 英格尔哈特(2013).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 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顾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7] 臧雷振(2015).变迁中的政治机会结构与政治参与:新媒体时代的中国图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 张明澍(2013).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 周晓虹等(2017).中国体验: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国人社会心态的嬗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Angus Campbell et al.(1954).TheVoterDecides.New York:Row,Peterson and Company.
[21] Andrew J.Nathan & Tianjian Shi(1993).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Findings from a Survey.Daedalus,122(2).
[22] Sidney Verba & Norman H.Nie(1972).ParticipationinAmerica:PoliticalDemocracyandSocialEqual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
[23] Tianjian Shi(1997).PoliticalParticipationinBeijing.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叶娟丽
Income Level,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alysis 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Opportunity Cogni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Transition
MaBaobin&YuLichun(Jilin University)DuPing
(Shanghai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y cognition from three dimensions:income level,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10.14086/j.cnki.wujss.2017.04.014
D0;D66
A
1672-7320(2017)04-0139-09
2017-01-2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2&ZD060)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s,the public’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are also increasing.Accordingly,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the political efficacy are more and more abundant.On the whole,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peopl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as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efficacy,the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In addition,in terms of content,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cludes not only the vote,but also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ly concerned with the latter.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y cognition will undoubtedly help promote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gnitive problems.
In theory,the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y cognition will be influenced by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come level,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willingness on the opportunity cognition of public political particip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illingness 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y cognition is not obviou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s,the more they think they hav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the community and work organization affairs; compared with the rural population,the urban population have mor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levant units and community affairs; the higher the individual income level is,the more they think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unit affairs.The research of this paper exte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ognition,and the conclusions obtained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enhance people’s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y cognition. Key words:the opportunity cogni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come level
■作者地址:麻宝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于丽春,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杜 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