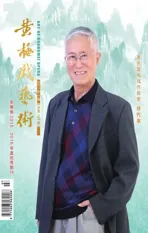谈谈戏德
—— 王少舫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连 载)
2017-07-04王少舫
○王少舫

1952年严凤英、王少舫等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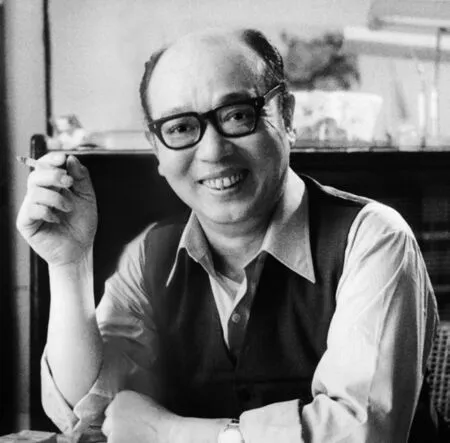
王少舫剧照
听取意见和建议
王少舫:还有听取意见和建议。我们作为演员,你要在艺术上求进步,我们说的你要听啊,演员要听各方面意见。好的要听,不好的、坏的也要听,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听进坏的、反面的意见。一个演员在艺术道路上你不广开门路,你光听人家的好话,那是没出息的!对你的艺术没有促进。比如说我的一个唱腔,一个表演,你提了我的意见,首先我要感激你。你提的这些,我来考虑考虑,好的我马上就照你这个改。如果模棱两可的,到底他好还是我好?如果他好我还按照他那个改,或者在他那个基础上,我能不能再换一个别的样子来丰富它;那个更坏的意见,那我就要很好地研究,我是不是这个样子?我经常跟他们讲,我九岁上台演戏,演戏演到三十几岁了,还在不断改进。
我举个例子:人家给我提的意见呢,那可是很尖锐的哟!那时候上海《新民晚报》有一个叫赵革金的报人,他跟我关系也蛮好的,我们俩也谈得来,我们之间谈问题都是“巷道里抬木头直来直去”。他与我说话是真实的,他常跟我说,少舫你不要来假的,我说我不会假的,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记得是在五几年的时候。赵革金他就跟我提出:“哎!少舫啊,我发现你啊,在艺术上是很有研究的,我也很崇拜你!你唱戏唱到今天,我也看你演了很多戏,但我给你提个意见,我在台下看你哭笑不分呐!……你这个哭、笑,脸上肯定有毛病,你自己找找……”
我说,“是吗?”这可是个尖锐的意见啊,我头脑里咯噔一下,就有了震动,如果说不震动一下子,那也是不合实际的。我想,我唱了三十多年戏了,在台上我哭是哭,笑是笑,怎么他讲我哭笑不分呢?我心里总有点别扭,我们俩关系再好,但听了这话,心里总是有点疙疙瘩瘩的。
回到家里,我心里纳闷,我来研究研究,我来仔细琢磨琢磨。我对着镜子我自己找啊,我哭笑不分?我哭,我笑,我对着镜子照,照也照不出来呀!后来我就想什么办法呢?到照相馆照相去!我哭也照,笑也照,(我当珍贵的资料留着,现在照片都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全都给抄掉了!)拿着照片自己一比较啊,再对镜子一看啊:哎呀!确实的,他这话讲的对呀!我发现在我脸上这个笑纹啊,你笑这样的,(示范)你哭呢,(示范)跟笑一样,为什么呢?主要是露了牙,我脸上这个纹路呢,不适于露牙哭。那么如果笑是这样笑,(示范露牙)我要这样子哭呢(示范露牙),区别不大。所以表演哭时一定不能露牙,这样才能在舞台上区别表演,那就给人看到笑是笑,哭是哭了。找到毛病了,我就跟赵革金讲了,我感激他,他也非常高兴!
“变声期”
记者:剧团里青年男演员有变声期这个问题存在吗?
王少舫:你这个变声的问题提的很好,这次艺校毕业来我们剧团的五个女孩,五个男孩,五个男孩都在变声期。男孩呢有时候有点灰心丧气,好像我们都是同学,女生来了马上就能派上用场了,我们来了还在跑龙套,心里有点不平衡!我们就抓住这个问题,因为我是老演员,我懂得这些,跟他们讲这是变声期,是生理现象,不要慌,也不可急躁,你们再过几年就好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们主要的是要合理妥善安排自己的艺术进程。嗓子呢,会变的,要锻炼,你不能等着嗓子恢复,你还是要锻炼呢,不要拼命地去喊、去唱,你这个声带你要使用它,高音不足的,你就慢慢地往上唱,慢慢地练,低音不足的,你就慢慢地往下唱,慢慢地来练。嗓子闷的你找各种共鸣、找气息,反正我们就是要科学练嗓子。慢慢地跟他们沟通。再一个呢,鼓励他们正式在舞台上实践。你跑龙套也好,你演个零碎也好,你要多到舞台去摔打磨练,你多在舞台上实践,把舞台上的一切熟悉了,一旦你演到正戏的时候你在舞台上就不会胆怯!这是其一,再一个呢,现在剧团里呢,像我们这些老的还在演戏,你们多看,多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自己应有个衡量标准,多为自己的艺术积累知识。
记者:女演员有没有变声期啊?
王少舫:我过去听上海音乐学院洪大奇教授讲过,女演员也变声。女演员变声掉三个音阶。她掉三个音阶,问题不大,很快她就可以恢复了。男演员呢,他掉十一个音阶下来,所以这个男女生理上不同啊,变化也不同。
可是男孩子们灰心丧气啊,我就开导他们,介绍过去京剧一些老演员,你比如京戏汪桂芬,汪大头嘛,就是跟谭鑫培他们差不多的,他嗓子变声期时他学拉胡琴,后来嗓子好他回过来照唱戏。杨宝忠也是唱戏的,后来他也改拉胡琴,但是他后来能唱了,他也不大唱了,他情愿拉胡琴了。像京戏有好多男演员,他的变声期,有的一两年,有的甚至三四年才恢复。这是生理变化,我跟他们说:从医学上来讲,男演员,肌体健全发育成熟的时候要到三十岁,生理卫生你们都应懂得的,现在书上都有啊!所以经常安慰他们,叫他们做好准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现在正是积累的时候,你要是在旧社会,你们没这个条件,你嗓子哑了,嗓子变声你照样要唱,你照样要干,干到最后是个什么效果呢?你唱坏了嗓子,艺术上没有造就了,一天到晚就只能唱零碎来糊口。你现在不是不能演戏,你能演戏,只是迟早的问题。另外,我们男演员艺术生命比较长,你不要看眼前的这几年,是不是啊?我六十三岁了,我今年还能在舞台上蹦跳、折腾,对不对?我再过十年,我不能唱小生,那我唱老生行不行?
现在这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我们演员来讲,应该是专心专意地来搞艺术,现在的客观条件是这么的好,你看我们过去,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我跟他们讲,我的嗓子在旧社会曾唱坏了的。我是唱工老生的,后来唱工老生嗓子唱坏了,我又改麒派,改麒派后,自己又练练嗓子,又把嗓子练回来了!我的嗓子恢复后,就这么一直保持下来了。主要还是在解放以后,参加革命以后,这个演出的时间呢,顶多一天一场了,(过去旧社会一天要演两场,有时还要多)那么一年当中也不一定给我去演三百六十场吧?给我演二百场戏就了不起了!我说你们现在嗓子倒仓了,长年的给你们保养,你们还是要常常用不同的方法练练啊,低声、中声、气息、润腔等等,什么事情,都要去练,都要花心思,花精力去琢磨的。
学流派学什么
记者:教孩子们学唱时,是不是非要跟你这么唱?还是教一些技巧?
王少舫:也不能一味地强求!这要根据他的本身的条件、嗓子条件。
记者:有些人教,就是你要像我。非要学我这个声音,这是不是讲派?
王少舫:这是派。就是现在,北京、上海,京剧,评剧、越剧不是都有派吗?这个讲的很对,你学派啊,你不是完全学他那个声音,你学他那个演唱技巧和味道。不是要你嗓音跟我一样,你那个嗓音就是你的嗓子,你要是完全学我的嗓子是不可以的!你的条件就在那里,但是你学他那个派别,学他的唱腔的韵味儿,学他表演手段的特点。但是你学也是要有目的地活学,不是原封不动照搬,你还要发展。
他们现在就讲黄梅戏男演员,王老,您是“王派”!我说我没有派,我从来也没敢讲过什么“王派”。我说我的派就是黄梅戏老艺人派,我是集各地方兄弟剧种派,我就是集他们大成,取他们之长,为黄梅戏男腔发展,不让它显得那么太单调,在这儿你取一点,在那儿你收一点,从各个地方兄弟剧种,包括歌曲我都学一点,使我们的唱腔既好听,又好唱,有韵味!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所追求的目标!所以在闲聊的时候啊,或者是他们喊嗓子的时候,我听到了就去跟他们讲讲啊,指导指导啊,希望他们进步,能得到提升,提高我们黄梅戏的品味和唱腔魅力。
记者:王老,听剧团领导和演员讲,您演出去剧场时,总是最早的一个,那是为什么?
王少舫:我每天晚上演出,下午三点多钟我就要去剧场化妆,因为我年纪大了,面部、体型都起变化了,要很好地在舞台上塑造角色,就需要在化妆、服装等许多地方来加工、美化,要提前做好演出的准备工作。
记者:你们黄梅戏要面向农村,要有一定的适应性。现在你也还常下农村吗?
王少舫:“文革”前我们都经过锻炼的,都蛮好的,到农村演出我都一担挑,都是自己挑,一天走几十里路,当天到当天演出。演出完了睡一觉第二天又挑着行李,到下一个点去演,锻炼得很好。现在也常去县城和农村演出,不用自己挑行李了!
记者:你们这个剧团现在还不能自负盈亏吧?
王少舫:还不能自负盈亏。
记者:要搞得好的时候可以吗?
王少舫:要搞得好可以。从去年开始,安排好了还是可以的。我们还是个事业单位,不是一个企业。我们团里呢,要安排好是能够盈利的。
赴港演出的意义
记者:能谈谈您们这次赴港演出的情况吗?
王少舫:这一次赴港呢,还是为了黄梅戏,为了宣传和发展黄梅戏这个剧种。
我想,十年动乱以后,黄梅戏呢,不像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样红火了。通过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一系列的国家方针政策深入人心,黄梅戏现在也在发展,精神面貌就跟以前也不同了。特别是这次,中央对外文委,能够考虑到黄梅戏到香港去演出,这也是扩大这个剧种的影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黄梅戏在全国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十年动乱以后,这次能够到香港去演出,我想,一定要让黄梅戏后继有人,起码要赶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因为人民有这样一个印象在那里。我是这么想的。
作为我本人呢,觉得这次赴港也不是一般的演出,而是一个政治任务。出发之前,我们也听到有些剧团呢,到香港啊,出去了呢,什么大一包小一包的,我总感觉到这个风气不好。或者是某某人,到了香港呢又是干爹、干娘哪,又是什么什么的,总会影响他这个剧种的声誉,对不对?我就考虑到,如果说我们自己要这样子做,那不是我王少舫的问题了,那主要就会是黄梅戏的问题,对不对?过去我们曾经有些人出去就不想回来了,对不对?我说旧社会我也待过,对不对?那种社会嘛无非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那有什么意思呢?我在旧社会奔了一辈子,我也没奔出什么名堂来嘛!你艺术再好,要是没人重视你,又能干什么?何况我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不管是哪方面,我刚才不是跟你讲嘛,过去艺术我是靠偷学来的,那都不“瓷实”!解放以后有了党的培养,我们得以到这里学习、那里学习,一九五七年上海的进修班让我去参加,让我去开开眼,长长见识!这些艺术能力,都是在解放后才得来的,是党一手培养的。有了黄梅戏的发展,才有今天的王少舫。
这次我们没有出境以前也讲到一些问题。到香港去啊,会亲啊,会朋友啊。在登记时,我想到这点,我说我不登记,我说香港我没有任何人,我不需要登记,我不需要去找哪一个。再一个呢,到香港我有一条,请领导给我把关,有外界来找我的、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找我的、要会我的,你都给我回掉,谢绝会面。有人送东西给我,我不接收。情不可却的情况下,他如果送了我什么什么东西,我就交公!我说我不找麻烦,我去主要是演戏,我说没有时间去接待。
后来呢到了香港,我的一个师兄找到了“新光戏院”,领导通知了我,是领导要我去会见的。在后台遇到师兄,他比我大,七十多岁了。拉拉家常和往事后,他问我想在香港带点什么东西,录音机啊、照相机、彩电啊什么的?我说什么都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也不开口。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地方戏主演来香港演出,是展现地方剧种的风采的。来这儿搞些东西往回带,我认为是伤国格的事情。我们要顾及自己的声誉和形象。
另外呢,我在那里碰到了京剧名角郭锦华,就是在《杨门女将》中演杨七娘的那个演员,我是在头一天那个宴会上碰到她,是银行界的票友请她去的,她是申请出境的。我在北京的时候呢,碰到我妹婿的二嫂子,郭锦华是我妹婿二嫂子侄女,她写信去讲我们在北京演出,她已经晓得了,她那个姑妈已经写信告诉她了,说我要去香港,刚好在第一天宴会上我就遇见她了。她说我晓得你要来了,我说我听讲写信也告诉她了,她当时还讲不清楚关系,她说你还是长辈呢,我说是的,我是你长辈哩!我们宴会以后出来讲话,碰到她爱人去接她,她介绍这是王少舫同志,他是我的亲戚,应该喊大舅。他问你住哪里,我住哪里没告诉他,我只告诉他我在“新光戏院”演出。我也没邀她到我这来玩,她讲那我有空到“新光戏院”去看你,反正是要看戏的,我说看戏你来吧。大概她也晓得国内文艺界的一些情况,也晓得在那里看戏不方便,后来我也一直没见她。如果说我要想搞点什么东西啊,我可以通过他们跟票房来讲讲,票房都是银行界的,我讲讲我要想带点什么东西回国内,跟她讲没关系的。来香港一趟,你周旋周旋给我搞点东西也还不可以吗?也不要我自己出面的!我总觉得像这些东西呢不能搞,你搞了以后等我离开香港,人家就会议论这件事,造成的社会影响不好。这倒不是我王少舫的问题,就个人来说大不了就是伤人格的事,更重要的是影响黄梅戏的声誉,你对剧种的损害就大了!到香港来展演,是进一步扩大黄梅戏的影响,是促进黄梅戏向前发展,是想把黄梅戏发展得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样轰轰烈烈的嘛!关于买进口电器的事我还有我的想法哩,其一,我家里也有彩电,其二,我若买我还不买外地的,我买安徽生产的,坏了修理方便!
我们是想通过黄梅戏在香港的展演,把我们的新秀和青年演员像马兰、吴亚玲、陈小芳、黄新德等都宣传出去,把黄梅戏发展好!让黄梅戏能够恢复到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轰轰烈烈的状况。作为我这样一个老演员,从事这个工作是极大的安慰,极大的享受。
记者:王先生,您今年(1982年)有六十岁吗?在香港除了亲戚外,还有哪些人?
王少舫:我今年六十三了。在香港有外孙女,还有师兄。我师父还有些学生在台湾,我说在台湾好啊,以后祖国统一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黄梅戏在台湾很流行,我还期待着到台湾去演出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