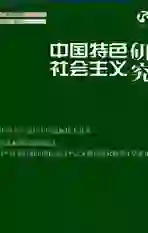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理论分析
2017-06-30袁富华张平
袁富华 张平
[摘要]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使得中国成功跨越低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大转型。但是,随着原有规模效率模式赖以发挥作用的因素的消失,中国开始步入以城市化为背景的二次经济转型。面对这种趋势,保持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效率模式的重塑,以内生性替代外生性、以内部化替代外向性、以外溢性替代外部性是二次转型的主要环节。为成功实现二次转型,在物质资本积累和广义人力资本积累之间进行再平衡,致力于消费结构升级和服务业效率提升,成为城市化新时期的重要路径保障。
[关键词]二次转型;城市化;消费结构;效率模式
[作者简介]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中国社会科學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研究”(批准文号:12&ZD08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转型风险与国家生产系统效率提升路径研究”(批准文号:14AJL006)资助。
引言
在向发达经济收敛的增长过程中,后发国家一般要跨越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这两个关键环节。对传统二元经济而言,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跨越低收入陷阱,可以看作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转型;之后,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内生动力的培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可视为二次转型。国际增长经验对比表明,虽然工业化在大多数后发国家发生并在很多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但是二次转型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因为二次转型涉及原有经济模式的重塑,增长方式与以前有质的不同。
改革开放以来,依托于劳动力资源禀赋和国内外有利的市场条件,中国实现了快速资本积累,以规模效率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其主要特征。但是,这种建立在外生性、外向性和外部性基础上的结构性加速,在面对人口结构转型、资源环境刚性和外部市场饱和的压力下,近年来日益演化为结构性减速趋势,中国经济新常态理论的提出,即是对这种系统性变化的回应。
作为新常态经济的内在趋势和调整阶段,二次转型要求在增长模式上实现新的突破,即内生性替代外生性、内部化替代外向性、外溢性取代外部性。在这种要求下,创新不再是简单意义的新技术、新产品创新,而是体现在增长联系当中的效率模式的重新塑造:包括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因此,从长期来看,增长方式也从由工业主导转换到由服务业和消费主导,城市化时期消费社会的到来——以广义人力资本提高为核心的社会开发替代资本驱动的不可持续路径,是实现二次转型成功的重要保障。
一、资本驱动工业化模式的终结及其冲击
从长期增长的阶段性变化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可以看作经济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转型。正如传统发展理论所言,依赖物质资本积累这个关键性条件的突破,中国经济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和持续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中国工业化过程具有外生性、外向性和外部性三个基本特点,经济增长整体上也表现出经由规模扩张促进效率提高的趋势。特定时期的增长绩效总是建立在经济系统的特定结构之上,当相应高增长因素消失,结构性减速也必然发生,面对这种趋势变化,如果没有更加有效的替代因素重塑新的效率模式,减速冲击将制约增长可持续性。
(一)支持资本驱动增长模式的三个基本经济条件正在消失
1.外生性问题:剩余劳动力资本化过程接近尾声
外部技术资源和国内廉价劳动力的生产组合,推动了中国资本积累进程。数量众多、素质低下的庞大剩余劳动力,构成了资本化的有利条件,这种人口结构特征既是资本驱动模式的基础,也是数量型、高速度经济规模扩张的根本动因。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流动限制的逐步解除,使得人口红利得以释放,至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下降、人口红利窗口关闭,中国人口结构转型过程正好与工业化高增长阶段重叠。但是,近年来出现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意味着剩余劳动力资本化的规模效率模式的终结。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拐点的发生将拉低资本积累速度,进而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随着低技能的劳动力被新一代高技能劳动力的逐步替代,更高的工资期望也不可能让粗放型生产资本得以再生产。
2.外向性问题:规模扩张的市场化过程面临约束
外生性技术加上人口红利机会,只是构成了资本积累循环中的生产性环节,循环的另一半即资本利润的实现还需要庞大市场的支撑。实际上,生产的外向性或国际市场的外部依赖性,贯穿了中国三十多年的高增长过程。外部动力的获得来源于低成本竞争优势,并且被两次有远见的经济政策进一步放大: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人民币汇率贬值,以此确立了轻工品生产的国际市场地位;第二次是加入WTO,使得中国极大地拓展了能源、原材料和重化工业品的大进大出空间,进而把资本积累阶段从初级品生产出口推向复杂品生产出口,为工业化向深加工度化和创新阶段过渡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低端市场的参与,这种外向性的规模效率也趋于消失。
3.外部性问题:资源环境资本化过程面临约束
中国快速资本积累过程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的资本化过程,持续高增长最终造成了对环境的负向冲击。据估计,1978—2008年GDP平均9.5%的潜在增长速度中,有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①可以比较的案例是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鉴于当时快速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的集中爆发,政府不得不加强立法管制,以此促使经济理念从强调高增长向多重目标转变(Nakamura,1981),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增长之后消费者优先的政策思路开始出现,社会开发被提上规划日程。②
(二)结构性减速趋势下的“新二元经济”问题
1.从结构性加速到结构性减速
上述三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可以具体化为增长核算的四要素动态,即物质资本积累速度变化、劳动力供给速度变化、“干中学”(规模经济)效应变化,以及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资本贡献和劳动贡献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是外生性、外部性和外向性增长条件失灵的原因。根据工业化追赶国家的普遍经验,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随着“消费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兴起,工业化主导的经济结构性加速,也将转向服务业和消费主导的结构性减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如果新的效率模式建构滞后,原有的城乡“旧二元经济”有可能演化为城市化“新二元经济”。endprint
2.劳动力的部门平移
上述趋势意味着,随着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原有高积累高增长的动力将消失,但是接下来将发生的问题很可能是:随着由投资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的终结,新的效率模式短时期难以建立起来。根据笔者的估算,2003年以来,农业每年的就业增量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负值,就业吸收能力较强的服务业已经接替农业成为新的劳动力贮水池。之所以说劳动力的这种部门再配置是“平移”,原因是正在发生的庞大劳动力的流动,依然没有摆脱低人力资本的困扰。③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城市即使替代农村吸收过剩劳动力,但是这种低技能和低就业能力的劳动力资源再配置,很可能再次变为城市部门的过剩劳动力。
3.效率非平衡
快速工业化结束之后的“新二元经济”问题,更加突出表现在工业与服务业的效率非平衡上。关于这一点,拉美学派的庞杂理论中存在不少线索,如有人认为拉美第三产业的“早熟”,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大量存在的原因,言下之意似乎是:比起可贸易部门,早熟的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较低。④不仅是拉美国家,当前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均有类似问题。⑤以中国为例,根据UNdata 2005年美元不变价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为1.1,两部门效率基本持平;但是90年代以来,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却呈现出快速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效率差异逐步拉大。
二、二次经济转型的经验事实及其障碍
对于上述可观察的趋势和事实,进一步的追问是:新二元经济发生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把部门效率不平衡或异质性归因于高增长惯性,那么是什么结构性因素使得这种惯性得以持续,以及这种持续的后果是什么?
(一)二次转型作为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结束后的一种典型事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规模工业化历经了剩余劳动力资本化、资源环境资本化,至20世纪70年代重化工业化让位于较少依赖能源原材料、较多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机械工业和服务业”,到80年代基本完成经济的二次转型。⑥总的来说,日本二次转型成功有以下经验:工业部门与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异质性低、趋于均衡;二次转型期间人力资本积累较快、作用突出;消费结构和服务业结构升级显著。相比较起来,拉美国家的二次转型过程挫折较多,鉴于其饱受诟病的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缓慢⑦,城市化过程出现了类似于上文所说的“平移效应”,低素质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但不能为经济转型贡献效率,而且演变为新二元经济下城市过剩劳动力,最终导致拉美“走走停停”的工业化后经济徘徊现象。
1.二次转型发生的关键机制:内部化过程重要性的诠释
发生在不同情境之下的典型化事实的对比表明,大规模工业化结束至二次转型发生,必有一种成长迅速的经济机制——既作为继往开来的衔接,又作为内生性动力的根基。为直观起见,不妨称之为“内部化”机制。这种机制充当了转化工业化时期外生性、外部性、外向性的管道,内生性动力通过它而建立起来,显然,消费模式升级——消费结构中与(科教文卫等)广义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消费比重的上升——是最直接的内部化机制。理由是:一方面,消费模式升级要求资本积累方式随经济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即从工业化阶段的物质资本驱动,转向城市化时期人力资本驱动,以实现增长速度与内生动力的再平衡,以低速度换取高效率和可持续;另一方面,消费模式升级将促进服务业结构突破传统模式,减少以吸收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成本型传统服务业比重,注重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效率型服务业发展。
2.二次转型的关键性临界条件的表征
像其他工业化追赶国家一样,中国突破传统农业社会和“旧二元经济”靠资本积累,持续高增长得益于这个关键临界条件的跨越,但是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变化,基于内部化过程的内生性动力,成为城市化时期有待突破的关键一环。按照这种假设,二次转型的关键临界条件的突破具有以下特征:内生性替代外生性;消费升级替代资本驱动,或者内部化替代外向性;服务业升级以发挥其对工业部门的带动,即外溢性取代外部性。创新不再是新技术、新产品意义上的简单理解,而是体现在增长联系当中的效率模式的重新塑造,因此城市化新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克服一系列瓶颈:包括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从长期来看,增长方式也由工业主导转换到由服务业和消费主导,消费社会的到来——尽管其利弊存在广泛争论,但是它替代生产社会是经济追赶绕不过的阶段。
(二)中国二次转型的瓶颈:人力资本与消费模式
1.(狭义)人力资本:中国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问题
在相关研究中,我们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追赶和经济转型,看作是人力资本积累能力的追赶和人力资本结构的梯度升级过程。人力资本追赶模式大致可以归納为三类⑧:第一类是较为顺利实现二次转型的国家,其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显著表现出工业化结构性加速时期初等和中等人力资本主导转向城市化时期高等人力资本主导的动态;第二类是拉美模式,在大规模工业化结束后,由初中等人力资本主导向高等人力资本主导增长的内生路径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经济表现出前文所述的迷惘和徘徊;第三类是中国模式,初中等文化程度劳动力占据了绝大比重、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问题突出,根据Barro-Lee(2014)数据,20世纪80年代,中国35—54岁主要储蓄者中,初级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比重约80%。⑨普遍认为,中国奇迹的一个十分值得赞叹的地方,恰恰在于仅仅依赖庞大的低价、半熟练劳动力支撑起来庞大的工业化过程。然而,若把这种人力资本模式放在二次转型的视角下观察,低层次人力资本“壅塞”问题也在于很难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环境,毕竟这种人力资本模式是与粗放的规模效率模式相匹配的。
2.广义人力资本:中国消费模式升级滞后问题
中国低素质劳动力的累积,源于资本驱动的工业化模式,这种狭义人力资本格局的固化,与消费升级滞后有关。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伴随着长期增长过程中生产结构的变化,消费结构发生相应升级,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城市化的发展促使消费结构中科教文卫等项目的支出比重增加,物质消费支出比重下降但绝对数额增加(一些最基本的项目如衣食绝对支出趋于饱和)。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经济追赶国家消费模式变化中,包括两个基本的趋势:第一,在消费结构中,物质品消费由以衣食为主到以耐用品为主,再到以知识消费为主;第二,在消费数额中,无论是物质品消费还是知识消费,均表现出增加趋势,全部物质品消费和服务品消费数额虽然表现出新古典理论所谓的“不餍足”,但是当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时,衣食住行等物质品支出数额也会出现饱和。日韩等成功追赶经验显示,二次转型发生且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消费模式发生倾向于科教文卫等项目的变化,而这些项目支出均与包括教育、健康、心智发展等广义人力资本提升密切相关。⑩不同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经济追赶国家,在二次转型的关键时期却发生了困难:第一,工业结构的深加工度化难以实现,要么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以技术进步衰退为特征的“去工业化”,要么发生像中国这样的被资源密集所统治的“后工业化”;第二,消费结构升级遇到了难以突破的边界,典型的是中国依靠初级劳动要素所导致的“低收入—低消费—低技能”循环。endprint
3.中国二次转型的关键临界条件:内部化和内生性的困难
以中国二次转型面临的困难为例,整体来看,受生产供给主导增长的惯性和理论认识滞后的影响,即使我们看到了现实中城市化的发展,但是进入城市的大部分“人”却没有从工业化时期的劳动力转化为城市化时期的广义人力资本。此时,主导产业形态虽然也发生了向服务业的转变,但是服务业仍以传统的成本型业态为主,囿于人力资本的缺乏无法实现向知识型、技能型的业态转变。这种意义上的服务业仍然是工业部门的延伸,服务业部门就业的“平移”问题、相对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等,为内部化和内生性带来新的阻碍。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现有体制框架下,如果任由物质资本积累主导增长,将会导致租金抽取模式的发生以及结构性减速螺旋的形成。{11}
三、二次转型路径:基于广义人力资本和消费视角
(一)二次转型的主线:大国效应倒逼机制
1.大国效应的弊端
与日本、韩国等经济追赶成功的经验比较起来,受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资本驱动模式惯性的影响,中国经济二次转型的压力更大,表现在:第一,受庞大的农村人口规模的制约,劳动力拐点出现较晚,规模效应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在这点上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不同。{12} 第二,“清理房间”滞后,外部机会少。受益于国内技术开发能力和外部经济环境,1968年以后,日本转移国内低端产业链的“清理房间”过程启动。相比较起来,中国资本驱动模式行将结束的现阶段,“清理房间”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启,且受制于国内外技术、市场因素,这种前景也不容乐观。第三,体制转型滞后,缺乏应对新经济阶段要求的反应灵活性。
2.二次转型的主线
减速时期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增长无效率问题,以及大国效应的自身弊端,迫使经济二次转型进行再平衡,尤其应当注重规模经济阶段被严重忽视的内部经济潜力的挖掘,以避免可能的减速循环。二次转型的主线可以概括为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以资本配置方式的改变扭转增长的外向性、以消费模式升级强化增长的内部化效应和以服务业升级带动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换言之,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调整、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
3.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重塑效率路径
从二次转型的要求及理想愿景出发,总结原有资本驱动的工业化的经验,可以得出:二次转型的核心环节是重塑效率路径。第一,原有规模效率模式的典型特点是:技术、规模和效率容易获得,鉴于国内充分的剩余劳动力禀赋,只要抓住了外部技术和市场,从规模扩张中获得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不是难事,因此中国工业化高增长时期只需要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利用剩余劳动力就足够了。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把这个时期的产业特点归结为标准化、规模化的通用技术部门的发展,而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大生产,正是适应于这种经济结构建立起来的。{13} 第二,当基于这种历史条件的结构性加速过程结束,面对系统性、结构性经济条件的变化,效率路径重新建立自然成为新时期的核心问题,此时,效率模式的塑造不可能只是个别产品和个别生产环节的创新,而是与经济结构和系统转换相关的整体绩效模式的再造。这个核心环节统摄了二次转型中投资激励模式调整、消费模式调整和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调整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二次转型的成败和绩效评价。
(二)服务业发展方式调整:知识部门作为效率模式重塑的支撑点
1.路径对比
为了突破结构性减速之后规模效率模式退化的障碍,有效途径是尽力打破“新二元经济”困境,为此,需要重新定位服务业的作用。就老牌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经历了商业发展和工业发展的漫长演化之后,部门间利润率趋同规律已经根植于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之中,并直观表现为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效率平衡。而且,正如Buera and Kaboski对发达国家服务业所观察到的那样,伴随着服务业份额的提高,服务业也越来越趋向于技能密集。{14}我们把这一理想图景放在二次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认识,就可得出:后发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结束之后,需要发展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效率模式,以便实现经济转型的顺利过渡。但是,受后发国家初始发展条件和经济演化路径的局限,“新二元經济”问题的发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偏差”。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而言,“新二元经济”态势的扭转,成为二次转型的重要任务。换句话说,当工业化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结束,城市化过程中如果服务业要担当起新的效率模式的创建任务,就需要至少不低于原有增长路径的效率改进方式;否则,城市化过程只能是以整体效率下降为代价,并迫使经济进入减速螺旋。
2.发展服务业:替代还是溢出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曾就中国服务业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问题进行过分析,提出服务业作用的“结果说”和“条件说”。{15}“结果说”认为,现阶段“新二元经济”问题,源于资本驱动模式下服务业对工业的从属地位——即作为传统工业发展的分工结果存在,此时服务业的发展以传统业态的规模扩张为主,对初级劳动力的吸收削弱了其效率改进和业态升级潜力。服务业作为经济整体增长“条件”,其重要性在于该部门的存在,有利于促进工业部门的持续发展。显然,处于分工结果之下的服务业,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部门外部性的影响,这种影响短期内虽然有助于服务业部门扩张,但长期中却有可能削弱其可持续增长潜力;处于“条件”链条中的服务业,其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发展上,而且体现在对其他部门的外溢性上,并成为城市化时期的效率源泉。
3.知识过程与服务业调整
通过发达国家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发展的对比,我们可以对一些实质性差异作出具体说明。实际上,能让服务业成为整体经济发展“条件”的依据,在于城市化阶段知识过程的突出作用。知识过程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一方面是服务业结构中知识部门比重上升,另一方面是知识部门对通用技术部门的溢出效应增强,也正是从这种表现上来说,服务业足可以摆脱大规模工业化时期的从属地位,进而以其整合能力接替工业部门成为新效率模式的支撑。知识部门作用的突显,与城市化阶段工业化部门比重下降、服务业部门比重上升的趋势有关,不论从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就业吸收角度看,服务业主导发达国家或经济发达阶段的态势显而易见,这种趋势与城市化时期资本积累路径的特殊性和广义人力资本发展有关。endprint
(三)资本积累路径调整:消费模式与广义人力资本
1.投资与消费的再平衡
重新回到消费结构升级路径的观察上来,研究不同增长阶段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及其再平衡问题。由于其本身外生性和外向性特征,为了保持高增长和对冲非生产部门规模扩张的成本,中国资本驱动模式日益陷入“低效率—高投资—更低的效率—更高的投资”的增长循环,尤其是垄断部门——不论是生产性部门还是非生产性部门,坐地生财、亏损国家补偿所导致的抽租问题越来越显著,原有增长理念和战略已经到了不得不扭转的地步。“重生产、轻消费”“重外向、轻内需”是规模效率的合理逻辑,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和市场、资源环境等约束的日益增强,投资与消费再平衡理应受到重视。作为二次转型的重要机制,消费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消费的效率补偿是投资消费再平衡得以实现的基础。结构性减速时期,要想避免“去投资依赖”的二次转型所隐含的增长退化风险,就需要建立“有效率”的消费模式,这是二次转型以质量换速度的核心标志。短期来看,投资消费之间是此消彼长的替换关系,二者不存在替换;长期则不然,原因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向劳动力和消费的倾斜有助于消费结构中新的效率源泉的培育,这种新的源泉寓于与广义人力资本有关的消费者创新当中。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越是现代化的经济,越需要消费者的开放性、主动性和品位多样性,这一切离开教育、健康、娱乐等高端消费几乎不会成为现实。简言之,在外向性、外生性、外部性经济受到刚性制约时,要想突破资本效率递减和避免减速螺旋,必须进行投资消费的跨期再平衡以培育新的效率源泉。
2.时间配置模式的再平衡
投资与消费的再平衡,蕴含了效率模式改进机制的变化,即原有资本驱动的外生的规模效率模式,向与消费结构升级有关的广义人力资本驱动的效率模式的转化。这就意味着转型过程中资本分布状态需要再评价——资本积累向人力资本的倾斜和权衡。这种认识同时意味着,以往经常被作为规范性和制度性框架的时间配置模式需要进行修正。因为消费结构中居于高端的一些项目,具有像生产过程那样资本化时间资源的作用,典型如娱乐——分布在时间阶段上的消费直接生成新的效率和业态。事实上,类似的时间配置再平衡机制,也是城市化的本来旨趣。
(四)消费模式调整:消费与生产一体化
二次转型过程中新的效率模式的重塑,具体体现在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一体化上{16},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传统工业化社会中,生产与消费虽然经由市场媒介,但是对于个体消费来说,由于服務品消费比重相对较低且大多局限于传统服务项目,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只有当消费模式出现知识技术消费占主导的情况下,消费与生产一体化中体现的高效率才能充分显现。一是随着个体把工作时间之外的休闲时间向文化娱乐的消费配置,很自然地延伸了“生产性”和效率,表现为上文所说的新业态的繁荣;二是随着消费经验的积累和消费学习,消费者对于制造品内含的技术知识要求提高,物品特性而非物质品本身越来越受到关注,物质品使用的“服务性”特征受到关注,消费与“售后”一体化要求增强,倒逼生产者注重质量和创新。第二,消费结构向知识技术密集消费品的升级,客观上促进了金融、健康、教育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发挥互联网在整合消费和供给中的优势,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第三,消费模式升级充当了产业升级的过滤器,消费的内部化效应使得高效率模式不可逆,消除了增长退化的隐患。供给创造需求的传统增长观点,只是在特定需求模式之下才能成立,就如中国现阶段产能过剩所呈现的那样。但在现有消费模式已经达到饱和的困境下,需要借助不同的路径——即通过需求侧的疏导和培育——来发掘新的增长机会。从二次转型的成功经验看,通过消费能力培育提高广义人力资本,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
结论
对于中国或长或短的经济转型而言,关键是实现增长观念的转变,包括转变工业化时期的生产供给主导思维,把增长目标转到“人”的发展上来。当我们意识到,为了应对城市化时期经济减速的各种系统性问题,除了物质资本动力之外,更需要重新积累和培育广义人力资本潜力,那么,针对现有增长约束的制度、组织环境进行变革,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中国二次转型的初期,虽然有大国效应的不利制约,但是转型过程中如果采取适当的疏通政策,大国效应的弊端也可以转化为优势。潜在的优势体现在:第一,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将成为内生性增长的新突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大城市和以大城市为纽带的城市群的崛起,成为二次转型新增长动力的动力源,这种模式不同于原有以农村劳动力供给为基础的资本化模式。基于此,中国大城市在消费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具有较大潜力,城市经济在产业结构和要素积累调整方面,也具有较好的基础和较大的创新外溢潜力。第二,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潜力大。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年轻人口组(典型如20—24岁、25—29岁)大学教育比重提高的态势较为显著。尽管短期内不可能达到日本、韩国70—80%的普及性,但是在对年轻人口普及高层次技能教育方面,中国凭借自己的经济能力却可以办到;而且在二次转型的预计较长的整个过渡时期里,以高层次技能人力资本为依托、以高等教育为龙头的人力资本结构,可能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第三,政府作用应该调整到支持广义人力资本积累上来。面对二次转型新的要求,政府的作用也将转移到“社会开发”上来,尤其应加大教育体系的建设和规划。
注释:
①袁富华.低碳经济约束下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0(8).
②宫崎勇.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26-127.
③{15}袁富华.中国经济“结构双重性”问题分析[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4(3).
④C.Kay. Latin America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andUnderdevelopment[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89:117-118.
⑤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J].经济研究,2012(11).
⑥Nakamura Takafusa.The Postwar Japanese Economy: Its Development andStruture[M].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Press, 1981: 100-102,258,102.
⑦A.Hofma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M].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0:62-63.
⑧袁富华、张平、陆明涛.长期增长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结构[J].经济学动态,2015(5).
⑨Barro-Lee. BL2013_MF_v1.3.xls, Barro-Lee educational attainmentdataset_2014.
⑩{13}{16}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11).
{11}袁富华、张平、陆明涛.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的退化[J].天津社会科学,2015(4).
{12}Shinohara Miyohei. Structural Changesin Japan`s Economic Develoment[M].Tokyo:Kinokuniya Bookstore Co., Ltd.,1970:22-23,345-346.
{14}F. J. Buera and J. P. Kaboski. The Rateof the Service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Vol. 102. No.6:2540-2569.
责任编辑:李瑞山
(本文发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杂志2016年第2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