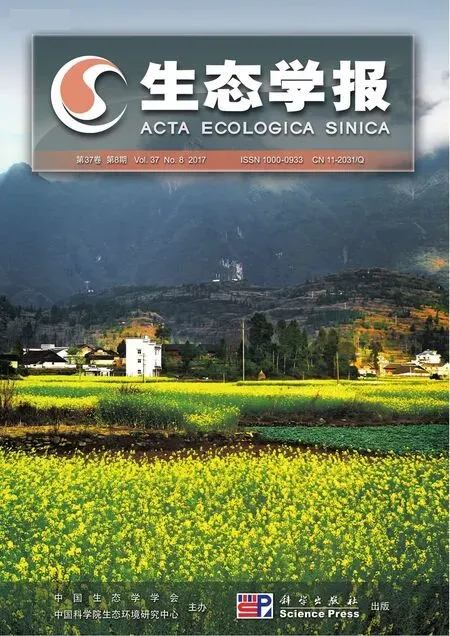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
2017-06-26徐中民宋晓谕程怀文
孙 克,徐中民,宋晓谕,程怀文,聂 坚
1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70 2 赣南师范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赣州 34100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4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00 5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南昌 330000
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
孙 克1,2,3,*,徐中民1,宋晓谕1,程怀文4,聂 坚5
1 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内陆河流域生态水文重点实验室,兰州 730070 2 赣南师范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赣州 34100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4 浙江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杭州 310000 5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南昌 330000
利用2013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截面数据,采用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估算了2013年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利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技术的STIRPAT模型,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空间异质性估计,同时验证了EKC假说。主要结论如下:(1)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2812.48亿元。(2)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3)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环境污染。(4)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大;富裕程度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5)基于现有样本的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假说。
人文因素;环境污染; STIRPAT模型;空间异质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环保健康意识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关注人群已不再局限于政府和学者,已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活动(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城镇化、工业化、产业结构调整等)必然会对环境造成影响[1],而科学准确地测定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大小,对解决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目前,人文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聚焦在经济规模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上[2- 8],把经济规模作为环境污染的唯一影响因素,通过构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计量模型,来验证EKC拐点的存在、曲线形状等,这些研究虽然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重要联系,但忽略了其他人文因素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影响关系,而且也没有考虑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不够全面科学。也有学者考虑了将多种人文因素纳入EKC模型,蔡风景[9]等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利用率、科技教育水平等人文因素纳入EKC模型,通过贝叶斯平均估计方法来检验我国环境污染的EKC形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该研究虽然考虑了多种人文影响因素,但忽略了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吴玉鸣[10]扩展了传统的EKC模型,将人口规模、城市化、产业结构等人文因素纳入模型,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省际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EKC的形状及人文影响因素,该研究虽然在模型设定中考虑了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但却忽视了空间异质性,这不符合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实际,研究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
回顾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当前大多数关于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忽略了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地理空间邻近的区域,其很多自然、人文因素会互相影响,存在“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现象,传统计量研究中所要求的研究区域彼此独立且均匀随机分布的前提条件很难满足,因此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的研究结果难免以偏概全[10-11]。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可以较好地处理空间异质性[12], 本文拟采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STIRPAT模型,测算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还将验证EKC假说。跟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在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中,考虑了空间样本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为制定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31个省级行政单元的相关经济、环境和能源计算数据来源于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资料。
1.2 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
本文需要测算省级尺度的环境污染水平,一般环境污染物质根据其物理化学特性,包括固体污染物、气体污染物,水体污染物和噪声污染。由于固体污染物数据获取和处理难度较大,本文只考虑水体污染(化学需氧量COD)、气体污染(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工业粉尘和烟尘)和噪声污染,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计采用IPCC的碳排放估计方法,即能源消费量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文选取煤炭、原油、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消费量和水泥生产量数据用于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现有大多研究对于环境污染的计量一般直接使用污染物质的排放量,而本文参考刘渝林[13]等文献的研究成果和方法,采用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的方法即消除环境污染带来损失所需要的资金货币量来近似计算环境污染经济成本,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方法可以将不同类型污染物质造成的环境损失统一为具有经济意义的货币单位,使得有关环境污染水平的测算和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可比性[10,13]。具体来说,按照1988年不变价格,COD污染成本为1.11663元/kg,二氧化碳污染成本为0.004965元/kg,二氧化硫污染成本为1.101742元/kg,工业粉尘和烟尘污染成本为0.617869元/kg,噪声污染成本为GDP的1%[10,13]。噪声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一般采用市场估值法、享乐价格法和意愿调查评估法,分别从居民健康损失、固定资产贬值、防护费用和消除噪音的支付意愿等方面对噪声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目前,国内学者采用上述标准评估方法进行噪声污染的经济损失估算主要集中在道路交通噪声方面,其估值占GDP的比值一般为0.8%—3%[14-15],综合考虑国情,在满足基本粗略计算的条件下,本文认为刘渝林和吴玉鸣两位学者在估算噪声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中,采用1990年世卫组织报告[16]所提出的噪声污染产生经济损失为GDP的1%的估算方法是合适的。各地区各类环境污染物质污染成本加总即可获得各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
1.3 环境污染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模型
由于许多环境污染物质具有跨区域的流动性,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不可避免会受到邻近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空间自相关Moran′s I模型可以较好地反映地区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具体模型为[11,17]:
Moran′sI的定义为:

(1)

1.4 STIRPAT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要进行人文因素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分析,一般采用STIRPAT模型,由于该模型是基于经典的人文环境影响分析框架即IPAT等式演变过来的,其计算结果具有较好的理论解释性,进行对数变换后,可以便捷地开展弹性分析[17-21]。其一般表达式为:
I=aPbAcTde
(2)
式中,I为环境污染,P、A和T分别为人口数量、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a为常数项,b、c、d为P、A和T的指数项,e为随机误差项。
中国国土面积广袤,地理地貌丰富多样,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历史、风土人情、经济发展等先天存在差异,“一刀切”的政策在省域情况不同的地方会产生不同的施策效果[22]。因此,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在地理空间上是有差异的。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适应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要求,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nI=a(u,v)+b(u,v)lnP+c(u,v)lnA+d(u,v)lnT+e
(3)
式中,(u,v)为省域中心地理坐标,a(u,v)为常数项的位置函数,b(u,v)、c(u,v)、d(u,v)为自变量系数的位置函数。由于STIRPAT模型是随机形式,可以在模型中增加富裕的自然对数二项式来验证EKC假说,参考以往的研究思路和方法[1,11],本文设计了无人口技术影响和有人口技术影响两种情景,具体形式如下:
lnI=a(u,v)+c(u,v)lnA+f(u,v)ln2A+e
(4)
和lnI=a(u,v)+b(u,v)lnP+c(u,v)lnA+f(u,v)ln2A+d(u,v)lnT+e
(5)
其中,(4)式为无人口技术影响模型,(5)式为有人口技术影响模型,f(u,v)为负,则EKC假说成立,通过对 (4)式或(5)式求导计算极值,就可获得曲线拐点值。
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应该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环境污染产生源和形成原因来看,除了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等人文因数以外,还有环境管制、社会资本、人口素质、环保意识等人文因素,按照Dietz和York等提出的人文驱动因素随机回归影响模型(STIRPAT模型)指标选取理论,模型选取的人文因素应该可以采用指数连乘的形式建立关联[1,21]。因此,本文摈弃了其他难以量化和概念化乘积形式的人文因素,将研究聚焦在人口、富裕和技术这3个关键人文因素上,技术水平的测算比较复杂,一般采用无量纲的比值数据,借鉴以往研究,本文将技术指标分解为结构性指标、现代化指标和开放性指标[1,11]。文章用各省域的人口数量和人均GDP数据来分别表示该地的人口规模和富裕程度;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结构性指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城镇化率来测度该地区的现代化水平,用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值来测度该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2 研究结果
2.1 环境污染的货币化估计
根据环境污染损失货币化方法,计算得到2013年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表1),从表1可以看出,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2812.48亿元(1988年不变价格),其中噪音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为1629亿元,可见噪音污染产生的经济损失是环境污染损失的主要祸首。长期以来,化学物质引起的环境污染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而噪音污染引起的危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噪音不仅对人类健康(生理、心理和身体)构成巨大威胁,而且对经济社会也会造成巨大损失,从而增加经济环境成本(身体康复防护费用、房地产等固定资产贬值和消除噪音采取的各种减噪措施成本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噪声来源和数量(道路里程和机动车辆数量增加导致交通噪声增加,建筑物增加导致施工噪声增加,商业活动频繁导致活动噪声增加等等)急剧增加,其产生的环境经济成本(损失)也随之大幅增加。因此,在环境污染中噪音危害不容小觑,应该予以高度关注。环境污染损失中最高的为山东243.84亿元,最低为西藏2.73亿元。
2.2 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特征
在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分析中,需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前提条件是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22-23],为此需要对省域环境污染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检验。基于GeoDa软件,2013年省域环境污染的全局Moran′sI指数计算结果为0.2328,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国省域环境污染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为进一步了解省域环境污染的局部集聚特征,判断其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可以绘制Moran散点图(图1),将散点图中各象限的省级区域划分为H-H型、L-L型、H-L型和L-H型4个类型,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从省域环境污染的分布数量来看,大部分省域属于H-H(8个)和L-L类型(9个),此两类型省域占比达到55%;从环境污染区域的分布地理空间来看, H-H型大多分布在东中部地带(如鲁苏浙辽冀豫湘晋),L-L型大多处在中西部地带(如黑新宁藏滇青甘陕黔),H-L型和L-H型则离散分布于东、中、西部地带。Moran 散点图较好地揭示了中国省域环境污染损失的局域集聚特征,H-H和L-L类型数量多,表明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H-H和L-L类型地理分布呈现地带集聚现象,说明省域环境污染水平存在空间异质性。事实上,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借鉴“中心-外围”理论,H-H和L-L类型其实就是省域环境污染的高污染中心区和低污染中心区,H-L和L-H则属于外围区,因此可以说,在省域环境污染的地理空间分布上,存在两个中心区,东部为高污染中心区(H-H),西部为低污染中心区(L-L),在东西部这两个中心区间又穿插分布若干H-L和L-H型省区构成外围区,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所表现出的“中心外围”空间模式,进一步凸现了空间异质性。由于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就有可能发生空间变异。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模型获得的全局不变估计参数只具有全局平均意义,无法细致地反映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特征,研究结论不太科学全面。因此,为了准确把握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细节,就有必要将空间区位信息纳入计量模型即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表1 2013年各省区环境污染损失情况(1988年不变价格 108元)
统计资料尚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等数据

图1 省域环境污染Moran散点图 Fig.1 Moran′s I scatter diagram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f Chinese provinces
2.3 环境污染计量结果分析
2.3.1 OLS结果分析
对全局STIRPAT模型式(2)进行对数变化,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可以获得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全局(平均)影响,计算结果见表3。
仔细分析表3计算数据,可以发现各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都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环境污染。因此在面对省域环境污染问题,对人文因素应该予以充分考虑和高度关注。进一步比较各因素影响系数估计值可以发现,人口规模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城镇化率,影响最小的为对外开放度。由于模型采用自然对数形式,根据自然对数的数学性质,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弹性分析,具体来说就是,人口数量增加1%,会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增加0.884%,城市化率每提高1%,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增加0.808%,第三产业占比每提高1%,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减少0.747%,人均GDP提高1%,引起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增加0.417%,对外开放度每提高1%,省域环境污染损失就减少0.076%。理论上来说,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扩张会加速资源的消耗和增加废物或污染物质的排放,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以低消耗低污染为特征的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则有利于环境污染的缓解,因此本文样本的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产业结构的系数估计值符合理论预期。同时,也要注意到,本文样本的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似乎不太符合理论预期。

表2 2013年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情况

表3 最小二乘法模型估计结果
*表示在0.05水平显著
2.3.2 GWR模型结果分析
省域中的省会城市一般为该地的人口和产业集聚中心,在省域范围内其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本文选取省会城市的经纬度作为省域中心地理坐标。GWR模型的权属函数选择固定高斯函数,带宽采用交叉确认法进行确定,运用GRW 4.0软件,对模型(3)进行回归计算,结果见表4。

表4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此模型计算的局部回归标准化残差的Moran′sI指数为-0.0043,残差呈空间随机分布

图2 GWR模型人口数量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population in the GWR model
比较表3和表4的模型计算结果,可以发现:从模型的拟合效果来看, OLS模型的拟合优度为0.95,GWR模型为0.961, GWR模型优于OLS模型;从人文影响因素系数估计值结果来看, GWR模型系数估计值与OLS模型正负符号一致,且GWR模型系数估计值的平均值与OLS模型相差不大,说明GWR和OLS模型都可用于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但OLS模型仅能反映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全局影响特征,而无法反映影响作用的局部特征。从这点来说, 在反映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局部细节方面,GWR模型较OLS模型具有先天优势。为深入分析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掌握其空间变化规律,可以将GWR模型计算的人文因素系数估计值导入GIS软件平台,进行可视化空间表达。
(1)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图2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大,其中海南(0.8917)的环境污染受人口因素相对影响最大,而青海(0.8738)最小。这意味着,如果想通过采取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环境的改善,东南地区可以比西北地区获得更好的政策效果。事实上,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的原因,中国人口在地理空间上历来存在东重西轻和南多北少的分布格局即东(南)部人口多,西(北)部人口少,人口规模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变化特征与中国人口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是相符的,这表明GWR模型的估计结果是符合中国人口分布实际的。
(2)富裕程度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图3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经济发展(富裕水平)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其中上海的环境污染受经济发展影响最大(0.5002),最小为新疆(0.3572)。
(3)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图4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其中产业结构对新疆(-0.8780)环境污染影响最大,黑龙江(-0.6121)最小。在相同条件下,如果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提高相同比例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则西部比东部获得的环境改善效果更好。

图3 GWR模型富裕程度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affluence in the GWR model

图4 GWR模型产业结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industry structure in the GWR model
(4)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图5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其中新疆(0.9830)的环境污染受城镇化影响最大,黑龙江(0.5427)最小。
(5)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图6所呈现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其中对外开放对新疆(-0.07989)环境污染影响最大,广东(-0.07240)最小。
2.3.3 EKC假说验证
根据EKC假说,经济发展初级阶段会对环境产生压力,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压力越大,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对环境的压力也达到峰值,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压力也逐渐减小,经济与环境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技术对模型(4)进行参数估计,可以得到各地区人均GDP平方项的系数值,如表5所示,人均GDP的系数值都为负值,且其T统计量都能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各地区的EKC都是开口向下的,EKC假说成立。通过曲线函数求极值计算,可以得到各省域拐点值(1988年不变价格),比较各地区拐点值,发现拐点值存在空间异质性。每个地区由于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同,要实现经济和环境良性互动的条件门槛也会不同即拐点值不同,西藏要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门槛最高(拐点值32004元),天津门槛最低(拐点值为12929元),拐点平均值为18257元。将2013年中国各省域人均实际GDP(1988年不变价格)与其拐点值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人均实际GDP超过拐点值的省域(鲁苏浙辽京津闽沪粤蒙)绝大部分都位于东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处于良性互动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均实际GDP低于拐点值(内蒙古除外),有些省份离环境改善的距离还比较远,中西部地区要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任重而道远。

图5 GWR模型城市化率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GWR model

图6 GWR模型对外开放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open index in the GWR model

表5 人均GDP的平方项系数和拐点估计结果
圆括号内为T统计量;拐点值按照1988年不变价格计算
模型(5)是对模型(4)的扩展,除考虑对数人均GDP的一二次项外,又增加了人口技术因素,通过地理加权回归,发现各省域对数人均GDP平方项系数估值有正有负,且其T统计量较小不显著。这意味着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在经济和环境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能暗示着适度控制人口规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紧凑精明质量优先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各省域实现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2.4 环境污染计量结果讨论
OLS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和对外开放度的估计系数不符合传统的理论预期。因此,有必要从机理方面进一步考察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
(1)就城镇化率来说,依照现代化理论,城镇化率代表一个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即城镇化率越高则该地的现代化水平越高,环境受到污染越低,但本文样本估计的城镇化率对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正,与理论预期不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可部分解释个中缘由,一是伴随农村优质人口的流失,农业生产方式发生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是退步式的,农村依靠有机农家肥增产的环境友好型、精耕细作式的传统生产方式逐步消失,而依靠不断增加化肥农药投入而增产的生产方式快速兴起,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增加,农村人居环境恶化;二是一个地区实现现代化一般意味着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产业结构、齐全的环保设施、普遍较高的环保意识、公共服务配套较齐全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现阶段很多地区的城镇化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只是身份城镇化即“户籍城镇化”,很多应该同步配套建立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政策制度没有建立,城镇化率这个指标相对于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水平来说代表性不够。
(2)就对外开放度来说,根据“污染天堂”的假说,对外开放会导致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环境污染问题恶化,但本文样本的计算结果不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来我国环境管制政策效果得到发挥,提高了外商投资的环保技术门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被拒之门外,而拥有低碳环保绿色技术的企业被大量引进。
GW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仔细分析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东西差异,可以获得以下政策启示:
(1)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西部地区,但同时要注意到东部地区的环境污染比西部地区要严重得多,这暗示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取得的。因此,西部地区在发展当地经济时应该提高警惕,引以为戒,切勿走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而轻视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非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而东部地区应该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淘汰高污染高消耗的落后产能,做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工作。
(2)就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而言,西部地区经济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较大,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甚至畸形,很多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有些省份已经落入了“资源诅咒”的尴尬境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口号规划多于行动执行,因此在产业升级方面(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例),西部省份比东部省份更加紧急,国家应该继续加大西部开发政策支持力度,充分调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同时西部地区自身也应该主动作为,简政放权,综合运用市场、财政、税收、政府投资等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企业)优化升级的活力,而东部地区应该树立低碳环保的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低碳绿色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
(3)就城镇化的发展程度而言,西部地区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很多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城镇化质量较低,在各方面配套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市,由此给城镇环境造成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西部省份在推进地区城镇化时,应该摒弃只重视城市规模扩张,而忽视城市配套建设的城镇化发展思路,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紧凑精明的城镇化发展思路,以便将城镇化带来的环境负面效应降到最低。
(4)东部地区地处沿海,对外交流具有先天区位优势,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西部地区地处内陆深处,交通不便,对外交流先天不足,东部地区由于对外开放历史较长,水平较高,外商投资存量巨大,依靠外商投资来改善环境的边际效应正在逐渐减小,而西部地区由于外商投资对外开放历史较短,水平较低,外商投资严重不足,外商投资经济环境边际效应较高。为此,西部地区应该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完善招商引资软硬环境,提高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形成环境与经济效益兼得的良好发展局面,同时东部地区应该厚植发展优势,做好对外开放的提质增效工作,打破经济环境边际效应递减瓶颈,将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3 结论
本文采用环境污染货币化方法估算了2013年中国省域的环境污染损失,利用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技术的STIRPAT模型,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产业结构、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等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了空间异质性估计,同时验证了EKC假说。主要结论如下:
(1)2013年中国环境污染引起的经济损失为2812.48亿元,噪音污染是造成环境污染损失的主要因素。
(2)各省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省域环境污染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
(3)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具有显著影响,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及推进城镇化将加剧省域环境污染,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助于缓解省域环境污染。
(4)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人口数量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由西北向东南渐次增大;经济发展(富裕水平)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梯次增大;产业结构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城镇化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西向东逐渐降低;对外开放对省域环境污染的影响由东向西逐渐增大。
(5)基于现有样本的计算结果有条件地支持EKC假说,适度控制人口规模、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紧凑精明质量优先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可能是各省域实现经济与环境良性互动发展的前提。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增长速度进入换档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而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复杂,环境治理进入关键节点阶段。由于人文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环境污染治理思路应该从各地单独治理转变为跨区域协同治理,从过去“一刀切”的政策思路转变为因城因地施策。总之,在环境治理方面,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协同各方,又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1] 徐中民, 程国栋. 中国人口和富裕对环境的影响. 冰川冻土. 2005. 27(5): 767- 773.
[2] Munasinghe M. Is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growth: Tunneling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 25(2):195- 208.
[3] 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财经研究,2000,26(10): 53- 59.
[4] 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地理研究,2002,21(2):239- 246.
[5] 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地理研究,2003,22(1):60- 66.
[6] 彭水军,包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财经问题研究,2006,(8):3- 17.
[7] 符淼.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态、拐点和影响因素.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1):40- 55.
[8] 苏梽芳,胡日东,林三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库兹尼茨关系空间计量分析.地理研究,2009,28(2):303- 307.
[9] 蔡风景,李元.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统计与决策,2014,(12):123- 126.
[10] 吴玉鸣,田斌.省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及其决定因素——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地理研究,2012,31(4):627- 640.
[11] 孙克, 徐中民. 环境影响评价中人文因素作用的空间计量. 生态学报, 2009, 29(3): 1563- 1570.
[12] Fotheringham A S, Brunsdon C, Charlton M.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The analysis of spatially varying relationships. Chichester: Wiley, 2002.
[13] 刘渝林,温怀德.环境污染损失的货币化估算与政策建议.改革,2006,(9):106- 109.
[14] 郭静男,朱建平,郭秀兰.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损失分析.中国环境科学,1989,9(6):415- 418.
[15] 李洁,沈毅,王新民.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经济损失及评估.西部交通科技,2013(9):33- 37.
[16] Daly H, Cobb J. For the common good. Beacon Press. Boston, 1990.
[17] Anselin L.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s and model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 16- 31.
[18] Waggoner P R, Ausubel J H. A framework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 renovated IPAT identity. Proc. Natl. Acad. Sci., 2002, 99: 7860- 7865.
[19] York R, Rosa E A, Dietz T. Bridg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with environmental policy: Plasticity of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2, 83(1): 18- 34.
[20] York R, Rosa E A, Dietz T. Footprints on the Earth: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68(4): 279- 300.
[21] York R, Rosa E A, Dietz T. STIRPAT, IPAT, and ImPACT: analytic tools for unpacking the driving forc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3, 23: 351- 365.
[22] 孙克,徐中民.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中国灰水足迹人文驱动因素分析.地理研究,2016,35(1):37- 48.
[23] 庞瑞秋, 腾飞, 魏冶.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动力机制分析.地理科学, 2014. 34(10): 1210- 1217.
Spatial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factor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
SUN Ke1,2,3,*, XU Zhongmin1,SONG Xiaoyu1, CHENG Huaiwen4, NIE Jian5
1KeyLaboratoryofEcohydrologyofInlandRiverBasin,NorthwestInstituteofEco-EnvironmentandResource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Lanzhou730070,China2GeographyandPlanningCollegeofGannanNormalUniversity,Ganzhou341000,China3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eijing100049,China4EconomicalCollegeofZhejia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Hangzhou310000,China5JiangxiNuclearIndustryGeologicalBureau,Nanchang330000,China
In China toda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become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tri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ccurat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uman factor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WR measurement model is more accurate than the traditional 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 model because of its spatial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los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currency, we estimated los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of 31 provincial regions in China in 2013 and explored the feature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We quantitatively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China′s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environment pollution by constructing a STIRPAT model based on the GWR.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economic los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in 2013 is ¥2812.48×108yuan. The noise pollution is the main factor causing the los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there ar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provinces is the pattern of the East High and West Low. (3)human factors to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promote urbanization will exacerbate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expanding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ill help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4) the influence of human factors on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spatial heterogeneity. Population of the extent of the impact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gradually increases; affluence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west to east echelon increase;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the impact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east to west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fluence from west to east gradually reduce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vinci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east to west increases gradually. (5)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based on the existing samples are conditional to support the EKC hypothesis.
human facto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TIRPAT model; spatial heterogeneity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125019,91325302)
2016- 02- 15; 网络出版日期:2016- 10- 29
10.5846/stxb201602150284
*通讯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 sunke07@163.com
孙克,徐中民,宋晓谕,程怀文,聂坚.人文因素对省域环境污染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估计.生态学报,2017,37(8):2588- 2599.
Sun K, Xu Z M,Song X Y, Cheng H W, Nie J.Spatial heterogeneity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s of human factors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Acta Ecologica Sinica,2017,37(8):2588- 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