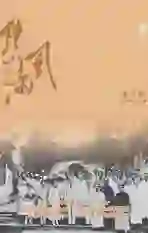一个革命家庭飘零苏联的跌宕经历
2017-06-24徐廷华
徐廷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干部秘密送往苏联学习。这其中就有任岳、王一两个年轻人。后来他们结为夫妻,成了革命的伴侣。他们在苏联学习、工作了25年,后来辗转回国,一生的经历跌宕起伏。
在西去莫斯科的列车上相识
任岳,1903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望城县清港镇一户农民家庭。1921年8月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一起赴苏联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到达莫斯科后,任岳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习。1923年4月,经陈延年、任弼时介绍,任岳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24年任岳等人毕业回国参加大革命,先后在安源煤矿从事工运,任矿党委组织部长、衡州地委组织部长。1926年3月被党派往广州国民革命军总部,担任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的秘书兼翻译,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这次任岳到苏联学习是第二次了,轮船到达海参崴,这批学员被安排住进国际饭店,几天后,便乘火车西行。同车的还有一大批被党中央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党员干部,约有一百多人。在列车上任岳认识了同行的王一。
王一是湖北省荆门县人,1908年5月出生在一户贫苦人家。1926年,北伐浪潮风起云涌之际,王一只身独闯武汉参加革命,1927年3月,由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十几天的行程中,任岳像大哥哥一样照顾王一,到莫斯科后,任岳更是给了王一更多的帮助。经过共同的理想追求和革命事业的牵引,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爱,在中山大学结为伉俪。
女儿在苏联伊尔库茨克出生
1930年1月,漫天大雪。任岳、王一等被分配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边疆斯列金斯克州一个金矿场,担任工人指导员。那里的工人大多是黑龙江南岸越境而来的中国破产农民和城镇苦力劳工。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任岳、王一等人一起深入到矿井调查研究,发动群众,和工人建立感情。白天,他们和矿工们一起劳动;晚上,深入工人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任岳、王一对矿工们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组织工人学习政治和文化,提高他们对生活的信心和生产积极性,同时在这群矿工中积极培养出了一批工人干部,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他们的工作很有成绩,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31年10月,王一在伊尔库茨克生下了女儿,取名任晶晔,同时也取了个俄文名字,意思是“十月”,以寄托他们的理想。
1935年5月,已转为苏联公民和联共党员的任岳、王一夫妇等25人,被联共派往新疆去做军阀盛世才的工作。那时任岳被任命为新疆省公安管理处副处长。盛世才把公安处牢牢抓在手里,大权独揽,一切国内外的情报都要向他汇报。任岳除了向盛世才汇报工作外,还要秘密向苏联领事馆汇报,时间一久,他的行动引起了盛世才的怀疑。为了监视任岳的行动,盛世才在苏联领事馆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特务们随时监视公安处与苏联领事馆的一切活动。不久,有人诬告任岳企图谋杀盛世才,盛撤了任岳的职,把他送回莫斯科受审。
在新疆女子学校工作的王一,也因此受到牵连,一同被送往莫斯科。在长达8个月的秘密审查中,查来查去,实在查不出有什么重大问题和错误,历经困难和艰险的他们,于1937年8月再次返回伊尔库茨克地区工作。
在那里,夫妻俩参加了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战时,伊尔库茨克是苏联的大后方,王一放下幼小的孩子,全力投入抢救伤病员的工作。她每天早出晚归,中途步行通过长达2公里的贝加尔湖大桥。冬天,桥上北风呼啸,几乎能把她推下去。住院的苏军伤病员称王一为“东方的喀秋莎”。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人民没有忘记他们的贡献。1996年9月3日,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代表叶利钦总统,授予王一等“1945——1995年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章”。
满怀着期望回到自己的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任岳夫妻立即向莫斯科提出回国的申请,有关部门说他们已经是苏联公民,不能直接找中国大使馆联系,必须听候批复。
1952年,经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在苏联学习、工作长达25年之久的任岳、王一夫妇等一批同志,终于回到了日夜思恋的祖国。
回国后,任岳夫妇见到了已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等人,当年的老同学、老战友萧劲光、帅孟奇亲切而热情地迎接他们。任岳被分配到公安部办公厅任副主任。王一被分配到卫生部北京医院工作。他们满怀报国之志,决心为阔别数十年的祖国尽绵薄之力。
不幸的是任岳终因积劳成疾,猝发心肌梗塞,于1954年5月去世,年仅51岁。王一在北京医院当医师兼耳鼻喉科主任。
后来,王一以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技术成为一名核防护医学专家,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于1982年离休。
在女儿的一次次奔波中逝世
再说出生于苏联伊尔库茨克的女儿任晶晔,在那里上完了小学、中学,于1954年大学毕业。刚好这时组织上派王一护送一名副部长去苏联治病,任务完成后,王一把女儿也带回国内,按当时的政策保留了双重国籍。
任晶晔在大学学的是地图测绘专业,回国后先分配在军事测绘总局工作,一年后调到国家测绘总局研究所,并以来自苏联工程师的身份,负责“典型地貌样图集”项目的研究编制。这个项目是国家12年(1956—1967)科学规划中的重点项目,1966年初步编成,至今这个样图集还名列在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资料库的名目中。任晶晔为这一项目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在工作中,任晶晔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不懂中文。1955年1月,组织上将她送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当时正好印尼共产党秘密派遣一批青年党员到中国来培养,在北京大学单独编成一个班,学习中文和政治。从苏联归来的任晶晔也插到了这个班上学习。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共同的学习中,正值青春年华的任晶晔和同班的印尼共产党员苏巴尔曼,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苏巴尔曼,1929年4月14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马兰市,父亲是一个小鞋店的老板。苏巴尔曼12岁时就離开家,投入印尼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参加了印尼共产党,还参加了武装斗争。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印尼人民掀起争取民族独立的八月革命高潮。8月17日,苏加诺和哈达签署《印尼独立宣言》,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当选第一任总统。在庆典上,苏巴尔曼作为对争取印尼民族独立作出贡献者的光荣代表,被选为4名升旗手之一,亲自参加升起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
两个年轻人常在北大校园里漫步,在未名湖畔探讨人生,有时也一起去颐和园游玩。有趣的是,一个不懂俄语,一个不会印尼语。他们两人就用刚刚学会的中文辅以英语,连说带比划,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这样,他们的爱情火花越烧越旺。
对于任晶晔和苏巴尔曼之间的婚恋,母亲王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老俩口在异国他乡奔波了大半辈子,吃尽了苦头。如果女儿再和外国人结婚,岂不是又要远走高飞,不仅母女难相见,而且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会发生什么事也难以预测。后来由于女儿的主意已定,女婿又是共产党员,人品也不错,她也就同意了。
1959年,任晶晔和苏巴尔曼结婚,先后生育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全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1965年苏巴尔曼研究生毕业后,一家四口准备回印尼去。苏巴尔曼已经十多年没有回国了,所以他乘飞机先回印尼做些准备,任晶晔和孩子们也已定好船票,待后出发。没想到这年9月,印尼发生了“九三○”事件,苏哈托攫取了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的权力,登上总统宝座,推行强权政治,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无以数计的华侨华人。任晶晔的丈夫苏巴尔曼也遭到杀害,为印尼人民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文革”开始了,因任晶晔的双重国籍,成了“苏修”之嫌,就连已经牺牲的丈夫苏巴尔曼的真实身份也受到怀疑。任晶晔被赶出北京,发配到武汉测绘学院。母亲王一也被送到湖北沙洋干校蹲牛棚。两地相距并不很远,但她们却互不知情。她给母亲写了很多信,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母女二人惟有朝思暮想、梦中相会而已。
任晶晔不堪迫害,带着两个孩子于1971年回到伊尔库茨克大学任教。“文革”后,任晶晔常奔波于伊尔库茨克——北京两地之间,回国探望年老的母亲,一住就是3个月,期满后又匆匆赶回伊尔库茨克。然后再申请,再回国,一次又一次无穷期。2001年11月11日,王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人民日报》发了“王一同志逝世”的消息。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风雨雨,遭遇了人生许许多多的悲欢离合,在国际共运史上,王一一家终于续写完这部活生生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