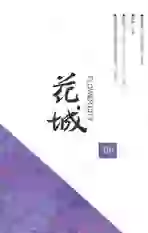访谈:“它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学”
2017-06-09何平陈楸帆
何平 陈楸帆
何平:我是先读了一系列短篇小说,再读你的《荒潮》,我的阅读印象中,《荒潮》放在同时代中国文学中是一部堪称宏大的巨制,虽然《荒潮》也会有时被你狂野的想象和过于显豁的现实批判拖累,但不妨碍它是近年一部重要的汉语长篇小说。以《荒潮》为例,我们能感到“科幻文学”和传统意义的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隔阂。《荒潮》在传统意义的中国当代文学界并没有引起与之相称的评价,我不知道这部作品,在科幻文学界的反响如何?
陈楸帆:感谢何平老师谬赞,《荒潮》由于是长篇处女作,现在回头看来很多地方还是有笔力不足与思想幼稚的毛病。在国内主流文学界评价不多,李敬泽老师曾经在媒体上推荐过。反倒在海外比较文学界里得到了一些关注,一些学者将其作为研究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文本范例,从环境保护、后人类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角度进行分析。包括Wellesley College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老师在许多篇关于中国科幻的论述中都有着重谈到敝作,9月份在昆山杜克(DKU)会有一个学术工作坊,由后人类主义学术泰斗N.Katherine Hayles主持,她也将《荒潮》作为此次工作坊研讨的核心文本。《荒潮》被刘慈欣老师称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并获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花地文学奖金奖等数个类型文学奖项,在国内文学界被当作“科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这一风格也是由我在2012年星云奖上首次提出的,最近北师大姜振宇博士正在作这一题目的博士论文。《荒潮》明年将会由北美最大的幻想文学出版社TOR出版英文版,译者也是刘宇昆,编辑是本届雨果奖得主、《三体》三部曲编辑Liz Gorinsky,后续几种主流语言版本都将出版。可以说,《荒潮》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幻文学界还是获得了颇多荣誉与认可。
何平:我们也许可以从《荒潮》看整个科幻文学。近年,特别是今年,传统文学界在很大的规模上悦纳科幻文学,甚至今年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以科幻文学为主题,但我看到的更多是表面的热闹,你作为很多活动的受邀者和参与者,你的感觉是怎样的?真的,科幻文学的春天来了吗?
陈楸帆:我已经连续数年参加了许多主流文学界邀约的活动,一个直观是谈论科幻、研究科幻包括开始创作科幻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科幻文学这种长期处于边缘化、被低幼化、标签化的文类来说肯定是一件好事情。但不得不说,在主流文学界与科幻文学界之间的“文化隔阂”依然颇为厚实,对于科幻文学的误解与偏狭也一时难以完全扭转,许多研究者将主流文学的评判标准与理论工具照搬到科幻文学分析上,却没有达到特别好的效果,这些都是有待双方进一步交流融合提升的。比较让人欣慰的是,主流文学界向大众推介科幻文学,让许多原先不看科幻或者对类型有偏见的读者开始摘下有色眼镜,开始阅读科幻小说,甚至喜爱上科幻,形成一股新的文学风潮,这对我们科幻创作者是莫大的鼓励。这个春天刚刚发芽,期待春风能够吹得更暖,让春意更盎然一些。
何平:我还注意到,很多和科幻小说无关的小说家,也开始在小说中植入“科幻”,这种植入常常是“硬”植入,但我并不看好“科幻”成为简单的小说技术。在我看,“科幻”从根本上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想象世界的方式,而不只是一种写作的小技巧。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陈楸帆: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个人也非常关注主流文学界对科幻的“跨界”,并且拜读了其中许多作品。坦白讲,大部分都只是将科幻作为一种表面的、刻板的外衣“硬”套在一个纯文学的躯体上,效果并不理想,有一些点子在科幻小说里已经被探索过许多遍,而呈现在主流文学作品中没有新奇之意,反有陈腐气息。科幻写作的本质是一种基于“What if”(如果……那么……)基础上的思想实验,是从对现实世界规则的某种改写,进而推演其如何影响到社会、人性乃至文明本身。最为优秀的科幻如《三体》《你一生的故事》《黑暗的左手》等会让人读完有三观颠覆之感,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冲击,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思维逻辑,是以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价值坐标,并不是单纯技巧所能达到的。
何平:王德威将新的二十一世纪前后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科幻热”进行比较,但我觉得这种比较是要谨慎的,因为两个时刻的中国科幻小说共享的不是一个世界文学。换句话说,我觉得当下中国文学真正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写作只有科幻小说。我读中国科幻小说,强烈感觉中国科幻小说的“世界性”。
陈楸帆:我觉得科幻之所以较其他文学类别更容易具有世界性,或者说更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流通,引发认可与共鸣,便是在于其建立在一个基于科幻文学发展史上的想象共同体,它所探讨的议题、价值观和情感,是跨越了民族、人种、语言和文化上的种种差异,是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出发点的文学。打个比方,我有许多小说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得到许多海外读者的积极反馈意见,我写北京的雾霾,会有来自美国中部地区居住在环境污染城市里的读者感同身受;我写大学生失业所带来的个体价值感消失,日本读者甚至给了我一个票选的奖项。这些在我写作之时,都是非常非常中国化的议题,但它由于具备普世性的价值与情感,因此能够打动世界范围内的人,这点我觉得是科幻的奇妙之处。
何平:但你的小说几乎所有出发点都有着“中国问题”。我不知道你是选择了科幻小说,而自然而然地在写作中思考中国问题,还是预先有反思中国问题的冲动,只是科幻小说又可以恰当地承载你需要的思考?因为科幻小说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先天自带问题意识,特别对人类未来问题的思考。
陈楸帆:科学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巨大“乌托邦”幻想中的一个,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走向反对科学的一面,科学乌托邦复杂的一点是它本身伪装成绝对理性、中立客观的中性物,但事实上却并没有这样的存在,科幻就是在科学从“魅化”走向“去魅”过程中的副产物,借助文字媒介,科幻最大的作用就是“提出问题”。同样的,我不认为当代中国和存在于古代典籍里的中国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也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想象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在不同人的眼中又折射出许多个棱镜般千变万化的切面。我没办法给出一个正确答案,说什么样的作品是具有中国特色或者价值观,我只能說,每个作者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并真诚地去提问、想象和书写,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包藏有一个中国的影子。
何平:你的《未来病史》几乎是当下科幻文学的“科幻指南”,差不多所有的科幻小说都共有你“未来病史”的“科学”,但你的小说重点在人类的“未来病”,无论是你的《荒潮》《鼠年》《动物观察者》《造像者》《开窍》,还是你这次给我的《美丽新世界的孤儿》也不例外。读你的小说,就是读人类,也是中国的“未来病”史,你是有意让你的小说集中在“病”吗?
陈楸帆:对于我而言,在自觉与不自觉间,我在创作里确实贯穿着这样的一个母题/主题/意象:异化。它其实包括了几个层次上的含义:生物学上的变形、疾病或变异;心理学上的疏离、扭曲、分裂;社会体系/人际结构上的隔离、对立、变迁。以上三种层次的异化经常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以单一或组合的形态),而技术变革往往作为其诱因或结果出现。当我们谈论“病”的时候,首先必须定义“正常”,这是一个会随着时间、地点及针对人群而变化的相对概念,比如对于穴居原始人来说,现代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无法理解的,而一个纽约客也会将同时期非洲部落风俗视为病态,即便是同在纽约生活的现代人,也会因为民族、肤色、信仰、政治立场或者性取向的不同而将异己者视为“异常”。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发展加速度的时代,异化将会愈加频繁地发生,人类的认知更迭交替之快,异常会变成正常,被我们接受、习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本雅明笔下背向未来,被进步之风吹着退行前进的天使,我们愿意看着过去,因为那是我们所熟悉,感觉安全舒适的世界。我们需要厘清什么是人?人类的边界在哪里?人性究竟是所有人身上特性的合集还是交集?究竟一个人身上器官被替换到什么比例,他会变成另一个人或者说,非人?这种种的问题都考验着我们社会在科技浪潮冲刷下的伦理道德底线,而科幻便是最佳的引起广泛思考的工具。
何平:世界科幻小说,从我的个人阅读趣味上,我喜欢波兰的莱姆。在我看,他的小说是科幻,也是文学。但当下中国科幻小说许多往往是以半生半熟的“科”的名义的“幻”,并无多少“小说”。我觉得如果要在“文学”上确证“科幻小说”,其实不能过于强调科幻小说的特殊性,至少要在人性、历史和现实、人类的命运、小说的形式和语言等维度应该确立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我认为在当下与强调科幻小说的科学性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意识到科幻小说也是文学。你的小说在这些维度其实是提供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范例的。对文学性的追求,这是不是和你的专业背景有关系?
陈楸帆:我也非常喜欢莱姆,同样的,在科幻小说里,我也更偏爱那些文学性强的作者,比如Ursula K.Le Guin(娥蘇拉·勒瑰恩),James Graham Ballard(J.G·巴拉德),Ted Chiang(特德·姜),Aldous Huxley(阿道司·赫胥黎),韩松等等,这也许跟我中文系的背景相关。我不认可那种认为科幻小说就不需要文学性,不需要塑造人物的观点,同样的,我认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浪潮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它将许多主流文学作家与技法带入科幻,拓宽了科幻文学的光谱,事实上这一运动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上的遗产却传承至今。我认为科幻应该更加自觉地在形式与语言上去进行大胆试验和突破,它是面向未来的一种文学,你能想象一种未来的文学还在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地摊文学语言进行书写吗?因此我认为许多科幻小说的问题在于过于受限于“科幻”的模式和套路,而却没有在小说上语言上下功夫,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寻求突破的方向。
责任编辑 杜小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