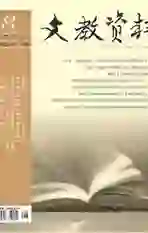卖给黄金的殖民地女人
2017-06-09王晨韵
王晨韵
摘 要: 梁太太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思想影响的女子,她在世俗的男权社会中找不到出路,为追求金钱而堕落变态,将自己和侄女都埋葬在婚姻的坟墓里,她们的婚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
关键词: 殖民地 封建思想 资本主义思想 女性婚姻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人们主要将目光投射在主人公葛薇龙身上,然而小说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梁太太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像她这样性格病态的贵妇常常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梁太太为了金钱牺牲青春和情欲,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头子,守寡后又疯狂地弥补自己失去的情欲,是一个曹七巧式的人物。她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葛薇龙在她恶意的教唆下一步步堕落成和她一样的人,和她共同埋葬在山顶的那座“皇陵”中。
一、惡毒的美貌
张爱玲曾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袖珍戏剧。”“个人住在个人的衣服里”。我们可以通过张爱玲对梁太太的外貌和服饰描写分析这一人物:“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坠未坠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那面网足有两三码长,像围巾似的兜在肩上,飘飘拂拂。”①
梁太太作为一个交际花,她与乔琪乔约会的打扮既不鲜艳又不暴露,相反她穿了一身黑,而且用面网将自己遮了个严严实实。梁太太因拜金而嫁给富商做姨太太,为他守寡穿黑色是不太可能的,有可能的是梁太太即使热爱交际,也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一样,想把自己给封闭起来,隔离起来,以获得一些安全感。而初尝爱情的葛薇龙就不会这样打扮,她穿的是“姜汁黄朵云绉的旗袍”、“瓷青薄绸旗袍”、“白裤子,赤铜色的衬衫,洒着锈绿圆点子,一色的包头”,对比可见在风月场上久混的梁太太未必将乔琪乔的爱情看得重要不可,乔琪乔只是她众多情人中的一个,她的内心更坚硬冰冷,而薇龙对乔琪乔确实一往情深。这就说明为何梁太太可以联合乔琪乔算计葛薇龙,愿意让乔琪乔和薇龙结婚,而薇龙为了乔琪乔的爱情奋不顾身地将自己卖给了他俩。梁太太一身黑衣,面网点缀着蜘蛛,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剧毒的“黑寡妇”蜘蛛,推测她是一个阴险毒辣之人。那绿宝石蜘蛛又像泪珠,又像青痣,隐含着梁太太的辛酸——一个流落风尘、孤苦无依的老女人,作者对她也是有些许同情的。
在面部特写中,梁太太的脸更是形同僵尸。“白腻中略透青苍,嘴唇上一抹紫黑色的胭脂,是这一季巴黎新拟的‘桑子红。薇龙却认识那一双似睡非睡的眼睛”。紫黑色的口红就像鲜血刚凝,仿佛要吃人一般,显得恶毒刻薄。眼睛似睡非睡,流露出媚态,缺少生气和活力,全然是对生活的不屑和颓丧。她是一个留存于过去的旧人,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是一个不会向往美好未来的人。
作者还在细节上着力刻画了梁太太的指甲:“两只雪白的手,仿佛才上过拶子似的,夹破了指尖,血滴滴的。”“一面笑,一面把一只血滴滴的食指点住了薇龙。”手指血滴滴的梁太太仿佛是一个杀人的恶魔,把食指点住薇龙时,就像将魔爪伸向薇龙,让人不禁感到惊心动魄、万分恐惧,纯洁的少女薇龙就在梁太太两面三刀的算计下一步步走进了堕落的深渊。
二、不中不西的居住环境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性格。小说大多借葛薇龙的眼睛观察梁太太的住处。葛薇龙第一次去梁太太家,她对这个新环境的印象是最新鲜直观的:“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卐字栏杆,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这个园子是突兀的,是孤立无援的,从园子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梁太太的居住环境是荒凉的,没有生气的,与周围格格不入的,也没有任何邻居,可以推断房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孤僻的、寂寞的、脱离时代的人。正如葛薇龙所想:“她看她姑母是一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梁太太的花园不够美丽芬芳。园子里只在草坪的一角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墙内的春天只是虚应个景儿,然而墙外是“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园子内布置谨严,花床疏疏落落,刻板少有生气,而园外是截然相反的另一个世界,是充满勃勃生机的。在这样的对照反差下,借环境描写显示出住在园内的梁太太人生的春天已经消逝,留下的只有荒凉的心境,她不像其他主妇那样对生活充满热情,积极打理装饰自己的家园,而园外的葛薇龙正是青春年少,如盛放的野杜鹃一般热烈,但是这里埋下一个伏笔——她最终走进了园子,成了一株花容惨淡的小杜鹃。
作者张爱玲说:“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这可做整篇文章环境描写的中心句。故事发生的大背景是在新旧交替的中西结合的殖民地香港,鱼龙混杂,封建思想残存,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又腐蚀着人们的心灵,梁太太和葛薇龙就是时代异化下的产物,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随波逐流,渐渐地为追求欲望而堕落,燃尽自己的一炉香。
作者在描写梁太太的典型殖民地式的房子时连用三个表示转折的连词突出梁太太既中又西,不伦不类,审美鉴赏水平很低。“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当地铺着红砖,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梁太太的房子色彩鲜明,奢侈豪华,为了迎合她的“朋友”的喜好,布置得花花绿绿,兼有一些东方式的小摆设取悦他们,但是缺少房主梁太太的个性喜好,从侧面反映出梁太太看似潇洒的生活其实并不自主,是依附于他人存活的。
薇龙还看到“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待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暗喻梁太太是一个蛇蝎美人,正在暗地里计划着对薇龙下毒手。
我们可以从梁太太的私人空间——小书房的布置近距离地窥测她的内心,她虽然穿西装、吃西餐,处处是西式作风,然而她骨子里还是一位封建社会的女子。“一引把她引进一间小小的书房里,却是中国旧式布置,白粉墙,地下铺着石青漆布,金漆大案,大红绫子椅垫,一色大红绫子窗帘”。第一,梁太太的房间布置得十分豪华,可以看出梁太太对于金钱和奢侈生活的极力追求;第二,房间配色浓重深沉,带有几分凄艳,令人感到压抑逼仄,可见梁太太内心的阴暗;第三,大红大绿对比鲜明,显示梁太太内心的躁动,尤其是大面积运用的大红色表明梁太太作为一个寡妇,并不是清心寡欲的,而是内心充满了汹涌的波涛,莫非她想做一个新娘子?
在葛薇龙的视角里“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薇龙觉得自己是《聊斋志异》里的书生,上山去探亲出来之后,转眼间那贵家宅第已经化成了一座大坟山”。梁太太家很有些鬼气,梁太太仿佛一个阴森的老妖魔,不仅自己葬送在这一个由金钱砌成的吃人不吐骨头的坟墓中,还圈禁控制了几位年轻女子为她“弄人”。梁太太是世俗社会中的受害者,将吸血吃人的傳统延续下去,继续迫害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让她们成为下一任吸血者。
在梁家举办宴会时的一段外景描写中:“梁家那白房子粘粘地溶化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只有小铁门边点了一盏赤铜攒花的仿古宫灯。”既有富有西洋色彩的玻璃窗和薄荷酒,又有仿古宫灯,构成了一幅迷幻的诡异的畸形的场景,梁太太之流本是生长在封建社会里的人物,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潮流的侵袭,终日陶醉于灯红酒绿和醉生梦死间不知今夕何夕,他们如鬼魅般生活在山间的迷雾里,看不见人生的方向和意义。他们效仿英国人举办园会,但只是东施效颦,装模作样。“草地上遍植五尺来高福字大灯笼,黄昏时点上了火,影影绰绰的,正像好莱坞拍摄《清宫秘史》时不可少的道具。灯笼丛里又歪歪斜斜插了几把海滩上用的遮阳伞,洋气十足,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作者将此时的场景比作清宫,更显神秘,丫头老妈子也都拖着油松大辫,作红楼梦式的打扮。这些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们,还继续在香港这一殖民地继续做贵族梦,像消散不去的旧社会的阴魂。作者刻意创造了腐朽淫糜的环境,更显得梁太太之流的麻木愚昧。关于西方文明他们只学了个影子,模仿一些奢侈享乐的生活习惯罢了,但思想仍旧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谈不上半点民主和科学上的进步。
三、流露传统观念的语言
梁太太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的人,骨子里还是封建的,她思想的矛盾性体现在语言上。梁太太一见葛薇龙劈头便问道:“葛豫琨死了吗?”在痛骂哥哥中可见其对娘家的怨念极深。梁太太又极力想打发葛薇龙离开,说:“你快请罢,给他知道了,有一场大闹呢!我这里不是你走动的地方,倒玷辱了你好名好姓的!”可见梁太太对自己名声不好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对娘家也心存芥蒂。梁太太是作风大胆泼辣的人,敢于为了追求富足的生活,不顾家庭阻拦一意孤行嫁给富商做姨太太,但是她并非是一个视封建传统道德规范为无物、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人,而是一个表面华丽光鲜,内心虚空的旧式女子,她所谓的女人的幸福只是靠畸形的婚姻谋取金钱,她不具有进步性,是诸多生活痛苦的世俗市民中的一个代表,挣扎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中,终究摆脱不了从小对传统道德理念耳濡目染,在别人如葛薇龙触及她的痛处时反应十分激烈。
她教训葛薇龙说:“等你到了我的岁数,你要有谈恋爱的机会,才怪呢!你看普通中等人家以下的女人,一过三四十岁,都变成了老太太。我若不是环境好,保养得当心,我早就老了。你呀——你这么不爱惜你的名誉,你把你的前途毁了,将来你不但嫁不到上等阶级的人,简直不知要弄到什么田地!”梁太太对自己嫁了个阔人这一点是得意扬扬的,她以青春和婚姻换取金钱,是张爱玲笔下诸多女性的共同点——没有谋生的能力,希望嫁个有钱人,依附丈夫过上好日子。她将自己的这个观点灌输给葛薇龙,将本来颇有些独立思想的葛薇龙调教成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花瓶。梁太太说:“一个女人,顶要紧的是名誉。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分别。现在脑筋新一些的人,倒不是那么讲究贞节了。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这一类的闲话,说得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望只有更高,对于你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妨碍。”梁太太认为女性的贞节并不是十分重要,但是嫁得一个好人家终究是不变的,只是时代变了,方法也随之变了而已。她的思想含有嫁得好人家的封建传统婚姻观念,又有西式的更开放的性观念,拿肉体用作谋求终身幸福的交易。
四、与曹七巧一类的怨妇
梁太太与曹七巧是有相同之处的。她们同样为了钱而将自己的一生抵押给了畸形的婚姻,曹七巧嫁给了患骨痨的残疾人,梁太太嫁给年老的富商做姨太太,同样因为追求金钱而丧失了青春和爱情,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足,过后又疯狂地追求情欲以弥补自己的缺失,最终性格变态扭曲,将自己遭受的迫害施加在后辈身上。曹七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在自己被践踏被残害后又将自己的女儿、儿子劈杀。长白的妻妾都死了,长安的婚事也落了空,两兄妹最终都成了吸鸦片的浪荡子。梁太太出于变态的报复心理,一手将葛薇龙囚禁在自己的“皇陵”里,把原来一心向学的进步青年毁成欢场卖笑的高级妓女。金刚钻镯子与黄金枷锁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时迟,那时快,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疾便和侦探出其不意地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黄金、钻石是枷锁,是手铐,一旦接受了,沾染上了,便不可自拔地陷入了金钱的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梁太太和曹七巧不仅自己被金钱囚禁,而且亲手打造了一副手铐,把自己的后人牢牢锁住。《金锁记》的结尾说:“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梁太太的侄女自然也学会了梁太太的手段和本领。
梁太太的悲剧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她自己踏进豪门的坟墓,而她的侄女也重复了她的求财之路,悲剧从踏进豪宅的那一刻开始。但她们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中,女子的自主权利很少,唯一的途径就是嫁人。“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薇龙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然而找到一份工作对她而言还是困难的,更不用提梁太太了。“在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里,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男性世界的精神价值体系牢牢地掌控了女性的内心世界,让她们将一生的悲欢交由男性来导演,并不自觉地将自己矮化,多是从男性观照女性、视女性为性玩物的视角看待自我,将自我异化为用身体取悦男性的工具”②。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传来的拜金主义之风吹得人心浮躁,一心想着追名逐利,不管是出身名门还是小门小户的女子在男权社会中都少有求生的机会,只能拼了命地将自己贱价出售,换取饱浸泪水的金钱,依附男性生存。她们缺少自力更生的能力,无法摆脱婚姻家庭的禁锢,因此只能忍气吞声,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娜拉出走后该怎样?“娜拉出走之后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出走意味着女性摆脱男性束缚,走向社会,走向独立,而鲁迅对当时无法独立的女性命运斩钉截铁地预测:‘正是由于女性自身的不彻底性——她们反抗得不彻底,出走得不彻底,所以命运只能如此,只能充满悲剧色彩。”③张爱玲没有写激烈的起来反抗的英雄人物,她更多地展现被时代悄无声息吞噬的不知情的人性悲剧。《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金锁记》里的曹七巧、《第二炉香》里的蜜秋儿太太、《半生缘》里的顾太太等一系列家长形象,传统女性意识占了她们的大半个头脑,既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又是害人者,作为女性,更加带有一股子阴气,将年轻的新生命一一掐死。
梁太太一类封建毒妇形象的塑造与张爱玲自身的经历有关。张爱玲生长于一个旧式封建大家庭,父母离婚,父亲和后母对她进行生理和心理上的虐待,曾因与后母发生口角而被父亲责打囚禁,父亲的遗少作风让她痛恨,张爱玲与母亲也有罅隙,作为一个接受新思想的女性,张爱玲对这种封建式的家长做派十分憎恶。之后爱情婚姻的不美满,社会舆论的压力,使得张爱玲对于真诚纯洁的爱情失去幻想,转而暴露了一出出与金钱交织的肮脏的情感交易,写下了一幕幕人财两空的悲剧。梁太太这个角色为张爱玲之后写曹七巧做了一次预告。
注释:
①张爱玲.张爱玲全集[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②周娟.漂若浮萍,韧如劲草——浅析张爱玲《连环套》中霓喜的人物形象[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4(6).
③何宗龙.张爱玲小说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