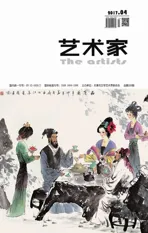自然机器
2017-06-07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郭 峰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庞辛森

1983年出生于河南永城市,2005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获学士学位,2012年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版画系,获硕士学位。作品多次参展各类美展并获奖,2017年在北京举办“自然机器”庞辛森个展。
庞辛森的作品,暗示着想象或重新理解自然的可能。这种暗示,可能不是艺术家本人从一开始就直接呐喊而出的。但散布于作品中的线条、图像、阴影、遗留和连接则在其创作过程中逐渐交织成一条线,诸多刺点的连缀。它占据着每一幅作品,同时又将一幅作品变成另一幅作品的扩展。因此,某种程度上,从倒转自我的“在世”处境的《自我反问》(2002年)开始至今,庞辛森的创作呈现出了一种颇为不同的形态,又互相延展,时常返回到一种倒转之中。正是这种极其当下的、艺术家本人纯身体性的倒转,对人与周遭之间位置的倒转,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人的自然或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倒转,才使得重新理解的暗示成为可能。
如何想象自然?如何理解或重新理解自然?如何在当代技术经验的托架(Gestelle)之上重新确立一种对自然的认识?人和自然的边界在何处?
在庞辛森这里,可以发现类似的一系列问题,或者其中的关键元素。它们基本是以混杂的样态被抓取、删减、复制、交叉在一起的。换句话说,艺术家如同一个肆意的新分类学家,他诉诸一己的观察和想象,试图重新发明世界的逻辑秩序,重新摆置动物、植物、人、山、水、兵器甚至星球,进而重新发掘一种“直接兴趣”——作为艺术家试图沉浸“在埋藏万物秘密的自然怀抱和创造的原始沉淀之中”的兴趣。
这种对自然的“直接兴趣”是必要的。正如保罗·克利曾断言:“对艺术家来说,与自然对话始终是必要条件。”因为在他看来,作为人,艺术家本身就是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上、宇宙中的生物。在这里,艺术家、自然、对话、必要条件,由这四者勾连起来的判断,表面上只是围绕着艺术家和自然的关系展开,却同时将判断的触角深入其他两重关系之中。这两重关系,便是艺术创作三角的另外两个端点:艺术家与创作的关系,创作与自然的关系。

庞辛森《理想国之一》77cm×57cm 丝网 2015年
很大程度上,以艺术家(作为人,或者说作为自然之部分和对话者)、创作(作为艺术品,或者说作为技艺之物和模仿物)和自然(作为起源和整体,或者说作为原则和本质)的三角来思考艺术,并不新鲜。或者更直接地说,对自然的“直接兴趣”颇为陈旧,却总是被召回。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家园,艺术在离家或者归家的运动中展开,艺术作品散落在途中,艺术家则是永恒的羁旅者。正如克利所言,这一切或是因为人无法摆脱自己是自然之部分的命运,即使在当今仍旧如此。尽管人已经在与自然的大规模作战中获得了某种短暂的、虚假性的胜利并沉浸在持续的自我肯定的喜悦和摧毁家园的焦虑和耻辱之中。
在庞辛森这里,我们或许可以说,某种对自然的“直接兴趣”以不同的方式被有意或无意地召回了。换句话说,庞辛森创作的兴趣,某种程度上可以纳入这种对自然的“直接兴趣”的古老潮流中,但在召回或者说试图召回的那个瞬间,他又寻得了一个早已存在的支点:个人性的倒转。倒转意味着一种非破坏性的颠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没有对自然的沉静观察,没有对自然的直接援引和求助,没有对自然的直接摹写,这一切在当今似乎都无法展开了。有的只是对这一切无法展开的承认和接受,以及由此而得以实施的某种扰乱、摆置、重构想象秩序的举动:几何机器、军事机器、居住机器被彻底安插在自我运动的自然机器之中,它们与山水、动物、植物、作为自然之部分和机器之部分的人共存于世。在《理想国》系列中,这种安插已经如此昭彰,而在《自然空间》系列中,重构的意图则更加集中地显现了。

庞辛森《强者的眼泪》100.5cm×61cm 木板综合 2017年

庞辛森《理想国之五》77cm×57cm 丝网 2016年

庞辛森《理想国之六》77cm×57cm 丝网 2016年
一种由个体性的倒转而生发出的重构,既是对长期以来的“直接兴趣”的延续,又是对之的倒转。在这个意义上,庞辛森所想象的“自然空间”,似乎是一种全新的自然。在其中,自然与机器实现了自然的共存,它们不再是观念史上互相争夺、互相角力、互相驱逐的两者,也不再是实践层面互相侵占、互相啃噬、互相破坏的两者;在其中,自然与机器相互渗透,艺术家既没有沉静地崇拜或敌视前者,也没有狂热地赞颂或鞭笞后者,他甚至不需要对两者的关系做任何思考,自然与机器就如其所是地互相渗透着、互相穿插、互相以彼此为托架。或者更极端地说,在这里,自然机器成为了可能。
这种可能性,提示着一种不再激烈的、不再二元化的想象方式。时至今日,能否同时将制作(poiēsis)、技艺(technē)与机巧(machenschaft)纳入对自然(physis)的理解或想象中?能否凭借某种当代的机器经验和自然经验将自然与机器直接连接起来?究竟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机器?二者之间能否存在一种连接状态?或者说,自然机器,庞辛森作品中所暗示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对自然和机器的双重折叠,是否可能?
很长时间以来,自然,在观念上和实践上,都面临着某种跌落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耻辱”。因此,当保罗·克利强调某种对话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时,本雅明哀悼的恰恰是对话性的消逝。夏日午后人与“地平线上的山峦起伏或一根洒下绿荫的树枝”之间的“悠闲”的“观察”关系被打破了,因此人无法再呼吸到山川树木的氛围(Aura)。这既是对洪堡意义上“面对自然时所体验到的自由之乐”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备受威胁的回响,也是对康德意义上“对自然的美产生直接兴趣”的某种反射,或许更是对海德格尔意义上“技巧”之反思的继续。
问题是,倘若我们被重新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倘若自然被重新赋予了一种别样的、倒转的“直接兴趣”之后,跌落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耻辱感”和“哀叹”是否也会被倒转为相反的趋势和相反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