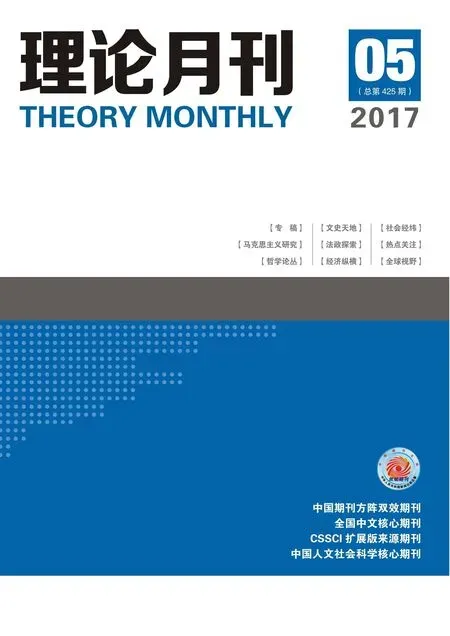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2017-06-05代孟良
□代孟良
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代孟良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香港999077)
在美国,学者对刑事错案的研究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其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方法的特点与趋势。目前随着我国刑事错案的不断曝光,促使该主题成为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成果涌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从刑事错案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层面对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对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进行评述,发现目前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与之相比,理论和方法方面还略显不足。因此,对刑事错案的研究在理论上应该继续加强,在方法上应该将多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刑事错案的研究,藉此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
美国;刑事错案;研究现状;研究方法
1 导论
目前普遍认为率先开展刑事错案研究的是美国法学教授爱德华·博查德(Edward Borchard),他于1913年就在美国的《刑法与犯罪学期刊》上发文进行了探讨,并且于1932年在其专著中——《被定罪的无辜者》(Convicting the Innocent)——对当时盛行的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即无辜者不会被错判。通过对65起案例的分析,他探讨了影响这些错案的原因并提出了补救的方法[1]。利奥(Leo)和古尔德(Gould)指出博查德的研究意义在于从是否存在错案的研究开始转移到为什么会存在错案以及如何进行纠正方面[2]。至今,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该领域已经产出了大量的成果,不仅法律学者,而且社会学家、犯罪学家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赫夫(Huff)等人认为大部分刑事错案并不是单一的原因导致[3]。相反,是多种原因相结合而致,比如,错误的目击证人辨认,虚假供述,无效的辩护,种族偏见等等。研究表明,由于刑事司法制度的缺陷,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于刑事错案[4]。的确,刑事错案的存在具有不可争论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学者利奥对刑事错案的研究进行了反思,特别是方法上的反思[5]。他指出应该实施更精密、更系统以及更有见地的犯罪学研究,而且要跳出目前单一的叙述研究方法(Narrative Methodology)。
鉴于此,本文主要从刑事错案研究的理论现状和研究方法为切入点,藉此回顾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特别对采用社会学方法的研究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对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进行述评,并重点关注样本的筛选标准和来源。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与美国相比没有突破传统的法律研究方法,而且还局限在法律学者当中。因此,本文提倡将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我国的刑事错案研究,同时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对刑事错案展开分析探讨,以此能够更好地理解我国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并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2 美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
2.1 多角度的探讨
其他学科的理论应用不但能够丰富本学科领域的研究,而且也能够拓展其研究视野。美国学者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也构建二分法对刑事错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尽管二分法的分析把复杂局面简单化,但正是二分法能够建立分析的基础,让我们能够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
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是罗福奎斯特(Lofquist)的研究,他首先指出目前对刑事错案的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分析[6]。因此他从组织结构理论出发,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分析理论框架:理性选择或机构理论与组织过程或结构理论。前者强调个人雄心、组织规划、外在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成本计算。而后者是众多决策者和更大环境的复杂互动的结果。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分析,结合戴尔·诺兰·约翰斯顿案(Dale Nolan Johnston,涉嫌谋杀,一审被判处死刑),运用上述理论对该案的侦查、审判等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每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有所不同,虽然案件的结果是司法组织的运作产物,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下,公检法三机关通常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因此,基于组织结构理论来探讨理论上与实际中的公检法的运行情况,不仅能够拓展该理论,而且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早在40多年前,帕克(Packer)就已开始研究刑事诉讼到底是一个高效还是低效的社会控制工具,为此他提出了犯罪控制模式(crime control model)和正当程序模式(due process model)[7]。前者倡导打击与控制犯罪是最重要的职责,在此模式下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逮捕和高效率的定罪。而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打击更是取决于刑事司法机关的速度以及案件的终局性,反过来这种高效率的速度带来随意性和一致性。侦诉审三个阶段的随意性频繁可见,而一致性导致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传送带(assembly-line conveyor),司法机关对打击犯罪的认同,目标上的一致性,构成了犯罪控制模式的显著特点。相反,正当程序模式的理念是预防和消除错误到最小程度,强调程序至上,保障当事人诉讼法上的权利,而控制模式接受这种错误的出现,或者说是为了安全所付出的代价。反观我国之前实施的“严打”政策,强调从重从快、联合办案,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因此有学者把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形容为做饭-端饭-吃饭[8]。在犯罪控制模式下错案的产生不可避免。弗罗斯特(Frost)指出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具体个案相应减少,同时人手不足,缺乏专业训练常常造成侦查工作不能正常展开。打击犯罪的压力越大,办案人员也就越具有攻击性,错误也就更可能发生[9]。
洛奇(Roach)从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和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即从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出发来探讨刑事错案的一些常见原因[10]。该模式的分析基础源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立场而对司法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作者认为两者各有优劣,比如在对抗制中,强调程序公正,强调充分的律师辩护,以及法官的消极审判地位。相反职权主义依赖于法官的积极主动介入,其中一个特点是不注重证据的展示,也不重视对证据的交叉质证,这种模式容易导致未审先判(pre-judgment)。作者表明应该将两种制度相结合,进行互补,这样更好地预防刑事错案。
另外,李辛格(Risinger)指出人们在思考刑事错案的时候会陷入两个阵营:佩利派(Paleyites)和罗米利派(Romillists)[11]。在文章中作者分析了两派各自的观点,18世纪功利主义者威廉·佩利牧师(Rev.William Paley)认为错判是不对的,但是他消极认为这是人类制度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向公众提供安全,维持执法的代价。因此不应该采取行动来避免错案的发生,否则会造成社会混乱。关于这一点,到底是任其发生还是防止发生会造成社会失序混乱,显然是矛盾的,通过良好制度的设计减少错案理应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社会正义,而不是这种保守观点所主张的任何改革都达不到预期目标。另一阵营罗米利派源于19世纪改革家塞缪尔·罗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的倡导,他对刑事错案深恶痛绝,提倡改革以此更好地保护无辜者。佩利派给这一阵营贴上愚蠢感伤主义者(soft-headed sentimentalists)的称号,相反罗米利把对方贴上铁石心肠的老顽固(hard-hearted troglodytes),认为他们反对改革并对无辜者漠不关心。但是作者认为两个阵营都没能很好地处理刑事错案的严重性问题,事实上目前的法律制度似乎是在佩利派控制下运作,旨在维持审判的整体和终局性。我们认为尽管没有完美的制度,但是通过合理的设计从而达到减少错案的发生是可行的。
2.2 多方法的运用
利奥和古尔德认为社会学方法能够更精准地挖掘刑事错案的多因素本质和复杂原因这一现象[12]。他们认为叙述研究方法最明显的缺陷就是过度简化了因果关系。而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诸如,实验、田野观察、访谈,能够得到有效以及可信赖的研究结果。而这些都还是法学研究比较缺乏的方法。根据他们的分类,包括聚合案例研究(aggregated case studies),对照比较样本(matched comparison studies)以及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本文着重讨论前两种。
2.2.1 聚合案例研究。首先,聚合案例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大数据、大样本为基础,这是得以开展研究的前提。贝道(Bedau)与拉特勒特(Radelet)[13]最先以此方法对刑事错案进行了研究。他们以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为研究对象,共搜集350起案例,其中23起案例的当事人已被执行,时间跨度从1900年到1985年。德利芩(Drizin)和利奥[14]则搜集了发生在1971至2002年期间的125起案例,其中55%发生在后10年。赫夫(Huff)、拉特纳(Rattner)和萨格林(Sagarin)他们3人则建立了一个205起案例的数据库,不过他们的样本主要来源于其他学者研究中的数据[15]。在另一项研究中,格罗斯(Gross)、雅各布(Jacoby)、马西森(Matheson)、蒙哥马利(Montgomery)和帕蒂尔(Patil)为了探讨现代心理讯问技术在刑事错案中的影响,研究了1989年至2003年期间的刑事错案,共搜集了340起案例,其中263起是因新证据而被赦免,144起由于DNA证据而得以宣告无罪。另外,超过一半已经被监禁10年以上,80%至少5年以上[16]。
其次,在这类研究中,其案例的搜集过程通常都下了一番功夫。贝道和拉特勒特[17]不但检索了自1900年以来的纽约时报、各大文献数据库、图书馆等,而且他们还于1984年通过邮寄信件给47个州的州长和哥伦比亚特区区长,虽然没有增加额外的案例,但也得到了18个回复。此外他们也联系检察长、辩护律师和受害者以进一步获取信息。德利芩和利奥也采用多种渠道搜集数据,包括联系办案律师、查看讯问笔录、录音录像带、警察报告、法院判决等等[18]。当然这些研究并不都是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搜集,格罗斯他们的数据就来自媒体的报道。他们认为由于美国联邦特点,没有全国性的统计[19]。这样不可避免导致统计不完全,而且样本可信性有所折扣。
最后,对搜集的案例采用了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不过都是一些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比如,在格罗斯他们的研究中,伪证方面,涉及警察的伪证报告有5起,24起涉及法医科学家的伪证信息,97起涉及监狱告密者或其他从中获益的人[21]。不难发现聚合案例研究,在样本上通常都很大,而且在样本获得上都利用各种方法获得有用的数据材料。但是在分析方法上则略显不足,大多是百分比这类简单的分析配以案例的叙述。
2.2.2 对照比较研究。正如古尔德和利奥指出对照比较研究能让我们更准确地知道哪些因素在起作用[21]。为何在一些案例中刑事司法制度能够恰当运行,但是在另外的案例中却不能。对照比较研究与上述研究的不同在于研究人员通常设置两组样本,并且提出假设,来寻找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验证影响刑事错案发生的因素。
例如,哈蒙(Harmon)对死刑案件错判的预测因素作了深入研究,设计了两组样本,一组已被释放,一组已被执行[22]。通过定量分析来研究这两组之间的差异。假设下列因素增加了推翻判决的可能性,包括:公诉人、警察的不当行为,伪证,新证据的发现等等。为了检验该假设,作者把搜集到的76起被释放的与被执行的案例进行对照比较研究。为了弥补样本方面的不足,哈蒙随后与罗福奎斯特展开合作,研究了两组真正无辜的死刑被告:被宣告无罪和被执行的。作者试图想知道为什么一些潜在的致命错误未能得到纠正,目的在于识别可能预测案件结果的因素。这次他们共搜集了97起案例,81起被宣告无罪的和16起被执行的。由于因变量的二元性(宣告无罪和执行死刑),他们采用逻辑回归分析,研究表明这些变量是重要的预测因素:伪证、证据、前科、辩护、被告种族。特别指出律师的表现与以后的宣告无罪有显著意义[23]。
这类研究数据的获得通常采用社会学研究中的普遍做法,诸如设计并发放问卷。在哈蒙的研究中他就通过问卷获得,还包括法庭记录等等[24]。另外,除了发放问卷外,学者们也使用各类数据库。例如,哈蒙与罗福奎斯特在死刑信息中心(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筛选符合条件的案例,同时联系办案律师,因为他们最熟悉自己曾办理的案件[25]。此外,格罗斯和奥布莱恩(O’Brien)指出是否是侦查程序引发了刑事错案,他们认为理论上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就是进行一项实验。比如可以随机分配两组刑事侦查,在其中一组使用强制讯问,然后进行比较[26]。不过正如他们所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权进行这样的实验,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
不难看出,在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中,聚合案例研究尽管样本很大,但是在数据的分析上由于没有提出假设,进而分析方法比较简单,其研究结论也显得单薄。相反,对照比较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基于文献分析提出假设,基于因变量的属性采用逻辑回归的分析进而验证假设。同样,数据的获得是关键,样本的大小,数据的效度与信度,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设置,变量的控制等等都需要充分的考虑。
3 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
与美国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相比,由于我国特定的历史原因,使得我们的研究起步很晚①最先开启这方面的研究有张军的《刑事错案研究》,作者长期在司法机关工作,通过调研收集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有李建明的《冤假错案》和陈波、陈正云编著的《刑事错案探究与判解》。。我国真正开始大量的研究还是随着错案的频繁曝光才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依法纠正的呼格吉勒图奸杀案、念斌投毒案、欧阳佳抢劫案等等案例,以及近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提审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案,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引发了学者对该问题的分析探讨。下面就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现状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3.1 研究角度的选取
在这方面,国内学者通常会选取公检法其中的一个环节来进行分析,当然也有全景式的探讨。正如前面提及,刑事错案的发生是多因素的结果,也是整个司法制度及各个机关运作的结果,单单从其中一个环节来看当然有失偏颇。但是各个环节都有其各自的特点,抓住这些特性,从而进行分析仍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和价值。例如,以检察机关为例,李建明认为刑事错案的发生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两个方面[27],而目前大多数是在探讨浅层次原因。但是该研究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由于以一些全国性的无罪判决、不起诉案件的数据和所调查的某市2000年至2008年期间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状况的一些不完全资料作为分析依据,因此数据方面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可避免会导致样本不具代表性,而且自侦案件以职务犯罪为主,包括贪污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等等。正如许多学者在分析错案的时候,这类犯罪比例并不高。同样,基于检察环节刑事错案产生和发展的复杂性,董坤从检察权行使的内外环境和检察官的个体因素两方面对错案的成因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作者提及的检警关系问题、内部运行中的“上命下从”问题[28],这些都能从另外两个机构——公安和法院的实际运行中能看到相应的现象。
另外也有学者从制度层面以及考核机制方面出发。在制度层面上学者都有所论及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是没有建立起各自的分析框架,文章都显得是泛泛而谈,其选择的分析角度并没有多大创新点,也没有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②蔡定剑.冤假错案与人权保护[J].法学,2000(4),认为司法中产生的错案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度设置问题。刘德富、刘路瑶.冤假错案与侦讯程序的法律再造[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1(4),他们认为在诉讼工具主义的法律价值观下,重实体轻程序。邓子滨:使刑事冤案得以昭雪的制度空间[J].环球法律评论,2003(2),认为破案压力使得警察超负荷运转,不可能抓住所有的线索。。同样,考核机制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是否对刑事错案有影响,要经过验证。比如,韩庚提及公安机关的“命案必破”,检察机关的“五率”(指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法院的“结案率”“无罪判决率”等等[29]。认为这些考评指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仅仅以此而下结论似有不妥,如何有推动作用需要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当然,这些指标可以纳入自变量分析③陈洁,秦洁.关于“中国式冤案”的制度性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3(29),指出政法委在案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和作用。刘仁文.冤案是如何酿成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3),指出政法委书记并不懂法(第157页)。诸如政法委、政法委书记等等指标都可纳入自变量的考察之中。。
3.2 以案例研究方法为主
3.2.1 个案研究。在个案研究方面,学者大多选择典型、影响力大的案例作为分析对象。有逻辑严密的分析,也有简单的原因对策研究。比如,陈柏峰从佘祥林案切入,指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被当作奉行原则,审视类似错案会发现各个环节错误频出,认为会导致对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和制度环境的忽略。他认为教条主义的指责与泛道德化话语的盛行贻害无穷,错案的发生是制度的产物,是经济与科学水平相适应的产物[30]。作者的分析讨论似乎如上文李辛格指出的两派阵营中的佩利派,认为错案不可避免,任何超前改革,或者与当下不相适应的改革都是达不到目的的。也有大量研究对赵作海案作了分析,有从诉讼法角度展开讨论的[31],认为法庭审判不独立是错案发生的关键因素[32]。同样,陈永生以赵作海案为分析样本,指出学界对此案的反思不够,认为不仅存在刑讯逼供,还有许多其它问题的存在,并且认为需要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33]。此外,冀祥德对杜培武案、佘祥林案的分析,作者另辟蹊径从民愤角度出发,对刑事司法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如果民愤处理得当也可以纳入正面效应[34]。这些对个案的研究,如上面所述,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不同角度的探讨,还有大量的研究还是传统的原因对策分析。
3.2.2 聚合案例案件。在我国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样本数量总的说来都不大,最少的只有10起案例,最多的也只有137起案例(见表1)。其原因一方面是除了典型案例之外我国并没有这方面的全面统计,另一方面民间的研究中心成立较晚①例如,由伍雷等几名律师发起的“拯救无辜者”洗冤行动于2013年11月20日成立;由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与尚权律师事务所联合发起的蒙冤者援助计划于2014年5月23日启动;以及2014年由徐昕发起的无辜者计划。,数据库的建立还在发展当中。因此要搜集到全面的、详细的、一手的案例有很大难度,这是开展这方面研究面临的一大难题。
首先,在选择样本上,大多数都设置了严格的标准。②在郭欣阳和王佳的研究中,并未发现作者提及样本的设定标准,以及样本来源问题。郭欣阳仅仅提到“笔者收集了137件暴力犯罪刑事错案”(第132页),参阅郭欣阳.暴力犯罪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J].法学杂志,2010(4)。对于后者,何家弘在序言中提到,本书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近50起刑事错案进行了实证研究,参阅王佳.追寻正义:法治视野下的刑事错案[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此外,黄士元以22起案例为样本,从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出发填补了这一角度的空白,不过作者并未提及样本标准问题,参阅黄士元.刑事错案形成的心理原因[J].法学研究,2014(3)。比如,陈永生设定的标准包括:经过侦查、起诉、一审三阶段被认定有罪,最终又证明无罪的案件;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确系被误判有罪的案件;近年被确认为错案的案件[35]。该研究样本不多,只有20起,但确是首次应用聚合案例研究的典范。随后许多学者以此为基础,将样本数量进行了扩充。例如,从侦查角度出发,董坤和胡志风分别搜集到25起和50起案例进行分析。不过在董坤的样本中,有一起是台湾的江国庆案,有疑问的是台湾就此一起吗,显然不能理解作者的筛选标准。也有的案例选取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赵琳琳选取了改革开放前的一些错案进行了分析,比如,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张志新反革命冤案等等[36]。
其次,在样本来源方面,除少数几项研究没有提到样本来源之外,其余的都有所提及。例如,陈永生因为参加最高检和最高法举办的会议所收集到的9起案例。以及胡志风提及自己在基层司法机关中获得的24起案例,另外的案例几乎都来自媒体、网络等[37]。这里对此要保持谨慎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实务部门会根据自身利益筛选案例,同样媒体有自己的利益偏好,案例报道是否客观难以定论。当然这也是上文提及的该项研究大部分学者所面临的难题。
总之,这类案例研究样本方面除了上述的问题之外,选取案例的标准有的似乎并不严谨,比如许多研究中都提到“全国引起一定震动”“具有轰动性”“广受关注”“有较大社会影响”等等模糊的术语,如何客观、科学地界定,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尽管西方学者在研究的时候同样面临一些问题,但是相比而言,我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比如有的研究已经采用邮寄问卷、联系办案人、联系办案律师等等方法①参阅何家弘,何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J].政法论坛,2008(2);Jianghong He and Ran He. Empirical Studie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Mainland China[J].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Law Review,2012(80)。。同时也存在案例与论述脱节,与支撑观点脱节,而且在分析的时候,援引的案例不是样本中的案例。因此有学者指出,案例研究浅尝辄止,过于发挥想象力[38]。

表1 :采用聚合案例研究一览表
4 启示
通过上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美国,学者对刑事错案的研究在理论上已经有所突破,能够提出分析框架,在此之下进行分析讨论;方法方面运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局限于简单的描述性案例分析。纵观我国刑事错案的研究,在理论及方法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案例研究上还没有拓展到比较研究等方法,特别是涉及到案例的来源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保证研究结果可靠性和可信性的前提,案例来源有问题,将对研究成果造成影响。从美国学界的研究中我们得知他们在研究刑事错案的时候,同样面临样本问题,但是已经作出了相当多的有价值的研究。比较而言我们作实证研究的环境还有一定难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研究更需要上升一个台阶,否则就是重复研究,价值有多大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第一,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正如崔敏在《刑事错案:症结与对策》一书的序言中评价道,此书还是纯理论的探讨,停留在应然层面[39]。这也反映出我们目前研究的现状。鉴于此,有人对传统的刑事法学研究进行了反思。指出即使获得了实证数据,也仍然跳不出对策法学的圈子,而缺乏实证的研究以所谓的问题论问题,只会提出虚假的对策[40]。很显然这类研究是经不起检验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对策研究,而是提醒我们的研究应该有所突破和建构。单纯地停留在简单假设,只是在做重复性的工作。依靠冥思苦想式的演绎通常难以获取尽可能翔实的研究素材与推论依据,只能立足于几项“自认为”的核心要素来展开研究[41]。因此,提倡各学科理论之间的结合将有助于推进本学科的发展,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学科,不应该局限于法学理论的研究之中。赵骏特别指出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竞争而是可以合作的[42]。完全局限在法学学科研究内,长期以来处于相对隔绝、互不关心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对我们的研究是极为不利的。
第二,方法上的多元化。目前,我们对刑事错案采用的方法单一,而且没有其他学科方法对此问题进行探讨,正如利奥指出案例研究方法有两个局限:缺乏随机样本和缺乏控制组[43]。这与上面我们所论述的美国学界的研究,有很大差距。正如上面的分析,我们还没有发现采用对照比较研究来研究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的成果。有人指出我国的实证研究在法律领域的运用起步晚,许多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改革通常都未经实证研究即付诸实践[44]。而且目前的研究最大问题在于方法本身的粗疏,简单的百分比描述只是一种数据化的研究而非数理化的研究,应该提升研究方法与技术[45]。也有学者撰文表明,实证研究的受众群体不应该是外来群体,也不应该是外来方法,需要融入一定程度的科学成分,但又认为这种科学成分不能脱离受众的接受程度[46]。实际上,这是作者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种妥协,我们并不同意。相反,目前需要实证的研究,否则相关研究只会停滞不前。定量研究在法学研究中仍是缺乏的,作者指出计量结果报告超出了法律人的接纳度,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法学院的课程设置是不是应该引入相关课程。否则,我们的研究不能和国际直接对话。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实证研究中的伦理问题,郭云忠指出,我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很少[47]。作者列举了7种情形,值得人们思考。比如吵得沸沸扬扬的《中县干部》,对此研究中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的争议②有关《中县干部》中研究伦理的讨论,参阅孟盛彬.参与观察与研究者角色处理的伦理探讨[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实属当下研究伦理缺乏所引起的。
总之,刑事错案的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48]。学者们应该走出现有的法学研究方法,多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诚如郭云忠认为的,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研究之间的相互融通,在其他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开始将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到法学研究领域[49]。特别是在信息公开越来越多的情形之下,实证研究作为发展趋势。我们认为在刑事错案的研究中采用对照比较方法也是完全可行的,不论是无罪与无罪之间的比较,还是无罪与有罪之间的比较,都要求掌握大量的案例,并且在包含详细信息的前提之下,进行讨论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刑事错案的产生原因。
[1]Edward Borchard,Convicting the Innocent:Sixty FiveActualErrorsofCriminalJustice[M]. Garden City,1932.
[2][12]Richard A.Leo and Jon B.Gould,Studying WrongfulConvictions:LearningfromSocial Science[J],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2009,(7):11.
[3][15]C.RonaldHuff,AryeRattnerandEdwardSagarin. Convicted but Innocent:Wrongful Convictions and Public Policy[M].Sage Publications 1996:26,62.
[4]LynneWeathered,WrongfulConvictionsin Australia[J].UniversityofCincinnatiLaw Review,2012(80):1392.
[5][43]RichardA.Leo,RethinkingtheStudyofMiscarriages of Justice:Developing a Criminology of Wrongful Conviction[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2005(21).
[6]William S.Lofquist,Whodunit?An Examina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Wrongful Convictions,in S. D.WesterveltandJ.A.Humphrey(eds.),Wrongly Convicted:Perspectives on Failed Justice[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175.
[7]Herbert L.Packer,The Limits of the Criminal Sanction[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8]He Weifang.The police and the rule of law: Commentary on principals and secret agents[J]. China Quarterly,2007:672.
[9]Brian Frost,Error of justice:Nature,Sources,and Remedi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0]Kent Roach,Wrongful Convictions:Adversarial and Inquisitorial Themes[J],North Carolina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 Regulation Association,2010(35).
[11]D.Michael Risinger,Innocents Convicted:An Empirical Justified Factual Wrongful Conviction Rate[J].JournalofCriminalLaw& Criminology,2007(97).
[13][17]Hugo Adam Bedau and Michael L.Radelet,Miscarriages of Justice in Potentially Capital Cases[J].Stanford Law Review,1987(40).
[14][18]Steven,A.Drizin and Richard A.Leo,The problem of false confessions in the post-DNA world[J].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2004(82).
[16][19][20]Samuel R.Gross,Kristen Jacoby,Daniel J.Matheson,Nicholas Montgomery and Sujata Patil,Exo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9 through 2003[J],Journal of Criminal Law& Criminology,1995(95).
[21]Jon B.Gould and Richard A.Leo,One-hundred YearsLater:WrongfulConvictionsaftera Century of Research[J].Journal of Criminal Law&Criminology,2010(100).
[22][24]Talia Roitberg Harmon,Predictors of Miscarriages ofJusticeinCapitalCases[J],Justice Quarterly,2001(18).
[23][25]Talia Roitberg Harmon and William S.Lofquist,Too Late for Luck:A Comparison of Post-FurmanExonerationsandExecutionsofthe Innocent[J],Crime&Delinquency,2005(51).
[26]SamuelR.GrossandBarbaraO’Brien,Frequency and Predictors of False Conviction: Why We Know so Little,and New Data on Capital Cases[J],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2008(5).
[27]李建明.刑事司法错误:以刑事错案为中心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8]董坤.检察环节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防治对策[J].中国法学,2014(6):221-223.
[29]韩庚.我国重大刑事冤案成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以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为视角[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2): 126.
[30]陈柏峰.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祥林案切入[J].开放时代,2000(2).
[31]叶青,陈海锋.由赵作海案引发的程序法思考[J].法学,2010(6).
[32]周长军.后赵作海时代的冤案防范:基于法社会学的分析[J].法学论坛,2010(4).
[33]陈永生.冤案的原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的分析[J].政法论坛,2011(6).
[34]冀祥德.民愤的正读: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的司法性反思[J].现代法学,2006(1).
[35]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J].中国法学,2007(3).
[36]赵琳琳.刑事冤案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37]胡志风.刑事错案的侦查程序分析与控制路径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38]缪因知.计量与案例: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的剖析[J].北方法学,2014(3).
[39]王乐龙.刑事错案:症结与对策[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40]刘璐,段陆平.论刑事法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基于问题意识的思考[J].公民与法,2010(6).
[41]申文宽,陈丽芳.从思辨到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0).
[42]赵骏.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回归与超越[J].政法论坛,2013(2).
[44]何挺.法律实证研究中的实验方法[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2).
[45]左卫民.法学实证研究的价值与未来发展[J].法学研究,2013(6).
[46]唐应茂.法律实证研究的受众问题[J].法学,2013(4).
[47]郭云忠.法律实证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以刑事法为视角[J].法学研究,2010(6).
[48]王敏远.死刑错案的类型[J].中外法学,2015(3).
[49]郭云忠.法律实证研究方法研讨会综述[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4).
责任编辑朱文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5.031
D93.712.4
A
1004-0544(2017)05-0174-08
代孟良(1982-),男,重庆人,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