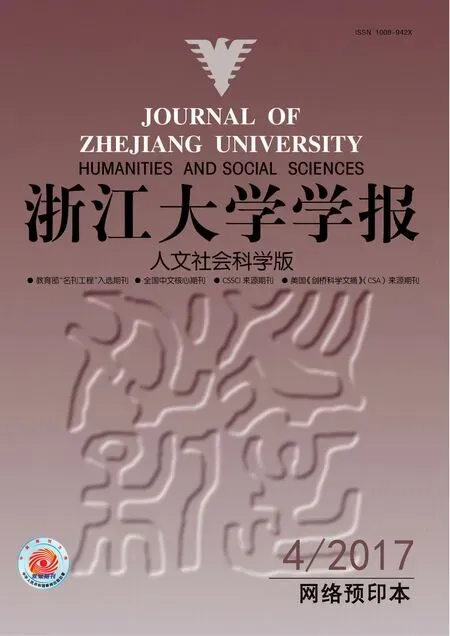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2017-06-05李杭春
李杭春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58)
讲学与传道:马一浮与国立浙江大学
李杭春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国立浙江大学被迫西迁,马一浮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请为浙江大学师生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校歌,这段历史成为浙大校史上光辉的一页。但相关文献和档案却显示,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交往充满各种误会与纠结,浙大险些因此错过这位“士林宗仰”的国学大师;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尽管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马一浮在浙大讲学并传道,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是马一浮一生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由此完成了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并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予浙大很深的希望。
马一浮;国立浙江大学;国学特约讲座
西迁途中,马一浮为国立浙江大学开设国学讲座,为浙大创制《大不自多》校歌,这段历史已成为浙大的一种荣光,被代代传诵。但检阅相关文献和档案,我们发现个中细节和当事人心态却仍值得还原。拂去些许历史的尘埃,将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明晰地认识马一浮与浙江大学的关系。
一、1936年的“罗生门”
1936年4月7日,竺可桢被国民政府确定为浙大校长[1]51。尽管他之前表示了诸多顾虑:不愿放弃的气象研究,不擅侍候官长,即将迫近的战争风云,经常不及时到位的办学经费等,但还是在向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的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提出了“三点要求”①“三点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竺可桢1936年3月8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竺可桢日记一集》,(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第36页。后,着手开始行使校长之职,并在5月6日的日记中透露“决定十八号补行宣誓典礼”[1]68。同一天,“马一浮”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竺可桢的日记里:
……至公安局晤赵华煦,渠介绍马一浮与邵裴子,此二人杭州视为瑰宝。马本名马福田,与大哥同榜为案首;汤寿潜选为东床,未几至美国。近卅年来潜研哲学,但始终未至大学教书。余托赵觅寿毅成为介,一探其愿否至浙大。邵裴子则余已访晤一次,请为国学教师极相宜。[1]68
对同为“杭州瑰宝”的邵裴子,竺校长请其担任“国学教师”的意向是极明确的;但对马一浮,竺可桢显然要慎重得多。他在此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与马一浮(及其弟子好友)交换意见甚至登门拜访。他先托赵华煦找到马一浮弟子寿毅成,探问马一浮意愿;又向章子梅、张圣征、任葆泉等征询,还通过章子梅、王子馀与其联系。可得到的信息或因环节杂乱、转达多重而多有所误,并导致了后来竺校长对马一浮在一些对话上的误会。竺校长也曾两次拜会马一浮,有两个“半小时”的面对面交流,惜乎双方的沟通似乎并不十分奏效。各种机缘附会,因1936年的一场场“罗生门”,马一浮错过了竺可桢的“仁至义尽”[1]124,竺可桢也遗憾地没能在真正懂马的基础上用马。
(一)马一浮的妥协与坚持
今《马一浮全集》收有致王子馀书信三通,其中“七月十八日”和“八月二日”两通书信中有马一浮对竺校长提议的明确回应。7月17日,竺校长第二次登门拜会马一浮,得马一浮允到校教课。次日,在致王子馀函②以下“分解”所引皆出自马一浮致王子馀7月18日函,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不再标注版本),第461-462页。信函日期标注为“一九三○年九月十日”,疑误,据函中有“昨竺君复枉谈”一说,时间或为1936年7月18日。中,马一浮表达了一些在面对面交谈中不便深入的问题。分解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
1.“弟平日所讲,不在学校之科,亦非初学所能喻,诚恐扞隔不入,未必有益,不如其已,非以距人自高也。”言马一浮“久而未答”的原因是考虑到自己平日所讲恐与学校不在一个系统,或为初学者不宜,并坦言并非自己不与世通,“距人自高”。
2.“若果有学生向学真切,在学校科目系统之外,自愿研究,到门请业,亦未尝不可。”如果有学生自愿向学,则在马一浮看来,“到门请业”就是表示向学之切的一桩自然而然的事情。
3.“昨竺君复枉过面谈,申述一切,欲改来学为往教。为体恤学生计,此层尚可通融。”说明竺校长的登门拜请还是很有收效的。为学生计,马一浮“不复坚持初见”,认为“往教”也可以通融。信至此,我们发现,因为马一浮的妥协,他与竺校长基本能取得一致。
4.“但竺君所望于弟者,谓但期指导学生,使略知国学门径。”对这个观点,马一浮的学究气就体现出来了:“弟谓欲明学术流别,须导之以义理,始有绳墨可循,然后乃可求通天下之志”,否则“群言淆乱而无所折衷,实今日学子之大患也。若只泛言国学,譬之万宝全书、百货商店,虽多,亦奚何为”?马一浮希望自己的国学讲习能使众人以义理而明学术流别,循墨绳而求通天下之志,而自己也可教学相长,怎能只是“略知”?
5.“不欲令种子断绝,此天下学者所同;然虽有嘉谷,投之石田,亦不能发荣滋长。”马一浮的这番担心并非毫无来由,“昔沈寐叟有言,今时少年未曾读过四书者,与吾辈言语不能相通”。马一浮本人也深有体会:“弟每与人言,引经语不能喻,则多方为之翻译。”自此,马一浮道出了自己的顾虑:“处今日之讲学,其难实倍于古人。”
6.“此当视诸生之资质如何,是否可与共学,非弟所能预必,非如普通教授有一定程式可计日而毕也。故讲论欲极自由,久暂亦无限制,乃可奉命,否则敬谢不敏。”尽管铺陈了各种质疑、担忧,如诸生之资质、有人未读过四书等,马一浮仍然没有一口回绝竺校长的意思,而是提出了底线的要求,即讲论自由,时间不限,有此一条,仍可奉命出山往教。
可见,马一浮意见很明确。竺马分歧的焦点似并不在马一浮之“距人自高”①马一浮致王子馀函,此件应为1936年7月18日函。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第461页。、“世故欠通”[1]124;也不在他“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②“接王子馀函,知马一浮不惯学校生活,不能来校讲课。”竺可桢1936年6月8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竺可桢日记一集》,第89页。,那更像是马一浮深思熟虑后的一个托词,毕竟当时才六月初,竺马会尚未深入;更不是“马或疑余请邀之心非真诚,无非欲假借渠之名义,似有疑余之真心”[1]114——任葆泉转述自张圣征的这个意思,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差池,竟让竺可桢有此无中生有之记录,真是冤煞马一浮也!
(二)“未能尽意”的竺马会晤
当然,为请马出山,竺可桢在上任之初的百忙之中也曾在1936年5月24日、7月17日两次专程面晤马一浮。马一浮住马所巷,即今浙医一院附近,与浙大相邻。对于两次会晤,竺可桢的记录尚比较乐观:
五点赵龙文、徐曙岑、寿毅成、晓沧来,偕至马一浮寓。马乃长塘人,与大哥同榜进学,马第一名,而大哥则为第五名也……马美髯须,而人颇矮。余等均劝其为学生授课,甚至学生至渠家听讲亦行。五点半出。[1]80(5月24日日记)
四点半至马所巷十三号甲马一浮处。马经眼科医生张圣征之劝驾已允到校教课。余拟在刀茅巷十七号特设一房为其教课之所。据马云,渠于1903年曾至美国圣鲁意博览会,未逾年即回,在日本留一年,前数年哈佛大学哲学教授Hockins曾来访云。渠对于教书,谓学生求学之态(度)不应以求得学分为重,(不)应以学分为前提,且不能全赖教师所讲,而应自求途径云云。谈半小时而出……[1]112(7月17日日记)
但在马一浮看来,“与竺君相见两次,所谈未能尽意。在竺君或以为弟已肯定,然弟实疑而未敢自任”③马一浮致王子馀函,此件应为1936年7月18日函。同上,第462页。。可见两者的交流实在是存在隔阂的,没能深入到讲习方式、培养目标和学生知识准备等深层次合作可能遇见的问题。或许是马一浮有所保留,也许是气象学家过于乐观,总之两人对任教一事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于是才有了上述马一浮写给王子馀的信,周到详细,不吐不快。
可惜这一函件所表达的重要信息似乎未能抵达竺校长,查《竺可桢日记》,这之后只在1936年7月20日的日记中有张圣征的“疑余真心”说。直到8月初,才又有几段密集的记载,内容却多有谬误:
九点至青年路晤张圣征……据张云,一浮提出一方案,谓其所授课不能在普通学程以内,此点余可允许,当为外国的一种Seminar。但一浮并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而其学程为国学研究会,则在座者均不赞同,余亦以为不可。大师之名有类佛号;名曰会,则必呈请党部,有种种麻烦矣。余允再与面洽。[1]121(8月1日日记)
子梅来,据云马一浮有若干条件不能通融,如称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愿减去,亦其一例,因此谓此事俟余南京回后再谈亦佳。[1]122(8月4日日记)
接章子梅函,知马一浮事因国学研究会之“会”字不肯取消故,事又不成。余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子梅谓其学问固优,世故欠通,信然。[1]124(8月7日日记)
矛盾的焦点似乎转移到马一浮在课程名称和个人称谓上的不近情理了,且从浙大方读来,马一浮已经不仅是冥顽不化。但是,情况究竟如何?
(三)莫须有的“国学研究会”
8月1日,竺可桢晤张圣征并得知马一浮“国学大师”、“国学研究会”方案,明确表示“不可”。马一浮应该很快得知了这个意见。于是8月2日,他又有一函发王子馀①以下所引皆出马一浮致王子馀8月2日函,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第463-464页。信函日期作“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据函中“昨竺君复托他友致语,以讲习会之名恐引起干涉”,与竺可桢8月1日日记内容直接相关,故本函日期当为8月2日。,对此事有所回应,不妨也拿来分解一下。
1.“前荷惠书,尚未俱答。初意且俟竺君之来,再与面论,察其所见是否与愚拙相同,然后从违之情一言可决。”竺可桢虽已两度拜访马一浮,但8月1日日记中仍有“余允再与面洽”的表示,这一信息或已同时转达至马一浮。故马一浮期待就国学讲习会与竺可桢作“面论”,然后察其所见,当面决定“从违”。
2.“必欲相求,须在学校中所有科目之外,纯粹以讲学意味出之,使知有修己之学,不关干禄之具,然后乃可进而语之以道。”这是马一浮的一贯主张,并强调纯粹之学修己、悟道、不关干禄。
3.“今日学生皆为毕业求出路来,所谓利禄之途然也,不知此外更有何事。荀卿云:‘古之学者以美其身,今之学者以为禽犊。’开宗明义,须令学生了解此意,方可商量。”可见,马一浮对“当今学生”评价不高,担心他们的学习目标过于世俗,全无古人自美其身的学习状态,要求他们放弃“利禄之途”。
4.“因恐竺君事繁,或未睱计及,辄不避越俎,为代拟设立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力求浅显,粗具厓略,留俟讨论。偶为张君圣征言之。”马一浮准备替竺校长代拟“国学讲习会”旨趣办法,这里,马一浮明确的表述是“国学讲习会”,而非竺可桢记录的张圣征转述的“国学研究会”,两字之差,意相远矣,而且直接影响到了竺校长后来的决策。
5.“昨竺君复托他友致语,以讲习会之名恐引起干涉,非学校所宜。大学规程弟所未谙,然未闻政府有讲学之禁也。此项名义亦与他种集会性质不同,此而须受干涉,则学校各系课堂上课亦须受干涉邪?既于学校无益而有妨,何为多此一举?”显然马一浮还不知道是不是传话的张圣征带错了意思,竺可桢的那些意见都是就“国学研究会”而发。如果竺可桢知是“讲习会”,想必不会有此等判断,两人之间的合作或许1936年就愉快地开始了。但历史不容假设。这之后几天,因既考虑到“研究会”作为课程名称的不合宜,也明知党部对“研究会”的一贯干涉,竺可桢坚持主张取消“研究会”的“会”字;而马一浮则认定“讲习会”不同于他种结社集会,而只是课堂讲习,他不理解怎会遭党部干涉,自然不愿意妥协。至此,这一“罗生门”可能导致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6.“今将所拟讲习会旨趣附呈一览,即便毁弃,不必更转竺君。竺君虽有尊师重道之心,弟实无化民成俗之德。今其言即无可采,是犹未能取信,前议自合取消。此事本于学校为骈枝,于学生为分外。且选拔生徒,尤感困难。为竺君计,不如其已也。”显然,马一浮比竺可桢更坚决地做出了取消前议的决定。
(四)国学讲习会与主讲大师
信中,马一浮还附了此前替竺校长拟写的《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全文如下:
一、本校为引导学生对于吾国固有学术之认识,兼欲启示学生使知注重内心之修养,特设国学讲习会。
二、国学讲习会设特别讲座,由本校延聘主讲大师,自由讲论。每星期一次,其时间另定之。但主讲大师有故不能到会时,得由本校商请派遣高足弟子出席代讲,或许学生造门请业,仍以每星期一次为限。
三、国学讲习会纯粹为养成国学基本知识,使学生离校后可进而为深切之研究,发挥本具之知能,阐扬固有之文化,故超然立于本校所有各院、各系科目范围之外。不列学分,不规定毕业期限。但每届一年终了时,由主讲大师考询其领受之深浅,另定甲乙。其学业优异者,经校长之特许,得酌予嘉奖。
四、本校各院各系学生中,不论年级,于所修科目之外,有志研究国学,曾读四书及五经中一经以上者,由校长选拔,令自行填具志愿书,得入国学讲习会听讲。其未读四书者不与。
五、国学讲习会暂分经术研究、义理研究二门。俟学生领解力增进时,得增学术流别(即哲学评判)、文章流别(即文学评判)二门,或其他门类。由主讲大师察看学生能力自由酌定之。
六、学生既入国学讲习会听讲,不得无故中途废辍。其有领解力薄弱或不守规则者,由主讲大师随时告知校长,令其退席。
七、国内通儒显学遇有缘会,由主讲大师介绍,经校长之同意,得临时特开讲座,延请讲论,示学者以多闻广益之道。①马一浮致王子馀8月2日函。信函日期作“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疑误。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第464页。段前序号“一”字到底,为顺序清晰计,本文径改。
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完整的讲学计划,足见马一浮之深思熟虑。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细节,一是“大师”之谓。马一浮用的是“主讲大师”,并非竺校长听说的“国学大师”。二是此一称谓对应的是“讲习会”这一不同于学校其他教学计划的特殊讲学设置,而断不是“研究会”。这应该是马一浮为“事”而设,绝非为“人”,尤其不是为自己。
而在竺可桢获得的信息里,他被告知马一浮“欲学校称其为国学大师”。不知这个谬误出自哪个环节,事实上,自封“大师”并挟校长令学校以从之,足以影响到一位校长对一名从教者道德人品、职业操守的判断;加之另一个莫须有的“国学研究会”之固不悔改,难怪竺可桢会表示自己在诚请马一浮一事上已“仁至义尽”,认定事之“不成”,错都在马一浮,甚至采信同事对马一浮“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非议。
这场“罗生门”爬梳至此,我们发现结果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不够充分的沟通和不够谨慎的理解,浙大差点错过了我们这个时代如此令人景仰的一位国学大师。
二、1938年的泰和、宜山之旅
(一)《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上的两则报道
国立浙江大学西迁时期的档案并不完整,幸好《国立浙江大学校刊》为我们保留了这段历史的部分面貌。学校从江西泰和西迁至广西宜山,因战争和迁徙而被迫停刊的校刊重新复刊,1938年12月5日复刊第1期和1939年2月13日复刊第11期,分别以《马一浮先生继续讲学》和《马一浮先生入蜀讲学》为题对马一浮的行踪做了报道。两文比较清楚地回顾了马一浮开设“国学特约讲座”的由来、讲座的盛况和即将开始的复性书院生涯。可惜这两份油印刊物字迹已不够清晰,《马一浮先生继续讲学》的内容只能抄个大概:
绍兴马湛翁先生(□字一浮)博学硕望,隐居西湖多年,好学之士子多□门就教。军兴以后,避居桐庐,竺校长一再敦聘,又以好友恳劝,始于三月底到赣,四月九日起在本校讲学。三四月中,讲阐六艺大旨,继说义理名相,谆谆以反躬力行诲人,受教者多所感发。先生于九月离赣,十月底来宜,继续讲学。本学期第一次系十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在第十八教室开讲,莅听者百余人,竺校长郑教务长梅副院长国文系郭洽周物理系张□□史地系……参加听讲。先生之学,会通……
省略号处和接下来的内容漶漫不清,能辨认者另有“三十日下午的第二次讲座,学生以外,教授参加者仍十多人”,及“最近宜山各界向学之士,慕名前来听讲者,亦有多人云”①见《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期,1938年12月5日,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百余人莅临听讲,称得上盛况空前。要知道那时候抵达泰和的学生总共“注册者327人”②这个数字截止于1938年2月24日。参看竺可桢1938年2月24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竺可桢日记一集》,第475页。。
第二篇报道《马一浮先生入蜀讲学》相对完整:
绍兴马一浮先生博学亮节,士林宗仰。二十七年四月,应竺校长之聘,担任本校国学特约讲座,在泰和讲学一学期,十月间来桂,本学期继续讲六艺要旨,学生自由听讲以外,文理学院教授中参与听讲先后不辍者,亦复不少,讲余谈学论艺,学生亦常有登门求教者。教育部陈部长雅慕先生,曾来杭专谒,秋间即有约先生入蜀讲学之意,几经商洽,马先生并提示数项意见,当局亦加采纳,先生并拟讲学之所在称复性书院。一月下旬教部□来□□,竺校长挽留不遂,□以学术天下公器,入蜀讲学,更又安布教□,特于月底与一部分教授公宴欢□,马先生并□诗赠别。二月初,马先生又接孔院长来电速□,先生书□甚多,应用车辆,经由教部商请□委会西南公路运输厅特派汽车三辆,因故稍□,至二月八日始到。马先生当于八日下午别本校启程西行,转黔赴渝。③见1939年2月13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1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
两篇报道给了我们许多历史的细节,比如讲座内容、开讲时间、听讲人员等,读来让人感慨。
当然,当时浙大聘请了两位“特别讲习”,马一浮之外,还有柳诒徵。“在我们打了很多次电报以后,他从扬州附近的兴化赶来,我们像对待马一样对待他。这两个人是我们学校的特别讲习,每个星期做一次讲座,每次一到两个小时。他们两人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2]414
(二)马一浮之就浙大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1937年秋,马一浮离开杭州。“弟自徒桐庐,甫及一月而嘉、湖沦陷,杭州几不守。沿江诸县,寇未至而兵已来骚乱,不可复居。”(1938年1月9日马一浮致熊十力函)[3]479“因于一月十五日附船至建德……一行十五人十七日自建德解缆,廿二日抵开化。”(1938年3月10日马一浮致丰子恺函)[3]512在开化,1938年2月12日,身受离乱之苦和迁徙之难的马一浮给在江西泰和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讲到自己的“流离”和“所望”:
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闻贵校早徙吉安,弦诵不辍。益见应变有余,示教无倦,弥复可钦。弟于秋间初徙桐庐,嗣因寇逼富阳,再迁开化。年衰力惫,琐尾流离,不堪其苦。平生所蓄,但有故书,辗转弃置,俱已荡析……因念贵校所在,师儒骈集,敷茵假馆,必与当地款接,相习能安。傥遵道载驰,瞻乌爰止,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虽过计私忧,初不敢存期必,然推己及物,实所望于仁贤。幸荷不遗,愿赐还答,并以赣中情势,及道路所经,有无舟车可附,需费若干,不吝详告……[3]529
拖家带书又身处危难的马一浮想到了此时离开化不远的竺可桢。竺可桢许是20日接到此函,不敢耽误,但却借重梅光迪和郑晓沧:“四点半至迪生处谈马一浮事。因去(前)岁曾约马至浙大教课,事将成而又谢却。现在开化,颇为狼狈,并有其甥丁安期、及门王星贤两家合十五人,愿入赣避难,嘱相容于浙大。迪生与晓沧均主张收容,遂拟复一电,聘为国学讲座。”[1]472对此,马一浮自是心存感激:“浙大亦有少数友人相招颇殷,不欲绝物太甚,遂以三月底来。”[3]513“学校诸人来访问者,皆意颇亲切。”①1938年4月7日马一浮致王培德函。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下),第818页。全集所注时间疑有误。此函有“已定四月九日开讲,每星期一次”的预告,当不会在4月9日以后,故取“四月七日”落款。
讲学浙大,马一浮所享的礼遇是崇高的。梅光迪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有过这样几段真切的回忆:“我们为他找到这里最好的房屋,以其他任何地方的教授都梦想不到的礼节接待他……学校私有的两辆黄包车之一,为他随时待命。路程稍长,竺校长的汽车就成了他的座驾。”[2]406“我还为听众制定了一些在讲座期间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则……(1)在马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我们必须起立,直到他坐下为止。(2)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如谈话或咳嗽;任何违规者将会被立即赶出教室。(3)在讲座最后,当演讲者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们都要起立,并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为止。让我满意的是,所有的这些原则都完全被遵守了,氛围保持了绝对安静,并且充满尊重。”[2]409
对此,马一浮显示出其复杂的心境:“浙大非知我者,然其接也以礼,吾方羁旅择地,是亦可以暂寄,寇退则返浙亦近。”[4]795“吾终自居客体,不在学校统系之内,庶可去住自由,观机而应。”[4]818可见,尽管浙大做足了细节和场面,但毕竟“国学会”一事过去仅年余,当事人心里多少还心存芥蒂。
(三)马一浮国学特约讲座:怎么讲,怎么听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和环境里开始的国学特约讲座,《校刊》报道里描绘的盛景可能并不是可持续的。在马一浮笔下,它体现的是这样一番模样:
弟在此大似生公聚石说法。翠岩青禅师坐下无一人,每日自击钟鼓上堂一次。人笑之曰:“公说与谁听?”青曰:“岂无天龙八部,汝自不见耳。”弟每赴讲,学生来听者不过十余人,诸教授来听者数亦相等,察其在坐时,亦颇凝神谛听,然讲过便了,无机会勘辨其领会深浅如何,以云兴趣,殊无可言。其间或竟无一个半个,吾讲亦自若。[5]480
两相对读,差别不小。而夫《校刊》者,以正能量示人也是常理。
以马一浮所讲的精深专研,教师和地方“向学之士”的热情高过学生,似亦不足为奇。而几位常去听讲的教师,如梅光迪、郑晓沧、张其昀、郭恰周、贺昌群、李絜非、王驾吾……其各自的学术方向后来亦并未发生转型,马一浮的影响或更多在精神层面,就像马一浮眼里“精于考据”[5]50、“才俊可喜”[4]537的贺昌群所感慨的,他“与文学院诸友,时至排田村湛翁先生(马一浮)草堂讲学论道”[6]118、诗词唱和,让他“在这家愁国恨中,竟寻到一种人生至高的情绪之和乐。忘生死,齐物我,我曾感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6]118。
在马一浮泰和、宜山讲学期间,竺可桢日记里有四次聆听讲座的记录,分别是1938年的5月14日、5月28日、11月23日、11月30日。作为一校之长,能多次前往聆听同一门课,足以说明其重视程度。但从竺可桢日记里,我们发现其听讲效果并没有多少记载,或许这只是校长给予马一浮的一种“礼”和“尊”。其中两次,他只记下马一浮所讲内容,不曾发表评价;另有两次或感叹“惜马君所言过于简单,未足尽其底蕴”[1]519,或直接表示质疑:“马一浮讲学问固然渊博,但其复古精神太过,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以为人为非,而为己是,则谬矣。”[1]624
不过,这里竺校长以为“谬”的马一浮“为己”之说,或许是马一浮哲学大厦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与马一浮一生倡导的六艺之学息息相关,即一切学问、义理皆由一己之心所发,反躬、自省亦首先指向自我。这当是与“自私自利”无干的。如此想来,不仅当年的浙大学子无法深知马一浮广博弘富、深邃悲悯的思想和情怀,即便是一校之长,在体认上亦难免有些错位。
三、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
尽管国立浙大从一开始就在清理自己的“血统”,意欲直接13年前中断的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的“龙脉”,但事实上,这个由工业专门学校和农业专门学校两所中等专科学校合并而来的大学,直到竺可桢掌校的1936年,其大学办学经历尚不足十年,基本还只在起步阶段,以至于一方面,校方自称“历史悠久”,一方面也承认“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①时浙江省教育厅长陈布雷在国立浙江大学建校三周年活动上的讲话,见1930年9月20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3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所以,竺校长于浙大的改变,于浙大的成长委实令人喟叹;而走过国立浙大的马一浮亦在他唯一任教的大学里,一方面完成了其更为高迈、通贯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人格的构建,另一方面,也以一场场思想与精神的盛宴,寄望于浙大及其研学者。
(一)马一浮之立人观
俗称的20世纪30年代,亦可以指1927年国民政府统治中国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这十年。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建设日新月异,故史有“黄金十年”之说;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已逾十年,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而启蒙文化又渐渐式微,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工业主义、实用主义思想及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理念渐成社会主流。不仅浙大校长是一位科学家,当年立在土山脚下的“工业教育廿周年纪念碑”②《土山剪影》,参见1934年6月16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177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该碑由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毕业同学集资筹建,于1931年3月28日下午2时行奠基礼。参《工学院举行浙江工业教育念周纪念展览会纪实》,见1931年4月4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48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亦可窥见一斑——这是对从1911年创办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即并入国立第三中山大学的浙江公立工业专科学校前身)开始的工业教育的纪念。这些或许都能从一个侧面体现那个年代人们的追逐和崇仰。
马一浮面对的就是这个历史时段的大学生。以马一浮的国学功底和学问积累,他对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整体评价不高。在他看来,这一代大学生正是废科举、新文化以后出生、成长、受教育的年轻人,相比于前辈,他们的知识储备、文化谱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话语方式都迥然有异。“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上的主要潮流是科学发展……”[7]8755而国立浙大又以工学院、农学院立身,自然倚重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工业教育、农业教育,尤其在郭任远掌校时期,正如竺校长后来指出的,“事事惟以实用为依归”,“郭之办学完全为物质主义,与余内心颇相冲突也”[1]36,可见问题之显在。文理学院内部发展则颇不平衡,物理、数学人才济济①继陈建功以后,1931年4月7日苏步青又加盟浙大,开始了学界知名的“苏陈学派”时代,而文科师资偏弱。参见《欢迎苏步青就职》,1931年4月11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49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而“国文竟无一个教授,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均无教授”[1]36。可见文史课程存在师资缺乏、课程不均等问题,学生所受文史教育和训练显然不够充分。向这样一个群体讲授国学,讲授六艺之学,“生而知之”(弘一法师语)的马一浮就颇有“嘉谷,投之石田”[3]462的顾虑。1936年他对王子馀讲“今日学生皆为毕业求出路来,所谓利禄之途然也,不知此外更有何事”[3]463-464的时候,或许只是猜测;两年以后,基于一学期的讲学体验,在写给张立民的函中,仍表示“学生入学只为出路,以学校比工厂,学生亦自安于工具,以人为器械,举世不知其非”[4]801,几乎没有向好的变化,甚至断言“国立诸学,恐已根本动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3]519。想当年马一浮设计的《大学特设国学讲习会之旨趣及办法》中,他甚至直接规定了讲习会的准入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其未读四书者不与”[3]464。
1936年马一浮之不就浙大,部分原因或与这样一种认知和担忧相关,“群迷不悟,只增悲心”[3]482。但战争改变了马一浮,他以为混沌可以产生秩序:“吾来泰和,直为避战乱耳,浙大诸人要我讲学,吾亦以人在危难中,其心或易收敛,故应之。”[4]796他因此接受了国立浙江大学“国学特约讲习”的聘请。这个时候,他颇寄厚望于浙大诸生:“闻各教授皆言诸生姿质聪颖,极肯用功,此不但是大学最好现象,亦是国家前途最好现象,深为可喜……某今日所言,只患不能感动诸生,不患诸生不能应。若诸生不是漠然听而不闻,则他日必可发生影响。”[8]3他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学生摒弃实用主义的现代工业观,回归对文化根本的关注。
可惜实际的讲学效果与其预想相距甚远。梅光迪看到,“马在熟知中国文化的所有中国人中,享有至高的声誉和尊重,但是他完全不为普通公众和年青一代所知”[2]406-407。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学生们对马一浮之言义理名相、心性六艺殊无兴趣,“听众几劣,吾又缘浅,在此未必能久羁”[3]481。而令马一浮失望的还不仅是学生,“时贤每轻疑圣学为无用,六经久成束阁”[4]536-537。他感慨道:“今之学校远不及昔之丛林矣”②1938年4月7日马一浮致王培德函,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下),第818页。书函时间有误,径改。;“今人以散乱心求知识,并心外营,不知自己心性为何事。忽有人教伊向内体究,真似风马牛不相及。弟意总与提持向上,欲使其自知习气陷溺之非,而思自拔于流俗,方可与适道。”[3]480悲凉无奈之心见诸纸上。
对此,乌以风在其《马一浮先生学赞》中的解读比较客观:“上智之士,闻者赞叹,而专以知解为学者,闻先生之说,颇疑过于高深,非一般人所能喻,或谓离现实太远,非社会所需等等。先生为之反复辩解……”[9]215
(二)“横渠四句教”及浙大校歌
因“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3]513以及周遭遍布的流俗、庸习,马一浮总是怀有更深更远的忧虑:“吾国固有特殊之文化,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今后生只习于现代浅薄之理论,无有向上精神,如何可望复兴?”[3]514但马一浮并不放弃一位儒者的本分。1938年4月9日,在泰和第一次国学讲座上,马一浮言此国学讲座“其意义在于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之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8]2,并特为拈出横渠四句教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的做一个人”[8]4,属望青年以为己任,以济蹇难,以正精神。
后来他在写给丰子恺的信中这样说:“顷来泰和为浙大诸生讲横渠四句教,颇觉此语伟大,与佛氏四弘誓愿相等”,“其意义光明俊伟,真先圣精神之寄托”。他请丰子恺找人制成歌曲,“欲令此间学生歌之,以资振作”[3]514,以更通俗的方式传播思想。待萧而化制作完成,马一浮还将“横渠四句教谱自用石印摹出二百份,一百份与浙大……”[3]517-518在这年6月26日举行的浙江大学第11届毕业典礼上,全校师生首次唱响张横渠四句歌①参看竺可桢1938年6月26日日记,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竺可桢日记一集》,第540页。,此情此景或令师生们印象深刻。
暑假以后,浙大辗转再度西迁至广西宜山。“本校本学期第1次校务会议于11月19日3时在总办事处会议厅举行,到教务长三院长总务长各系主任及教授代表共20余人……并决定本校校训为‘求是’两字,又校歌则特请马湛翁先生撰制云。”②《校务会议纪要》,1938年12月5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竺可桢当晚日记中也有相同表述:“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1]615公推马一浮为校歌歌词作者,或与马一浮推倡“横渠四句歌”的创意和效果密切相关。
12月8日,不到20天,马一浮拿出了《大不自多》歌词。“三点开校务会议,讨论校歌问题。本校训前次已定为‘求是’,校歌由马一浮制成,拟请人将歌谱制就后一并通过。”[1]624后又“以陈义过高,更请其另作校歌释词一篇”③《总理纪念周-竺校长训话》,据1941年12月10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02期,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也就是马一浮的《拟浙江大学校歌附说明》。后来还是因“词高难谱”,两年以后的1941年春,方“始获国立音乐院代制歌谱焉”④同上。。
“校歌为一校精神之所附丽”。人的禀性精神断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尽管马一浮倾力于讲论诗教国学,提振国人心志精神,但在一个集中了各种非常状态的社会环境里,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还是相当遥远。将离浙大的1939年初,在写给吴敬生的信中,马一浮仍不客气地指出:“浙大精神涣散,吾本客体,去住无关,然欲蔚成一种学风,似非现在诸人所能及。”[4]857此一说法或基于对这所他唯一讲学的高等学府更高的要求与期待,正如校歌中“无曰己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这几句歌词所蕴含的:“‘无曰’四句,是诫勉之词,明义理无穷,不可自足,勿矜创获,勿忘古训,乃可日新……此章之言丁宁谆至,所望于浙大者深矣。”[8]82所以,代代相传的校歌或正是马一浮寄托心志以涵养学风的良好载体,哪怕他带着遗憾和失望离开宜山。在马一浮看来,校歌“乃当述立教之意,师弟子相勖勉诰诫之言,义与箴诗为近。辞不厌朴,但取雅正,寓教思无穷之旨,庶几歌者、听者咸可感发兴起,方不失《乐》教之意”[8]81。传唱至今并召唤了一代代人的浙大校歌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我们都能体会到,马一浮是有多想从根本上激发一个民族的精神潜能,有多想让浙大诸生引领和完成这样一种精神的激荡和传承。
(三)讲学与传道
马一浮在浙大任讲的时间不长,但结集而成的《宜山泰和会语》却是马一浮历经此一乱世的深刻体悟,也是他一生中讲阐六艺国学最集中的部分。马一浮借讲学而传道,开始了他人生中一段新的辉煌。
1.出山讲学,知行合一。战争到来之前,身为“读书种子”和“杭州瑰宝”的马一浮就住在浙大附近,与浙大同仁多有接触①1931年4月18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50期刊有“潭秋”《一浮先生招饮楼外楼赋谢》一诗,浙江省档案馆浙江大学卷宗。,登门求教者直是络绎不绝。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11月7日与钱潮、马巽伯一起“去看一位研究佛学的马一浮氏”[10]338。如果不发生战争,马一浮一定还将一如此前地静静深居于小巷,做个象牙塔外的大学者,接待“来学”者,抵制“往教”说,都不在话下。
战争让马一浮失去了安静的书桌,失去了读书人惯有的矜持与自尊,而开始在外奔波。在轰炸频仍、满目疮痍的日居环境中,他走出书斋,拖家带口,迁徙流离,开始更多地看到、听到、经历到,而不仅仅是读到、想到、揣摩到。他开始接受现实世界之无情、无奈和无常,“或容有讲论之地,能以束脩自给,则吾虽衰耄,犹可力为,尽此残年,甘于羁旅”[3]304;他开始在国人“以危为安,以亡图存,以乱为治,颠倒迷惘,不知所极,良可哀愍”的共同体验中,质询“人类何以至此,谁为为之,孰使致之”,感慨“圣贤之道不明,众生永无宁日”[4]856;他开始将“知”与“行”的体会付诸实践并诉诸学子:“人生的内部是思想,其发现于外的便是言行。故孔子先说知,后说言行。知是体,言行是用也……思想之涵养愈深厚,愈充实,斯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言论愈光大,不是空虚贫乏。”[8]42而此一阶段发明并阐述的“义理名相”、“六艺之学”,亦从思想联系实际,由知进入行,以致力于改变知识贤达“言常有余,行常不足”[4]565的状态。于是,出山讲学就成了这个时候他躬身力行的一种重要方式,并视其为儒者分内事,“无间于安危”[4]536——先是泰和宜山,继是复性书院。
2.化民成俗,学用合一。战争改变了马一浮对学术功能的预期与判断。那段时间,马一浮僻居乡间,“除早晚看云树外,无可遣意”[3]516。看云看树间写下的诗行,心境也颇寂寥。或者“老夫观树心常寂,尽日江楼坐深碧。密叶不因霜雪改,孤根几阅人代易”[5]49,或者“鸦飞不度狼烟远,独自登楼望月明”[5]49。但一个读书人本性里的安贫乐道、以苦为乐,这个时候被激发得淋漓尽致:“且喜此地景物尚佳,老树当门,平畴弥望,乡村风味亦颇不恶。”[3]514转而影响其艺术观:“目睹战祸之烈,身经乱离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3]513“由艺术观点看来,任何现象剪取一部分,皆可令人艺术,实无入而不自得也。贤前云,在汉时见民众抗战情绪是一幅美丽图画,实则做难民流离颠沛亦可作如是观。许多不可磨灭之文艺,即由此产生。此吾所谓诗以感为体也……然艺术之作用在能唤起人生内蕴之情绪,使与艺术融合为一,斯即移风易俗之功用矣。”[3]520泰和宜山而后,马一浮当是从学术的高塔、楼台走了下来,开始了更接地气的人际交往②据对《马一浮全集》所收信函的不完全统计,马一浮与友朋学人书信交往最密集的时间发生在1938年浙大讲学到1942年复性书院收山期间。给丰子恺的23通书信中,作于浙大讲学期间的有12通,占比52.2%;与谢无量信函往来最多(120通),时间跨度最长(1908—1962,共54年),但发生在这4年里的竟有50通,占比41.7%。何况那还是一个兵荒马乱、“书种”难存的年代。参见《马一浮全集》第2册。和思想传播,将学术致力于功用,致力于“开物前民”,致力于化民成俗,以使人人“明是非,别同异”[3]389,一如他讲六艺,也传诗教,用更通俗的方式传播智慧,传播守望家园的勇气和信念。
3.穷理致知,尽人之性。在浙大和复性书院讲学期间,马一浮多次提到,读书是为穷理,穷理则能致知。穷理在穷尽事物之理,穷尽事物之根原、之条理;而致知则为推及吾心之知,字字反之身心,以应“吾心本具之理”[8]94。他认同《中庸》所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8]92学术若以此为基,当能达到事之“理”与心之“知”“理事双融,一心所摄”[8]91之境界。但事实上,这种天人合一的治学境界在大多数人是难以企及的。“凡人心攀缘驰逐,意念纷飞,必至昏昧。以昏昧之心应事接物,动成差忒。”[8]45而更严重的是:“今时学者每以某种事物为研究之对象,好言‘解决问题’、‘探求真理’,未尝不用思力,然不知为性分内事,是以宇宙人生为外也。自其研究之对象言之,则己亦外也。彼此相消,无主可得,而每矜为创获,岂非虚妄之中更增虚妄?以是为穷理,只是增长习气;以是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谓穷理致知也。”[8]93这是马一浮对“今时”学术的批评与思量。面对只是增长习气和佑护自私的“今时学者”,他更希望学术能以人本具之性尽物之性,持求是、启真、溯本、探源之精神,以“穷理尽性,明伦察物”[8]85,“一心贯万事,一心具众理”[8]91,既向外探察,穷天地之理,又向内体究,尽本性之知,从而构建一个“物我无间,人己是同”[8]93的学理王国。这当是马一浮所慕求的最高学术境界,也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深切属望。
三年里,马一浮与浙大有误会,有隔膜,有患难与共,有相知相容。他为浙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在这里构筑了自己的学术大厦。
[1]竺可桢:《竺可桢日记一集》,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Zhu Kezhen,Diary of Zhu Kezhen:Vol.1,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Kezhen:Vol.6,Shanghai: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5.]
[2]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编:《梅光迪文存(中卷·家书集)》,张钰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Chinese Meis Cul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Mei Guangdi(The Middle Volume,Collection of Familys Letter),trans.by Zhang Yu,Wuha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11.]
[3]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2册(上),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Ma Yifu,The Complete Works of Ma Yifu:Vol.2(Ⅰ),edited by Wu Guang,Hangzhou: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4]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2册(下),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Ma Yifu,The Complete Works of Ma Yifu:Vol.2(Ⅱ),edited by Wu Guang,Hangzhou: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5]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3册(上),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Ma Yifu,The Complete Works of Ma Yifu:Vol.3(Ⅰ),edited by Wu Guang,Hangzhou: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6]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He Changqun,Collected Works of He Changqun:Vol.3,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2003.]
[7]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Zhang Qiyun,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Qiyun,Taipei: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1989.]
[8]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1册(上),吴光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Ma Yifu,The Complete Works of Ma Yifu:Vol.1(Ⅰ),edited by Wu Guang,Hangzhou:Zhejia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2013.]
[9]乌以风:《马一浮先生学赞》,见夏宗禹编:《马一浮遗墨》,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214-215页。[Wu Yifeng,″Introduction to Mr.Ma Yifu,″in Xia Zongyu(ed.),Ma Yifus Calligraphy Works,Beijing:Huaxia Publishing House,1991,pp.214-215.]
[10]郁达夫:《水明楼日记》,见《郁达夫全集》第5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Yu Dafu,Diary of Yu Dafu,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Yu Dafu:Vol.5,Hangzhou: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2007.]
Teaching and Preaching:Ma Yifu and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Li Hangchun
(The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310058,China)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broke out,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was forced to move westward.In exile with his family and books,Ma Yifu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Zhu Kezhen,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to give lectures about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at both Taihe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Yishan of Guangxi province.He also wrote the University Anthem.This period could be the most glorious part in the history of Chekiang University.But after reviewing and scrutinizing the related literature,for example,The Complete Works of Ma Yifu,The Complete Works of Zhu Kezhen,lots of essays,memoirs and letters from Chang Chiyun,Mei Guangdi,He Changqun,Li Xiefei,Feng Zikai,who were close to Ma during those days,and after digging through the old files of Chekiang University,we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 Yifu and Chekiang University was fraught with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nfusions.One widely spread misunderstanding about Ma in particular was about his self-conferred title″Master of traditionalChinese culture,″and his persistence in establishing the″Seminar of Traditional Sinology Institute″in-1936,which directly affected the understanding of,trust in and judgment of Ma Yifu from the people around,including Zhu Kezhen.Some of the rumors have even been passed down to the present-day,and som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incorrect.Chekiang University might have missed the respectable mas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f the Anti-Japanese War hadnt happened.In the-1930s,with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the construction throughout the land was changing with each passing day.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ault appeared and the enlightenment culture gradually declined as more than ten years had elapsed after the May-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The thoughts of industrialism or pragmatism and saving the country with industry,whi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elied on,were gradually growing into mainstream.Ma Yifu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grew up and
education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May-4th Movement of New Culture,as they chose not to read the Four Books,and they had blind faith in modern science.This could be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a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from 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 before the War.After the War broke out,he decided to go to Chekiang University to give lectures,with the hope that the War could not only bring back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eliefs,but also make every Chinese rethink deeply about the modern culture.At the only university he taught as an instructor,Ma tried every means to guide the young people to abandon the utilitarian view of modern industry and drew their attention back to culture itself.For various reasons,however,Ma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his lectures on national culture in Chekiang University were far from his expectations.In spite of this,it helped Ma finish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grand academic thoughts.During the two semesters at Taihe and Yishan,Ma Yifu compiled more than-20lectures on″traditional Chinese″into a book entitled Yishan and Taihe Lectures.In these lectures,Ma Yifu spent more time and energy on″Six Arts″than any other time in his life.During the-3years,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 Yifu and Chekiang University was full of misunderstandings and gaps,but also of the sharing of hardships and compatibility.Nowadays the Study of Ma Yifu is becoming popular and significant.As an established master of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studies,Ma Yifus high academic achievements are undeniable.A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es on Ma have proved i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and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 Yifu and Chekiang University,which may help us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aster.
Ma Yifu;National Chekiang University;guest lectures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4.11.041
2014-11-04[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7-04-30[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CN33-6000/C
2013年度浙江大学校史研究重点课题(XSYJ2013-04)
李杭春(http://orcid.org/0000-0001-7102-0605),女,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人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主题栏目: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