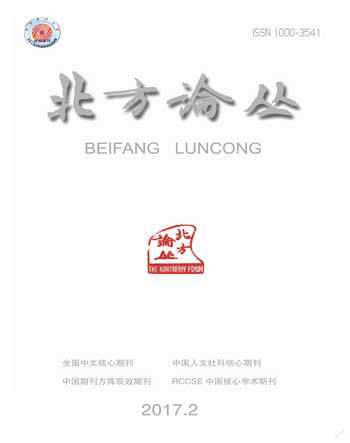美国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和种族操演
2017-05-30董晓烨
[摘要]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和文化霸权的心理投射下,东方被塑造为他者,以其贫穷、软弱、落后和神秘烘托西方的富有、强大、先进和理性。汤亭亭、黄哲伦、赵健秀、徐忠雄等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华裔男性气质建构问题进行深刻的思索,他们创作的华人男性形象或是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包容性,或是极具勇气、魅力和反叛等支配型男性气质特征。无论是美国主流媒体,还是华裔作家对华人男性形象的种族和性别身份的操演,都是为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虽然华裔作家内部对如何建构华人男性气质尚有争议,但他们的创作不约而同地展現出反政治压迫、反种族歧视和反文化强权的创作立场。
[关键词]当代华裔;美国写作;华人男性形象;性别操演;种族操演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61-07
Abstract: Under the pressure of Orientalism and cultural hegemony, orient is produced as Other with its features of poverty, powerlessness, underdevelopment and mystery to contrast prosperity, power, development and advancement, which are regarded as western features.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Maxine Hong Kingston, David Henry Hwang, Frank Chin and Shawn Wong for instances speculat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male images complex, dynamic and involving or gallant, charming and rebellious. American main stream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perform Chinese American male images for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purposes. The latter may not share the same perception of what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y is, whereas their works no doubt deny political oppressi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without prior consultation.
Key words: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writing; Chinese male images; gender performativity; racial performativity
就美国少数族裔人群而言,“身份远非种族问题那么简单,其中还蕴含着阶级、性别、性征、族裔文化、地缘文化、空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年龄等问题”[1](pp.xi-xii)。其中,性属与族裔性的关系最为密切。族裔文学中往往蕴含着性别隐喻,种族优越感与性别叙事常常被人为地牵连在一起。美国的主流叙事语境生产出的文化观念是“恰如男性比女性优越,某些民族同样比另外一些民族更为优秀”[2](p.71)。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体制和文化霸权的心理投射下,东方被塑造为他者,以其贫穷、软弱、落后和神秘烘托西方的富有、强大、先进和理性。这样的东方主义思维转化成性别隐喻,折射在《蝴蝶夫人》和《西区故事》等有关东方臣服于西方的、感伤的罗曼史中。
在这样的类型叙事中,美丽、柔弱而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女性为了获得西方男性的爱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性别优势暗示种族优势,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主宰和顺从的关系喻指西方和东方之间的统治与臣服的关系,由此形成有关东西方交往的性政治。在有关种族和文化的性政治中,西方主流媒体将东方塑造成意识形态化的他者,以此实现对东方的话语控制。在主流话语的反复演绎下,“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3](p.57)。在这样的话语管制下,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同样被刻板化和定型化。
如果说主流媒体出于生产、复制和维持种族隔离的目的而创造出制度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一系列的话语与权力的过程就是种族操演(performativity)的过程,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这种本质化的种族主义刻板形象进行反思和解构的过程,同样是一种种族操演,与其相关的性别操演过程。近年来,“操演”逐渐成为性别研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概念之一。
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这部当代性别理论研究的经典和奠基之作中,朱迪斯·巴特勒首次提出,性别身份是通过操演而生成的,是后天的文化建构,而不是先天的自然生成。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女孩”就是性别建构的开始。这一基本的质询和命名过程,既是为了设立界限,也是权威对规范的重复和反复灌输。被“质询”为“女孩”的主体,在规范的“反复灌输”下,被迫按照规范所质询的性别特征不断地模仿和表演,将自身塑造为权力话语所质询的主体。作为复杂文化建构的性别身份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复制和演绎,成为话语和权力建构的有效助益。所谓的性别麻烦就是因为不遵从已经确立的性别规范,而为性别带来的“流动性、颠覆性和多样性”[4](p.34)特征。在《沉重的肉身:性别的话语限制》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提出: “种族也是可以被操演的。”[5](p.275)在文化霸权的体制下,东西方文化被设置为二元对立的模式。这种本质主义和本体论的规训话语反复演绎西方对东方的霸权立场,因此,无论是种族操演还是性别操演都是有意识的政治建构和实践。一、 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男性他者化形象的操演 华人形象的他者化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演变经历几个阶段和层次。从19世纪中叶起,华人劳工开始大规模输入美国。彼时中国国内贫困凋敝,而美国的工业化和帝国主义扩张迅速崛起和发展。中国衰落的政治、经济、军事局势使其国际形象跌至低谷。西奥多·罗斯福在1899年的一篇演讲中,公开宣称:“中国人胆小、软弱、懒惰、不思进取,因此,如今唯有承担恶果……最终将被那些具有雄性冒险特征的国家给远远甩在后面。”[6](pp319-322)这种舆论宣传比较有代表性地表明,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偏见。文学人物在具体语境中的角色意义受到文本外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在上述言论的主导下,“无论是在布莱特·哈特、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弗兰克·诺里斯、约翰·斯坦贝克等主流作家笔下,还是在流行文学中,都涌现出了大量被肆意歪曲的华人刻板形象”[7](p.68)。残暴的东方君主、鸦片贩子、不可教化的异教徒、滑稽而忠诚的仆人、廉价而肮脏的苦力等反面华人男性形象充斥于当时的主流文学。
华人男性在当时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典型地体现出福斯特式的扁平人物的特征。扁平人物具有“某种单一的观念或特质……没有深度, 容易预测、识别和记忆,并往往具有类型性、喜剧性和反讽性”[8](p.47)。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形象的类型化认知,体现东方主义的二元化思维特征。那些顺从的华人被认为是好的,而那些挑战西方主流文化的华人则被认为是坏的。当代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先行者赵健秀将这种二元化的霸权定型形象归纳为“种族主义之爱”和“种族主义之恨”。两种觀点都“不仅是对成为某种歧视的替罪羊的虚假形象的刻画, 还是一种更为含混的反射和内射, 是隐喻和转喻性的策略”[9](p.68)。它们是具有很强的种族主义色彩的本质主义臆断,体现美国主流社会的主观的和东方主义式的猜想,他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将华人群体孤立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
西部开发所引发的华人移民的涌入触发西方语境对“黄祸”(yellow peril)的恐慌。中国移民的吃苦耐劳和坚毅隐忍,使他们较西方移民更容易适应西部艰苦的生活而定居下来,因而美国西部尤其是西海岸的华人人口逐渐增多。华人与西方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背景使西方主流媒体心生警惕,担心大量华人移民的涌入会动摇白人的统治和破坏西方文化的纯洁性。
为了保持体制和文化的稳固,西方主流社会将华人移民置于生物学决定论和道德劝诫的框架中,将他们质询(interpellation)为文化和政治的他者。因此,这一时期的华人形象常与引起西方社会不安的诸因素联系在一起。华人被操演为“令人悲哀的异类”[3](p.36)。他们或是放纵、懒散、愚昧、落后的未开化的人种,或是残忍、神秘、邪恶、狡诈、堕落的罪犯。这种种族主义之恨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傅满洲(Fu Manchu)这个“整个东方人种的残酷和狡猾”[10](p.165)的化身。在法农看来,“每种神经症、每种不正常表现、每种情感过敏……都是文化境遇的产物。换言之,在书籍、报纸、学校、教科书、广告、电影、收音机的推波助澜之下, 一系列假设和主张慢慢地、微妙地渗透进意识, 并塑造了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的看法”[11](p.152)。1913—1959年间,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的13部长篇、4部短篇和一系列的傅满洲电影,将妖魔化的东方形象和邪恶而神秘的东方力量深深地植入西方读者的脑海。
性别形象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动态建构。随着华人的经济能力的增强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更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华人男性的刻板形象由邪恶转变为臣服。20世纪上半期,不断出现的种族纷争又使种族主义者试图拉拢不甚激进的华人群体, 将华人从潜在的敌人塑造成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华人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历角色转变。从反面敌手(antagonist)转变为正面的主人公(protagonist)。
这种“种族主义之爱”的集中体现就是华人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这个美国主流社会的驯服的附属品形象。美国作家厄尔·比格斯创作于1925—1932年间的6部小说和好莱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热映的47部电影,将陈查理这个矮胖、行动迟缓却思维缜密,操着蹩脚的洋泾浜英语的,爱引用中国格言的华人侦探塑造为代表“种族主义之爱”的,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华人刻板形象。
傅满洲和陈查理呈现出的都是扁平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漫画式的刻板形象特征。人物特征模仿性的消减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物的功能性和符号性特征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出人物同时具有“模仿性”(mimetic)、“主题性”(thematic)和“虚构性”(synthetic)等三种功能。其中,模仿性强调人物像真人,主题性认为,人物为表达主题服务,虚构性强调人物是人工建构物。在阅读叙事作品时,读者既会感受到人物的虚构性,也会觉得这个人物在故事世界里是真实的。另外,由于小说家创作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表达特定主题,因此,人物塑造必然是为特定主题服务的[12](pp.9-14)。[12]。美国大众传媒中的有关中国人物的扁平形象在引起噱头和带来滑稽可笑的接受效果的同时,在一片轻松幽默中宣传美国的主导话语,并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主流社会所塑造的华人形象,无论名为傅满洲,还是陈查理,实际上都丧失心理型人物所具有的真实性,沦为文本符号和功能,成为“修辞格的一种经过(和返回)场所”[13](p.179)。另外,无论是邪恶、野心勃勃、性变态的傅满洲,还是温顺、谦卑、女人气的陈查理,集中指向的都是主流媒体对华人男性气质的阉割。因此,“阶级和性别具有相似性”[14](p.140)。华人男性人物形象的抽象存在就是为了凸显白人男性的以强壮、有力、极具竞争性和领导力为特征的支配型男性气质罗伯特·康奈尔将男性气质划分为四类:支配型(hegemony)男性气质(在主流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从属型(subordination)男性气质(受压迫、受歧视的一方,如同性恋男性对异性恋男性的从属)、共谋型(complicity)男性气质(指那些支配型男性气质不明显又从支配型男性气质中受益或潜在地支持男性霸权的男性)、边缘型(marginalization)男性气质(指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集团的边缘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16](p.104)。在东方主义的霸权话语的统治下,白人男性被赋予支配性特征,而华人男性则由于在社会和文化上处于从属地位,被边缘化而成为边缘型男性。。为了烘托这一西方男性气质的假设,华人男性被强制赋予从属型和共谋型男性气质特征。
综上所述,华人男性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生产对象,有关华人男性的意识形态偏见被反复强化和重复。他们失去似真性和模仿性,而更多具有的是文化符号的意义和具体的社会功能。这种他者话语的强制建构就是华裔美国人所面对的“性别的奥秘”和社会规约。在种族主义的语境下,华人男性形象的定型化、反面性和漫画性引起当代华裔作家的警惕和不满,他们在各自的创作中,从不同角度对主流媒体中的华人男性形象误现做出猛烈的抨击和深刻的反思。二、 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真实华人男性形象的操演 在其代表作《蝴蝶君》(M. Butterfly,1988)中,被誉为“当今美国戏剧界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和最有才华的剧作家”[15](p. 72)的黄哲伦塑造一个备受争议的华人男性形象。剧中的主人公宋丽玲男扮女装与法国外交官伽利马同居20年,利用身份的伪装窃取情报,真相败露之后,舆论哗然。宋丽玲这一文学角色将一个前所未有的华人男性形象推至美国主流媒体面前。在敌意的语境下,宋丽玲以性别操演的方式建构一个具有主动性、复杂性和解构性的与以往不同的华人男性形象。
宋丽玲是首位出现在美国白人读者面前的主动而非被动进行性别操演的华人男性角色。从文本话语来看,华人男性形象在整个的叙事体系中,由边缘逐渐走向文本叙事的中心,由原本的辅助性角色变成叙事中的主要人物。从叙事内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东西方的从属话语模式的解构和颠覆:宋丽玲取代伽利马,成为故事的权力关系网络中,具有控制力和权力的一方;反之,伽利马处于从属地位,成为被控制和利用的一方。在东方主义的语境下,宋丽玲进行有限的自主身份建构,并在东西方罗曼史中起到主动的引导作用。宋氏以精心设置的行动策略主导他与伽利马两人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手安排伽利马的命运走向,最终以臣服的姿态发声,从政治上的失语者和隐身人变成政治主体,完成华人男性的政治实践。
宋丽玲进行性别操演的实践也赋予角色以复杂性,这使得华人男性形象首次被赋予圆形人物的特征,因而较以往的扁平人物具有更多的似真性和可信性。宋丽玲较以往的华人男性形象具有更为丰富的心理和人格特征。宋丽玲打破以往华人形象非好即坏的两分性质,华人男性的内心情感首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人物的模仿性和主题性具有内在关联。作为语境的产物,华人男性只能在自己所在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限定下,选择自己的性别身份,而华人男性通过身份操演赋予自身性别和文化身份多样的动态可能性。宋丽玲在一定的阈限内对他被设定的身份进行反复演绎。因此,宋丽玲女性化的变装行为是美国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象的性别操演和华人男性主体有意识的性别倒错所导致的双重后果。
宋丽玲进行性别操演的政治意义在于,在禁忌的限制中,对文化霸权的话语质询进行有效的抵抗。宋氏利用性别隐喻来颠覆蝴蝶夫人式的东方刻板形象,实现华裔身份的自我表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宋丽玲对东西方交往中的权利运行机制具有警觉性。宋氏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主流媒体对东方形象的性别角色预设。宋曾向读者表述:“我是个东方人。作为一个东方人,我从来不可能完全是个男人。”[17](p.130)宋同样敏锐地认识到,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因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因为我们“没有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大笔的钞票”[17](p.129)。宋认识到性别的形成和权力话语的紧密联系。因为对蕴含着社会等级秩序的性别政治具有明确的先期认知,宋丽玲对伽利马所向往的东西方交往的罗曼史嗤之以鼻。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样想一下,假如某个金发碧眼的返校节女王爱上了一个矮小的日本商人,你会说什么?这日本人商人残酷地对待她,然后,这家伙回国了,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这期间她对着日本商人的照片祷告,还拒绝了年轻的肯尼迪的求婚。 接着,当她知道这个日本男子已经再婚后,她自杀了。现在,我相信,你会认为这个女孩是个精神错乱的白痴,对不对?”[17](p.29)总的来看,宋丽玲这一文学角色打破长期存在于美国主流媒体中的华人刻板形象的坚冰。自此,这样具有复杂性、动态性和反叛性的华人男性形象在其他作家笔下也屡有出现。
汤亭亭是目前最受关注也是影响最大的华裔美国作家。在《引路人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1989)一书中,汤亭亭同样创作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华裔男性形象。小说的主人公是23岁的第五代华裔青年惠特曼·阿新(Wittman Ah Sing)。惠特曼的身上体现出的是鲜明的反文化精神和“赵健秀式的愤怒的青年的传统”[18](p.xi)。惠特曼留着长发和垮掉派式的胡须,爱穿牛仔长靴;毕业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英文系, 既是公车上的朗读员,又是剧作家,在旧金山建立戏剧团体;把《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当作亚裔美国文学的重要遗产,将关公尊为亚裔美国人的祖先,“战争和戏剧之神”[19](p.216)。读者在惠特曼的身上已很难再找到黄祸、顺民或模范少数族裔的影子。作者所塑造的不过是一个受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影响的典型的美国青年,惠特曼的身上积聚强烈的真实性和模仿性。汤亭亭曾表示,赵健秀就是惠特曼的原型[2](p.149),也曾表明如果她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话,也会成为惠特曼那样的人[20](p.74),汤甚至认为,惠特曼的身上也有其丈夫的影子[21](p.170)。这说明,惠特曼这一人物具有较强的模仿性。人物的真实性既体现为个性的逼真,又体现为对群体共性特征的隐喻。
在力图操演真实的华裔男性形象的同时,汤亭亭同样在惠特曼这一人物身份赋予强烈的主题意义。主题性特点和功能不是人物与生俱来的副产品,而是作者有意的艺术创造。《引路人孙行者》的人物形象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的隐喻功能,具有复杂的意义指涉。惠特曼首先被操演为一个文化反英雄的形象。惠特曼深受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一个文化叛逆。这种叛逆精神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 更是人格的重要体现。惠特曼嬉皮士派头十足,吸食大麻, 迷恋爵士乐, 享受不受约束的生活, 并从中感受到“难言的自由”。惠特曼也是一个旅行者和精神漫游者的形象。《引路人孙行者》的第一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尤利西斯》的第三章。史蒂芬和惠特曼都是年轻的艺术家。两个人都思考着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诘问。
汤亭亭借用互文性来说明她所操演的华人男性是典型的西方反英雄的继承,但是,作为华裔,惠特曼又被质询为美国社会中的边缘人。场景的随意拼贴、地点的不断迁移、意识流等叙事手段的运用都暗示主人公身份的不确定性。惠特曼虽然毕业于名校, 却是个失业者;虽有雄心壮志, 致力于剧本创作,其作品却得不到白人读者的认可,只能在唐人街找到剧场与观众。惠特曼虽想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却并未为美国所接受。通过惠特曼的形象,华裔美国人的存在困境和身份的不稳定性被前景化。
为了对抗被边缘化的困境,惠特曼将自身操演为“美国猴王”。 作为常常出现在美国族裔文学中的原型人物,猴子的身上具有鲜明的族裔隐喻。“白人总是将黑人或是其他有色人种看作是猴子”[22](p.105)。白人自诩为文明世界的人,将少数族裔贬为非人的动物,或是原始的初具人形的次人类。“猴子”这一种族主义的称谓带有极大的侮辱性。一方面表明亚裔在美国社会无家、失业、贫穷的地位;另一方面,表明亚裔所遭受的来自白人社会的偏见、威胁、侮辱、暴力和不公。然而在少数族裔作家的创作中,“猴子”这一人物原型被操演出积极的意义。在《表意的猴子》一书中,盖茨用“表意的猴子”这个意象来解释黑人文本所具有的双重声音和表意功能。盖茨认为,黑人文学通过运用修辞性的戏仿来重复、修正和颠覆已存在的白人文学中的形式、范式、话语和意义等。这正如猴子用恶作剧戏耍狮子和大象在此,猴子成为一个恶作剧精灵(trickster)。恶作剧精灵源自美国黑人文化中的神话形象。盖茨利用福柯的文化考古学的方法,发现在非洲文化之中,始终存在埃苏(Esu)这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埃苏是约鲁巴(Yoruba)神话传说中众神的使者。这一形象在口述传统中代代相传,在古巴、海地、美国等不同地点有不同的形象和名称。。通过修辞和语言的诡计,黑人文学达到对抗刻板形象和反抗压迫的目的,以此,作家表述身份的多样和流动。惠特曼将自身操演为恶作剧者,一个“将美国文化和猴子形象交织在一起的新猴王”[23](p.98)。作家打破已有的疆界,将(旅)行者/吸毒者/引路人和猴的形象相结合,暗示惠特曼将中国传统与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进行了有机结合。惠特曼身具孙悟空和引路人、反传统和反文化、中国和美国两种文化的特征,具有极强的反叛性。如同孙悟空一样,惠特曼既有大闹天宫的反叛, 又有偷蟠桃盗仙丹的捣蛋;既有智斗妖魔时的机智,又有不避艰险的勇气。更为重要的是,惠特曼和孙悟空一样,是一个居间的角色。他们都具有非正统的身份,一个是石猴,一个是华裔。居间的身份又赋予他们在两个领域穿行的特权。孙悟空跨越生死和神妖的界限,而惠特曼跨越文化界限,这使得他们的身份都具有流动性,永远处在进程当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与黄哲伦着重展现中美交往中的极端事例不同,汤亭亭更为关注华裔在当下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着力操演华裔男性文化身份的越界、杂交和反叛的属性。然而,在赵健秀等人看来,无论是汤亭亭,还是黄哲伦对主流话语的认知暴力所进行的反抗都不彻底。赵健秀和徐忠雄等人试图建构华人男性的英雄传统,以从根本上驳斥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男性形象进行误导性的性别和种族操演的谎言。三、 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对华人男性支配型气质的操演 被誉为“现代亚裔美国文学之父”[24](p.67)的赵健秀在其创作中,充分发挥文学的战斗功能,将颠覆消极的、虚假的、被阉割的华人/华裔男性形象, 恢复华人/华裔男性的阳刚气概和树立华裔男子的主体性和历史合法地位作为其终身奋斗的目标。在其首部长篇小说《唐老亚》中,赵健秀塑造一个理想化的、具有支配型男性气质并具有自觉的文化身份的华人男性形象——金·达克。
为了凸显华裔男性气质,赵健秀将金和关公的形象融为一体。“关公是华人崇拜的偶像,是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象征。赵健秀发掘并重述了关公等英雄人物,并将他们认作体现中国古代侠义男性主体意识的英雄形象和代表了自由、反抗和创造等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典型”[7](p.65)。与赵健秀20世纪70年代短篇小说中懦弱、平庸和猥琐的父亲形象不同, 金是华人男性英雄主义气质的典范。金是成功的餐馆经营者和出色的厨师。金具有侠义心肠,常常接济食不果腹的芳芳姐妹。金是一位自律和出众的演员:为了演好关公,在演出前三天禁食荤腥;前两天的最后一次彩排之后不见任何人;前一天休息和冥想。更为重要的是,金是一位称职的父亲和文化导师,对种族歧视和文化帝国主义具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唐老亚的自我殖民倾向, 金引领着困惑的儿子找到身份归属。从父亲那里,唐老亚懂得责任与历史的意义。金教导他:“一个人要想成为男性的楷模,就必须做到纯洁、禁欲,具有个性,同时控制好男性常有的暴力倾向。”[25](p.156)当唐老亚因为美国主流历史抹杀华人的功绩而烦恼不平时,金不失时机地向他解释中国人的为人处世态度:“历史是战争,不是游戏!……你必须自己保留历史,不然就会永远失去它。这就是天命。”[25](p.122)
华人男性的担当和勇气还在修建铁路的华工身上得以操演。不同于以往贫困、肮脏、逆来顺受、默默无闻的苦力形象,赵健秀对华工的性别操演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在唐老亚的梦境中,关公、李逵、岳飞等英雄化身为华裔祖先,在北美大陆开创、拼搏。在查阅华工修建铁路的历史史料之后,华人男性的支配型男性气质生动地展现在唐老亚的眼前。“关姓汉子手握克罗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的六响枪,在克罗克还没反应过来之前,就手握缰绳,跃上马鞍。他策马忽东忽西,溅了克罗克一身泥浆……克罗克在后面跑著追赶,一身白西装早已变了颜色。关姓汉子在淤泥中疾驰奔往华工的帐篷,用克罗克的六响枪连开三枪……‘明天!10英里!关姓汉子吼道:‘10英里的铁轨!”[25](p.77)上面的场景显示,关姓工头不但骁勇无比, 而且颇具领袖气质。关领导华工罢工追回拖欠的工资,带领华工与爱尔兰工人竞赛修铁路并创造10个小时铺设10英里铁轨的世界纪录。除此之外,关在与白人打交道时,也处处占上风。铁路公司的股东克罗克,这个白人男性个性和创造力的化身,在关姓工头面前狼狈不堪。关姓工头的形象挑战美国官方历史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消解华人生性“懦弱懒惰”和“缺乏进取”的刻板化形象。华工并非白人教师米莱特在课堂上,宣称的被动、胆怯、内向、缺乏自信和无能为力,而是充满阳刚之气,华工可以一天铺10英里的铁路, 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引爆炸药打通隧道。华人男性有着久远的英雄传统,其中既有关公和岳飞的忠义, 又有李逵与宋江的反叛;既有战场杀敌的豪迈,又有律己时的冷静克制。然而,这一切都在白人主流话语霸权下被抹杀。于是,在东方主义的凝视下,重申华人的英雄传统,在被他者化的社会中确立华人男性的身份就成为“唐老亚”这个华裔英雄传统的接受者和继承者所承担的“天命”。
赵健秀对华人男性的性别和种族形象进行深入的探讨。赵氏将男性气质与中国英雄传统相联系,将华人修建铁路的历史与中国古典小说的英雄故事相结合,试图在华人文化环境和传承之间建立关联。关公、父亲和祖先融为一个共同的华人英雄形象。在小说的最后,唐老亚继承进攻性的、强悍的、梁山好汉式的华人男性英雄传统,以此反驳华人“胆小、软弱、懒惰、不思进取”[6](pp. 319-322)的刻板形象,成为华裔英雄传统的代言人。赵健秀通过强化华裔男性形象来争取权利的做法产生广泛的影响。徐忠雄、李健孙、雷祖威等人继续拓宽赵健秀所开辟的道路,以塑造勇敢而富有魅力的华人男性形象为己任。
徐忠雄和赵健秀同为《唉咦!亚裔美国作家文选》和《大唉咦!华裔与日裔美国文学选集》这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选集的编者。他对美国主流话语对华人男性形象的消极操演极为敏感,猛烈抨击主流媒体所操演的同性恋和性变态的傅满洲和性无能的陈查理倾向。“在美国电影与电视中,亚裔男性极少以丈夫、父亲或情人的身份出现。他们要么是呆板的花匠、仆人、厨子、冷酷的生意人,要么便是一个败于意大利裔少年空手道新手脚下的所谓中国功夫大师”[26](p.64)。为了驳斥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男性的去势化和种族主义者有关种族阉割的想象,在其小说《美国膝》(American Knees,1995)中,徐忠雄延续赵健秀对于华人男性的性魅力的操演。徐忠雄不遗余力地展现华裔男性的身体魅力,以至于许多读者认为,《美国膝》一书中“露骨的性描写”[27](p.124)过多。徐忠雄对此的解答是:“这些性描写是有政治意义的。翻开华裔文学史, 你会发现亚裔文学中缺乏对亚裔的性身份的刻画。在电影中也一样。如果电影中有华裔男性性生活的片断, 那也是扭曲的、类型化的描写。他们要么在强奸,要么有性功能障碍。所以说《美国膝》中有关雷蒙德性生活的片断非常重要, 性的身份是有关种族问题、身份问题探讨中重要的一环。”[27](p.124)“单纯赋予华人男性以支配型的白人男性气质似乎还不足以强调华裔男性的雄风。”[7](p.65)徐忠雄笔下的华裔一反以往美国主流文学中不可捉摸的、狡猾的、傻气的、滑稽的、奴性十足的、性变态的或是毫无性感的(尤其指亚裔男性)形象,成为美丽动人、魅力超群的人物。
伍德“是唐人街王子,是整个城市的王子”[28](p.25)。他长得很像爱德华·G罗宾森,个子不高,但结实有力。他开着凯迪拉克,受到白人女孩子的追捧。故事的主人公雷蒙德更是男性魅力的体现。他身高6英尺,长相帅气。在布兰达眼中,“雷蒙德非常性感……他的颧骨很漂亮。他有笑起来仍然神采奕奕的大眼睛、秀挺的鼻子、高个子、时髦的发式,虽然不及西方人腿长,但衣着考究”[28](p.66)。在欧若拉眼中,“你(雷蒙德)可以开一间魅力学校,‘魅力有何坏处?是你的座右铭”[28](p.66)。雷蒙德举手投足间无时无刻不在散发魅力,在与他的离婚律师的短暂会面中,这位职业女性手足无措,始终在担心“他们坐得太近,她的上衣太紧,裙子太短”。想象他在盯着她的红色脚指甲[28](p.13)。
作者如此直白地、不遗余力地操演年近四旬的主人公的身体魅力,其用意令人深思。在当代美国主流文化当中,亚裔男性的身体受到规训,“扮演的仍是持续了百余年的滑稽、胆小、无能、失败、毫无男性魅力的漫画式形象”[7](p.71)。在这样的语境下,作者以塑造身体来建立权力、知识、意义和欲望的创作意图十分明显。徐忠雄以强化华裔男性形象和描绘亚裔男性的理想一面,来反抗常规的意萨斯实施策略,进而强化自身的权力。因此,文本中随处可见对于亚裔身体美学的称颂。在女性人物的眼中,中国男性散发着性感,是“气味清爽、沉默寡言的李小龙”[28](p.72)。泰裔男孩招人喜爱,因为他们彬彬有礼而且有美丽的肌肤[28](p.92)。“亚裔男性确实有很棒的身体……他们体毛少,而且有李小龙式的肌肉……拥有男子气概、英雄气质和强壮体魄”[28](p.91)。上述对于亚裔男性精英从内至外的全面展現,在凸显真实的身体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符号系统。可以说,徐忠雄似乎将他和赵健秀在20世纪70年代所强调的亚裔美国感性具象化为身体,通过创造理想的身体形象来定义自身。
按照这样的理论假设来理解,小说中那些令读者困扰的性爱场面也就具有它们存在的价值。如同作者所说:“这些描写有助于塑造华裔的性的身份(sexual identity),这样小说中的华裔人物才丰满, 他们的族裔身份才完整。与此同时, 对雷蒙德性爱生活的描写也是我用来反抗亚裔在美国社会中被忽视的一种方式。”[27](p.124)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得知,徐忠雄笔下的身体叙事是一种自觉、有意的设计,而非自发、随意的显现。身体不仅意味着物理维度,还是一种隐喻的存在,它的符号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物理存在。通过将亚裔身体直接暴露在小说的读者和电影观众面前这种极端的方式,徐忠雄给读者塑造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亚裔身体,突显亚裔身份的可见性。通过自我、肉体和欲望的全面释放,作者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实践,令身体超越它的外部形貌,具有政治意义。
综上所述,在当代后种族主义文化语境下,种族问题往往包含性别隐喻。作为文化生产的结果,族裔文学中的性别形象不但是社会的,而且是自我的建构。美国主流媒体和华裔作家从不同的政治诉求出发,操演出迥异的华人男性形象。作为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建制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黄哲伦、汤亭亭、赵健秀、徐忠雄等人不约而同地对华人男性形象的本质进行思考,并创作出前所未有的华人男性形象。他们或是戏剧化亚裔男性被阉割和被女性化的境遇;或是探求当代华裔男性的流动的文化身份和反叛精神;或是挖掘华人男性的雄壮、豪迈和阳刚之气;或是凸显华人男性身体的性感魅力。然而,无论是塑造真实的,还是理想的华人男性形象的努力,无论对于华人男性的复杂性、流动性和反叛性的操演,还是对于华人男性的英雄传统和男性气质的强调,实际上都表现20世纪末当代华裔作家的自觉创作诉求,即打破亚裔男性长期被消音和扭曲的历史,驳斥主流话语的文化霸权,操演正面、积极、真实、深刻的华裔男性形象。这既是时代对他们提出的需求,也是他们身为族裔作家的职责所在。时至今日,我们不禁要问,新时代的华裔美国作家是否应整合前人的成绩,执行斯皮瓦克式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建构华人男性气质的核心和传承,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力量同主流媒体中依然存在的文化霸权相抗衡。这也许是时代对于作家提出的新的要求。
[参考文献]
[1]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M].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2.
[2]Amy Ling, Between Worlds: 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 NY:Pergamon P, 1990.
[3][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4]Judith Butler, Undoing Gender[M].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5]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M]. NY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6]Theodore Roosevelt, The Works of Theodore Roosvelt[M]. 13th vol. New York: Scribner, 1926.
[7]董晓烨.《甘加丁之路》的性别政治与人物叙事策略 [J].当代外国文学,2014(3).
[8]E.M.Forster, Aspects of the Novel[M]. London:Hodder & Stoughton, 1993.
[9]Homi K.Bhabha, The Other Question:Differenc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M]. London:Routledge, 1994.
[10]William F.Wu, The Yellow Peril: Chinese-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M]. Hamden, CT: Archon Books,1982.
[11]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NY: Grove, 1967.
[12]James Phelan, Reading People, Reading Plots:Character, Proress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rrative[M]. Chicago:U of Chicago P, 1989.
[13][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14]许文博.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与性别表演理论的关系——阶级与性别的相似性[J].北方论丛,2015(1).
[15]Edith Oliver, Poor Butterfly[J]. The New Yorker, 1988(7).
[16]Robert Connell, Masculinities[M]. Cambridge & London: Polity Press, 1995.
[17][美]黃哲伦.蝴蝶君[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8]Bharati Mukherjee, Wittman at the Golden Gate[J]. The Washington Post, 1989 (4).
[19]Maxine Hong Kingston,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M]. NY: Vintage International,1989.
[20]T. Minh-ha Talbot, Outside In Inside Out[C]//When the Moon Waxes Red:Representation,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cs. NY:Routledge, 1991.
[21]方红.和平·沉默·叙述技巧——《第五和平书》创作谈[J]. 当代外国文学,2008(1).
[22]Jennie Wang, Tripmaster Monkey:Kingstons Postmodern Representation of New China Man [J]. MELUS, 1995 (1).
[23]Diane Simmons, Maxine Hong Kingston[M]. NY:Twayne Publishers, 1999.
[24]Williams Wei, The Asian American Movement[M].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3.
[25]Frank Chin, Donald Duk[M]. Minneapolis: Coffee House P, 1991.
[26]Shawn Wong, Beyond Bruce Lee[J]. Essence,1993(11).
[27]方红.命名、叙述声音与亚裔身份——徐忠雄访谈录[J].外国文学,2007(1).
[28]Shawn Wong, American Knee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1995.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文学博士)[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