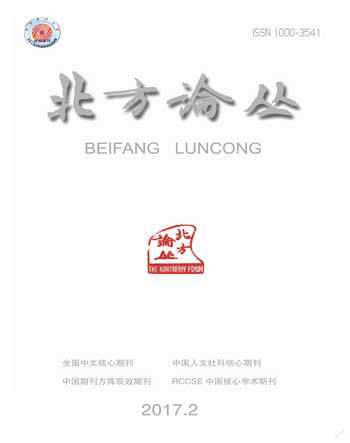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潜夫论》引用经书问题研究
2017-05-30蒋泽枫
蒋泽枫
[摘要]《潜夫论》对经书内容引用很多。在引用方式上主要有明引和暗引两种,也存在只引经书名称或具体篇章名称而不引文句内容的情况。《潜夫论》对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兼顾今古文经,体现了东汉中后期今古文经融合的发展趋势。《潜夫论》对经书的引用是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同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儒家学术观有着直接关系,是王符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理解和诠释。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的分析既突出了王符的学术特点,也再次表明了经今古文问题的复杂性。
[关键词]潜夫论;王符;汉代学术
[中图分类号]K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32-07Research on
Abstract: The Qianfulun had largely cit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itation means were mainly divided direct and indirect citation two forms, also existed the situations that only citing the name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r specific chapter names without citing textual content. Attention and focus of Qianfulun to different contents of Confucian classics were distinct, the citation to Confucian classics reflect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the pre-Qin scrip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lerical script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Qianfuluns citation to Confucian classics wa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Han Dynasty Confucian era, had a 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Wang Fus Confucian academic concept of “Mingdao, learning saints, learning classics”, was Wang Fus understanding and annot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nalysis on Qianfulun citing Confucian classics highlighted Wang Fus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lso showed the complexity between the pre-Qin script Confucian classics and clerical script Confucian classics.
Key words:Qianfulun; Fu Wang;Academic of Han dynasty
一、引用經书的具体方式
(一)对经书的引用方式主要分明引和暗引两种形式
明引是指那些直接将《诗》《书》《易》《左传》等书名及其所载相应内容,或人名及其所说之言论并存,诸如《思贤》:“《易》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衰制》:“《文言》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渐矣,由变之不蚤变也。”《忠贵》:“《书》称:‘天工人其代之。”《本政》:“《诗》伤:‘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救边》:“《春秋》讥‘郑弃其师。”《三式》:“《传》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述赦》:“是故周官差八议之辟。”《实贡》:“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巫列》:“《孝经》云:‘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暗引是指不提及任何书籍名称或人名,但其引用内容出自相应典籍或者相应人物的言论。除上述明引所列的一类例子之外,均属于暗引之列。如《边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此语出自于《小雅·裳裳者华》。《班禄》:“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此语出自于《尚书·尧典》。《本政》:“性相近而习相远。”此语出自于《论语·阳货》。《忠贵》:“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此语出自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另外,由于古代学术研究并没有现如今明确的学术规范,所以,从《潜夫论》引用的文字内容上来看,无论是明引或是暗引,都存在着在不改变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对原文内容进行化用改变的情况。明引除少数引文与今本不一致之外,绝大多数情况多是引用原文内容的,而暗引则对原文进行化用的情况较多。将引文内容同经书原文进行对比,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些特点,此处不再举例赘述。
(二)对经书内容的引用存在只引用经书名或具体篇章名的情况,即引用经书之义或各个篇章内容之义
如《赞学》:“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救边》:“《春秋》讥‘郑弃其师”。《断讼》:“《春秋》之义,责知诛率。”这三处引用都是对经书名称的直接引用。在具体篇章名称的引用上以对《诗经》的引用最为明显。如《赞学》:“《国风》歌《北门》,故所谓不忧贫也。”《交际》:“夫处卑下之位,怀《北门》之殷忧。”《赞学》:“退赋《桑柔》之诗以讽”。《思贤》:“虽有尧、舜之美,必考于《周颂》。”《思贤》:“虽有桀、纣之恶,必讥于《版》《荡》。”《浮侈》:“《七月》诗大小教之,终而复始。”《班禄》:“其后忽养贤而《鹿鸣》思,背宗族而《采蘩》怨,履亩税而《硕鼠》作,赋敛重而《谭告》通,班禄颇而《倾甫》刺,行人定而《绵蛮》讽。”《断讼》:“贞女不二心以数变,故有匪石之《诗》。”《边议》:“《诗》美薄伐”。《交际》:“而望日忘之贵,此《谷风》所为内摧伤。”《交际》:“所谓平者,内怀《鸤鸠》之恩。”《志氏姓》:“诗人忧之,故作《羔裘》,闵其痛悼也。”《志氏姓》:“《匪风》,冀君先教也。”除此之外,其他经传也偶有提及,如《卜列》:“故《鸿范》之占,大同是尚。”《叙录》:“《洪范》忧民。”通过对相应引用经传或具体篇章内容的了解,可以发现这些引用主要是借用或发挥其经传或具体篇章的内容大意,以此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对经书内容的侧重和取舍
(一)对各类经书的关注侧重点不同
不同的学者虽然在广泛引用经书内容作为立论基础方面有着一定的共性,但对于经书内容的选择和使用上情况却不完全相同,即每个学者对于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通过一个简单的量化分析,大致可以看出王符对不同经书内容的关注度和侧重点是不同的,其中引用三《礼》共计10条、引《诗经》共计111条、引《尚书》及《尚书大传》共计52条、引《周易》共计64条、引《春秋左传》共计103条、引《春秋公羊传》共计4条、引《论语》共计57条、引《孝经》共计5条。相比其他四经来看,王符对三《礼》内容引用相对较少,共计10条。其中引《周礼》《仪礼》各1条,引《礼记》6条,引《大戴礼记》2条。这种情况的出现首先同东汉时期三《礼》的研习者较少有关,如《儒林传·卫宏传》云:“中兴以后,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其次,更重要的是同三《礼》本身所侧重内容有直接关系。《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相比前两者,《礼记》的内容更适用于王符对于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分析论证的需要,所引6条内容涉及人才使用问题、俸禄等级问题、丧葬问题、祭祀问题、分封问题,因此,在引用数量上略占优势。对于《孝经》而言,汉代强调以“孝”治天下,《孝经》自然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但《潜夫论》中对《孝经》的引用次数同样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内容过于单一,不适用于王符立论写作的需要。相反,被引用最多的《诗经》便具备这种特性,孔子称“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正是基于《诗》的这种特点,古人著作通常以《诗》的内容作为论述的依据,战国时期的《孟子》《荀子》,以及其后的两汉诸子著作均对《诗》的内容征引很多。王符通過自己对《诗经》的理解,将其应用到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阐述之中,以诗言其志。五经之外的《论语》内容在《潜夫论》中出现的次数也非常之多,这表明王符对孔子是十分崇敬的,圣人之语也自然成为王符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说事论理,衡量、判断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引用经书体现出以今文经学为主,古文经学为辅,兼顾今古文经学的特点
“王符虽然是最早的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而仍然是今文经学的信奉者”[1](p614),这种情况是由今古文经学自身学术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恰好符合王符社会批判思想构建的需要和汉代中后期经学发展趋势所决定的。首先,王符身上兼顾了今古文经学各自的学术特点。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视孔子为教育家、思想家,所以将五经顺序定为《诗》《书》《礼》《易》《春秋》,由浅入深;而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视孔子为史学家,将五经顺序定为《易》《书》《诗》《礼》《春秋》,按时间顺序排列。王符在《赞学》说:“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他认为,五经在对人的教育方面是由浅入深的,从这方面阐述来看,他有明显的今文经学的特征倾向。另外,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分析的需要,王符在构建其批判思想时,更多地要发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评论时政的功能特性汉代许多儒生都利用今文经学中倡导的阴阳、言灾思想去指陈时弊,匡扶政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是这批儒生的理论依据。他们借助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揭露政治弊端,向统治者进谏,以求改善政治。这种说法虽然蒙着一层神秘、迷信、荒诞的色彩,但却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有补于改善政治的建议。西汉一代,自董仲舒后,昭、宣之时的眭孟、夏侯胜;元、成之时的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之时的李寻、田终术等,都利用今文经学服务于现实政治。如京房称:“陛下继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汉书·京房传》)以此暗示元帝用人不当,影射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如翼奉在元帝时上疏,借助关东大水、饥疫、地震等天灾人祸现象,劝皇帝夺外戚之权,“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汉书·翼奉传》)由于元成哀平之际政治日益腐败昏暗,这些人借助今文经学中阴阳灾异思想的言论活动就愈发显得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以及阐发义理的特点,通过上述对经传的引用方面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在分析具体问题,需要拿出有力的立论证据材料考证史实时,如在分析上古帝系,以及姓氏源流演变问题的时候,王符更多的是引用史料丰富翔实的《左传》,而不是侧重阐述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和《谷梁传》。其次,除了今古文经学自身特点的原因之外,王符对今古文经的兼用情况也完全迎合了此时期兼通今古文经的学术趋势。西汉末年兴起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是由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为利禄和学术统治地位而展开的相互争斗,尽管先后出现了四次相互攻讦的大争论,但因为今古文经学派在维护封建统治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这成为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政治基础。另外一些现实因素也促使了两者的最终合流。其一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博学通识的古文经学大师,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后汉经学盛于前汉者,有二事。一则前汉多专一经,罕能兼通。经学初兴,藏书始出,且有或为《雅》,或为《颂》,不能尽一经者。若申公兼通《诗》《春秋》,韩婴兼通《诗》《易》,孟卿兼通《礼》《春秋》,已为难能可贵。夏侯始昌通五经,更绝无仅有矣。后汉则尹敏习欧阳《尚书》,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景鸾能理《齐诗》、施氏《易》,兼受河洛图纬,又撰《礼内外说》。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蔡玄学通五经。此其盛于前汉者一也。”[2](p84)相对于专守一经的陋儒,这些博学多识的古文经学者成为促进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学术基础。其二是此时的今文经学自身出现了严重问题,逐步走向了烦琐化。虽然在东汉中期以前,今文经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五经皆列于学官。但随着经学的不断发展,今文经学中的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今文经学家从信仰主义出发,他们认为,所有的经书都是圣人之言,经书中的一字一句都寓有圣人的微言大义,这直接导致了儒生们对经典的解释章句支离蔓衍,极其繁杂。桓谭《新论》云:“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3](p1724)王充说:“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4](p583)经上述,可以想象当时今文经学的解释多么荒诞和烦琐。然而,对于这种弊病早在刘歆时就已被其揭露指出,他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批评今文经学家们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5](p1970)“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5](p1971)等等。今古文经之争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刘歆批评今文经学专务繁琐训释,固守师说而不知返本求经,却是一语言中其弊。东汉以后,今文章句的减省工作一直在进行。汉章帝时,校书郎杨终在建议召开白虎观会议的奏疏中指出了今文经学的弊病:“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梁故事,永为后世则。”[6](p1599)章帝也在诏书中说:“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欲使诸儒共正经义。”[7](p138)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出,今文经学虽然在汉代一直受到君主重视,处于官学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章句繁滥及释义杂乱之弊病却越来越暴露无遗,以至于今文经学的这种弊病不仅仅遭受到古文经学的攻讦,就连今文经学者杨终和颇为重视今文经学的汉章帝也不得不提出质疑。这种训释文字烦琐的弊病,也使其渐渐变成了无用之学。正如皮锡瑞所说:“凡学有用则盛、无用则衰。存大体,玩经文,则有用;辞义逃难,便辞巧说,则无用。有用则为人崇尚而学盛,无用则为人所诟病而学衰。”[2](p90)如果一种学术,烦琐到皓首也难穷经,支离到令人莫知所从,这种学术也就走到尽头了。经历了许慎、马融、郑玄等通人的努力,今古文经学最终走向合流。而王符也生活在这个今古文经学逐步走向融合的时代,深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影响。在今古文经的使用上,体现出了兼收并蓄的特点,其出发点并不是经学家本身对于经学的研究,而是完全出于在野处士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一种立论的需要,一方面发挥了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结合比较紧密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古文经学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的鲜明特色。
三、《潜夫论》引用经书原因
王符《潜夫论》引用经书内容非常之多,这个情况在王符之外前后时期的其他学者身上也体现得尤为明显。刘勰说:“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8](p503)其原因在于:
(一)《潜夫论》对经书内容的引用是两汉经学时代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学取得了一家独尊的地位。随之儒家《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崇高的法定经典,士人对于五经的传习、解释成为了思想学术的主流,经学时代由此开辟。经学是权威之学,又被誉为圣人之文。宋孙复《答张洞书》云:“是故《诗》《书》《礼》《乐》《易》《春秋》,皆文也。总而谓之经者,以其终于孔子之手,尊而异之尔,斯圣人之文也。”[9]因此,圣人的言论内容也自然成为衡量人类社会善恶是非的一个重要行为准则。汉人著书立说纷纷引用经传所载内容作为重要的立论依据,以求让自己的言论和观点有强大的说服力,“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10](p103)。此处所讲正是此种情况。
(二)《潜夫论》对经书内容的引用同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儒家学术观有着直接关系
在这样一个经学兴盛的时代,王符继承了荀子关于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的儒家学术观。举凡一切学说和言辞,必以彰明正道为宗旨;唯圣人能明此道,因而明道要在征圣;圣人之心见诸五经,于是征圣又必宗经。无论是明道还是征圣,最后都要落实在宗经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总结写文章宗法儒家典经的六大效益,名之曰“六义”。他说:“若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11](p19)所以,五经就成为文学著述之最高原则的体现。后人之为文,皆当以五经为归依,“书不经”则不必著书,“言不经”亦不必有言。这就是王符的明道、征圣、宗经的观念,它上承先秦荀子的思想,下启唐宋时期“文以载道”之说的先声。《赞学》:“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先圣之智,心达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经典以遗后人。试使贤人君子,释于学问,抱质而行,必弗具也;及使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故修经之贤,德近于圣矣。”王符认为,先圣为勉励贤人入其道,而造经典以遗后贤,道体现在经典之中,经典往合圣之心,乃圣人之作。这段王符对道、典、圣三者关系的阐释正是其集成发扬“明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最好体现。
(三)《潜夫论》对经书内容的引用是王符对儒家经典的一种理解和诠释
王符虽不是一个以研习经书而闻名于世的经学家,但他对经书内容的引用也体现了其对于经书内容的一種理解和诠释。儒家诠释学特点之一是,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即许多儒者是透过注经以表述企慕圣贤境界之心路历程黄俊杰认为,儒家诠释学至少有三个突出的面相:其一,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学,即许多儒者是透过注经以表述企慕圣贤境界之心路历程;其二,作为政治学的儒家诠释学,即儒家学者在有志难伸之余,以经典注疏之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其三,作为护教学的儒家诠释学,即历代儒者以经典注疏作为武器来批驳佛、老而为儒学辩护。参见黄俊杰《中国孟学诠释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页。。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古圣先贤的名字在王符的文章中可谓俯拾即是,如《赞学》:“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祝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墨如,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秀,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于凡人乎?”《叙录》:“先圣遗业,莫大教训。博学多识,疑则思问。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夫子好学,诲人不倦。”而且这种对于圣人、先贤的仰慕之心始终贯穿在其全书之中,他在《叙录》篇表达了全书的创作宗旨“刍荛虽微陋,先圣亦咨询。草创叙先贤,三十六篇,以继前训。”这段话表明,王符把自己的文章创作完全当成了是对圣人先贤足迹的一种践履,是对圣人先贤之言的一种继承和发扬。特点之二是,作为政治学的儒家诠释学,即儒家学者在有志难伸之余,以经典注疏之学术事业寄寓其经世济民之政治理想。孔子的“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社会历代知识分子读书学习的基本信条,生活在社会状况日渐衰败的东汉中后期的王符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当时社会黑暗腐败和自身性格的耿直而使其终身未仕。现实的黑暗让王符对于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新的思考,《叙录》:“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尝服斯役,无所效其勋。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出仕为官为朝廷献计献策,是封建士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首要选择,在出仕不成的情况下,王符并没有就此消沉没落,而是积极投身于对于现实社会的思考,随之流传至今的社会批判性著作《潜夫论》便得以问世。在《潜夫论》中,王符对五经内容大量引用,这些引用完全是在王符对于经传内容的理解基础之上而展开的,这个理解基础也就是王符对于经传的一种诠释过程,寓五经内容于文中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进而做到以经证事,以经证己之说。例如:
对《诗》的引用。《劝将》:“诗云:‘修尔舆马,弓矢戈兵,用戒作则,用逖蛮方。故曰:‘兵之设也久矣。”此语出自《大雅·抑》,乃以《诗》内容证明先人对于武器的使用,以及通过对武力战争使国家变得强大。
对《尚书》的引用。《边议》:“夫以小民受天永命。”《巫列》:“《书》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此语出自《尚书·召诰》,以此表明君王对民众要加以重视。
对《仪礼》《礼记》的引用。《浮侈》:“孔子曰:‘多货财伤于德,弊则没礼。”此语出自《仪礼·聘礼》,王符以此语说明社会上僭越礼制的情况。《浮侈》:“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堕,弟子请治之。夫子泣曰:‘礼不修墓。”此语本于《礼记·檀弓》,王符借此语阐述以提倡节俭,反对厚葬。
对《易经》《易传》的引用。《思贤》:“《易》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是故养寿之士,先病服药;养世之君,先乱任贤,是以身常安而国永永也。”王符以此句阐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明忠》:“是故圣人显诸仁,藏诸用。” 此语出自《易传·系辞上》,王符以此内容阐明统治者对统治手段的运用。
对《左传》的引用。因为《左传》属于古文经学,其记载的内容翔实可靠,所以,王符对《左传》内容的使用基本都是以证事为主要目的,如《思贤》:“子产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伤实多……此所谓‘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哉!”此语出自《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王符以此表达君主对于人才的使用要做到论其才而授其官。《巫列》:“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气炎以取之。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此语出自《左传·庄公十四年》,王符以此语表明“人不可以多忌,多忌妄畏,实致妖祥”的观点。另外,以阐述上古帝王兴衰历史的《五德志》和阐述古代姓氏来源及流变的《志氏姓》两篇内容对《左传》的引用尤为明显,《左传》记载的史实成为构建其文章内容的重要源泉之一。如《五德志》:“世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此语出自《左传·文公十八年》。《志氏姓》:“及文公见姞,赐兰而御之。姞言其梦,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遂生穆公。”此语出自《左传·宣公三年》。
四、《潜夫论》引经书问题分析带来的启示
王符仅仅是东汉时期学术特点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其《潜夫论》引用经书情况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王符的学术特点,同时也可以发现在研究其他汉代学者学术特点时均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希望我们能从这些问题中得到一些反思和启示,进一步指导和引领对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提及汉代经学,必然要涉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处理起来非常复杂的问题。东汉时期,今古文经学并行,王符自然也会受到这种学术特点的影响。但是,除了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将王符列为今文经学者之外,无论是《后汉书》王符本传,或是现存其他史籍中均无关于王符师承关系和学术特点的介绍。通过前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王符《潜夫论》对于今古文经学内容都进行了引用,体现了东汉中后期的今古文经学融合的学术发展趋势。另外,通过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的梳理,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辨别今古文经的这种复杂性,其主要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今古文经传本的多样性
东汉时期,今古文经传本比较多,王符在引用时并没有明显表现出其出自何种版本。就王符生活的时代而言,《潜夫论》中所引共有《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七经,其中《礼》《春秋》有三礼、三传之分,《易》由于其从未间断师承,故此并无严格的今古文之分,因此,相对容易判断。而其余的几经则显然复杂的多。《诗》有齐、鲁、韩、毛四家诗之分,并且除《毛诗》之外,前三者均已亡佚;《论语》分齐、鲁、古论语三家,均已亡佚。西汉安昌侯张禹将《鲁论》后和《齐论》两个本子融合为一,篇目以《鲁论》为根据,名为《张侯论》,后世广为流传,今本《论语》即本于此关于今本《论语》的由来,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杨伯峻认为,今本“基本上就是《張侯论》”(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古棣等也认为古注和“近现代各种《论语》注解本依据的都是《张侯论》”(古棣,戚文,周英:《孔子批判上·孔子十日谈·第二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黄立振认为,郑玄本“即是现行《论语》的来源”(黄立振:〈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黄怀信认为今本杂糅了《张侯论》和郑玄本。(黄怀信:《今本〈论语〉传本由来考》,《文献》2007年第2期)。;《书》的今古文之分则更为复杂,不仅有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张霸百两传本,还有古文孔安国孔壁书传本、杜林漆书传本和河内女子所得传本。
(二)古人化用原文和经书传本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古人在引书时候,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准则可以遵循。通过对《潜夫论》所引用的经传文字内容来看,有很多是与原文不同的,或增或减,甚至完全化用原文的情况也比比皆是。宋王楙就曾说“古人引用经子语,不纯用其言,往往随意增减”正是此意[12](p89)。但我们也不应该据此就完全否定古代经、传传本多样性特点。通过对《潜夫论》引经书内容同其他传本对比情况来看,二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吻合之处的,这意味着王符《潜夫论》所引经传内容并不是完全化用、删减篡改而成的,相反其所引内容是有相应传本的。因此,我们要做到顾此兼彼,一方面要注意《潜夫论》引经传化用经传原文的情况的存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仅据一些异文、化用原文的情况就完全忽视经书传本的多样性的特点。
(三)今古文经传本中今古文字的混用
今、古文字在经书中的混用情况的存在,让依据个别文字的为今或古字去断定整句或出于今文经或出于古文经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结论不能做到完全准确。古文经在社会上被学者进行传授的时候一般不会以古文字体的形式传授给学生。如孔安国对《古文尚书》便“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13](p3125)。王国维称:“盖《古文尚书》初出,其本与伏生所传颇有异同,而尚无章句训诂。安国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是谓以今文读之。”[14](pp189-190)这些古文本经过了汉人“隶古定”之后,其中的文字很多已经不是原来先秦时期的古文了。《汉书·楚元王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于是章句义理备焉。”[5](p1967)这意味着其中含有古文,但也含有今文。段玉裁也称:“壁中亦有今文,伏生亦有古文。非孔氏者皆古文无今字,伏生者皆今文无古字也。”[15](p6)
(四)避讳问题给经今古文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
在《潜夫论》中,有这样两处引文,《思贤》:“《书》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国乃其昌。”引自《尚书·洪范》。《本政》:“孔子曰:‘国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国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引自《论语·泰伯》。两处“国”字,今本皆作“邦”字。关于汉代的“邦”“国”字问题,一般认为为避讳高祖刘邦,书写中“邦”字均作“国”。用“邦”字为古文经,用“国”字为今文经。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学者指出,汉代人并不能完全执行避讳这种习俗。洪适曾说:“汉人作文不避国讳。威宗讳志,顺帝讳保,石经皆临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刘熊碑来臻我邦之类,未尝为高帝讳也。此碑邦君为两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书》安定厥邦,皆书邦作国,疑汉儒所传如此,非独远避此讳也。”[16](p155)这种情况表明,在引文中出现的避讳问题又为经今古文问题的分析增添了一份不确定性。
(五)许慎、郑玄、汉代熹平石碑、陆德明等关于今古文分析结论同出土文献的矛盾及其可取性
前人在研究经今古文问题上主要依据许慎《说文解字》、郑玄《仪礼》注、汉代熹平石碑所载文字、陆德明《经典释文》等内容进行界定。但随着战国楚竹书《周易》的出土,让这种分析方法打了一丝折扣。下面就列举《潜夫论》中三个今古文问题上的常见字来予以说明。第一,“车”和“舆”。汉熹平石经所刻《论语》中“舆”皆作“车”,石经内容为今文,故作“车”者为今文,而作“舆”者为古文。(今本)大畜:九二,舆说輹。(帛书本)泰蓄:九二,车说緮。(竹书本)大土竺:九二,车敚复。可见,古文也作“车”。第二,“弗”和“不”。《仪礼·士昏礼》:“某子之惷愚,又弗能教。”郑玄注:“今文弗为不。”郑玄认为“不”为今文,“弗”为古文。(今本)习坎:上六……三岁不得,凶。(帛书本)习赣……三岁弗得,兇。竹书本此卦缺,但其载无妄卦中六二爻作“不耕获,不菑畬”,今本和竹书本同,皆作“不”。战国楚竹书《周易》中所载文字有限,并不能证明其他文字的今古文情况是怎样的,但依照这种逻辑,就意味着,前人在研究经今古文问题上如果依据《仪礼》郑玄注和汉代熹平石碑所载文字内容为是,其得出的结论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性,即十分有可能出现误混今古文经的情况。其实这种情况在《春秋》三传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第三,如《仪礼·士昏礼》《大射礼》郑玄注均云:“今文於为于。”《仪礼·既夕礼》郑玄注云:“今文处为居,於为于。”但战国楚竹书《周易》卦辞中“於”皆作“于”。桓公十一年(前701年)《左传》:“公会宋公於夫鍾”,《谷梁传》文与其同,而《公羊传》为“公会宋公于夫童”。隐公二年(前721年)《左传》:“莒子盟於密”,《谷梁传》《公羊传》皆作“于”。定公四年《左传》:“战于柏举”,《谷梁传》《公羊传》皆作“于”。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郑玄的论断是正确的,当时古文作“於”,今文作“于”。但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例子,如昭公元年《左传》:“曹人于虢”,《谷梁传》《公羊传》“于”字皆同。昭公十一年《左传》:“盟于祲祥”,《谷梁传》《公羊传》“于”字皆同。昭公二十三年《左传》:“陈、许之师于鸡父”,《谷梁传》《公羊传》“于”字皆同。僖公二十九年《左传》:“盟于翟泉”,《谷梁传》《公羊传》“于”字皆同。由此可见,古文经中也有作“于”字的,这同战国楚竹书《周易》卦辞中“於”皆作“于”是一致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当时没有今古文经学界限的约束,在文字使用上并不严格,这些文字的不同或为流传过程中后人书写不同而造成的。
从另一个方面看,现如今我们以战国楚竹书所见古文字内容进行对比,看到郑玄的结论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似乎也是很正常的。我们重视楚竹书《周易》的出土带来的这种新发现的同时,也十分有必要讨论一下许慎、郑玄、陆德明等人对今、古文字的结论,对今古文经进行界定有着怎样的合理性。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因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在其所在的时代范围内进行的。相比之下,囿于科学技术的原因,郑玄生活的时代不可能见到太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籍的原貌,这些古文经书开始时候大多是民间私下传授,经过众人之手后,究竟文字面貌发生怎样的变化也不得而知。前文提到的“车”和“舆”“不”和“弗”“于”和“於”出现的混用情况,更多的原因在于在书籍流传过程中书写的文字经常被改动。这一切都影响着郑玄最终对今、古文字的判断。这三部著作,是在学者们掌握了一定的古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对比研究的一个结果。以郑玄为例,《后汉书》有这样一段记载:“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17](p1207)作为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家,兼通今古文,但他出于师承的关系,仍是以研习古文经学为主。自然他能见到和使用的古文经书也一定较其他一般学者丰富。而这些古文经书就是在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的一些古文经书,很多人能够见得到,文字使用上具有一定的共性,譬如,前面所说的“车”和“舆”“不”和“弗”“于”和“於”等一些今古文字就是真真切切地展现在他们所见到的今古文经书中,所以郑玄才有了如此的结论。那么其他的东汉学者在使用这些文字时,可能也是按照这些经书中的文字书写而进行的,他们也认为“车”“不”即是今文,“舆”“弗”即是古文。郑玄对今古文字的这种界定,大概反映了东汉时期今古文经书的文字不同。所以,郑玄等人的结论带有普遍性,对于我们分析经今古文问题是有一定价值的,不能简单盲目地予以完全否定。
[参考文献]
[1]金春峰.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汉]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黄晖.论衡校释·效力[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汉]班固.汉书·楚元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南朝]范晔.后汉书·杨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南朝]范晔.后汉书·章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南朝]刘勰著,周震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才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吴承学,陈赟.对“文本于经”说的文体学考察[J].学术研究,2006(1).
[10][清]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南朝]刘勰著,周震甫注.文心雕龙注释·宗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2]张文治.古书修辞例[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3][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5][清]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宋]洪适.隶释·隶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7][南朝]范曄.后汉书·郑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系通化师范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责任编辑连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