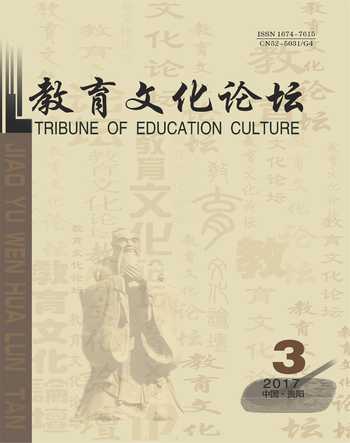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及其影响
2017-05-30谭德兴
谭德兴
摘要: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发展十分繁荣。明清贵州书院从设置到日常运行,都呈现出强烈的儒学色彩。书院从最初的选址便极具儒学文化特征,将儒家的修身正心与明山秀水有机融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书院的主体建筑和园林风景均体现出浓郁的儒学色彩,显示了明清书院文化的丰富儒学内涵。书院的日常教育多以儒家经学为主导,对书院山长、讲席和生徒的选择也呈现出强烈的儒学标准,而书院更是将儒学教育细化到师生日常的行为规范之中。明清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效果十分显著,对提升贵州文化发展品格和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明清;贵州;书院;儒学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3-01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3.026
一、明清贵州书院环境蕴含的儒学内涵
作为儒学传播的重要场所,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内外环境处处彰显着强烈的儒学文化色彩,给书院的儒学教育营造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从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处时时刻刻给书院士子以儒学熏陶。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环境所呈现的儒学文化内涵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书院建设选址的儒学意蕴
古代书院建设,在选址方面是十分讲究的。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易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407
“择胜地”而建书院,这不仅是石鼓、岳麓、白鹿洞书院的基本特征,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建书院为何要择“胜地”?这与书院的功能有关。书院主要属于民间性质的教育机构,与官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功能有所不同。朱熹《衡州石鼓书院记》指出:
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义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閒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1]407
官学只讲功利不讲德行,一味追求科举功名,教育极度的世俗化。而书院则注重个人道德品行的修为,以修身为主要目的,读的是圣贤书,追求的是高雅的教育境界(后世书院发展亦重科举功名,与官学无异)。显然,书院的选址要求与其修身目标是相吻合的。故黄清宪《登瀛书院记》说:
先儒或择胜地建精舍以讲授生徒,其时为政者辄就而褒表之,号曰书院。书院,固讲学之所也,学者可正心修身也。齐家、治国、平天下,必本于修身。[2]
修身正心正是儒学的重要思想。《礼记·大学》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3]1673为达到这一目標,书院首先在选址上就得远离尘世世俗环境的干扰,必须选择“胜地”而建。何谓“胜地”?按朱熹所言,即“燕閒清旷之地”,具体的地理位置特征如石鼓书院“据烝湘之会,江流环带,最为一郡佳处”。实际上就是山水最美风景最秀丽的地方。古人修身正心,十分注重地理环境的作用。自然环境的明秀清丽,有助于人的身心纯净高洁,有助于个人品格的提升。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一直是儒家所十分强调的。《论语·雍也》载孔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论语集解义疏》曰:“智者乐运其智化物,如流水之不息,故乐水也;仁者恻隐之义,山者不动之物也,仁人之性愿四方安静,如山之不动,故云乐山也。”[4]君子比德,儒家将仁、智这二种最重要的人之品德与山、水之德相比拟,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将修身、正心与自然山水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启了于山水间修身养性的模式。
明清时期贵州的书院建设就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合一的修身养性思想。例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八载程番府中峰书院:
在府城内北,弘治间知府汪藻建,本人诗:“北来山趾固,郡后突三峰。中有层峦起,分明秀气锺。青影随皂盖,白屋遶苍松。无限烟云色,其如归兴浓。”[5]
知府汪藻建中峰书院,其诗歌描绘了书院周围的胜景:峰峦叠嶂、青帐如盖,书院掩映在苍松翠柏间,云雾缭绕,胜似人间仙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修身,恰似寻找到了人生的精神归宿。类似的:
道光《大定府志》载陈汝梅《新建狮山书院碑记》:
水西旧有义学无书院。义学仅令小子就学,而成材者不与焉。邑尚书李恭勤始谋诸当事,捐课田、设膏火、搆堂于文峰山下。惜其地卑远,课读维艰,肄业者数年来指不多屈,人杰地灵盖难言之矣。州署后狮山详载邑志,当州协署之西,蜿蜒而下,屹然中止,群山环立,气象万千。青鸟家谓撷全州之秀,其后必有伟人者出。[6]326
光绪《平越直隶州志》载程荣寿《重建墨香书院记》:
其旧址正东向,列峰当前,嫌其障蔽,复与诸绅临视其地,稍折而南至苍坡,凭高四顾,则左右峰峦,重重分列,势皆合抱,如舒翼,后面远山周遭如设座,而前面远近山水如屏如案,山则九十九峰,名曰万笏朝天。水则三江汇合,中有石笋屹立,名曰中流砥柱。墨池文笔布设天然,其大势则左黎峨右犀水,以及月山叠翠,石壁书声诸名迹皆归一览,州城形势实会于此。移书院以当之,直据全州之胜。[7]
以上两例均为书院重建。狮山书院、墨香书院二者在重建时均改换了地址。狮山书院原来建在文峰山下,但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故改建至州署后狮山下。新址群山环立、气象万千,新建的狮山书院因为占据“风水宝地”而被一些堪舆家寄予振兴文教的厚望。同样,墨香书院背山面水“据全州之胜”,正符合朱熹所说的“择胜地”,成为理想的书院位置。从陈汝梅《新建狮山书院碑记》和程荣寿《重建墨香书院记》不难看出,当时士人以书院能占据“胜地”而极度自豪,字里行间渗透出儒者们获得一理想读书修身场所的无比兴奋。
其二,书院主体建筑的儒学意蕴
书院是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其主体建筑也呈现出浓郁的儒学色彩。例如,道光《大定府志》载平远平阳书院:
郡中有义学旧基,尾盤魁崙,首注平江,诸山屏翰,势若星拱。郡伯以山川灵秀,就其地而前建龙门,囊括秀气;中建讲堂,昌明大道;左右建馆舍数十间,储养英才;后建九贤祠,崇祀濂、洛、关、闽诸子,使诸生知理学渊源之有自。[6]325
在城北隅,旧为义学。知州冷宗昱捐建。知州苏松重修。岁久倾颓,仅存基址。乾隆二十年知州李云龙捐俸修建,改为书院。前大门三间,中间讲堂三间,悬圣祖仁皇帝御笔“文教遐宣”匾额,后盖景贤堂五间,祀濂、洛、关、闽九贤神主。左右厢房共三十二间,延师讲学,集士子肄业其中。[6]325
平阳书院的主体建筑以中轴对称,这体现的是儒家中和诚正的思想。院落又分为前、中、后三部分。每部分都蕴意着丰富的儒学文化内涵,前门被称之为龙门,喻示着书院能吸纳一切钟秀之气,中间为讲堂,平日为书院讲学、研习和从事各种礼仪活动的主要场所,悬挂的是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文教遐宣”,儒家教化意味甚浓。书院后面为祠堂,供奉的是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先师,崇儒色彩十分浓烈。
又如,民国《黄平县志》卷十载龙渊书院:
文昌阁于书院后,移节孝祠于右,前建牌楼一座,头门三间,二门一间,讲堂三间,左右书舍各五间,曰“博文约礼”,后为院长书屋三间,左右书舍各五间,曰“进德修业”。后厨房二间,讲堂侧厨房三间,仓廒二间,缭以周垣,规模宏敞。[8]269
龙渊书院与文昌阁、节孝祠等建在一起,形成一个儒学文化建筑群。书院因其中士子们要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故祭祀建筑文昌阁常常与书院毗邻,实际上成为书院建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节孝祠以及文庙等往往也与书院紧邻,相互发明儒家思想。
另外,龙渊书院的匾额“博文约礼”“进德修业”“讲学明伦”辉耀着强烈的儒家文化,时时提醒院中的士子以弘扬儒学为己任。龙渊书院中的楹联也呈现强烈的儒学色彩:
按院在城西,咸丰丙辰毁于苗乱,至光绪庚辰年署知州刘启端建有三楹,旋圮,仅存一联
曰:“龙虎风云有志竟成诸生岂让凤池麟阁,渊源濂洛相观而善此地何殊鹿洞鹅湖。”……书院讲堂匾曰:“讲学明伦。”联曰:“说礼乐以敦诗书愿诸君鼓吹休明振起党庠盛事,先器识而后文艺从此日讲求体用蔚为王国人材。”考棚联曰:“试院听茶声忆昔年露布书勋此事已自崖而返,宏规开社厦看今日风檐献艺诸君当磨砺以须。”[8]269
龙渊书院,顾名思义即该书院为俊彦汇集之所。“诸生岂让凤池麟阁”表明书院建设者立志高远,有儒学比肩中原的雄心;“此地何殊鹿洞鹅湖”显示出书院建设者学路纯正,有理学续接朱、陆的壮志。从龙渊书院的匾额、楹联不难看出明清贵州书院在弘扬儒学方面确实做出了巨大努力。
其三,书院园林景观的儒学意蕴
除了主体建筑、匾额、楹联等呈现浓郁的儒學色彩外,书院中的园林景观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儒学韵味。例如,光绪《普安直隶厅志》所载凤山书院:
凤山书院在城西门内山半。嘉庆十二年建。前面笔峰,后枕奎阁,地势雄特,万象森罗。有头门二门讲堂三楹。上有楼,正中祀仓圣,颇极轩敞。两旁翼室为斋房。讲堂右折为山长内室三楹,右偏为厨湢,对面有亭翼然。署同知吴公宗兰榜曰:绿绕青来讲堂下,有丹桂紫薇各一株,花时足供游赏。院后有井泉,甘洌清香。前教谕刘汉英缀为八景曰:魁阁飞霞、书楼赏雨、薇云夏幕、桂露秋香、笔峀凌云、斗亭留月、山房抱胜、井泉洗心,各系以诗。[10]
凤山书院内部园林景观浓缩为八景,八景绝非纯自然景观,其中赋予了强烈的人文内涵。飞霞、山雨等自然景色充满诗情画意,一旦与魁阁、书楼等书院建筑融为一体,则其修身养性韵味跃然而出。所有的秀美景色,最终落实在“抱胜”——“洗心”之上,则凤山书院八种园林景观的书院味十分浓厚,书院的宗旨全部蕴含在这些园林景观之中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达到修身正心的儒学追求。又如,黄鉴《湘川书院艺圃序》说:
征君因名其处曰“芝”;之下曰“竹径”;又下则高砌,有柏苍然,独立于云,曰“柏鄩”;东舍之砌与竹径对,大桃双株,曰“桃蹊”;其下高砌,三桔树迤逦墙阴而下上,曰“桔墱”,殆取春华秋实、成蹊不化枳之义。凡为、为径、为鄩、为蹊、为墱,皆编竹为栏,区界曲折,玲明四通。中砌高阶,则竹栅屏门,门以内,杂莳花卉随时,统其名曰艺圃,亦有取于文圃游艺,自寄其意,且以隐勗多士者乎!夫藏修有所,游息有地,此儒者分内之事,惟征君知之,而已任之。[11]516
湘川书院乃遵义的著名书院,培养了郑珍、莫友芝等西南巨儒。湘川书院浓郁的儒学氛围从其园林景观即可窥知。郑珍给湘川书院的艺圃取了一系列富有文化意蕴的名字:芝、竹径、柏鄩、桔墱,并以总名“艺圃”名之。古代文人修身,往往以梅、兰、竹、菊、松等品格自喻,表达淡泊名利、追求个人道德修为的高洁境界。郑珍以(茶)、竹、柏、桔命名湘川书院园林景观,正是儒者修身行为与理想的寄托。对书院中花圃的耘作,实际表达的是在湘川书院这座巨大的文圃中“游艺”。《论语·述而》:“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邢昺疏:“六艺谓礼、乐、射、驭、书、数也。”[3]2482在书院中游艺,实际上就是对儒学(六艺)的研习。郑珍就是如此做的。将儒学研究视为自己的使命,视儒学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超越功名利禄的物质追求,真正做到修身正心,这正是郑珍在西南僻壤湘川书院的行事。故曰“藏修有所,游息有地,此儒者分内之事,惟征君知之,而已任之”,郑珍是王阳明之后贵州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儒者。
二、明清贵州书院教育的儒学内涵
明清时期贵州书院日常教育内容实际上与府、州、县等官学无异。关于书院的学习内容,实际上清代统治者是有明确规定的。民国《黄平县志》卷十载:
乾隆元年议准书院肄业士子,应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而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当先攻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之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听酌赏以示鼓励。[8]268
清廷要求书院留心讲贯的是经学、史学、治术诸书,即使资质较差的也以八股文、经学为主要学习内容,这些都是在儒学主导下的学习。书院每月有考试,称之课艺,模拟科举考试的形式与内容,以八股文为主。考题全部出自儒家经典,且重点出自《论语》《孟子》《诗经》等经典。《黔南三书院课艺初集》就是书院课艺活动最典型和最高水平之体现。其中满篇渗透的都是浓烈的儒学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有书院将儒家经学视为头等重要的学习大事,甚至立为书院条规。例如,乾隆《独山州志》卷四载书院“教条”,列的竟然是五经传授源流图,[12]151-153详细排列出《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礼》学源流图,图文并茂,无异一部简略的经学发展史。为什么乾隆《独山州志》书院教条不像其他书院条规规定师生行为、经费开支等内容,而独出心裁开列五经源流图呢?史志编纂者自己有说明:
小学教人之法,经史子集之事业文章,茫乎!浩乎!固任人取携矣。今先载五经源流,后附朱子《白鹿洞教条》,俾为师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学,边方文教庶有裨焉。[12]150
在经、史、子、集教学中,独取经学以教,这种教育理念明显与史志编撰者艾茂自身学术经历有关。民国《麻江县志》卷十六载:“艾茂,字颖新,别号凤岩。六岁即授经训,年十四应童子试,督学邹一桂拔置第一,赠诗云:‘两序温文归大雅,五经讲诵逊神童。”[13]489艾茂年幼即以经学出名,其著有《易经人道》《贵山四书集讲》《五经类纂》等经学著作,其主讲贵山书院时门下人才泉涌,显然与艾茂经学教育理念有关。艾茂的这种教育理念影响到独山的莫与俦,莫与俦为汉学大师阮元学生,其任遵义府学教授,立志要在贵州续接汉学学统。莫与俦又影响到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萧光远等,使得“边方”文教获益匪浅。无独有偶,光绪乙未,天津严修视学黔中,一见雷庭珍则大奇之,聘主经世书院讲席,选诸生四十人肄业其中。雷庭珍《原学》曰:“夫能使政材、艺材,保其心之善,启其心之智,益其心之力,增其心之才,以善其才之用者,其惟经学乎!若志在圣贤,志在天下,而欲修齐治平之业,成智仁圣神之功者,舍五经更莫得其道。是经也者,诚中西政艺之脑筋也。”[14]598从经世书院讲席雷庭珍言行可知,即使在晚清时期,贵州儒者仍然坚守着经学教育传统,这是近代贵州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近代贵州文化能能居全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书院日常儒学教育还体现在对老师和生徒的行为规范上。因为书院主要是读书修身之所,故对进入书院的老师和生徒均有明确要求,其标准自然也是儒学的。例如,民国《黄平县志》卷十载:
乾隆三十年慎选山长谕:陕甘总督杨应琚奏,甘肃兰山书院延请丁忧在籍之府丞史茂来主讲席,此甚非是。督抚有维持风教之责,缙绅中积学砥行之儒,足备师资者谅不乏人,何必令丁忧人员靦居讲席,是应聘者固不能以礼自处,而延请之地方大吏亦复不能以礼处人,于风化士习,微有关系,恐他省不无类此者,特为明切晓示通谕之。[8]268
书院山长人选关乎书院办学品质,故清代统治者对此有十分明确要求。甘肃兰山书院延请丁忧在籍的人员做书院讲席,这显然不符合儒家礼仪。丁忧期间,频繁从事讲席活动,明显违背儒家丁忧的相关礼仪要求,对移风易俗有巨大的负作用。故清廷要严厉禁止此类行为。又如《乾隆元年整饬书院课程诏》:
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条规》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摒斥勿留。学臣三年任满,谘访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才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舞。[8]268
书院山长必选明经修行的社会楷模,生徒必须择文行兼优者。清廷的这种要求,被切实贯彻到了明清贵州的书院教育之中。如道光《松桃厅志》卷十书院条规:
肄业生童各宜肃衣冠、谨言行、端品立身,以期上进。如有不知自爱,博弈饮酒游荡不检,或吸食洋烟,以及扛帮词讼,一经查出,分别斥逐,并治以应得之罪。
肄业生童分住斋房,各宜潜心读书,不得常相往来,以己知旷惰扰人之造修,更不得招引戚党友朋进院聚谈,违者戒饬。
本署府诸生中访择平素安静、品学兼优者,立为斋长,每月給膏火钱一千二百文,米三京斗,即著住院读书,并稽查各生童行止。如有荡检踰闲、任性妄为,即禀明山长责处,不可丝毫徇隐。[15]549
这些条规是明清贵州书院日常儒学教育的具体表现。实际上也是《乾隆元年整饬书院课程诏》在贵州书院的落地与细化。松桃厅书院其他条规的儒学标准也是十分明确的,如“父母宜敬顺”“兄弟须友爱”“家人宜和睦”“朋友宜劝勉”“书籍宜多读” [15]550-551等均是十分明确的儒家思想教育内容。
三、明清贵州书院儒学教育的影响
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发展十分繁榮。据民国《贵州通志·学校志》的《书院表》统计,明清时期贵州共有书院141所。特别是晚清贵州书院众多,自1840年至1902年的60余年中,贵州新建与改建的书院就有79所,最迟到1900年前后还在新建书院。书院的繁荣,无疑对贵州文化发展影响巨大,特别是晚清贵州文化辉煌,能跃居全国前列,与书院的发展密不可分。明清贵州书院的儒学教育,直接推动贵州文化飞速发展,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对提升贵州文化品格产生了的巨大推动作用
贵州文化从明代以前的几乎荒蛮,到近代跃居全国文化发展前列,其中根本原因,即在于儒学的大力普及与推广。而书院作为民间色彩浓郁、义学性质明显的儒学教育机构,使得普通百姓、寒门学子能有机会接触高水平的学者,接受高品质的教育。从而迅速改变了贵州文化发展水平。前文所引艾茂、雷庭珍等人的言行即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又如光绪《平越直隶州志》载墨香书院:
平越旧有书院乎?曰:有。数椽老屋附于府治西偏,卑隘凋残,久虚讲席,不可以为有也。有之,自太守唐乐宇始。乐宇以农部尚书郎于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出典是郡,适岁试童子,览其文弗善也,越明年再举科试,览其文犹弗善也。夫以平越山川之奇丽,人物仪容之秀美而艺业若此,岂非不学之过?与急思所以教之,而必求其肄业之所。于是谋诸僚佐乡大夫士皆曰:善。三阅月得募金千七百有奇,卜地城之东南隅,作于乾隆五十年秋八月,成于五十有一年夏四月。若堂若斋若门若室楼阁亭池之属,厘然具备,于戏何其速也。[7]193
乾隆时期,太守唐乐宇在平越建墨香书院,其原因在于有感当地士子“文弗善”。“文弗善”在清代中叶以前可以说是贵州士子的普遍现象,病因自然在于教育的缺失。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大力扶持书院建设,这也给贵州文化发展带来契机。清代中叶以后,贵州书院蓬勃发展。墨香书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建,其对区域文化发展成效十分明显。故道光《遵义府志》卷二十四载刘诏升《建修湘川书院记》:
学校为育才之地,书院则以济学校之所不及也。学校以官为师,即寓法于教,书院之设于官者,则官为择师,专主于教,其即古者党庠、术序之遗而变通之欤!方今寿考作人,化逮遐荒,百余年黔省人才蔚起,皆出于学校,而书院之设,各府州县皆然。……顾萃一方之秀良,循循于规矩准绳中,气质于是变化焉,性情于是陶融焉,士尚文艺,不能自外德性也。欣逢文治日隆,郡人士涵濡圣教,文风之盛甲通省,而习俗移人,或朴而流于野,或直而失之率,陶融变化之方,其在温文尔雅和平中正之则乎![11]515-516
从乾隆至道光,贵州书院“专主于教”,其“化逮遐荒”,故经百年发展,“黔省人才蔚起”“文风之盛甲通省”,贵州文化的飞速发展而书院实在功不可没。事实上,明清时期贵州书院的建设与发展也并非容易之举。书院虽然带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但实际上是受到官方严控的。书院的建立首先都必须经过官府审批,建前必须呈报请求官府批准。有的虽然是地方官员新建、重建、修葺书院,但其如何运行,朝廷是有具体要求的。在朝廷眼里,书院就是义务教育性质的学校,故雍正元年,奉上谕:“书院令改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 [11]514
《遵义府志·学校志》叙书院却先叙义学发展源流,书院实际上属于广义的义学范畴。既然是义学,则经费方面民间捐助的色彩要浓郁些,书院的运行模式有官府监管,但主要以山长主管,束脩膏火多半是乡绅捐资,有的有固定的田产,通过收租来维系书院日常开支。书院、义学的增废现象则十分普遍。其废毁主要是社会动乱、经费不足等原因,如遵义启秀书院,有田一百九十七亩,岁收租息百金有奇,除长教束脩外,已经不敷肄业生膏火资,远方负笈来者,往往僦屋寄餐于旅馆。道光《大定府志》载王绪昆《重修万松书院记》:
余以道光壬辰七月摄篆大方,甫下车即以课试为首务。郡有万松书院,其租息甲于他郡,而堂室斋舍俱颓败而不可支。询之首事,咸云自嘉庆元年以来,其本年束脩膏火之费必俟下年租入始给,或不及待则称贷以应之,是以费无赢余。欲谋修葺,计惟暂停课士一年,庶乎费有所出焉。信如是也,必待一年收租一年兴作,是一停两年矣。其或一年所入不敷所费,又将取给于下年,而下年束脩膏火之费者又不能不出息称贷以给之。是终无赢余以为岁修也。因捐俸鸠工择可任者经理其事。先建坐房五间,其次讲堂头二门及内外斋舍,次第修理……请于大中丞嵩公书额曰“读书明理”。旨哉!其言之也。夫学者朝夕絃诵,非徒求工于文辞也,必实就乎理道。上之将以企于圣贤之域,次之亦不失为谨饬之儒,出可以为国家倚重之臣,处亦不失为品行端方之彦。盖所以为多士勗者,意良深也。[6]325
尽管贵州书院的发展十分不易,但总有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坚持着发展书院,或新建、或重建、或修葺,从筹资开工,到书院束脩膏火的维系,都有赖于卓识之士的功劳。这种坚持,最终收到回报。清代中叶以后贵州人才蔚起,与书院繁荣有很大关系。
其二,对贵州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贵州进士举人泉涌,特别是近代,据民国《贵州通志·选举志》可知,道光朝贵州有进士95人,舉人596人,其中包括著名学者萧光远、郑珍、莫友芝等。咸丰朝有进士30人,举人90人,其中包括名臣丁宝桢。同治朝有进士45人,举人389人,其中包括维新大员李端棻。光绪朝有进士143人,举人706人,其中包括状元赵以炯、夏同龢和探花杨兆麟。[14]50-66 这些人才出现多与书院有密切关系,如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就是在兴义笔山书院的文化氛围中读书成长。西南巨儒郑珍,就是遵义湘川书院培养的杰出人才。明清贵州书院对贵州人才培养贡献巨大。郭子章《黔记》卷十六“学校志”云:
龙岗书院在治龙场驿内,正德间王文成守仁建。都御史刘大直诗:梦寐先生几十春,龙场遗像谒兹晨。百年过化居夷地,万里来游报国身。道在山川随应接,功存社稷自经纶。芳尘欲步惭无伎,仕学工夫只日新。[16]360
王阳明入黔,这是贵州文化品格的一次质的飞跃。而阳明先生建龙岗书院,对贵州的人才培养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真可谓“道在山川随应接,功存社稷自经纶”。故郭子章《黔记》卷四十五说:
王文成谪龙场,黔士大夫始兴起于学。当时龙场诸生问答,莫着其姓名,闻而私淑者,则有马内江、孙淮海、李同野三公云,予尝读内江诗“寒夜窗前听雨时,暗思往事坐如凝。穷愁百结随年长,人在虚空老不知。垂眼朦胧看远山,不知身尚寄尘寰。他年观化应何处,想在虚无缥渺间。”真有朝闻夕可之意,呜呼,可以不愧龙场矣![17]
王阳明对贵州儒学人才的培养效果明显,龙岗书院所发挥的作用毋庸多说。又如,明代都匀鹤楼书院,嘉靖间为主事张翀建。张翀《都匀读书堂记》曰:
人之有堂,所以安身也;堂之有书,所以明心也。庶人不明书则不足以保身,士大夫不明书则不足以启性灵而弘功业,军旅不明书则不足以察古今之成败,夷狄不明书则无君臣而上下乱。贵州虽在西南,去中州不甚远,六籍亦往往具备,今诸君能取而读之,与余聚堂中一事商榷邪?诸君曰:唯唯。[16]365
张翀言传身教,以读书勉励都匀士子,以建书院培养人才,对都匀乃至贵州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其后,都匀邹元标又建南皋书院,巡抚江东之《南皋书院碑记》:
张公翀者,马平人,嘉靖中以比部郎疏论分宜,戍于匀,匀人构此以读书张公,是为鹤楼书院。而公视张公,后先一辙,遂结茆于张公堂左右。居匀六年,时时与都人士讲天人性衍之学,倏然皭然,无夷狄患难相,亦无无夷狄患难心。盖身在局中,法流界外,委化运于傥来,而不以人我参耳。其门第之高者,往往负奇气,掇巍科,词章行谊,得庐陵文宪之传。如陈给谏尚象亦以谠言放逐,要其凌霄亮节,不负所学,又宛然邹氏家法也。[16]367
邹元标继承张翀做法,在都匀建书院培养人才,形成了邹氏家法。其生徒如陈尚象等多为名儒。黔南最终能产生诸如夏同龢这样的状元,显然与当地文化积淀深厚有较大关系。通过书院以培养人才在明清时期的贵州十分普遍,如民国《麻江县志》卷十六言艾茂:“应滇黔督抚聘主讲五华、贵山两书院,凡十四年,得士称盛,膺荐加侍讲衔。其教人必先器识,故门人花杰、严匡山等多以文章经济显茂。”[13]489民国《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二言萧光远:“主讲湘川、育才、培英书院,弟子尝从讲学者甚众。”[18]民国《贵州通志》载雷庭珍“学问益博,尤醉心经学,顾亭林、黄梨洲二派多所折衷。严范生学使剏设经世学堂聘主经学讲席,刘统之观察又延往南笼设帐,时黔中英俊多出其门。著有《经义正衡》《文字正衡》《时学正衡》等书传世。廷珍光绪戊子举人,乙未丙申应经世学堂聘主讲经学于省门,成材甚盛。后应兴义聘主笔山书院讲席,士风丕变,学者辈出。”[14]598民国《绥阳县志》卷六载雷庭珍“主讲洋川书院、主讲贵阳学古书院、主讲兴义笔山书院,游其门者皆欲揣摩时艺,弋取功名,而玉峰则科其学弊,广其裁成,竭半生来之心得,特著《经义正衡》,以倡黔省之风气”。[19]363“易道涵,研精经史……年六十四主讲洋川书院十一年,成就者众。”[19]361道光《贵阳府志》载王国元,主讲贵山书院,循循善诱,出其门者多知名士,及其卒业门人祀之尹公祠中。[20]
孙士毅《启秀书院记》云:
黔之士如其地然,弇涩而少华,椒崦皆童阜也;黔之文如其居然,杂糅而失次,庖、湢而无异位也。使者瞿如惄如,而不能以按。壬辰夏,至且兰,既扄衿弁而试之,翌日,校遵邑童子七百有奇,阅其文,烝烝遂遂,饫醇而哜……,其于道也几矣,异之!询邑之宰同年友沈虚谷,知其地旧有育才、湘川两书院,……悉其力于艺文,用是大进,两君之用心亦挚矣。事患弗克创耳,今规制已具,向风者众,弦诵声琅琅如吴越。后之宦斯土者,踵而行之,收效愈远。[11]517
初至贵州的孙士毅,对贵州文化发展水平感到十分惊异,没想到黔地居然文风醇厚,几近于道。通过询问同僚,才知原来是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发展十分繁荣,书院以儒学传播为己任,对贵州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撰,朱子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黄清宪著,半弓居文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79.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魏)何晏集解,(南朝)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M]中华书局,1985:79.
[5](明)沈庠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M]成都:巴蜀书社,2006:90.
[6](清)黄宅中修,邹汉勋纂.(道光)大定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8)[M].成都:巴蜀书社,2006.
[7](清)瞿鸿锡修;(清)贺绪蕃纂,(光绪)平越直隶州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6)[M].成都:巴蜀书社,2006:194.
[8]陈绍令等修,李承栋纂,(民国)黄平县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1)[M].成都:巴蜀书社,2006.
[9](清)徐丰玉、周溶修,(清)谌厚光撰,(道光)平远州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50)[M].成都:巴蜀书社,2006:368.
[10](清)曹昌祺修,(清)覃梦榕、李燕颐纂,(光緒)普安直隶厅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4)[M].成都:巴蜀书社,2006:378.
[11](清)平翰等修,(清)郑珍、莫友芝纂,(道光)遵义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2)[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2](清)刘岱修,(清)艾茂,谢庭薰纂,(乾隆)独山州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4)[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3]拓泽忠,周恭寿修,熊继飞等纂,(民国)麻江县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8)[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4]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9)[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5](清)徐鋐修,(清)萧琯纂,(道光)松桃厅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6)[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6](明)郭子章撰,(万历)黔记[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7](明)郭子章撰,(万历)黔记[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M].成都:巴蜀书社,2006:281.
[18]周恭寿修,赵恺、杨恩元纂,(民国)续遵义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M].成都:巴蜀书社,2006:154.
[19]胡仁修,李培枝纂,(民国)绥阳县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36)[M].成都:巴蜀书社,2006.
[20](清)周作楫修,(清)萧琯等纂,(道光)贵阳府志[M]//黄加服,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3)[M].成都:巴蜀书社,2006:438.
(责任编辑:赵广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