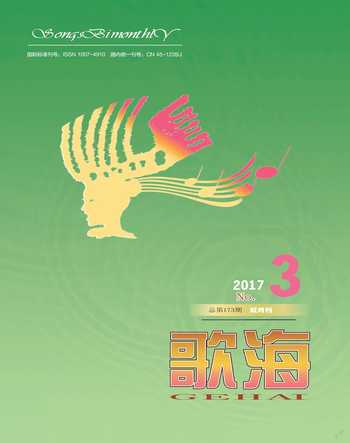迁徙后的文化困惑与坚守
2017-05-30曹昆
曹昆
[摘 要]“三月三”作为壮族传统民歌节是壮族音乐文化的重要身份符号,但就广西合浦三合口农场的东兰县壮族移民而言,却很难在每年举办这项活动。由于这些移民从原住地迁移到安置地,不论是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传统民歌文化的传承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但是,迁移与安置模式对于这些壮文化又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移民;壮族;民歌;东兰
随着农历“三月三”的到来,壮族传统的歌节盛会也紧锣密鼓地在广西各个地方展开。2016年,本人有幸带领团队到北海合浦参与了广西农垦局下属的三合口农场举办的壮族“三月三歌节”活动。这是“广西农垦国有三合口农场东兰籍壮族水库移民首次在平头岭分场举行了他们扎根北海24年来规模甚是隆重的集中庆祝‘壮族三月三传统节日活动”?譹?訛。而2017年,获知三合口农场由于工作时间上的冲突(今年甘蔗的收割比去年推迟了一个月),因此,“三月三”期间的民俗活动则由职工自主安排。通过走访与调研,了解到虽然有部分壮族移民职工很想继续这项活动,但是不论从资金还是人员组织、时间安排等方面确实存在着较多的困难。最终,2017年的三合口农场没有了去年的欢庆与热闹。
尽管,三合口农场的“三月三”活动没有继续举办,但是,三合口农场下的“平头领分场”却成为了当地民族团结的示范点。从2016年的“三月三”活动举办过后,北部湾农垦局下的三合口农场、星星农场等得到当地民政局、宗教事务局等政府部门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配合国家级项目岩滩水库的建设,三合口农场与星星农场分别接收了来自东兰县与大化县4000多人的移民。这些移民多以壮族为主,尤其是三合口农场,近99%的移民都是壮族,而且都基本上来自同一个乡——大同乡。这些壮族移民在迁移到农场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他们依然对自身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从1992年到2004年,三合口农场几乎每年都自发组织开展“三月三”歌节活动。但是,由于一些移民政策的遗留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从2005年到2015年期间都没有开展过“三月三”的活动。虽然,在这期间有过几次较重要的文艺活动,如移民建设二十周年庆典等,但都是以各种综合节目为主,并没有特别突出壮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移民政策的不断落实与完善,这些壮族移民的生活得到巨大地提升与改善。三合口农场的壮族移民不仅解决了基本的生活需求,很多住户都有了自己的住房、小车等。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随之带动着他们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些壮族移民从内心更希望得到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从而显示出他们的出众与不同。因此,他们对自身文化個性的追求也愈发强烈。2016年的“三月三”歌节正是在这样的内在驱动下举办的。
“三月三”作为壮、侗、瑶、苗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节日已在广西获得了法定假日的权利。因此,作为壮族人民来说,“三月三”举办节庆活动是极其重要且普遍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些集体迁移的壮族移民来说,传统“三月三”活动的开展依然面临很多难以言说的困难。
一、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对移民传统民歌
文化的冲击
(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于三合口农场的东兰移民来说,其最大的转变就是来自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尽管,农场提供的生产方式依然是种植为主,但是在现代工业文明下的规模化种植已经完全不同于农村传统小农经济型个体化种植的性质。首先,东兰县这些以传统水稻种植为主的壮族移民开始了以经济型作物为主的甘蔗种植。不论在具体劳动的方式、习惯、周期、环境等方面都与过去截然不同。以前在山间劳动时,可以与朋友遥相呼应,而现代的劳动基本上就是各自忙碌,电话联系。以前的劳动时间、强度相对有弹性,个人生活与劳作相对悠闲。现代劳动时间与强度都有基本要求,不管怎样都必须完成,这种劳作背后则是强制性规则所带来的约束与压力。而且,传统水稻种植的收获节庆在转变为甘蔗后也不再存在。如“蚂节”就在这些移民的生活中逐渐淡化、失去。
另外,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些迁移到三合口农场的壮族移民,他们已经不再是迁移之前单纯务农的村民,而是获得国家认可下的国有企业员工。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不再是农村而是城镇,他们的收入不再是简单的农作物的收成,而是国家与企业根据其劳动付出所付与的劳动工资。这种由于生产方式转变而形成的社会角色的改变,也使其劳动力生产价值的体现也不同于之前。以前的个体劳动价值由于劳动工具简单,生产活动主要依靠人的体力劳动,因此劳动力是其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价值也主要以农作物的收成为其主要衡量依据。移民后,由于生产要素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以机器为动力的大生产逐步取代以人工为动力的小生产,商品价值结构中对应于人工劳动量的价值的部分越来越少”?譹?訛。这些移民的主要生产力价值已经由其所在农场发放的工资所体现。社会生产方式及其劳动力价值体现的转变已经直接改变了这些壮族移民以前生产劳动时的关系。以前山间田头的小集体合作的亲密关系被现代工业机械与制度化所替代,劳作中的亲情与友情慢慢变成规则或利益之间的交换。
从历史发展的历程来看,生产方式的转变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很多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往往都是渐进式的,是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与过渡而形成的。可是,对于这些东兰壮族移民来说,这种转变是一种突发性、断裂性的转变。因此,随之而产生的生活方式转变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也显得尤为强烈。
(二)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
在我们所做的采访调研中,对于初来安置地最大困境这一问题的调查,基本上都会涉及到移民与周边原住民之间的矛盾。语言的不通、生活习俗的不同、经济利益的争夺等等都造成很多东兰壮族移民们的困惑。如果说,迁移之初的这些问题是能够通过法律、政策、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解决。那么,生活方式的转变则是这些移民们安置之初最难以适应的困境。以前这些移民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式生活方式。对他们而言,只要能解决温饱问题就基本上可以安身立命,传宗接代。其间,对于他们的支出多只需考虑逢年过节或一些亲戚朋友交往时的开销。但到了农场后,移民周围的生活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熟悉的亲人与朋友都换成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从20世纪90年代迁移到合浦,这些壮族移民被分别安置在三合口农场下面的18个分场,生活中的一切开支都基本上得用钱来支付。他们需要学会赶公车、骑自行车、开摩托车甚至到现在的开汽车;他们需要习惯去特定的地方买菜、买米、买肉;他们需要去给孩子找学校读书,需要每周五天去某个地方工作报到,需要一种新的语言与他人交流。甚至,他们需要更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生活质量(衣服、电器等)的提升等等。为此,他们需要通过更多的方式去获取更多的收入来满足现实生活改变所带来的这些需求。这样的结果也直接反映在生产力价值的复杂性一面:农作物收成已经不是其劳动力价值体现的唯一来源,而是还包括其个体自由贸易、个体劳动力外租等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因此,以前较为单纯的农作物收成作为近似唯一的劳动力价值体现已经逐渐被多元化的劳动力价值体现方式所替代。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东兰壮族移民更多的思想与行为是围绕着如何解决现实生活的物质需求,精神文化方面则远远退居在他们内心的边缘。
另外,城镇制度化的生活节奏已经改变了移民之前的村落生活节奏与习惯。安置早期十年,这些移民结婚、安葬、生小孩都还会请歌手去唱歌、摆酒宴。而其后,一些移民则在这些方面开始简化,或者受当地文化影响变换了方式,如结婚时不再请民间歌手来唱歌,而是在酒店摆宴席、闹洞房,去影楼拍婚纱照等;以前每周两到三天一次的赶圩、集市也变成周末式的休假或轮休。可以说,东兰移民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活习惯的转变,更多是一种对周围环境适应的反应。但这种转变对传统民歌文化环境的伤害却是具有毁灭性的冲击。
就整体而言,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对这些壮族移民自身的传统民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譹?訛民歌文化,作为这些东兰壮族移民的传统,是与其长期的小农生产与生活模式息息相关。而“民歌的生态环境,特别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根本上制约着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演化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譺?訛。因此,对于这些迁徙到农场的壮族村民来说,旧的民歌生态环境已改变,新的环境对于其传统民歌文化的传承也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与挑战。
二、社会环境对移民心理影响所造成的民歌文化危机
前面谈到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对这些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环境的冲击是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而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则是社会环境改变对移民心理的深刻影响。
(一)社会角色改变带来的心理影响
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这些东兰壮族移民社会身份角色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仅在社会生产力价值的体现上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时,这种角色的转变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群体的变化,进而也进一步影响到其思想与行为。
早期这批东兰壮族移民迁移到农场时,还保留有以前较为传统的习惯。在1992~2004年间,几乎每年“三月三”,村民们都会自发地举办一些活动,以强调自身民族的独特性。但是,这些年的“三月三”活动基本上都是小范围的、自发性的行为。由于迁移到三合口农场的东兰移民基本上都是同一個乡(大同乡)的村民,其中涉及7个村委,20多个生产队,共计2000余人迁移到三合口农场,包括乡长、书记、乡卫生院院长等各级基层领导。而且,原大同乡书记也在迁移后任三合口农场副场长,专门负责这些壮族移民的相关工作。因此,前十年左右,这些东兰壮族移民都还在老基层领导的带领下自发的维持着传统的“三月三”活动。但是,由于后期移民政策的一些问题,农场领导为了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不再关注相关活动。从2004年到2015年间,三合口壮族移民的“三月三”集体民俗活动就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从上述情况我们不难看出,这批东兰移民迁移到农场后,他们的身份转换成了国家企业的职工,他们的言行都受到企业环境的约束。以前在村里,同村的人们都主要以宗法“血缘”构成其经济形态的结构支架。这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核心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具有浓厚的乡土性、稳定性、排他性、孤立性。在各种事务处理过程中,“血缘”关系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血缘”关系使得每个人在其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话语权,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社会群体性质基本属于“首属群体”?譹?訛。而迁移后的工作生活中,“业缘”关系则成为其生活工作的主要构架,“血缘”关系在事务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明显降低,社会群体性质则是以次属群体?譺?訛为主。由于社会分工与职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群体关系的差别,这些移民不得不受限于企业环境的约束。譬如在“三月三”活动中的人员组织、费用开支、场地申请、节目审核等等都必须通过企业领导层面的讨论与决议。这种情况对于这些壮族移民来说,无疑从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迁移前他们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人格与文化尊严等在迁移后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些都无疑会造成移民心理上强烈的失落感。
此外,移民行为的调整方向也是随着迁入地本土文化的强弱优势而变化的。“其中,数量优势,即迁入地土著居民的人口优势,往往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当其数量处于劣势时,往往会选择对外封闭的生存方式、拒绝改变其行为方式,或向迁入地的文化方式趋同。”?譻?訛因此,在迁移后的早期时间(1992~2004年),这些东兰壮族移民基本上都是小范围的进行传统“三月三”民俗活动,甚至同一时期迁移到另一分场(星星农场)的大化县同族移民都没有受到活动邀请。可见,早期这些东兰壮族移民对迁入地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一方面可能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所造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经济、文化的相对滞后所带来的某种卑微的心理使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其传统民歌文化而言,不仅其民歌文化发展受到局限,而且在其后续的传承中,对年轻人心理也会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即只有在熟悉的人群与特定的时间才能唱这一类的歌曲。而这与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内涵相去甚远。
(二)城市化的环境对思想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影响
在少数民族村落的迁移中,移民自身的文化背景和迁入地的文化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差别。但就三合口这批东兰壮族移民而言,除开民族文化差异外,对其思想与价值观念冲击最强烈的还是来自于迁移后的城市文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很多新观念、新方式正在我国沿海地区融汇成型。我国的城市化与城镇化建设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广西合浦县隶属于北海市,南临北部湾,距北海市仅28公里。而且,广西合浦县是我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历来就具有商贸的传统与积淀。因此,合浦的城市文化建设受外来思想文化影响较大。而东兰移民所在地三合口农场距合浦县城仅5公里。因此,这一批东兰壮族移民的生活受县城文化思想影响较大。一方面,移民受改革开放思潮的影响,更富有竞争与进取意识;另一方面,开放与进取意识也使移民能够获取更多价值实现的途径,扩大了交往范围,增强了与周围人群的交流情感,从而影响了当地土著居民对移民群体的认知、态度与情感。
如今,当年的东兰壮族移民已经和当地居民融为一体。移民不仅学会了当地的语言,而且受地方文化影响,喜欢听各种地方音乐以及大众流行文化音乐。同时,这些壮族移民也不再拘束于自己的文化活动,而是更具有包容与开放性的展示自身的民族文化特点。这也是2016年三合口“三月三”民族文化活动得以开展的民众心态之一。当然,随着移民自身文化与地方文化的交融,也注定了这些壮族移民传统文化的改变。“这些新元素(城市化的思想意识、社会观念、价值取向)的注入将会使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如民风民俗、民族风情、民族建筑艺术风格、民族服饰、生活情趣等逐渐得到改变、更新和消亡。”事实上,“迁入者文化与安置地文化必然在长期交融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使自身不断得到改变,甚至发生同化或变异”?譼?訛。这种文化上的改变其实质是“两个民族间的相互接触所产生的文化移入过程的结果”。文化移入的前提则是心理移入,而心理移入又是受到文化移入的约束。“一个群体或民族的文化移入过程首先是从该群体或民族中的某些个体的心理移入开始,随着群体或民族中与其他群体或民族接触交往而发生心理移入的人数日益增多,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整个群体或民族的文化移入。”?譹?訛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东兰壮族移民在语言、价值观、道德、宗教等各个方面都与当地主流群体产生过各种摩擦、冲突。这也是2004到2015年期间“三月三”民俗活动没有开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但随着移民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东兰移民对现实生活的逐渐适应,双方冲突也逐渐减少,东兰移民也逐步完成了整个文化移入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改变还是从个体心理变化开始的。譬如这些壯族移民在服饰、饮食习惯上逐渐与合浦地方一致,只有某些节日中才会穿民族服饰,做五色饭、红鸡蛋等。此外,一些移民在农场的帮助下学会了新的生产技能与知识,还有一些移民在与周围居民进行一些经济来往过程中,产生了商贸经济的观念等。这些改变直接导致东兰移民在兴趣、爱好、动机、价值观、世界观等的变化。特别是在农场长大的新一代移民,他们基本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等情况。而这些新一代移民,他们对于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已较他们的父辈们淡化了很多。在采访调研中我们得知:1992年迁移过来23对歌手,现在还剩四个老歌手,整个三合口农场3000多移民群体中,既能编歌也会唱歌的歌手大概也就20人左右,年龄均在30~50岁之间。很多小孩与年青人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学习唱山歌时,多数的回答是不好听,觉得老土。可见,新生代的这些壮族移民在心理上已经被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了。
三、迁移与安置模式对其民歌文化发展的影响
从目前来看,国内对于移民性质的划分基本上还是从移民自身的意愿(自愿与非自愿、主动与被动)、移民行为与现象(工程性、灾害性、战争性、政治性、经济性)、迁移与安置方式(集体性与分散性)进行的分类。而初迁移到三合口农场的东兰移民是为了岩滩水库建设而进行水库移民,是属于较为典型的非自愿性移民,其迁移与安置方式为集体性迁移和集中性安置。这种迁移与安置方式对其民歌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影响。
(一)壮族民歌演唱的主要特点对移民传统民歌文化保护的意义
对于水库移民,一般都采用集体性迁徙的形式进行,由政府进行相关组织、安排与落实。极少数以个体的形式去投亲靠友的,也多由政府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资助。而集中型安置“是以库区原住民组成的一个新群体集中在安置区进行生产、生活。即使其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发生了改变,原有的邻里关系及其人文环境优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存”?譺?訛。事实上,也正是当年的迁移与安置方式使得现在这些壮族移民还能保留一些传统音乐文化。集体性迁移与集中性安置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就是对移民原有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的保留。1992年,三合口农场接收安置河池市东兰县岩滩库区东兰壮族移民442户,2196人,其中大同乡440户,长江乡仅2户。另外,当时迁移过来的人口也以青壮年为主,因为农场是按户分配种植土地,因此,每一户人家基本上都会保证至少一个年富力强的劳动力。而且,集体性迁移能够让这些村民在生产生活方面继续延续以前的关系,相互扶助。同时也促使这批东兰移民在思想更新、经济转型、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做到相对同步与统一。另外,在安置方面,虽然这些移民被分别安置在18个不同的分场,但这些分场彼此间的距离不远,最近的3里路,最远的也就14公里。移民之间依然能够保持较为便利的交往与交流。因此,这些三合口的东兰移民基本上还能有很多传统习俗在彼此生活中得以保留。安置后早十年间的“三月三”活动也多是因为大家彼此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而且能够时常走门串户,守望相助的原因。当然,民歌文化,作为东兰移民最重要的民俗习惯自然也在这样的环境中被保留了下来。
(二)对移民社区民歌文化发展的意义
移民文化是“移民社会产生的观念形态文化,即移民社会中人们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主要包括伦理道德、宗教、哲学、艺术、政治法律思想、教育思想等成分,其中价值观是它的核心”?譹?訛。
三合口农场作为岩滩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点,与移民原居住地较远,两地相距510多公里。而且东兰县属于广西河池市,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形多样,结构复杂,交通极为不便。而三合口属于海边城市,具有典型的冲积平原地貌。而且东兰县是以壮族为主,杂有苗、瑶、侗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壮话为当地居民的重要土著语言。合浦则是以汉族为主的一个行政地区,白话、客家话、粤语为其主要地方语言。因此,两地的文化差异性较大,致使东兰移民的文化很难融入到当地的文化中。东兰移民文化作为外迁型移民文化,早期在面临合浦地方文化环境与社会群体时,所受到的外界压力较大。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却促使了东兰移民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保护。移民文化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保守性。“水库移民在库区原居住地的文化世代沿袭,根深蒂固,即使移民搬迁引起区域环境的巨大变化,他们也不可能全部抛弃原有的文化;相反,人们总是力图在新环境中保持原有的文化,并在新区域的容纳下继承和发展原有的传统文化。”?譺?訛对于这些东兰移民而言,保留自身的民歌文化传统不仅仅是自我民族身份的归属与认同。同时,对于安置地移民社区民歌文化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合浦当地的文化来看,汉文化是其主要表现形态与形式。当地的民歌主要有“西海歌”、“叹家姐”、“黎歌”等。这些歌谣都是用客家话、白话或是廉州话演唱。而东兰壮族移民所带来的歌谣文化,则为本地歌谣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方面,移民本身开始学习合浦的地方主流语言,甚至有些歌手也能够唱当地的民谣,这无疑是移民与原住民之间最好的沟通桥梁;另一方面,东兰壮族移民的传统民俗活动,如三月三、蚂节等也吸引了大量周边原住民的兴趣。2016年的三合口农场下属的平头岭分场所举办的“三月三”活动就吸引了很多周边的原住民一起来观看,甚至还有当地歌手表示出同台演唱和参与的兴趣与态度。这种不同民歌文化的交流与学习,恰恰为移民社区的多元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榜样与贡献。移民文化不仅有稳定与保守的一面,其更重要的是具有开放、发展、兼容的特性。集中性安置能让移民既能够保证自身文化传统符号的不变,同时又能吸纳新环境中的优秀文化元素,去发展出超越原有差异的新的民歌文化。
四、结语
文化的影响总是双方的,这种发展与变化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东兰壮族移民的现实情况来看,他们在生活上已经基本适应了当地的民俗习惯,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而这时,一些壮族移民,特别是一些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开始呼吁族人们来学习他们的传统民歌。这也是作为少数民族移民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对自身民族身份、民族情感的一种自我认同与归属感。但是,传统民族文化在现实中的没落让这些具有民族情怀与身份的移民深感焦虑,因为民族身份的体现其根本就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壮族传统民歌文化在这些东兰壮族移民身上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民族身份符号。而这种符号在当前的移民安置地又显得那么微弱。这或许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移民安置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普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