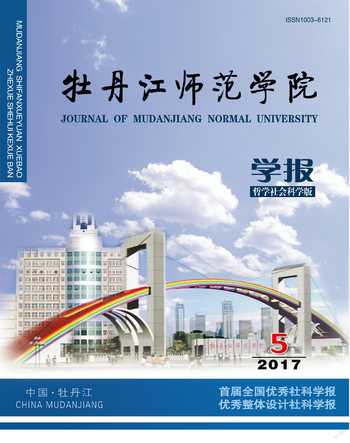第一人称叙事文本的张力
2017-05-30彭成广
彭成广
[摘要]不同的人称叙事在同一文本中的应用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本张力,并能深层影响读者接受感知机制的形成,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韩少功在多种文本与不同文类中偏爱第一人称叙事的应用,这既展现了他熟练的叙述技巧,更是其本人文学观与写作立场,乃至艺术美学思想的充分体现。他在作品中通过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既充分干预控制了“叙述者”,又使得作者与“叙述者”的身份交替与重合,产生了“互文”式的独特美学效果,彰显了自我言说的自由权利,实现了写作与现实的交融。
[关键词]韩少功;第一人称叙事;张力;互文
[中图分类号]I01,I04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7)05006305
叙事人称在文学文本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拥有高度书写自觉的作者而言,使用不同的人称叙事,绝不只是作者的写作习惯,而是作者精心运作的结果。一方面,不管作者有意无意,同一文本使用不同的人称叙事必定会产生不同的文本张力,深刻影响读者接受感知机制的形成,从而产生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这是文本所产生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選用何种人称叙事,与作者的文学观念、写作立场乃至艺术美学思想是高度契合的,与作者为实现某种特定的文学主张或艺术理念紧密相关。本文以韩少功的作品为例,探讨他偏爱第一人称叙事,即“我”叙事的深层原因,以期能够阐述第一人称叙事的文本所产生的独特艺术张力和审美效果。
一、第一人称叙事的文本张力
申丹认为,“第一人称在回顾性叙述中有着特有的双重聚焦,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的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1]238概括来说,第一人称叙事使得“叙述者”与“被叙述者”的关系交织不确定,也使得所叙述的文本处于“可靠”与“不可靠”之间,而“叙述者”不必为叙述的“可靠性”做出任何承诺;同时,“叙述者”既可以透过自我的真实经历“全知视角”叙述,也可以用个体的一面之词作“半知视角”叙述,叙事的空间和灵活性得到了有效的拓宽。最为主要的是,这种叙事的含混性给予了接受者更多的揣测和质疑空间,从而使得原本封闭的文本更具开放性,产生了独特的文本张力。以韩少功《报告政府》中的片段为例:
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骂我。我后来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我坐在他上方,耳光都扇在他脸上了……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是受害者呵,被我的上方打得更重,左脸早成了热面包。我那一刻只惦记着身后晃悠的电棒,哪里管得住自己出手的轻重?……
我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一直到我一年多以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也不知道这事是谁干的,就像我不知道监仓里很多秘密,按规矩也不能打听这些秘密,永远也不能说出这些秘密。比方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守所有那么高的围墙,拉了那么多的电网,装了那么坚实的铁门,连一只蟑螂都混不进来,但居然还有蜡烛、香烟、味精、酱油、白酒混过了关卡,甚至有锉子、钉子、刀子、淫秽画片这些严重违禁品混进仓来。有的女犯还在这里受精怀孕!这是一池永远不会澄清的浑水,你没法明白其中的全部故事。[2]208
这段文本中,第一人称叙事“我”的出现频率相当高,这必然涉及到“我”的身份问题,“我”在这里有三重身份,即:作为“叙述者”的“我”、作为“被叙述者”的“我”和作者本人,“我”在“现在”与“过去”的历时转换中存在。例如,第一句“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骂我”,这样改写也许才能更准确地解读:“(现在的)我才知道他是骂(当时的)我”,而连续使用“我后来……”这种回顾性的叙述手法,把“过去将来式”的感知通过“现在的我”来完成。问题是,这种完成到底是什么时候?是“现在的我”开始回顾之时,还是早属于“过去”?这种含混性会造成读者接受文本时产生延宕感,属于典型的叙事干预。本来用第一人称叙事会显得文本更确定,但“我”反复出现,反而使得文本更加不确定,“我”身份的游离使得接受者会质疑叙述者的权威;而“我也是受害者呵”中的“我”,既可以看作现在的“我”对经历者“我”的追述,也可以作为经历者“我”对当时情景的描述。“我”的游离性带来“我”的多重视角,既让文本更可信,又让文本更可疑,这是第一人称叙事带来的文本张力。
读者对“叙述者”所叙述文本的可靠性产生了质疑,这无疑是对叙述者叙述权威的挑战,所以,有很多文学文本的叙述者为了加强叙述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会对文本故事发生的背景、人物故事的环境等详细交待。第一人称叙事所拥有多重视角在同一文本中重叠,叙述者的视角介于全知和半知之间,尤其涉及到“被叙述者”的心理描写活动时,一方面,“我”的心理活动的真实性不容质疑,叙述内容不需要过多的修饰、限定与解释,语言精简明晰,叙述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叙述者和作者又是分离的,作者如何能作为全知者洞察“被叙述者”的心理动态?这一问题至今仍是叙事学的难题。对于接受者来说,在文本的现实接受中,接受者由于对真实作者的经验认知、了解与信任,用第一人称叙事会对读者的接受造成干预,无形中加强了作者与读者的情感交流,从而获得文本之外的真实感。
第一人称叙事“我”的反复出现,还会造成文本多声部的复调效果,其中有作者的声音,也有叙述者的声音;有现在的“我”的声音,还有过去的“我”的声音。这种复调性对于作者来说,“我”也许更能表达作者的身心感受,作者真实的经历在小说中大量出现,作者能够随时与“我”的情感进行同步体验,这是文学作品重要的位移属性。“借他人美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可以视为我与叙述者、作者的关系,其文本在更加确定与不确定、真实与不真实中实现对立统一,也增强了文本的张力。
二、第一人称叙事文本的“互文”效果
第一人称叙事还可以造成独特的“互文性”效果,“互文性”理论创始者朱丽叶·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3]36对于传统狭义的“互文性”理论而言,互文主要是从历时性的维度来解读,即较早的文本在较晚的文本中的体现,如王小波小说作品对唐传奇的互文。其实,互文也应该兼具共时性的解读维度,就是说,同时期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织穿插,互相印证,特别是同一文类之间,同一主题的重复出现和交叉征引。如,现代派武侠小说中的多种派别组织、武功招式和武器等在不同的武侠小说中反复出现,这有两个直接的美学效果:其一,为小说的虚构平添了真实性,使得文本更可靠;其二,通过这种交织构建,形成独特的“类网”,为所构建的世界赋予自律性和合法性,这类文本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则。
韩少功偏爱第一人称叙事,大大拓展了文本“互文性”的空间。其一,他打破了文类的限制,同一文本内容,如散文随笔中出现的人物、情节、故事再次出现在小说类型文本中。反之亦然,如《鞋癖》(载《上海文学》1991年第10期)作为一篇小说,其文本内容又在自传性随笔《母亲的看》中大量出现。类似的例子在《马桥词典》中俯拾皆是。其二,韩少功还把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访谈甚至讲座经历也直接插入复制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
从文本上讲,偏爱于用“我”叙述,似乎使得互文无所不包,使得文本更具张力,从而拓展了“我”的生存空间。正如艾柯所言,“当小说人物开始从一个文本迁徙到另一个文本,他们就在现实世界里得到了一张身份证,并从创造他们的文本里解放了出来。……严肃地对待那些小说人物可以制造出一种不同寻常的互文性,一部小说作品里的一个人物可以出现在另一个小说作品里,以一个真实性的信号出现。”[4]133由于第一人称“我”在不同文本不同文类之间拥有多重合一的身份证,“我”似乎无所不能,畅游于各种作品之中,可以从容地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自由活动,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身份增加了可信度和真实感。也就是说,“我”的身份能够在不同的文本甚至文体中得到印证。这样一来,本来在散文中“我”所具有的真实性由于在小说中同现而打折扣;而在小说中“我”的虚构性又会由于在散文和随笔中的同现平添真实感。“我”永远处在游动中,能够在虚构与真实之间畅游,在文本间拥有了流动的生存形态,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第一人称叙事“我”所造成的文本张力还对传统文体分类进行了有力的质疑与反叛。传统认为,文体的划分是既定沿袭的,是一种规则传承,后来者只能遵守既定规则。诗歌就是诗歌,散文要像散文,小说只是小说,而韩少功对此显然很不满。他在《文体与精神分裂主义》一文中对此提出了批评:“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理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方便,而是一种体制化的利益强制之下,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到了这一步,写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5]6768如果让形式(即文体)来限制内容,无疑是削足适履,这对人特别是作家的表达机制而言,实在是一种戕害。
借用哈罗德·布鲁姆的在《影响的焦虑》中的著名观点:“作家和诗人一样,永远无法摆脱前辈的深远的影响,作家从意识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不得不承受着这挥之不去的巨大阴影,处在无休无止的焦虑之中。”[6]54韩少功一直试图解蔽这种阴影。他一表立场:“我想可以尝试一种文史哲全部打通,不仅仅散文、随笔,各种文体皆可为我所用,合而为一。当然,不是为打通而打通,而是像我前面所说的,目的是把马桥和世界打通。这样可以找到一种比较自由的天地。我以前写小说常常不太满意,一进入到情节,就受模式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到一种感知成规的控制,一种传统小说意识形态的控制,在那种模式中推进,这就受了遮蔽,很多东西表达不出来,这样一打通,自由了不少,当然,也必定会产生新的遮蔽。 ……我的小说兴趣是继续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7]
不同文本中“我”的反复出现也会影响读者的接受感知机制。如前文所言,由于自传体中的“我”同时出现在某本小说集中,“我”的真实性就会降低,事实上,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某个作家的自传,谁能保证作者不是在以自传的名义创作一部小说?同理,冠名“小说”的文本中,谁又能断言此部小说完全无“真实性”?也许这只是自传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是韩少功对传统的叙述模式的反叛所带来的美学效果。他打破了读者原有的接受机制,自传体不一定要真实,而小说也不一定就是虚构。
通过频繁地使用第一人称叙事打破现有的叙事模式,还我一个“自由”身,这是韩少功多年的夙愿。他认为,这是一个健全的人本来应该具备的生存权利:“让我们自己在写作之前,首先成为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像常人一样来感知和言说这个眼前的世界。”[7]常人的感受机制应该是丰富的,是理性与感性的合一,其言说方式是多姿多彩、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绝不能用传统规则如文类的限制来束缚钳制。他巧妙地通过赋予“我”的多重身份,较为有效地打破了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与规定,让既定的所谓文体类型变得模糊,是对传统文体分类的否定和解构。
三、写作是言说自由与生存权利的统一
韓少功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来叙述,可以看作是对写作“自由”与主体“自由”之生存美学观念的践行,是超越传统与实现自我的尝试。用“我”叙述,是作者对自我叙事权利的肯定;不管何种文类,都根据作者本人的实际言说需要,随手拈来为“我”所用,以此寻求比较自由的叙述天地,进而成为对自我生存权的争取和延伸。生存权不只体现在基本的生活权利,如衣食住行的满足上,更应该体现为个体表达机制的完善、个人尊严权利的肯定与维护。对于作家而言,这种尊严首先体现在自由书写的权利上,找到适合自我心脑解放的书写方式尤为必要。而打破传统文体的界限,颠覆文坛的既定规则,挑战传统的思维定势,这些都是方式途径,却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解放自由书写的约束和规则钳制,恢复了作家心脑合一的书写权利。书写不仅仅要承担对他人乃至社会的公共功用,更是个体内心言说的释放与践行,是外向性和内在性的统一。韩少功作品的“互文”,是广泛意义上的“互文性”。互文不再是文本间的互文,而是文本中“我”与现实中“我”的交织关系。书写不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事情,书写与生活是言行合一的典型方式。
当然,作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写作必然要承担着现实生活中无法尽善的责任。这一点韩少功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从创作论到思想方法》《好作品主义》等文中作了具体阐述。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他说:“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当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语言的世界,当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语言来养育和呈现,语言的写作和解读就已经超越了一切职业。”[5]51他在此强调的是,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和自我“观照”的生活态度。从个人角度上看,作者自我的生存观和现实主张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言为心声,文学所具有的情感宣泄功能使现实生活中的焦虑不安等负面情绪得到很好的释放。此外,文学还可以点燃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想,作者理想式的生存方式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圆满地实现,从而实现审美的超越。从社会角度来看,文学应该有自己的特定社会属性,它必须反映人生一些永恒的主题,以此来对日新月异的现实做必要的养分补给和精神坚守。这包括批判也包括推崇、包括坚守也包括舍弃、包括前进也包括回归。这也是韩少功一贯的文学主张:“有幸的是,我们的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使命,相对于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学不会像电脑286、386、486那样的换代升级;恰恰相反,文学永远像是一个回归者,一个逆行者,一个反动者,总是把任何时代都变成同一个时代,总是把我们的目光锁定于一些永恒的主题,比如良知,比如同情,比如知识的公共交流。”[8]10
韩少功作品中对第一人称叙事的应用,是韩少功文学主张的集中体现,产生了独特的文本张力及美学效果。以此,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在于,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仅仅要自觉的逾越传统、打破传统定势,创新传播和接受机制,实现传承、反叛、解构与建构的统一,更要把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乃至生存观念内化在作品中,实现言说自由与生存自由的高度融合,彰显人性的良知与美好,建构向善向美的精神世界,这既是作家必有的立场,也是作家应有的追求和梦想。
[参考文献]
[1]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韩少功.韩少功精选集·报告政府[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3]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86.
[4][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吴义勤.李莉,胡健玲编选.韩少功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