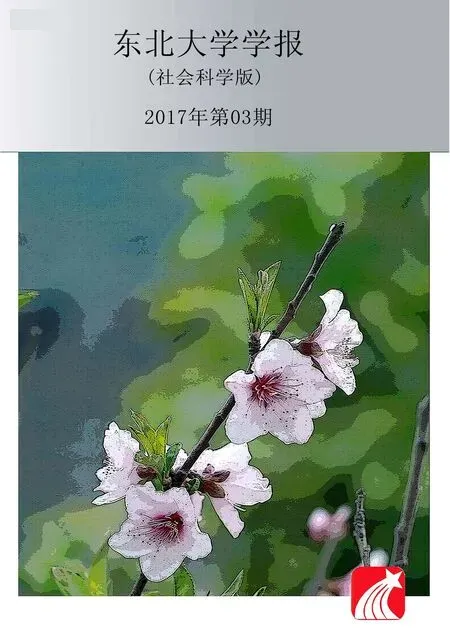环境治理政策的工具偏好与路径优化
----基于43个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2017-05-25杨志军王若雪
杨志军, 耿 旭, 王若雪
(1.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3.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环境治理政策的工具偏好与路径优化
----基于43个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杨志军1, 耿 旭2, 王若雪3
(1.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2. 深圳大学 管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3. 西南交通大学 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有效的环境治理离不开环境政策工具的科学选择与运用。借助内容分析法,按照样本选择、分析框架构建、文本单元编码及数据分析的逻辑,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颁布的43个环境治理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揭示我国政府在环境治理工具选择上的一般规律及其偏好。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治理中存在强制型政策工具运用过溢、政府行政主体运用分布不均,以及经济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等问题,并提出适度降低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重视经济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加强公民与第三方组织参与度、健全政策工具使用机制等优化路径。
环境治理; 内容分析法; 强制型政策工具; 自愿型政策工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治理问题也已经摆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和新要求:“一是了解和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重大意义;二是作出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三是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四是让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五是认真解决关系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六是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更加完善”[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环境治理的关键要靠政策工具。要使政策有效,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权威和财力支持,良好的政策执行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2]。欧文·E. 休斯将政策工具定义为:“政府的行为方式,以及通过某种途径用以调节政府行为的机制。”[3]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社指出:“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是政府在部署和贯彻政策时拥有的实际方法和手段。”[4]作为政策工具的一种特殊类型,环境政策工具是指公共政策主体为解决特定的环境问题或者实现一定环境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手段的总称。当前,主流的环境政策工具被分为命令强制型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及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三种, 如何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不同的被规制对象科学地选择环境政策工具成为重要议题。基于此,论文采用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methed),选取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中央政府颁布的43个政策法律文本,构建“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进行文本编码和数据分析,总结我国政府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
一、 研究方法与样本选择
1. 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最早源于“二战”期间的新闻界,主要用于传播学和政治学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随着内容分析方法在计算机领域中的运用,其应用范围逐渐从新闻界扩展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5],尤其是在情报科学和管理学领域,得到了很好的使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认为,内容分析方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信息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6]。内容分析法一般需遵循以下几个步骤:①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②抽取研究样本;③选择分析单元;④建立分析类目;⑤定量处理与计算[7]。其优势在于可以将用语言表达的文字性材料或政策文本转换成用数量表达的资料,从大量文本和历史数据源中提取和获悉新观点,找到能反映文献内容本质且易于计数的特征,从而克服定性研究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有助于了解真实的事件范围和验证其他方法的有效性,达到对文献“质”的更深刻、更精确的认识[8]。
这种方法适合于对一切可以记录与保存并且有价值的文献作定量研究,抽样方法较为多元,一般有来源抽样、日期抽样和单元抽样三种方式,其抽样原则包括符合研究目的、信息含量大、具有连续性、内容体例基本一致等[9]。诸多统计技术,如频数、百分比、卡方分析、相关分析及T-TEST等都可用来展示所分析内容的特性。其基本逻辑在于:研究者可先设立评价标准和分析单元,然后将文字的或图画的非定量内容转化为定量的数据,这个转化的过程主要是根据理论引导观点来进行。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按照最先确定的评价标准、分析的类别和单位进行统计,统计出什么结果,就只能表达和传播什么结果,不能从个人认识或主观情感出发左右分析的数量结果,更不能通过修改或者调整数据结果来呈现符合研究预期的结论。
本文严格按照上述规范、要求和流程来使用内容分析法。首先选择我国制定的环境治理政策文本作为内容分析样本,再根据政策分析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然后将各个政策文本中的政策工具内容进行编码来定义分析单元,随后把契合框架的政策编号归入分析框架中进行频数统计,最后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样本选择
从政策文本中挖掘我国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揭示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成为研究环境政策工具的重要路径。已有环境政策文本领域比较广泛,数量也很多,为了保证取得的政策文本具有针对性和代表性,本文主要聚焦水、大气和土壤三个方面的政策文本。考虑到样本来源的权威性、代表性及覆盖面,主要选择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直属机构而非地方性机构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意见、办法、通知公告等,所有文本均可公开查询,具有较强公信力和关注度。通过梳理和筛选,最终确定有效文本43份,时间跨度为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颁布施行到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等多部法律法规颁布,按照颁布的时间先后顺序制作文本表,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环境治理政策法律文本
二、分析框架:工具—价值链二维框架
政策工具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理性要素,更要考虑价值要素。合理的政策结构需要政策主体兼顾自己所在的政策位置与其他政策主体的上下、左右、前后的关系。例如,时间层面表现为先行政策、现行政策与后续政策间的继承,空间层面表现为多个平行或不同层级政策间的互补等[10]。在确定研究问题和数据来源后,最核心的步骤是建立文本编码的理论框架和参照标准。本文从工具和价值链维度出发,构建政策工具分析的二维分析框架,从而进行文本编码分析。其中,工具维度是X维度,代表环境政策工具的不同类型;价值链维度是Y维度,代表环境治理领域涉及到的被规制主体。通过工具-价值链二维框架,能够更加全面细致地分析我国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情况。
1.X维度:基于政策工具维度
正如引言所述,基于政策工具对被规制者的强制性程度,可将环境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强制型政策工具、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和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三种类型,其中命令强制型政策工具采用行政命令的强制手段对环境治理进行直接作用,经济激励型政策工具采用经济手段对环境治理进行作用。相对于行政强制型和市场经济型来说,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间接作用。
第一,命令强制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其表现为国家或政府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强制的直接作用,通过法律或行政命令的强制型手段对环境进行治理,对环境治理发生作用。本文将其细分为行政处罚、目标责任制(考核制)、环境问责、运用评价、淘汰制等。
第二,经济激励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它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理论基础来自于“庇古理论”和“科斯定理”,污染费、许可证、技术支持、财税补给等都是其具体的治理工具[11]。本文将其具体化为污染费、许可证、技术支持和财税补给四种类型。
第三,社会自愿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它是自愿性协议,类似于俱乐部理论的治理方案。企业实行自愿性环境政策,自愿改善环境的动机在于外在管制压力、非管制压力(如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的兴起、环保 NGO 组织等),以及企业和自愿性协议自身的特征[12]。可以细分为环保NGO、第三方评估两种。
2.Y维度:价值链维度
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有社会、政府、企业、公民, 依次从社会可持续发展、政府稳定、企业形象、公民“三生”(生命、生存、生活)四个视角着手展开分析, 实施政策工具就是为了达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目标, 不同的环境政策工具在不同的主体作用下生的效果和影响并不一样。 将四个主体的作用和影响简化为价值链维度, 也就是Y维度, 结合基于三种政策工具的X维度, 最终形成了环境政策工具分析的二维框架, 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政策工具分析的二维框架
X轴主要集中于命令强制、经济激励和社会自愿三种政策工具类型,分别嵌入具体的政策工具内容。Y轴中社会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合力共治的作用;政府则是为了维护生态安全和获得环境治理绩效而采取的政策行动;企业代表的是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要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公民体现的是对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追求。
三、 文本单元编码与数据分析
1. 文本单元编码
在本文的内容分析法中,分析单元是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有关政策条款。首先对43份政策文本的内容按照“政策编号-具体条款-章节”的格式来进行编码,然后根据建立的环境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将这些政策文本进行归类,最终形成了内容分析单元,如表2所示。
2. 数据分析
按照政策工具-价值链的二维框架,将不同编码进行归类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从总体上来看,43份环境治理政策文本兼顾了行政强制型、市场经济型、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内容涉及了公民、企业、政府、社会四个领域主体,对环境治理提供了多方面的激励和规制。从三种类型环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看,我国环境治理中以行政强制型为主,文本编码统计频次达到94,比例达到61.438%;其次是市场经济型,文本编码统计频次达到52,比例达到33.987%,最少的是自愿型政策工具,文本编码统计频次仅为7,所占比例为4.575%。

表2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节选)

表3 环境政策文本的三种工具选择频数分布
具体到各个类型的环境政策工具,如图2所示,在强制型政策工具中,行政处罚比例为40.426%,占了将近一半,其次是运用评价(19.149%)和目标责任制(18.085%),最少的是淘汰制(6.383%)。在经济型政策工具中,许可证(26.923%)、技术支持(26.923%)、财税补给(30.769%)的比例相当,污染费(15.385%)比重稍小。自愿型政策工具在整个政策文本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在政策分析单元中的第三方评估占绝大部分,比例为71.429%,环保NGO为28.571%。

图2 环境政策工具三种类型的具体选择频数分布
引入主体价值链维度影响因素,得到工具-价值链框架下的环境政策工具选择频数分布,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在环境治理政策的主体价值链维度中,针对公民、企业、政府和社会的环境政策工具使用比例分别为3.268%、65.359%、29.412%、1.961%。从总体来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覆盖的主体比较全面,但是对于在各个主体中的比重就不一致,企业和政府的比重较高,而对公民个体和社会涉及少,两者之和不到10%。这进一步说明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和政府所占的比重和作用较大,但也可以看出我国在环境治理方面对于公民个人及社会的力量有所忽视,在鼓励公民和社会参与环境治理方面的力度不够。

表4 工具—价值链框架下环境政策工具选择频数分布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第一,过多使用以“行政处罚”为代表的强制型政策工具。根据环境治理政策文本的条款单元频数分析,环境治理政策文本涉及到的政策工具条款大部分是强制型政策工具(61.438%),而在强制型政策工具中“行政处罚”政策工具占到了40.426%。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有11条政策条款是属于强制型政策工具,行政处罚就有8条,并且政策条款中还存在违反相同的政策条款时,行政处罚的政策条款分做两条来解决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在制定环境治理政策的时候,往往由于先前的环境治理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而后期新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又在不断涌现;或者是环境治理政策在前期的执行中没有达到预期成效,在新一轮政策制定之时为了弥补前期的不足又必须再提及和贯彻,如此便造成了过度重视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
第二,经济型政策工具和自愿型政策工具采用比例不匹配。图2结果显示,经济型政策工具的比重为33.987%,自愿型政策工具的比重为4.575%,总和不到40%,与强制型政策工具(61.438%)相比,使用频率严重失衡。其中自愿型政策工具比例更是不到整个政策文本条款单元的十分之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级政府习惯于采用强制型手段开展环境治理行动,短平快,往往能收到效果;再加上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环保NGO和第三方评估发展尚未完善,缺乏使用自愿型政策工具的行政动力,社会也缺乏合作治理精神。很多政策文本只是稍稍提及“鼓励公众参与”,比如《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中“加强社会监督”的条款,对于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参与社会监督没有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对于鼓励第三方评估的政策文本更是少之又少。
第三,环境政策工具运用中政府、企业、公民主体间关系失衡。从表4来看,企业的政策工具(65.359%)和政府的政策工具(29.412%)占了政策文本条款的绝大多数,公民(3.268%)和社会(1.961%)所占比例很少。在43个政策文本中,以行政处罚式的命令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数最多,其次是以排污许可证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型政策工具,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最少。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推行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文本只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这些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在行政主体间的权力失衡极易导致环境治理格局失衡,最后造成环境政策执行的效果不佳。从依法行政的角度来讲,环境治理的问题解决应该是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来共同进行而不仅仅是依靠政府权威和企业力量。
第四,基于经济型、自愿型的环境政策工具并没有取代传统的强制型工具。尽管西方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基于市场信息工具、自愿型工具等新环境政策工具,但并没有放弃或取代以命令—控制为特征的强制型或管制型工具。2008年以来,我国逐渐建立了新环境政策工具的初步体系,具体包括环境收费、绿色税收、生态补偿、绿色资本市场、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绿色保险等基于市场的工具和以ISO14000、清洁生产为主的自愿型工具等。然而,这些新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在“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排污收费”“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限期治理”“集中控制”等环境治理管制型政策制度的基础之上。所以,对于强制型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价值及其效果,应该一分为二地加以评判。
第五,基于经济型、自愿型的环境政策工具的运用平台和评价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一方面,市场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平台和评价机制尚存在缺陷,难以实现政策工具的政策合力,发挥政策效应,实现功能互补。另一方面,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又缺乏健全的使用机制和成熟的运用平台,很难确保环境治理时空格局的连续性、系统性。以“行政处罚”“目标责任制(考核制)”“环境问责”“运用评价”“淘汰制”“许可证”“技术支持”“财税补给”“环保NGO”“第三方评估”等内容构成的环境政策工具内在关系不匹配,比例不协调,性质单一,不利于建立和完善环境治理新格局。随着政府角色由传统的政府至上转变为公民至上、社会至上,必须随之转变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类型,建立科学专业的新型政府政策工具使用机制和操作平台。
2. 政策建议
环境保护工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环境治理工作要达到好的效果,不仅要完善政策文本,更要注重政策工具的使用和执行效度,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通过建立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的追踪评价机制保障政策执行效果。环境治理政策制定部门应该对现有的强制型政策工具进行统计,对相关环境政策治理政策的实施时间及具体情况进行落实,制定政策实施时间表,严格按照规定,监督和督促相关部门的环境治理政策实施情况,同时要健全和完善相应环境治理政策的配套政策体系,提高环境治理政策制定、实施、评估、反馈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要强而有力地监督政策执行,最近开展的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启动,已组建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7个省(市)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在环境治理政策制定方面大力引入环境影响评价机制,对重大公共工程项目决策必须加强环境影响的评价,而且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不仅要加强执行效度,更要突出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第二,切实提高市场经济型和社会自愿型政策工具在环境治理中的使用程度。目前的问题不是不能使用强制型环境政策工具,而是这一工具使用过度,相对应的是,基于市场经济和社会志愿型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又严重不足。需要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促使企业主动改造排污设备,提高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频次,加快研发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源头治理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尤其是在雾霾治理上,要致力于成因攻关[13]。利用社会传媒渠道加强对企业进行环保意识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真正树立环保靠大家、建设美好家园的观念。同时,改善环保NGO及第三方评估的生存发展环境,重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活动,提高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在我国环境治理中为环保NGO和第三方评估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进而借助环保NGO和第三方评估力量支持环境治理,与政府和企业一道解决环境问题。
第三,加快政府转型,运用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构建环境治理新格局。环境治理要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紧紧围绕还权于民、让利于社目标,有权不能任性,让人民有幸福感、获得感,打赢蓝天保卫战。新型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应该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采用多中心治理方式,充分吸纳和发挥各类环境治理主体的作用,不同的治理主体承担不同的责任。政府在清单制度中要强化对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的引导功能,通过法律制度培育好环境治理市场,吸引企业主体参与政策创新过程。企业在环保排污中要加强技术改造升级投入,把社会责任意识摆在首位,遵守法律制度,配合地方政府搞好环境治理。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及环保组织共同发挥自愿型环境政策工具作用,切实履行好公众参与的权利,发挥“人人有责、从我做起”的主人翁意识。由此合力共治,为新型环境治理政策工具有效运行提供良好的运行氛围。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顺利修定并向社会发布,从“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转变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下,环境治理政策的运用要具有系统性:①在顶层设计的宏观层面,要考虑到制定环境治理政策,包括法律法规、制度条例、通知意见的适用性;②在运行载体的中观层面,要注意到本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情况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差异性;③在执行操作的微观层面,要不断创新使用环境政策工具,做到精准施策,综合发力。只有建立健全综合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的环境政策治理工具,细化其使用机制,才能实现政策合力,功能互补,推动环境治理出实效。最后,在政策主体的功能发挥和政策标的的接受程度上,要通过建立健全科学合力的政策结构,让环境政策决策和执行主体能够依法行政,在法律制度上保障社会力量在决策和执行两个环节都有参与权利,在绩效考评环节考虑社会力量的认知感受,对环境治理不力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倒逼地方在环境治理方面积极作为。
[1] 周生贤. 适应新常态,打好攻坚战,全面完成“十二五”目标任务----在2015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17-03-30]. http:∥www.zhb.gov.cn/gkml/hbb/qt/201501/t20150120_294355.htm.
[2] 刘媛. 西方政策工具选择理论的多途径研究述评[J]. 国外社会科学, 2010(5):25-31.
[3] 欧文·E.休斯. 公共管理导论[M]. 彭和平,周明德,金竹青,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99.
[4] 迈克尔·豪利特,拉米社M. 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M]. 庞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141.
[5] 陈维军. 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的比较研究[J]. 情报科学, 200l(8):884-886.
[6] Wimmer R D, Dominick J R.Mass Media Research : An Introduction[M]. Boston:Wadsworth Publishing, 2003:163.
[7] U. 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Content Analysis:A Methodology for Structuring and Analyzing Written Material[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
[8] 吴世忠. 内容分析方法论纲[J]. 情报资料工作, 1991(2):37-39.
[9] LU Xiaoli,WU Chunyou,Donohoe H. Conceptualizing Ecotourism from a Distinct Criteria Approach by Using Content Analysis[J].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6,26(4):1213-1220.
[10] 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M]. London:Logman Group Limited, 1985:83-104.
[11] 吴小建.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描述与实现[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28(1):16-19.
[12] 李伟伟. 中国环境政策的演变与政策工具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24(S2):107-110.
[13] 李克强. 不惜重金组织攻关,抓紧找出雾霾形成的未知因素[EB/OL]. (2017-03-15)[2017-03-30].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03-15/8174484.shtml.
(责任编辑: 付示威)
Tool Preference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43 Policy Texts
YANG Zhi-jun1, GENG Xu2, WANG Ruo-xue3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Law,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cientific choice and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tools. Based on the logic of sample selection, framework construction, text unit coding and data analysis, cont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study the 43 environmental policy texts issued by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hoice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ol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such problems as the overuse of coercive policy tools, uneven use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bodies, and inefficient use of economic policies and voluntary policy tool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ome optimization paths were then advocated including the less use of mandatory policy tools, the emphasis of economic and voluntary policy tools, the enhanced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and third-party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use mechanisms for policy tool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mandatory policy tools; voluntary policy tools
10.15936/j.cnki.1008-3758.2017.03.009
2016-11-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15CZZ034); 贵州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黔科合基础[2016]1512-3号); 贵州大学文科重大科研资助项目(GDZT201505)。
杨志军(1983- ),男,湖北公安人,贵州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运动式治理、环境抗争与政策过程研究; 耿 旭(1987- ),女,江苏连云港人,深圳大学助理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政策分析和政府改革研究。
D 60
A
1008-3758(2017)03-02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