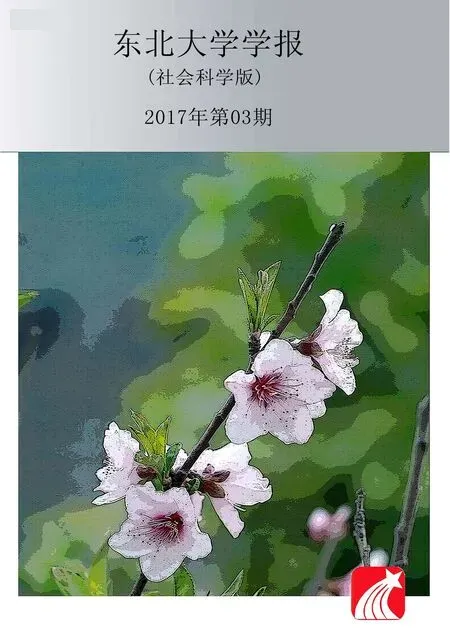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论视角:优势、逻辑与框架
2017-05-25郭随磊魏淑艳
郭随磊, 魏淑艳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论视角:优势、逻辑与框架
郭随磊, 魏淑艳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在政策工具研究形成的技术论、设计论和过程论三个流派中,技术论过于微观、发散,并且与其他研究领域重叠;设计论趋于抽象、复杂,与经验分析存在一定距离;过程论的优势在于,它是事实与规范结合最为均衡的视角,并且与政策过程论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对政策工具形成、运用、变迁的认识构成了理解政策工具全生命周期运转的逻辑基础。根据近年来政策工具理论的发展,结合对政策工具过程理论优势和逻辑基础的分析,可总结出政策工具议程、工具-制度变迁及政策工具创新三个过程论的主要分析框架,从而为推进政策工具研究提供参考。
政策工具; 工具设计; 工具过程; 工具拥护者; 工具创新
作为政策科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政策工具研究在西方已经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政策工具的理论源于政策过程理论的深入发展,在推进政策执行研究中,研究者发现把决策后的政策化解为次级的、操作层面工具的重要性,从界定、分类和选择等角度对政策工具进行了规范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政策工具研究得到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萨拉蒙、豪利特等学者的推动下,新世纪以来,政策工具理论有了明显的进展。
在国内方面,虽然有陈振明、薛澜、顾建光、黄红华等研究者呼吁,但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并不算很理想。相对比较新的视角包括政策工具运用中的交易费用分析、政策工具理论的历史诠释学分析等,但是目前仍然以引介为主,由于没有做好基本的政策工具理论发展过程的学理分析,国内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隔断性,很难结合研究者近四十年探索所积累的学术资源进行再创新。作为连接政策目标和政策现实的政策工具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萨拉蒙甚至认为,改进政府表现的关键就在于改善政府的工具使用[1]。由于国内政策工具研究与西方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本文首先对政策工具学派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科学研究特定假设出发,对政策工具研究三个学派进行评析;最后,对政策工具研究主要知识贡献,即政策工具过程论的分析框架进行总结,以期为推进政策工具研究作一定程度的铺垫。
一、政策工具研究的三个学派及其评价
1. 政策工具研究的学派
在政策工具研究学派的分类上,布鲁金和霍芬分为经典研究、工具环境研究和背景研究三个流派,林德尔和彼得斯则分为工具论、备用论、过程论和构造论四个流派[2]11-44。后一种分类的前三种与前者相似,只是单独列出构造学派(强调工具价值、社会影响因素),在实际的政策工具研究中,多数过程论视角也强调工具价值要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涵盖了构造学派的研究内容。三个类别的划分基本涵盖了政策工具研究的所有范围,本文仍然沿用三类别划分,把政策工具研究分为技术论、设计论和过程论,他们有着不同的渊源和发展脉络。
(1) 技术论
技术论强调政策工具的工具属性,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政策学派的较为独特的特征,其研究范围包括货币政策、环境政策、教育政策、社会管理及政府改革等,例如货币政策中的数量性、价格性工具;环境政策中的环保标志、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工具;教育政策中的教育券;社会管理中的政府兜底、运动式执法;政府自身管理中的流程再造、标杆管理等。除对单个政策工具特性进行研究以外,另一类研究则较为重视政策工具的整体技术特征,即是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对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内容解析,得出其中政策工具运用的整体比例结构,从而对政策工具运用的恰当与否进行判断。这类研究在产业政策和教育政策中较为常见。比如,通过研发、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生产维度,以及通过强制、混合和自愿的政策工具强制维度,对政策工具进行编码统计,从而得出特定的趋势。
(2) 设计论
与技术论研究多学科发散研究不同,设计论研究则具有积聚的特征,主要侧重从总体上对社会问题和对策进行结构化分析。邓恩、麦克唐纳和英格拉姆的研究为政策工具设计论的早期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邓恩最早在政策分析中把问题和对策进行结构化,认为政策分析应首先区分结构良好的问题和结构不良的问题,对不同类型的问题应该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3]。
麦克唐纳对政策工具的研究旨在探讨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机制,认为管制工具旨在促使个人和机构服从命令;激励则旨在使个人和机构用特定行动来换取经济回报;能力构建工具则通过投入资金获得物质、智力及人力资源回报,从而使社会得到特定能力;系统改变工具则通过权威在不同个人和机构中的分配,从而改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系统[4]。施耐德和英格拉姆发展了麦克唐纳的工具行为假定理论,认为政策工具总是试图让人们做在其他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5]。他们研究的问题还包括政策执行中政策方案设计的详细程度, 指出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应运用不同的执行方式,采取不同的政策设计方案[6]。
政策网络的研究从另外的角度推进了政策工具设计理论,强调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运用的适应性,例如布雷塞尔斯根据目标一致性程度和相互关系程度把政策网络分为四类,每种政策网络对应选取不同的政策工具,比如在目标一致及依赖关系强的条件下,工具运用应充分发挥目标团体的能动性,反之亦然[7]。
在沉寂多年以后,政策设计的研究重新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其中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豪利特,他认为新一代的政策设计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变:从单个工具到多个工具的设计内容;从政策策划人到政策咨询系统的政策设计者;从寻找技术知识到实现政治理念的设计动力;从技术到背景考虑的设计方式;从替代到镶嵌的设计过程[8]。在进一步的政策工具设计研究中,他还从抽象程度和层次上对政府目标和工具匹配进行深入探讨,把政策规划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9]。
(3) 过程论
与设计论者重视整体及浓重的思辨色彩不同,过程论研究起源于政策工具所处问题情境的经验分析,强调政策工具的价值因素、推动力量及其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2]38-39。过程论学派认为制度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体现着特定组织价值,离开价值分析,政策工具的分类、选择、使用将变得不可理解[10]。围绕着政策工具往往形成特定的团体,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中,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利益结构、组织关系、知识联系,甚至对于政策工具能够解决特定问题的信念,按照沃斯和西蒙斯的观点,可以把它们界定为政策工具拥护者(instrument constituencies)[11]。在秉持特定价值理念的政策工具拥护者的推动下,政策工具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有着复杂的博弈关系。
研究者们运用过程论进行了多项经验分析,主要涉及工具的制度、价值方面与政策环境的互动关系。马乔纳通过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控制政策工具并不是机械地填补到政策工具的背景之中的,经济学家虽然设计了很多看似合理的经济型政策工具,但不断被批判的管制、法律型政策工具仍然被更多地使用,因为后者与政策制度所在背景更为适应[12]。巴格丘斯在研究教育政策工具时发现,政府所能使用的治理手段仅限于司法及经济等少数政策工具,在这有限的备选政策工具中,政策工具虽然效果并不明显,但仍然被反复使用,政策工具选择本身体现着过程价值、历史价值和程序价值[2]45-62。政策工具与组织的这种互适性,也使其具有指示组织变迁过程的作用。安德鲁·乔丹在研究中把从统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环境政策工具进行分类,通过对欧洲国家环境政策工具的使用状况来考察是不是真正在发生着治理变化,发现虽然多数政府采取了环境治理工具,但这种转变趋势并不明显,新工具与旧工具有一定的互补性[13]。
目前政策工具过程论有与政策过程论其他研究结合的趋势,例如政策工具研究与议程设置多源流模型的结合、与政策循环—子系统模型的结合研究,为拓展政策工具过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14]。
2. 政策工具学派评价
(1) 政策工具理论评价标准
对政策工具三个学派进行评述,本文主要依据以下三个评价标准。
标准1:政策工具研究应该从中观的角度连接抽象理念与微观具体事项的处理,实现事实与规范的均衡。政策工具涉及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形而上的政治哲学的思辨,到微观层面的各种技术细节。每个研究领域都有特定的学科知识支撑,例如就其细致程度而言,政策工具研究远不如经济学家、技术专家对于特定问题的理解,全部纳入政策工具研究的视野不仅不可能也没太大必要。这就需要发挥政策工具研究特有的连接机制,即从中观层面上思考终极价值、政府理想和决策目标与经验事实之间的连接机制。
标准2:政策工具研究必须以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展开。按照政策科学创建者拉斯威尔的观点,政策科学具有问题导向的特征。公共政策学的目标在于发展一套理论体系,针对现实问题,把各种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有机连接,从而有利于作出科学的决策。作为政策学的分支领域,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政策工具研究也应与具体案例结合,在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不断发展。
标准3:政策工具研究的重要目标在于发展一套理论框架来有效地抓住政策现象的本质。按照胡塞尔对科学理论的思考,经验事实所拥有的信息往往是无穷尽的。科学研究并不需要传递关于研究对象的所有信息,而是需要以最有效的方式提炼信息。这一论断对于政策工具研究来说,更有其现实意义。作为应用性强的研究领域,政策工具对象处于高度变化中,发展出一套理论透镜去审视现实,提取有价值的政策信息方便学术交流、传播政策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2) 对三个学派的评价
从总体上看,技术论研究过于微观、发散,并且与其他研究领域重合,使其很难成为较为一般的理论。把这类以“工具”为名的研究统一界定为技术论可以使其区别于有一定理论特征的设计论和过程论学派,但实际上并不具有统一的规范性。从技术论研究的范围来看,多数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重合,其中一部分可归于经济学或环境科学的研究,另外一部分虽然可归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一般只是对某些具有突出特征的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很难与一般的公共政策研究相区分。就当前运用比较多的政策内容分析而言,对于总结政策中工具的一般特征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静态性和与实践的脱节性,可开拓的研究区间非常受限制。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政策工具研究中,技术论研究仍然会按照前文所描绘的方向拓扑发散。
从上文的政策工具设计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设计论注重基于理念从整体上对政策工具运用进行设计,这种研究角度在给人以整体感的同时,也加剧了政策工具研究的复杂性。以上特征,造成设计论的研究与经验分析有着距离感,除了少量经验分析外,多数都以理论推演为主。按照豪利特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后,设计论研究的衰落在于新公共管理及治理研究多中心假定对于设计论研究政府中心论假定的冲击[8]。但另外一个可能更为关键的原因是其理论的过于抽象化。设计论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挑战是如何与实践相连接。例如,梁鹤年提出能够较好地与实践结合的政策设计S-CAD法,即是在主观价值(S)分析的前提下,考虑政策工具使用过程的一致(C)、充要(A)和互赖(D),增加了政策工具设计理论的可应用性[15]。但从总体上来看,政策工具设计论与经验分析的脱节性仍然没有改变。
与技术论过于偏重事实与设计论过于偏重规范相比,过程论是事实—价值因素均衡、应用性强而且开放多元的政策工具研究学派,因而也是最有潜力的一个学派,具体而言,其比较优势如下文所述。
二、 政策工具过程论的比较优势
首先,与技术论仅注重事实因素不同,过程论注重事实与价值因素的平衡。从一开始,政策工具过程论研究者就在经验分析中发现,政策工具与一定的习惯、风俗、历史、文化及理念相连接,政策工具变迁体现着对特定价值的强调。学者们一般把政策工具划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工具,可以以这三类政策工具为例进行说明。对于强制性工具来说,从微观经济管制退出到社会管制加强本身就代表着对市场价值的认可;对于混合性工具来说,原来强制要求的职业资格认证,现在通过补贴培训机构、发布相关认证信息,本身就体现着在特定领域对政府与社会伙伴关系的重视;对于自愿性工具的更多使用,反映了在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政府在社区服务、慈善事业领域内对民主自治及社会能力的认同。
其次,与设计论难以用来进行经验分析不同,过程论更符合人们对政策现象的认知,也更符合我国的治理实践。设计论和过程论有着不同的认知论基础,设计论基于完全理性,对公共政策进行整体构设的思路;过程论则基于有限理性,充分考虑时间因素在认识事物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在不断试验、试探后找出合适的政策工具。后一种思路更加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发展的历程,强调对具体环境充分认知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变换政策工具,防止系统性风险。
最后,过程论与政策过程理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技术论和设计论共有的特点在于强调政策制定中理性与规范的运用,实际的政策现象却是复杂多变的,在把握政策现象时有其先天的不足;而理性和价值因素较为均衡的“过程启示法”则具有比较优势,这也是政策工具过程论优于技术论和设计论较为根本的原因。政策学理论的主要框架模型都是过程论的,这就使得政策过程论与政策工具过程论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实践中,这种结合研究包括政策工具研究与多源流议程设置的融合、政策工具与制度理论的融合、政策工具过程论与政策创新的融合等。
三、 政策工具过程论的逻辑基础
正如研究者对这一学派的命名,政策工具过程论即是认为,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一个过程。结合学者们的研究,可以从政策工具形成、运用及变迁三个角度对政策工具运行的一般过程进行描述。
首先,政策工具形成过程。政策工具是否常见及其所在环境是决定政策工具形成差异的主要因素,可以结合我国政策执行及治理转型背景描述政策工具形成较为一般的过程。对于一些不常被使用的政策工具而言,通常不会毫无征兆地直接进入决策,一般都要经历反复的论证和试验过程。对于我国的政策工具选择来讲,多数重要的政策工具选择都要经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地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就保证了对于政策工具及其所在环境的充分认识。政策工具的形成还受行政环境的影响,在合作共治背景下,管制和激励工具也表现出新的形态,例如把某些技术标准交给第三部门来制定,通过与第三方企业签订合同的形式提供公共物品等。
其次,政策工具运用过程。从文本上的政策工具到实际的政策工具施行往往有着比较远的距离,其具体落实受政策工具属性、政策网络等因素的多重影响。就其受政策工具属性影响而言,以全国性的管制政策为例,涉及的政策对象范围较广,在实行之前常常需要做好充分的信息沟通、标准制定及政策修改工作,特定的管制还要通过立法部门实现政策的合法化。就其受政策网络影响而言,以激励性工具运用为例,往往形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消费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网络,工具执行与网络有效性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最后,政策工具变迁过程。按照萨巴蒂尔的观点,政策变迁主要原因在于对外部因素的变化的政策学习,扮演不同角色行动主体的认识变化同样也构成了政策工具变迁的原因。在具体的政策过程中,政策子系统构成了以政策为导向进行学习的行为主体,具体而言可分为倡导者联盟、知识团体及政策工具拥护者,他们分别影响着对政策工具所在政治环境、所欲解决问题及政策工具本身的认识。政策工具拥护者更加注重对特定政府手段的捍卫,在实践过程中与倡导者联盟和知识团体及其他围绕政策而形成的团体有着互动博弈关系,最终使政策工具进入决策议程并投入使用。这些拥护者在政策工具的生命周期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某种政策工具失去支持时,就会很快失去生命力。
四、 政策工具过程论的分析框架
政策工具研究过程论的主要价值在于发展出对经验事实分析的框架。结合已有的工具过程论的经验和理论分析及政策工具过程论的逻辑过程,可以从政策工具议程设置、工具—制度变迁及政策工具创新三个维度总结目前政策工具过程论的主要分析框架。
1. 政策工具议程设置维度
结合政策循环、多源流、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已经得到了豪利特、贝兰德等学者的重视。多源流分析是政策过程理论最为成功的隐喻之一,已经有了比较多的经验应用,通过结合多源流议程设置模型去理解政策工具选择,能够增加政策工具研究的系统性。政策工具进入决策议程需要问题流(包含界定的问题)、政策流(包含政策工具)及政治流(包含政治信念)的汇合。政策子系统则包括倡导者联盟、知识团体及政策工具拥护团体,他们各自因为不同的理由推动着政策溪流的汇合。最终,由于问题溪流中的特定问题或政治溪流中政治家的推动下,政策之窗开启,特定政策工具被选择。这种结合研究典型范例在表1的政策子系统模型中体现最为明显[14]。

表1 影响政策工具进入议程的政策子系统
2. 工具—制度变迁维度
政策工具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被使用,并且在使用的过程中政策工具也创设了一定的制度,两者的互动形成特定的动态平衡结构。具体而言,工具—制度变迁维度的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把政策工具理解为因变量。先将制度理解为相对固定的,然后分析政策工具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变化,例如同样的政策工具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变化。另一方面把政策工具理解为自变量,通过分析政策工具选择变化的一般趋势来分析整体制度环境是否发生了变化。例如,通过环境政策工具选择的变化趋势来分析政府的管理方式是否发生着治理转变。
3. 政策工具创新维度
在政策创新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一个困惑就是政策创新、创新政策进入议程及创新政策执行存在的断裂关系[11]。从政策工具拥护者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创新研究。在政策工具运用的生命周期中,工具拥护者对政策工具的创新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包括在工具创制阶段拥护者内部及其与其他工具拥护者的互动关系,在进入决策议程的过程中与倡导者联盟和知识团体的互动关系,以及在政策实旋过程中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政策工具创新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政策工具创新过程
五、 结 语
综合上文分析,可以对政策工具研究的一般过程进行概括。起初,政策工具技术属性的分散性激发了政策科学研究者寻找政策工具研究的统一范式。静态的政策工具设计论和动态的政策工具过程论几乎同时出现。政策工具设计论与实践的脱节性使其在达到特定阶段后进展缓慢。研究者不断发现,过程论这一非线性逻辑的理论能更好地描述现实中的政策工具运用,各种具有启发性的模型推动了过程论走向成熟。政策工具过程论成为政策工具研究的核心范式有其自洽的逻辑,也在经验研究中得以验证。从政策工具的最近研究动态来看,政策工具的过程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处于不完善状态。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同样伴随着政策工具的调整变迁,例如,从广泛的微观经济管制到更多的社会管制,通过运用市场机制、志愿者组织等手段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创造力。对我国治理实践来说,设计或总结出符合我国政策工具运用过程的分析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就需要研究者一方面从理论上去完善,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案例研究对构设的政策工具过程理论进行验证。
[1] 莱斯特·萨拉蒙. 政府工具:新治理指南[M]. 肖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526.
[2] 盖伊·彼得斯,弗兰斯·冯尼斯潘. 公共政策工具:对公共管理工具的评价[M]. 顾建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3] Dunn W N. Methods of the Second Type: Coping with the Wilderness of Conventional Policy Analysis[J].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1988,7(4):720-737.
[4] McDonnell L M, Elmore R F. Getting the Job Done: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J]. 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1987,9(2):133-152.
[5] Ingram H,Schneider A. Improving Implementation Through Framing Smarter Statutes[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0,10(1):67-88.
[6] Schneider A I,Ingram H.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90,52(2):510-529.
[7] Hans T A B, Laurence J O. The Selec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s: A Network-base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8,18(3):213-239.
[8] Howlett M.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Policy Design: Design Thinking Beyond Markets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Policy Sciences, 2014,47(3):187-207.
[9] Howlett M. Governance Modes, Policy Regimes and Operational Plans: A Multi-level Nested Model of Policy Instrument Choice and Policy Design[J]. Policy Sciences, 2009,42(1):73-89.
[10] Pierre L, Patrick L G. Introduction: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Through Its Instruments: From the Nature of Instruments to the Sociology of Public Policy Instrumentation[J]. Governance, 2007,20(1):1-21.
[11] Voß J P, Simons A. Instrument Constituencies and the Supply Side of Policy Innovation: The Social Life of Emissions Trading[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14,23(5):735-754.
[12] Majone G. Choice Among Policy Instruments for Pollution Control[J]. Policy Analysis, 1976,2(4):589-613.
[13] Jordan A,Wurzel R K W,Zito A. The Rise of “New” Policy Instrument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s Governance Eclipsed Government?[J]. Political Studies, 2005,53:477-496.
[14] Béland D,Howlett M. How Solutions Chase Problems: Instrument Constituencies in the Policy Process[J]. Governance, 2016,29(3):393-409.
[15] 梁鹤年. 政策规划与评估方法[M]. 丁进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16-17.
(责任编辑: 付示威)
Process Perspective of Policy Instrument Research: Advantage, Logic and Framework
GUO Sui-lei, WEI Shu-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China)
In the three schools of technical theory, design theory and process theory formed during the research of policy instruments, the technical school is too microscopic, diverging, and overlapping with other areas of research, and the design school tends to be abstract and complex, departing from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mong the three schools, the process theory is the most balanced perspective, which combines facts and norms and has a high degree of fit with the policy process theory. The understanding of policy instrument formation, application and change constitutes the log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policy instruments. Based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policy instrument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together with the logic basis of the policy instrument process, three main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the process theory should be summed up in terms of policy instrument agenda, instrument-institution change and policy instrument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omotion of policy instrument research.
policy instrument; instrument design; instrument process; instrument constituencies; instrument innovation
10.15936/j.cnki.1008-3758.2017.03.008
2016-08-27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15AGL017)。
郭随磊(1987- ),男,河南遂平人,东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策工具、政策执行研究; 魏淑艳(1965- ),女(满族),辽宁北镇人,东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政府应急管理研究。
D 60
A
1008-3758(2017)03-027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