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收信人的城
2017-05-18马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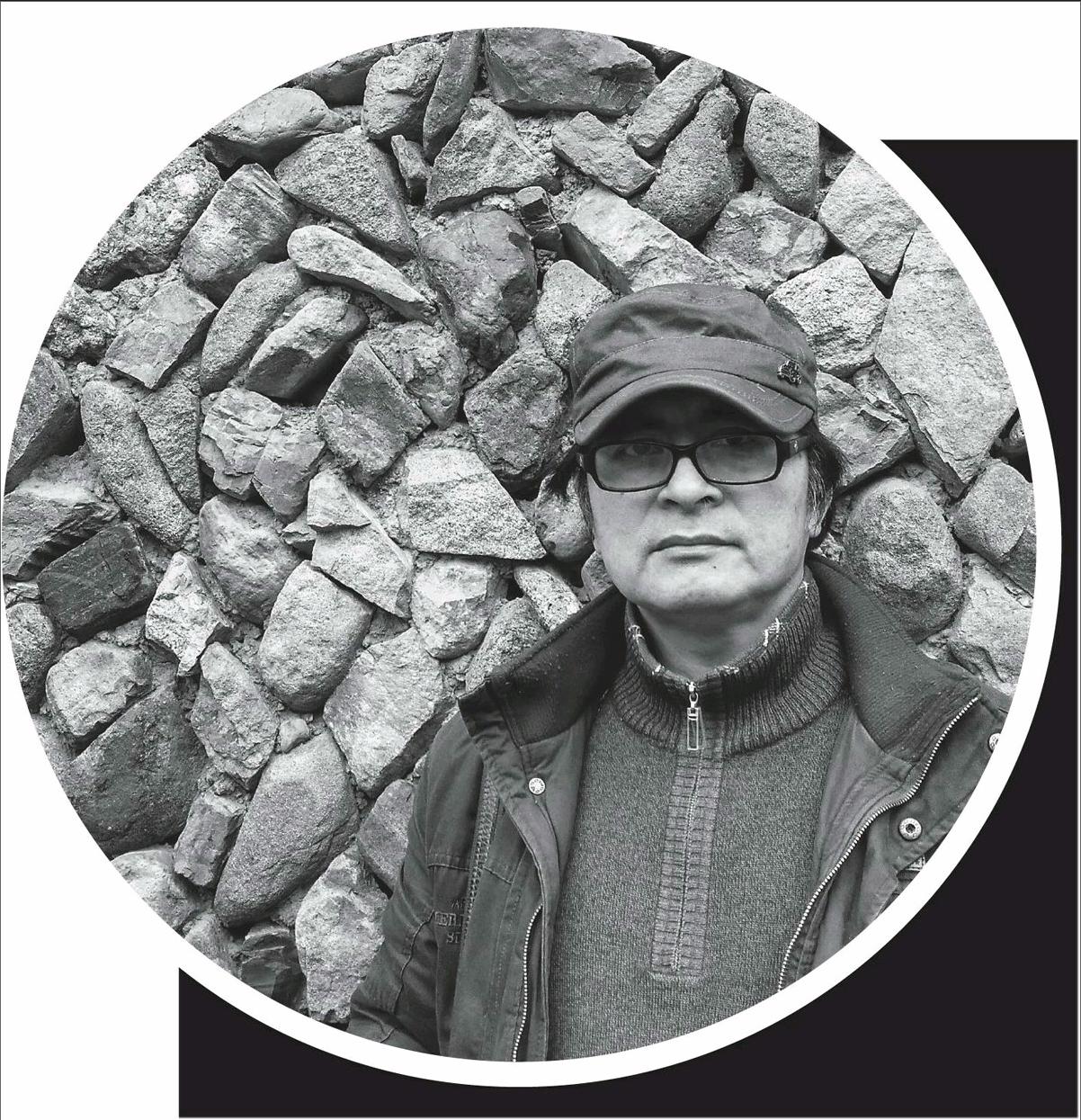
马叙,1959年生,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过十月文学奖。有作品发于《人民文学》《十月》《当代》《天涯》《作家》等刊物,并入选国内多种选本。出版有诗集《浮世集》《倾斜》,小说集《别人的生活》《伪生活书》《他的生活有点小小的变化》,散文集《时光词语》《在雷声中停顿》和水墨图文集《装一朵云玩玩怎么样》。现居浙江乐清。
1
去慈城。慈城在宁波的江北区,西北角。
这一天,我在文学活动的人潮中退场。所有熟人的脸孔,熟悉的话语,熟悉的场景,都退去了,隐去了。持续的十多天的雨,突然收住,放晴,犹如一封未写完的长信遭到粗暴中止,投递。这么长的雨天,周作人可以陆陆续续地写一部书,普鲁斯特可以写满几章布满绵密细节的文字。也足以使一个原本粗心的人有了新的耐心去谈情说爱,取悦情人。而天气的突然骤变,刺眼的阳光猛烈倾泻,一如被突然中止的长信的书写。如果有写信人,而写信人的忧伤也会因此被转为了愁绪与苦恼。在这一天,我像是一个蓝衣邮差,邮包里塞着这封被强行中止的才写到三分之二的长信,独自启程去往慈城。这一天,仿佛被这样用于跑腿,及寻找投递的邮址。如果不是因这次到宁波,我可能从来不会去慈城,过去没有去,今后也不会去。尽管我到过许多次宁波,到过东钱湖、月湖、开明街、老外滩,但是那么多次我从没去过慈城。在这之前,慈城于我,像一位陌生又陌生的远处的人,在某处,而从不知,亦从不遇。
一天之前,在大雨中,想到慈城这个名字,我竟然会想到狂风暴雨,狂风暴雨中的倾倒的行道树,之后是一座干净得像明镜一样的一座城。我知道,我的想象不着边际,它与慈城毫不相关,它事实上是一座安静的古城,与俗世距离很近,应该在某一巷弄里吃着牛肉面时去想象它,在某一茶座的下午时光里去想象它。这样它会在想象中更接近事实的城镇呈现在头脑之中。比如,那些对落叶的想象过于浪漫,狂风的想象也似乎不着边际,而想象中的行走于古城中的邮差也太过于像旧时代的人物。
去慈城,几乎没有什么过程。宁波口音司机开的出租车,有着邮差一样的墨绿的颜色,50元,慈城。
2
“马上就到慈城了。”
“慈城很小。”
“直接到縣衙,还是这里下车?”
“不,就这里下车。”
晴朗天气里的声音是响亮而短促的。南城沿路,解放路,十字路口。选择热闹杂乱的解放路进入。解放路,搜狗五笔输入法中的一个词组,在解放这个词的后缀组合中,它的使用频率高到排名第三。这个路名,极大地消解了慈城的地域性。这是一个使人熟悉到麻木而且生厌的路名。十一月初的慈城,在解放路上呈现着它的有关一座城的最基本的生活与商业元素。手机店。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小米专卖。苹果专卖。手机大卖场。一条二百米的街道,有着十多家手机店。即使是一座小座,它也及快速地与这个时代同步。全民智能手机。全城智能手机。随手拍。微信。公众号。点赞。评论。转发。拉黑。屏蔽。这一系列名词组成了这个时代的重要即时方式。也许在下一刻这些又已经成为过去。这一切,同样把生活方式迅速地改变着,变得当下而即时,变得只有现在没有过去。这条街道上的店铺,其次是家用橱柜,卫浴设施,建材电器,数家宾馆,几家家庭旅舍。此时,解放路的慈城,是一个即时的、现场的慈城。现实主义,俗世生活,家庭冷暖与烦恼,匆匆而行的生意人,无所事事的中年人,许多人都那么地面目模糊。老年人蹒跚行走,走很久,背影才慢慢地消失……少年从巷口冲出,跑三十来米,旋即跑进另一个巷口,迅即消失。我在许多城镇中看到,少年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干净,同样的,慈城的少年也不多,闪讨的少数少年.是这条街道里最干净也最明净的所在。此时,又一个少年从我身后跑来,跑向我的正前方,他背着红色书包,这红比其他的红要鲜艳明亮,这鲜艳明亮都是因背在这少年的身上的缘故。杂乱的街道,慵懒的中年人,旁边的一家又一家的店铺,因这团燃烧的红色的划过,而现出了一时的动静,我侧过身看到一个中年女人看少年远去的眼神,这时她的眼神动人明亮,这年纪的中年女人即使看情人时的眼神也没有看少年时的眼神明亮。
3
太阳殿路是从解放路上横接出去的一条支路。它是慈城古城区前面的第一条路。与孔庙比邻。孔庙,一座文庙,它掌控着慈城文脉与慈城的大部分历史,在慈城,凡家有文房四宝或族氏中出有文人名人者,都会说起这座庙。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侵,孔庙遭焚毁,淳熙四年(1177)重建修复。孔庙边上的中城小学的老师教着学生,少年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诵读课文,把尾音拉长,学着深奥的奥林匹克数学。这里的近千名学生,他们出入于孔庙旁边,成群的学生身影快速从孔庙高高的紫红色围墙下跑过。有时,他们会在晴空下停留(低年级的学生一放学就被他们的父母强行接走,然后做着无限的复杂的作业,高年级的学生则有着相对的自由),大胆地评论老师,互相说着对家长的怨气。而孔庙的存在,使得慈城中城小学学生们的家教更加严厉,家长们对儿女的学业与成长寄予更大的希望。在行政或事业单位上班的学生家长,他们会经常地想到孔庙,在孔庙数个匾额中想到最多的是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御书的“斯文在兹”额。这一切都因他们与孔庙靠得太近了。而此时的太阳殿路,出奇地安静,也许学生们正在上课,还未到放学时间。这条路是自东向西的单行线,但几乎没有一辆车开过。电动自行车修理铺,靠近路口,门楣上挂满着大锁与轮胎。店面纵深处幽暗宁静,没有待修的车辆,也没有买配件的人。店主在门口百无聊赖,胖,慵懒,迷离,他的内心存放有店铺纵深的每一种配件数与规格型号,以及一些已经开始生锈的铁件。他只要转身,弯腰,伸手,就能摸到大尺寸的铁扳手,螺丝刀,以及电动工具。孔庙与他毫无关系,他小学毕业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但他几乎没有想到过爱新觉罗·载湉题的那块“斯文在兹”匾。整整一下午,他没有一个上门修理电动车或买配件的顾客,我来时他这样站着,几小时后,我再次经过这里时,他还是这样站着。曾经在这里修理过或买过配件的人,星散在慈城的各个角落,做着日复一日的单调的活计(许多人远没有配件店主这么自在悠闲)。离这配件店不远处,是一个中医诊所。大大的玻璃推门上贴着大大的红色字:“中医,针灸”,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针灸为特色的中医诊所。太阳殿路不宽,就一巷子的规模,中医诊所位于这段路的中间位置。大门紧闭的诊所内弥漫着艾灸点燃的味道,它似乎是慈城另一种灵异的味道,穿白大褂的中医师穿行其间,声音低沉,与艾味浑然一体。中医神奇的无中生有的疗法,三焦,脉象,舌苔,寒热,穴位,诊所比大医院更有效,诊所宁静、幽暗,中医师声音低沉,手腕柔软,长针闪亮细长,艾灸香烟缭绕。我想象着一个中年病体,在其间,因了诊所的空间而安静,病体在洁白的床上,松弛的肉体的边际下坠,它的某一些穴位接受着细长的银针插入,旋转,酸麻的感觉弥漫开来,再辅以艾灸。在这狭小的诊所内,中医古老的气息与慈城的旧时光慢慢地融成一体。
慈城的其他地方还有小学(慈城中心小学),还有电动自行车修理铺,还有卫生院所(离这不远的孔庙边的慈城镇医院,以及距离相对远了一些的宁波第二医院保黎院区、慈中牙医、吴华祥内科诊所、唐杏娟妇科、国庆村卫生室、上岙村社区卫生站……)。但是太阳殿路是整个慈城的最核心处,它把握着慈城作为古城的这一角的最根本的气息。
4
再往纵深走,太湖路在转弯处对接太阳殿路。太湖路空前的干净。民权路,尚志路,太阳殿路,太湖路。四条路构成古城的四方横“中”字格局。我走在太湖路上,沒遇见过一个慈城的居民。我走在尚志路上,没遇见一个居民。在太阳殿路东段,我也没遇见过一个慈城居民。一小时之后,在太阳殿路与太湖路的十字路口,遇见一位六十多岁的戴眼镜的慈城人。
我问:“为什么整条太阳殿路的北边的每堵一墙上都写着一个‘拆字?”
“拆了是为了建新墙。”
“为什么?”
“建新墙是为了建新的古城。”
“居民呢?”
“迁走了。”
回答完了话,他慢慢地远去,背影落寞,孤单。
居民迁走了。这座呈横“中”字的城池剩下一个空壳。这事在微信上得到了证实,赵柏田在留言中说,原住民都迁走了。柏田后来又加了一句,去年与郑亚洪来慈城时好像还没有这么空荡。此时,一条路,尚志路仅我一人在走着。我坐在位于金家井巷的布政房前的石头台阶上。背后及面前是一座完全空了的城池。原住民全迁走了,他们被分布到慈城的各个角落或集中在某一小区的商品房里。他们几十年的生活痕迹不再。我想象着今后重新开放的古城成为新的旅游景区,摆着满目的旅游纪念品,把空城打造成博物馆式的处所。当那些迁走的原住民重新从这条路上走过时,他们再也找不到自己曾经生活过、恋爱过、吵闹过的地方了,这地方还在,但已经不是曾经的生活过的地方了,他们过往的痕迹彻底不存在了。他们可触的记忆与生活只存在于如今的小区里,高层建筑,电梯,直上直下,一幢矗立的楼房同住着几十房人家。也许有一部分人会回迁,而回迁的原住民将是作为这里经营旅游纪念品的小商贩,而不是一个散漫的冬日放松晒太阳的生活者。这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他们原先所生活的区域成了博物馆,将被附上说明书,接受一批又一批无关的陌生人的观看。
5
太湖路。在“润”咖啡馆。我一人坐下,无所事事。我置身在这座空城之中,犹如一个投递完了所有邮件的邮差。其中那封未写完的雨天长信,被投进了这座空城。阳光倾泻下来,而这里没有收信人。这座空城的所有地址、门牌号,似乎都不真切,都是虚幻的,真实的号牌后面,没有向外看的目光,没有人来打开眼前的门户,整座城都没有收信人。咖啡馆前的几个人,都不是本城人,也不是慈城人。我起身,逆向行走。太湖路,空无一人。东城沿路,空无一人。竺巷东路,空无一人。叶家弄,空无一人。袁家巷,空无一人。一直行走到东镇桥街最西头,才看到几家店铺。它们接续了慈城人的世俗生活。也重现了收信人的真实状况。如果一个真实的邮差到来,他应该很容易就能找到温和的收信人,而不是一个空邮址。并且还会捎走一封短短的回信。这个时代也正如一座没有收信人的空城,再也没有人写信,再也没有人收信,文字的体温正在迅速地流失,没有墨水,没有歪斜的、颤抖的笔迹,没有信封,没有方格稿纸,没有划着清淡红线的信笺。在保黎北路,一家特色牛味面馆里的一碗大牛骨面终止了这次的慈城之行。双手抓着牛筒骨,加进一勺辣椒,吃得满头大汗,十八元,付清,走人。才想起,那封雨天的未完成的虚拟长信,根本就不可能有收信人,它可能再次被我带了回来……
2015/11/21于乐清
责任编辑 周明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