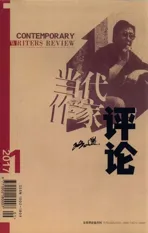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标本
——王蒙作品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2017-05-15薛红云
薛红云

——王蒙作品的海外传播与研究
薛红云
王蒙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集作家、知识分子、官员等多重身份于一身,著述涉猎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红楼梦》研究等多方面,又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政治和文化风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面镜子,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学、文化包括政治的一个绝佳的标本。由于王蒙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身份,他的很多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很多学者在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身份”、“场域”等角度对王蒙的作品进行文化研究,拓宽了王蒙研究的视野,弥补了国内研究的某些问题和不足。
近年来,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发展迅速并产生了一批成果。相比于莫言、余华等作家,相比于王蒙自身丰沛的创作,王蒙作品的海外传播及研究都有些单薄。本文拟通过考察王蒙作品的翻译和传播状况、特别是海外的研究状况,探讨影响王蒙作品传播的因素,借助“他者”的眼光发现王蒙创作的独特价值,同时对照国内的研究,在凸显国内外研究方法等的不同的基础上,力图呈现一个立体、多维的王蒙研究。
一、王蒙小说的海外译介情况
在当代作家中,王蒙的作品是较早翻译到海外的。据王蒙说,捷克共和国在1959年就翻译了他的《冬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外大规模的译介王蒙作品主要始于1980年代。下面笔者将王蒙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和出版情况按照语种进行了梳理,以期相对清晰地呈现其海外传播的状貌与态势。
英语:《蝴蝶及其他》(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北京外文出版社,1983年,《王蒙作品选(2卷)》(Selected Works of Wang Meng 2 vols),北京外文,1989年;《雪球》(Snowball,译者Cathy Silber、Deidre Huang),北京外文,1989年。《布礼》(A Bolshevik Salute: A Modernist Chinese Novel,译者Wendy Larson),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新疆下放故事》(Tales from the Xinjiang exile),纽约Bogos&Rosenberg出版社,1991年;《坚硬的稀粥及其他》(The Stubborn Porridge and Other Stories,译者朱虹),George Braziller出版社,1994年;《异化》(Alienation,译者Nancy Lin、Tong Qi Lin),香港联合出版,1993年。
法语:《蝴蝶》(Le papillon),北京外文出版,1982年。《布礼》(Le Salut bolchevique,译者 Chen-Andro),巴黎Messidor出版,1989年。《新疆下放故事》(Contes de l’Ouest lointain : 〔nouvelles du Xinjiang),《淡灰色的眼珠》(Des yeux gris clair)、《智者的笑容》(Les sourires du sage)《跳舞》(Celle qui dansait,译者Franc oise Naour)分别于2002、2002、2003、2004由巴黎Bleu de Chine出版,其中《跳舞》2005年又版一次。
德语:《蝴蝶》,北京外文出版,1987年;《蝴蝶》,柏林建设出版社,1988年;《夜的眼》,瑞士第三世界对话出版社,1987年;《说客盈门及其他》(Lauter Fu rsprecher und andere Geschichten,译者InseCornelssen),波鸿Brockmeyer出版,1990年;《活动变人形》,罗曼·瓦尔特库特出版社,1994年。
意大利语:《西藏的遐思》,米兰赛维德书局出版,1987年;《活动变人形》(译者康薇玛),米兰加尔赞蒂书局,1989年;《不如酸辣汤及其他》,拉孔蒂马尔西利奥出版,1998年;《坚硬的稀粥》,卡福斯卡里纳出版,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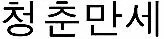
日语:《蝴蝶》,大阪三铃书房出版,1981年;《淡灰色的眼珠》(淡い灰色の瞳,译者Hiroshi Ichikawa; Eiji Makita),德間書店,1987年;《活动变人形》(译者林芳),东京白帝社,1992年。

匈牙利语:《说客盈门》,欧洲出版社,1984年。
罗马尼亚语:《深的湖》,书籍出版社,1984年。
西班牙语:《王蒙短篇小说集》Cuentos,墨西哥学院出版社,1985年。
俄语:《王蒙选集》(Izbrannoe : 〔sbornik〕,译者华克生),MoskvaRaduga出版社,1988年。

由以上统计可见,王蒙作品的译介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语种很丰富,英、法、德及西班牙语这几种国际通用的语言都有了,连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越南语等应用范围相对狭窄的小语种也有译介,这使得王蒙作品传播的空间范围很广,可以说遍及欧亚美三大洲;其次是在海外传播中经历了一个从“送出去”到“迎出去”的过程:在1980年代前期,主要是我国的北京外文出版社主动向海外特别是欧美推介王蒙的作品,到了1980年代后期及以后,主要是国外出版社主动翻译传播王蒙作品;第三是译介面相对狭窄,主要集中于王蒙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1980年前后的《蝴蝶》《布礼》等一批作品和1980年代末的事件性作品《坚硬的稀粥》上,长篇小说只有《活动变人形》被译介,早年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1990年代之后的“季节”系列等长篇目前尚未见有译介。
王蒙作品传播相对单薄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大众文化的冲击、部分知识分子对王蒙文化立场的不认同等等,但主要的原因一方面跟作家和批评家的代际更替有关:1990年代后,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及“五○后”、“六○后”后批评家渐渐登上历史舞台,右派作家及其一代批评家渐渐淡出,在国内受到的学术关注较少,必然影响其海外的传播,另一方面跟王蒙在1990年代后在创作上转入“语言的狂欢”有关,他汪洋恣肆、旁逸斜出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播和接受的难度,也正因此,国外对王蒙的研究(因笔者语言能力所限,此处主要指英语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蝴蝶》等作品和《坚硬的稀粥》上。
笔者发现,在王蒙的海外研究方面,存在着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路向,而且这两方面的研究在时间顺序上基本上是文学研究在前,文化研究偏后。再有,《蝴蝶》等作品国外较多从文学史意义、主题、叙述声音等角度入手进行文化研究,而《坚硬的稀粥》本身的事件性使得国际研究很难只关注小说而不关心其背景,所以更偏重文化研究。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王蒙的早期作品也有很多被纳入思想史等文化研究的框架的。下面笔者拟通过梳理国外对王蒙不同时期作品的研究来看海外研究的特点,并与国内研究进行比较和对照,以对王蒙研究形成一个整体的观照。
二、“意识流”阶段的海外研究
王蒙在1980年代前后发表的小说是译介最多的,也是引起西方研究最多的。《夜的眼》等小说在国内发表后,因为“意识流”的西方色彩和现代主义的特点,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因而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国内的批评也主要是围绕着“意识流”这种手法以及与现实的关系展开。很多人肯定这种手法的同时又努力撇清与西方的关系,如陈骏涛认为王蒙的探索“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探索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但王蒙的小说并不是西方“意识流”的简单移植,因为西方的意识流没有故事情节,人物的意识流动是“下意识”的或者是琐碎的、荒诞的、颓废的意识活动,而王蒙的小说是讲究故事情节的、不描写下意识的。有的批评家则认为虽然王蒙“非常善于描摹人的意识状态”,但这只是王蒙创作的“外观”,他的小说是“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上”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批评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最高的甚至唯一的准则,但在当时,这是对王蒙的创作的很大肯定甚至保护。陈晓明多年以后也从“意识流”与现实的关系进行阐释,他的阐释可能更深刻、更具有穿透力:他认为王蒙的“书写始终与现实构成一种深刻的紧张关系”,“王蒙运用意识流手法,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形式变革的需要,而是出于表现他意识到的复杂的内容,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难以直接表达的那些意义,他采取人物心理活动的方式,把那种复杂性呈现出来”,他是在运用艺术形式掩盖他的思想质疑,或者说“形式本身也就是内容”,那种恍恍惚惚的心理表明了劫后余生的人们“对现实的犹疑”。
海外对于王蒙这个时期的创作大多给予高度评价,如郑树森把这些作品放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来看其意义,说“《海的梦》和之前讨论的两篇小说(指《夜的眼》《春之声》),总体来说,明确标志着一种新方向——不仅是王蒙的,也是中国小说的。这三篇小说不再强调情节的重要性,而是聚焦内在生命,显示了一种前所未有从模仿到心理的变化,这种变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小说史上无疑是很先锋的”,但他也指出“尽管这些技术创新可以说是现代主义的,但是王蒙一贯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致的光明的乐观主义的来结束他的小说”。这一点和李欧梵等人的看法很相似。
菲利普·威廉姆斯( Philip Williams)对王蒙这个时期的作品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并归纳出其共同特征。他把王蒙的作品主要分为三类:“历史的反思、心理上的自我发现和讽刺类作品”。历史反思类作品包括《悠悠寸草心》《布礼》《蝴蝶》,心理上的自我发现类作品包括《海的梦》《夜的眼》。讽刺类作品包括《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轶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发现“几乎每一类都出现了四种共同特征:强调主人公对社会环境的情感和心理反应多过强调对环境本身的反应;采用了非历时手法例如闪回和非直接的(第三人称)内心独白的叙述结构;单人视点;从某种意义上的创伤中解脱出来的、以乐观结尾为标志的喜剧模式。”他高度评价王蒙的创作,认为“现代中国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持续的提升或许更加依靠像王蒙这样的文体家的著作”。
以上郑树森和菲利普·威廉姆斯等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文学的内部研究,他们的结论和国内对于王蒙研究的一些定论是相通的,或者说是相同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超越国内的研究。
在文化研究视野的观照下,国外对王蒙作品的研究呈现出很多新意。如马丁·赫尔马特(Martin Helmut)对《相见时难》的解读,他从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外国主题切入研究,同时运用性别、身份等文化研究的角度,超越了纯粹主题研究的局限性。他认为小说对蓝佩玉和翁式含关系的描写有很深的含义:“不同文化和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国人的交锋反映了中国与西方的交锋”,“它让人看到重新定义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问题,向我们呈现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外开放政策所描绘的复兴蓝图中的心理定位”。在把王蒙小说与冯骥才的小说进行比较时发现他们都采取了“简单的选择:弱者遇见强者!绝望孤独的女性与强壮自信的爱国者(男性:笔者加)的对比”。虽然作者没有涉及“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但王蒙的这篇小说恰恰属于“第三世界文学”,是“民族寓言”的绝好注脚,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男性遭遇第一世界国家时的下意识反应:把对方女性化,特别是把对方描写为单身不幸的女性。当时李子云认为王蒙没有“能够把握住、揭示出她(指蓝佩玉)的充满矛盾很不一般的心理状态”,可以说只是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其实质。曾镇南看到小说中翁式含“保持着一个对蓝佩玉稍稍俯视的角度”,“对蓝佩玉与西方文化的内在的、现实的联系描绘不够,这是被他当时确定了的小说主题的取值方向决定的”,因为作者要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内聚力”。用“第三世界文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看,曾镇南仍然没有揭示王蒙小说中存在的这些不足的真正原因。
波拉·埃文(Paola Iovene)则把《相见时难》放在文化认同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她认为王蒙引用李商隐诗歌有深刻的用意,因为李商隐诗歌的互文性“在中国诗歌传统和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之间建立了密切关系和连续性”,不仅如此,李商隐诗歌还与文化认同有关:“按照叙述功能,李商隐的诗歌在主人公之间重建模糊的联系,为正在寻求从多年的政治暴力中康复的国家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凝聚的可能元素”。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身份认同之间有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建立了文化认同才有可能形成国家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波拉与曾镇南认为小说要表达的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与内聚力”是异曲同工的。
知识分子的身份问题更是西方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拉森·温迪(Larson Wendy)通过阅读王蒙的《布礼》来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对《布礼》进行细致的文本解读后,他发现王蒙尽管“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维持着道德立场”,但他还是用现代派的技巧和结构挑战了当代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扬知识分子也能是革命的,而王蒙则断言,“从1949年到1979年间中国所定义的‘革命’和‘知识分子’的术语,是不相容的、自相矛盾的”:“惟一确定‘革命’身份的方法对知识分子来说是难以达到的——因为身体力行地积极参加革命不再可能,而即使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他或者她的作为知识分子‘真正的本性’被看做经常潜伏在表面之下。因此,在《布礼》中,现代派的结构和技巧同时作用,创造了一种异化的、不完整的知识分子身份。”
在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也从“身份”入手研究王蒙的作品,他探讨的是王蒙的官员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作品的影响。他对《悠悠寸草心》的研究可谓新颖:既探讨小说的叙述声音,又把中国当时的漫画引入研究。他认为小说发表的时间——1979年9月,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小说写出了“重放的鲜花”这一代“右派”作家在复出之后,在两头作战——外部要面对领导和读者对于文学的不信任、内部在邓小平提出“向前看”后要对自身经验的重新调整——的情况下重建信任的努力,表现出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他认为王蒙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用一个老老实实、技术熟练的理发师作为叙述者,是试图由此建立作品的可信性。作者联系当时的漫画,证明理发师的工作有象征含义,因为“剃剃头”是“让人接受严厉批评的一个常见的隐喻”,而理发师/批评家和顾客/干部之间有“轻微的隐喻关系”。王蒙在50年代中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就对官僚主义持一个温和的立场,在《悠悠寸草心》中同样认为“顾客”是愿意“理发”和“整容”的。因而,作者认为“文本中的理发师和领导以及他的同代人,更不用说他的诚实可靠的意图,可信性都很低”,“无论文本还是情节都与政治家王蒙附加上的物质相疏离”,这表现出“一个技巧熟练的文学工匠和一个试图用某种必要性说服自己和他人的政治家之间的紧张”。
国内对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除了早期的争论之外,较多仍在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之内,而海外研究者们并未特别关注“意识流”这种手法本身——除了台湾去美、相对更了解中国文化生态的郑树森等人外,他们在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尤其关注小说人物的身份以及作家的身份,更多进行文化研究,把作品当作了解中国文学、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及心态的标本。这种研究确实视野开阔,让人耳目一新,但由于王蒙的特殊身份,也由于国外研究者总不免有窥秘的心态,有时也不免把标本当作真实去考证而做出政治性解读,如鲁道夫·瓦格纳(Rudolph Wagner)认为《悠悠寸草心》中的“唐久远”与邓小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等,就显得牵强。
三、“稀粥风波”的海外研究
“稀粥风波”出现后,港台及西方的媒体给予了很大关注,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很多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很有些窥秘、揭秘的性质,而很少关注《坚硬的稀粥》小说本身的美学价值。特别是有“中国通”之称的汉学家白杰明(Barme Geremie),把“稀粥风波”描述为王蒙和他的同仁对保守派的斗争,“从始至终不过是派系内斗的一个例子”,“尽管它可能对研究当代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学生来说是迷人的,但它跟今天大众文化这一主要领域的革新没有任何关系”。
凯泽(Keyser Anne Sytske)对《坚硬的稀粥》评价并不太高,认为小说是“一个讽刺性的寓言”,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特定的群体和几代人以及他们对改革态度的拙劣模仿”。但是旁观者清,他发现双方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写作并出版一个批评当代中国社会和改革的短篇小说是否是合法的”,而从来没有人提出文本自足性的问题:“有一点很显著,那就是所有的批评都认为王蒙就是故事中的‘我’,假设叙事者表达的观点就是王蒙自己的观点,没有人提出文本的自足性的论据。”文学与生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问题被忽略了。而中国的研究者似乎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以上两位研究者发表文章的时间(均为1992年)比较接近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他们还不能跳出争论有更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时间的沉淀,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对于《坚硬的稀粥》有了更新颖独到的发现。
关注中国新启蒙运动的闵琳(Min Lin),把文学研究和思想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他深入到《坚硬的稀粥》的文本内部进行分析,认为小说“表面简单实际复杂”,“与其说小说是对中国政治场景中某些党派和个人攻击和批评,不如说它是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深层矛盾和问题的揭示”,而这些矛盾和问题从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时就已经存在了。他认为小说是新启蒙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因为王蒙在描绘传统家长制的许多特性时,“突出了家庭结构的超稳定性和旧秩序的异常顽固性”,“在许多方面呼应了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著作”,小说“可以看做是对某些浪漫天真的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保守派的批评,而王蒙因此可以稳稳地置身于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的主流中”。从小说结论可以看出,作者是通过文本细读来探讨王蒙这一身份复杂的作家与新启蒙运动的关系,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史。
与闵琳把《坚硬的稀粥》纳入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不同,沙克哈·瑞哈夫(Shakhar Rahav)把“稀粥风波”纳入到布尔迪厄“场域”的框架内,虽然他也关注事件多于关注文本,但由于视角的不同,他的研究呈现出一些很新颖的东西。
沙克哈·瑞哈夫(Shakhar Rahav)认为“稀粥风波”正好发生在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间的过渡期。他的文章“试图阐明在这个过渡期形塑中国文化政治的各种力量”。他认为“稀粥事件”“标志着建国后政党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暧昧的合作关系的一种变化”:“在整个80年代,政党国家和知识分子大都在‘改革开放’的共识下合作”,但1989年王蒙离开政府职位则标志着知识分子和国家的联盟破裂,“1992年重新确认的改革可能提高了个人自由,但是它也使知识分子和国家更加分离,因为改革是由市场经济的逻辑驱动的”。作者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利用“场域”理论分析“稀粥事件”,认为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使王蒙获得巨大声誉,而这无形的象征资本“使他成为政党国家的文化部长,也使他在疏远国家并抨击它时有了可能性”。王蒙胜出的过程“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文化领域的迅速变化和国家文化机构可选择性的增加,责难王蒙的企图反而增加了他的象征资本”。所以,对王蒙的攻击反而进一步削弱了保守派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
不仅如此,此文还指出了之前研究存在的不足:“许多关于这个事件的研究运用了一种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的二元框架:西方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经常把知识分子定义为不同政见者,并且把他们理想化为体现了自由民主理想的勇敢的个人。”由此可见,这篇文章反映出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事件研究的视野的开阔,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也跳出了揭秘、窥秘式的研究,更为客观公允,也更为深入了。
相对于海外研究的热烈,国内对于《坚硬的稀粥》的研究很是冷落,这一篇有国际影响的小说在批评界既没有批评大家的研究,也没有特别有分量的文章,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如张志平在一篇研究文坛影射事件时,指出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问题,指出了“稀粥风波”的盲区。在这篇作品的研读上,相对于西方研究的方法多样,国内的研究显得相对不足。
结 语
从以上研究可见,海外对于王蒙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出方法多样、视野开阔的特点,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对“身份”、“认同”、“场域”等的特殊关注,使得王蒙作品有更多的解读的可能性,这也启发国内的研究者可以尝试用文化研究的方法重新审视王蒙的作品;另一方面却显出很多不足,如某些研究过于关注作品内容,甚至过度阐释文本,将其作品当作研究中国文学、文化以至政治的标本,而对形成这个标本的“意识流”手法、对王蒙作品的语言、风格、文体意识等等的研究,与国内比起来却十分缺乏。这当然有各有所长的原因:文化研究本来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而王蒙汪洋恣肆、原汁原味的语言可能更适合中国的研究者。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视域方面的不足: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80年代的中短篇小说,而对同样译介较多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却无人关注。而对王蒙1990年代之后的作品如“季节”系列和《青狐》等,无论是译介还是研究方面都还是空白。再有,就是整体上的量的不足,笔者几乎查阅了所有研究王蒙的英语资料,而其数量只有30篇左右,这对于王蒙这样一位创作丰盛,身份与思想复杂,在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来说,未免太少了。
其实,不仅仅国外对于王蒙的研究相对不足,国内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自1990年代以来,王蒙的作品似乎就淡出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王蒙的思想立场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还是他的创作已经不合时宜?是市场经济中大众文化的冲击,还是批评家的更新换代、兴趣转移?还是这些原因兼而有之?一直关注王蒙研究的朱寿桐认为:国内的王蒙研究“尚处于较为薄弱的环节,即是说,与王蒙的文学贡献、文化贡献乃至社会贡献相比,严格的学术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这固然与一定的意识形态因素的疑虑及其约束有关,但毕竟是汉语新文学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疏失”。笔者认为,或许正是国内研究的不足,才导致了海外重视不够,这就要求国内学界扎扎实实做好王蒙的学术研究,以弥补这一“重要疏失”。
〔本文为国家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批准号:12AZD086)、国家课题“当代小说海外传播的地理特征与策略效果研究”(批准号:15BZW16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桂玲)
薛红云,文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