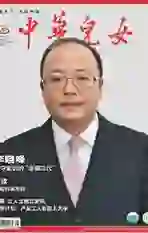舒乙 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
2017-05-12吴志菲
吴志菲
老舍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
舒乙,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画家、老舍研究专家,北京胡同和四合院的坚定保护者。
在舒乙眼里,“夹着尾巴做人”其实是一种尊严,不看他人脸色就是给自己“面子”。淡泊名利的舒乙从不张扬自己是谁的儿子,也从不对外打老舍这张牌,而是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赢得尊严。
“折腰”与不看他人脸色
一年,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考察,发现专门开辟有手稿研究阅览室。于是,他联想到自己工作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我们收藏了数以万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手稿,却基本无人利用。因为没有手稿学”。为此,他呼吁建立手稿学。
要建立手稿学,舒乙首先想到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国外的手稿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可以翻译一些他们的研究成果,看看他们的学科体系,看看他们的研究方法,看看他们的具体结论。试想,有时一本对某一部名著的手稿研究专著,竟会比那部作品本身还厚,那是何等精深的学问啊。手稿学既研究作品的形成过程、修改过程,试图解释作家的主观追求,又阐述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舒乙说,手稿学的研究成果,常带有惊人的震撼力,往往连作者本人都迫不及待地要读。因为作者主观意图和研究者客观分析是不相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但因为言之有理,是对大家都有启迪的。
据悉,舒乙曾和姐妹一起将老舍《四世同堂》的原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很快被定为国家的档案遗产。“当时后方没有钢笔水,用毛笔,老舍先生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他的字写得又工整又漂亮,因为写得慢,所以就像抄稿一样漂亮,他自己也很喜欢。《四世同堂》手稿特别长,摞起来也有一尺多高,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他自己也认为是很漂亮的东西。我们兄妹商量,认为这是民族的遗产,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应该保存在环境更好的地方,就捐了出去。”
鲁迅先生说过这样的话:想知道该怎么写,要读名著;想知道不该怎么写,要念手稿。舒乙认为,手稿学不可或缺,不论对写作者,还是对阅读者。
受父母亲的影响,舒乙对文化的保护是执着的,他为了保护文化小院,不辞劳苦,屡次上访,多次用画作和言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舒乙保护北京历史文化的执著人们褒贬不一,有的人热烈响应,反响强烈;也有人激烈反对,反响同样强烈。舒乙还因此“光荣地”获得了“爱国者导弹(捣蛋)”的外号,但舒乙坚信“说了不白说”。因为,他们的苦口婆心终于有了正面的实际反馈:北京市政府责成首都规划委员会、市文物局和市规划院限期制定保护古都风貌的规划。后来,规划几乎吸取了他们的全部建议。为此,舒乙曾激动地当面向市长们说“我要‘叩头了!”
早年的一次北京市政协小组会上,舒乙痛斥“官本位”———冰心先生因几十年前翻译了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和《沙与沫》,黎巴嫩总统签署命令,授予她国家级勋章。授勋仪式上,主持人介绍贵宾,第三位才介绍冰心先生,而她正是授勋仪式的主角。第四个介绍黎巴嫩大使和夫人,然后是各级官员,直到所有的官员都介绍完了,才开始介绍到会的著名作家张光年、王蒙、萧乾……舒乙对此十分不满:“毛病出在不分场合不看具体情况一律以官位来排队,把它当成衡量事物的第一标准和惟一标准。这是个相当迂腐的坏习惯,不仅败坏风气,而且常闹笑话,完全违背了我们的干部行为原则,即不论多大的职位,都是人民的公仆。”
一次,中国作协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集中在北戴河办学习班。对于领导的发言,许多人都顺着领导人思路,表示赞同,或者就着领导的意思发挥,尽管个人方式不同。大家为了这种任务式的学习,谁也不愿得罪领导。可是,舒乙却“不识时务”地提出了与领导相反的观点,而且理论联系实际,旁征博引,讲得有根有据,慷慨激昂,根本不顾领导的“面子”!
坐在前排专门来听大会发言的作协领导,脸色渐渐不悦。主持会议的作协机关党委负责人再也坐不住了,直跟舒乙使眼色、作手势……舒乙全看在眼里,但他一点也不停顿,反而口若悬河,越讲越激动,越讲声音越大!
这就是一个外表长得斯文、儒雅,但骨子里很有些文人的清高和桀骜的舒乙。他不惧上、不媚俗,不攀附权贵,不看别人眼色行事。看到舒乙書桌上的鲁迅著作,让笔者觉得自己好像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里的那个“我”,被他的高大“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想起他当年因古城文化保护向市长大人抱拳“叩头”的场面与这次在作协会上不给面子的情景,笔者十分感动:向市长“折腰”是一种睿智,不看脸色说话同样是一种高贵!
谈到父亲时以“先生”相称
老舍曾多次说过: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实际上,老舍非常热爱生命,他最后在公园里待了整整一天,还是选择离开。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绑到国子监孔庙批斗,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后又被继续毒打至深夜。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下被接回家。第二天,老舍独自前往太平湖,以一句“跟爷爷说再见”向孙女作了人生的最后告别。在太平湖畔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于深夜时刻投湖自杀……
文化界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认为是“文革”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殉难,以身谏,老舍其实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世人,他骨子里是格外坚硬的,拥有宁折不弯的正义坚定的人生态度。父亲的死给舒乙带来了巨大的伤痛。他在回忆的文章中写道:“那一夜,我不知道在椅子上坐了多久,天早就黑了,周围是漆黑一团。公园里没有路灯,天上没有月亮和星星。整个公园里,大概就剩我们父子二人,一死一活。天下起雨来,是蒙蒙细雨,我没动。时间长了,顺着我的脸流下来的是雨水,是泪水,我分不清。我爱这雨,它使我不必掩盖我的泪。我爱这雨,它能陪着我哭,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我摸了父亲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做爱回报给他。”
或许在那个时候,舒乙想起了父亲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我童年时代的记忆中第一次真正出现父亲,是在我两岁的时候……不过,说起来有点泄气,这次记忆中的父亲正在撒尿。母亲带我到便所去撒尿,尿不出,父亲走了进来,做示范,母亲说:‘小乙,尿泡泡,爸也尿泡泡,你看,你们俩一样!于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父亲,而且明白了,我和他一样。”于是,“大文豪为子起名一笔解决”成为佳话。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舍予,就是舍我的意思。”舒乙说,老舍先生把“舍我”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并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一辈子。老舍是“文革”之初中国作家舍身殉难第一人,直至1978年6月3日才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两个月后,邓小平在胡潔青的上书中批示:“对老舍这样有影响的有代表性的人,应当珍视,由统战部或北京市委作出结论均可,不可拖延”。这个批示为沉冤九泉的“人民艺术家”彻底平反一锤定音。
今天,在谈到父亲的时候,舒乙几乎句句以“老舍先生”相称;但对母亲胡潔青,他称的是“妈妈”或”母亲”。问到他为什么这样称父亲,舒乙说自己1984年从文以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来审视父亲,称其先生而不称父亲,是要将父亲拉远,客观地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他。另外,“先生”是别人对老舍的尊称,所以他也从众,称其为先生。
舒乙回忆,老舍平时在家是严肃而沉默的,因为他每天不是在写作就是在思考如何写作,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还在写。舒乙说:“他写得慢,字斟句酌,年轻时候一天写3000字,年纪大了只能写1000字。”当完成了一天的写作,若逢有朋友到访,老舍立刻就像换了一个人,非常热情、幽默。“他有一肚子故事,非把你逗乐不可。只要老舍在场,其他人都不用说话,听着就行,他的笑话永远讲不完。”舒乙说。
舒乙提到父亲笔下的老北京,说道:他笔下有着最地道的老北京,这和他是满族很有关系。清末民初的每个旗人,都会养花、养狗、养马、养鸽子、养蛐蛐,都会骑马射箭,都会舞枪弄棍,都会拳术,都是美食家,都懂各种礼仪……老舍先生熟悉老北京和满族人,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就特别真,特别乡土。
“老舍先生的作品,我看有11部半是他的代表作,那半部就是《正红旗下》。他的作品好多属于‘隐式满族文学。他没有正面描写过一个满族人,其实他写了大量的满族人。祥子,我分析了,他不是满族人,而是河北乡下人。”在文学研究中,舒乙把工程的分类法、统计法运用上了,发现老舍留下的25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以北京为背景的有150万字。他运用理工统计方法统计出老舍全部作品中共出现240多个地名,95%都是真实的。“这些地名从地图上标出来,会发现全部在北京的北角,他小时候就出生在这边。”舒乙从地名的分类和功能研究老舍身世的关系,有关研究文章在老舍学术研究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大家的兴趣,有人将此命名为“文学地理学”,由此派生出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日本研究老舍的中山矢子教授看了舒乙写的关于《骆驼祥子》中祥子拉车路线的研究,率队由舒乙陪同走了5次祥子的拉车路线。“老舍先生的作品改编为影视剧的最多,改得较好的有《离婚》、《四世同堂》,有些本来只可改为10集,结果大量注水,拉得很长,他们追求的是广告。”
老舍有非常朴素的创作观,他生前拒绝对自己的作品有任何拔高的评价。
捐出来与展出来是家教
对于舒乙的婚姻,老舍完全尊重舒乙自己的选择。婚礼那天,他送给舒乙一幅亲笔书写的大条幅,红纸上8个大字:“勤俭持家,健康是福。”下署“老舍”。可惜,后来红卫兵把它撕成了两半,扔在地下乱踩。等他们走后,舒乙从地上将它们捡起来收藏好,保存至今,虽然残破不堪,但是老舍先生留给舒乙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花甲之年,舒乙才开始画画,没有师从任何画派,没有学过技法,而是从感情出发,从生活出发,用自己的方法画画。他的画风颇为独特,画中典型的意境是“一湾碧水,一片黄叶,一抹惆怅,一腔呆情”。谈到绘画,舒乙说,尽管母亲胡潔青是师从齐白石、于非闇两位大师的国画家,但他认为父亲对自己在画画方面的影响要更大一些,相反并没从技法上受母亲一点影响。父母的家庭熏陶对舒乙来说是迥然不同的——父亲从来不会告诉舒乙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以身作则;而母亲则告诉他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
“老舍先生不懂画,但评画却一流,他的鉴赏力极佳,常对着一张字画品头论足。我从中就平白无故地知道了许多艺术标准。而我母亲则日日作画写字,她收藏的许多书画图册我都看过。母亲又大写意,也会工笔,她有一个独门‘菊花。国画的题材本来很窄的,但她有很多发展。”谈到个人的心得,舒乙说,“从我个人来看,我能画画要得益于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我觉得画画的人要有一双特殊的眼睛,这双眼睛能从平凡中发现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先感动了自己,经过长期思考后选出一个奇特的角度来表现。”他认为,无新意的画不是好画,画画是传递新的东西、新的意思、新的情感。“换一双眼睛,什么都能成画。画画让我发现了普通人看不见的美丽和有意思的东西。”
舒乙的《西北的田》、《窗前小草依旧》、《卢森堡公园》、《小貓爪》、《老爷树》等作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展览时,都受到了高度的评价。他的画作题材广泛,色彩鲜艳,贴近现实,文学性浓郁,常常有奇思妙想和非理性的表现,突出表达生活中强烈的感受和新鲜的意思,美术界权威人士称舒乙的画非常有“笔墨情趣”。舒乙指着一幅题为《窗前小草依旧绿》的画作告诉笔者,在每天都经过的一片砖地中,有一天突然为砖缝儿长出的小草而感动,产生了创作冲动,画出了这幅充满生机的作品。舒乙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严肃求新的创作观与老舍先生一脉相承。
他归纳自己的作画心得——就像鲁迅先生创作阿Q的形象一样。先是“静观默察”,在生活中观察;之后“烂熟于心”,对观察到的东西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凝神竭想”,在内心琢磨表现的方法;最后“一挥而就”,把意思表达出来。
近些年来,老舍的后人将老舍的不少藏画无偿捐赠了出去。“老舍生前藏画不叫收藏,叫‘积藏,就是不要藏起来。”对于持续捐出老舍生前遗作与藏品,舒乙说:“捐出来,展出来,这是老舍、胡潔青的家教。”
在介绍舒乙时,常常有人少不了说“这是老舍先生的儿子”。这时,舒乙往往有些无奈。舒乙承认:“作为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一个人靠吃父辈的饭,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站住脚的。父亲是大作家,母亲是画家,当老舍先生的儿子有种压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很好的动力,常提醒自己再努力一些,要夹着尾巴做人。而且,因为有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老舍先生,我为此而感到很骄傲。”
是的,既要做出成就,又不能张扬,尤其不能打老舍这张牌,必须用自己的表现来证实实力,让别人来评价——很“为难”的。说起父亲老舍,舒乙充满深情,他很感谢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热爱生活,热爱朋友和周围的人,特别能同情别人,特别愿意帮助别人。
责任编辑 李肖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