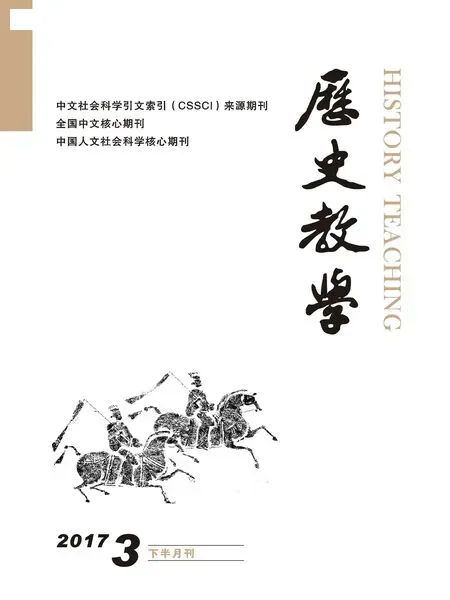近代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
2017-05-11刘志英
刘志英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近代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
刘志英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在近代,上海长时期里居于中国金融业的中心,与全国各地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并通过这种金融互动,对其他地区的经济以及各方面事业,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就是一个典型。本文以抗战的全面爆发为界线,考察了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在战前、战后不同的表现,从而揭示出在不同时期,上海与西南地区在金融领域发生的密切联系及其重要作用和影响。
近代,上海,西南,埠际金融,互动影响
在近代中国,随着新式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全国逐渐形成了若干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全国性金融中心也在不同区域之间不断变迁,这一变迁的基本轨迹是:上海—北京与天津—上海—重庆—上海。①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总体而言,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经济和金融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它的金融业,集中代表了中国金融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而西南地区则僻处中国内陆,交通不便,地区间彼此的金融往来并不多,可是与上海却存在着埠际金融的联系。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上海与重庆地区间的金融互动进一步加强,空前规模的金融资源转移至重庆,不仅极大地有利于抗战,还促使重庆成为了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中心,并带动了西南地区的金融业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纵观目前学界的研究,分别考察近代上海金融与西南金融的相关成果不少,但从埠际往来的角度研究二者相互关系与影响的成果却不多见。本文将以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为分界线,分两个时段重点探究近代以来上海与西南地区金融业的互动关系,以就教学界同仁。
西南地区,就疆域论,通常包括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七省以及西藏全部,但是,由于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省与其他几省在经济与金融的发展中存在根本差别,特别是广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沦陷区,国民政府在战时提倡的“西南开发”,主要指以四川(包括重庆)、贵州、云南、西康、广西为主的五省区。②唐寿民:《开发西南之现状》,《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291页。因此,在本文的论述中,为研究的前后一致与行文的方便,“西南地区”即是以此五省区为主要考察对象。
一、近代以来至抗战爆发前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
近代以来,中国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虽仍以票号、钱庄、当铺等旧式金融机构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新式金融机构,在清末民初的西南也有零星出现,代表着西南地区的金融业也在缓慢地向近代化迈进。在这一过程中,西南的金融业并非完全封闭,与上海为中心的东部金融业还是存在着显著的金融互动。
(一)以重庆为中心的申汇及其市场是战前上海与西南地区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
申汇又称为“上海头寸”,是近代中国各地同上海之间电汇的简称,是一种埠际资金调拨方式,通过申汇将各地与上海联系起来,于是在天津、汉口、重庆、西安、南昌、宁波、杭州等全国各重要城市形成了申汇市场,构筑起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范围内的汇兑体系。
作为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重庆与上海两地间因资金流动而形成的申汇及其市场,成为了上海与西南地区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晚清时期,重庆与上海间商品货币的清算,基本上是依靠两地票号的汇划来完成。民国之后,随着票号的衰落,钱庄业开始在省外口岸城市设庄自行办理汇兑,成为重庆汇兑市场的主力,特别是操控了重庆货帮与上海的资金汇兑。
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主要受重庆与上海的进出口贸易之比差以及重庆银根之活滞为转移,如进口繁盛或当银根呆滞时,由重庆汇往上海之汇率即涨;反之,如为出口繁盛或银根活动时即跌。其次,汇水的涨落还与局势之变动有密切关系。这从1922~1926年间的重庆申汇市场的涨跌即可得到印证(见表1)。

表1:1922~1926年间重庆申汇市场涨跌幅度表
然而,1927年起,重庆申汇市场,受政治因素、自然灾害以及钱帮投机操纵的影响,导致行情暴涨暴跌。国民军兴,江浙吃紧,渝申间进出口形成有入无出状态,川帮欠申之款不能措还,导致申汇行情暴涨至1179两,合洋1647元,此后渐趋稳定,1931年夏,长江水灾,渝市入口锐减,汇价为1400元(1931年重庆实行废两改元,上海汇兑每千两以规元折合计算)上下,“九一八”后,川帮在申活动能力全赖调款挹注,有出无入导致申汇由1400元涨至1600多元,投机活跃,市场极度动摇,波及弱小钱庄,宣告搁浅者多家,一日之间申汇有30~40元的涨跌,买卖申汇,举市若狂。①卢澜康:《从申汇问题说到现金问题》,《四川经济月刊》第1卷第4期(1934年4月),第5~7页。引发了对申汇市场的整顿,重庆市政府决定将申汇市场纳入1932年4月刚刚建立的重庆证券交易所经营,每日前后两市,成交总数,多至200万,少亦数10万,行市涨落,尚觉稳定。但时间一久,投机气氛浓烈,汇价剧烈变动。6月30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在四川美丰银行召开第十六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申汇奇涨问题,并做出由银钱业公会与川省财政厅联合制定平定汇价治本、治标办法,调剂汇市。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0086-1-117。然而,申汇市场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8月1日,重庆钱业公会与交易所的“钱交风潮”发生,钱业公会沥陈交易所操纵申汇,危害市场,请求取缔交易所。后经市政府召集两方代表调解,交易所与钱业协议,对于申汇,钱业做近期,交易所做远期。③《重庆申汇风潮之追述与现状》,《四川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8月),第8页。但仍是业务矛盾不断,后经军方多次干预,允许钱业入所,才告解决。1933~1934年的申汇市场仍不平静,1934年10月,重庆市商会为平准渝申汇水,曾具呈二十一军部请由官商出资100万元组织公司收买土产货品运申销售,军部照准,其商股50万元中拟请重庆银行公会担任大部,得到重庆银行公会的赞成。④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重庆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未刊档案,档号0086-1-117。这些措施均无济于事,重庆申汇市场,完全变成赌场,1935年2月1日,交易所被迫关闭,停拍申汇,仅由银钱业组织交易处经营,以维市场。⑤四川地方银行经济调查部:《二十四年四川金融大事日志》,《四川经济月刊》第5卷第1期(1936年1月),第10页。
总之,清末民初,重庆与上海之间的资金需求比较平衡,申汇的价格也比较稳定,但进入民国后,由于军阀连年征战,导致出口萎缩,商业不振,重庆申汇的投机性较强,1932年之前,重庆申汇交易市场设在钱业公会内,此后则利用重庆证券交易所开拍申汇。在抗战爆发前的重庆申汇市场,虽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上海作为商品流通网络的中心以及汇兑中心,主导着全国主要商品的价格。这样,申汇就以一种重要的埠际资金汇兑方式,以重庆申汇市场为纽带,将西南地区的资金网络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金融机构是战前上海与西南地区金融互动的主体
在清末民初的四川,传统金融机构占主导地位,晚清时期以票号为主,光绪二十年(1894年),山西票号在四川共有27家。四川的主要城市,如成都、重庆等地,票号十分发达,据宣统二年(1910年)出版的《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的票号有日升昌、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蔚盛长、天顺祥、蔚丰厚、百川通、协同庆、存义公、裕川银、恒裕银、金盛元、宝丰银、宝丰隆、宝丰厚、蔚长厚等34家,他们在广州、长沙、汉口、贵阳、南昌、北京、沙市、上海、天津、云南、芜湖等地都分设有汇兑代办处,以异地汇兑为主要业务。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6页。重庆中国银行编:《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34年,第36~38页。
清末的云南与贵州僻处西南,交通不便,与外界甚少往还,云南的金融组织,以山西帮之百川通,江浙帮之盈泰兴,云南帮之天顺祥等为钱庄巨擘,经营存放汇兑业务。贵州省内金融,民国以前仅百川通、天顺祥两家票号。②《贵州省银行简史》,《西北经济》第1卷第4期(1948年6月15日),第36页。《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小史》,《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第196页。晚清广西银号多集中在商业较为发达的桂林、柳州、南宁、梧州。光绪三十年,为解决龙州、南宁间贸易资金不足,由龙州对汛督办郑孝胥在龙州组织官商合营的新龙银号,还设分号于广州,汇兑可通上海。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金融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6~57页。
辛亥革命后,票号收歇,四川钱庄兴起,到1913年底,四川钱庄达243家。④田茂德、吴瑞雨、王大敏整理:《辛亥革命至抗战前夕四川金融大事记(初稿)》(一),《西南金融》1984年第4期,第21页。其中重庆钱庄,在民初最盛时达50余家。⑤重庆中国银行调查组:《民国二十三年重庆之银钱业》,《四川月报》第6卷第4期(1935年4月),第9页。后逐年减少,1923年,仅存30余家。1927年,刘湘占据重庆,政局较为稳定,钱庄又增至49家。此后政局动荡,钱庄倒闭、歇业不断,1934年,重庆有18家钱庄,总资本为126.3万元,存款为687.5万元,而此时新兴的银行总资本为888.5万元,存款为4251.7万元。钱庄的资本和存款总额不及银行的1/6,足见重庆金融业的垄断地位已非钱庄所有。⑥唐学峰:《抗战前的重庆钱庄》,《成都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抗战爆发前,重庆市各钱庄还是西部地区金融积汇转输之所。
近代中国华商新式银行业,以1897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为嚆矢,它在西部地区唯一设立的分行就是重庆分行,于1899年创立,也是上海首个在西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可谓西部金融近代化的开端。后受八国联军之役的影响,到1905年,业务收歇,其分支行号只留京、沪、汉三行与烟台一支店。⑦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初创时期(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1~182页。从1897年至1911年,西南地区华资新式银行之设立仅4家:四川省的濬川源银行、四川银行,广西省的广西银行,贵州省的贵州银行。民国建立以后,在西南地区陆续建立的新式银行,其组织以上海的银行为榜样,其业务不仅局限于本地区,还加强与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的联系,纷纷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
西南地区影响较大的商业银行是1915年在重庆开业的聚兴诚银行。该行先后在省外上海、宜昌、沙市等商埠及省内成都、自贡、内江等城市,共设立29个分支机构。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25页。聚兴诚银行在上海的分行设在九江路,经过近20年的经营,业务极为发达,到1934年5月5日,又在法租界八仙桥设立办事处一所,开幕当天,到场祝贺的有: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邹琳、海军部长陈绍宽、国民政府委员黄复生、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代表傅常等及金融界要人暨留沪川籍绅商,颇极一时之盛。⑨《聚兴诚银行八仙桥办事处开幕》,《银行周报》1934年第18卷第18期,第5页。该行在抗战爆发后,不仅在上海继续保留分支机构,还将苏州支行及香港办事处撤归上海分行,业务不断扩大,下设两个办事处。⑩《沪聚兴诚银行增设静安寺路办事处》,《金融周报》1941年第11卷第1~2期合刊,第32页。1919年由重庆汪云松、长寿孙仲山发起建立的重庆大中银行,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也曾在上海等地设立分行。1922年,由华人与美国人雷文(Reven)在重庆合组之中美合资的四川美丰银行,该行美股于1927年全体退出,由川中军政商界集资收买。该行同样在上海、汉口、万县、平津等处设有代理机关。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成都市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内部发行,1985年,第6页。重庆中国银行编:《重庆经济概况(民国十一年至二十年)》,1934年,第36~38页。1931年,四川美丰银行正式在上海设立分行。1930年创立的川康殖业银行,也在1931年后,陆续设立上海、汉口、宜昌、万县等分行,加强与东部地区的业务联系。②《贵州省银行简史》,《西北经济》第1卷第4期(1948年6月15日),第36页。《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小史》,《四川经济季刊》1944年第1卷第4期,第196页。
抗战爆发前,上海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国家银行为核心,以“南三行”和“北四行”为中心的商业银行为主流的现代化银行体系,居于控制和支配全国金融的中心地位。然而,这些国家银行与商业银行在西南地区的分支机构却较少。商业银行中只有金城银行在西南地区成立了办事处,1933年至1936年间,金城银行分别设长沙、西安、重庆等办事处。①重庆市档案馆馆藏金城银行重庆分行未刊档案,档号0304-1-185。国家银行在西南设立的分支机构见表2:
这些机构在整个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中所占比重很小,云南、广西在抗战前都没有一家国家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
再从近代中国的华资保险事业来看,抗战爆发前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中部地区,1935年,全国有华商保险公司总公司48家,就地域而言,上海25家、香港13家、广州3家、福州3家、天津2家、而北平、重庆各1家;分公司121家,其中西部地区也仅重庆有4家。②沈雷春主编:《中国保险年鉴(1936)》,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1936年,第2~4页。
总之,在抗战爆发之前,以上海为中心的金融网络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东中部沿海沿江地区,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联系主要体现在申汇市场中,主体是金融机构,其中传统金融机构尤为活跃,而以银行等为主的现代金融机构之间的往来并不是太密切。
二、抗战以后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互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与西南地区之间的埠际金融往来与互动大为增强,比抗战前要紧密得多,不仅贯穿整个抗战时期,还延续到战后,对西南经济开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上海金融机构的内迁是战时两地区间金融互动增强的主渠道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后,以银行、保险为核心的金融机构,陆续随国民政府西迁,它们从以上海为首的东部沿长江一路向西,辗转迁徙到长江上游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两地区间金融互动的主渠道。
战时金融的指挥部四联总处从上海迁徙到重庆。1937年7月29日,国民政府财政部授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在上海合组联合贴现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业务。八一三事变后,为加强国家行局的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8月16日,上海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法租界开业。此后,汉口、重庆、南京、南昌、广州、济南、郑州、长沙8处成立联合办事分处,随即国内各重要城市之四行,先后组成联合办事分处达52处。后因上海失陷,南京告急,四行联合办事处的工作一度停顿。③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53~61、118~120页。1937年11月25日,四行联合办事处在汉口恢复工作,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并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上海则改为分处。武汉局势紧张后,1938年初,四联总处由汉口迁至重庆。
四联总处从抗战爆发初期在上海建立的一个临时金融协调组织,到后来经过从上海到汉口再到重庆的不断迁徙过程,最终在重庆确定为领导全国金融的地位,并将分支机构扩建到西南西北为主体的整个国统区,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业的指挥中心,参与了重大经济金融事务的决策,为抗战军需民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表2: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家银行西南地区分支行处统计表
国家银行带头西迁。1937年11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之后,作为政府金融机构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开始向西部大后方迁移,上海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改称分行,办理汇兑买卖。当国民政府政治中心迁移到重庆后,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不仅把总行总处移设重庆,其分支行处先后因战区之推移,而内撤者更达200余处。①重庆市档案馆等编:《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4页。
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四行在西南、西北所设分支机构共340个,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实现了西南地区的全覆盖,所有340个分支机构中,西南为267处,比1941年底(204个)增加了63个,占78.53%。②沈雷春主编:《中国金融年鉴》(1947),上海:黎明书局,1947年,第A113~A114页。
战时商业银行从上海向西南地区的迁徙。抗战爆发前,中国各类私营银行共计124家,占全国银行总数164家的75.61%,其中总行设在上海的为35家,占该类私营银行的28.23%。分类情况如下:商业储蓄银行全国73家,其中总行设在上海的24家,占32.88%;农工银行全国36家,总行设在上海的6家,占16.67%;专业银行全国15家,总行设于上海的5家,占33.33%。③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上海:汉文正楷印书局,1937年,第A13~17页。最重要的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小四行”等,其总行都集中设在上海,属于全国私营银行的精华。
战时上海金融界积极将上海的银行迁往西部支持抗战,各商业银行纷纷向汉口、重庆等地添设分支行及办事处。到1943年7月,东部迁往重庆的商业银行共计12家,几乎全是战前上海的私营银行,“北四行”中的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等三行,“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二行,还有“小四行”中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三行。在这些内迁的商业银行中,金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都是内迁商业银行中的典范。
金城银行是内迁商业银行中在西部建立分支机构最多的一家银行,1938年武汉沦陷,原汉口分行重要部分撤退到重庆。1941年金城银行设立重庆管辖行以督导管理内地各行处业务与人事,并在大后方的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陆续设置了一系列的分支机构,总计18个,其中分行1个:重庆分行;支行4个:成都、贵阳、昆明、桂林支行;办事处11个:重庆的民权路、两路口、沙坪坝办事处,四川省的川大、华西坝、自流井、乐山、泸县办事处,云南省的西南联大办事处,广西省的柳州、梧州办事处;信托分部1个:重庆信托分部;寄庄1个:四川省的威远寄庄。④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单位内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0页。
中国通商银行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大规模向内地迁移的商业银行。1942年5月12日,该行重庆分行被国民政府财政部指定为内地管辖行,内地各行处受该管辖行指导监督。1943年6月10日,中国通商银行总行正式在重庆成立,重庆方面一切业务,仍由重庆分行办理。中国通商银行致力于在内地增设分支行处和拓展业务,先在四川扩增分支机构,1942年7月3日,该行在成都、内江、自流井筹设分支行。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各分支机构继续撤迁至重庆。1939年,该行在贵阳、昆明、桂林三市设立分行,建立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四省的业务中心,为西南各省的物资、资金流通提供方便服务。194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将“总经理驻渝办事处”改为“总行”,但是上海的组织并没有改变,因此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体系内形成了重庆与上海两个“总行”,而重庆已经成为全行的重心。⑤蒋慧:《陈光甫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05页。
与国家银行内迁有所不同的是,商业银行内迁的根本动机还是为了躲避战火及由此带来的损失,而非如国家银行那样,首先是为了维护政府对金融的领导地位和控制力,进而坚持抗战。商业银行内迁中,先行迁徙的是分支行处,总行则大多有一个滞留上海的时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由上海迁往重庆。
保险业从上海向西南的迁徙。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和武汉等地的一些保险机构陆续迁至重庆,以重庆为中枢,先后在各地新建了分公司。无论保险机构、从业人员、资金力量和分保关系,除上海外均大量集中于重庆。于是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保险市场。
重庆是西南地区保险业的中心,截至1944年11月,重庆的保险业已增达53家,计外商保险公司3家(均陷于停顿状态),华商保险公司50家。①董幼娴:《重庆保险业概况》,《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1期(1945年1月1日),第334页。重庆保险业的发达时间,主要是自抗战发生以后,特别是集中于1942~1944年的3年内。据中央银行所编《全国金融机构一览》统计:截至1945年8月,仅川、云、贵、陕、甘五省,就有保险总公司及分支公司机构134家,为抗战前的5倍。到1945年底止,西南、西北各省及湖南的沅陵、衡阳,湖北的襄樊、老河口等地,共有59家保险公司约200个营业机构。其中:四川(含重庆)约135处、云南24处、贵州10处、陕西9处、甘肃6处,以及广西、西康、新疆、湖南、湖北等省也各有几处营业机构。②中国保险学会主编:《中国保险史》,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第132~133页。在战时的特殊条件下,保险业的发展,也为安定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了—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抗战时期,银行业、保险业的内迁,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金融机构大迁徙,它是在特殊时代背景和历史时期,中国金融业所经历的一场深刻变迁,对当时乃至长时期里都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战时上海金融界对西南地区的投资是两地区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基于贸易往来的申汇与申汇市场是战前上海与西南地区间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顺应抗战要求的上海对西南地区的投资,则是战后两地区间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1937年“八一三”抗战结束之后,上海华界地区被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沦为“孤岛”,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这段时间里,租界当局宣告“中立”,由于日本还没有和英、法、美等国正式开战,暂时容忍了这种“中立”状态的存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奠定了上海“孤岛”与西南地区贸易的基础。
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地的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支持,上海与西南地区间的资金流通是否顺畅,决定着西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建设的成败。1938年陆续有不少金融家前往大西南进行实地考察,如邮政总局副局长兼邮政汇业局局长刘攻芸,就因战区日渐扩大,人口及工商机关均相继移往西南各地,特赴西南各省及南洋一带考察邮政储金发展事宜,以备将来在主要地点设立分局或改善业务机构。湖北省财政厅长贾士毅,因整理鄂省财政成绩甚著,被孔祥熙聘为财政部专门委员,也于1938年8月初前往西南考察财政,以期改善后方之金融机构。③《经济考察在西南》,《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第3期,第40~41页。而上海市银行界为了解西南情形,于1939年农历新年结束后,组织一西南考察团,定期于3月间出发。④《金融重心移港银行业谋向西南发展》,《会讯》1939年第1期,第26页。上海银行业开始寻求到西南发展金融,积极投资西南经济建设。如杜月笙、钱新之等人发起创办滇丰纸厂,资本140万元,到1939年上半年,筹组成功,是为西南诸省大规模商办新式企业设立之先例。⑤潘序伦:《开发西南之新机运》,《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293页。
1939年新年伊始,上海金融界发出“到西南去”的号召:“上海的金融界和实业界要踊跃地大量投资到西南去,这一方面固然帮助了国家,使经济建设赶快完成,一方面却正因为有着这有利的决定因素,保障了一切投资者的利益,它是起着这样互助作用的。”⑥以学:《到西南去》,《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1期,第260页。1939年的上海游资充斥,据估计上海各银行存款总额在20~30万万元间,对于这些游资,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目前上海这一个范围来说,消纳游资的途径,委实太狭小,而且多半不是康庄大道……我们知道,西南西北各省安全地带,新兴实业,气象蓬勃,各种富源,都在积极开发,这一块自由的新天地……需要多量的资金……因此,我们谈到上海游资的运用问题,最后就不得不恳切的希望上海贤明的银行家,从速以集体的行动,自动向当局提出一个一方面可以保持自身头寸调拨的灵便,同时又能献身国家的办法,勇敢的大量的向内地投资。”⑦民生:《上海游资的运用》,《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304页。
紧接着,1939年8月20日,上海银钱界召集上海金融经济座谈会,专门讨论上海工商业与金融界的出路问题,特别强调投资西南是此后一条很重要的出路,许多人认为,虽然工厂内迁存在着诸多困难,但资金内移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上海资金过剩,影响到上海工业的畸形繁荣。对于资金内移后投资的途径和方式是值得研究的,内地提倡小工业合作,从事小规模生产,似可认为最妥善最易举的途径。①《上海工商业与金融界的出路》,《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485~488页。于是明确提出了《上海金融界在开发总后方中的任务》,指出,后方需要上海的资金,而上海游资也有去后方的必要,尽管内地工商业尚欠发达,孤岛上的诱惑也较大,内地与上海汇兑的不便,头寸的调拨存在困难,等等,这些都不利于资金的内移。然而,西南西北的开发关系抗战既定国策,要使上海的资金能够积极的动员,首先是“金融界领袖负起抗战中后方建设的责任来,并且应该尽量以内地建设中种种真实的报道与正确的事实去解释许多人的怀疑,使他们的视线从孤岛看到后方,从现在看到将来,从自我看到国家”。②吴承禧:《上海金融界在开发总后方的任务》,《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295页。总之,“为了使上海的资金与整个抗战的形式相配合,上海金融界必须在发展总后方中尽其应尽的最大的任务”。③吴承禧:《上海金融界在开发总后方的任务》,《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2期,第295页。
1939年的重庆申汇市场更是集中反映了上海资金内流的情况,7月末8月初,重庆的申汇市场空前大跌,内地汇申之款,由每百元取费50元,跌至每百元取费22元,上海汇票汇费为18%~22%,其下跌的原因在于,香港富民携巨款赴渝及上海非放置存款之安全地点。汇水下跌有利于资金源源不断流至内地。④《申汇大跌资金内流》,《金融周报》1939年第8卷第13期,第12页。
战时上海金融界到西南去投资,首先看中的是西南交通的建设,上海的金融界对西南在战时国防地位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西南各省在国防上地位的重要,还不仅在于其本身的富庶,以所处地位而言,在交通军事上也占着极重要的价值。这就内地的交通来讲,有京滇、川黔、桂黔、川陕、川湘等公路,同时政府并计划完成十一条铁路线,贯穿了西南各省并密切地与内地联系起来;至于对国外交通,那末在目前广州失守以后,云南的滇越铁路更成为中国进出口的咽喉。”⑤⑥以学:《到西南去》,《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1期,第260页。“假使十一条铁路线能够完成的话,那西南各省不再是被人们认做是辽远边鄙的省份,而将成为各地货物输出的总枢纽,其一切经济金融的发达,正有着这样决定的因素。”⑥以学:《到西南去》,《银钱界》1939年第3卷第1期,第260页。因此,上海金融界不仅要致力于开发西南的富源和加紧经济建设,还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西南交通建设方面。1938年国民政府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后,对开发西南交通积极进行,第一步计划完成西南五省的铁路建设计划,为宝成、川康、成渝、川黔、黔桂、粤桂、湘黔、滇黔、滇缅、湘桂、桂粤11线,共长6400千米,发起筹款2000万元,择其首要之铁路建筑,以及电话电报等重要交通工具,经该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与各银行界领袖接洽后,各银行踊跃投资,如数筹足。⑦《各银行投资建设西南交通》,《金融周报》1938年第6卷第11期,第13页。
总之,战时上海对西南地区的资金支持,是两地之间金融互动的主要内容,并极大地支持了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
(三)战时上海金融家和金融人才的内移是与西南地区金融互动的重要推手
抗战爆发前,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聚集了一大批专业的银行家和金融人才。他们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还曾留学国外,接受过西方经济学、财政学、商学和货币银行学等现代专业的系统训练,他们熟悉国情、掌握现代金融银行知识,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专业金融人才。抗战爆发后,上海银行家作为一个整体,随着战局的变化和国家金融中心的转移,频繁来往于“上海—汉口—香港—重庆”之间,当上海陷落后,这些声名赫赫的金融家们除极少数如唐寿民、傅筱庵投敌卖国外,大部分都坚持抗战。不少人随着国民政府的西迁,而选择前往西南大后方,如陈光甫、张嘉璈、钱新之、王志莘、虞洽卿、吴鼎昌等,他们在大后方努力发挥自己的金融才干。
陈光甫以民族大义激励上海银行员工们:“吾人在今日抗战局面下,亦应有抗战之精神。”⑧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编:《陈光甫先生言论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49年,第190页。他除了料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本职业务外,还积极参与国民政府的各项活动,为抗战服务。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说:“对于抗日战争,我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我是战时‘贸易调整委员会’的主任;第二,我在1939年和1940年通过谈判获得两笔美国贷款,尽管中国官员认为这些钱并不够,但我觉得这为后来的援助铺平了道路;第三,从1941年到1943年我任‘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①郑焱、蒋慧:《陈光甫传稿》,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张嘉璈在战时虽担任交通部长,但并未完全脱离金融圈子,仍然活跃在金融决策层里。他在1939年5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不问金融已久,今后财政金融,日见困难。每次遇有关于财金之会议,必被邀参加。”②姚崧龄编著:《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8页。而且修筑铁路、公路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张嘉璈提倡中国银行界投资铁路:“华商银行若能参加投资,可使外国投资者有减轻风险之感,对于新投资必更踊跃。”③张嘉璈:《中国铁道建设》,杨湘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50页。
1938年,钱新之接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后,致力于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添设交行分支行处。他曾表示开发西南是金融界应尽的责任,要求交通银行雇员经常注意各地工商实业发展情形和社会动态,竭力开拓业务,为发展后方工商业出力。1942年3月,钱新之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1943年7月,出任杜月笙筹设的“通济公司”常务董事。在钱新之主持下,交通银行赞助了昆明裕滇纱厂、长江裕新纺织公司、贵州实业公司等重要企业,并创立了生产中型纱厂机械设备的经纬纺织机器公司,为推动后方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④徐矛、顾关林等主编:《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抗战爆发后,王志莘经香港辗转到重庆,在重庆设立新华银行总管理处,管理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分行业务。1941年,虞洽卿拒在日伪政权任职,离开上海,转道香港赴重庆,在港期间,他料定大后方必定急需卡车,断然向华伦银行贷借五万英镑,买下一批福特牌卡车。他押运着这批卡车,绕道越南的海防、河内,经缅甸的仰光,沿着滇缅公路驶抵昆明,一路辗转,始达重庆。在渝期间,由于日军封锁,大后方军需民用物资匮乏,他与王晓籁等组织三民运输公司,运来大宗的布匹、粮食等日用百货,缓解了后方的物资匮乏。⑤刘夏:《超级大亨虞洽卿》,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1年,第303~304页。
战时的吴鼎昌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长达六年(1938~1943年),由于他曾长期任职银行界,深知发展经济离不开金融支持。在贵州任职期间,他认为:“本省的金融政策,首注意于各县合作事业的发展。”⑥贵州全省县政会议秘书处:《贵州省全省会议纪要》,1940年,第17页。主张由贵州省政府与农本局合办合作金库,规定,双方合办贵阳、贵定、定番、息烽、安顺、平坝、镇宁、镇远、毕节、黔西、玉屏、独山、都匀、盘县、遵义15县合作金库,并优先成立贵阳、遵义、安顺、镇远、独山5县合作金库。以后视实际需要及合作事业发展情形,再分期成立其余各县合作金库。⑦《贵州省政府、农本局合办合作金库合同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402,案卷号11271。这些措施发展了贵州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恢复和发展。
抗战时期,在西南大后方,如此众多金融机构的建立,除需要有名望、有影响、有地位的金融家之推动外,还需要大量了解熟悉现代金融业务的金融人才的加入。而这些金融人才,有不少是从东部发达地区内迁转移到大后方的,如内迁银行中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内迁的初期,主要通过将东部人才调往西部筹办机构,以解燃眉之急。中国银行即将原在沿海城市分行负责人员大批调到西南筹设分支行处。1938年8月,中国银行总处通知沪驻港处:嘱令在云南、广西两省筹设支行。派原上海分行襄理兼虹口办事处主任王振芳等筹建昆明支行,派原济南支行经理陈隽人筹建桂林支行。经过数月筹备,1938年11月1日昆明支行开业,1939年1月26日桂林支行开业。1938年12月25日成立贵阳支行,调派石家庄支行经理赵宗溥任经理。⑧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第418~420页。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分行成立时,曾派骆清华前往筹设,此后沈景时等人内调支援,才使该分行顺利成立。⑨陈礼茂:《抗战时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内迁和战后的复员》,《上海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70页。
抗战时期从上海地区内迁的金融家与金融人才是促进与西南地区金融互动的重要推手,不仅加强和密切两地区之间的金融埠际往来,而且在西南大后方的金融现代化进程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落后的西南地区带来了现代化的金融思想,大大推动了西南地区金融业从经营理念到方式的转变,使西南地区金融业逐步走向现代化轨道。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上海与西南地区的金融往来从疏到密,从简单到复杂,以全面抗战的爆发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战前,两地间金融互动之内容,主要是申汇与申汇市场;互动的主体则是金融机构,其中,由于现代银行在西南地区尚欠发达,因此传统金融机构占据了申汇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战时,两地间金融互动之内容,是以上海对西南地区的投资为主,互动的主体则是以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为主,保险机构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往来。不仅如此,战时的两地间的金融互动,已远非战前基于埠际贸易下的常态的金融往来,而是处于战争背景下的特殊的金融往来,因此呈现出的金融互动远较战前密切和复杂,并且实际形成了上海的金融资源,包括资金、机构、人员等等,向西南地区的大转移,其产生的影响亦非常深远。首先,它改变了战前中国现代化金融机构集中沿海地区,而内地较少的不平衡状态,促进了东西部金融格局的区域平衡。其次,促使战时中国金融中心从上海向重庆的转移,还带动了现代金融机构在西南西北地区的迅速发展。最后,保存了中国金融业的精华,并直接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这一转移,不仅使大量现代金融机构免于为敌所用,而且,以上海内迁金融机构为中坚,构建起了大后方金融体系,直至取得最终胜利,从而为坚持抗战与西部开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Finan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Southwest China in Modern Times
During modern China,Shanghai had a long-term occupation in the heart of financial industry. Through continuous financial interaction with other regions in China,Shanghai had pose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economyand related undertakings toother regions within China.A typical and significant example is the finan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Shanghai and Southwest China.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Shanghai and Southwest China financially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before and after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Japanese Aggression,and discusses the close financial ties between Shanghai and Southwest China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e.
Modern Times,Shanghai,Southwest China,Inter-port Finance,Interactive Influence
K2
A
0457-6241(2017)06-0018-09
刘志英,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经济史、金融史。
【责任编辑:杨莲霞】
2017-01-15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络的构建与变迁》(项目编号:13BZS05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