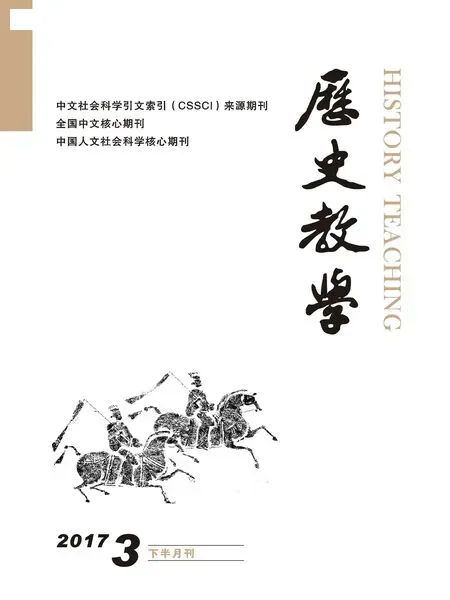*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选任与群体特征
2017-03-11初庆东
初庆东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
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选任与群体特征
初庆东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权力急剧膨胀,成为英国解决犯罪、贫困等社会问题的中坚力量。以国王与大法官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利用对治安法官的选任权,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敦促治安法官勤政为国。但充任治安法官的乡绅不靠国家薪俸过活的特点与有限的治安法官人选,决定了中央对治安法官控制的有限性。同时,治安法官通过财富积累、教育、血缘、姻缘与政治庇护等途径与中央政府建立联系,二者形成相互依赖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中央政府与治安法官的妥协与合作,这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与国家有序治理提供了保证。
治安法官,国家治理,选任权,社会关系,英国
英国治安法官制度起源于14世纪,职权几经更迭,存续至今。从都铎时期开始,治安法官的权力急剧膨胀,一直延续到斯图亚特时期。治安法官的职责广泛,控制地方的司法与行政大权,是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特别是在十六七世纪,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临贫困、犯罪、流民、瘟疫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治安法官成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力量,是国王的“仆役”与地方社会的“家长”,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提供保障。著名法律史学家梅特兰(F.W.Maitland)认为:“(由治安法官组成的)治安委员会稳定地发展……(它)如此重要而又如此完好地存续下来。治安委员会是纯粹英国式的……政府架构。”①研究治安法官的学者格利森(J.H.Gleason)也毫不吝惜对治安法官的赞誉,他说:“持久而普遍的治安委员会毫不逊色于人们所熟知的议会。”②那么,治安法官的选任程序如何,哪些因素影响治安法官的选任,以及治安法官群体又有哪些特征呢?尽管国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偏重制度演进,未能系统梳理治安法官选任过程中的权力博弈及其群体特征。③相较而言,国内学者对这些问题尚未给出比较完备的解答。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治安法官的选任及其群体特征,进而揭示转型时期英国社会的某些面相。
一、治安法官的选任程序与资格
英王理查二世和亨利六世相继颁布法令,规定每郡治安委员会由土地年收入20镑以上的6人组成。但到近代早期治安委员会的人数限制早已不合时宜,如威廉·兰巴德(William Lambarde)所言:“治安法官执行着日益增多的法令,而导致现在每郡治安法官的人数猛增。”④同时,兰巴德也认为财产限制早已形同虚设:“制定相关法律的时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丹桂计划”项目“社会转型时期英国治安法官研究(15~18世纪)”(项目编号:CCNU16A030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资助编号:2016M600605)的阶段性成果。
①F.W.Maitland,“The Shallows and Silences of Real Life”,in H.A.L.Fisher,ed.,The Collected Papers of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Vol.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11,p.470.
②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122.
③国外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Charles Austin Beard,The Office of Justice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New York:Burt Franklin,1904;L.K.Glassey,Politic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1675-172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Sir Thomas Skyrme,History of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Chichester:Barry Rose,1991;Alison Wall,“‘The Greatest Disgrace’: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JPsin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England”,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19,No.481(Apr.,2004),pp.312~332.
④William Lambarde,Eirenarcha,or,The Office of the Justices of Peace,London:Company of Stationers,1619,p.35.候,情况与现在不同……从那以后物价飞涨,年收入20镑的财产限定对治安法官的收入而言,所占比重已大为下降。”①William Lambarde,Eirenarcha,or,The Office of the Justices of Peace,p.38.在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时期,治安委员会的人数普遍增加。
都铎早期,各郡治安法官平均不到10名,但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中期,每郡治安法官人数多达40到50名。1580年,英格兰治安法官的总人数为1738名,人数最少的拉特兰郡有13名,人数最多的肯特郡有83名。诺福克郡在伊丽莎白一世继位之时有37名治安法官,到1602年增至61名。②A.G.R.Smith,The Government of Elizabethan England,London:Edward Arnold,1978,pp.90~91.1562~1636年,肯特郡、诺福克郡、北安普顿郡、萨默塞特郡、伍斯特郡、北约克郡六郡治安法官的总数从210人增加到356人。③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49.兰开夏治安委员会在1561年有36名治安法官,1583年至少有40名,1592年达到56名。1603年12月,兰开夏治安委员会人数达到49名,一直到1608年共有10个治安委员会存在,平均人数为56名。1626~1630年治安委员会平均有62人,到1636~1640年平均有54人。④D.J.Wilkinson,“The Commission of the Peace in Lancashire,1603-1642”,Transactions of the Historic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Vol.132(1983),pp.42~44;David Underdown,“Settlement in the Counties 1653-1658”,in G.E.Aylmer,ed.,The Interregnum:The Quest for Settlement 1646-1660,London:Macmillan,1972,pp.168,170~171,173,175~181;Lionel K.J.Glassey,Politic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1675-1720,pp.15~17,272;James Tait,ed.,Lancashire Quarter Sessions Records,Vol.1.Quarter Sessions Rolls 1590-1606,The Chetham Society,1917,pp.vi~viii.威尔特郡治安委员会的人数也呈现迅速增长之势。1562年,治安委员会有30名治安法官;1600年,治安委员会总数增至52名;1657年,治安委员会总数达到79名。⑤J.Hurstfield,“County Government 1530-1660”,in R.B.Pugh and Elizabeth Crittall,eds.,The Victoria History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A History of Wiltshire,Vol.V,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p.89.东约克郡治安委员会的人数在1621~1622年是伊丽莎白一世后期的两倍。⑥G.C.F.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York:East Yorkshire Local History Society, 1973,p.20.从中可以看出,从伊丽莎白一世到斯图亚特时期,治安委员会中治安法官的数量大幅增长。
治安法官人数的增加,无疑与该时期治安法官职责的增加有关,也与各郡分区的发展对治安法官的需求增加有关。例如,德比郡、诺福克郡、萨塞克斯郡和威斯特摩兰郡都曾以分区治安法官空缺为由,要求增加治安法官。⑦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p.38~39.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乡绅对治安法官职务的需求增加。地方乡绅出于荣誉与权力的考量、宗教热情与公共义务传统的驱使,积极谋求出任治安法官。那么,治安法官是通过什么程序选任的呢?
除兰开夏外,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治安法官都通过加盖国玺的治安委员会委任状(letters patent)获得任命。⑧D.J.Wilkinson,“The Commission of the Peace in Lancashire,1603-1642”,p.41.治安法官的委任状从14世纪到1590年间基本保持不变,详细记载了治安法官需要推行的所有法令和推行办法。委任状有时保留早已废弃的法令,或已经被后来相关法令替代的法令。如此一来,委任状的法令冗长、笨重。兰巴德曾抱怨由此引起的混乱,迫切希望改革委任状的形式。兰巴德在1581年指出:“治安法官需要遵循的法令有很多是徒劳地重复,其他则已不合时宜。把这些法令揉作一团,致使漏洞百出,必须予以纠正。”1590年,王座法庭、普通诉讼法庭和财政法庭的法官,在各自首席法官的带领下,起草一份委任状修正案,获得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Christopher Hatton)的同意。此后,所有委任状执行新的规范,一直存续到1878年。⑨Sir ThomasSkyrme,History of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Vol.I,p.185.
1590年改革后的治安法官委任状包括三个条款:第一条款授权一名治安法官在郡内担任治安维持官,负责执行法令并惩罚不法者,并要求不良行为者保证遵守秩序,如有违反则予以监禁。第二条款是两名或多名治安法官(其中一名须是法定人数治安法官)有权召开季审法庭,行使司法权力,调查重罪、下毒、巫术、非法侵入、垄断市场、囤积居奇、非法集会、危害生命安全、啤酒馆经营者的不法行为、短斤少两、官员(包括郡长、法警、警役、狱卒等)滥用职权等案件,受理讼状,调查未处理的讼状,审讯被告,听取和判决罪行并处罚金。疑难案件则须在王座法庭法官或巡回法官在场时才能审理。治安法官决定开庭时间与地点,郡长负责召集陪审团和根据治安法官的要求出席季审法庭。第三条款则是任命首席治安法官。首席治安法官需居住在本郡,负责保管季审法庭卷档,有权任命治安书记员。治安书记员负责携带令状、法令、讼状到季审法庭,以供治安法官断案之需。①H.C.Johnson,ed.,Wiltshire County Records:Minutes of Proceedings in Sessions 1563 and 1574 to 1592,Devizes:Wiltshire Archaeological and Natural History Society,1949,pp.viii~ix;T.G.Barnes and A.Hassell Smith,“Justices of the Peace from 1558 to 1688—a Revised List of Sources”,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Vol.32(1959),p.222;Sir Thomas Skyrme,History of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Vol.I,pp.185~186.
法定人数治安法官的选任,是基于治安法官多为非专业法律人员担任的事实。为保证治安法官依法办案,由专业律师担任法定人数治安法官。随着16、17世纪越来越多的乡绅通过大学或律师会馆学习法律,法定人数治安法官则多由具有行政经验的高级治安法官担任。兰巴德高度肯定由专业法律人员充当法定人数治安法官,他说道:
尽管谨慎的人(但不精通法律)可能足以应付维持治安的种种规定,但当通过证人的证据和陪审员的宣誓而形成讼状,并根据法律条文进行听证和决断时……通晓法律是一道必不可少的亮光。没有它,所有的工作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结果肯定是错误和危险的。②William Lambarde,Eirenarcha,or,The Office of the Justices of Peace,p.49.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法定人数治安法官的数量膨胀,从约占治安法官总数的1/3增加到接近3/4。③D.H.Allen,ed.,Essex Quarter Sessions Order Book 1652-1661,Chelmsford:The Essex County Council,1974,p.xii.
从15世纪中叶开始,担任治安法官的条件是“最富裕的骑士(knights)、准骑士(esquires)和绅士(gentlemen)”,他们须是担任治安法官所在郡的居民,并且拥有年收入不少于20镑的地产。但财富不是担任治安法官的充要条件,正如16世纪后期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所言:
治安法官从高级贵族(nobility)或低级贵族中选任,即公爵(D uke)、侯爵(M arquis)、男爵(Baron)、骑士、准骑士和绅士,也从通晓法律者中选任。治安法官智慧过人,郡居民对其充分信任。④Sir ThomasSmith,De Republica Anglorum,edited by Mary De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103~104.
简言之,治安法官是经济独立、有地位的当地居民,他们是“乡绅”的代表。⑤G.C.F.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22~23.到17世纪初,乡绅最核心的两个属性是独立和闲暇。“独立”意味着有足够的收入来养活自己和家仆,也意味着有不受制于他人(领主、雇主等)的自由。“闲暇”是指不为生计所迫,有为政府服务的自由,而且拥有公平、明智和负责的心态与性格。乡绅的“绅士风度”不是对其社会职能的描述,而是一种治理(govern)的品质与能力。⑥John Morrill,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Longman,1993,pp.196~197;Mary Wolffe,Gentry Leaders in Peace and War:The Gentry Governors of Dev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 Press,1997,pp.6~7.乡绅积极出任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政府的权力中枢,也是近代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
二、治安法官选任的影响因素
乡绅虽然汲汲出任治安法官,但治安法官的选任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重臣的建议、大法官掌握的信息、巡回法官的报告、郡督或主教等地方贵族的看法,以及郡重要人物的举荐等因素。巡回法官巡视治安法官所辖郡的情况,其反馈意见对治安法官的选任可以施加影响。例如,1595年,掌玺大臣帕克林(Puckering)在巡回法官夏季巡回辖区之前告诫巡回法官:女王“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看着她的仆人”,她仔细审核治安法官名单并划掉不合适的人选。⑦John Hawarde,Les Reportes del Cases in Camera Stellata,1593 to 1609,edited by W.P.Baildon,London:Privately Printed, 1894,pp.21、368.1608年,巡回法官被告知要留意推荐治安法官人选,因为很多治安法官参加季审法庭时“像傻子一样发呆而无所事事”。⑧John Hawarde,Les Reportes del Cases in Camera Stellata,1593 to 1609,edited by W.P.Baildon,London:Privately Printed, 1894,pp.21、368.1617年,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在巡回法官夏季巡回的指令中说:“你们有义务将国王的荣光与关切传达给民众;在你们回来的时候,有义务向国王汇报民众的不满与悲伤。”⑨JamesSpedding,ed.,The Letters and the Life of Francis Bacon,Vol.VI,London:Longmans,1872,p.211.郡督对治安法官的选任也颇有影响,詹姆斯一世时期郡督的作用更加凸显。例如,1619年,萨塞克斯郡的郡督阻止多名治安法官提名人选担任治安法官。复辟之后,郡督再次拥有改组治安委员会的主动权。⑩Anthony Fletcher,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Sussex 1600-1660,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75,p.129.郡中重要人物对治安法官人选的提名,对治安法官的选任也有重要影响。例如,萨默塞特郡的约翰·波利特(John Poulett)与国王宠臣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往来密切,1627年波利特举荐其叔乔治·波利特(George Poulett)和弗朗西斯·罗格斯爵士(Sir Francis Rogers)作为治安法官的人选。在白金汉公爵的直接干预下,两人被正式任命为治安法官。①Thomas Garden Barnes,Somerset 1625-1640:A County’s Government During the“Personal Ru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42~43.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p.9、10.由此可见,治安法官的选任是多重权力交织与博弈的过程。
国王与大法官利用对治安法官的选任权,罢免不称职的治安法官,加强对治安法官的控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枢密院经常表达对地方管理现状的不满,枢密大臣在议会和星室法庭抱怨地方政府的无效率与懒惰,但枢密院针对地方政府弊端的改革却存有分歧。②A.Hassell Smith,County and Court: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Norfolk,1558-1603,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pp.76、77~86.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75~76、75.一些人希望增加治安法官的人数,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工作负担;另一些人则希望缩减治安法官的人数,仅任命勤政的治安法官,如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所言:“(勤政的治安法官)以大无畏的勇气伸张公正。”③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5.JamesM.Rosenheim,ed.,“The Notebook of Robert Doughty,1662-1665”,Norfolk Record Society,Vol.LIV,1989,p.8.伯利勋爵的看法有其合理性,并得到至少三位大法官的强烈支持:尼古拉斯·培根爵士、约翰·帕克林爵士和托马斯·伊格尔顿爵士(Sir Thomas Egerton)。在他们眼中,乡绅是争吵的根源。很多乡绅担任治安法官的目的是利用职权为派系服务,而且品行不端的治安法官只会带来消极影响。16世纪90年代,伯利勋爵抱怨数量众多且不称职的治安法官,使那些称职的治安法官以与他们共事为耻。于是,伯利勋爵开始着手清洗那些不称职的治安法官,他先后进行了至少7次较大规模的清洗,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④A.Hassell Smith,County and Court: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Norfolk,1558-1603,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pp.76、77~86.
1625年11月,托马斯·考文垂勋爵担任大法官,开启了为期15年(1625~1640年)严格控制治安法官人数的时代。北约克郡治安法官人数从17世纪20年代的59名锐减至1626年的29名,东约克郡治安法官人数则从58人减至30人左右。⑤G.C.F.Forster,“The North Riding Justicesand their Sessions,1603-1625,”Northern History,Vol.10,No.1(1975),p.125;G.C.F. 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20.1626年肯特郡一些反对国王的治安法官遭到清洗,1636年治安法官的人数再次减少,比1626年减少1/8,变为63人。⑥Peter Clark,English Provincial Society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Revolution:Religion,Politics and Society in Kent 1500-1640, Hassocks:The Harvester Press,1977,p.376.1625年12月,考文垂勋爵在萨塞克斯郡一次性罢免21位治安法官,治安法官人数从48人降至27人。在随后的15年内,萨塞克斯郡治安法官的人数从未超过35人。⑦Anthony Fletcher,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Sussex,1600-1660,p.129.控制治安法官的人数,成为伊丽莎白一世后期和斯图亚特早期枢密院的政策,也是中央加强地方控制的表现,但这种控制更多地出自大法官个人的意愿。
治安法官遭到罢免的原因多种多样。例如,17世纪30年代,考文垂勋爵主要罢免年龄过大与懒惰的治安法官。⑧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p.9、10.公开反对政府政策的治安法官也会被解职。例如,1635年,林肯郡治安法官约翰·雷爵士和托马斯·奥格尔(Thomas Ogle)因为拒缴船税而被免职。⑨Clive Holmes,Seventeenth-Century Lincolnshire,Lincoln:The History of Lincolnshire Committee,1980,p.81.萨默塞特郡治安法官罗伯特·菲利普斯(Robert Phelips)、约翰·赛姆斯(John Symes)和休·佩恩(Hugh Pyne)因为反对国王征税而被免职。查理一世时期,休·佩恩因为抨击国王强制借款而被拘禁,并在王座法庭受审。⑩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75~76、75.1629年,有40名左右治安法官因为反对强制借款而被免职。①Thomas Garden Barnes,Somerset 1625-1640:A County’s Government During the“Personal Rule”,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p.42~43.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p.9、10.再者,政治冲突也可能使治安法官遭到罢免。例如,1622年,约克郡治安法官托马斯·霍比爵士(Sir Thomas Hoby)因与北方委员会主席斯克罗普勋爵(Lord Scrope)发生争执而被免职。②A.Hassell Smith,County and Court: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Norfolk,1558-1603,Oxford:Clarendon Press,1974,pp.76、77~86.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75~76、75.诺福克郡治安法官罗伯特·道蒂(Robert Doughty)因为在出任税收委员时,冒犯了一位有影响的骑士而遭免职。③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5.JamesM.Rosenheim,ed.,“The Notebook of Robert Doughty,1662-1665”,Norfolk Record Society,Vol.LIV,1989,p.8.内战时期,政治立场成为治安法官选任最为重要的考量因素。641年夏天,议会成功地将教士从地方政府中全部清除。紧接着,国王替换了约200名治安法官。从内战爆发到复辟,对治安委员会的控制成为地方权力争夺的中心。以萨塞克斯郡为例,1644年托马斯·佩勒姆爵士(Sir Thomas Pelham)清除27位治安法官,并新任命24名治安法官。任何同情保王党,抑或中立的治安法官,均被罢免。沃里克郡和德文郡治安委员会也彻底重组。①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p.11~13;Stephen K.Roberts,Recovery and Restoration in an English County:Devon Local Administration 1646-1670,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1985,pp.26~27.可见,政治因素对治安法官选任的影响较大,不同政见或派系的治安法官常常成为被罢免的对象。
1649~1653年,地方政治最为重要的特征是,随着传统世家大族从行政管理和政治活动中退出达到高潮,地方权力圈迅速缩小。这一时期个人对治安法官的选任具有主导作用,成为郡寡头(countyboss)统治的黄金时期。例如,约翰·佩恩统治萨默塞特郡,米歇尔·利夫西爵士(Sir Michael Livesey)在肯特郡进行专制统治。一些郡寡头是狂热的宗教和政治激进派,如康沃尔郡的罗伯特·贝内特(Robert Bennett)和兰开夏的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但郡寡头并不能我行我素、一手遮天,而且并非所有的郡寡头都是暴发户或政治激进者。例如,柴郡和萨塞克斯郡世家大族仍担任治安法官。②David Underdown,Somerset in the Civil War and Interregnum,Newton Abbot:David&Charles,1973,pp.155~172;J.S.Morrill, Cheshire 1630-1660:Coun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p.258;Anthony Fletcher,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Sussex,1600-1660,p.295;J.A.Sharpe,Crim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A County Stud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9.因此,尽管郡治安委员会中激进派占优势,但保守派仍然拥有重要影响力。
护国主时期,枢密院对治安委员会的控制措施比较温和,既未清除1653年的激进者,也未任命很多新人。枢密院继续寻求地方世家大族的支持,正如戴维·安德唐(David Underdown)总结的那样:“友谊与裙带又一次比意识形态更重要。”③David Underdown,Somerset in the Civil War and Interregnum,p.176.克伦威尔仅要求治安法官在获得任命时,需对护国主宣誓效忠。威尔士治安法官中激进的福音派宣传者被免职。除威尔士之外,其他各郡治安委员会并无较大变动。一些在共和国时期不参与公共事务的“长老会”成员重新执掌官职,如诺福克的约翰·帕尔格雷夫爵士(Sir John Palgrave)、柴郡的乔治·布思爵士(Sir George Booth)和康沃尔郡的安东尼·尼科尔(AnthonyNicoll)。那些极力反对克伦威尔的郡寡头则失去权势,如佩恩、利夫西。④David Underdown,“Settlement in the Counties,1653-1658”,pp.172~173、177.一些温和派,如萨塞克斯的赫伯特·莫利(Herbert Morley),仍然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开始慢慢重新进入治安委员会。例如,1655年,在总检察长戈夫(Goffe)的举荐下,萨塞克斯郡的佩勒姆爵士进入治安委员会。⑤Anthony Fletcher,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Sussex,1600-1660,pp.131,300~301.1656年秋,德比郡的一些权贵重新进入治安委员会。⑥Richard Clark,“Why was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in 1662 Possible?Derbyshire:A Provincial Perspective”, Midland History,Vol.8,Issue 1(1983),p.94.1657年3月,萨默塞特郡治安委员会重组,议会温和派和骑士家族的子嗣进入治安委员会。⑦David Underdown,“Settlement in the Counties,1653-1658”,pp.172~173、177.
与克伦威尔对治安法官的温和措施相比,1660年的复辟对大多数治安委员会的冲击较大。德文郡54名治安法官中有23名被免职,萨塞克斯郡有35名治安法官失去官职。大空位时期(1649~1660年)的军事和行政人员以及与统治者联系密切的治安法官均遭清洗。但治安法官的连续性与任职经验是必需的,这就使得治安法官的清洗不彻底。例如,1660年,德文郡治安委员会是不同政治利益集团和解的结果。同一时期,柴郡治安委员会“巧妙地平衡了之前保王党、长老派和克伦威尔保守派”。⑧J.S.Morrill,“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on”,in B.E.Harris,ed.,A History of the County of Chester,Vol.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115.德文郡的具体情况,参见Stephen K.Roberts,Recovery and Restoration in an English County:Devon Local Administration 1646-1670,pp.148~150,153~155.根据莫里尔(J.S.Morrill)对8个郡治安委员会的统计,约40%来自保王党,33%是17世纪50年代未担任治安法官的议会党,另有27%是17世纪50年代治安委员会的成员。⑨Cited in 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19.蒙茅斯郡和赫特福德郡治安委员会中17世纪50年代的治安法官约占1/4。⑩Philip Jenkins,“‘The Old Leaven’:The Welsh RoundheadsAfter 1660,”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24,No.4(Dec.,1981),p.815.
治安法官的宗教信仰也会影响其选任,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例如,1625~1640年间,德文郡治安法官威廉·考特尼爵士(Sir William Courtenay)因为被怀疑是天主教徒而遭免职,约翰·惠登爵士(Sir John Whidden)因为与天主教有联系而被免职。①Mary Wolffe,Gentry Leaders in Peace and War:The Gentry Governors of Dev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19~20,23.1564年,道纳姆主教(Bishop Downham)汇报,兰开夏的25名治安法官中只有6人支持新教,而且对其中两名治安法官的忠诚与否没有把握。由于兰开夏乡绅人数不足且分散,所以清除保守的治安法官困难重重。到1583年,那些不支持新教的治安法官中,仍有8人继续担任治安法官,而且有4人是积极、活跃的治安法官。②Christopher Haigh,Re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udor Lancash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p.213.北安普敦郡、伍斯特郡和北约克郡有数目众多的治安法官,尽管在主教们看来他们并不支持国家的宗教政策,但仍担任治安法官。③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71.
总体而言,治安法官被永久罢免的情况并不多见。兰巴德回忆道:“我仅记得有一位治安法官被星室法庭解除职务。”④William Lambarde,Eirenarcha,or,The Office of the Justices of Peace,p.87.斯图亚特时期,因为各种原因(如个人恩怨、拒绝执行王室政策、反对国王等)被罢黜的治安法官,经常稍后便官复原职。这表明,国王与大法官在解除治安法官职务时并无绝对权力。治安法官的选任权握在贵族和重要乡绅之手,尽管一些治安法官人选不会得到大法官同意,但数量有限。一个忠诚的治安委员会是国王与中央梦寐以求的结果,但由于从郡领导者中选任治安法官的人选有限,所以,国王与中央必须容忍治安法官的一些过失,而且其政策必须考虑治安法官的意见。⑤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66~67、81~82.这就决定了治安法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攸关国家法令与中央决策在地方的执行力度,这就使治安法官成为地方治理的决定性力量。
治安法官的选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重要场域。国家对治安法官的选任表明,一方面国家加强对治安法官的控制,另一方面国家又不得不放任在地方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治安法官。治安法官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地方自治的形成,并对国家治理模式的形塑起到重要作用。
三、治安法官的群体特征
作为社会群体的治安法官是地方政府的主体和地方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有着共同的“乡绅”身份认同,而且在财富、教育和社会网络等方面又有一些共性,从而构成治安法官的群体特征。
首先,治安法官有一定的财富积累。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治安法官的财富总体上有所增加,但富裕和中等收入治安法官的数量减少,而低等收入治安法官的数量增加。根据1624年补助金卷档和1641年清教徒申报表估算,1624~1641年,德文郡共有大乡绅(准男爵、骑士、准骑士)379人,绅士1623人,乡绅总人数为2002人。1625~1641年间,共有100位准男爵、骑士和准骑士担任过治安法官,在可辨别的补助金卷档中,有61%缴纳20镑以上的补助金,而在不担任郡职务者中,只有11%缴纳此数目的补助金。⑥Mary Wolffe,Gentry Leaders in Peace and War:The Gentry Governors of Dev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7~8,22.1609年各郡治安法官应纳补助金,与1596年治安法官应纳补助金相比,多位治安法官应纳补助金低于法律规定的20镑,但仍然担任治安法官职务。1621年,枢密院要求担任治安法官者,必须满足土地年收入20镑的法律规定,否则将被解除职务。此后,治安法官的补助金均高于20镑。⑦J.H.Gleason,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63~64、261~262.由此可见,内战之前尽管存在年收入不足20镑而出任治安法官的情况,但不占多数。
治安法官财富来源的形式各异,不限于地租收入。有的治安法官通过继承获得财富。例如,德文郡治安法官爱德华·贾尔斯爵士(Sir Edward Giles)在宝登(Bowden)的地产,继承自16世纪德文郡最富有的商人。⑧Mary Wolffe,Gentry Leaders in Peace and War:The Gentry Governors of Dev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p.19~20,23.也有治安法官通过商业积累财富。如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的财产便是通过商业途径积聚。威廉·彼得(WilliamPetre)的父亲是制革工人,儿子成为瑞特尔的彼得男爵(Baron Petre of Writtle);理查德·雷切(Richard Riche)的祖父在切姆斯福德兜售货物,而他的孙子出任菲茨沃特伯爵(Earl ofFitzwalter);托马斯·迈尔德梅(ThomasMildmay)的父亲是一名伦敦商人,其子成为男爵,其孙成为沃里克伯爵。埃塞克斯郡出身小乡绅的治安法官,获取财产的途径包括为国王服务、商业经营和勤奋工作。例如,托马斯·罗林斯(Thomas Rawlens)和约翰·塞姆斯(John Sames)是约曼农,在1588年国王借款时出资50镑,两年之后均被任命为治安法官。罗杰·哈莱肯顿(Roger Harlaikendon)曾经担任牛津伯爵的管家,后来买下厄尔斯科恩(Earls Colne)的地产。①Joel Samaha,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 1974,pp.71~73.J.S.Morrill,Cheshire 1630-1660:Coun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pp.233~234.由此可见,随着“价格革命”与“商业革命”的展开,乡绅获得财富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财富数量也迅速增加。
其次,治安法官的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这成为近代早期英国“教育革命”的一个注脚。②Lawrence Stone,“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1560-1640”,Past and Present,No.28(Jul.,1964),pp.41~80.都铎时期,贵族和上层乡绅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孩子送往牛津、剑桥和律师会馆接受教育。以肯特郡、诺福克郡、北安普顿郡、萨默塞特郡、伍斯特郡、北约克郡六郡治安委员会为例,1562年六郡治安法官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仅为4.89%,但到1636年六郡治安法官中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猛增至61.65%。③Mary Wolffe,Gentry Leaders in Peace and War:The Gentry Governors of Devo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24;J.H.Gleason, 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England 1558 to 1640:A Later Eirenarcha,pp.123~245.1562~1601年,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接受大学和律师会馆教育的治安法官增幅分别是27%和40%。④Joel Samaha,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p.74;F.G.Emmison,Elizabethan Life:Disorder,Chelmsford:Essex County Council,1970,p.325.1611~1620年间,威尔特郡新任治安法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高达82%。⑤Victor Morgan,“Cambridge University and‘The Country’1560-1640”,in Lawrence Stone,ed.,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Vol. 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238,229~234.
治安法官进入大学或律师会馆接受教育,不仅得以了解本郡之外的事情,开阔视野,而且又结识朋友,拓展社会关系网络。例如,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剑桥大学成为社会、政治、神学和文化“信息爆炸”的集散地。⑥Victor Morgan,“Cambridge University and‘The Country’1560-1640”,in Lawrence Stone,ed.,The University in Society,Vol. I,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238,229~234.再如,格罗夫纳爵士13岁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接受4年大学教育。女王学院的清教氛围对格罗夫纳造成很大影响。格罗夫纳后来将女王学院的导师称为“精神之父”。⑦Richard Cust,ed.,“The Papersof Sir Richard Grosvenor,1st Bart.(1585-1645)”,Record Society of Lancashire and Cheshire,1996, p.xiv.治安法官在大学与律师会馆的学习,也丰富了他们的法律知识,有助于治安法官依法治理地方社会。
最后,治安法官为加强和巩固个人权威,通过家族、婚姻与政治庇护等方式构筑社会关系网络。治安法官大都由世家大族把持,家族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治安法官的选任和决定治安法官的活动。从伊丽莎白一世继位到内战,一些郡世家大族世代占据治安法官职位。例如,东约克郡博因顿(Boynton)家族、霍瑟姆(Hotham)家族和莱加德(Legard)家族,北约克郡达西家族、乔姆利(Cholmley)家族和高尔(Gower)家族。⑧G.C.F.Forster,The East Riding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23;G.C.F.Forster,“The North Riding Justicesand their Sessions,1603-1625”,p.106.伊丽莎白时期,埃塞克斯郡治安委员会一直由威廉·彼得(William Petre)、理查德·雷切(Richard Riche)和托马斯·迈尔德梅(Thomas Mildmay)三大家族控制。⑨Joel Samaha,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pp.70~71.1640年,萨塞克斯郡治安委员会中,41%的治安法官有父亲、祖父、叔叔或叔父曾经担任过治安法官。⑩Anthony Fletcher,A County Community in Peace and War:Sussex,1600-1660,p.357.这种家族控制的治安委员会模式,在政治不稳定的内战时期,有利于增强治安法官的凝聚力。正如莫里尔所言:“家族或熟人模式……有助于形成一种自然的信任感。”①Joel Samaha,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New York and London:Academic Press, 1974,pp.71~73.J.S.Morrill,Cheshire 1630-1660:Count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pp.233~234.
另外,婚姻网络与政治庇护是家族网络的外延与补充。婚姻成为治安法官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本的重要来源。例如,埃塞克斯郡治安法官罗杰·埃米斯(Roger Amyce)的一个女儿嫁给威廉·卡迪纳尔(WilliamCardinal),卡迪纳尔的女儿嫁给治安法官亨利·阿普尔顿(HenryAppleton)。阿普尔顿是治安法官尤斯塔斯·苏利亚德(Sulyard)的养子,而苏利亚德的姐姐嫁给了治安法官威廉·艾洛夫(WilliamAyloff)。①Joel Samaha,Law and Ord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ase of Elizabethan Essex,p.76.柴郡治安法官格罗夫纳爵士通过婚姻纽带维系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格罗夫纳先后三次娶地方大乡绅的女儿为妻,加上他姐妹和孩子的姻亲关系,格罗夫纳的姻亲网络扩展到柴郡南部和西部。②Richard Cust,ed.,The Papers of Sir Richard Grosvenor,1st Bart.(1585-1645),pp.xii~xiv.同时,政治庇护也有助于加强治安法官之间以及治安法官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同盟关系。卡那封郡治安法官约翰·温爵士(Sir John Wynn)的通信展示了政治庇护的重要性。1610年11月19日,温致罗伯特·利维斯(Robert Lewys)的信中提到,他给潘顿10镑,作为他帮助其子和女婿进入治安委员会的回报。1617年3月,理查德·琼斯(Richard Jones)致信温,他成功阻止了一次解除其治安法官职务的企图。③The Wynnsof Gwydir,Calendar of Wynn(of Gwydir)Papers,1515-1690,London:Humphrey Milford,1926,pp.88,127,131~132.
简言之,治安法官的财富变化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也与治安法官社会构成的变化同步,成为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治安法官财富的增长,有助于治安法官保持经济独立,全身心地投入地方治理。治安法官在大学与律师会馆的学习,不仅丰富了他们的法律知识,有助于治安法官依法断案,而且有利于培养治安法官的“国家意识”。治安法官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加强治安法官在地方社会的权威,另一方面也为中央控制治安法官提供渠道。正是在治安法官的财富、教育与社会关系网络的群体特征中,蕴含了中央与治安法官妥协与合作的本质关系。
总之,16、17世纪是英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段,为18世纪后的“起飞”准备了前提条件。
英国作为“第一个起飞的国家”,尽管在政治上试图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限于“军事官僚国家机器比较薄弱”,使得英国必须依赖各社会阶层的合作,通过和平渐进地改革,实现社会转型。④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页。治安法官作为国家的“官僚”,不领取薪俸;作为地方社会的治理者,通常生于斯而死于斯。治安法官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涉英国社会稳定转型与国家有序治理。
随着“价格革命”和人口增长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近代早期英国加强社会治理,成为一个“高度治理的国家”,国家权力日益渗透到地方社会。⑤Anthony Fletcher,Reform in the Provinces:The Government of Stuart England,p.372.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的渗透依赖治安法官的合作,因此,国家通过治安法官的选任权控制治安法官,要求治安法官服从国家意志,贯彻国家法令。然而,治安法官的地方属性与不靠国家薪俸过活的特点,决定了治安法官的相对独立性。同时,担任治安法官的有限人选也使得中央控制治安法官的选任权大打折扣。虽然二者存在竞争关系,但又相互依赖。治安法官通过教育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获取国家的支持,从而取得统治地方的合法性;中央官员通过与治安法官的血缘、姻亲、庇护等社会网络加强对治安法官的控制,取得治安法官的合作。中央与治安法官在追求社会秩序的共识下达成妥协与合作,以推进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
Appointment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 and their Group Feat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power of Justices of the Peace increased greatly in early modern time,and were backbone power solve problems of crime and poverty.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King and Lord Chancellor made use of appointment to maintain their rights and to enforce Justices of the Peace work hard.However,Justices ofthe Peace did not dependent on state salaries and their limited suitable candidates,determined the limited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Meanwhile, justices of the peace made connections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y means of wealth, education,kinship,marriage and political patronage,which made them to be mutually dependent community.As a result,it leads to compromis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entrality and locality,and provides guarantee for social transition and state governance.
Justices ofthe Peace,State Governance,Power ofAppointment,Social Relations,England
K1
A
0457-6241(2017)06-0057-08
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
2017-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