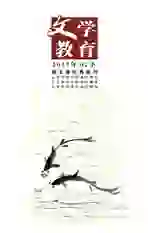从《老炮儿》看全球化的影响
2017-05-09田晓萌
田晓萌
内容摘要:全球化的蔓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变化,也给电影内容带来了革新。在电影《老炮儿》中,全球化成了一种文化断裂的诱因。这种断裂是一种新老规矩的冲突,更是一种钱权与仁义的对立。影片紧紧植根于中国当下普通民众的生存,讲述了老炮儿们在面对全球化这一棘手问题所作出的选择和反应,真实地还原了老北京人骨子里的“侠义”精神。
关键词:老炮儿 球化 断裂 回归
一、“老炮儿”简介
要想弄清楚《老炮儿》这部电影,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老炮儿”这个词。老炮儿,北京俚语,也可以叫“老泡儿”,用来指经常进局子的流氓。当然,这里说的流氓无关道德,只是北京人对混混儿的一种称呼。因此,“老炮儿”在最初是一个贬义词。但如今,“老炮儿”这个词指那些在某一行业曾经风光过的老前辈,至今仍然保持着自尊和技艺,受人尊重,为褒义。
电影《老炮儿》讲述的是当年风光四九城的老炮儿六爷为解救自己的儿子晓波重出江湖的故事。在纠纷中,六爷试图用自己的规矩摆平事件却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这个时代已经有了一群新的 “话事人”,而自己这个顽主的江湖地位已经被撼动, 固守的规矩与方式也已渐渐被时代所抛弃。但最终“老炮儿”们凭着那股与时代相抗的韧劲儿,在一场敌我势力悬殊的较量中彰显了老北京人的精神与情怀。
这个故事正是发生在开放兼容的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来自外部的物质消费刺激逐渐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一些人将这种影响看做是一个浪漫的开端,享受金钱消费带来的快感,释放个人欲望,强调自我价值。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看做是一种侵犯,坚持传统,固守原则,反抗着全球化的吞噬。这两部分人正是电影中的“小炮儿”和“老炮儿”。他们在生活模式上的差异,以及相互间力量与规则的对抗,让我们感受到了全球化下一个城市和一种文化的断裂。还有,更重要的,是老炮儿从血肉中散发出的受人敬仰的侠义精神。
二、全球化下的断裂
电影《老炮儿》是在新北京和老北京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中切换展开的。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影响下的“颓废”的,充满“欲望”的都市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感受到了“执拗”的,坚守规则的传统性风格。之间的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双方在消费、权力上的力量再分配,以及在生活模式中的转变。
1.消费革命
从都市性来看,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通首先引起了消费端的膨胀。人们手中可支配的资本多了,便有了享受生活的基础,试图寻求一种当下的“浪漫”与“闲暇”。因而他们也不再满足于曾经千篇一律的物质生活,希望通过消费来体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彰显自己个体生命的特殊性。(张颐武,2003)电影中新生代混混小飞豪车数辆,日日进出迪厅酒吧,已经将金钱的消耗看作人生享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老炮儿洋火儿,实现了从卖炮仗的小贩儿到掌管整个华北地区造纸厂烟硫酸盐的资本家的转变,兄弟见面约秘书排日程,嘴里张口闭口生意金钱,将拜金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反观与全球化近乎“脱节”的群体,那种“古董”式消费模式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六爷永不离手的枸杞银耳汤,传统的煎饼油条早餐,住的四合院儿,坐的太师椅,遛的鸟儿、滑的冰,已经和当代的消费休闲方式大相径庭。六爷无奈地看着摆在儿子门外的那双时尚的短靴,看着成天进进出出洋酒吧的青年男女,看着一眼望不到顶的摩天大厦。这种“消费”是老炮儿们不能理解的。
这种难以理解的原因就在于两部分人群對金钱和消费的价值认同的差异。对于老炮儿而言,金钱是用来满足人性和仁义的消费。我可以守着没有收益的小卖部,每天过着相同的生活,吃着相同的饭,不在过日子上多花一分钱。但是兄弟有难我要伸出援手,看到乞讨者我要出手相助。总之,花钱不是用来凸显自我,而是用来帮助他人。但年轻人相反,他们的消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为了彰显自身的特殊性,强调自身存在的价值。买豪车,穿奇装异服,出入高消费场合,让别人众星捧月般环绕着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强调“我”的存在。
2.权力分配
金钱和权力往往是相勾连的。六爷曾在电影中感叹道“现在这帮孩子,怎么不讲规矩了呢?只能他们打别人,就不能让别人打他们?”这是六爷对规矩丧失所发出的由衷的愤怒与无奈。但实际上,这并非是原有规矩的丢失,而是金钱强权下的新的规矩的建立。这个世界不再是理为先,义为本,而是钱权者为胜。有权力的人可以打没权力的人,但不准许他们还手。即使出了人命也可以利用权力通过公关和潜逃洗白自己。电影中这些有权之人正是以小飞为首的“小炮儿”们。他们在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后,便试图利用权力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一种只有同等身份的人才能使用的规则,去挑衅和压榨他人。而此时处于权力末端的老炮们只能眼看着自己曾经积攒的势力逐步衰退却束手无措。
在贫富、权力差距越来越大的今天,似乎这种规则已经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潮流。少部分人占有大部分的资产和权力,或用消费力或用控制力制约他人,影响社会。
3.生活模式
电影的冲突是围绕着一辆高端跑车开始的,除此之外当中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也是反映生活方式差异的有力佐证。片中,六爷在自行车上威风凛凛,在制作煎饼车时巧夺天工,却在不经意间败下阵来。为了去见儿子,六爷坐上了现代化的地铁,那种在地铁上的拘谨和转车时的迟缓,显得他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还有在听到Ferrari时的一脸困惑,挺胸抬头的傲气也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无知与心虚……在现代化的一次次冲击下,六爷那可怜又可笑形象印刻在了大屏幕上。
这种生活方式上的转变是全球化影响下的最普遍、最直观的体现。顺应时代的人生活日渐便利,不顺应的人则慢慢举步维艰。直到最后,一个城市变成了“城中之城”,顺应的人包围四周,剩下的小部分人群则圈地围城,正如电影中夹在林立高楼间的老北京四合院,象征着一种文化的割裂。
从符号学认知来看,符号是用来表达、解释意义的,任何意义也只有依靠符号才能进行传递。符号表意不仅是个人之间,而且是文明之间、世代之间的意义行为。(高锋,2016)上文出现的每一幕场景、每一件物品都是有象征性的符号,它映射了全球化后中国的选择。顺应派的将全球化后的变化当做一种新的规则和普世价值,消费享乐,强调个性,尊崇自我,时刻为实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而努力。而保守派则将全球化不断陌生化,固守在四合院内的四角蓝天之中,似乎要隔绝一切来维护自身古老的荣耀与骄傲。这种“断裂”的现象是存在的,也是普遍的,尤其是反映在像“老炮儿”和“小炮儿”这样两代人的身上。
三、全球化下的回归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在除去其带来了外向化、分裂化发展,我们也能渐渐感受到“断裂之后的回归”。这种能够回归不但是一种对本土化境遇的关怀,还是一种对传统化情义的褒奖。
电影中两条对全球化的感情线索,看似是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主义”的对抗,但实则是对中国当下状态的敏锐反应。这种情感带领观众回归到了一个真实的自然的空间,植根于当前民众的生存环境,描述了中国市民在面对如此境遇时所作出的反思与行动。尤其体现了对老炮儿这一本地社群的真切关怀。
老炮儿作为一群被时代抛弃的底层市民,在面对时代变迁时所体现的仍是其固有的情怀和规矩。做人做事时刻将“仁义”挂在嘴边:在兄弟有难时,帮助其赔钱出气攒车;在自己有难时,仍对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在筹钱时还给兄弟200元),在儿子有难时,仍不忘“嗅蜜实为不仁,划车实为不义”的道理。
在规矩上,你小偷可以偷钱包,但你得把人家身份证寄回去;你城管可以没收煎饼摊,但你不能打人;你年轻人有钱有权可以在路上横行,但你不能对着比你老的人嘴里不干不净。这是老炮儿的规矩,是六爷的哲学。这些仅存于四九城胡同的“老规矩”向你展示了盗亦有道,一码归一码的生存模式。
这种模式,是传统底层民众在面对全球化后的选择。此时的全球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时代背景,而是反映在社会和电影中的棘手问题。电影将这个问题放在了一个个具体的情境中,观察老时代的人们在遇到现实问题时所作出的决定与反应。
老炮儿们的决定就是坚持属于他们时代人的尊严与骄傲。就像老舍在《四世同堂》里說的,“可是他豪横了一生,难道,就真把以前的光荣一笔抹去,而甘心向敌人低头吗!”当然不能!尽管老炮儿身体已垮,将校呢军大衣已皱,二八钢圈自行车已老,日本武士刀也不再光亮,但仍要挺直腰杆,向强大的敌人前进,挽留那份属于自己的,属于曾经时代的仗义情怀。
正如颐和园后野湖中那棵独自被冰冻着的枯木,它是不寻常的,是弱小的但却又是孤傲的。它和奔跑在冰面上的六爷一样,正用自己残留的最后一份尊严,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与对面的敌人抗争,也与整个世界抗争。此时此刻,无论是枯木还是六爷,都变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属于传统的情义和道德的回归。
总之,全球化的蔓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变化,也给电影内容带来了变化。消费端的拉动使得一个文化的北京正在断裂。高楼大厦与红砖绿瓦,灯红酒绿与曲径幽深,“老北京”与“新北京”复杂融合的景象,展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和一个旧的时代为了吞噬对方而做出的各自挣扎。不同阶层市民的生活情况就是最真实的反应。新规矩与旧规矩的斗争,钱权与仁义的对抗,顺应全球化一派与反抗全球化一派在一个个小的场景中将自己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也就是电影内容的改变。不再追求宏大的叙事,而是回归到最朴实的市民选择和经验。这种回归,能够从最根本上还原最真实的一面,也能让我们从心灵的最深处引起对老北京情怀的共鸣。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