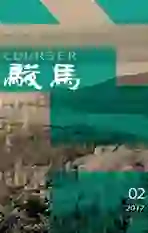最童年
2017-05-08卢国强
卢国强
杀猪
腊月初十这天上午,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震落了大口钦人民公社艾屯大队第一生产队隐没在蒸腾江雾里的白花花的树挂。我和几个小伙伴一大早就包围了生产队的伙房,亲眼看着张向荣把一尺多长的杀猪刀捅进那头已经养了两年多的克郎猪的胸膛。紫红色的血水顺着花瓣样的伤口流到搪瓷盆里,张向荣放下屠刀,抄起一把高粱杆熟稔地搅拌起来。
伙房连着牲口棚新搭了个大灶,四百多斤的大肥猪压弯了大铁锅上的门板,浇上开水,一股难以名状的腌臜气味随着脱落的猪毛弥散开来。这种味道与后来开膛、破肚、摘下水(内脏)、洗肠子的气息合成在一起,持续而强烈地刺激着社员们的味蕾神经。这独特的气息,一年一次,把每个清癯的脸颊都涂成绯红。
割猪肉的时候最为热闹。有人迫不及待地把手掌按在刚割开的肥膘上,“四指膘”这是对饲养员的表扬,透着过年特有的喜庆。然后把手指肚上的油花反反复复涂抹在红肿的手背上。不是为了美容,而是在治疗冻伤。
大人们称完猪肉回家剁馅子、包饺子、做红烧肉,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并不散去。我们的手和脸早被冻得通红,新衣服还没有上身,袄袖上油光锃亮一道鼻涕印。看起来像是心不在焉地在伙房外玩耍,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一直在观察着牲口棚里的进展,我们在等待分享最后一道大餐。
此时张向荣的角色由屠夫转变成厨师。牲口棚里的大铁锅已经刷得干干净净,倒上水,添上柴,没卖出去的排骨、脊骨、腿骨、里脊肉(那时候肥肉不但能吃还能靠油,瘦肉反而没人爱要),连同灌好的血肠一起下锅煮。
牲口棚后墙有个狭小的窗口,没有窗扇,四边用木棍撑着。平时,牲口棚里的马粪和牛粪就从这个窗口被扔到生产队的后墙外。现在,冷空气把铁锅里溢出的热气堵在出粪口,四框和墙皮上的稻草茬挂满白花花的树挂。一袋烟的功夫过去,浓郁的肉香伴随着滚滚蒸汽冲出牲口棚在寒冷的东北平原上恣意飘荡。所有村子的狗都兴奋地吠叫起来,有几只没栓住的,被我们踹在身后不安地雀跃。
傍晚十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了。张向荣把烀熟的骨头捞出锅,稍晾一下就动手撕扯骨头上的瘦肉,烫得受不了就在嘴边吹一吹,顺便塞一块肉在嘴里大嚼,嚼得满嘴流油。我的嘴与他的嘴一起蠕动,咽下的却只有口水……
张向荣是我家的邻居,岁数比我爸小,个子却比我爸高,遇到婚丧娶嫁,他常托举着摆满美味佳肴的长方形木盘,高喊着“油着油着”从我们头顶掠过。由于长时间高举右臂,他的右肩要比左肩高出一块。就是这个“栽楞膀子”的张向荣今天再一次刺激了我,他近水楼台先吃肉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上初中时,我还把杀猪匠作为偶像顶礼膜拜。
很快,撕下的瘦肉盛满了整个搪瓷盆,剩下的骨头则一根根划着完美的弧线落在地中间一只又脏又旧的土篮子里。我从来不对盆里美味有所奢望,也不知道这些瘦肉的最后去向,我瞪得发绿的眼睛紧盯的是盛满骨头的土篮。我看见张向荣同志瞄了孩子们一眼就善解人意地拎起了那只土篮,然后以极其优美的动作把里边的骨头从那个挂满雾凇的出粪口倒了出去。我和伙伴们就像听到发令枪响的运动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式翻跃了生产队后墙。连那几条馋红了眼的狗都被我们敏捷的动作惊得目瞪口呆。
后墙外攒了整个腊月的大粪堆已经不知去向,银光闪闪的雪地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香喷喷的大骨头棒、小骨头棒、肋条、肩胛骨、嘎拉哈……
我们饿狼一样扑上去,也不管干净不干净,连雪带泥抢在手里,然后开始贪婪地撕咬、咀嚼、吸吮,无边的幸福与不可名状的快乐,连同骨头上的油水和融化了的雪水涂滿了每个红彤彤的小脸蛋儿。
其实,这些骨头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肉,却有一种特殊的滋味萦绕于心头。仔细回忆,原因出在土篮子上。这种柳条编织的农具在农村非常普遍,几乎每家都有几只,人们用它装土、盛菜,我还用它拣过粪。牲口棚的土篮是盛草料用的,但同时也用它出马粪。所以,我啃的骨头除了浓郁的肉香之外还夹杂着淡淡的甜杆味以及马粪所特有的土腥味。这并不让我反胃,在物质极度困乏的年代,味蕾对肉欲的强烈需求掩盖了所有的异味,而时间既像筛网也像一把锉刀,过滤了所有杂质之后,把那些经典的瞬间,在脑海深处篆刻成永恒。
冻饺子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民间也开始置办年货。那时,只有身上穿的和头上戴的要在集上买,比如妹妹在三十晚上才能上身的平纹方格花上衣,就是妈妈花两块钱扯回二尺布,用自家的缝纫机给做的。不过,她一天要给小朋友看N遍的红绫子到是一个半成品,毛边没扦,丝丝缕缕飘飘扬扬地系了一个正月。而小朋友们,每人怀里都揣一个豆包或者冻秋梨,一边滑冰一边把冰凉的冻秋梨啃出一道白色的沟槽,还有硬邦邦的黏豆包,压得扁扁的小饽饽,都被啃出绛紫色的小豆馅。
这些面食都自己做,蒸熟后冻在雪地里,吃的时候用饭锅一蒸,非常省事,特别适合寒冬腊月天天打麻将玩扑克的东北闲人。最费事的要属包饺子。我老家有包冻饺子的习惯,小年过后,家家叮叮当当剁馅子,最少两大盆,有白菜馅的、芹菜馅的,更多的是猪肉酸菜馅。我还吃过妈妈用冰得拔凉的手给我切下的酸菜心,“这家伙,口急得跟捍孩子老婆似的(害口的孕妇)”,妈妈总是这样说。没有恶意,挺幸福,好像她自己吃了一样。条件所限,那时候我没有吃过三鲜馅或者羊肉馅饺子。包饺子时邻居们互相帮衬,一边干活一边唠家常。内容多半是婆媳矛盾、邻里纠纷、男女关系,要不就是饺馅子咸了淡了,还有谁包的饺子一冻就开口等等。诸如肉多还是菜多这个敏感话题她们一般回避不说。因为饺馅子质量直接反映主人的生活水平,说白了,日子过得好不好,从饺馅子里就能看出来。这些妇女总是回到自己家里才会对别人家的饺子馅品头论足盖棺定论。所以,这几大盆饺馅子也是主人的脸面,一般人家舍出老本也会把这顿饺子包好的。
如果说杀猪请客是老爷们头年的一次聚会,那么包饺子就是村里大姑娘小媳妇的一次party。如今,条件好了,她们不但要在完工后喝上几杯,有时候还会跑到歌厅吼几嗓子。但是,当时没这个习惯,也没有这个条件。包好的饺子齐刷刷码在盖帘上,放在墙头,或者雪地里,抽袋烟的功夫,饺子就冻成冰蛋蛋,主人收起来,装进编织袋,放在仓房藏猪肉的大缸里。这便是整个正月的主要吃食。腊月里呢?憋着呗!秫秆穿成的经线笔直通透,饺子站成的纬线整齐划一,在那些没油水的日子,雪地里,数百枚,亮晶晶的,香气四溢的饺子,真是吸引我们的馋虫。
这天晚上,轮到杨子芳家包饺子,半条街的老娘们都去他家帮忙了,一群小孩牙子无以为遣,趁冻饺子的人不注意,用衣服偷出来一包,就在小卖店的铁炉子上烤了吃。杨子芳是村长,他家的饺子肉多油大,香得不得了。又有人把刚掏来的家雀放在一起烧,外焦里嫩香气扑鼻的饺子与滋滋冒油的家雀肉就成了那个时代最丰盛也是最美味的夜宵。后来,如法炮制,每家包饺子时,我们都能在第一时间尝鲜。即使被主人发现,顶多亦嗔亦怪地骂上一句,这些饿痨,馋鬼!无伤大雅。这样,偷冻饺子就被视为不会被惩罚的调皮行为。直到吃到赵奎武家的时候,事情发生重大改变。我们发现,他家的饺子馅是用大豆腐做的,一点肉丝也没有。“这也太难吃了”,“扔了吧”,“把村长家的拿出来煮!”大家七嘴八舌,都忘了,他本人也在吃饺子的队伍里。赵奎武黯然起身,转身离去,炉盖上有滴眼泪“嗞”地一声被蒸发掉。大家这才意识到说错话了,追到门外,赵奎武已经不知去向。赵奎武家境不好,但不影响我们做朋友,因嘴馋而伤害朋友的自尊,让我们十分难堪,也很后悔。我们把剩下的饺子一股脑扔进猪圈。后来,我们再也没偷人家的冻饺子吃。
秧歌
在电视机还没普及,麻将也未复兴的特殊时代,没有什么能比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东北大秧歌更具吸引力了。
正月里,路上的雪还没化净,几匹挂着红花响着脆铃的高头大马拉来几付爬犁。有人点着“二踢脚”,鞭炮声也噼里啪啦响起来,爬犁上下来一群人,都很年轻。他们头上花枝招展,身上怡红快绿,脸蛋一个个都红扑扑、粉嘟噜的。当然,擦粉是一方面,天冷冻的也有可能,他们下爬犁就猛劲跺脚,用手哈气。等他们活动开身子骨,闻讯赶来的大人小孩已经把街筒子包围了。唢呐响起,重鼓捶下,队伍一分为二,一支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一支是一水儿水儿的大姑娘小媳妇。他们时而统一姿势、步调一致、节奏鲜明地向前开进,时而止步后腿、耸肩飞眼、互相挑逗,他们会突然一个转身跳到对方的脚下,瞬间完成队伍位置的互换,其时间动作配合之默契,真是天衣无缝。到了学校的操场上,锣鼓愈发局促紧密,两支队伍互相穿插在一起,分不清个数。只看见红绿两种彩扇蝴蝶般上下翻飞,让人眼花缭乱。最后,两支队伍卷成一颗大白菜,所有的彩扇在最后一声重槌下陡然展开,一朵硕大无比的向日葵在人们的欢呼中灿烂开放……
只见队长举着一沓人民币高声喊道:东家赏钱四十!大家齐声回道:谢东家赏钱!其实大家都知道东家只赏了二十元,喊四十是出于礼貌,这是扭秧歌拜年的规矩之一。不过钱多钱少没人计较。过年图得是喜庆,赚得是逍遥与快乐。
这期间,佝偻腰,粘了一脸猴毛的孙悟空和挺着大肚皮的猪八戒一直在打架。他们的金箍棒和九齿钉耙戳到人们眼前的时候很有分寸,让人感觉武功十分高强。唐僧一个跟头也不翻,就一个动作,双手合十,念咒。这些在小人书中才能看见的传奇人物深受孩子们喜欢,有调皮的男生会突然伸手摸一下猪八戒的肚皮,然后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喊:是大车里袋刷上油漆做的!
然而,让我着迷的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她踩高跷时险些摔倒,我及时扶了一把,换来她回眸一笑,那双美丽的丹凤眼瞬间就钻进我的心坎里。虽然那时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当她匆匆跳上马爬犁赶向下一个村子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小心脏霎时就被她掏空了。
这种感觉一直蔓延到正月十五。是夜,圆月当空,姑娘所在的秧歌队手持各种彩纸扎成的灯笼,火龙一样涌进村。按东北民俗,正月里扭秧歌(扮成古人给人拜年),一定要在月圆之夜用灯火把附着在人身上的妖魔鬼怪带走。
我用麻绳栓住一个空罐头瓶,里边点燃一根红蜡,用木棍挑起,就成了我的灯笼。在粉红色的雪地里,在一片火光的长龙中,我紧紧跟在她的身后,跑过一村又一村……
秧歌队给所有的村子都送完了灯,最后,队伍鱼贯来到松花江边,她们把手里的彩灯往卵石滩上一扔,熊熊大火立即燃烧起来。那个丹凤眼的姑娘先是脱下戏服扔进火堆,然后小心翼翼地摘下头上的花冠,恋恋不舍地扔进去,火光忽地爆燃,一个标准的男儿身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捧起被火烤化的雪水,洗去了脸上的油彩,然后和其他伙伴疯狂地打闹起来。被小丰满发电站搅热的松花江水浩浩汤汤,两岸的树挂在火光里跳舞,月光铺在江水里,晃晃悠悠,想站却站不起来。
我失落地跌坐在卵石灘,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江风袭来,湿透的后背凉涔涔的,我打了个寒战,赶紧把手里的罐头瓶放进江水里。红烛摇曳,江波荡漾,我透明的罐头灯笼就这样载着我梦幻般的初恋漂向远方……
稠李子树
那是一团团、一簇簇奶白色小花,从村子东头潮水般漫过村西的河堤,把一缕缕黯淡的香气浓雾一样揉进村民的梦乡。炎热的夏天,无边的翠绿淹没了整个村庄的同时也窖藏了这个村庄的心事。秋分一过,一嘟噜一嘟噜黛青色的果实吸引了无数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它们玲珑婉转地鸣叫,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用尖尖的喙敲开稠李子林里发酵的秘密。
鸟儿跳跃的高度我无法企及,但是所有能够攀援到的树干则是孩子们的天下。尽管初秋的果实青嫩苦涩,每次上树,我依旧会把舌头吃得又黑又绿,涩得回不过来弯。直到霜降过后,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梢依然能发现熟透的稠李子,像葡萄,像那些鸟雀的眼睛,时刻勾引着我的童心。
采摘果实的同时,我会折下纤细的枝叶编成草帽,然后像潘冬子那样,隐藏在稠密的绿荫里,即使妈妈来找吃饭也不应声。稠李子树下,有一条豆油一样黏稠的小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不顾父母的告诫,经常赤条条扎进河水里游泳,或者摸鱼。杨金先精通渔事,即使三九天,树上结满了白花花的树挂,他也能凿开冰眼把鱼舀出来。而整个夏天,他就跟老僧人一样定坐在树荫下钓鱼。他串蚯蚓的鱼钩是用烧红的缝衣针弯成的,我没有,但是我有更简易有效的方法:用罐头瓶或者洗脸盆蒙上塑料,上边抠一个小洞,塞进一把苞米碴子饭,沉进水里,第二天清晨,准能收获一份惊喜。有一次竟然俘获一条一尺多长的鲶鱼。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一条肥硕的大嘴鲶鱼对于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无疑是最奢华的一顿美餐。
我俘获的那条鲶鱼跟后来知青们淘出的鱼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们筑泥为坝,把上下游分别堵死,然后用两只水筲轮番往坝外舀水。一上午时间,河水退到了膝盖以下,浑浊的泥水里,浮起无数只张大的嘴巴。我左抓一把,右抓一把,经过无数次失败,终于逮住一条比我胳膊还长的鲶鱼。出水的瞬间,我和这条不停挣扎的鲶鱼一起摔倒在泥泞的河滩上。那天,像这样的鲶鱼,知青们足足捉了三水筲。
尽管那时候的日子比稠李子树还稠,但是有酸涩的果实和取之不尽吃之不竭的鲶鱼,我们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
稠李子树消失的时候刚好分产到户,老队长用他最后的权力砍伐了整片树林。理由是有孩子上树摔坏了腿,实际连村里的傻子都知道他要用卖树的钱给儿子娶媳妇。九八年很快到了,松花江水汹涌上涨,小河上游的水库开始泄洪,守护村庄几百年的稠李子树已经消失,就连河堤上盘根错节的树根也早已被村民们刨出去烧火了。面对滔滔的洪水,村长只能命令所有村民转移到山坡上避险。一夜暴雨过后,大家清点人数,唯独不见老队长,回到村里寻找,河堤已经被洪水吐开一个口子,在五公里外的淤泥里,人们找到老队长的尸体。他紧握一把铁锹,圆睁的双眼里写满了懊悔与不甘。
十年后,村子周围密植了很多杨树,红砖碧瓦重新被葱翠隐藏起来,那种朦胧葱郁的美似曾相识。鸟雀却已不多见了,小河瘦成了一条线,深深地陷进村南的庄稼地里。鲶鱼早已绝迹,还有网,两鬓斑白的杨金先每天像举行某种仪式似的定时起网查看,仿佛不是为了吃那几条树叶大的小鱼,而是在打捞我们沉在水底的那些陈年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