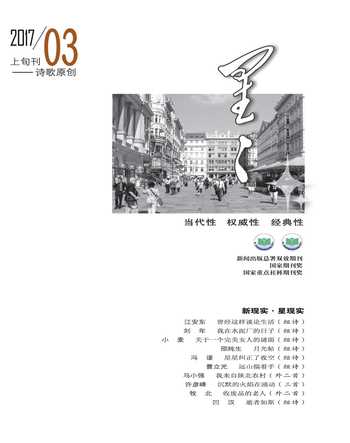更上最高意义的欢乐
2017-04-29芦苇岸
芦苇岸
孤绝、温润、盈动、阔远……作为灵魂事业,诗与非诗的界定,有谱!
人所共知:在全球化进程的诗歌背景下,在异景纷呈的精神世界中,诸元活力的源源注入,使得模糊无定的诗歌边界渐行渐远却又前所未有地砥砺于生活本身。新世纪以来的当代诗歌,因保有悖行习见的纯质,而一直冒尖于文学前沿。
是的,无论见与不见,诗歌的存在依然强大,她是洪荒时代滚滚轮毂的一侧,在默然中展现虚无的力量。她直接作用于人,在人的灵魂深处发酵,去伪存真,让美接近真美,让精神愉悦更上最高意义的欢乐。
应该看到,价值多元的现实,诗歌不再大富大贵,也不再是喧嚣而炫目的堂皇。诗人的执着坚守与日益精进,让诗歌深度融汇于全球性的文学语境,充分呈现汉语现场的共生性繁荣,又强大地持有跨越自身历史语境的节律。尽管纷纭的外部世界冲荡剧烈,诗却依就不失高贵的矜持与责任担当。
如今就发展性而言,诗的独立轨道延伸更远,承载量更大,容纳力更强。在不可避免的花拳绣腿和泥沙俱下中,诗的艺术品位,也然升格显赫,诗歌的前行,从未像今天一样豁然开朗:哲思劲道,视野辽阔;截杀自我复制,惊醒于诗歌淤结的沉疴。尝试着赞美残缺的世界——如扎加耶夫斯基般者,不乏其人。
人在诗在,诗歌没有幸与不幸。曾经这神领的物语,已经普渡苍生,在人间落脚,呵手围炉,自得其乐。博尔赫斯说:“完全没有必要认为诗在文字里、在思想里,或者说在对宇宙的美学理解里。我个人在上了年纪后,觉得诗基本上就是在句子的语调里,在词的换气处。”
显然,这是最高层次的诗,如同白居易说的“花非花,雾非雾”一样。但是,跳过文字、思想和宇宙美学的诗,得有“上了年纪”的历练作为铺垫,等达到诗就是说话的高度,达到向自然自言自语和向生活窃窃私语的境界,那腔调的本身及其腔调的转折处,诗,活得很自在。
通常,诗思阻滞,貌似难以逾越的困境,多于畅达的人生。当一重“现实”挡住了精神“去路”,世人会自动止步,浅尝辄止者,比比皆是。而诗人,则会苦心寻求另一重“现实”开启的通道。荷尔德林训导有先:“如若大师使你却步,不妨请教大自然。”哲人的指点,往往被视作为诗人亮灯。
自修灵魂课,探知人性深处的种种可能,还原自然与社会、人类与生活的真切关联,在分行的细微建构中挖掘内心世界的审美经验,祈得新发现,为新美的再生如醉如痴。
此在,何所往,亦无所不往。
“美是存在的在场。存在是存在者之真……远行人须让大地的美呈现出来,只要作為诗人,他们就必须说出真实……诗人的天职是在对美的筹划中让美的东西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在与荷尔德林的灵魂对话中悟出上述真言。王国维也认为“美之极致”乃“有境界”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之经典结论。
让作品说话,不是自贴标签的装饰,而是鉴照人心纯赤的禅定。如果语言的气味和修辞缔造的秩序,是诗人内心最可靠的动力之一,那么这样的诗歌,也可以悱发凡心,在更广阔的人文景观中,拥有一席之地。我为此也在努力,每一次换行,都是重新出发。
在真实的诗歌境遇的无力感中,以及当下市井語言面貌的出格与失范的影响下,有屏蔽喧嚣现场的勇气,敢于直面消解精神气象的人为圭臬,在文本中探测和打通精神的远方,实乃真经要义。
长期的一线创作实践,使我发现,只有诗歌,能够让满布污点但还不至于朽坏的灵魂得到安顿。因此,找寻诗意,就几乎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全部。通过文字的诗意捕获而发出温暖的光芒,照见时间黑暗的部分,为之播撒灿若星辰的种子,无疑是一份人生美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