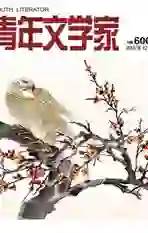语言陌生化
2017-04-26徐妮娜
摘 要:蕭红小说以其独特的情味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语言陌生化是成就她小说独具一格魅力的重要因素。生动的修辞、巧妙的方言、语法的突破,构成了萧红小说的语言陌生化倾向。正是这种陌生化手法的运用,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加强了小说的审美效果,体现了萧红独特的审美追求。
关键词:萧红;小说;陌生化;语言
作者简介:徐妮娜,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6-0-02
1914年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陌生化”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阐释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所谓“陌生化”,即在文学创作中,将生活中本来熟悉的、司空见惯的对象通过艺术的手法变形,使其变得“陌生”起来。俄国形式主义者对“陌生化”理论的研究,强调了语言陌生化的重要作用。在他们看来,语言的陌生化是实现叙事陌生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被称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百万字的珍贵文学遗产。在萧红小说中,陌生化的语言,是她作品独一无二的标志。
所谓“陌生化”的叙事语言,就是指文学语言与生活语言有一定的距离。接受者在欣赏时会感受到一定的阻滞性,延长了接受者的审美时间,从而体会出小说语言的独特魅力。萧红擅于用陌生化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事物,使用一些不合语法规范的言语组合方式,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生命力。总的来说,萧红运用陌生化的手法,使其小说的语言呈现出一种自然稚拙的状态,进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言世界。
一、生动的修辞
在萧红的小说中,一些修辞格的巧妙运用增强了其文本的语言魅力。如她在《生死场》中写道:“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1] 这句话中她用动物的声音来比喻人的声音,既表现出了麻面婆说话声音不清不楚的模样,又表现出了麻面婆愚笨呆傻的样子。又如“她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又无望……她的腿像两条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里她连续用“患病的猫”、“竹竿”、“直角”、“灯笼”这样一系列生活中的物体来比喻月英,把月英此刻悲惨可怜的模样描写得淋漓尽致。这样新颖别致的修辞,使接受者如见其形。再如“李二婶子的喉咙变做细长的管道,使声音出来做出三角形。”作者为把本来没有形状的声音比作三角形,原来不可见的声音顿时有了形象感。再加上被比作细长管道的喉咙,接受者好像既看见了“李二婶子”又尖又细的三角形的声音,又感受到了“李二婶子”声音的棱角,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自然地交织在一起。这样新颖别致的修辞,使接受者如见其形,如闻其声。 萧红善于选用设定场景中的日常物品来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做比。“人”“物”难辨的状态,深刻揭示了“人像动物、物品一样麻木”的主题。运用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来和作品中的人做比,既巧妙自然,又打破常规,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特有的感觉。给人一种陌生的新鲜感,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在萧红的小说中,运用陌生化的修辞方式来加强语言感染力的例子不可胜数。在《呼兰河传》中,排比和反复这两种原本应该是属于诗歌的修辞手法却被萧红在小说中反复的使用。如“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它。”这种随意性很大的排比句在小说中大量出现。相似的结构,整齐的形式,增加了小说的诗化程度和散文化程度,读起来回味悠长。在语言的有趣排列中,不仅流露出作者此刻轻松愉悦的心情,更为小说增添了一点温情的色彩。而这一部分温情的语言与小说后部分所描绘的悲惨又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衬出小说主人公悲戚的心境,带给接受者一种悲凉的审美感受。又如:“我家是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我家是荒凉的……”萧红在第四章第二节中反复强调“我家是荒凉的”这句话,渲染了荒凉的氛围,接受者在一种难以掩抑的悲凉感中,感受到了叙述者对爱的渴望。借助排比的修辞手法产生的回环复沓的效果,既强化了小说充满诗意的情感氛围,又奠定了小说后部分悲凉的感情基调,感人肺腑。
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萧红反复的使用结构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句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手法的运用使得作品层次分明,强化了作者的情感体验。而且多用于诗歌的排比修辞手法被萧红在小说中熟练运用,这一点加强了小说的节奏感,具有“一唱三叹”的特殊表达效果,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张力。在萧红的手里,小说的叙事功能被放逐,抒情的功能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因而她的小说语言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抒情性的诗意感。这种诗意的状态,是与之前的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的地方。这也是萧红善于运用陌生化手法处理修辞的结果。
二、巧妙的方言
“语言是人类与动物分道扬镳的最后也是最重要、最本质的标志,是创造性的活动和人类精神活动的第一次肯定。”[2]语言是最有独特性、区别性的文化要素之一。方言是由于地域不同形成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它与某一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在各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中,作为一种带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载体,方言承载着厚重的地域文化,折射出不同地域下的人们不同的性情和特点,反映不同的文化模式、文化心理和文化积淀。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恰当巧妙地运用方言更增添了作品的无限感染力和文化内涵。萧红小说中对方言的自觉巧妙运用,也是其作品独具魅力的地方。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真实的还原了儿时在呼兰城的生活,随着独特的呼兰方言的描述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的呼兰风俗味。如“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的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 野台子戏; 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等这些 都是东北当地特色文化活动的特殊表达。作者运用这些东北特有的词汇和语句表达,不仅刻画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还在特有的语调和语词之间透露出呼兰当地的乡风乡俗,描绘了一幅异于他乡的生活风景图。
老舍曾這样强调文学语言与生活的关系:“不要只在语言上打圈子,而忘了与此无关语言血肉相关的东西——生活。字典上有一切的字。但是,只抱着一本字典是写不出东西来的。”[3]萧红在创作中注意到了对富有自己故乡特色的生活化语言的巧妙使用,如:
“小老婆,你真能败毁。摘青柿子。昨夜我骂了你,不服气么?”
“金枝站在门限向妈妈问:“豆油又没了,装一点水吧?”
“这又是一片洋人打仗。你看‘老毛子夺城,那真是稀里哗啦!”
“那地方的晚霞是很好看的,有一个土名,叫火烧云。”
“看得人,正在寻找马尾巴的时候,那马就变靡了。”
“从此那磨坊里的磨倌就看不见天日了。”
“败毁”等于胡闹、败家,“门限”等于门槛,“变靡了”就是变没了,这些词语都是萧红老家呼兰当地的方言;“老毛子”指的是外国人,“火烧云”就是晚霞,“磨倌”就是磨房的工人,这些都是呼兰当地特有的称呼。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呼兰作家,萧红在进行创作时,势必会把呼兰的生活带到她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的“萧红气”,给整部小说罩上了属于萧红的东北呼兰味道。方言在文本中的巧妙运用,塑造出了生命的质感,使得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有温度,有情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粗粝的生命体。萧红把人们从自己惯常的文化模式中领出来,去感受呼兰的文化环境,感受呼兰河的生命的真实。
三、语法的突破
萧红对语言保持着自己独有的感觉,文学评论家胡风就曾批评《生死场》的语言,说它“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4]萧红小说总是试图跳出原有的语法束缚,自由地行走在语言中。如:
“乱坟岗子上活人为死人撅着坑子了,坑子深了些,二里半先跳下去。”
这句话打破了原有的语法规范。按照语法规范,前半句应该是,“活人为死人在乱坟岗子上撅着坑子”。萧红在这里加了一个语气副词“了”,使得整句话变成了一个口语似的时间定语,反衬出整个环境的恶劣、气氛的压抑。尽管这句话不符合语法规范,但却与上下文所描写的氛围完全一致。接受者凭着阅读直觉接受了这句话,也完全理解了这句话中的逻辑含义。这不循规蹈矩的语句表达了作者难以明白表达的情绪,刻画了语言背后人物麻木的心理状态。
“王婆被凉风飞着头发, 在篱墙外远听从山坡传来的童谣。”这句话也是一个不规范的被动句式。王婆的头发应该是被风“吹”的“飞了”起来。作者在这里跳过“吹”这个动作而直接强调了“飞”这个结果。如此搭配表现了一种凝练的动感,生动地表现出了“王婆”此刻麻木承受的状态。
“他们心中的悲哀, 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4]这句话在搭配上也存在着不通顺的问题,抽出句子主干即为“悲哀去观望”。但是由于作者连续的几个定语的增加,让阅读者感受到了一种不能呼吸的窒息感。“悲哀”的凝重感和“观望”随意的态度的对比,在不经意间营造了一种悲剧的氛围。
这种越轨的笔致在小说中屡见不鲜。萧红忠实于自己对于文字的特殊感觉,所以在小说语言的处理中,她并没有因为语法规范束缚自己,这才有了“萧红式”的小说的独特情味。对于语法规范的突破,让萧红小说有了更多营造特殊氛围的可能。
在《<生死场>序》中,鲁迅这样称赞过萧红小说的语言:“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添了不少明丽和新鲜。”[5]在鲁迅眼里,萧红小说的语言因其越轨的笔致,增加了语言的明丽感与新鲜感。赵园也曾这样评价萧红的语言:“这是一些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常常显得不规范的文句……萧红的语言感在于,她能让她组织的文字,其‘组织本身就会有意味。她以‘文字组织捕捉‘情调,为此不惜牺牲通常认为的‘文字之美,却又正与‘情调一起,收获了文字之美。”[6] 在赵园先生看来,萧红的小说语言是使用一种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正是这种独特的组织语言的方式,使她的小说语言独具“情调”。运用陌生化手法对语言的修辞、方言、语法规则进行处理,再加上她浓浓的情思,使得萧红的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带给阅读者一种新鲜的阅读体验和陌生的审美感受。这正是萧红小说独具韵味的地方,也是萧红小说最出彩的地方。
注释:
[1]萧红.萧红作品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以下选文皆出自本书,以下不一一赘述).
[2]刘守华.文化学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128.
[3]史青玲.《骆驼祥子》语言陌生化手法及其在翻译中的再现[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
[4]胡风.《生死场》后记.胡风评论集(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96.
[5]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414.
[6]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赵园自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