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远去的父亲方厚枢
2017-04-25文|方群
文|方 群
怀念远去的父亲方厚枢
文|方 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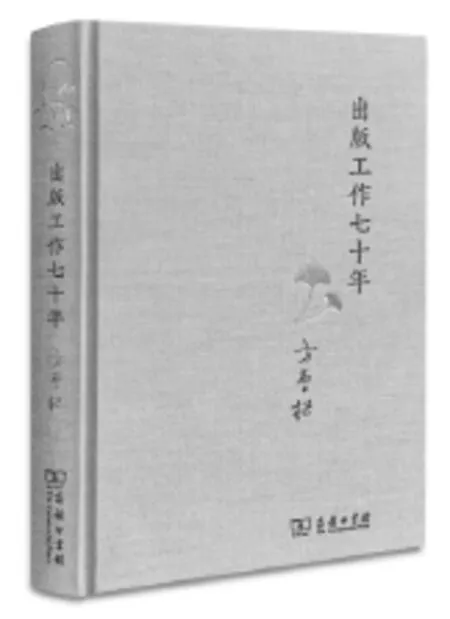
方厚枢著《出版工作七十年》书影
清明雨纷纷,泪眼思故人。两年前的清明节,我为先后辞世的父母落葬。墓碑前翻开的大理石书页上,父亲的一面镌刻着“出版为业著书修史,笔耕一世常伴书眠”的铭文。一本父亲临终前写就却未及亲见的《出版工作七十年》被安放于墓穴中,将永远陪伴着父亲。
又近清明,我对父亲的思念始终萦绕于怀。他生前曾为黄洛峰、叶圣陶、许力以、王益、陈翰伯、边春光等十多位先后故去的编辑出版界前辈、专家(其中很多曾一起工作过)撰写比较详尽的追思纪念文章。自从父亲走后,我也总想着写些寄托哀思的文章。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我努力搜寻记忆中的父亲,反复出现的却总是他那伏案写作的身影,一幅几乎静止的画面。回忆过往,由于父亲生性内敛少言,整日埋头工作,很少与家人沟通交流,所以,我只知父亲一辈子在出版行业工作,而具体从事什么却知之甚少。
于是我想,从父亲留下的书中或许能寻觅到点滴。我曾无数次翻阅父亲临终前完成却未及等到出版的那本《出版工作七十年》,从字里行间探寻父亲是如何从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练习生,一步步成长为编辑出版行业专门家的心路历程,感悟他那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翻开《出版工作七十年》一书,宋木文先生(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所作的序《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首先映入眼帘,其中写道:“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从建国到新时期的几十年里,凡出版的事,只要问他,他都能说出准确的情况,提供详实的资料。而对于他经手的工作,无论自己分管的、领导交办的、同事委托的、单位求助的,他都能不辞辛劳、不事张扬地做好,使领导放心、同事满意。他是在完成任务中不忘收集积累资料,结合工作任务又不忘进行研究的。他似乎无时不在收集资料,无时不在进行研究。他对辞书的研究、年鉴的研究、出版史的研究,都是‘边学边干边研究’,是在完成任务中铸就的专门家……”宋木文先生曾是父亲的直接领导,从其序文中,不难看出宋先生对父亲的工作以及为人有较多的了解。他称父亲为“出版史家”,如此高的评价是我未曾想到的,也促使我去重新认识我的父亲……
父亲少年时期就爱好读书作文。1940年,在上海读书期间,他曾应约主编《新儿童》小报。之后写的一篇纪实散文《在大别山下》,投寄至《大公报》副刊,被采用发表。父亲17岁时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偶有机会到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做练习生,从此决定了他与书为伴的生涯。每天身处“书林”之中,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书学习,汲取知识。借助馆内丰富的辞典和工具书,父亲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相当于上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20世纪50年代初,作者一家人在公园合影
1951年,父亲从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调到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我们全家也随之迁居北京。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曾带全家人一起去过一次中山公园,还单独带我看过一次卓别林主演的电影、一次苏联大马戏团的演出。除了这几次美好的记忆,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每天下班吃过晚饭,就坐到桌前开始写字。那时,全家人挤在两间不大的房子里。晚上家人就寝时,父亲便用旧报纸把电灯围起来。有时半夜醒来,看到父亲还在灯下埋头写着,他那透过灯光投在墙上的身影令我至今难忘。
1962年,父亲调入文化部出版局工作,进到国家出版事业的最高管理机构,视野开阔了,工作也更忙了。特别是受到老同志的启发影响,他萌生了有朝一日研究写作出版史的想法,并开始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资料。
四年后“文革”爆发。过了一年,文化部几乎所有人员开始陆续被下放至五七干校。就在全家人惶恐不安地等待着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时,一天,父亲下班后兴冲冲地告诉母亲:中央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他作为出版局的唯一人选被抽调到这个办公室。一家人由此免于下放,父亲也自感荣幸。后来父亲在这个机构里,利用所有有关出版工作的文件、批件都经过他手的条件,有意识地收集抄录有保存价值的出版资料。如一次父亲听说办公室隔壁存放的一批档案资料将送到造纸厂化浆,在征得军代表同意后,连续翻检了三天,共捡回30多捆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出版工作的历史文件,抢出了一批有用的史料。“文革”期间,父亲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因而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968年,我到山西农村插队,两年后参军到陕西,1985年转业回京,有了自己的家,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是周末和节假日去看他们。父亲几乎每次都和我们打个招呼,问问近况,然后又一如既往地回到桌前工作。逢年过节家人一起聊天时,父亲也总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唯有家里来了同事或在电话里谈工作,他才会打开话匣子。长年写作,他难有闲暇与家人交流,更少提及工作上的事,所以,父亲白天上班在忙些什么,回家又在写些什么,家人并不清楚。虽然感觉他的生活与常人不同,但久而久之也习惯了他的生活方式,有时甚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总之,父亲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

1980年,《汉语大词典》部分编纂人员合影。左起:陈原、罗竹风、陈落、吕叔湘、方厚枢
父亲60岁到了退休年龄,因工作需要,从出版局机关调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一职,继续忙他的事业。直到1993年66岁时,父亲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从日常事务及兼职工作中脱身出来,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父亲更是如鱼得水。适逢之前家中住房条件改善,他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虽然只有11平米,且大部分空间都被书柜书架占据,但他已很知足。一个周末我去父母家,看到父亲正忙着将退休后从单位搬回的几十包资料与家中原有的资料一起重新整理分类,并打包。小小的屋子里堆满了书籍资料。母亲说,父亲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折腾好几天了。看到父亲这把年纪还在当打包搬运工,我立刻对他说,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再干。父亲只是说你不懂……待下个周末再来时,分类整理完毕的大包小包已经塞满了父亲的书柜、书架以及床下,连家里放被褥杂物的壁橱也被占用了。母亲对此自然牢骚满腹,说父亲眼里只有他的书,哪还有这个家。说归说,我知道那是父亲几十年锲而不舍精心收集的,是父亲赖以研究写作的珍贵资料,父亲将它们视如珍宝。后来,父亲只留下了写作需要的资料,将其余的无偿捐给了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出版博物馆。其中,出版史料达100多件,包括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相关的出版文献等,还有父亲的主要著作、图书共30捆,500余册。
父亲的小屋里,门窗之间只能摆下一张老式书桌,那还是80年代由邻居手工打造的,狭小而简陋,却一直陪伴着父亲直到终老。或许是对它寄情太深,我几次提出换个大点儿的写字台,父亲都不同意。今天想来,那应该是父亲心中的一方圣地,每当坐在桌前,父亲一定是神定气清,沉浸在写作的愉悦之中。而每当看到桌上摆满各种资料,便知父亲又要作“大文章”了。后来才知道,父亲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过的500多篇、520多万字的文稿,大部分都是退休后在这张狭小简陋的书桌上完成的。每想至此便心中感叹!书桌上方挂着我为父亲画的油画肖像,那是父亲查出癌症后第二年画的,他看后很满意,当即决定将其用作将要付梓的文集《出版工作七十年》的扉页。虽遗憾父亲有生之年没能等到文集出版,但欣慰的是,画像里父亲手中的书恰似那本文集。
2003年,父母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安徽老家祭祖,顺道寻访年轻时生活过的沪宁等城市。他们回京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感叹人生苦短。此前我刚学会用电脑打字,便鼓励母亲把过去的经历写下来,经我整理后取名《往事的回忆》,打印成“书”,母亲看了很激动。不久,父亲也悄悄塞给我一份名为《历史回望纪事——附〈耕耘文存目录〉》的手稿,嘱我“如法炮制”。父亲八十寿辰时,又增补内容,写成《八十回望纪事》。打印父亲交给我的两份文稿时,随着电脑屏幕上流出的一行行文字,我才真正了解了父亲几十年间的工作业绩:在辞书和年鉴研究方面,父亲协助几位老专家修订了《辞源》、新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以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几部大项目,主编了《中国出版人名词典》,责编了《中国人名词典》(出版部分),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及《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中国出版史分支的主编,撰写了《中国辞书史话》《中国辞书编纂概况》等;参与创办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年鉴》,主编了《年鉴工作与研究》《出版参考》等。在出版史研究方面,撰写了改革开放后最早发表的中国出版史专著《中国出版史话》,以及《中国出版史文丛》《中国出版史话新编》,主编和参与主编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出版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高校专业教材《中国编辑出版史》,以及《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等等。“耕耘文存编目”中列出的一篇篇文章题目更长达十多页。其中还提到了1987年职称评审时,父亲以初中肄业学历,靠着自学成才和工作实践积累被破格评为编审;几年后又被聘为出版系统高评委;1991年,与新闻出版界的27位老专家一起获得国务院颁发的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由此,父亲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伏案写作的形象活了起来,我也第一次感到父亲的工作成绩确实非同一般。

父亲退休后,在这张狭小简陋的书桌上完成了出版史的大部分著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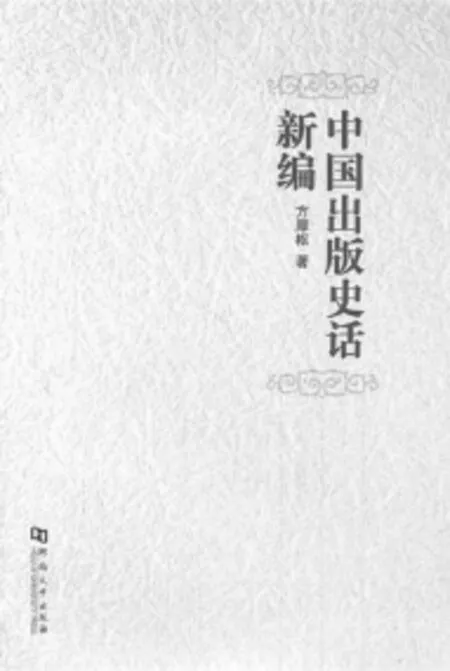
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新编》书影
述及此,我对母亲的怀念之情亦涌上心头。父亲毕生能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并做出成绩,一个重要条件是母亲独自承担了照顾家庭、抚养子女的重任,辛苦操劳了一生。父亲晚年曾多次提到,他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一半要归功于老伴儿。尽管母亲对父亲的不问家事唠叨了一辈子,但父亲去世后,母亲悲痛难抑,在父亲走后49天,母亲竟也紧随而去。
我与父亲真正的朝夕相处,是2014年在病床前陪伴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此前父亲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着手编写《出版工作七十年》。相较已出版的几本专著,父亲对这一部似乎格外看重。此前两年,父亲已查出肺癌晚期,因不忍干扰他的写作,家人未对他说出癌症实情。但父亲已预感到病情不容乐观,开始与病魔“赛跑”。2014年年初,病情开始恶化,多次抢救后又服用进口靶向药,病情渐有缓解。暂时出院后,父亲竟瞒着家人,从商务印书馆要回已付排的700多页校样,连续埋头校阅修改,终致肠梗阻复发再次入院抢救。这一次父亲或许预感到来日无多,刚解除警报,又执意要在病床上校完最后部分。我们虽百般劝阻,终究拗不过。父亲强撑着病体完成一校,叮嘱我尽快送回,方如释重负,昏昏睡去。

1996年,父母迁入新居后全家合影
我曾对父亲的“执迷”不解:一辈子已有那么多著述,生命攸关之际,何必如此在乎这一部。直到我读过文集,方悟出其中缘由:父亲17岁进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一生挚爱的编辑出版事业,最终又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文集画上生命的句号,冥冥巧合中寄托着他与商务印书馆难以割舍的情缘。文集内容经过父亲悉心筛选,上编“出版工作七十年的回顾”清晰可见父亲一生以出版为业走过的路径;下编“耕耘文存”精选了父亲笔耕一世的主要成果。全书则展现了父亲作为亲历者,对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轨迹的历史见证……父亲分明是把这部文集当成了自己毕生事业的一份全面总结。此外,附编“乡情家事”,也是父亲对自己87年人生历程的郑重交代。
父亲的病情日渐恶化,一次,他一反虚弱病态,忽然兴奋异常,多次挣脱输液器材,自己坐起来,口中不停地念念不休。尽管含混不清,我却能听出大概,一会儿像谈工作,一会儿像作报告,内容全都与出版工作和那本文集有关。这种情况竟持续了一天一夜。我很不安,想到了那个不吉利的说法。后从医生口中得知,这是医学上的“谵妄症”。我虽不太懂,但可想见必定是思虑过度所致。
最后的弥留之际,我能感觉到父亲迷离眼神中流露出的那一丝不甘——是没能等到文集出版的遗憾?或是不甘就此离去,因为还有那么多要做的事……
父亲走后,在清理遗物和书稿时,我感觉到父亲一定渴望能再次回到桌前继续工作。在稍显凌乱的一摞摞书稿中,有父亲搜集整理的“中国出版图史资料集”(含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部分),有厚厚的一摞《作品自选集》(含中国出版史综述、古代出版探索、当代出版纪事、出版资料选集等8个部分),有《文化、出版人物资料选辑》《名人名家手迹选》《参考资料选辑》等,还有一个文件夹中的若干作了标记的文章手稿,有些拟了题目纲要,有些已开了头……父亲此行带走了多少未及完成的写作计划!

2013年,病中的方厚枢接受新闻出版研究院“口述出版史”采访
父亲去世后,我们难抑悲痛。唯能聊以自慰的是,父亲一生与书为伴,专事他钟爱的编辑出版事业,苦中求乐,甘之如饴,特别是能有著述传世,留予后人。相信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必将惠及后辈。我的女儿自幼崇拜爷爷,说爷爷这么好的人,一定是去了天堂。我相信女儿的话,愿父亲在天堂继续从事他挚爱的出版事业,继续他那些未及完成的著述修史,永远享受那份艰辛却充满愉悦的时光!
责任编辑/崔金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