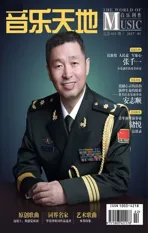青年钢琴演奏家储悦访谈录
2017-04-24孙鸣,储悦
青年钢琴演奏家储悦访谈录

2016年12月19日,我邀请了旅美青年钢琴演奏家储悦来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学并举办专场音乐会,在上午的公开课上他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精湛的示范演奏,伟岸高大的身材都给大家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师生们赞不绝口,引起了我对这位年轻钢琴家的强烈兴趣,于是我利用午饭后休息时间在我办公室对他进行了专访。
孙:孙 鸣
储:储 悦
孙
储博士您好,您上午的讲座非常精彩,老师和同学们反响很强烈,要求我要经常邀请您来上课和开音乐会。
储:孙院长您太客气了,没有您的大力支持,我这次就没有机会来山西师大做讲座,对我来讲,分享音乐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尤其能遇到您和诸多钢琴老师,能够理解和喜欢我分享的音乐,上课的整个过程我都非常兴奋和快乐,大家也体验了音乐本身所具有的魅力,这是很幸福的事情。
孙
请介绍一下您是怎样走上职业钢琴家之路的?
储:谈不上钢琴家之路,我出生于天津, 从三、四岁开始由妈妈带着学习唱歌,因为母亲是声乐老师,小时候音乐方面是她一直在辅导我,从认谱到练琴都跟妈妈有很大的关系;爸爸工作本身就在天津音乐学院,尽管他没有搞音乐,但他乐感很好,我从小生活的环境都跟音乐有关,在爸爸妈妈鼓励和带动下,从5岁开始我逐渐走上了学习钢琴的道路,后来也经历过很多转折点,但越来越觉得对钢琴有非常大的热情,最后还是选择了走钢琴专业这条路。
十二岁时我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张晋、吴元教授,2001年留学加拿大,2004年考入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先后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2010年获得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最高演奏家文凭,后来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独奏,室内乐,乐团合作,以及多元艺术我都涉猎,合作过的著名指挥家有马泽尔,阿什肯纳吉,西蒙拉特等;卓越的艺术家有小提琴家帕尔曼,大提琴家马友友,钢琴家李查古德等;优秀的团体有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旧金山,巴黎,柏林,德累斯顿等乐团,以及Juipiter, Boromeo,帕克,阿里埃尔,八重鸟,紫禁城室内乐团等多个艺术团体。演出足迹跨及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多个国家及城市。很多世界著名的音乐厅:如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波士顿乔丹音乐厅,法国卢浮宫音乐厅,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德累斯顿音乐厅,中国北京中山音乐堂、大剧院音乐厅等都曾响彻我的琴声。目前我任教于美国新英格兰音乐学院、曼尼斯音乐学院、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
孙
您活跃在国际舞台多年,媒体称您的演奏为“纯正的古典音乐,纳美国际音乐节用和平的声音震撼了林肯中心的舞台!”。您感觉国外的钢琴教学和国内相比究竟有多大差别呢?
储:如果拿国外和国内相比的话,其实更多的是老师,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法。如果从整体的教学氛围来说,国外更多注重的是音乐表现力和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热情以及对音乐的历史背景、包括情境等的探讨、热情和追求。国内可能是注重一些基础,比如对声音的要求,对句子的要求,对乐曲的要求更多的是我们做老师的,我们把自己弹过的东西,很熟的东西,专门研究过的东西,传授给自己的学生;但国外更多的是从整体的音乐理解,一些原则性的共性的东西交给学生,学生学会之后就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拓展思考的能力。
孙
您认为在钢琴演奏方法及风格方面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储:单从钢琴弹奏方法来讲,我们在六七年前还是分学派的,比如俄国派很大重量的、爆发力强的触键,很圆润的声音;德国派精细的,颗粒的,句子清晰的风格与特点;法国派比较平一点的触键,出来的声音会柔一点,软一点;意大利也类似是这样的。后来出了很多比赛型选手,比如韩国选手和中国选手是最明显的,技巧性非常强,对音乐的整体把控很到位,这也算是一派。但这几年,看很多公开的比赛也好,很多交流演出也好,大家都是互相学习。比如说2015年的一次柴可夫斯基比赛,当时冠军是俄国人,但他是在意大利学的。还有一个让人印象很深的,2014年的,法国人,弹爵士乐的,他后来很认真的转成钢琴古典乐派,他演奏的作品非常受大家欢迎。这些现象说明当今钢琴界,大家是相互学习的,不能说我拿俄国派的东西去弹法国作品,听起来是不合理,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寻找一个曲子的初衷,或是研究揣摩作曲家当时在写作时的心态,对音乐的一种向往,描写什么样的情境,什么样的情绪,可以从这个角度进行二度创作。更多的所谓的乐派其实慢慢已经淡化,或者说有一些改善,不是禁锢在一定要走那个门派,而是在于我们弹奏的方法,怎么能更好地去服从音乐的需要。
孙
您觉得儿童钢琴教学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储:我不好意思这样讲,因为在教学方面我是个晚辈,其实我也是在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但是我很庆幸我从十三岁开始就有机会去帮助别人学习钢琴,不能算是教别人,就是把我自己学到的很多东西和别人分享。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每周回到天津,我的启蒙老师陈教授每次都会开大班课,请我给他当时的学生演奏并讲解,算是稍微辅导一些他的学生。这样我就积累了很多的学习方法,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去观察别人演奏和教学。最近这一年多,我开始回国进行更多的学术交流。我发现国内现在更多还是处于前辈怎么教我,我就怎么去教学生。我冒昧地讲,琴童大多是处于被动学习这样一个状态。可能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了,吸引小孩子的东西比我们当时多多了,比如手机、电脑等等很多这些高科技电子产品。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讲,时代变迁,对于现在的小孩,以前的方式硬要输入给他们,对他们来讲可能还是很难接受的。我认为,对于儿童钢琴教学,我可能更多的是从带动和音乐欣赏入手去帮助他们。最近我在天津跟我一个朋友(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视唱练耳老师)合作了四个星期的课程,也算是一种尝试,主要是从音乐欣赏和视唱练耳入手,我请他先从音乐欣赏和带动小孩子们歌唱、识谱开始,从视觉的角度,听觉的角度,甚至加上很多肢体动作来带动孩子们,从音符,音高、音程,慢慢到和声、和弦等等。我们发现两个星期以后,孩子们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他们会对音乐有一个很主动的表现。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种需求,他们有想把心里对于音乐的这种好奇和热爱表现出来的愿望,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荐一个乐器给他们进行尝试。当然要以小孩子表现的特点为根据。有的小孩可能对韵律更感兴趣,表现出来的热情更强,那我们选择的乐器也好,表现的方式也好,可能从舞蹈或者打击乐开始。有的小孩对音高不太敏感,那从钢琴入手就比较合适。这四个星期的课程对于参加这次尝试的小孩或家长来讲,反应是特别好的。他们常常希望有下一节课,希望学到更新的东西,希望开始弹一些曲子,希望去接触更新鲜的音乐的节奏型或音乐的写法等等。最关键的就是心态问题,这对于儿童教学,可能更多的是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对音乐的主动性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再去学习钢琴,会接受和吸取更多的精神和音乐的魅力。
孙
钢琴教学方法众说纷纭,有人提倡高抬指,有人反对,您是怎么认为的?
储:所谓高抬指其实是钢琴触键的一种方法,训练高抬指是有很多用途的,比如说掌握掌关节重量的运用,手指的独立性,指尖的牢固性等等,综合起来说,它的利大于弊,但绝对不是就这一种训练方法。如果单一的只要求高抬指,那很多钢琴其它的触键方式我们就没有机会去实践和尝试,从而在音色控制方面,或者弹句子,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只能说,除了高抬指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钢琴触键方式。另外,人的体型、手指、手型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强加于每一个人都用同样的手型、触键方式的话,
其实我们训练的是琴匠,而不是钢琴演奏的音乐家。所以,训练高抬指是钢琴技巧训练中小小的一部分,更多的应该是去尝试和实践不一样的触键方法,去寻找适合演奏者自身的演奏方法,越自然越好,不能刻板和教条。
孙
谢谢,您能谈谈重量弹奏法吗?储:所谓重量弹奏其实就是一种对琴键的控制技术,触键点不在琴键的表面,而是在琴键下去以后借着杠杆原理翘起将榔头打到琴弦的那一刹那,有一个小小的反弹,我们加上重量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反弹。当然重量有很多级别,从人体运用的部位来讲,从小到大,如果指尖运用的重量够了,其它重量不需要额外的加进去;从关节来讲,由指尖到一、二关节再到掌关节、到手腕、小臂、大臂、肘、肩膀、后背等等,是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不是说所有的重量在弹每一个音时都放进去,这个要根据声音的需要而变化。音乐是属于美学范畴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我们弹出来的声音必须符合美的原则;从曲子的角度来看,只有很少的一些作品要求弹出一些很矛盾、很尖锐(描写特殊情景的,战争场面的)暴力的声音。绝大部分乐曲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情境、情绪或美丽的心情,不能极端;从古典音乐方面来讲,一二百年之前的情境,我们考虑的角度要回归到作曲家当时的一种创作角度,我们给予它再创作,我们一般还是追求一种比较圆润、比较漂亮的声音表达方式。

孙
请谈谈美国专业和业余钢琴教学目前是个什么状况?
储: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以我自己的学习经验,高中出去以钢琴为专业特长去加拿大上学,同事还学习文化知识。现在有很多小朋友考茱莉亚的预科,我自己的学生也有考上茱莉亚预科及柯蒂斯音乐学院这样的所谓天才音乐学院的,大多数都是亚洲小孩,真正美国本土的小孩在中小学阶段往往培养的是一种对钢琴的热情和兴趣,甚至一直保持到大学之后。美国大部分学生都是在大学时候接触全方位的知识、素养方面的教育(美国有一些艺术高中,这些学校也是以文化课为主的),大学之后他们才会更专注地去选择一门专业。研究生阶段,美国本土的小孩会更多,大学本科阶段,美国本土的小孩专业不会那么好,反而是亚洲的小孩在高中和大学时期专业更突出。

孙
美国中学生不进音乐学院附中进行专业学习,他们的基本功能达到专业要求吗?
储:其实是可以的,这跟我们之前讲到的练琴方式、弹奏方式都有一定关系,从美国大部分钢琴教育来讲,不会完全只专注于手指训练,更多的是去发现和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主动性和探索习惯,用音乐去带动他们的技术,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伸缩性的教学方式。我的一个学生,他有很多弹八度的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不会专门让他去训练八度的弹法,我给他有目的地听了一些乐曲,比如李斯特的第六匈牙利狂想曲(最后比较欢快、庆祝的段落基本都是八度),他对舞蹈的部分非常感兴趣,兴致很高,最后他主动弹了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六首,弹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刻意地去训练八度,而是用韵律带动自己,身体的运用不是硬来的,是顺其自然的,根据他自己弹奏八度的感觉、惯性、触键方式等进行练习,八度很容易就训练出来了,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
孙
您对网络钢琴教学有何看法?
储:网络教学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我们可以更好地运用网络传播,比如对于作品的分析、框架,乐谱,从网络上看,搞不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或者介绍一些弹奏方法,也是可以从网络上进行传授的,或者说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整体的音乐效果,从韵律的角度,句子的角度,都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教学。但有些东西运用网络传播效果就不太好,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声音,目前网络传达真实钢琴声音还没有那么确切,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依然会去音乐厅听现场音乐会的一个原因,感受钢琴真实的声音效果,网络教学没办法做到。另外,就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影响、感染等方面讲,也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从技术层面讲,有时需要亲身经历,老师可能会在学生手臂上做出重量区别,这些都是需要学习者亲自感受的,所以网络教学不能说不好,而是说它是我们当今社会的一种工具、途径,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但不能依赖它。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揣测或者思考什么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传播(因为网络拉近了距离,比如我在美国,你在中国,我们可以在网上进行互动和交流),哪些东西是不能依靠网络只能面对面教学的,这样可能会更好。
孙
您认为经常参加比赛对业余琴童有没有必要?
储: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从小孩子学习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肯定,学任何东西,如果只是一味地学,得不到任何成绩和肯定,慢慢也会失去兴趣,尤其是小孩。比赛也好,考级也好,其实更多的是给了孩子们不同程度的肯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创造一些平台,定期去展现,音乐会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比赛和考级是有证书,有实体的肯定,这些能积极的去推动、鼓励小孩子对音乐的热爱。但很多情况下,家长和小孩把考级和比赛当成学琴的目的的话,性质就会有一些变化,我不建议家长和学生朝这方面发展,应该更多地去调动自己的积极性,热爱音乐,为了音乐去学习。
孙
您是怎样处理工作、练琴、讲学以及开音乐会之间的关系的?
储:我从13岁开始,慢慢地对音乐和生活有所理解,意识到音乐是从生活中来的,把它们变成紧密相关的事情,音乐对我来讲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活更多的是去享受和分享音乐,从生活中去学习,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会引起我的思考、包括现在跟您的交流,同时我也会联想到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对于学习音乐来讲都是一种必要的体验,经常在演奏的过程中,生活中体验过的情景,不经意地就进入到了音乐当中,一些对于音乐的感悟、情绪的把控、揣摩,更多的都是从生活当中获取的。回到您刚刚的问题,工作和学习就是合理地安排时间。比如说练琴,我一天至少要保证六个小时的练琴时间,要保证手的整个活动。现在的练琴跟以前不太一样,小时候的练琴可能是一种应试的练琴,现在更多是一种思考性的练琴,上了琴,可能更多的是去尝试我思考过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音乐的处理方式,或者想到的一些音乐当中的可能性,上琴之后会尝试把它做出来,除了保证身体的积极状态,手的敏感度,还要保证对音乐思考的深度等。至于讲学、演出,那是我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安排好每天固定的练琴时间之后再安排演出及其它活动。
孙
对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说,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储: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职业演奏家来讲,心态和对音乐的热爱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一腔热忱,很难把真正的音乐分享给别人,也很难坚持下去。
孙
除了钢琴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储:钢琴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表达我对音乐理解的一个途径,我很热爱它,我把它当成我一个很亲密的朋友,演奏的时候它是我表达内心情绪的一个伙伴。平时在我生活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否则我的音乐灵感会枯竭,会越来越单薄,甚至停止。我的业余爱好其实还是蛮多的.从小因为父亲的影响,我对于体育很感兴趣,除了冰上运动,其它运动项目我几乎都尝试过,尤其是篮球、网球、乒乓球、游泳,我都很喜欢。此外,我也很喜欢看书,书给人留下很大的遐想空间,可以通过看书去了解音乐以外的世界、掌握其它方面的知识。不瞒您说,对于吃我也很喜欢(笑),这也是受到我父亲和老师的影响,我父亲饭做的很好,我从小非常有口福。我波士顿的老师谢尔曼,对吃非常讲究,比如吃什么肉配什么酒,烧肉的火候、调料、口感等要求很高,他说人的品味是从吃开始的。我那时候上学经济上比较紧缩,自己会做的东西也不多,最常做的就是汤面,又简单又方便,放些青菜、鸡蛋什么的,也不缺营养。有一次谢尔曼先生碰到了,跟我开玩笑说:“哦,储悦,难怪你弹琴是一片一片的,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但是都不够清楚。”他这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后来我慢慢意识到吃东西细嚼慢咽的过程其实也是体验饭菜味道的过程,体验了才会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滋味。
孙
除了钢琴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储:我最近一年多开始在国内做一些学术交流,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个是自己成长了一些,更多体会到了责任,想把我学到的东西通过我的方式分享给更多的人,希望国内爱好音乐的人能更多地接触到更健康的享受音乐的方式,这是我主要的目的。另外一点我的父母在国内,我定期回来看他们,每次回来和国内同仁做一些交流,或者去讲学或上课,对我来讲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孙
孝心和责任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美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国内琴童的一个福气。
储:您说福气我很开心,我现在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在美国也有一些职务,比如“纽约音乐家协会执行总监”,还有我自己创立的乐团或者团体,我更多地是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能把这些资源带到国内。另一方面,我在考虑怎样才能适合国内的需求,创立一套长久发展的体系。因为现在回国做交流的人很多,但经常是东一下西一下,尤其是外国朋友来一趟中国,转一圈走了,很快就过去了,真正要问我们自己的是,他们走了以后究竟留下了什么?当然理解方面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透一些,有些人可能只抓到了一些皮毛。好的一面是大家都在积极参与、积极思考一些跟音乐有关的问题,或讨论或交流。但也有一些情况,理解错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比如因为咬文嚼字、断章取义、钻牛角尖、语言翻译不准确,或今天这个专家讲一个样子,明天那个专家同一个问题又讲成另一个样子,这些原因都会给听者造成误解、曲解和无所适从。所以光靠外来的专家一次、两次的交流还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一个体系,就像铺路一样,要把控好大的方向,打好基础,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有一个标准,这对我来说也正在摸索和学习,也希望国内外志趣相同的朋友也来倡导这样一个体系吧。
孙
好,谢谢,希望我们加强联系,也希望这样的体系尽快建立起来,为我们国家的钢琴教育事业出力。
储:谢谢您的大力支持,希望我们有更多交流合作的机会,祝愿我们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伟大的祖国更加昌盛。


作者:孙 鸣 (简介)
孙 鸣:陕西旬邑人,1991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现任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钢琴硕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钢琴学会理事,山西省钢琴学会副会长,山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艺术团团长,爱乐合唱团常任指挥,主要从事钢琴教学及钢琴音乐口述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