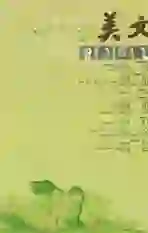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2017-04-21阿来
阿来
我今天早上起来,有点小焦虑:今天讲点什么?今天讲文学。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讲一种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什么意思呢?我们只是在一个大家来自于一般的教科书上的对最一般的文学的定义的框架当中,在讲文学。一些对文学的解释和理解,与我们当下文学的创作当中正在发生的情况是非常脱离的。当然,它就更不能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写作当中遇到的具体的情形,我们进行写作的作品当中所呈现的那些好处,给一个充分的解释。它与我们这样的写作群体所需要的一个整体写作水准的提升,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些什么》让我反思同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卡佛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谈论爱情时,我们谈的真的是我们具体的每个人身上发生的那个爱情吗?还是仅仅停留在宗教的、道德的、伦理观念指定的定义的爱情?也就是,我们平时在谈论一个事物的时候,是作为一个名词在谈论?还是把这个事物当成一个真正的过程,真正的实体,触及这个实体,触及这个实体的过程来谈论?文学也一样。我们谈论的文学,真是文学吗?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那个文学吗?
就是我们来这里听讲座,听的是一种普及性的关于文学的基本常识?还是一种我所需要的、具有创造性的、具有独特性的、催我个人生命的、情感深刻的体察的文学?还是通过讲座,得到一个非常宽阔的、深刻的认知的一些经验?文学是表达,文学总是从表达个体经验开始的。
所以,我今天想谈谈人物,即叙事文学中的人物。我们来探讨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们在谈论人物的时候,经常会离开小说具体的场景和故事。如人物要有性格。毋庸置疑,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性格。文学中人物也应该有性格。我们通过一个人物能让我们看到一类人物、一群人物、一个阶层、某种写照,或某种典型性、代表性。我们在谈论人物的时候,要谈人物和时代的关系。
因此,我们应在审美发生学的角度问:一部戏剧、一部小说,在这样一个构架当中,人物是怎么生成的?我们所需要的那些东西,在这样一个叙述的进程中,它是如何发生的?就真正的写作,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成功,显然,我们在这方面是失败的。如果我们成功,很显然,我们在这些方面找到了一些的诀窍。
所以,我们可以一个一个问题来谈。
社会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人。马克思有一个很好的定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单独的人有什么意思?如果放在一个小说中,他只是一个独立的人。除了一些极端的小说,大部分的叙述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发生故事。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故事呢?那他一定是和别的人建立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各种关系的模仿。这种关系很重要,因为我们会谈到另外一些事情。比如:小说是讲故事。“故事”在小说里头还有一个近义词——情节。在某种程度上,故事跟情节是合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些小说或者叙事文学它只是好看呢?因为情节跌宕起伏。我们在构思文学的时候,不管是写一部电影、电视剧、小说,会下意识地跟人脱开,或者说对人的关系照顾不充分。我们去虚拟、去构想一种曲折的情节。我常听一些导演说:“我们用电脑分析了一些好莱坞的电影的情节原则:三分钟要有一个小高潮,八分钟要有一个大高潮,五十分钟一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高潮——所有高潮汇聚起来的高潮。”这对基于一些商业数据分析的情景是有一定道理的。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探究高潮是怎么产生的?尤其在今天图像、视频发达的时代,它正在改变我们对情节的理解。很多写小说的人正在把小说场景化、图片化。场景化、图片化以后的结果是人在里头只是一个道具,只构造一些火爆的场面。按照好莱坞的方式:男女主人公出现,三分钟,该上一次床了吧。这是一个小高潮。刚上床出来,遇到炸弹爆炸,大高潮。然后,开始追车,很惊险。很多汽车追在一起,又是一个小高潮。再布置一次上床,三分钟的小高潮。最后,快结束了,一个惊天的大爆炸。烟火中奔跑,大大高潮。然后,男女主人公一脸硝烟,很潇洒,kiss一下,“走,我们再开间房去”。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叙事情节,包括对小说的理解、故事的构思情节的设计,很大程度上脱离开了人,脱离了人跟人的关系。而我们就需要寻找这样的点和关系。人的所有行动就只是把设想好的场景串联起来,人就成了一个串联起这些刺激性场景的道具。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离开了文学。
我们真正好的情节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大家想:有离开人的情节吗?其实,情节就是人的行动,而且还不只是人的个体的行动。在小说、叙事文学当中,不管你设计了几个人物,他们扭结成了一种关系,是这种关系的变化的演变的一个过程。这个关系有时候动作性很强,比如:武侠、战争。在谈到情节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倾向于外在的动作性。所以,写谈恋爱,光是拉拉手不行,必须得上床。因为这个才是动作。大家觉得这才是动起来了。而我们真正来看大量的小说,尤其是经典小说。它们的动作性不是那么强烈。例外的如:杰克·伦敦,他身上就有探险的气质。但更多的小说是从内在展开的。它的人物关系的演进、时间的演进,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情感上的。比如契诃夫小说《草原》:几个人坐在一辆大车上,在茫茫的草原上行走。它有什么动作呢?动作就是那辆马车,像一个活动的舞台,人就坐在马车上。这就展开了心理的描述。心理的过程即是一个情感的过程。
今天我们的很多小说有一个问题:很少能把人的情感、心理,尤其是把人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那种微妙的联系,得到一个生动细腻的微妙的敏感的表达。艺术的魅力不是大路货,不是像好莱坞那样几分钟一个小高潮,几分钟一个大高潮。更何况好莱坞还有别的一些特点,我们只是看到了它较商业的一面。比如《护送钱斯》。钱斯在伊拉克战场上战死。电影一开始,他已经战死。牧师要把他装进棺材。入棺材之前,要给他清洗一下,穿上军服,盖上国旗。整部电影是讲送棺材里的钱斯回家的故事。这样一个故事虽没有惊险刺激的场面,却十分感人。第一,他的战友在机场与他告别。告别时没有人趴在棺材上哭。而美国大兵,各种各样的神情。上了飞机两个人护送他。下了飞机,又上了一个普通的民航飞机上。他躺在货舱里,这两个人就在下面。后来人们渐渐知道,这两个人是护送一个战死的美國士兵回家。他们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复杂情感。然后,下飞机,上汽车,一路上,无非就是人们知道这是一个战死的士兵,表达了他们应该有的同情。真正的好的美国电影,都是比较节制的,没有大哭大闹,大喊大叫。一个两小时的电影,最后就是送个士兵回到家乡。他的父母、同学、朋友,很平静地,非常节制地怀念他。很平静地下葬,鸣枪升旗,电影结束。
整部电影没有强烈的动作,尽管有飞机,但是没有一个情节让我们联想到惊险、曲折。在这个过程中,它掌握了非常重要的东西——情感。尽管它是一个叙事情节,但它始终像一首抒情诗一样,水一样地缓缓流淌。只有形形色色的人的反应,而这些反应时时刻刻让我们想起那个棺材里的士兵。甚至,连棺材在电影里也很少出现。但是,我们的感情却始终在那个死去的躺在棺材里的士兵的身上。始终有一种深刻的真切的情感贯穿始终,始终在感染你,在不经意间通过一个人的眼神或动作触动你。我想这才是今天我们这个文学所需要的。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东方的消费主义者面对美国,我们只看到了美国狂热消费的一面,而没有看到美国那些最好的东西。或者即使这些东西出现了我们却视而不见。
这是一部电影,若是把它写成一部小说,可能更精彩。镜头本身是客观的,尽管它可能带上一些抒情性。但若是我们用文字来表达,发挥文字的主观抒情性,肯定会比镜头更有优势。
我们说一个小说太干巴了。为什么干巴?因为我们写作它的时候没有饱满的情感。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刘勰谈创作时,就十分强调情感。在书写自然对象的时候便要“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们在写山的时候,首先要使情感把山铺盖,写海的时候,心思比海还宏大,大海都装不下,它都溢出来了。杜甫诗:“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说的都是我们在叙事、描绘自然时所需要的那种饱满情感。
今天我们过分注重叙事学情节因素、故事因素的分析的时候,恰恰忽视了灌注在文字里的情感,不管是在我们叙述中静止的或动态的人的情感,还是在人物关系展开后,触动人物的情感的漩涡和波澜。
今天的小说,展开人物关系的时候感情很少。因为我们理解的情感是爱情或亲情。我们很少触及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丰富的情感。人是情感的动物,一旦建立关系,他就会呈现不同的情感色彩。我们首先对人物关系展开后,情感因素探讨的不够深入、丰富。
我们的小说比较干巴,比较直白。可能是因为我们处于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主义的社会中,我们也不太相信情感。也可能是忽略了。所以,对于小说中人物之间忽明忽暗的关系,我们往往不是从情感心理出发,而是从日常生活的那种功利的算计出发。比如:一个人想另一个人的钱,或一个人想巴结权力,诸如此类,互相利用,我们要写出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学最悲惨的是我们在写这些现实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堕入了现实,而丧失了人类崇高的情感和雅正的审美能力,丧失了本该赐予文学的那种净化人心的力量。如果文学失去了这样的力量,文学是堕落的。
谈到故事情节,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问题:故事情节的每一步发展一定是与人的关系的变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造成的情节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这样才能使这个情节具有非常好的叙事弹性。这个弹性是来自于生活的质感,更重要的是来自于人物的心理、情感的丰富性。把那些最隐秘的最微妙的东西揭露出来才是最最重要的。
脱离开人来讲故事、讲情节,是非常危险的。当我们只剩下情节、故事的时候,各种各样问题就会出现。但是这与文学雅正的审美、文学的最初使命又离得很远。同样,脱离情节故事来谈人物也是很危险的。比如:在医学院,有个尸体。一刀把肝拿出来,“同学们,这是肝。”再一刀把胃拿出来,“同学们,这是胃。”这确实是人的构成。但是我们把它装进去,缝起来,让他站起来,这是不是人?我们解剖一具尸体,知道了人的身体的构成。但是当我们把它缝合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是人吗?再借用卡佛的标题,当我们谈论人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当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它是假人,不是真人。为什么?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经过一番切割以后,心跳、呼吸早都没有了。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谈,要复原一个文学,我们必须对文学整体有个把握。现在,我们在进入一个碎片化的局部的看似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回到原处?把我们带回到文学作为一个对文学的整体把握那样一个语境当中。怕就怕我们会迷失在一个被知识分割的世界当中,比如说把情节、人物、情感分开来谈。离开人物的关系的进展、行动的、心理的、情感的因素,谈情节有用吗?没有用。
另外,情节是不是一律都要曲折呢?有些小说可以写得很曲折,因为它本身具有曲折性。它本身也不是故事要曲折,而是它塑造的人物给故事提供了一种可能。《基督山伯爵》就具有足够的传奇性。但是我们要写一个小民呢?比如说詹姆斯·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写的一个小城市的小人物。美国小说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我通常都是把它们当作一本长篇来看。它们描绘的是一个群像。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就写一个小城一条街,不是写外在的畸形,而是写心理。不像我们这里写一下,那里写一下,他就是集中写一个地区。海明威写过一个很好的短篇小说集《尼克·亚当斯小说集》,我觉得它可以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齐名。在我的心目中,它更好,但是它肯定没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情节那么曲折离奇。因为他就写一个小孩,尼克·亚当斯。这本书每一个短篇都是写的那个小孩,写小孩那种乡野的生活,钓鱼,打猎等等。为什么这些简单的故事就成了经典?
不是一谈到情节就是曲折,离奇、惊险、刺激。情节更多的还是在故事的展开当中,还是一个情感的因素。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过分关注情节,而失去了对情感的关注。我们只剩下与世俗人那样功利心了。比如:一对男女谈恋爱,分手了。原因是父母反对,嫌弃男方是农村的,家穷。只写这个有什么意义?如果小说只提供这样一种解释,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小说?我们身边任何一对情人分手了,人家告诉我们的都是这样的情況,而缺少一些更多地更微妙地在他们之间的使他们不能在一起的原因。
小说中丰富情节,有明暗、起伏的转折。转折有时是事件性的转折,比如战争。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在书写当下生活时,大部分的波澜还是情感的波澜,而此时小说的重点便是情感的起伏、暗涌、回旋、分析、再分析。
小说一般有两个逻辑:现实生活的逻辑和人物情感的逻辑。我们还需给它加上第三个——基于净化和拯救的“审美的逻辑”。
我们在讲人物的时候,首先要想清楚人物和故事的关系:人物是小说的中心。即便我刚才提的那个例子:那个士兵是一个死去的人,是一具尸体,没有表情、言语、动作,但是他却作为一个巨大的情感磁场。在整个电影中,紧紧抓住情感的因素,最后让我们潸然泪下。而且这种潸然泪下,不仅是基于同情,更是让人产生一种特别崇高的情感。通过这个过程使我们对于那种牺牲的精神产生一种纯粹的崇高的情感洗礼。同时,你会发现:如果选择了一种合适的书写死亡的方式,死亡也是一件庄严的事情。
看电影时,我正好在华盛顿。接待我的教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哈林顿公墓。我去过一次,所以,我要再去一次。”那个老美说:“太好了!第一,我要亲自带你去!第二,回来后,我还要请你喝酒!这才是美国精神。”我说:“你能不能说这是人类精神?否则,我不去了。”
哈林顿公墓埋葬着独立战争时期战死的几十万士兵的亡灵。在那样一个墓地行走,我却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前天我在一个山上,山很漂亮,但是山上的坟墓,就让我非常不舒服。为什么这些坟墓就让你感觉不到美感,很不舒服、很怪异?而在另外一片墓地,你就感觉美感、自然。这就和文学的创作相似。
文学的创作,首先基于对人的理解、对情节的把握,尤其是小说设计情节的时候,对于人的关系的认识。这不是要求写作的人高人一等,而是要求他在审美上、情感上要超越一般的人。
当谈论一个小说的情节不合理时,有人说的:“假!不真实!”这肯定是深入生活不够。我们便深入生活,比如:写农民。虽然,农民的情感表达和作家的不一样,重要的是作家对要深入农村,在乡间田野的生活中对自身情感的认知和观察。
小说的逻辑的合理性就是情感逻辑的合理性。我们要脱离开人的心理的情感的发展的逻辑,一定要加一个带给人视觉上高潮的一个事件,或者一些情感的出乎意料的事件。这些事件有时由人的行动实现的。若他的心理、情感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你就让他发生这样一个转折。那么,这就不叫“转折”,而叫“断裂”。情感转折的合理性消失了。
我为什么一开始讲人与故事、与情节的关系?没有脱离开人物关系的情节和故事,更没有脱离开人的心理逻辑、情感逻辑的情节的进展。情节的进展一定是与外在的故事的完成,与内在的人物的情感的激荡的记录相起伏。如果小说是一个尺度更长,时间更大的情节,它就可能呈现一个人命运,呈现一个民族的国家的大事件。但其中一定得有人物。比如:《战争与和平》写了不少战争的场景。但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物拿掉,比如拿破仑、库图佐夫,那么这本小说还剩下什么呢?你会发现:它就像房子抽掉了栋梁,没有了承重的东西,轰然倒塌。别的场景、人物写得再好,都不过是一地碎砖烂瓦而已。这些事件不论是大小,都是由人物来支撑的。
有的小说也有人物,但这个人物一直是一个符号化的,是人物促进情节的发展,而不是情节的进展服务于人的情感的发展。这是要不得的。我们在写人物的时候,真正要面对的是情节和人物的关系,和内在的情感逻辑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就等于情节。
什么是人物的关系?小说要有创新,但是很难。古希腊的戏剧很辉煌。有人就说:“看了古希腊的戏剧后,后来的人们就没法写作了。”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母题。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别的世界的文学,不可能再找到新的母題,就是再也找不到新的人物关系了。人无非就是这些关系:亲属之间:近亲远亲。社会之间关系:上下等级、各种管制。古希腊戏剧的母题,后来的人写小说、编故事,都是避免不了。
我们现在说的“情节”也是从古希腊戏剧提炼出来的。如:《俄底浦斯》的情节:儿子把父亲杀了——弑父情节。古希腊就从一个家庭、家族里面观察,观察到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一个家庭成员当中,一般来说,都是儿子爱母亲,女儿爱父亲。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异性交换的关系呢?西方人问这个问题,我们不问这个问题。各种人物关系几乎被古希腊戏剧所穷尽了。比如特洛伊战争中的爱情、战争、死亡、愤怒等。
写人物关系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继承前人;另一方面,在人物关系上几乎没有创新的可能了。种种关系都被古人穷尽了。今天各种网络小说,写多癖、肉欲,一个男人与多少个女人好。《金瓶梅》《红楼梦》不就是这样吗?这是人物关系的相似处。
此外,人物关系也可以扩展为阵营与阵营的关系。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是一个头儿带一帮兄弟对付另一个头儿带的另一帮兄弟,中间再穿插很多情节。所有的情节不就是靠这种关系的互动推进的吗?《三国演义》就是三个带头大哥:曹操、孙权、刘备。他们各自带着一帮兄弟相互斗争,逐鹿中原。《水浒传》略微变了一点,也是一个带头大哥,带了一帮兄弟,一百单八将。前面是每个人的传,后面是对抗另一拨儿人:皇帝、方腊等。
真正要写小说的人一定要做这样的分析。然后,你才能知道该写什么?大的格局已经定下来的时候,在小的地方你还能做些什么?人物关系抽出来,你会发现《红楼梦》和《金瓶梅》是一样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写一部反腐小说,人物关系可能也会像《三国演义》。若我们写情场小说,或许也会像《金瓶梅》或《红楼梦》,一男多女。
今天的科幻电影,看似写的是外星人,但那些外星人不就是变了样子的地球人吗?他们的情感,逻辑,包括他们的语言,说的不是人的语言,但你一听都懂。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基于人的情感和判断,基于人的关系和逻辑。《星球大战》不是地球上战争的翻版吗?
有人问:“您这样一说,我们都绝望了。您说写小说要出新,我们写小说还出什么新呢?”
对于人物怎么出新,这就要谈到背景。今天我们说作家要多读书,一类是理论的书,另一类是要搜集各种各样的社会材料、历史材料。我们要多掌握一些别的学科,因为今天和古代不一样。
现代社会创造了很多科学方法,学问也很多、很博杂。我们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工具,才能更有效地看待世界事物。这样,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才会知道该写些什么、怎么写。我们要写政治,我们就有必要具备一些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方法。要了解一个地区人群、族群的精神状况,我们就有必要具备一些宗教学的知识和方法。不能一写道士就是杀个鸡儿,泼个血儿,贴个符儿,念“急急如律令”,一写和尚就是合掌出来说“阿弥陀佛”。
关于人物关系,如何写出新意?同样是这样的关系,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它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关系还是关系,但是它展开的生活内容是不一样的,是代表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性。
比如:明代的《金瓶梅》。明朝是中国色情文学最为发达的时期,由绘画到戏曲、到诗词、小说多是如此。当时,市井文化和消费文化也兴盛,人的思想也自由。因为从宋以来到明,发展到一个极致。这时候很自然就是这种东西。《金瓶梅》也出现了,它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那个时代人们的需求。那么,可以想象明代社会生活情色生活比较泛滥。况且,明代色情话本小说超过《金瓶梅》的太多了。为什么它留下来了?它留下了那个时代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今天很多学者会严肃地研究《金瓶梅》而不会研究《肉蒲团》或《灯草和尚》。
而到了《红楼梦》还是一个男人与多个女人的关系。但是,清代的社会风气与明朝时的不一样了。作家想展示的是内部的情感,同样的人物关系而社会生活、人物的生命却不一样。《金瓶梅》成功了,《红楼梦》也成功了。将来我们也可以写一男多女的情况,但你不是抄《金瓶梅》或《红楼梦》。那就要求你把当下的社会感受和对当下社会的深刻的认知写到这个人物关系中去。
太阳之下无新事,人物的关系大致相同。而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昨天踏进那条河。今天,虽然河堤一样,但是,河里的水已经不是昨天的水了。所以,在人物关系不变的情况下,要看到变。历史像水流一样,时代像水流一样,在往前发展。而这个水流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当我们脱掉鞋子,卷起裤腿,下到水里时,我们会感觉到温度、力量,这就是新。
人物关系在古代小说中几乎被穷尽了,甚至人物关系当中那种所包含的精神意味也几乎被穷尽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施展的空间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生活的变化。那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最敏锐的感觉捕捉到这些新的东西?而且用非常质感的方式把它与人物的命运、性格、情感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在这过程中,把人物的性格、情感特别质感地、特别准确地呈现出来。
强大的艺术传统已经占据了巨大空间。我们的创作空间在哪?这就是我们怎么来看了。当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开始就说人物要有性格。请问:哪个人没有性格?强弱而已,明暗而已。脱离开情节,脱离开社会关系以及内容,这样的讨论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讨论现代派的作品,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今天在中国谈论《百年孤独》的文章,好像还没有一篇讨论它的深刻社会意义,只是讨论它的那些表面的绚丽的技巧。某种程度上说,那些技巧是没有太大意义。技巧不过是一些魔幻的外因,而大家忽略了马尔克斯真正所具有的那种巨大的批判力!这个批判力就是扭结在人物身上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
马孔多镇是一个适合种香蕉的地区,也是被殖民的地方。欧洲人发现这个地方适合种植香蕉,就在这里大量种植和收购香蕉。有香蕉贸易就有集散地,渐渐地,这个地方就发展、繁荣起来。但從故事展开的时候,这个镇子就开始衰落了。因为殖民者发现这个地方种了很多年香蕉,土地贫瘠了;而且,当地人也学会了讨价还价。所以,他们到别的地方种香蕉去了。香蕉贸易停止,这个镇子便衰败了。
可以说,《百年孤独》讲的是一个血淋淋的跨国资本掠夺第三世界财富的现实。今天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在发生,我们把它叫作“产业转移”。
同样,我们也处在一个和马尔克斯当年的所批判的现实中,我们的文学对此不但毫无反应,而且,我们在读到反映这样残酷历史现实的马孔多时,我们还仅仅把它当作一个特别技巧的作品,而看不到它的批判性。所以,我问:“当我们在谈论《百年孤独》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些什吗?”
为什么我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谈不到那些真正该谈的东西呢?以至于我们写作时,写不出真正的文学。我们在写作时,我们到底在写什么?古往今来的经典包含了很多的模式,我们只需要把它的一些东西抽掉,填补一些新的时代的东西。好比博物馆里的恐龙。恐龙的骨架就像小说的人物关系,而我们就是要给它“长血长肉”。
什么是“长血长肉”?那就是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现实。即便是我们要写历史、穿越、未来,但我们不论对历史还是对未来的认知,都是基于当下。有句话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也可以说:“任何未来都是当代史。”我们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历史、真正的未来,对历史的、未来的书写未尝不是对当下现实的书写。所以,要推陈出新,就要基于我们对当下的认知。认知就需要深入生活。
采风是一个途径。但是有的采风是不是形式主义了?拿个小本子,来到下乡。“老乡,今年家里养了几头猪呀?”“三头。”“卖了多少钱?”“五千。”
这样很不好。生活是一种体验、体察、认知。深入生活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切的体验,要有现场感,建立丰富的资料和有深度的观察。今天我们小说里面就缺少这些。“长血长肉”,这就是所谓的“血肉”。
光有生活经验是不够的,还得有“理论之光”的照耀。农民天天观察,若仅需观察,农民早写了。人类社会进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不由得你不进行一些理论的积累和训练。
八十年代的王蒙讨论:作家要学者化。我认为:作家要具备一定的学者理论素养和观察事物的方法。农民有丰富的经验没有写出好的作品,因为缺乏理论素养。但是,有的大学者为什么没有写出好小说?因此,仅有理论也是不行的。而文学家刚好就是这两者的中和,把生活经验和理论达到一种中和。这便需要作家从个别人物出发。
因此,情节是根据人物关系展开的。我们得找一些方法,给人物关系注入现代人对时代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认知、体察。
谈到人物的性格,人物不一定都要有复杂的性格。一个小说只需要有两三个人有丰富的性格就可以了。若所有人都有丰富的性格,那小说就没法写了,除非它只有两三个人物。
著名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提出了一种分类: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所谓的“圆形人物”就是性格复杂、心理多变、情感丰富的多面的立体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往往是小说人物关系的中心。如果《红楼梦》中所有的人物都像林黛玉性格那样复杂,那么这小说就真的没法写了。所以,还需要一些简单点的人物,如香菱、史湘云等。这类人物性格都比较鲜明。出来时,大声“哈哈”,走开时,也是“哈哈”,作为串场。性格不复杂,却很鲜明,所以叫作“扁平人物”。
所以,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要考虑“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的问题。小说是有空间的,舞台是有局限的,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人物都设计成“圆形人物”。小说中,一个人出现多少次,就是他的空间。不可能每个人都展示他的复杂性、丰富性。这也就是我们在描绘人物性格上要有侧重。
一部小说人物之间也需要对比。一个人很直率、很爽朗是和另一个不直率的、阴郁的人比较出来,而一个圆形人物也是和一个扁平人物比较出来的。
我们真正要深入写作,就要对写作方式有更深的体味,尤其是理论上的学习。它也是让作家获得一种能力。我们在写作过程中,把这种理论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互相生发,互相印证。然后,才有创新的可能、成长的可能、丰富的可能。
今天谈这么多,我不敢说我谈得多么好。但是,这是出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把人物放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怎么让它慢慢呈现、慢慢丰富。反过来,怎样让它的丰富和呈现成就一篇小说好的情节。这个情节既有外在的行动,也有内在的心理的情感。
今天很多小说过于偏重外在的,而对内在的情感重视不够。小说走到今天这个视频、音频、图片空前發达的时代,若它还有一席之地,那么它的长处便是心理描写。托尔斯泰用大量的篇幅写俄军和法军如何冲锋。今天请斯皮尔伯格来,两边两个摄像机一开,十秒钟就能让我们在视觉上享受一场盛宴。并且,更生动、更壮观。当这些都让渡给电影图片以后,人物的内在的情感的悲喜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构建人物关系而造就小说的情节和故事的时候。过去我们总是把他们分裂开来谈,我们谈肝、谈胃,不把它当作生命的一部分,只是孤立的来谈。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这些就是我对小说的人物和情节的写作经验。
阿 来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