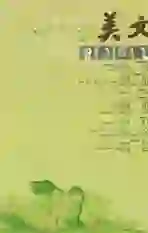缅怀老吕
2017-04-21张大文
据说我是不宜留在市区的,但我偏偏在南桥碰上了老吕;后来,据说我是不宜留在县城的,但我恰恰在钱桥碰上了老俞。这真是我不幸的一生中的两大幸事。现在,老吕和老俞都先后过世了,我可以解放嘴巴说他们的好话了。
这篇文章是写给奉贤中学百年校庆的特刊的,所以要以缅怀老吕为主,但几十年以后老俞也调到奉贤中学当人事干部了,我说了老吕后再说老俞,也是十分切题的。即使老俞后来一直在钱桥工作,我在这篇文章也要说说他,而且相信同样十分切题。因为奉贤中学是奉贤的中学的代表,在奉贤的中学中出了一个老吕,出了一个老俞,是我们奉贤的中学的光荣,是我们在奉贤的中学中工作过的人的共同的光荣!
那么,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自己的旨意强加在对老吕或者老俞不以为意甚至不以为然的老师们的头上呢?请这些老师先听听我讲了什么,再对我或者肯定或者否定罢。而且,我相信,你是终于会肯定我的。
一九六一年老吕上任不久,有一天,突然来听我的课。我在教《孔乙己》,把“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左讲右讲,讲得十分得意。老吕听了以后点点头,补充说:“他排出的还是大钱嘛。”老吕大概捕捉到我心不在焉的样子,第二天,他在篮球场边走近我说:“他排出的不是大钱嘛!”——这一下,我才警觉起来,翻出《现代汉语词典》一查,“大钱”赫然是一个条目!我当即满脸通红,体会到至今不忘的“汗颜”为何物。原来,大钱、小钱与一般的制钱虽然作为货币的价值一样,但人们还是喜欢使用大钱,孔乙己也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而把大钱作为“排”这个夸张了的动作的物质基础。讲“排”字而不讲它的物质基础,岂能讲好!老吕的意见真是击中要害啊!这个教训我在“文革”后教马烽的《结婚现场会》时还在吸取。其中人物老牛筋有一次对女婿发脾气:“我嫁女儿的时候,有没有要过你一个小钱?”在这里,正好用得着老吕二十年前对我的提醒啊!于是我便从大钱与小钱的关系讲起,使学生明白老牛筋之所以用小钱穷尽不拿彩礼的意图的原因。——这一反一正的经过告诉我:这大钱小钱的问题虽然跟我阅历浅有关,但是关键在于备课。备课的深入可以弥补经历的不足。
现在再回到六十年代初。有一天,老吕走进我们语文组办公室,把当天的《文汇报》交给我,要我向大家朗读一篇社论。我当即顺畅地读下来,一点口误都没有。按说这是我们语文老师起码的基本功,但在我也确实靠了从小刻苦练习。我从十三岁开始养活自己,每天为《新民报》(晚刊)写五角钱一条的花边新闻,从此跟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社论之类天天读,才有那样的成绩。至少在老吕眼里,我不是一根扶来扶去扶不起来的烂草绳,而是一扶就立得起来的竹竿。
一九六二年春天,市教育局和市教育学院联合举办了一个研修班,委托十一名老教师各自带领两名年轻教师进修。我从师于敬业中学的杜功乐老师,平时听他上课,偶尔也代他上课,每逢星期四则去市教育学院读书,由张撝之、林拀敔两位老师作指导。几十年过来,我觉得这种进修方式是最好的。我们二十二个青年教师中二十一个没过几年都是什么“长”了,都脱离了教学第一线。只有我最没出息,终身青灯枯坐,仿佛就在等待着奉贤中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到来。
等到“文革”时候的“复课闹革命”阶段,当时工人老师傅只要求我“上一堂使学生屁股坐得住的课”,我却托毛主席老人家的福,把他的诗词同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路线挂起钩来,讲得学生很要听,下课铃响了,大家却高声嚷着“不要下课,不要下课”。——消息传到老吕耳朵里,他也来听我的课了。记得正好讲“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引申到天是无情因而天是不老的。老吕听了以后点点头,补充说“天在变化中还是会老的”。但他接着说“文革”初期他们在南桥饭店(当时南桥饭店的三楼是南桥的制高点,对准县中的大门)监视我,我每天去余庆桥堍的老虎灶泡水,他们说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特务呢。——当时我也耳闻有特嫌之说,便每天一封信寄往香港和台湾的亲戚,每封都是按时收到,说明上层对我根本不怀疑,我还为共产党做了正面的宣传工作。我这样说,并不说明我是一个坚定的人,九十年代党组织通过一位同我关系亲密的老师做我的工作,希望我申请入党,不会吃空心汤圆。我记得斯大林在《悼列宁》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么,我是不是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呢?我恐怕还经不起一条毒蛇的考验哩!我只是在黑板前指手画脚、对学生发发脾气的庸人啊!
我到钱桥工作以后,有时路过南桥,也去敲敲老吕家的门。有一天,是老吕开的门,刚从庄行干校回来,老尤还在那边。两个孩子也不知道寄养在什么地方。跟所有干部家庭一样,冷气袭人。但老吕却热情地留我吃饭。厨房里响起砧板的铮铮声,碗里的打蛋声,拿出一大锅汤,原来是冰箱里的红烧肉放的汤,加上蛋花,加上一把葱,竟使我胃口大开,一连吃了三碗饭。老尤后来说,她一辈子都没吃过老吕烧的饭。更想不到的是,老吕饭后拿出香烟来一定要我抽。我说我从来没有抽过烟,他就一定要我抽,把火送到我面前,我就只好抽。后来他看我抽烟实在不像样,也随我掐灭了。
那么,老吕何以要我抽烟呢?他的本意并不在于烟。他无非是对我说:你何为自苦如此?因为“文革”以后,我更陷入沉思,而且走到东、走到西,都是穿着“文革”初期做牛鬼蛇神、进劳改队时的一件劳改服。他的意思一定要像老俞最后一次從家里送我走上通往古华公园的一条马路时在背后对我的叮嘱一样:“老张,你要善待自己啊!”
我最后一次跟老吕对话,是偕内子去看他。正当老尤跟我们闲谈时,老吕输血回来了。内子一见老吕和善的脸,一听他和善的声音,便说跟她姐夫一模一样。说起来还是老吕的战友,都属于李干城部下。由此我想到做领导干部首先要平易近人,在谈言微笑中做你的思想工作,调动你的积极性,使你一如既往地展开工作,搞出成绩;另一方面,也不轻易改变自己看准了的事情,善于等待未来的时间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在战争年代成熟起来的干部老吕是这样,在和平年代成熟起来的干部如老俞也是这样。
据长期在钱桥工作,今年已经98岁的沈伟君老先生说,老俞三五岁时成了孤儿,完全靠刻苦自励成才。我同老俞十年早晚相处,认识到他的马列主义修养是很好的。首先表現在行动上。钱桥小学一埭平房,屋脊高达三层楼,有一次老俞爬上屋脊修房,不小心从屋面滚跌到地上,从此每年菜花越开,头就越痛。沈老先生跟我交谈时,如果是菜花时节,她就会联想到老俞的头又在发痛了。顺便讲一下沈伟君先生。她数学教得非常好,每年钱桥小学毕业生参加升学考,总是名列前茅,因此加了薪加了级。有关领导在“文革”中当然少不了受到错误的指责。我心里在想,如果你是教育局局长,对这样的下属不加薪不加级,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
其次,老俞是认真办公,深入调查研究的。他听了我的课,扼要地指点说:你对45分钟(当时一堂课是45分钟,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40分钟了,大家毫无意见,如同改成双休用不到讨论,大家马上实行一样)的分层掌握是经过长期刻苦磨练的,你对你的教学过程能不能留下三分钟作个小结,以完成对教学过程的教学?——我以为老俞说得十分知心。十分厚重。我不到钱桥,不找到老俞,是听不到的。因此,2005年我把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专著面呈老俞,诚恳指导时,他对我作了实事求是、又鼓励有加的评语:“不少学者专家的论文或专著是靠组织他人试验、或者参阅他人论文或专著,或者自己做了个‘蹲点撰写而成的,它们到底能否指导再实践,很难说,更谈不上经典之作。而您,是自己亲临一线,每年,每月,每日,每课,每班甚至每生的教法不套公式,这样形成的理论,真正是科学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里的每一句话,老俞都是看到过的,因此我既受之无愧,又急起直追。而这种精神,既是县中培养的,又是钱桥延续的。当然,也是在曙光中学延续着的。在这篇文章中,我几次想写到吴哨老师,他是我在奉贤25年中的第三个好领导,我有许多话要说,但在这篇文章中实在不能沾边,只好暂付阙如。老吴,请勿生气。
老俞在病重期间,每次到中山医院看病,始终不叫公车,由臧老师陪同每次清晨到公共汽车站排队候车。有一次我想送点车马费给老俞。老俞说,他一生中从不接受他人资助。我一想,要他破例也不好,只得收回。可见老俞一定是一个清官。在县中,在我熟知的同事中,有两位如果做官,也一定是清官,一个是钟明德,一个是顾必先。其他同事,因为我不熟知,所以也暂付阙如,请勿生气。而老俞,虽然到头来是个低级干部,却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低级干部,他要比没有脱离低级趣味的高级干部高级得多。在我心中,老俞是一个追求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即使生活细节,我们也在渗透着辩证法。有一次,我在老俞的房间里发现他盖的被头很厚很厚,但垫的被子却很薄很薄,我当即说:“垫比盖重要。”他一实验,对我说:“果真如此。”
那么,在奉贤中学百年华诞之时,我到底要向老吕、老俞学习些什么?我以为,要学习他们的党性原则。有一个人,以调干生的名义生活在我们学生之中,实际上操纵着我们的分配大权,一直受到信任的,但不知何年何月,突然听到他自己因为哥哥、姐姐解放前就在台湾所以是内控人员而大为不满,马上探亲,马上脱离共产党,马上加入国民党,有时还回大陆来探我们这些同学之亲。在我眼里,这样的人狗屁不值。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反而要入党给你看看。什么一条毒蛇,什么一条老虎凳,我统统不怕,我就是一个老吕、老俞熏陶出来的、78岁的硬汉!
张大文 1937年11月出生,浙江省余姚市人。196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教授。1991年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并授予“人民教师”奖章。1992年被评为上海市特级教师。已发表文学作品1000万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