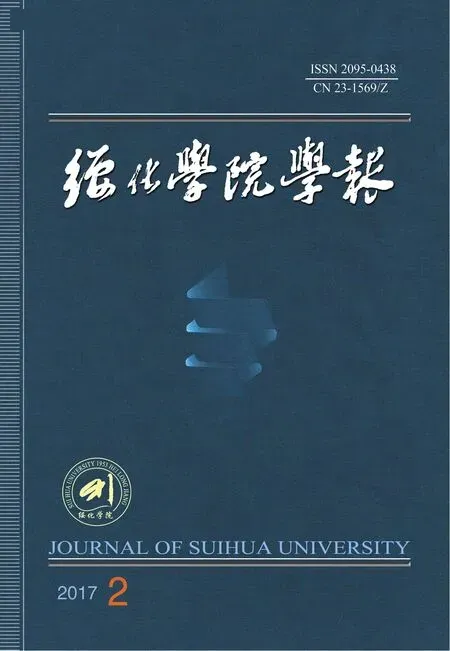跨学科视野中的《钢琴教师》与音乐
2017-04-14陈剑雨
陈剑雨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跨学科视野中的《钢琴教师》与音乐
陈剑雨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 401331)
奥地利女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与音乐联系紧密:一种是潜在联系,表现在音乐对小说“性”主题的建构、对小说情境的建构以及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建构。另一种是深层联系,文学作品与作品中的音乐元素表现出了“自由与反抗”“以悲为美”的审美共性。将《钢琴教师》与音乐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探寻作品的艺术追求与音乐的内在品质之间的联系。
《钢琴教师》;耶利内克;音乐;文本建构;审美共性
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是当代最具争议的小说家之一,她作品由于露骨的性描写多为评论界诟病,但其创作确实不拘一格。她的代表作《钢琴教师》描写了钢琴女教师埃里卡和学生克雷默尔之间变态的性关系。小说与音乐理论巧妙融合,是作者弹奏的一曲“文学音乐”,其中不乏性描写的场面,但作家较高的音乐素养将文学与音乐这两种艺术完美融合,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追求。
一、音乐与《钢琴教师》小说文本建构
(一)音乐对小说“性”主题的建构。耶利内克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中年女钢琴教师性心理的变态与扭曲,借此表现了上流社会的虚伪与人性的扭曲。那么,作为音乐家出身的耶利内克如何借用音乐来表现“性”的主题是值得读者深思的。
音乐旋律正如意识流一样,当无数琴键发出的声音组合在一起,音乐往往呈现出流状,文本中人物的性欲意识便可以随着音乐旋律的高低或强或弱。在音乐的引导下,人的意识自由生发,暴露出来的是人性最真的东西,性作为人的原欲便以极真的状态表现了出来。例如巴赫三段曲式音乐与小说中对应段落的第一句:
1.“巴赫的音乐如溪水流淌”——“她用能切割的目光挨个打量学生,然后微微的摇了摇头”[1](P59)
2.“巴赫的溪流进入快板”——“克雷默尔以逐渐增强的饥渴目光从下面打量他的钢琴女教师座位以下的身体”[1](P60)
3.“巴赫的最后一个乐章”——“克雷默尔先生两颊绯红”[1](P60)
当巴赫音乐响起时,女教师埃里卡的性欲意识流动是相对平缓的。随后巴赫的音乐增强,学生克雷默尔的性欲达到了饥渴的程度,当进入最后一个乐章时,克雷默尔的性欲以及产生性欲的意识仍在不停的运转,然而较之此前快板的阶段,它的程度慢慢降低而不是戛然而止,这时候学生克雷默尔理性地想使自己从精神的角度去评价埃里卡的整体形象,但是他失败了,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科胡特小姐正是那种年轻男人进入生活时想要的女人。”[1](P61)由此可见,巴赫音乐对小说《钢琴教师》性主题的建构起着引导和推动的双重作用。
小说创作中音乐对小说“性”主题的建构并不是西方独有的,比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退潮后出现的一位作家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完美的诠释了音乐与“性”结合的可能。《钢琴教师》中音乐与性主题的建构具有独特性,这一特点与西方的传统思想文化相关。西方文学传统认为悲剧是人类最崇高的审美,“音乐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便表达了命运的悲惨,《钢琴教师》选取了肖邦、舒伯特表达痛苦之情的一部分音乐作品来表达作者自我内心的痛苦与压抑,是文学与音乐“悲哀”主题的延续。相对而言,阎连科的小说《坚硬如水》则希冀身心的快乐以求对苦难的忘却。革命音乐表现出的高亢、振奋以及所激起主人公强烈的性欲与耶利内克中西文化虽然异趣,但现代小说的创作同样存在将音乐与“性”结合运用的手法,这并不是巧合,“性”是人类的一种情感表达,当文学语言无法完美诠释它,音乐这种富于表达情感的方式就弥补了小说语言表达的不足。
(二)音乐对小说情境的建构。小说主人公埃里卡因为母亲的监视、性爱的缺乏,导致了她精神世界的变态和扭曲,耶利内克通过钢琴音乐对埃里卡扭曲的生活情境进行了一种仿写。文中这样描绘埃里卡的生活情境:“钢琴键盘在触摸下开始歌唱。文化废墟的巨大裙裾窸窣作响,轻轻地从四面八方涌上来,一毫米一毫米的合围。”[1](P55)用音乐入耳的压迫和紧张感来仿写现实生活的凌乱琐碎对埃里卡造成的心理压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仿写,是因为“小说对于音乐的借鉴,只能是一种模糊的类比,而非严格的对应”[2](P111)。“音乐和文学毕竟是不同的艺术类型,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无法抹煞的”[2](P111)。钢琴的乐音是由一些音符组成,而生活中充满了琐碎的事物,当音乐元素从四面八方灌入耳中,生活中的琐碎也从四周向我们的眼睛袭来。从这方面来说两者造成一种紧张与压迫感是相似的。
音乐理论中的不和谐音也参与了小说情境的建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说道:“她用超凡的语言以及在小说中表现出的音乐的动感,显示了社会的荒谬及它们使人屈服的奇异力量”[3](P1255),说明了其文本语言的音乐性。不和谐音是音乐术语,相较于和谐音不和谐音听起来更加刺耳浑浊。“现代音乐,尤其是摇滚音乐,摒弃圆熟的流畅,而掺入不和谐音,以表现人复杂的欲望,骚动不安的情绪和汹涌奔突的思想”[4]。文学对音乐不和谐音的借鉴表现为文本中对男性下体,女性生殖器官,性交场面的描绘,这些污秽不堪的情境描绘,使小说的情境变得生活化、俗化甚至异化。
此外,男女主人公关系也体现出音乐对小说情境的建构。音乐对小说男女主人公关系的建构贯穿于小说的主线,这条主线便是男女主人公的活动。首先音乐是女钢琴教师埃里卡与学生克雷默尔相识相知的前提,是男女主人公关系最初建构的契机。其次,在上述二人建立相对和谐的关系之前,音乐是充当了二人关系的内在阻力。比如说母亲防着任何男人接触埃里卡的举动造成了她内心的性压抑,这种压抑是借音乐表现出来的,例如令埃里卡大加赞赏的莫扎特音乐,因为莫扎特音乐与埃里卡的精神痛苦有着深层的联系,再如文本中描绘的勃拉姆斯音乐流淌到人们嘴里留下是“对女人不满足的音乐家的乳清”[1](P54)。再者,《钢琴教师》文本中插入了科胡特与克雷默尔的二重奏,联系两者的首先是共同演奏的乐曲,但是随着乐曲的流淌,起着连接作用的是他们情感上的交汇,是他们在“中间音,中间世界,中间领域的松散的尘土层上温柔地漫步”[1](P68)时意识与情感的交汇,最后,“舒伯特音乐中指涉的爱情悲剧性”[5](P34)让埃里卡原本可以得到的克雷默尔的爱情,因为一封“求虐”信造成了克雷默尔对埃里卡的强暴行为,使得爱在萌芽期便被扼杀了,男女两性的关系因此呈现出畸形状态。
(三)音乐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建构。《钢琴教师》的叙事手法学者们观点不一。方向真认为:“在耶利内克的作品里,《钢琴教师》的叙事手法算是传统的了,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性格比较明析。”[6](P14)张柠倾向于:“小说《钢琴教师》的叙事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结构,或者说它的结构随意松散,一大堆心理联想式的语言游移不定、蜂拥而至。”[7](P344)这两种说法站在各自的角度上都有其道理,但是都没有将《钢琴教师》的叙事结构更加明析的呈现给读者,若借助主调音乐的概念,小说便有了可以言说的结构。
主调音乐是与复调相对的概念,多与复调结合起来使用,但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并不是复调小说。根据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的修订》中有关复调小说的三大特征的论述《钢琴教师》不是复调小说的原因总结起来有两点:首先,《钢琴教师》中主人公的思想心理等方面受到作者的支配,主人公没有处于与作者同等的地位,不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主体性。其次,《钢琴教师》文本中几乎不存在对话,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复调小说中存在着多重对话:有主人公与作者间的对话,有人物意识之间的对话,甚至还存在篇章结构的对话,但是,这些对话形式在《钢琴教师》小说文本中几乎不存在。作者对于小说所起的作用延续了西方小说的传统,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作者大量描绘了主人公埃里卡的心理活动,仅仅是作为“全知视角”窥探人物心理的便利,作者没有给主人公更多的权利和自我意识,小说的对话没有形成的基础。文本中分为上下两章,两部分间的没有明显的逻辑联系,也不存在对话的可能,起着连接作用的是故事主线男女主人公的活动线索。复调小说的第三个特征是未完成性,是基于对话的基础之上的,这点因为《钢琴教师》几乎无对话而没有论述的必要。至于《一幅肖像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传》中说:“钢琴教师同样充斥着复调意味,低谷与高昂,悲剧与讥诮携手并行。”[8](P18)说的是文本中两种风格的并行,使文本具有了戏仿的特点,这是作品风格模糊的比喻,而非叙事结构的复调意味。
《钢琴教师》小说文本主要讲述埃里卡和克雷默尔之间畸形的性关系,其主旋律在文本的开头和结尾显露了出来。文本开头写了女教师埃里卡回家路上的一段意识流,而以埃里卡拖着自虐受伤的身体往家走结尾,开头与结尾颇似音乐学上的复现手法。虽然文本中间部分的内容较为驳杂,但是主旋律在开篇与结尾处仍清晰可见。文本中的数个声部如母亲、表弟、克雷默尔以及父亲,紧紧围绕在主旋律埃里卡意识活动的周围,从各个方面突出和增强了主调。首先,母亲的期望与控制欲造成了埃里卡内心性压抑,其次,表弟布尔西的男性诱惑加强了埃里卡的性欲,克雷默尔的求爱使埃里卡性欲更加强烈,再者,父亲被母亲送进巴赫疗养院时他的悲伤和无助增强了埃里卡自虐的心理。主调与各声部相协调,共同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小说文本。
顺延着主旋律,读者可以发现各个声部的安排有其逻辑顺序而且通常处于主旋律埃里卡的活动空间之外的空间当中,如母亲、克雷默尔等意识流动的空间是独立的,从不与埃里卡意识空间交织。各个声部出现有其内在的逻辑顺序,基本上按照程度由轻到重交替出现,这点暗合了与主调密切相关的和声学的要求。上述特点使得文本变得有序化,文本的结构明晰可见,但又不同于复调小说各部分间严格的对位,表现出了非对称的结构美。在“错落有致”的叙事中,主旋律表现出的情感得以强化。例如母亲的声部多次出现,而每一次的影响都强于前一次,甚至演变成埃里卡对母亲的“爱欲试验”,最后都加深埃里卡内心的痛苦。
二、音乐与小说文本的审美共性
(一)作为隐喻的“乐器”与“身体”。女教师埃里卡与学生克雷默尔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场所是厕所,作者对男女性场面的描写并没有参杂任何情欲,而仅仅是两具躯体机械地交合,埃里卡丝毫没有性欲的快感。因此《一幅肖像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传》中说:“小说中的它们(原文中指厕所)是性爱试验的场所,身体在其中像乐器一样遭到各种虐待和折磨。”[8](P11)将身体比作乐器更深层面是将音乐与乐器,性与身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类比。文本中“身体”之所以能与乐器进行类比,是因为“身体”已经被符号化了,“身体”作为他者进入人们的视野而被书写。
文本中的音乐表达了两种痛苦:一种是音乐家的痛苦,他们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音乐如泣如诉,借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精神痛苦,如舒伯特的“冬之旅”,借曲调舒缓的音乐表达了情场失意人的孤独和无望。另一种音乐痛苦是处于从属地位,被压迫者乐器发出的尖叫与哀鸣,耶利内克认为:“音乐绝非一种温柔艺术,而是对乐器的艰难拷问。”[8](P18)文本的中心主题是“小市民借音乐平步青云的努力”[8](P19),对一般学习者来说像莫扎特的精神痛苦很难领悟,他们弹奏出来的音乐无比刺耳,原文中用了“尖叫”一次来渲染乐器被不懂音乐的人摆弄的痛苦。而对于像埃里卡这样技艺纯熟但无法成名的音乐家来说,用以演奏的乐器表达了一种控诉和不平,以及因为音乐剥夺了她美好的童年和长大后梦寐以求的平凡人生的一种报复心理。
文本中爱情描写表现的痛苦与折磨主要是身体,同样,身体也如乐器一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无法摆脱痛苦的深渊。主人公埃里卡具有强烈的自虐心理,自虐心理的深层来源是童年的创伤性记忆,患精神病的父亲在她小时候被母亲送往巴赫疗养院,之后便死在了那里,而自己成为母亲的保护对象,成为了她阉割的对象。潜在原因是“性”的引诱,埃里卡是位中年女人,她渴求被爱,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有玩弄与被玩弄,她变态扭曲的心理甚至还希望自己被强暴,埃里卡深知自己无法拥有真爱,她的理智要求她面对情欲要冷静,但生理需求往往搅得她心烦意乱,作为性欲望直接来源的身体成为了她发泄的对象。
乐器和身体是作为人们宣泄的对象存在的,最终人们都会获得一种暂时的快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补偿。埃里卡称父亲的刀片为“吉祥物”,文本中多次描写血液汇成的涓涓细流,作者甚至将它们改写成《冬之旅》的歌词,埃里卡给学生上课时甚至想将学生的头按下去撞击钢琴,“直到琴弦血淋淋的内脏发出刺耳的尖叫,鲜血从盖子底下喷射出来”[1](P100)。乐器与身体在文本中表现了一种“畸形美”的审美共性。乐器与身体两者的隐喻意义表现为处于从属地位的它们想要反叛音乐与性的统治地位,获得自我独立与解放。因而,乐器和身体又具有了一种自由与反抗的审美共性。
(二)作为指涉的“音乐悲剧”与“人生悲剧”。音乐与文学学科的悲剧主题在小说文本《钢琴教师》中巧妙结合,作品表现出的悲剧性成为音乐与文学的共同的审美特征,“音乐悲剧”指涉了主人公埃里卡的“人生悲剧”,从作家创作的角度,甚至还指涉了像耶利内克这样生活在维也纳人们的“人生悲剧”。那么,“音乐悲剧”能够指涉“人生悲剧”,以及在维也纳,在作者的创作中“音乐”与“文学”最终都指向了悲剧性的原因都值得读者深入思考。
“音乐悲剧”能够指涉“人生悲剧”是因为上述提到音乐表达了两种痛苦,其中一种是音乐家的痛苦,文学写作并非是音乐家个人的传记,这些在文本中隐去了背景生平的音乐家的名字,在享誉世界的音乐之都奥地利来说,就像是特殊的文化标记,使得文本写作文词简练而含意深远。像巴赫、莫扎特、勃拉姆斯、肖邦、舒曼、舒伯特、贝多芬等众多音乐家在文本中都是痛苦的代名词,例如勃拉姆斯爱慕克拉拉(舒曼之妻),强压性欲冲动,他将此表现在了音乐中,因此文中写道:“过后流到他们嘴里的便是勃拉姆斯这位特别是对女人不满足的音乐家的乳清。”[1](P34)而这种性压抑更是克雷默尔对埃里卡此刻性欲望的写照。读懂《钢琴教师》需要良好的音乐修养,否则读者很难理解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从而无法了解作品的精神内质。
“音乐”与“文学”在作者的创作中最终都指向了悲剧性,这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音乐”的悲剧性源于艺术家的生活体验,贫民音乐家跻身于上流社会,因为民间视野使他们更加关心一些社会问题,如莫扎特表现德奥知识分子反压迫题材的音乐,悲剧性还源于他们的情感体验,如肖邦、勃拉姆斯等音乐家都受情感所累。然而,一般人听肖邦、莫扎特的音乐并不能领会他们的精神痛苦,只能引起听者内心情感的共鸣,《钢琴教师》的中心主题是“小市民借音乐平步青云的努力”[8](P19),在维也纳,众多民众都怀揣着一个音乐梦想,这是他们成功的阶梯,甚至连作者耶利内克也是他们众多人中的一员,但是那些没有音乐才华的人备受音乐的煎熬,因而悲伤的音乐更能引发他们内心的情感。《钢琴教师》主人公埃里卡与众人不同,她有音乐才华,但因为一次失败的表演错失了成为音乐家的机会,漫长的音乐生涯使她变成了一位性变态的中年女人。“音乐”和“文学”的悲剧性虽然动因不尽相同,但“音乐”和“文学”在维也纳共同具有悲剧性的审美特征。
三、结语
《钢琴教师》小说中音乐与文学作品交相辉映,徜徉于耶利内克的小说世界,读者既能感受到音乐震撼人心的审美力,又能体验到文本世界的绚丽多彩。小说中音乐元素无处不在,音乐既参与了小说“性”主题的建构,又参与了小说情境的建构以及小说叙事结构的建构,文本建构与音乐紧密融合体现了作者精湛的小说技艺,为读者营造了音乐与文学的双重审美空间,带给了读者独特的文化体验。
音乐与性主题结合的写作手法是新颖的,耶利内克作品“性”描写招致众多非议,但音乐对“性”主题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它能够反映个人与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表达无法描摹的细腻情感。主调音乐理论较少应用于小说批评,但借助主调音乐的概念《钢琴教师》的叙事结构更明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音乐和小说《钢琴教师》表现出的“反抗与自由”和“以悲为美”的共同的审美特色,体现出了文学与音乐更深层的联系。这些共同的审美特色是小说与音乐相似之处的体现,同时也是耶利内克对生活与小说创作的独特体验。
[1]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钢琴教师[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
[2]瞿世镜.音乐 美术 文学——意识流小说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3]宋兆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下[M].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
[4]张春蕾.以语言墨镜烛照社会的丑陋与荒诞——埃尔弗德·耶利内克论[J].当代外国文学,2006.
[5]张磊.跨文化视野下的古典音乐与世界文学[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6]方向真.她们的自由历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
[7]张柠.想象的衰败 欠发达国家精神现象解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8][奥]薇蕾娜·迈尔,罗兰德·科贝尔格.一幅肖像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传[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7)02-0059-04
2015-10-15
陈剑雨(1992-),女,江苏盐城人,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