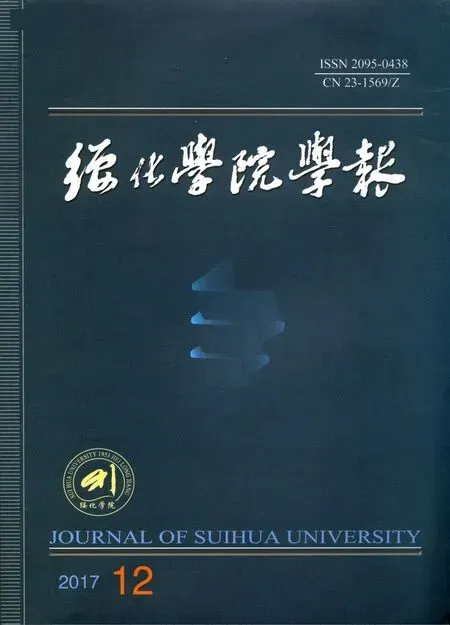出世与入世:北宋契嵩“佛儒会通”的孝道思想
2017-04-14左金众
韩 绿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出世与入世:北宋契嵩“佛儒会通”的孝道思想
韩 绿 左金众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062)
契嵩在北宋儒家士大夫的排佛的思想浪潮中,融合儒、佛的的孝道思想以及北宋以前的僧俗护教孝道理论,“以儒释佛”,“以佛摄儒”,会通儒佛,提出“孝为戒端,成佛由孝”的“大孝”思想。契嵩的“大孝”理论是一种具有出世与入世的“二元性”特征的佛教孝道思想。此外,契嵩的“大孝”思想可分为“物质之孝”“精神之孝”“显德之孝”和“达道之纯孝”等四个层次,并鲜明地体现着“大孝”的出世与入世特征。契嵩的“大孝”思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以及中国孝道思想的构建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北宋契嵩儒佛汇通孝道
北宋初年,儒家学者上承李唐韩愈的“道统”论,并通过“古文运动”使儒学逐渐复苏;此外,北宋汉族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矛盾以及佛教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出现“佛教与儒家社会伦理纲常相违背、佛教危害儒家王道政治以及夷夏之辩”[1]等问题再度刺激了儒家知识分子那敏感的神经。以孙复、石介、宋祁、范仲淹、欧阳修、曾巩、司马光、李觏、蔡襄、王令等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借助传统儒学的伦理思想在思想界进行声势浩大的排佛浪潮,诚如孙复所言:“儒之辱也,……佛老之徒滥于中国,……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2]石介也认为佛教“非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宾客、朋友之位,是悖人道”。诚如陈舜俞在《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中所言:“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3]。
契嵩面对“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的社会现实状况,以“谋道不谋身,为法不为名”的勇于护教的精神,在“山中尝窃著书以谕世”,力彰“佛道与王道合”之理,并冀望皇帝“诏以示学者,使其知佛之法者,有益于帝王之道德。”在排佛与反排佛的思想交锋之中,佛教的孝道问题无疑是这场运动的聚焦点。因此,契嵩作《原教》阐述佛教戒律与儒家伦理纲常相通性,又作《广原教》25篇,同《孝论》《劝书》《坛经赞》等合为《辅教篇》,并系统阐发佛教出世与入世的“大孝”思想。它的问世不仅仅对中国佛教,还对中国的孝道伦理产生深远地影响。
一、契嵩“大孝”的思想渊源及其主要观点
“孝”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佛教虽以出世为目的,但是在佛教的经典之中却存有大量的有关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内容体裁,其中诸如《四十二章经》《善生子经》《华严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大方便报恩经》《大无量寿经》《佛说盂兰盆经》《佛说父母恩重经》《梵网经》《那先比丘经》《优婆塞戒经》等等,这些佛教经典以佛教特有的方式展现佛教的孝道观,宣扬佛教的孝道思想。
随着佛教不断的中土化,在排佛与反排佛不断的交锋中,出现大量僧俗护教的孝道理论。最早的如汉魏时期的《牟子理惑论》,牟子借用孔子对泰伯、许由、伯夷、叔齐称赞的观点和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为德”思想,来回应中土士大夫对佛教“不孝”的诘难,并以此来说明“佛教的出家是重质而不形,是大德不拘小节之举”[4]。随后,东晋名士孙绰在《喻道论》中讲:“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若匍匐怀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万物遵己,举世我赖,以之养亲,其荣近矣!夫缘督以为经,守柔以为常,形名两绝,亲我交忘,养亲之道也。”[5]孙绰认为,相比在家简单地以饮食起居孝养父母而言,出家修道行法,成为天下万世之楷模,更是一种大孝。诚如慧远所言:“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在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6]萧梁之际的刘勰在《灭惑论》中将佛教的轮回报应说与中国固有的灵魂不死观念相结合,强调佛教的孝亲不局限于现世,认为“学(佛)道拔亲,则冥苦永灭”[7],是兼济三世,并从精神上彻底解脱父母之苦的大孝,因而,认为佛教的孝是一种“至极之孝”。唐代法琳从儒家《孝经》的三孝之义出发,明确提出“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8],并盛赞佛教之孝乃是“大孝”和“巨孝”。
契嵩以“儒佛一贯”为核心,融合儒佛的孝道思想以及前人的护教孝道理论,提出“孝为戒端,因孝成佛”的“大孝”论。契嵩认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至哉大矣”[9],又认为“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10]在契嵩看来,出家的目的是依据佛法而行善于一切众生,如果这种善行不能普及到父母身上,那么佛道将不为佛道,同时也辜负佛陀的教法。“出家者,将以道而普善也。普善而不善其父母,岂曰道耶?不唯不见其心,抑亦无辜于圣人之法也”[11]。然而,“佛子情可正,而亲不可遗也”[12],出家并不是意味不要家和抛弃家中的父母,“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故律教其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出家修行同时也要安顿和照顾好父母,僧尼要用衣钵之资赡养父母。
契嵩认为孝为戒端,因孝成佛,将孝作为一种佛法。《梵网经》云:“孝顺,至道之法。”[13]六祖慧能大师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14]世间法和佛法其本身而言就是一体的,世间法即是佛法,佛法不离世间之法。因此,孝作为世间法是人们生活的基本伦理,同时作为佛法又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法门。正如契嵩在《孝论·明孝章》中所言:
“子亦闻吾先圣人,其始振也,为大戒,即曰孝名为戒。盖以孝而为戒之端也。子欲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也。为善微戒,善何生耶?为戒微孝,戒何自耶?故经曰:使我疾成于无上正真之道者由孝德也。”[15]
在契嵩认为,“孝”是佛教信众所必须执行的,其基本逻辑,即孝——戒——善——正觉(佛),孝为戒端,戒生众善,由善得道成正觉。契嵩的“大孝”思想,一方面将儒家的“万善之首”,内化成佛教的“正觉之端”;另一方面,孝为戒端,成佛由孝,契嵩不惜悖于传统佛教的教旨,极力提升“孝”的地位,从而在佛教内部彰显“孝”之大。
二、契嵩“大孝”论的“二元性”特征
契嵩的“大孝”既是一种入世的孝,又是一种出世的孝。在《孝论·叙》中明确地表明他的孝道思想,即“发明吾圣人大孝之奥理密意,会夫儒者之说。”[16]儒家代表的是入世主义,佛教则体现是出世的情怀。因此,契嵩的“大孝”思想的本质上是一种兼容“出世之孝”和“入世之孝”的二元性的孝道思想。
契嵩以佛教的“五戒”“六度”配以儒家之“五常”,使出世与入世相融。“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语,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身,显其亲,不亦孝乎?”[17]契嵩以佛教的不杀、不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来配儒家仁、义、礼、智、信,认为在现世中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同本异名。此外,契嵩还强调佛教的六度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具有一致性,“儒家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与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无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语绮语,其为目虽不同,而其所以立诚修行,善世教人,岂异乎哉?圣人之为心者,欲人皆善……,又吾佛有以万行而为人也,今儒者之仁义礼智信,岂非吾佛所施之万行乎。”[18]
然而,契嵩的“大孝”思想的本质是一种出世之孝。“虽有与儒家的孝相同、相近的内容,然而,其特有的宗教色彩也是很鲜明的。”[19]正如汤用彤先生说:“佛教最重要之信条为神灵不灭,轮转报应之说。”[20]契嵩的孝道理论作为佛教孝道思想的一部分,其孝道观也必然体现佛教的因果轮回报应和出世间的超现实的色彩。如《孝论·评孝章》所言:
“追父母于既往,则逮乎七世,为父母虑其未然,则逮乎更生。虽驧然骇世,而在道然也,……天下苟以其陷神为父母虑,犹可以馆乎孝子慎终追远之心也。况其于变化而得其实者也,校夫世之谓孝者居一世而暗玄览,求于人而不求于神,是不为远,而孰为远乎?是不为大,而孰为大乎?”[21]
虽然,契嵩的孝道思想,以佛教固有灵魂不灭和三世轮回为核心,十分注重对父母之累世和累世之父母的孝,着重强调精神不灭和三世轮回的真实可信赖性,并以此认为佛教的这种出世的孝道是一种更深远广大的“大孝”;但是契嵩认为“孝也极焉,以儒为守,以佛广之;以儒人之,以佛神之,孝其至大哉”,并没有抬高佛教之孝为大,也没有贬低儒家之孝为小;而是以“孝”为“体”,以儒、佛为“用”,儒家之旨和佛教之法皆是普及“孝”的一种方式。
三、契嵩“大孝”思想的几个层次
契嵩认为“孝”有“可见之孝”和“不可见之孝”两种,并认为不可见之孝为孝之理,可见之孝为孝之行。
“孝有可见也,有不可见也。不可见者,孝之理也;可见者,孝之行也。理也者,孝之所以出也;行也者,孝之所以形容也。修其形容而其中不修,则事父母不笃,惠人不仁,修其中而形容亦修,岂惠父母而惠人,是亦振天地而感鬼神也。”[22]
在契嵩看来,“孝理”是“孝行”的内涵,“孝行”是“孝理”的外延。孝养父母要以“诚”为核心,理行兼备。因此,孝养父母的孝之行,若离开孝之理便会致使孝顺父母不诚,便非真孝之举。契嵩在融会儒、释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大孝”理论体系。在契嵩的“大孝”思想中,按照高下依此可分为“物质之孝”“精神之孝”“显德之孝”“达道之纯孝”等四种层次。
首先,物质之孝。契嵩在《孝论·必孝章》引《摩诃僧祇律》讲:“经谓,父母与一生补处菩萨等,故当承事供养。故律教其弟子,得减衣钵之资,而养其父母。”[23]。僧尼出家修行,并非是“遗亲弃爱”不要父母,因此,出家之后也必须先安顿好父母,注重在衣食等物质上赡养父母。
其次,精神之孝。孝养父母不仅仅是物质等低级的孝顺,无论是儒家还是佛教都十分重视精神上对父母的孝养。在《论语》中孔子讲:“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4]儒家认为,如果不以真诚恭敬之心孝顺父母,那么就和饲养狗马畜生别无二样,体现了儒家注重精神层次“孝”。然而,契嵩也同样地重视精神层次上对父母的孝,《孝行·原孝章》言:
“孝行者,养亲之谓也。行不以诚,则其养有时而匮也。夫以诚而孝之,其事亲也全,其惠人恤物也均。孝也者,效也;诚也者,成也。成者,成其道也;效者,效其孝也。为孝而无效,非孝也;为诚而无成,非诚也,……是故圣人之孝,以诚为贵也。”[25]
契嵩提出孝顺父母要“诚”,其“以诚而孝之”的孝道观,明显是融会儒家的“以敬而孝之”的思想,并另辟蹊径,将“孝”与“诚”联系起来,把“孝行”内化为心之“诚”,并指出孝行不仅是在物质上供养父母,而且还要求子女必须诚心诚意地从精神情感上孝顺父母,反之就是“伪孝”。
再次,“显亲之孝”。契嵩在“精神之孝”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德报之孝”,即“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又“善天下,道为大;显其亲,德为优”[26]。契嵩在《孝论·德报章》中对佛教与儒家之德孝,作了明确的区分:
“德也者,非世之所谓德也。备完善,被幽被明,圣人之德。……(儒家)君子之所谓孝也,国人称愿。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谓孝也已。虽然,盖意同,而义异也。”[27]
从中可以看出,佛教的所说的“德”是包有万善,洞彻幽明,慈爱万物的“至德”。因此,契嵩所说的“显亲”之孝,是指自身求得佛教的妙理真谛,并达到“出死生之至道”,并以此“至德”来彰显父母,报答父母。契嵩这种出世之孝显然与儒家的“扬名于后世,德显父母”的入世之孝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最后,“达道之纯孝”。契嵩认为物质、精神以及显亲之孝都没有触及到孝的最高层次,“天下之报恩者,吾圣人可谓至报恩者也;天下之为孝者,吾圣人可谓纯孝者也”[28],唯有“以道达之”的“纯孝”才是最高级别的孝。“养不足以报父母,而圣人以德报之;德不足以达父母,而圣人以道达之。道也者,非世之所谓道也,妙神明出死生,圣人之至道也”[29]。佛教的“达道”是指领悟佛法真谛,从生死轮回之苦中解脱出来,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盘之佛境。因此,契嵩的“大孝”把使父母觉悟佛法之真谛,超凡入圣,脱离轮回之苦,成就圣人之境界的“纯孝”作为至高至大的“大孝”。
总而言之,契嵩认为物质和精神上孝顺父母是最基本的要求,体现的是一种“世间之孝”,而更高层次的“显亲之孝”,以及最高层次的“达道之纯孝”则具有“出世间之孝”的意蕴。前两者,深为儒家所推崇;后两者则是“佛教之所独尊”。契嵩的“大孝”思想,会通儒、释,完美的融合了世间与出世间的孝道。
结语
在北宋儒学复兴的新社会思想形势之下,契嵩“以儒释佛”和“以佛摄儒”为特征的“大孝”思想,“要求把儒家伦理置于佛教戒律之上,承认儒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至高地位,并作了理论阐发,从而成为最适用于君主专制社会的原则,几乎被所有正统佛徒所遵循。”[30]契嵩的出世与入世的“大孝”思想的实质是佛教的出世伦理与儒家入世伦理消解矛盾对立,促进儒、释的融合。契嵩通过对儒家核心伦理——“孝”的接纳、吸收和转化,极大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孝道伦理思想,使宋元明清之际的佛教更大限度的为传统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并广泛的传播和普及,并成为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得佛教的存在与发展更广泛的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与支持,也为近现代中国的佛教的复兴奠定民众思想基础。
[1]陶新宏.宋初佛教教儒学化之管窥——以契嵩《辅教篇》为例[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2][北宋]孙复.孙明复小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北宋]陈舜俞.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48.
[4]刘立夫.佛教与中国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5.
[5][东晋]孙绰.弘明集[M]//大正藏(第 5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7.
[6][东晋]慧远.高僧传[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6.
[7][萧梁]刘勰.弘明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0.
[8][唐]法琳,撰.辨正论[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533.
[9][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10][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11[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12][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13][后秦]鸠摩罗什,译:梵网经[M]//大正藏(第 24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1004.
[14][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M]//大正藏(第 48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351.
[15][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16][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17][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18][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86.
[19]杨曾文.宋元禅宗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13.
[2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61.
[21][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22][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23][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2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14.
[25][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0.
[26][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2.
[27][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28][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29][北宋]契嵩,撰.镡津文集[M]大正藏(第 52 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661.
[30]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26.
B949.9
A
2095-0438(2017)12-0088-04
2017-09-09
韩绿(1992-),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思想;左金众(1991-),男,河北广宗人,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佛教史。
[责任编辑 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