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十一)
2017-04-14博特乐图郭晶晶
博特乐图郭晶晶
(1.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
蒙古族音乐研究百年(十一)
博特乐图1郭晶晶2
(1.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
蒙古族宗教音乐研究(下)
二、佛教音乐研究
蒙古族佛教俗称喇嘛教、黄教,是蒙古民族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其音乐文化是蒙古族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初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际,所谓佛教教义显现重要方式之一的佛教音乐也随即传播。它的音乐文化在历史传承、经文内涵、使用乐器、唱诵声腔及演奏方法等方面,具有其源传地印藏文化的鲜明特点。但在蒙古地区几个世纪的流传过程中,与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佛教音乐文化,并对萨满、史诗、长调、器乐、短调等其他传统音乐产生深刻影响,成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蒙古族佛教音乐的搜集整理
乌兰杰的《清代蒙古喇嘛教音乐》[1]一文中,收录了杰多尔·扎仓(经院哲学)内4首西藏乐曲,即《杜洛布》《苏德》《帕尔金》《纳木莱》;居多巴·扎仓(佛学经典)中的6首西藏乐曲,即《古勒》《纳尔斯德玛》《当令玛》《齐布当玛》《苏木登》《阿尔登》。以及蒙古诵经音乐器乐曲《小华严》;诵经调《丁哈尼森》(长调)、《诵经调》(短调)、《浴佛》;佛教赞美诗《关老爷颂》;《玛尼调》。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蒙古族佛教歌曲概述》一文中,收录佛祖、菩萨颂歌《宗喀巴颂》《观世音菩萨颂》《关老爷颂》等3首;佛经颂歌《玛尼经颂》1首;活佛赞美诗《尊贵无比》《班禅额尔德尼赞美诗》2首;寺庙、佛教胜地颂歌《格根庙颂》《南海普陀颂》2首;佛教箴言诗《救世三昧》《初生的太阳》2首;佛教仪式歌曲《朝圣歌》《库伦·玛尼》《安魂玛尼经》3首;佛教叙事歌曲《木莲救母》《唐僧取经》《童阜》《雅政词》《吉古尔旃丹》《达姆哈达山颂》6首。[2]呼格吉勒图的《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3]一文,是根据《元史》以及元代诗歌中所记载的一些资料,以及作者长期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文章中收录了《姊妹护法供养经》《十一面观音玛尼颂》《祭黄河万福经》《梅日更活佛祭灶祈愿经》4首诵经曲、《花加尔凳》这首法会器乐曲。并对元代时候蒙古寺院的佛事活动“白伞盖”、元代法曲“西番经曲”、四“扎仓”及喇嘛教音乐、“八供”及其“饶勒木”(音乐)以及寺庙的佛事活动及诵经内容以及诵经曲的演唱形式、乐器、记谱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
(二)蒙古族佛教音乐的理论研究
1.蒙古族佛教音乐的产生历史及风格发展演变研究
蒙古族佛教音乐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位音乐学家是乌兰杰先生。在《清代蒙古族喇嘛教音乐》一文中,他对蒙古族佛教音乐的历史、分类、特征等进行了概括总结。尤其对蒙古族地区佛教音乐的来源及其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总结:
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封建主俺答汗,在青海湖畔会见了西藏喇嘛教黄帽派首领索南嘉措,率其汗妃、大臣等众多封建贵族昄依喇嘛教,举行了隆重的灌顶仪式。自此,喇嘛教便大举传入蒙古草原,而原先的萨满教则遭到命令禁止,失去了昔日的统治地位。1635年至1636年间,蒙古喇嘛教高僧涅只·托因,赴东部科尔沁草原弘扬佛教,受到蒙古封建主奥巴·台吉的青睐,遂在图什业图汗“乌鲁思”境内,巴颜和朔之地封建庙宇,招收门徒,传播喇嘛教,成为佛教东渐的先锋。直至清朝初期,满清统治者为了削弱蒙古,更是大力提倡和扶植喇嘛教。于是,在蒙古草原上寺庙林立,竟有半数以上的青少年入寺当喇嘛。与此有关,喇嘛教特有的音乐文化,也随之在蒙古各地传播开来。[1]
关于藏传佛教音乐在蒙古地区的发展,乌兰杰认为,元朝覆亡,蒙古人退回塞北草原,曾一度放弃佛教信仰,佛教音乐亦随之衰微。蒙古地区的佛教音乐真正得到传播,并且站稳脚跟,以致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还是16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2]自从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来,西藏的佛教音乐便传入蒙古高原和中原地区。1578年,土默特蒙古部封建领主阿勒坦昄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取缔萨满教以来,藏传佛教音乐更是以空前规模传播,席卷整个蒙古高原。清代以来,藏传佛教音乐依旧兴盛,且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佛教歌舞剧形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蒙古族喇嘛音乐家开始追求佛教音乐的民族化。诸如,创作蒙古语诵经调和佛教颂歌、叙事曲等。器乐方面,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寺庙,出现所谓“经厢乐”,吸收汉族民间乐器和乐曲,出外作法事时为民众演奏,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4](55)呼格吉勒图认为,从17世中期开始,在清朝统治阶级和蒙古封建贵族的扶持下,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发展到鼎盛时期经过200余年的传播和发展,深入到整个蒙古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领域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那些丰富多彩的喇嘛教音乐,无论从它的音乐形态还是风格特征都具有其独特的一面。特别是在喇嘛教音乐中占有中心地位的各种诵经曲和法会器乐曲,在它传承的过程中既保留了原来的风貌,又有了地区特色。[3]
关于蒙古佛教音乐的来源,乌兰杰认为,从渊源上关系上说,蒙古族喇嘛教音乐是从西藏传入的。但究其输入的途径,却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例如,香火鼎盛、僧侣众多的某些大寺庙,往往直接派人前往西藏或青海,从那里学习喇嘛音乐与查玛舞蹈,而那些偏僻地区的小庙则无力进藏,只好派人到近处大寺庙,从那里坚决学得必须的宗教音乐舞蹈。乾隆年间,为了使蒙古各地的喇嘛教音乐舞蹈走向规范化,北京雍和宫从西藏聘请一批高僧,专门传授喇嘛教音乐舞蹈。为此,蒙古各地寺庙均曾派喇嘛进京,在雍和宫接受训练。然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蒙古族喇嘛教音乐舞蹈却经历了一场民族化、群众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过程。[1]色仁道尔吉认为,蒙古族音乐源于西藏佛教寺院,使用的诵经音乐、乐舞(又称法舞)表演、乐器及演奏方式与藏区基本相同。记谱多使用来自西藏藏传佛教的图形乐谱——央移谱。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是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部分,是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在传播和流传过程中与蒙古族原有的音乐文化产生碰撞、融合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5]包·达尔罕认为,蒙古佛教来源于西藏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但不等同于藏传佛教。蒙古佛教音乐文化是包容藏族、汉族、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综合音乐文化,是一个含多元性质的音乐复合文化体。蒙古佛教及其音乐文化的形成,是不同民族的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融汇于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藏传佛教的流入蒙古地区则是蒙古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形成的关键。[6]

图1 蒙古族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
关于蒙古族佛教音乐时代风格的发展与演变这一问题,乌兰杰认为,是沿着以下方向开展的:(一)推行“拿来主义”,全盘接受西藏佛教音乐,同时又兼收并蓄汉族、西夏、乃至印度的佛教音乐,呈现出多民族文化色彩。(二)将外来的藏传佛教音乐加以改造,使之适应蒙古人的音乐审美习惯,逐渐走向民族化。(三)在佛教文化迅猛发展得背景下,蒙古人创造出了自身富有草原特色的佛教音乐,使佛教音乐风格彻底转变,与民族音乐传统风格完全接轨。[2]呼格吉勒图认为,总的来说,喇嘛教音乐虽为纯碎的宗教音乐,但并没有脱离开时代文化的大背景而独立存在,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在今天它和民俗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也存在着群众化、多样化以及多元化的发展迹象,体现着艺术生存的适应性特点。[3]包·达尔汗认为,蒙古佛教是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与固有文化相撞、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其音乐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文化质点,具有多元的文化特性。[7]博特乐图认为,13世纪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仅晋中于元大都城内。16世纪北元俺答汗时期始,藏传佛教音乐随佛教的广泛传播,逐步走向蒙古化的道路,包括诵经调、查玛、经堂乐、法会乐等在内的佛教音乐在广泛流传的同时,在一些地区得到了民族化改造,逐渐与当地民俗文化生活相结合,发展成为蒙藏文化交融生成的重要体裁。[8](395)以乌拉特梅日更寺为代表的一些寺庙,将藏语佛教经文翻译成蒙文,并开创蒙古语诵经,重新编创查玛舞、设计经堂乐,从而实现了藏传佛教音乐的本土化、民族化改造。成为蒙古族传统音乐又一个重要源头。[9]使之最终成为蒙古地区重要的、全民化的文化现象,广泛被蒙古部众接受。因此,在以后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佛教音乐文化除了藏区传入的佛教音乐艺术外,广泛吸收汉地传入的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并融合蒙古族传统萨满教和民间传统文化的因素,形成了具有多元一体的宗教音乐文化。[8](395)
2.蒙古族佛教音乐的分类研究
关于蒙古族佛教音乐的分类问题,乌兰杰指出,蒙古族佛教音乐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声乐、器乐、又有歌舞、宗教歌舞剧,堪称琳琅满目。“梵呗清越,朝鼓暮钟”与博大精深佛教学说相适应,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佛教音乐体系。[2]呼格吉乐图将其分为诵经、器乐曲和查玛乐舞音乐等三部分。他认为,各寺庙的乐曲音乐在活动方式、使用场合、音乐形态特征方面皆基本相同,但还略有差异。[3]包·达尔汗认为,蒙古佛教音乐的表现形式有纯声乐、纯器乐、声乐加器乐、舞蹈加器乐、表演歌唱剧等几类。其中以声乐(包括声乐加器乐)的数量最多。[10]色仁道尔基根据其宗教活动场合、仪式内容和音乐演奏形式等体裁特征,将蒙古族佛教音乐诵经音乐、乐舞音乐、佛教剧音乐及器乐音乐。他将蒙古族佛教音乐分为诵经音乐和器乐音乐两大类。[8](395)《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一书,根据其宗教活动场合、仪式内容和音乐演奏形式等体裁特征,将佛教音乐分为诵经音乐、乐舞音乐、佛教剧及其器乐音乐。其中蒙古佛教音乐的构成包括诵经音乐和器乐音乐两大类。[8](395)
(1)诵经音乐研究
乌兰杰将蒙古寺庙中的佛教“声乐”基本上分为两个类型,一是诵经调:包括藏族风格的诵经调,以及蒙古风格的诵经调,蒙古喇嘛在朝暮课读、法会诵经时用之。二是佛教歌曲:包括颂歌和赞美诗、箴言诗、仪式歌曲、叙事歌曲[2]他在《蒙古族佛教歌曲概述》一文中,详细的对蒙古族佛教歌曲的各类体裁形式做了详细的介绍。
关于蒙古风格的诵经调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乌兰杰认为,在喇嘛教音乐中,诵经调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从其渊源关系上说,喇嘛寺庙的诵经音乐,分为西藏风格与蒙古风格两大类别。佛教东渐之初,从西藏直接引入的诵经调,虽说产生了某些变化,已不同于西藏的诵经音乐,但基本上却保持着西藏风格。另外,喇嘛们将有些佛经从藏文译成了蒙古文,陆续出现了一些采用蒙古文诵经念佛的喇嘛寺庙。这样,原先的诵经调便不完全适合于蒙古佛经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蒙古喇嘛们编创了一些新的诵经调,经过学识渊博的高僧们审议批准,即科学习实用。后来,大凡在群众中作法事时经常念诵的藏文佛经,也都配上了蒙古风格的诵经调,并受到了广大信徒的认同。[1]呼格吉乐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喇嘛寺庙的诵经调,可分为西藏风格、藏蒙的合流风格和纯蒙古风格三大类。[3]包·达尔汗将蒙古佛教诵经音乐包括藏语诵经音乐和蒙古语诵经音乐。[7]他还认为,声乐体裁音乐主要用于诵经活动,所以称这一类音乐为诵经音乐。蒙古佛教的诵经音乐按照经文文字和念诵语言的不同,分为藏语诵经音乐和蒙古语诵经音乐两种。两种诵经音乐在语言上虽有很大差别但在音调上共同体现了多韵白、以宣叙性为主的特征。[7]博特乐图,蒙古族佛教诵经音乐(又称经堂乐、法会乐、诵经调),是喇嘛在佛教经典的唱诵过程中,与蒙、藏语言韵律特征紧密相结合的,具有宣叙性特征的“旋律语言”。音乐多为念、诵、唱交替进行,其旋律紧跟于经文的韵律、语言的抑扬顿挫而起伏,其音域不宽,旋律音程以级进为主、起伏较小,节奏整齐有序。他根据类型和功能,将佛教诵经音乐分为佛教经典诵经音乐和特定节日祭祀、祝颂经文诵经音乐。又按照经文文种、诵经语言的不同,将诵经音乐又分为蒙古语诵经音乐和藏语诵经音乐两种。[8](396)
关于藏语诵经音乐,是指蒙古佛教寺院吟诵藏传佛教原经典时,用藏语念诵过程中产生的音乐。乌兰杰认为,从西藏直接引入的诵经调,虽说产生了某些变化,已不同于西藏的诵经音乐,但基本上却仍保持着西藏风格。[1]包·达尔汗根据蒙古喇嘛寺院传诵的藏语诵经音乐的经文所涉及内容的文化特征,将其分为“原经典”诵经音乐和“关公经”诵经音乐,他认为,前者属于藏族文化系统,后者属于汉族文化系统。
关于藏语诵经音乐的基本特征,博特乐图认为,藏语诵经音乐的基本特征:韵律紧密结合藏语发音特征,具有沉稳、宁静的色彩。旋律主要以二、三度级进为主,在段落结束处出现一些大跳音程收束终止。整体特征是:音域不宽,音高变化较少;节奏整齐,音调变化较多,乐器为鼓、锣等打击乐器和哄哈(铃)、达玛加(鼗鼓)、毕西古尔(唢呐)、冈令(羊角号、胫骨号、冈咚)等体质较轻便,发音轻柔的乐器。[8](397)
蒙古语诵经音乐是指念诵翻译成蒙古语的佛教经典或蒙古文创作的祭祀、祝颂词。关于蒙古寺院的蒙古语诵经活动何时开始,没有确切的记载,目前众说纷纭。真正开始用蒙古语诵经的确切时期始16世纪初,是由蒙古高僧涅只·托音呼图克图(1557-1653)发起并鼎力推行于一些寺院的。在他的倡导、实践以及其后世众多弟子的不懈努力下,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诵经体系和诵经制度[11],并在1629年开始科尔沁地区的巴音胡硕庙、呼和浩特市的小召寺、乌拉特梅日更寺、巴林右旗的特古斯布日德格勒图寺、阿鲁科尔沁旗的赫西格图格齐寺、敖包罕寺(援宁寺、隆安寺,1663年)等寺院均有过蒙古语诵经。蒙古语诵经音乐保留藏语的原有语音特征的同时,与蒙古语经文的韵律风格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蒙古语诵经音乐的独特风格。
关于诵经音乐的音乐形态问题,乌兰杰认为,诵经音乐又有长调与短调之别。例如,《古勒》《道克希德》《塔本·王》诸经,属于长调范畴。短调则节奏规整,曲式短小,具有吟诵性特点。喇嘛诵经调中,偶尔也能听到多声部音乐,只是在长调诵经音乐中有所发现。[4](56)而蒙古语诵经音乐保留藏语言的原有语音特征的同时,与蒙古语经文的韵律风格有机结合,最终形成了蒙古语诵经音乐的独特风格。[8](396-397)关于诵经调的演唱,乌兰杰根据不同音域与音色,又将喇嘛教诵经调分为三种声部,一曰“宝尔·浩赖”,即是低音;二曰,“哈木·浩赖”,则是中音;三曰“星根·浩赖”,便是高音。[4](56)
蒙古语诵经调是与以希日巴喇嘛为首的一批保守派高层喇嘛的“保持藏语诵经”的主要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后来,第一世涅只·托因的大弟子第一世梅日更葛根继承师业,在乌拉特西公旗将蒙古语诵经付诸于实践,并通过历史葛根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而完善的蒙古语诵经传统。目前学界关于蒙古语诵经音乐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梅日更葛根与蒙古语诵经音乐的研究加以展开。
包·达尔汗的《罗桑丹毕坚赞与蒙古语诵经音乐》[12]和《梅日更召蒙古诵经音乐》[13]主要论述了罗桑丹毕坚赞创编的蒙古语诵经音乐的语言特点及他对诵经音乐做出的贡献。《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匠梅力更葛根》[9]一文的作者,论述了梅力更葛根洛布桑丹毕坚赞对蒙古诵经音乐的贡献,重点论述了梅日更葛根创作“希鲁格哆”。梅日更葛根通过“希鲁格哆”,把自己的思想观念传输于民间社会,来影响人们的习俗生活,从而创造出一种又符合佛教思想要求,又合乎蒙古族传统习俗规范的礼俗新秩序。作者认为,梅日更葛根在印藏文化与蒙古传统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又在宗教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开拓出一条大道。宗教大师的虔诚与冷静,艺术家的浪漫与激情,在这位杰出人物的身上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相互并存的、和谐相依的同一体,使他的一生光芒四射,因此他也成为蒙古族音乐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音乐巨匠。博特乐图认为,三世梅日更葛根在蒙古语诵经中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种叫“均整沙德”的方法。他根据蒙语诗歌的格律特点和蒙语音节的分节规则,对诗行内字数、音节、格律、音步等进行均整,将蒙语音节重音、音步律动与唱经音乐的节拍节奏匹配起来。其次,通过均整“沙德”解决蒙古语诵经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在保证佛教诵经音乐原来风貌的前提下,他创造性地结合蒙古族民间祝赞词、祈祷词和民歌的吟唱规律,创编出了富有蒙古民族风格的诵经曲调。[8](398-400)
有关蒙古族诵经音乐的研究还有楚高娃的《蒙古族诵经音乐中唱诵音乐的形态类型初探》[14]、《透过文本看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15]和《蒙古语诵经音乐中乐器的演奏方法》[16],红梅的《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化因素——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17]等。
(2)佛教乐器和器乐音乐研究
乌兰杰认为,蒙古寺庙中的喇嘛乐队,所谓法器与乐器之分。法器,指的是唢呐、长号(布列)、短号(罡洞)、海螺(洞),以及鼓、钹、铙、铃等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就其宗教功能而言,这些乐器只用于念经诵佛,跳查玛等场合,故谓之法器。与“法器”相对,喇嘛们遂将笙、管、笛、箫,以及云璈、拍板之类,统称之为“乐器”。另外,喇嘛乐手中除却有人擅长演奏四胡、马头琴、三弦等乐器外,寺庙乐队中是从不使用弦乐器的。[1]
包·达尔汗认为,蒙古族地区佛教音乐的器乐,根据其被使用的场合可以分为“寺院乐曲”和“非寺院乐曲”两大类。“寺院乐曲”是指在喇嘛寺院内的各类佛事活动中演奏的佛教器乐曲。“非寺院乐曲”则是相对于“寺院乐曲”而言的,是在喇嘛寺院外的场所举行的具有一定佛教意义的各种活动中,由喇嘛乐师演奏的佛教器乐曲。他将蒙古佛教乐器(法器)分为体鸣类乐器;膜鸣类乐器;气鸣类乐器;将蒙古佛教器乐曲分为寺院乐曲和非寺院乐曲。[18]博特乐图认为,佛教器乐音乐是喇嘛艺人在寺院内外诵经、乐舞表演等各类仪式中演奏的有较高演奏水准的纯器乐曲。佛教器乐音乐是佛教教义内涵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包括佛教乐舞“查玛”音乐、佛教乐舞剧和寺院乐曲。佛教器乐音乐是佛教教义内涵表现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包括佛教乐舞“查玛”音乐、佛教乐舞剧音乐和寺院乐曲“扎尔登”等。其形式主要有诵经过程中与诵经曲调交替演奏的纯器乐曲(喇嘛艺人称之为扎尔噔)、“查玛”表演或佛教乐舞剧表演时的具有一定伴奏性质的器乐演奏、寺院内外的各种法事或民间民俗活动中演奏的佛教乐器合奏曲。[8]
呼格吉乐图将喇嘛器乐曲分为“法会乐曲”与“世俗乐曲”两大类。[3]博特乐图将蒙古族佛教器乐音乐分为两种形式,一为,藏传佛教传统乐曲,利用佛教固有的乐器,在佛教仪式和各类佛教法会上演奏的器乐音乐,其旋律古朴、典雅、宁静、与诵经活动或佛教乐舞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寺院佛事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另一为源自汉族民间曲牌,并与蒙古族有些民间曲调相融合,由汉族传统的吹打乐器演奏的,在各种民间仪式上表演器乐曲。[8](406)
包·达尔汗认为,在蒙古各寺院中使用乐器的种类和形制基本相同,只有个别的差异,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存在于蒙古地区的东部(主要是科尔沁、蒙古贞、喀喇沁以及周边地域),由于这些地区与汉族文化接触得比较早且又频繁,汉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比较大。
(3)查玛乐舞音乐研究
“查玛”,俗称“跳鬼”“打鬼”,源于藏族“羌姆”,是各寺院举行大型佛事活动时进行表演的鬼神面具舞蹈,属宗教乐舞形式。“查玛”一字是蒙古族沿袭了藏语“羌姆”之发音,13世纪初随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羌姆”在蒙古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传承与发展,逐渐形成了鲜明蒙古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乐舞。查玛乐舞是在藏传佛教乐舞“羌姆”的基础上,逐渐吸收、融合蒙古族传统的萨满艺术有些神灵舞蹈、请神娱神灯祭祀舞蹈以及蒙古族民间音乐舞蹈灯形式而形成的,具有蒙古族音乐文化特色,融蒙、藏民族宗教音乐文化为一体的佛教乐舞形式,是蒙、藏宗教文化交流的产物。其音乐属于纯器乐音乐,使用打击乐器和吹管乐器进行伴奏。
关于查玛乐舞音乐,色仁道尔吉的《论佛教乐舞“查玛”艺术——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届硕士学位论文)以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及其在内蒙古地区的传播为对象进行了研究。试图通过对藏传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对查玛乐舞的内容形式、表现特征及对蒙古族音乐文化方面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查玛乐舞是怎样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并形成为独具特色的宗教艺术种类。另一方面,深入分析佛教乐舞查玛艺术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受到的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态之影响。
额尔德尼所著《蒙古查玛》[19],是一部关于佛教查玛歌舞的系统专著。该书首先对蒙古查玛的来源以及查玛在蒙古族当中的传播历程进行梳理,分别对梅力更葛根创编的查玛经和丹毕巴拉珠尔创编的查玛以及对北京和蒙古地区几座主要寺庙的查玛进行了介绍。根据功能,书中将蒙古查玛分为祛灾查玛和祭祀查玛两类,共列举19种。尤其珍贵的是,书中还就“陶孙查玛”(偶人查玛)、《木莲救母》《月亮布谷鸟传奇》《古日道》等传统查玛形式和经典剧目进行了详细说明,从查玛民俗、查玛乐曲、查玛服饰、查玛角色、查玛舞蹈动作、查玛典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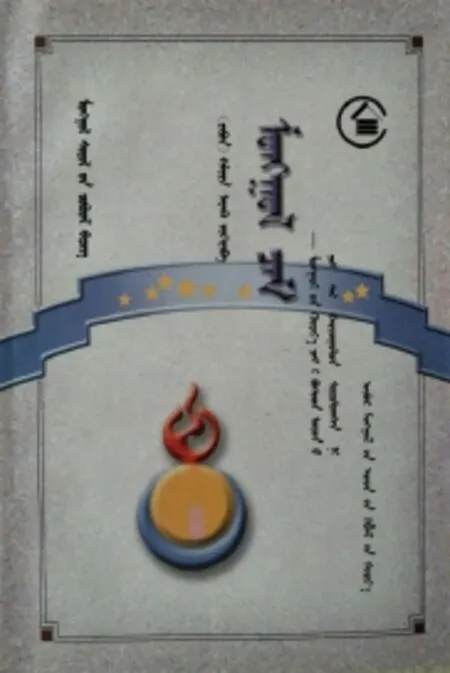
图2 《蒙古查玛——蒙古国库伦查玛与其他地区查玛的比较研究》书影
日本学者木村理子所著《蒙古查玛——蒙古国库伦查玛与其他地区查玛的比较研究》[20]一书,从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角度对蒙古族查玛进行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这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库伦查玛”的系统介绍,其中包括查玛乐器、道具和乐器等音乐相关内容。第二部分是对拉卜楞寺、雍和宫、大召寺、梅力更寺等近二十座寺庙查玛歌舞的简要论述。第三部分是库伦查玛与这些其他各地寺庙查玛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中,对查玛器乐文化的宗教根源进行阐释,指出查玛器乐有吹奏乐和打击乐两种,而无弦乐器。这是因为,佛教认为弦乐器是对上层佛圣所享用乐器,查玛歌舞中没有佛祖,而是其下层的神灵、神仙,故不用弦乐器。
3. 佛教音乐的专题研究
卓娜的《草原“圣”会——呼伦贝尔地区甘珠尔庙宗教音乐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0届硕士学位论文)一文主要运用民族音乐学局内人与局外人双视角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甘珠尔庙大法会仪式音乐实录进行研究。同时,笔者借用音乐文化丛分类系统,审视了甘珠尔庙仪式音乐分类的问题。对甘珠尔庙仪式音乐从核心、中介、外围三个层次进行划分。此外,通过对甘珠尔庙仪式音乐功能及文化特征的透析,从宏观把握甘珠尔庙音乐文化传统及变迁。楚高娃的《蒙古语诵经音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本文通过对蒙古语诵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特征的研究来解释藏传佛教的蒙古化过程。任静的《乌拉特中旗席热庙佛教音乐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内蒙古大学2015届硕士学位论文)一文将乌拉特中旗席热庙置于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通过对乌拉特中旗席热庙音乐文化这样一个缩影的研究,体现出藏传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民族化历程及其表现出来的诸般特征,通过“微观”与“宏观”的研究模式,结合翔实的田野调查,分析乌拉特中旗席热庙佛教音乐的文化特征,进一步阐释其中藏传佛教音乐文化与蒙古族固有的文化之间的融合现象,并对席热庙的社会组织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多元质点进行阐释。
包·达尔汗的《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是一部从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的多学科角度对佛教音乐进行的系统性研究成果。作者以自行设计一种方法——“质点扩散性文化观照法”,试图将相对凌乱的文化质点规整于一个体系之内,以实现对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质的具体讨论。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探讨蒙古佛教音乐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提出“蒙古佛教及其音乐文化是一个包含了不同文化特质的复合的文化体。是一个具备了多元族别的文化结构体。蒙古佛教文化在丰富的文化特质分属于藏、汉、蒙古三个不同的文化范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汇合到一起,相互涵化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的观点。第二部分,作者充分发挥其“质点扩散性文化关照法”,从基础技术层面的多元质点、社会组织层的多元质点、思想意识层的多元质点等三个方面,阐述蒙古佛教音乐文化诸层面的多元质点。2006年该书出版蒙文版《蒙古佛教音乐》(蒙文,包·达尔汗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萨满教、佛教是包括宗教学、历史学、民间文学、民俗学、语言学、音乐学、舞蹈学在内的诸学科共同关注的领域,而音乐是蒙古族萨满教、佛教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蒙古学各学科领域,从各自的角度和不同的侧重度,对萨满教、佛教中的神歌、器乐、舞蹈等音乐相关领域进行研究,而音乐学界也把宗教音乐的探讨,放置在宗教本身的整体结构当中进行研究,以此来揭示音乐在宗教与仪式中特定的意义和功能,阐释其不同于世俗民间音乐的特征。
[1]乌兰杰.清代蒙古族喇嘛教音乐[J].中国音乐学,1997(1).
[2] 乌兰杰.蒙古族佛教歌曲概述[J].音乐研究,1999(4).
[3]呼格吉勒图.内蒙古藏传佛教乐曲考[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0(4).
[4]乌兰杰.蒙古学百科全书·艺术[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3年.
[5]色仁道尔吉.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研究概说[J].内蒙古艺术,2006(1).
[6]包·达尔汗.藏传佛教及其音乐文化流传蒙古地区缘由探究[J].中国音乐(季刊),2008(3).
[7]包·达尔汗.蒙古佛教诵经音乐的多元文化特征[J].中国音乐学,2002(3).
[8]博特乐图.蒙古族传统音乐概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
[9]博特勒图.18世纪蒙古族音乐巨匠梅日更葛根[J].内蒙古艺术,2003(2).
[10]包·达尔汗.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11]包·达尔汗.论蒙古佛教音乐文化的多元性[J].中国音乐学,2002(3).
[12]包·达尔汗.罗桑丹毕坚赞与蒙古语诵经仪式[J].内蒙古大学学报,2006(5). [13]包·达尔汗.梅日更召蒙古诵经音乐[M].载巴图查干、塔木、巴·孟和编著.梅日更葛根研究萃集[M].(蒙文)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14]楚高娃.蒙古族诵经音乐中的唱诵音乐的形态类型初探[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12(3).
[15]楚高娃.透过文本看蒙古化的藏语诵经音乐[J].民族艺术研究》,2016(5).
[16]楚高娃.蒙古语诵经音乐中乐器的演奏方法[J].大众文艺,2011(12).
[17]红梅.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胡因素——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J].世界宗教文化,2011(5).
[18]包·达尔汗.蒙古佛教器乐曲种类[J].音乐研究,2002.
[19] 额尔德尼.蒙古查玛》[M].(蒙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20] [日]木村理子.蒙古查玛——蒙古国库伦查玛与其他地区查玛的比较研究[M].(蒙文)白音门德转写,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黄隽瑾】
Centuries Research on Mongolian Music(PartⅪ)
Boteletu1, GUO Jingjing2
(1.Art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Inner Mongol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J609.2
A
1672-9838(2017)01-121-07
2017-03-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蒙古族传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13JJD76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博特乐图(1973-),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库伦旗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晶晶(1982-),女,达斡尔族,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