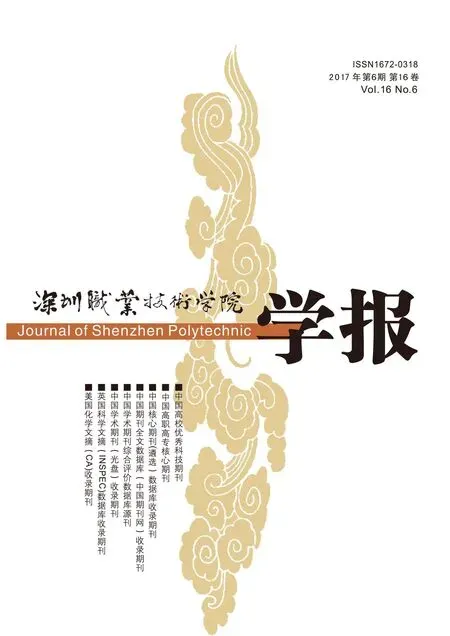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诗人的生命意识
2017-04-13林玲,罗明
林 玲,罗 明
论中国现代诗人的生命意识
林 玲,罗 明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广东深圳518001)
中国现代诗人的生命意识,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是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他们在创作理论上,强调观照生命、体验生命和表现生命的生命美学。在诗歌作品中,充满了对生命的爱和温情,对残忍行为和暴虐者的激愤与仇恨,创作了琳琅满目的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的生命意象。
现代诗歌;生命意识;生命美学
目前,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人本思想”将极大地推动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时代的能动力量。在这一背景之下,回归人本逻辑的探索,成为了新时代理论探索的重要主题。我们回顾人本思想的历史,就有着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人本思想发展的研究和现代诗歌的研究中,中国现代诗人的人本思想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因此,不管是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还是从诗歌史研究的角度看,探讨现代诗歌的人本思想及其对现代诗歌美学的影响,都是有待开拓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一点系统的探索,重点评述中国现代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关怀。这是因为生命意识是人本思想最核心的内涵,也是现代诗歌最核心的思想内涵。
1 创作理论中的生命意识
现代诗歌作者众多,繁星闪耀。诗人组织各类社团,形成各种流派,出现了百花争妍的创作局面。孙玉石先生研究中国现代诗歌流派,得出这样的结论:“新诗的不同流派的发展共同建设了现代诗歌的艺术传统。他们是郭沫若和闻一多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艾青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戴望舒代表的象征主义传统。”①
不同的传统自然有不同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就是同一传统内部,各位诗人也有他们的独特探索。但是作为同一时代的诗人,他们的诗歌有着共同的基本主题,这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正如周作人所概括的:“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②人道主义的目标,是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实现人性的解放,使人的自然本性和感情欲求得到自由发展。兽道的核心是摧残人、消灭人;神道的核心是从精神上桎梏人;人道的核心是尊重人、解放人。所以,早期的重要诗人康白情说:“我觉得做人是我们的事业,发挥人性是做人所必具的条件。我想从兽性和神性底中间,找出人性来。”③康白情的诗的创作,是实践了他的理论的。其他诗人的创造,也实现了这一目标。于是现代诗歌便闪现着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光辉。“人”,这一面光辉的大旗,飘扬在现代诗歌繁星闪耀的长空。
人的存在,不是无生物的存在,而是生命的存在,而且是高级生命的存在,是万物之灵的存在。尊重人,即是尊重生命;解放人,即是解放生命,解放生命力,解放生命的创造力。现代诗人观照生命的存在,体验生命的存在,集聚了内容丰厚的生命意识。诗人将自己所体验和观照的生命意识,用自己所体验和观照的生命形象表现出来,创造出千千万万优美动人的意象,具有生命特征和审美特征的意象,感动和启迪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群。现代诗歌的园地,绽放着表现生命之美的鲜花,其中的精品,是数也数不清的。
与此同时,诗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天才和直觉,创造了观照生命、体验生命、表现生命之美的独特经验和方法,形成了一套具有独立价值和创新意义的诗歌创作美学。这就是生命美学。
如果要概括现代诗歌的思想特征,那就是四个字:生命意识;如果要总结现代诗歌的审美特征,那也是四个字:生命美学。中国现代诗歌的魅力,也就是这八个字: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生命意识是它的思想魅力,生命美学是它的艺术魅力。当然,这两种魅力是水乳交融般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诗歌中,没有脱离生命美学的生命意识,因为生命意识是蕴含在审美意象中的。同样也没有脱离生命意识的生命美学,因为,审美意象的灵魂是生命意识。没有生命意识,何来生命美学?
中国现代的诗人们,不是盲目的创造者。而是自觉的创造者。他们是自觉地主动地进行着生命的观照、体验和表现,自觉地主动地创造着生命意识和生命意象。就三大艺术传统而言,不管是哪个传统,诗人们的共同追求都是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的创造。这在他们的创作中有明确的表述。
浪漫主义传统的代表诗人郭沫若在《论诗三札》中说:“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这种冲动接触到我们,对于我们的人格不能不发生影响。”④人格,作为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的综合,正是人的生命的表征,也是人的生命的要素。人格创造冲动,是生命创造冲动的最主要内容,它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这种创作冲动的结果,只能是饱含生命意识的生命意象。
浪漫主义传统的另一代表诗人闻一多是认可并赞颂这种冲动的。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他引用了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中的诗句:“大都会底脉搏呀!/生底鼓动呀!/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诗中写道的大都会是一个生命意象,因为它像人一样,有脉搏的跳动。“生的鼓动”,即“生命的鼓动”。闻一多在引用之后,用赞赏的口吻说:“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阅《新生》与《笔立山头展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⑤所谓“压不平的活动之欲”,在郭沫若那里叫“人格创造冲动”。对于郭沫若由生命冲动、生命体验而创造的生命意象,闻一多予以充分的肯定。
象征主义传统的代表诗人戴望舒,也有自己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他在《望舒诗论》中说:“诗当将自己的情绪表现出来,而使人感到一种东西,诗本身就像是一个生物,不是无生物。”“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种笔触又须是活的,千变万化的。”⑥不仅诗的内容——情绪,是生命的博动,而且诗的表现也必须是“活”的,即是有生命的。创作出来的诗才可能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生物),而不是无生命的东西(无生物)。在“生物”和“无生物”的对比中,凸显了戴望舒鲜明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
戴望舒还说:“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达这情绪的形式。”⑥这“新的情绪”是什么?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穆木天的话可以作此语注脚。穆木天说:“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要有大的暗示功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深处。诗是要暗示出人的内生命的深秘。”⑦可以说,戴望舒所说“新的情绪”,与穆木天所说“潜在意识的世界”、“内生命的深秘”意思相同。象征主义诗人强调“内生命”,而在形式上强调暗示,这是他们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的特殊之处。
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诗人艾青也同样高扬“人”的旗帜,关注诗歌的生命意识和生命美学。在《诗人论》一文中,强调生命体验对于诗人的重要:“因世界充满欺诈,倾轧,迫害,而对世界流连;因生之历程是无限的颠簸与坎坷而爱生命。”同时也强调艺术表现中生命精神对与形象的灌注和契合:“只有在诗人的世界里,自然与生命有了契合,旷野与山岳能日夜喧谈,岩石能沉思,河流能絮语……”⑧
三大艺术传统的诗人共同的追求,于上引述可见一斑。而共同追求中的各自特色,也可略窥端倪。如浪漫主义诗人主观生命欲望的宣泄,偏重于显意识的、抒情方式多是直接的。象征主义诗人注重潜意识、内在生命的体验,表现方式侧重间接的暗示。现实主义诗人偏于客观世界现实生命的历程和表现,与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们的偏于主观大相径庭。他们的诗,与现实生活较多直接的联系,因而在较长时间受到研究者的青眯。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区别是存在的。但是,三大艺术传统各自对生命意识的建构,对生命美学的创造,都不可抹杀。他们的经典诗篇,已汇入中国现代文化的洪流,成为充满魅力的不朽之作。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供我们鉴赏,给我们启迪。
2 诗歌作品中的生命意识
中国现代诗人的生命意识,最基础最核心的内容是尊重生命,热爱生命。以抒情为主的现代诗歌,到处充溢着诗人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情怀、情结和情愫。面对生命,特别是弱小的生命,诗人胸中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情。而面对毁灭生命、摧残生命的残暴行为和暴虐者,诗人则充满了激愤,充满了仇恨。爱与恨,交织在现代诗篇中,呈现为使现代诗歌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
2.1 对生命的珍爱
面对生命,诗人之所以会产生爱的温情,首先因为生命本身不仅是可爱的,而且是可贵的,诗人体验生命的存在的时候,因此才会油然而生爱的情感。而爱对于生命本身来说,也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特别对于弱小的生命,更是需要爱,需要同情。在现实生活中,爱有时可以给绝望者以希望,甚至能挽救生命。这些体验和认识,对于现代诗人来说,是普遍的事实,因而反映在他们不同的诗篇之中。
诗人是博爱者。他们所爱的生命,不仅是人类的生命,而且包括自然界的生命。因为他们是诗人,而诗是用意象来表达情感的,所以他们也常常用自然界的生命意象来寄托自己的爱感。自然界的草木花朵,形象鲜明,色彩绚丽,更能体现生命的可爱和美。自然界的生命意象,并非只是代表自然生命,同时也是人类生命的象征。
《地球,我的母亲》,是创造社诗人郭沫若的代表作之一。这首直抒激情的诗,在表现了对“田地里的农人”和“炭坑里的工人”的“羡慕”,以后,紧接着就表达了对自然界生命的“羡慕”:“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那一切的草木,我的同胞,你的儿孙,/他们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享受着他们的赋生。”羡慕,是仰视的爱。对草木的爱,爱的是它们的“赋生”,即自然赋予的生命,因而是生命之爱。自然界的生命值得羡慕,它们的生命最能体现生命的自由本质。自然界的生命是美丽的,因为它们的生命是自由的、自主的。诗人郭沫若,既爱人类的生命,也爱自然界的生命。
生命的可贵在于它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的自身。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比不上拥有生命重要,都不比生命的存在更有价值。因此,诗人不仅体验生命的可爱,更体验生命的可贵。诗人对生命的爱,不纯是欣赏的爱,更包含着尊重和珍惜,因而是珍爱。
陈梦家的《九龙壁》,是一首寓言诗,其寓意,正是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诗人要赐给九天龙以庄严、骄傲、神奇、云彩、膂力、灵眼、神通,但被九条龙拒绝了。这些人所具有的能力、品格、荣耀,远远没有生命本身有价值,因为离开了生命的存在,这些东西都不过是虚幻的,无价值的。所以九龙壁中的九条龙什么都不要,只要生命——“九条龙一齐喊:我们要生命!”。古代的画家,讲气韵生动,讲画龙点睛,追求的是形象的生命感。雕塑当然也是如此。但陈梦家的这首寓言诗,其立意并不在专讲雕塑形象的生命感,而是讲的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可贵,传达的是现代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
正因为人的生命价值高于其他价值,所以生命是宝贵的,不能随便抛弃,更不能受到侵害。只有为了更多生命的保存,才可以牺牲某些个体生命。即使是这样的牺牲,不仅是不得已,而且是十分痛苦的事。诗人在写这样的牺牲者的时候,伤悼之情也仍然忍不住溢于言外。新月派女诗人林微因,三弟在抗战的一次空战中阵亡,她有一首《哭三弟恒》。三弟为了“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而献出“生的权利”,诗人是肯定的,因此她写道:“弟弟,难为你的勇敢”。但是,“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那是不会消逝的。
汉园派诗人李广田,在《消息》一诗中描写,弟弟穿上旧军衣去前线作战,并传消息告诉哥哥:“是为了生,要先去死!”诗人写道:“故乡的原野该是枯寂的,/然而那多沙的土地上一定染了血迹……”这悲壮的场景描写,既有对弟弟浴血沙场的肯定,也有难以排遣的悲悼。
九叶派诗人穆旦,有组诗《森林之魅》,副标题是《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其中的《祭歌》中写道:“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战争,/你们的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生命是不能随便牺牲掉的。只有为了更多生命的保存,牺牲个体生命才有意义。肯定有价值的牺牲,同样体现诗人对生命的珍爱。
诗人提醒人们要尊重生命,不要轻视生命,不要忽略生命的存在。新月派诗人刘梦苇,对“可爱的姑娘”说:“莫要把人命看同鹅绒轻!”(《最后的坚决》同属新月派的诗人于赓虞,质问忽略花卉存在的园丁:“你不诚实的园丁,怎不,怎不返转园篱?/如何忍,如何忍这祖园的花卉,棵棵萎去!”(《花卉已无人理》)花卉是生命的象征,花卉的枯萎是生命的枯萎。这里所批评的,正是忽略生命的现象。说明生命是宝贵的,不容忽略的。
2.2 对残忍的谴责
一个热爱生命、悲悯生命弱者的诗人,面对虐待生命、摧残生命甚至毁灭生命的残忍行为,是不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的,他在哀悼生命的不幸的同时,必然会产生激愤、震怒等多种复杂的情感,从而爆发创作冲动。这样,表现激烈的愤怒情感的诗篇就诞生了。这样的诗篇,其内容就不仅仅是悲悯、伤悼,而更多的是悲愤、谴责和控诉。
在一个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善良的生命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经常受到处于强势地位的暴虐者的欺凌。在现代诗歌产生的时代,中国社会刚刚结束封建帝制,处于新旧军阀的统治之下,而且还遭受到列强的欺压和侵略,暴虐者欺凌甚至残害弱者的现象时时可见。这些,必然反映在现代诗歌的描写中。现代诗人所面对的暴虐者有两种情况:一是国内的强权者,二是外国侵略者。诗人面对这两种暴虐者的残忍杀戮行为,都表示了强烈的愤怒和控诉。他们还以花草为喻,说明即使对自然界的生命,残忍的伤害行为,也是不能容忍的。
强权者,即是戴望舒诗中所说的“魔道者”。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是一钱不值的,是可以随意摧残和毁灭的。面对这些“魔道者”,诗人只有愤怒和忧伤。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多次发生枪击平民百姓的事件。这些平民百姓是徒手的、无辜的。诗人的同情和支持,是在平民百姓这一边。他们反对强权者对平民百姓的残酷杀害。1926年3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前,发生北洋军阀政府屠杀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激起有正义感的诗人的愤怒。诗人以正义的笔为武器,与手执凶器的北洋军阀政府抗争。就新月派诗人来说,闻一多、饶孟侃、刘梦苇都写有抗议的诗篇。
闻一多在《文艺与爱国》一文中写道:“我觉得诸志士们3月18日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⑨在《天安门》一诗中,他借洋车夫的口,描写惨案造成的恐怖:“怨不得小秃子吓掉了魂,/劝人黑夜里别走天安门。”市民的恐怖心理,当然是由军阀政府的屠杀暴行造成的。貌似客观的描写,实际包含着强烈的主观控诉。
饶孟侃有《三月十八》和《天安门》两首诗,采用现实主义笔法,揭露军阀政府残忍地毁灭生命的暴行。《三月十八》运用侧面描写,间接表现惨案现实。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子参加3月18日的请愿,结果只有一个儿子回来,而且衣襟上带有血迹。母亲担心另一个儿子的生死,归来的儿子却不敢说出兄弟惨死的真相。诗人在矛盾中展开叙述,在家庭悲剧的展示中实现了揭露和控诉的主题。叙事带着情感,读后令人激愤。
刘梦苇的《写给玛丽雅》,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愤懑”。诗人假设自己也去参加3月18日的请愿,“我胸口纵不被子弹洞穿,/怕也愤懑得破裂了喉管!”“我生命纵未被子弹打断,/但伤心的眼泪何曾会干!”“我又怎能独自地心安,享受爱情的美满和温暖?”“同情的火已经熊熊地燃,我欲手刃那卖国的汉奸!”“自古道覆巢之下无完卵,痛快的事儿是血染衣衫!”诗人“伤心的眼泪”为牺牲者而流,“同情的火”为牺牲者而燃,这是爱的泪和火。诗人的“愤懑”,则是指向“贼人”和“豺狼”的,愤懑到要手刃汉奸,“血染衣衫”!表达了报仇雪恨的意愿和决心。
1925年5月30日,上海英租界巡捕枪击在街头宣传和游行的学生、工人,打死了13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五州惨案。朱自清的《血歌》是为这次悲惨事件而作的。诗篇揭露侵略者的残酷和受害者的惨状:“破了天灵盖!/断了肚肠子!”“血是长流的!/血是长流的!/长长的扬子江,/黄海的茫茫!”而被枪杀的百姓是无辜的:“中国人的血!/中国人的血!/都是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此诗反复使用了16个“血”字,而且很多句子也是重复的。词句的反复,一是强调侵略者的残忍,二是表现自己的激烈情绪。抗议、激愤、谴责,用浓重的笔调得到充分的表达。诗人还有一首《给死者》,也是写这次事件的。
鲜血的流淌,是生命被摧残被毁灭的确证。鲜红的血的意象,对侵略者是最有力的控诉,对读者是最有力的感染和警醒。诗中此类意象甚多。表现哀伤、沉痛的意象有:日月无光,云雾弥漫,风的哀号,雨的愁惨。表现愤怒的意象有:江水的翻腾,电线杆的颤抖,城市的地震。表现同情、悼念的意象有:人民的哀哭和沉默,以及花的黯淡、鸟的无言。
谴责侵略者残忍暴行的诗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将诗人愤怒的情感和行动的意志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有道义上的谴责,又有反抗的呼吁。是愤怒的诗、行动的诗,也是反抗的诗。反抗强暴,反抗残忍,反抗侵略。朱自清所说的“我们将与他沉沦!”,即是后来的人们所说的:我们要与敌人血战到底!
冰心是以写母爱主题闻名于世的现代诗人。冰心笔下的母爱,是有博大胸怀的爱,而不是狭隘的爱。面对列强侵略中国的现状,冰心与1928年写下了《我爱,归来罢,我爱!》,以一个母亲的口吻,呼唤在海外的儿女回到祖国,参加捍卫家园的战斗。诗篇首先控告侵略者屠杀生命,“欺凌孤寡”的暴行:“可奈那强邻暴客/到你家来,/东冲西突/随他的便,/他欺凌孤寡,/不住的烹煎!”强邻暴客比喻侵略者。他们最残忍的暴行,便是血染遍地的屠杀生命,以及烹煎孤寡的摧残生命。”
创造社诗人穆木天,是东北人。《黄浦江舟中》一诗,写于1936年,那时东北早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诗人在上海,“遥遥地想着我的故乡,/血染的松花江的原上。”其中写着:“松花江的原上,/现在,是杀人和放火,/到处洒着民族的鲜血,/受虐杀的,和争自由的血,/在敌人铁蹄下被践踏着。”“血”的意象一再在诗人笔下出现。因为血是人的命脉。“到处洒着民族的鲜血”,有多少生命被侵略者残杀。侵略者的残暴和诗人的愤怒,都在“血”的意象中蕴藏着。诗人强调“争自由的血”,是在赞扬反抗侵略的斗争。
以上就中国现代诗人在创作理论和诗歌作品中的生命意识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论述的是生命意识中最基本的问题,即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的问题。有些比较深入的问题,如生命意识中的青春意识、主题意识和力量意识等,由于篇幅限制,不能在同一片文章中同时展开,因此,在文章中没有涉及。但这些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现代诗歌中的生命主题意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意识十分合拍,放射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的光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笔者已另著专文论述这些问题,所以在本篇文章中省略了。
注释:
① 孙玉石.新诗流派发展的历史启示[G]//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下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322.
②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G]//扬扬.周作人批评文集.广州:珠江出版社,1998:46.
③ 康白情.新诗的我见[G]//谢冕,吴思敬.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45.
④ 郭沫若.论诗三札[G]//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52.
⑤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G]//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82.
⑥ 戴望舒.望舒诗论[G]//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161-162.
⑦穆木天.谭诗[G]//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编).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98.
⑧ 艾青.诗人论[G]//谢冕,吴思敬.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267,274.
⑨闻一多.文艺与爱国[G]//周良沛.中国新诗库(四集).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11.
On the Lif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odern Poets
LIN Ling, LUO Ming
()
The fundamental and core content of life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modern poets is to respect and love life. Life aesthetics, which focuses on life, experiencing life and expressing life, is emphasized in their theory of creation. Their poetry is full of love and warmth of life and hatred of cruelty and tyranny. Their works are a dazzling collection of brilliant humanitarian life images.
Modern Poetry; Life Consciousness; Life Aesthetics
10.13899/j.cnki.szptxb.2017.06.010
I206.7
A
1672-0318(2017)06-0054-06
2017-10-18
林玲 (1963-),女,深圳人,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学。
罗明(1963-),男,深圳人,硕士,高级实验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