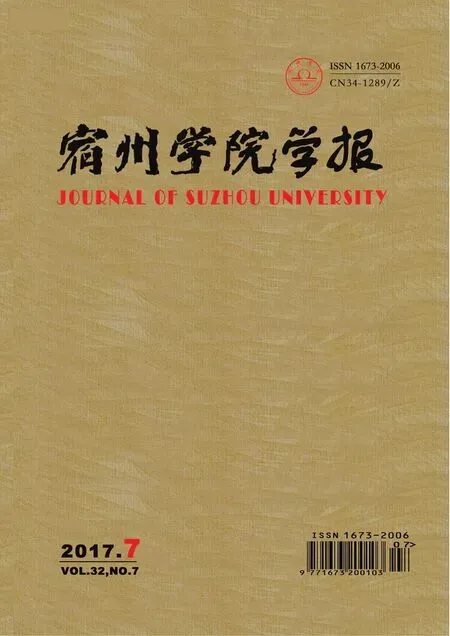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难民工作述论
2017-04-13方乾坤
方乾坤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1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难民工作述论
方乾坤
安徽大学历史系,合肥,230031
为对上海战区难民临时难民救济会难民工作及特点进行全面的深入探讨,依据现有材料,以难民救助为中心,从组织概况、难民救助、工作评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该组织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对战区难民救济工作进行全面呈现并予以客观评价。在“一·二八”抗战期间,该组织专注于难民救助工作,积极组织两支救护队、设立多所难民寄宿所并联合同乡会组织及时对滞留难民进行遣散,数十万战区难民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救助,使其中一部分无家可归的难民得到收容安置,免遭冻馁、饥饿、伤病折磨,保全了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损失,为民族保存了几分元气。
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一·二八”抗战;难民救助
1 问题提出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闸北虹口一带率先沦为战区;此时租界戒严,交通受阻,大量居民被困于战区无法脱险,“人民扶老携幼,逃生无路,群聚于租界四周之铁门以外者不下数十万人,哭声震天、凄惨万状”[1]1,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各慈善团体人士许世英、朱庆瀾、王一亭、屈文六等人为救济被难同胞,遂于1932年1月30日在仁济堂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以下简称临时救济会),以许世英为主席[2],专事战区难民救助工作。
临时救济会以“救济上海战区被难同胞”为宗旨,在“一·二八”抗战难民救助工作中,积极组织救护队,设立难民寄宿所和临时医院,使得大量因战火破坏而无家可归的难民获得及时救助。现有的关于临时救济会的研究成果就笔者所知尚无一篇专门讨论改组组织救济活动和特点的文章出现。刘敏对该组织作过介绍,但过于简略,且主要研究救助效果,而对组织状况、难民救助过程几乎未提。美国学者韩起瀾和法国安克强在相关文献中也提及过该组织。因此,对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难民救助工作进行全面探讨仍非常有价值和意义。本文依据《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报告书》《申报》等材料,从组织概况、难民救助、工作评析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求全面客观地还原事实。
2 临时救济会组织概况
临时救济会虽然是一个临时战时难民救济组织,但却拥有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该体系对临时救济会难民救助工作有序高效的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密的组织体系、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合理的管理模式是临时救济会高效开展救济工作的前提。难民临时救济会采用委员制,按照章程规定,临时救济会设常务委员15~25人,并以其中的5或7人为常驻委员;设财务委员3人,总干事1人,副总干事2人,另设执行委员若干。财务会下只设总务、执行、财务、交涉、卫生五组和统计处,除统计处外,各组(处)设主任1人,副主任1或2人;组(处)下设股,每股设股长一人,必要时会视具体情况设副股长,干事若干。具体运作模式如下:由全体执行委员参加的每月一次的执行委员大会为最高决策机关,每周一次的常务委员会作为常设机关,负责对前期工作的总结和以后工作的部署,然后由各组具体负责实施。日常事务由各组分工负责;重要事务“由总干事、副总干事与各组正副主任暨常驻委员商洽”[3]149-150。
另外,难民临时救济会为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将组织机构进行了三次调整,显示出了机构的灵活性。初期,该会由于战事紧张,救济任务繁重,尤其是救护、遣送、收容及医疗等工作需同时进行,此时的组织最健全,共设五组一处。除此之外,同乡会也在该会设有联合办事处,附属于该会“专门负责、登记遣送两事”[1]2。战事爆发初期,由于战事激烈,救护工作紧张,需要大量人员,难民临时救济会的办事人员达到500余人[1]2。在主要战事结束、停战协定签订前这个时期,由于主要战事结束,每日新到的难民大量减少,另外各寄宿所对所收容的难民也在设法遣送,难民的救助工作减少,难民救济会已无继续维持原来庞大机构的必要,遂将各组加以归并、裁撤。其中,总务组撤销特务股,执行组则将救护、交通、管理、给养4股全部撤销,每股仅留下一二名干事办理相关事宜;遣送股除股长陈唯一外,仅保留4名干事;财务组的赈款、赈品两股并入稽核股,交涉组的查访、登记、文牍三股全部裁撤,仅留一二名干事;卫生组的检查、诊治两股被撤,统计处除主任外仅留3名干事。各寄宿所也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归并,办事人员大为减少。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战事正式结束,救济会各寄宿所难民也已经遣返大半,除第十八寄宿所外临时医院和寄宿所均被裁撤,其余各机构同样被逐渐撤销,直至5月23日,善后工作交由新成立的辛末救济会接管,临时救济会解散。
3 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概述
临时救济会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难民救济工作中,工作主要内容是募款、救护、收容、疏散、救治施药等。
3.1 筹集资金
资金是难民救助工作的基础。战争难民与受自然灾害袭击的灾民不同,兵灾之后,性命能保无虞已属万幸,家园财产瞬间被炮火摧毁。因此,筹措经费成为难民工作的首要难题。临时救济会凭借出色的救济工作,获得了政府和社会其他各界的认可,纷纷向临时救济会提供资金援助。据统计,近4个月时间里临时救济会共筹集资金21万余元[1]64,其他物资不算。据《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记载,“捐款在一万元以上者计有6户”[1]63,其中巴达维亚华侨通过上海市商会向临时救济会捐款2万元,为此临时救济会还专门登报感谢[4]。此事还有一段小插曲,《申报》在3月14日第2版误将2万元的信息当成200元登了出来,为此,临时救济会专门发更正函,3月15日更正。社会各界捐赠的大量资金为临时救济会继续从事难民救助提供了物质基础。
3.2 难民救护
难民救护是一项既危险又繁杂的工作。战争爆发后,虹口成为战区,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中国平民生命面临着严重威胁。由于战争突然爆发,不少中国平民一时未能撤离,尤其是被日军占领的北四川路附近的居民,“被困多日断水绝食呼吁无门死于非命者,不可胜计”[1]5。为救济被难同胞,临时救济会迅速组织救济队赶赴战区积极救助被困难民。在救护过程中,临时救济会为尽可能地救护更多难民,特将救护队一分为二,其中第一、二两队分赴日防区和十九路军防区救护被困难民。其中临时救济会救护被困日军占领区中国难民时,不仅需要临时救济会救济队员,还需要由工部局日籍人员随同。在救护虹口附近难民时,临时救济会同工部局和日领事署协商后,定下救护办法:凡救护队赴虹口一带救护难民时,每辆救护车上须配懂日语的队员一人,同时由工部局再派日籍人员一名随车同往[5]。并且困难重重,《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中提到,当救护队赶赴日战区救护难民之时,所到之处必受严格检查,“即一纸之微亦必反复检查”[1]5,所过市区各街均有日军把守,“不准华人任意通过,违者即遭射杀”[1]5。救护队所经过的街道,“华人绝迹,并不见一难胞,当经逐户叩门,温语慰藉偕登救护专车”,甚至救护队员本身都有可能被日军拘留,“救护队员于从事工作之际,被日海军不问情由横加拘留者尤复习见不鲜”[1]5。
另外,由于没有专用旗帜和袖章,临时救济会主动同红十字会合作,借用红十字会旗和会章。该会救护队队员出动执行救护任务时,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一律悬挂红十字会旗帜,佩戴红十字会袖章[1]2,以资鉴别。但即便如此,救护队依然不时遭到日军轰炸。据悉,救护队第二队在江湾一带救护时,日本军机“对于救护卡车仍不惜加以袭击,我救护队员数遇炮弹地雷”[1]6。
总之,临时救济会从事难民救护工作时,困难重重,危险不断,各救护队员不顾个人安危,克服各种困难,使得难民救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仅1932年2月21日一日之内,临时救济会便在江湾附近救出难民1 302人[6]。据统计,在“一·二八”抗战期间,临时救济会先后从战区救助75 004名难民脱离危险[1]4。因此,临时救济会难民救护工作理应得到肯定。
3.3 难民收容
难民收容是难民救助工作的重要内容。战争爆发后,战区的中国平民大批离开家园,数十万人流落街头,面临着饥饿,伤病的威胁,难民的收容成为上海社会各界不得不严肃对待的社会问题。在此之际,临时救济会于成立之初便设立寄宿所,主动承担起收容难民的责任。临时救济会先后设立难民寄宿所31处,共收容难民133 967人。
临时救济会救护队救护难民脱险后,对于有亲可投的难民,及时设法使其奔赴各地投亲;对于无亲可投的难民,则设立寄宿所收容。该会难民寄宿所的设立,得到了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及团体的支持。面对众多无亲可投、无家可归的难民,不少热心人士纷纷腾出自己房宅,供难民栖息。其中,刘灵纪女士将自己的亚尔培路大厦,黄金容借出自己经营的大世界、齐天大舞台和金荣学校借给临时救济会收容难民之用;旅沪湖州同乡会则将湖社全部开放,并租赁拉都路雷米坊新屋作为临时救济会第15寄宿所[7]。这些房舍成为大量无家可归难民的临时栖身之处。
此外,临时救济会对于离散妇孺的收容工作也相当重视。难民中妇孺处于弱势,尤其是孑身一人与家人失散的妇孺,随时都有被拐卖的可能,为了保护孑身妇孺,临时救济会设立了离散妇孺寄宿专所,进行收容[8],以加强对这类难民的保护。相比之下,红卍字会却没有设立类似的收容所。对离散妇孺的专门照顾,可以说是临时救济会难民收容工作的一大特色。
最后,临时救济会为不中断学龄儿童的学业,特意将各所内儿童不分性别地集中到了一处,施行分级教育[1]7。而红卍字会各收容所的教育与之相比则显得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划。“各所妇孺多来自乡间,或目不认丁或中途辍学,由各所主任视该所情形,施以相当之训育。”[9]18
3.4 难民遣散
资遣难民是临时救济会难民救助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难民遣散之所以重要,一方面上海处于交战区域,大量难民滞留上海,安全得不到保障,疏散到后方则相对安全;另一方面,由于寄宿所空间有限,为使更多的难民得到临时栖息之处,需要对已收容的难民进行定期疏散,以腾出空间。因此,临时救济会从成立之初便十分重视难民的遣散工作。
临时救济会为使难民得到及时疏散,积极同各方协调,请求予以协助。为了使滞留难民得到及时遣散,临时救济会一经成立,便电函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和上海市政府,请求协助遣护闸北战区难民至安全地带;并函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借车两列,输送难民到该铁路沿线的松江、嘉兴等地,同时派员赴上海市联合办事处商借该办事处所属的浦江渡轮。另外,为护送难民到安全地带,临时救济会派潘公展等人先到宝山、太仓、昆山、青浦等地,向各县政府及商会接洽难民收容事宜,并承诺可提供经费补助[10];不久又向各同乡会发函请求协助[11]。临时救济会的努力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为协助临时救济会及时疏散难民,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同意“即日起,每班车专备贫苦难民免费搭客车二辆”[10],大约可供1 000人搭乘;苏州商会派船两只进行协助;各旅沪同乡会则在临时救济会设立旅沪各同乡会联合办事处,专门负责协助临时救济会登记、遣送难民。
临时救济会先通过轮船或火车,将难民运送至难民原籍所在县,然后由县政府或商会负责具体安置。在轮船运输过程中,临时救济会不仅提供干粮还派随船医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据不完全统计,临时救济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先后遣送难民约137 151人[1]38。虽然数量有限,但对于临时救济会来说已经相当不易。
此外,临时救济会的难民保释和医疗服务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战争期间,日军扣押了大量中国无辜平民。为此,不少被日军扣押的难民家属向临时救济会报告情况,请求该会营救。为使这些难民重获自由,临时救济会交涉组多次“前往与日领交涉”[12],最终使297名难民获释,得以同其家人团聚。另外,临时救济会为使伤病难民得到及时救治,不仅设立临时医院,还联系了多家特约医院,同时设有巡回治疗所和驻所医师。病情较轻的难民可由驻所医师和巡回诊疗所的特约医师施以及时诊疗;病情较重的难民则直接送往临时医院或特约医院,临时救济会4个月内共治愈难民88 099人,治愈率达99.55%[1]47。
4 临时救济会工作评析
临时救济会虽然仅是一个临时难民救助团体,但在其存在的约四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大量成效显著而又富有特色的工作。
首先,保释被日拘捕难民效果显著。据该会会议记录显示,最初交涉组是为救济被困在日军占领区的虹口一带难民所设[3]102,由谢福生担任主任,后改由英工部局警务部总稽查督查张尚义担任[13],余祥琴任副主任。该机构不仅办理普通的如联络其他团体之类的涉外事物,而且负责同日方相关机构接洽救护日军占领区难民出险及保释被日军拘捕的无辜难民,据统计,经临时救济会保释的被日均拘捕的难民总数达297人,并且对临时救济会保释被日军拘捕难民消息仅《申报》上就有3次报道。与临时救济会相比,红卍字会在此次难民救助时的指挥机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虽然也设有交际组,负责涉外事宜,但在当时的主要报刊《申报》和《大公报》上却未曾见到有关他们保释被日拘捕难民的消息,红十字会亦是如此。
其次,医疗系统特色鲜明。临时救济会不仅设立临时医院、巡回诊疗所,还有特约医院及医师,并且为缓解护士紧缺的局面特别开设了护士培训班。难民相对较少时,为使寄宿所难民得到及时救助,该会特设巡回诊疗所,每日派医师数人巡回诊察,并且各寄宿所安排有护士二三人,以备不时之需。后来,随着难民不断增多 ,寄宿所也随之增加,由于各所间距离较远,临时救济会决议容纳1 000人以上的寄宿所安排常驻医师一人[14],同特约医师共同进行救护工作,病情较轻的难民直接在寄宿所内便可得到治疗。对于病情较重的难民,临时救济会又设4处医院,每院有常驻医生和特约医生,并“附设药局自行调剂药品”[1]1。为弥补护理人员的不足,临时救济会,特开办护士培训班,所有教授均由上海知名医师和药师担任,该班共培训学员50人,其中42人得以顺利毕业。护士培训班的开设对缓解护理人员紧缺的状况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再次,临时救济会与各同乡会联系密切。同乡会在临时救济会设有办事机构。各旅沪同乡会为救济被难同乡,“自动组织旅沪各同乡会联合办事处”附属临时救济会,“专办登记遣送两事”[1]2。为加强临时救济会力量,每省同乡会又分别推举驻处代笔一二人,协助临时救济会从事救济事宜。双方合作范围涉及难民登记、遣送、资金、难民寄宿所房屋的提供等多个方面。其他团体,如红卍字会虽然同各同乡会也有合作,如在难民遣送方面,遣送苏北各县难民回籍时,得到了崇启海五县同乡会的雇船协助[15]。另外,烟台、宁波同乡会为红卍字会上海总办事处提供过1 150元的资金支持[16]45。但由于红卍字会上海总办事处的组织机构中不存在各旅沪同乡会办事处,自然也就无法像临时救济会一样召开由各同乡会代表参加的商讨难民救助工作的联席会议,更无法使双方能够长期合作。
最后,救助工作专一。临时救济会是专门为救济上海战区被难同胞而设,对伤兵的救护关注不多。临时救济会在“一·二八”抗战期间,成立救护队两支,先后设难民收容所31处,共救护、收容、遣送战区被难同胞300 000余人。而红卍字会不仅关注难民救济,还要负责伤兵救护。究其原因,大致如下:首先,二者宗旨不同。临时救济会以“救济上海战区被难同胞”为宗旨,专门救济上海市战区难民,救济目标明确,甚至对非此次战事造成的灾民都不予收容[1]7。红卍字会则以“促进世界和平、救济灾患”[9]1为宗旨,可见红卍字会救济范围广泛,另外,在《世界红卍字会呈政府文》中提到:“其宗旨仿造万国红十字会,办理慈善事业,救济水旱灾民,遇有战事发生,即组织救济队,前往战区救济伤兵难民。”[17]可见,救护伤兵是其战事救助的重要工作之一。其次,二者实力悬殊。临时救济会仅是一临时慈善组织,发起人为慈善团体人士,所筹资金有限,各种资源有限,并且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而红卍字会在一国拥有数百处分会的慈善团体[18],由于平时救济范围广泛,救护经验丰富,且从事救护的人力资源丰富。常设有施诊所、卍字医院等医疗机构,所以战事爆发后,可迅速从中抽调人力,组成临时医院,从事救护工作。资金主要来自于卍字会会员特别捐献和各分会之间的捐助,来源稳定。以本此战事救济为例,红卍字会共筹集救济资金186 000余元,其中来自总会和各分会的捐助达85 100元,占总数的45.6%[16]13。
当然,在承认临时救济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他们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的不足。首先资金有限,虽然救济会筹集20余万救助经费,平均分到30余万的难民身上,尚不1元,这对于广大家园毁于战火之中的难民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其次,难民救护过程中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在日战区救护难民出险过程中受到时间、地点等多方限制,并且整个救护过程受到日方严密监视 ,影响救护效率。再次,人员不足,尤其是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正是医护人员欠缺,才使得临时救济会不得不自办培训班来培训护理人员。最后,各团体之间总体合作程度不深。临时救济会同各同乡会合作相对密切,但却未发现同红卍字会的合作。红卍字会各分会在东南地区拥有严密的社会救助网络,若临时救济会在难民遣送过程中与红卍字会合作,则对提高难民遣送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5 余 论
难民问题,在“一·二八”抗战时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于难民的妥善安置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更在一定成上为全面抗战保存了部分实力。临时救济会大规模高效有序的难民救助工作,使得30余万难民得到及时救助,其中一部分无家可归的难民得到收容安置,免遭冻馁、饥饿、伤病折磨,保全了生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损失,为民族保存了几分元气,其难民救助工作理应得到肯定。虽然临时救济会救助难民人数同红卍字会相比,稍有逊色,在救助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但对于这么一个临时慈善组织来说,取得如此成绩已实属不易。
[1]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R].上海: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1932:1-70
[2]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许世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185
[3]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工作报告书[R].上海: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1932:附录
[4]来函[N].申报,1932-03-15(02)
[5]救护难民出险[N].申报,1932-02-05(02)
[6]战区会营救江湾难民[N].申报,1932-02-23(02)
[7]难民救济会消息[N].申报,1932-02-14(05)
[8]难民救济会设离散妇孺寄宿专所[N].申报,1932-03-25(05)
[9]赈救工作报告书:甲编[R].上海: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1933:1-18
[10]战区难民救济会工作[N].申报,1932-02-04(03)
[11]请各同乡会救难民[N].申报,1932-03-07(01)
[12]战区临时救济会消息[N].申报,1932-02-20(05)
[13]战区救济会交涉组添设三股[N].申报,1932-02-12(06)
[14]战区难民救济会第八次常务会议[N].申报,1932-04-03(06)
[15]八一三救济征信录[R].上海:世界红卍字会东南各会联合救济总监理部,1939:55
[16]世界红卍字会中华东南主会上海总办事处.赈救工作报告书:乙编[M].1933
[17]周秋光.熊希龄集:下册[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1756
[18]世界红卍字会史料汇编[Z].香港:红卍字会中华主会,2000:2
(责任编辑:周博)
K264
:A
:1673-2006(2017)07-0080-05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7.021
2017-04-15
安徽大学淮河流域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HHYJZX2016CO12);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研究(HHYJZX2016YCO12)。
方乾坤(1989-),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