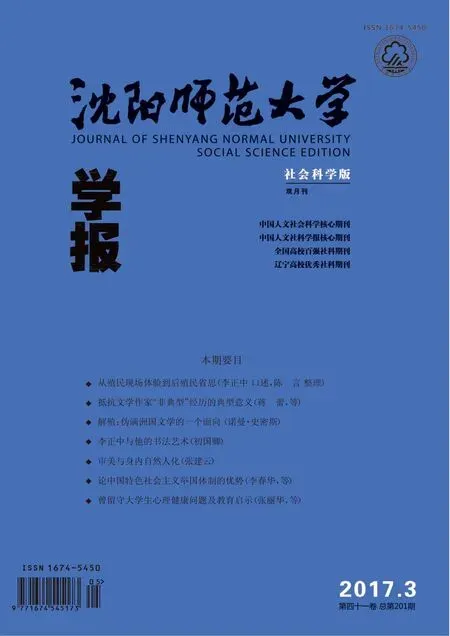解殖:伪满洲国文学的一个面向
——李正中和张杏娟笔下的“忧郁”主题
2017-04-13诺曼史密斯
诺曼·史密斯
(圭尔夫大学 历史系,加拿大 圭尔夫 N1G2W1)
解殖:伪满洲国文学的一个面向
——李正中和张杏娟笔下的“忧郁”主题
诺曼·史密斯
(圭尔夫大学 历史系,加拿大 圭尔夫 N1G2W1)
李正中和张杏娟是两位在伪满洲国时期从事写作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之一。他们小说中的“忧郁”主题,反映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参与及在其中异化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是由个人、社会和日本统治者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的。其文学中的主人公都力争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一个被描述为黑暗,甚至流毒的经济社会里寻找一个符合道德的道路。评价其文学作品需将其放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八不主义”和梁山丁受迫害的阴影下,他们以政治为主导的短篇小说为流行媒介来批评伪满社会,反对官方宣扬的、以儒家为基础的所谓伪满洲国“乐土”。
伪满洲国;李正中(柯炬);张杏娟(朱);忧郁
李正中(1921—)和张杏娟(1923—2012年)是两位在伪满洲国时期从事写作的进步作家,同时,也是“东北四大知名夫妇作家”之一①另外三对是:吴郎和吴瑛、山丁和左蒂、柳龙光和梅娘。。他们分别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文学界。当时的文学界深受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重大事件的冲击:五四运动(1919年)和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1年)。这两个事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日本的侵略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而五四运动提高了他们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特别是社会现实主义对于社会政治变革的反映。他们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伪满洲国出版,也在北京②其时称北平,为保持一致,本文全部称其为北京。、上海及跨国刊物——《华文大阪每日》上刊登。本文论证他们小说中的“忧郁”主题,反映他们对当时社会的参与及在其中的异化。在专注于他们最重要的小说作品——李正中的长篇小说《乡怀》及张杏娟的短篇小说《梦与青春》《大黑龙江的忧郁》和《樱》之前,需简略概述他们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20世纪20年代早期,五四运动席卷中国,提倡对自我和国家的新认识。社会活动家谴责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其是中华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前十年曾被视作现代化进程模范的日本,则因其帝国主义强权行为和不断被批评家认为是“过时的社会理想”而被谴责。谋求赋权于青年和妇女的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的文化纷争,也是令李张夫妇自我身份和职业理想开始形成的一个社会侧影。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而后在1932年3月8日,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个以日本为主导的政权,尊奉儒家思想中的“王道主义”。“王道主义”被作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的替代品进行宣传,其特别作用在于反对当时被取缔的“三民主义”。伪满的政治宣传阐述了保守的理念,历史学者Prasenjit Duara(杜赞奇)将其定性为“现代中的传统”[1]。这些都是被伪满洲国的“满系”作家重点批判的。
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文学法规禁止颠覆性的、消极的甚至是悲观的著作发表,至20世纪40年代,法规愈加复杂繁琐。在1941年2月21日的《满洲日日新闻》中,当局刊登了“八不主义”:
1.对时局有逆行性倾向的;
2.对国策的批判缺乏诚实且非建设性意见的;
3.刺激民族意识对立的;
4.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
5.以颓废思想为主题的;
6.写恋爱及风流韵事时,描写逢场作戏,三角关系,轻视贞操等恋爱游戏及情欲,变态性欲或情死,乱伦,通奸的;
7.描写犯罪时的残虐行为或过于露骨刺激的;
8.以媒婆、女招待为主题,专事夸张描写红灯区特有世态人情的[2]。
这些规定旨在遏制地方文学对于政权的批评。如下文所论述,李正中和张杏娟违反了“八不主义”的大部分内容。他们反对官方宣扬的、以儒家为基础的所谓伪满洲国“乐土”,而他们的批判文章应该被置于此背景下来评价。
一、个人生活
李正中最为人所熟识的笔名包括柯炬、韦长明和李莫①李正中的笔名包括:李征、郑中、郑实、杏郎、葛宛华、万年青、木可、李鑫、靳革、韦烽、韦若樱、魏成名、魏之吉、小柯、小金、余金、里刃、常春藤、史宛、紫荆等。。他出生于一个注重教育的家庭,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的一个原因是其父母意识到他们负担不起另一个孩子的教育。早年,他母亲很喜爱诗歌,常背诵唐诗给他听,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热爱。1928年,他开始在吉林省小学正式接受教育。1931年,转学至伊通县第一高等小学。同年,10岁的他在上海杂志《小朋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小朋友〉十周年纪念(祝词)》”②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陈实于2015年12月找到这份材料,并与我共享。[3]。因日本侵略,李正中全家迁居哈尔滨,后于1932年底搬到吉林市,因此,他的中学学业,是先后在哈尔滨北满特区二三中学和吉林市永吉县立中学完成的。1936年,他进入吉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班。1937年,他认识了当时14岁的中学生张杏娟③张杏娟和李正中访谈,维多利亚(加拿大),2004年4月24日。。李正中的姑姑在吉林市与张杏娟一家住在同一宅院,李正中频繁的探访和他们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令他与张杏娟的关系日渐亲密。同年,16岁的李正中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余荫馆诗存》,可惜该集今已佚失。次年,李正中开始参加其毕生经常参与其中的各种书法比赛。他于1939年进入法政大学,1941年出版了小说《乡怀》④《乡怀》于1941年由“新京”益智书店出版,当时作者署名为柯炬,全书共104页。。1942年考入大同学院学习,同时出版诗集《七月》。他的文学作品刊登在当时东北地区最负盛名的出版物上,包括《大同报》《盛京时报》《新满洲》《麒麟》和《新青年》。1945年,《无限之生与无限之旅》《笋》《春天一株草》和《炉火》出版,《七月》再版于1945年。
张杏娟,1923年3月16日出生于北京。她最为人熟知的笔名是朱和杏子。1925年,她两岁时,经商的父亲被东北蓬勃发展的经济所吸引,决定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到吉林市居住,从此,张杏娟在松花江畔长大。张杏娟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和谐的家庭,父母鼓励她学习和参与户外活动。据她回忆,孩提时代的她最为人所知的,是她的勤奋好学和要强的性格⑤张杏娟访谈,沈阳,2001年2月14日。。1929年,张杏娟开始了正规的小学教育,但由于1931年日本的侵略,大多数学校被迫关闭直到1932年春,因此,张杏娟的学习也被短暂地打断。张杏娟立志投身教学事业,伪满洲国教育被官员吹嘘为他们进步统治的象征,而批评家则指责这种专业技术的学习,实质是培养奴颜婢膝的中国劳动阶层。在她的短篇小说《我和我的孩子们》(1945年)中,张杏娟抨击伪满洲国教育,认为“在今日的情势下‘中国孩子’竞失掉了升学的机会”[4]。1936年,13岁的张杏娟完成小学学业,进入吉林市女子中学,那里同时也是著名作家吴瑛(1915—1961年)和梅娘(1920—2013年)的母校。张杏娟对于阅读的兴趣及前辈们的影响促使她开始写作;另外,在《樱》的序言中,张杏娟称:写作帮助她战胜青春期的挣扎。1940年中学毕业后,张杏娟升入吉林女中师范学院住读。1941年,作为师范生的她开始在“新京”《大同报》上刊登短文,由此与李正中结识。
张杏娟于1942年毕业并开始任教于吉林市北山小学,其后她的生活有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社会愈加贫困、通货膨胀加剧、消费品短缺和战争因素迫使她的父母放弃在伪满洲国的生活而搬到氛围相对自由的北京,但随后北京也被日本侵占。为了消除父母对她仍留在伪满洲国的担忧,这对年轻的情侣不顾女方父母反对,宣布订婚。1943年,他们结为伉俪。她最著名的作品《大黑龙江的忧郁》也在这年出版。在伪满洲国存在的最后几年中,夫妇两人在文坛上获得很高的知名度,但因很少刊物能支付较好的稿费给作家,他们并不能仅靠写作收入来维持生活。张杏娟以教书贴补家用,而李正中则担任法官①李正中访谈,温哥华(加拿大),2001年9月23日。。1943年,夫妇两人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从此,张杏娟忙于照顾孩子和获取生活必需品。1944年和1945年,夫妇俩的大部分著作在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下得以出版。
二、李正中笔下的“悒郁”
1941年10月,在“八不主义”公布十个月之后,李正中以笔名“柯炬”发表了《乡怀》。《乡怀》讲述主人公金祥“出走—回归”的故事。金祥逃离村里“阴暗的日子”而去较为安全的大城市完成了学业并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不像周遭的普通城市人那样过着“麻将加咖啡式的奢侈生活”[5],而是花时间在阅读和自我反省中。然而,金祥还是觉得“疲惫与麻木”的城市生活给他带来“冷酷和恨恶的感情”[5]3:曾经与他相爱的女人——白雪如,听从家里人的意思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对于工作前景的失望加上全身的倦怠使金祥感到“阴郁的,冷酷的,没有希望的日子,他像失掉了理智……”[5]7,因而,他决定回到家乡。但金祥很快发觉家乡无聊且郁闷。他回归之初,本打算与他多年未见的青梅竹马——何慧姑结婚,但何慧姑含泪告知金祥,她已订婚。金祥心灰意冷。
他的另一个旧相识——教师李爽,带金祥去感受当下村子破败。李爽说:
(村子里的人)转变是太快了。从前是那样的正直,现在又是那样邪僻,从前是那样勤俭,现在又是那样奢侈,这里的人仿佛都不知道有明天似的。我每从这里走过,就感到墟墓一样的使我冷颤[5]19-20!
金祥看到很多人(包括他曾经尊敬的叔叔)已经屈服于艰难时世。李爽给金祥看何谓“一天不如一天的日趋于毁败”[5]17。令金祥更加吃惊的是漂亮的年轻女人却“偏偏堕落得不可收拾”[5]22,靠出卖自己身体过活。金祥感到完全幻灭,意识到他的“乡村的一切都改了,再不能给他‘这个’旅人以往昔的孩子时代的温暖了”[5]24。现实变得过于残酷。于是,在一个祖母还没有醒来的清早,他离开了家乡。
回到城市后,金祥“如同一片不载着雨的云彩”[5]32,失业的同时也失去婚姻和未来,而且家乡正在堕落。痛苦主宰了金祥的生命,“他成了愚蠢的命运的沦落者了”[5]44。后来,他的朋友田鑫为金祥谋求一份印刷厂的工作,但工资并不能支撑金祥的生活。之后,金祥遇上昔日恋人白雪如。她不仅在经济上援助金祥而且带他夜夜玩乐。白雪如对生命持悲观态度:人生是太空虚了。我们在社会的洪流里又过于渺小了。酒,只能告诉我,生命是怎样一个寂寞的尸体。
堕落的生活并不能拯救他。金祥因神经虚弱症而住院。在医院,一直无微不至照顾金祥的护士询问他如何正确地生活。金祥回答道:“我也同样的是找不到路的人。”[5]71在金祥离开之前,白雪如答应金祥一起生活,但最终她还是离开了。白雪如告诉金祥:“生活的枷锁害苦了我们!”[5]74她已经习惯了通过和男人的关系而获得的那种生活方式,她不能为了浪漫情怀或农家生活而抛弃现在生活。正如她向金祥解释的那样:“是我中毒过深了。从前我被人们逼着去安适于我过不惯的生活,现在我又脱离不开。”[5]95被失败的感情、疾病和失业击倒的金祥告诉李爽:“我自己也很了解一个人为了生存的苦斗,是需求着刻苦与冒险的。”[5]80李爽和金祥互相鼓励着对方拿出意志和勇敢来继续生活,但意识到他们的言语是如此苍白无力——金祥的现在和过去都是一样的被“空虚与死寂所充塞着。”[5]81最后,金祥决定再次回到他的家乡。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当天,得知何慧姑在婚后一个月就死了的消息。
在某一层面上而言,这部小说可以被视作是一个青年人在背负着摇摇欲坠的道德观和经历着经济困难的社会中,失去爱情的故事。整部小说中,金祥十分清楚自己的生活一直在恶化。但是金祥并没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勇敢。动荡的时局和金祥自身对此的反应令他认为“那生活的本身又是空虚的死灭了希望的体。”[5]56最重要的是,《乡怀》消极地反映了伪满洲国当时的环境和习俗。金祥的家乡“转变是太快了”,之前曾是正直的邻居们如今花时间在赌博或喝酒。而三个主角,金祥、白雪如和何慧姑则以无力去改变自己生活的懦弱者形象出现。没有坚定意志的金祥同样也没有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决定的胆量。白雪如沦为社会的受害者,最终和另一个男人离去;何慧姑则违背自己意志走进一段封建婚姻并死去。金祥希望回去的家乡早已面目全非,这为金祥的生活带来极大灾难的同时也迫使金祥意识到要纠正时代的错谬,个人的积极性是必不可少的。或许最强烈的谴责是金祥所控诉的社会“有着光明和一切,却只把我丢在无边际的暗黑的漠野。”什么是所谓的“光明和一切”?其实就是明确地意指所谓“伪满乐土”。所有的这些带给金祥的却是一个“无边际的暗黑的漠野。”更为重要的是金祥在被土匪打乱生活的七年后回到村子的这一个情节。李正中于1941年发表《乡怀》,这一年也被称为“康德八年”①在小说的最后,李正中并没有使用官方日历,而是写下“四一,三月”。。土匪七年前侵袭的日子正是“康德时代”的开端,言下之意伪满洲国的成立及其社会经济问题与作品中的动乱有关。
三、张杏娟笔下的“忧郁”
张杏娟在一个有利于女性作家的出现,但又严重受官方监管的文坛环境下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当张杏娟开始发表作品时,著名作家萧红、白朗等已离开东北地区或已改变职业道路了。受她们作品的启发及张杏娟日后的丈夫李正中的影响,张杏娟仿效他们对于女性屈从于社会的谴责。从1943年到1945年,张杏娟的作品在不同刊物上发表,包括长春的《新潮》和《兴亚》、北京的《妇女画报》和跨国的《华文大阪每日》。张杏娟受过的两次挫折正好体现了伪满洲国压抑的环境。1944年,她写了两篇具有争议性的小说《小银子和她的家族》《渡渤海》。她把《小银子和她的家族》投稿至《新满洲》,但小说因涉及强奸及贩卖年轻女孩而被拒绝;小说《渡渤海》被《兴亚》接受,但之后被审查员切除公然反满的内容——它其后被作为《樱》的三部分之一而发表。张杏娟的作品和被禁的这两部小说显示出当时生活中的固有矛盾——张杏娟担任教师的同时写出越界的文章来告诫读者,“流毒”在社会上盛行。张杏娟和李正中自此认为,在伪满洲国的中国女作家在殖民地的“厌女主义”之下反而获得某些权力,一来是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及其工作被认为是非政治性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当局认为女性作家并没有危害性;二来是因为女性作家并不像大部分男性作家那样激烈地进行调查研究,因而对于当局而言,女性作家所带来的“麻烦”更少[6]。1945年的春天,令张杏娟的写作生涯达到顶峰的是她的文集《樱》的出版。当局准许具有消极意义的《樱》的出版,很可能是因为审查员并不认为女性作家的作品能带来广泛影响并带来政治问题。
1945年4月,国民图书出版社发行两千本《樱》,但只有极少数流传至今。该文集包含前言,八篇文学小说和卷首诗。当时的评论家称赞张杏娟的文笔具有“乡土的气味”,不仅如此,当局也相当满意张杏娟作品中的乡土气息甚至宣扬这种气息,以便区分伪满洲国文学和中华民国的中国文学。但在《樱》序言中,张杏娟提到其他因素对她有巨大的影响:
其实,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除掉了曾致力于渲染乡土的气味之外,我也另有其一点小小的意识在。无疑义的,读过这册书的人立刻就可以看得出,这种意识在《樱》里就更清楚地刻画出它的正面。我始终觉得女人本身的生活如果必须仰赖于男人的供给,则于女人这将是一种绝大的耻辱。当然,我并不是反对两性生活者,我是进而研讨着怎样才能使两性生活更合理,更有秩序地组织起来。也唯有两性的生活才是人类永远发扬不已的动脉。不过,作为女人的应该始终持有要独自生活下去的这样最后的自觉与野望,这样才能完成女人的本身[7]。
张杏娟以“女人”作为分析重点以宣扬她认为的理想女性特质中必不可少的特性:自我意识和独立。她的作品批评不公平的性别结构,认为男人征服女人有损于女人作为“女人的本身”的能力。张杏娟认为自己“当然……并不是反对两性生活者”,她旨在令它们对于女性而言更加“合理”而不是强加这种关系。张杏娟的文章没有涉及任何日本或日本人的题材内容,这令她的许多作品在殖民地官员看来是没有什么危害的。但她谴责她这一代人的可悲状况的作品,比如“在生活的轮轴下被压榨了的”这种题材正是“八不主义”所设法铲除的破坏性文学类型。
在《梦与青春》《大黑龙江的忧郁》和《樱》中,张杏娟探讨了婚姻对于女性生活的影响。在她文集的序言中,张杏娟提及她以这些作品所构成三部曲来发展形成她对社会的批判。这些小说的特点是刻画了越来越阴暗的女性生活:在《梦与青春》中,沙夏以患有抑郁症且家庭不幸福的形象出现;在《大黑龙江的忧郁》中,即将死去的亚娜深受自己过去的折磨;而在《樱》中,母亲被奸污、抢劫和流放。尽管女主人公们都面临着这些挑战,但是她们每个都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梦与青春》的开场与结束都是同一个场景:女主角沙夏被一个男子追赶着从房子的门洞跑出来。通过倒叙,读者知道了24岁的有着绿眼睛的沙夏在六年前与嘉私奔。但在两人的婚姻生活中,沙夏被抑郁沮丧消耗尽了,因为她深受幸福的恋爱和不美满的婚姻之间差异的打击。不堪重负的绝望令她悲伤:“生活是一种威胁,是一种可恨的存在。”[8]37她因为抛弃了自己的家族而和一个并没有回报自己感情的男人一起生活而充满了自责。尽管他努力安抚她,沙夏还是抛弃了他并且认为她必须离开,“同一的家族里,若失掉了爱的维系呢?”[8]39沙夏断言婚姻必须植根于爱,而不是义务。由于无法忍受和一个不爱她的男人一起生活,沙夏出逃去寻找就像家门前河水流过一样的梦想与青春。
张杏娟最广受好评的小说《大黑龙江的忧郁》讲述的是患有肺结核的白人女子——亚娜,她和女儿卢丽一起在黑龙江乘船回到俄国的故事。驱使亚娜回到俄国的原因是卢丽在伪满洲国没有未来这个现实,并且亚娜希望在自己死之前安排好女儿的婚事。在船上,她们刚好遇到亚娜的前夫——莫托夫。小说通过倒叙讲述了15年前的故事:当丈夫外出经商时,亚娜与一个中国男子坠入爱河继而跟随他来到伪满洲国。在那里,亚娜发现自己怀孕了,其后亚娜与她的中国情人一起把卢丽养大,直至亚娜的情人在工作中死亡。卢丽直到在船上才得知那个中国男人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因为不愿与莫托夫和解,亚娜拒绝了莫托夫让她回来的请求,亚娜相信如果女人和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一起生活,那是“女人给男人的绝大的侮辱”[8]14。旅程的最后,在俄国,亚娜把卢丽交托给莫托夫,然后再次登上那艘船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当船驶离岸边的时候,亚娜把绣花手帕扔进江中。在手帕上绣着的是当年莫托夫的一句话:“我们底爱永生,我们底青春不死。”[8]27亚娜凝视着江面直至江水吞噬了她的手帕。
在《大黑龙江的忧郁》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相当突出。俄国的温暖和面朝黄土的百姓与她的中国情人所宣称的在江对面的伪满洲国是“千百亩的熟地,是富有的资产阶级”[9]形成鲜明对比。亚娜开始嫌弃伪满洲国社会:“盖着一层烟的土城,没有舞厅和酒场,没有可值得享乐的设施,也吃不着了家乡风味的面包,仅是并不可口的米饭……”[9]7即使她到了有着众多俄罗斯居民的“北边的小巴黎”哈尔滨,也并没有被它所吸引,因为那里的人们轻蔑地对待她们母女。亚娜认为伪满洲国的唯一可取之处便是对寡妇贞节的强调,这令她可以在她的后半生独立生活——这是她出于想要实现自我而不是出于尊重她的丈夫而想要的。纵观整部小说,亚娜对于勾起她回忆而使她手足无措的黑龙江是又爱又恨。凝视着江水,她看到或从窃窃私语中听到她的过去;波浪拍打着船边的声音令她记起西方的舞蹈“加尔登,西班牙之夜”。她回忆起在年轻的时候听着平静的江水的她进入梦幻的世界。旅行者经过永恒的动人的江水、黑土地、绿田野和山,但他们因为个人的痛苦而并不能乐在其中,正如亚娜对于过往的哀悼,令她对于黑龙江有着惆怅的感情。
三部曲以张杏娟最长的小说作为完结,并且文集标题也以此小说命名——《樱》①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最后的一章,其他全部以《渡渤海》为标题刊登。。这由三部分所组成的小说(《雁》《藻》《樱》)是张杏娟最为越界的作品,因为它刻画了在伪满洲国“新的土地”②在1986年的印刷中,“新”被替换为“陌生”。参见梁山丁主编的《长夜萤火》中《渡渤海》,第493页。上降临到女主人公——妈妈身上的灾难。小说中并没有明确地告诉读者在这片土地上什么是“新”的,但与当初吸引妈妈的那个社会环境相比,实际的社会条件相去甚远。在《樱》中,吸引妈妈的伪满洲国自然环境之美和其具破坏性质的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妈妈带着儿子从山东老家坐脚车去寻找五年前去了伪满洲国打工的丈夫。文中叙事揭示:即使“妈妈底对于乡土的爱恋的心情是并不减于别人的”[10],但她不能接受没有丈夫而度过余生。可是,自她抵达大沽口登上去往营口的船,她就饱受来自男人的折磨,比如,她在山东从未遇到过的——“这样为一个陌生的男人打量还算是第一次呢[10]124。”当她想买渡过渤海的船票时,被告知女人不能在没有男人的陪同下进入伪满洲国,惊恐的她只能“雇男人”。绝望之下,她雇佣了卖票者的同伙,这男人在途中奸污了她,使这趟航行变成妈妈的“海上的囚狱”。当船抵达码头,海关官员夺取了她的银元,而那个强奸犯则把她的随身物品抢走了,她几乎身无分文。
一旦进入伪满洲国,妈妈和儿子就登上开往未知未来的列车。垂头丧气的他们和威严的东北大山、土地形成强烈对比。妈妈的生活跌入低谷:“也许自己和孩子的命运注定是该饿死到满洲这块新土地上了吧!”[10]135虽然身无分文还挨着饿,妈妈仍以找到丈夫为希望来鼓励自己。妈妈在丈夫最后出现过的地方——巴堡,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地名,临时性地打着工。在那里,妈妈被她的老板奸污。在老板被人发现遭到伤害后,妈妈被判入狱,但她拒绝回应对她的指控。在监牢里等待着判决的妈妈“想起了耻辱的渤海,饥馑的大陆,和残暴与淫虐”[10]144。她的苦难与大陆的困苦是明确联系在一起的。
《樱》的最后一章描述了流亡的母子来到一个农场,而妈妈在那里重新建立一种新生活。她摆脱了自己是受害者的思想情绪。故事的高潮在于她偶然遇见她曾拼命寻找的丈夫,却又拒绝了这个因过往而自我放逐的男人所提出的重聚要求。在流亡中,妈妈发现实现自我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力更生的收获,而不是依赖于丈夫:“妈妈觉到自己的生命毕竟还是自己的。绝不是归属于谁的。或是附合于谁的。与一个男人的合力虽然会更幸福,失掉了一个男人的合力也不能因之沮丧自己的活动。”[10]161
《樱》歌颂农村生活,这是伪满洲国政治宣传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樱》也完全否定女性对于父权的屈服。由妈妈准备离开山东开始,经历了被奸污、抢劫和流放之后,妈妈开始意识到她不需要依赖于男人而活。最终在伪满洲国做出了反抗。张杏娟完全消极地描绘伪满洲国生活,因而该小说被禁止在《兴亚》上刊登,但她灵活地绕过了种种限制并以增加新标题来使它得以作为《樱》刊登。
这三部曲《梦与青春》《大黑龙江的忧郁》和《樱》像图表一样显示了张杏娟对于伪满洲国社会环境的越来越消极负面的描绘。读者不由得同情起女主人公,她们愈加消极悲惨的生活不仅体现于她们在感情上的失败,也体现于她们在社会上的失败。显然,三部曲中的每个故事都指明了东北雄伟的自然风光,尤其是江河,是如何影响女性的生活。正是这种女性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结迫使她们拒绝在伪满洲国屈从的社会地位。
四、结语
李正中和张杏娟的写作,戏剧性地说明了伪满洲国的社会情况。他们的生活是由个人事务、社会限制和日本统治三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构成的。日本的统治开始时,他们还只是孩子,伪满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让他们能够以写作为生。正如本文所论述的,他们以政治为主导的短篇文学小说为流行媒介来批评伪满社会。毫无疑问,他们的作品明确违反伪满洲国官方所谓“八不”中的第四条:“专以描写建国前后黑暗面为目的的”,但他们所违反的程度则是一个比较主观的问题。在他们的文学小说中,主人公们都力争改变自己的生活,在一个被描述为暗黑,甚至流毒的经济社会里寻找一条符合道德的道路。五四运动鼓舞了中国文坛,作家们寻求提升社会对于经济不平等的认识,同时在日本殖民地的语境下,追求由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所倡导的文学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1881—1936年)以本土写作推动潜在的现实主义的变革。李正中和张杏娟从事的正是这样的文学创作。虽说他们就业于教学和法律行业,但这样的职业生涯很可能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余地。
他们的作品里并没有着重刻画与日本相关的题材。所有与日本相关的题材并没有以积极或消极的面貌出现于作品中,反而是被完全忽略。考虑到夫妇二人在伪满洲国的重要地位,这种日本题材的缺失是明智的,因为作家很可能会因明确消极或悲观地反映日本而被给予严重的处罚。张杏娟的几部小说,如《大黑龙江的忧郁》和《梦与青春》,都以白人这个于日本人而言并非具有重大意义的种族为主人公,但在伪满洲国,中国人则被归为从属位置。杜赞奇于2004年对于梁山丁的小说《绿色的谷》(1942年)提出疑问,因为,这小说没有明确批评日本,他质疑它是否能作为一部反帝国主义作品来评价。也许,梁山丁在写《绿色的谷》的时候并不能预料将受到的迫害,但李正中和张杏娟却看得到梁山丁为该小说付出的代价:1943年,梁出逃到北京,家人被迫害,在长春的家被破坏。因此,李正中和张杏娟的作品必须放在他们的历史语境下评价,尤其是在“八不主义”和梁山丁受迫害的阴影下,夫妇二人主要的文学作品都出版于“梁山丁事件”之后。日本或日本人题材的缺失,令他们能够从事对当时社会的批评。
日本帝国的崩溃、内战,还有当地居民渴望一个模糊的殖民历史,这些因素令伪满洲国的过往处于一个完全被谴责的叙事语境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它的爱国主义热情抹去了复杂的伪满洲国的统治,并且将焦点从曾活跃于当地文化的黑暗、反封建、反父权制的讨论转移到以文学积极而广泛地赞颂新国家。在1945年,张杏娟以诗歌《自己的歌吟,自己的感情》来庆祝《樱》的出版,她写道:“我不过是大地涯 的一条小河/我不过是榛莽丛中的一株小草。”[11]在《乡怀》中,李正中对他的小说的评价是“这未成熟的作品”[5]2。这种谦逊反映了作家们品格的同时,也可能是为了麻痹伪满洲国的审查员,使他们对于李正中和张杏娟的文学作品产生“无害的错觉”,但这种谦虚情怀并不能准确评估李正中和张杏娟作品中“抑郁”的宣扬对读者的影响。
[1]PrasenjitDuara.SovereigntyandAuthenticity:ManchukuoandtheEastAsianModern[M].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3:147.
[2]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304.
[3]李正中.《小朋友》十周年纪念(祝词)[J].小朋友,1931(483):154.
[5]柯炬.乡怀[M].“新京”:益智书店,1941:3.
Lyo-Colonial Literature:A Field of The Literature in Manchukuo——The Subject of“Melancholy”by Li Zhengzhong and Zhang Xingjuan
Norman Smith
(Department ofHistory,UniversityofGuelph,CanadaN1G2W1)
Li Zhengzhong(Ke Ju)and ZhangXingjuan(Zhu Ti)were twoactive Chinese writers duringthe false Manchukuoperiod.Theywere lauded as one ofthe Northeast’s four famous writingcouples.The theme ofmelancholyis prominent in their writings,representing their engagement with and alienation from contemporary society.Their lives and careers were shaped by individual experiences,societal conditions,and Japanese imperialist rule.The protagonists in their stories fight tochange their lives,strugglingtofind a moral path forward in the dark,poisoned“economic society”in which theyare depicted.This paper situates the lives and writings ofLi Zhengzhongand ZhangXingjuan in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in the shadowof sham state policies such as the“Eight Abstentions”and the famed persecution of fellowwriter Liang Shanding.These writings are deeply critical of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demonstrating resistance tostate regulations and criticismofthe veryfoundations ofthe so-called“Manchukuoparadise land.”
false Manchukuo;Li Zhengzhong(Ke Ju);ZhangXingjuan(Zhu Ti);melancholy
I206.6
A
1674-5450(2017)03-0015-07
【责任编辑:詹 丽 责任校对:王凤娥】
2017-03-03
诺曼·史密斯,男,加拿大人,圭尔夫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伪满洲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