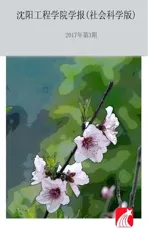新时期形象思维讨论及其历史意义
2017-04-13安静
安 静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新时期形象思维讨论及其历史意义
安 静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新时期形象思维讨论经过《人民日报》社、《诗刊》社、《人民文学》编辑部的组织宣传,于1977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刊发《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而正式开始。这次形象思维讨论为文艺正名,率先扭转了社会风气,为新时期的文艺理论研究、美学热与文化热开辟了道路。
新时期;形象思维;历史意义
当我们论及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对“纯文学”的追求与探索。正如程光炜先生在《“85文化热”三十年》的结尾中写道:“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历史链条,历史暗夜与纯文学的历史链条,就在这个特殊时刻连接在一起了。这个连接,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学术的整整三十年。”[1]毫无疑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交汇点上,“纯文学”的旗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说80年代“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是一条涌动的河流的话,那么架设在这条河流上的大坝则是在历史交接点上的形象思维讨论的再次登场,是这场讨论率先扭转了时代风气,在一个业已封闭的理论禁区中打开一个缺口,从理论层面推动了纯文学的研究。随着形象思维研究的转型,文艺理论界从形象思维出发,带动了中国古典美学、文艺心理学乃至思维科学的研究,最终形成波澜壮阔的文化热。新时期形象思维讨论始于1977年底,如今已经过去整整40年。40年来,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术界研究的话题日益多样,也不会再倾全国之力长时间集中于某个话题。今天再提这段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回顾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形象思维重新登场的历史过程,从中发现中国自主性学术话题生成的历史规律,总结经验,以期对未来的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一、 新时期形象思维讨论的准备工作与隆重登场
197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邀请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等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11月2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座谈会的报道,同时登载茅盾的发言《贯彻“双百”方针,砸碎精神枷锁》和刘白羽的发言《从“文艺黑线专政”到阴谋文艺》;12月7日又登载了张光年的发言《驳“文艺黑线专政论”——从所谓“文艺黑线”的“黑八论”谈起》。在“编者按”中,还对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行了揭露。这个座谈会召开后不久,《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召开驻京部队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揭露江青勾结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出席座谈会的有魏巍、丁毅、时乐濛、杜烽、唐诃、陆柱国、严寄洲、黄宗江等。在这一阶段的准备过程中,文艺界的主要任务是批判“文艺黑线专政”。会议认为,形象思维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毛主席的这封信为批判“‘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主义,尤其是为当前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提供了武器。
197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邀集在京诗歌界、文艺界的著名作家、学者到《诗刊》社学习、座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2]。会议首先在小范围内举行,25日和26日后扩大,出席会议的人数达到三百多人。在这次座谈会上,贺敬之、臧克家、冯牧、唐弢、蔡仪、谢冕等六十多位学者发表感言。此次座谈会认为,毛主席信件的发表是整个文艺战线和我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根据当年的这份《座谈会纪要》,对形象思维也首先肯定了它的社会意义,是我们打碎“四人帮”强加于文艺界的种种精神枷锁,批判“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的极其锐利的思想武器。郑季翘在1966年发表于《红旗》第5期的文章《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在此时成为众矢之的,座谈会将这篇文章作为“四人帮”所有言论的组成部分,表示了极大愤慨。在反驳郑季翘言论的过程中,其实也依然充斥着政治斗争的味道,会议认为,否定了形象思维,也就否定了作家深入生活、掌握丰富的艺术原料的极端重要性,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家脱离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使文学艺术脱离人民生活这个唯一的源泉。归根结底,也就实际上否定了文学艺术。
在召开有关形象思维的座谈会之后,《人民文学》编辑部于1977年12月28日到31日之间,邀请在京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文学编辑等一百多人举行座谈会,就深入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如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国家主席为《人民文学》题词——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这次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批判“四人帮”留下的历史遗毒,重新高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复兴党的文艺事业。
从两次会议的内容来看,《诗刊》社有关形象思维的讨论为《人民文学》的讨论奠定了话语方向转变的基础。如果说形象思维讨论的是一个具体的理论话题,那么,《人民文学》召开此次座谈会的主要目标是讨论有关新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大方针问题。经过前期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充分准备,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之后,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毛泽东《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并附上毛泽东手迹。这封信原本写于1965年7月21日,起因是陈毅把自己写的几首诗寄给毛泽东,请他修改。毛泽东把修改过的《西行》附上,并对陈毅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一些意见。毛泽东在信中说:“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解决斗争与生产斗争……”1978年第1期的《诗刊》和《人民文学》也同时刊登这封信,肯定形象思维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报纸版面分为两个部分,上半部分以仿宋体字排印,下半部分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进行影印。在报纸的右侧上方,配以“毛主席语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两份报纸的排版设计完全一致。在这一期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登了12月30日来自中宣部关于文艺界座谈会的消息。这次宣传工作的会议带来广泛持久的影响,为清理“四人帮”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开辟了道路。
在1978年第1期的《诗刊》与《人民文学》,同样刊登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诗刊》还发表了《座谈纪要》与林默涵的《读毛主席谈诗的信》、臧克家的《论诗遗典在》,《人民文学》刊发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的书面讲话》《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同志的讲话》以及作家杜埃的《调整和贯彻好党的文艺政策》等文章。这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承认形象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重新将毛泽东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作为文艺的指导方针,彻底扭转“四人帮”所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至此,形象思维不再是一个文艺学具体的学术问题,而是成为整个时代扭转话语风气的契机。
二、 第二次形象思维讨论的高潮及其特征
随着中央高层对形象思维理论的倡导,全国立刻展开了形象思维大讨论,1978年第1期的众多学术期刊,都选择了形象思维作为刊物的主要话题。《文学评论》刊登了王朝闻的《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蔡仪的《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唐弢的《谈“诗美”——读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王元化的《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等四篇文章谈论形象思维。有学者统计,仅在1978年1月在全国报刊上发表形象思维问题的署名文章达58篇以上,报导在87篇以上;仅1月在报纸上用“诗要用形象思维”七个字的同题作文在8篇以上。自2月至年底,不到一年时间,在《红旗》《哲学研究》《文学评论》以及主要大学学报和各省文艺刊物上发表的“形象思维”专论,在60篇以上。以“形象思维”为主题的论文集,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1978年5月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组编辑的《形象思维问题参考资料》;1978年6月,湘潭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湘潭市文化馆编印的《形象思维资料集》出版;1978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将近50万字的巨著《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问世;1978年9月,由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辑的《形象思维问题资料选编》正式出版。正因如此,1978年被称为文艺界的形象思维年。这种热潮延续到了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研究室与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理论编辑室合编的《美学》(俗称“大美学”)的创刊号上,刊登了有关形象思维的文章:朱光潜的《形象思维:从认识论角度和实践角度来看》、赵宋光的《论音乐的形象性》、张瑶均的《电影艺术与形象思维》,也刊登了关于形象思维理论的总结与回顾文章《形象思维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流传》,这一次形象思维讨论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重提形象思维更多的是出于社会变革的需要,借助为文艺正名的时机,目的是要为整个社会提供扭转风气的契机,因此,原来被上纲上线的形象思维否定论,同样也以上纲上线的方式被反驳,仿佛在有意无意之中清偿了一笔历史的债务。在这一次讨论中,学者们特别强调形象思维存在对艺术的意义,它不仅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体现着艺术的独特性,形象思维之于艺术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人类认知的一种特殊方式,而是成为艺术存在的依据,艺术的本体存在依托于形象思维。于是,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否定形象思维就是否定了艺术。当时颇为急切的论证过程其实是缺乏相应的学理依据的,假如否定形象思维,也不过是否定了艺术创作的以“形象”来进行思维过程,形象是否能够进行思维,而思维究竟是否能够以“形象”为中介而展开,还没有经过论证和研究,仅仅凭借伟人的信件而肯定一个需要验证的学术问题,其实也还是“文革”思维的延续,与郑季翘不同的只有立场的赞同与否,论战双方对形象思维都没有持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的态度。
第二,从哲学基础而言,本次大讨论与上一次50年代的形象思维讨论有相同的哲学基础,都是以哲学反映论作为立论的根本,还没有走出艺术作为认识反映的园囿,艺术的任务还是要塑造一个典型形象。在50年代的论争中,无论是形象思维的赞同者还是否定者,一个共同的结论是,形象思维的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一点从苏联到中国都是相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将文学看成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与机械的认识论相对立,允许作家进行主观创造,根据现实生活的状况而在艺术世界里合成一个新的“形象”,形象的形成过程就是形象思维的展开过程。艺术家所创造出来的形象要符合现实主义作品的理想,最高目标是创造出来一个“典型”。在这一次讨论的初期依然如此。例如,1978年第3期的《解放军文艺》刊发了孟伟哉的论文《形象思维二题》,文章谈到,形象思维在艺术实践中的直接任务“归结起来就是创造典型形象”[3]54。我们知道,典型寄托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是现实主义作品所追求的目标。囿于当时的理论局限,几乎多数理论家在谈到形象思维时,一个强大的惯性结论就是“典型”。这一点在1978年早期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非常明显。其实,并非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孟伟哉的这篇论文中,就谈到了音乐在创作过程想要表现的主题和感情,想要描绘的情景和形象,其实这也是不能用“典型”一而括之的。在这篇文章中,孟伟哉试图提出一个“语言”的中介,以此来作为思维的媒介,将形象思维过渡到了用语言来思维,这就为突破“典型”论创造了契机。
从引证的资料来分析,在“文革”前被划定为“修正主义”的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论断重新作为资料支撑形象思维,如提出形象思维的别林斯基,现在有很多理论家与作家在谈论形象思维时会引用别林斯基的观点,这一点也带来了对俄国民主主义革命者及其作品的正名。此外,如维柯、黑格尔等一些曾经“腐朽的、资产阶级”美学家的言论也开始解禁,很多学者开始以黑格尔的论述作为论文的重要论据。虽然是“批判地”引证,但学者们也在逐步突破原来险隘的哲学反映论框架,为后来的美学讨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浦满春的文章《形象思维探讨》在文中就引证了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而不再是法捷耶夫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别林斯基的形象思维论直接来源于黑格尔,强调的蕴含在形象思维中的艺术的审美特性,而法捷耶夫作为“拉普”的领导人,更看重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第二次有关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中,学者们提到形象思维理论时,更多引用别林斯基“寓于形象的思维”这一说法,强调蕴含在形象思维中对艺术特性的探索。
第三,从当时讨论的内容来看,伴随形象思维讨论的还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反对“四人帮”的“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理论,反驳郑季翘的文章,普遍认为是郑季翘的文章为“四人帮”的言论提供了理论支持。现在艺术界要支持“双百”方针,反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郑季翘早年的文章也成为众矢之的。如1978年蔡仪的文章《批判反形象思维论》,就是专门反驳郑季翘文章的论文。蔡仪的理由在于,思维不只是抽象,概念可以有形象。他说,“思维作用对于感性材料的加工改造所形成的东西,既有抽象性重的,也有形象性重的,前者一般称为概念,也不能认为只是抽象的;后者一般称为意象,也不是毫无抽象的。”[4]67在蔡仪看来,形象思维也不否认抽象的作用,“所谓形象思维并不否认在它的思维活动过程中有抽象作用。……所谓形象思维或抽象思维,是指思维活动的某一过程就其主要倾向而说的,至于思维活动的某一过程中的抽象作用或具象作用,两者……却总是相反相成、相须为用的。”[5]68与很多理论家一样,蔡仪也非常认同创造性想象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蔡仪的这篇文章,主要是从学理上反对郑季翘的观点,反对“文革”时期的“三突出”创作方法。此时,形象思维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在谈到这一点时,先前形象思维的赞同论者在文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果说第一次形象思维大讨论还在争论一个学术问题的话,而这一次的形象思维大讨论从一开始几乎成为一种艺术的抒情。学者、作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饱受“四人帮”摧残的人们,将压抑了十余年的生活热情、学术热情与工作热情,全部迸发出来,投射在形象思维的讨论中,人们因伟人信件的发表而欢欣鼓舞。
第四,形象思维理论一跃而成为古今中外美学发展的主纲,似乎所有的艺术理论、美学现象、审美理想都可以统摄到形象思维理论的大旗之下,这不仅是社科院主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5]的初衷,而且也是众多文章立论的基础。如王文生、郭绍虞的文章《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开篇提出,“毛主席肯定的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一切以形象来反映生活的文艺,因而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实践意义。”文章以形象思维为总纲,梳理了我国文艺理论中对形象思维认识的发展过程。王朝闻在《艺术创作有特殊规律》中提出,“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再一次阐明了文艺创作的特殊方法。”[6]59唐弢的文章《谈“诗美”——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主要以毛泽东所谈的“诗味”为出发点,讨论艺术独特的审美特性。作者认为,“诗美,无论是音乐美或者图画美,都是诗人通过形象思维对他熟悉的生活的概括。一个人有了开阔的政治视野,才能从复杂多样的生活中捕捉他所需要的新鲜的形象;尤其重要的事,只有对复杂多样的生活作了深入的比较、考察、思索,不仅有自己切身的经验,而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这种经验和感受随着时间钻入毛孔,流进血管,成为诗人本身的细胞与神经,这时才会有我们所要追求的对象。”[7]98这就将所有的艺术规律都归结为形象思维的创作过程。这种观点其中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大家都把各种问题的特殊性压抑下去,将所有的艺术规律都集中到形象思维的话题之中。例如,在舞蹈艺术中,更多应该将舞蹈作为一种形体艺术,其形象的动态性,主要表现人体的律动、姿态和表情,这就不一定适合以形象思维来解释了。
三、 形象思维讨论再次登场的美学意义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化,首先是通过文艺战线表现出来的。最先发声的是一大批批判“文革”、呼唤新时期的文艺作品发表,如郭沫若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贺敬之的诗《中国的十月》以及卢新华的《伤痕》。紧接着,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开始,批驳“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重提“双百”方针。在这一系列的重大方针调整之前,第二次形象思维全国大讨论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逐步展开。60年代的中国美学争鸣终于“形象思维”,而新时期的美学复兴始于“形象思维”,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从延安时期开始,文艺被放置于从属政治的地位,建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运作的必要保障,其最高的理想是在艺术作品中创造出“典型形象”。而实现典型的方法,则是受到文艺界领导人大力支持的形象思维理论。在文革前夕,形象思维因其与“修正主义”的渊源和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被划上终止符,但是,当时的“典型”却被异化为“三突出”理论,观念先行,主题先行,由概念而生形象成为一种必然。新时期到来之际,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早年终结中国美学讨论的形象思维必须首先进行理论的突破,然后才能翻转文艺界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风气。于是,从形象思维讨论之后,久违的“双百”方针才能顺利登场,后来的写本质、写真实、人性人道主义讨论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在这里,形象思维话题像一道闸门,只有先将具体的创作打开局面之后,后来更加具有抽象性的问题才能进一步展开。第一次形象思维讨论的终结是一个历史的选择,第二次形象思维讨论的开始则重新创造了文艺理论的历史。
承认形象思维,意味着承认艺术创作的独特性,政治不能够代替艺术,一般的认识论规律不能够代替艺术的规律。这就蕴含了社会风气走出十年浩劫的契机。其实,从王国维的无功利艺术观与梁启超的小说救亡论开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中国美学现代性进程中就打一个结,成为相互较量的二元对立因素。在上世纪30年代,形象思维由左联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引入中国,他所依据的资料是法捷耶夫关于形象思维的阐释,而不是别林斯基提出的形象思维,二者强调的形象思维的内涵是不同的。40年代,随着延安《讲话》精神的传达,政治成为艺术首先需要高举的大旗。50年代中期的胡风事件就是用政治过分干预文艺的历史教训,而到60年代的“文革”,更是以政治清洗文艺的极端错误。时代风气转寰,不仅形象思维不再是一个理论禁区,而是一切艺术的共通规律。在此前提下,寻找艺术的独特规律成为一个可以探索的话题,这样就可以赋予艺术家与艺术创作相对独立的空间。形象思维在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转型,它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形象思维、艺术的审美无功利性、艺术的审美认知功能等话题都存在相互沟通和借鉴的可能性,这些话题都可以在美学领域里寻找到相应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说,形象思维为新时期的“美学热”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艺美学的研究,“从意识形态的理论角度转向了对文艺审美性征的研究。”[8]154
再到后来,形象思维研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方向,由形象思维的研究转向了思维科学的研究。形象思维走出人文科学而跨入自然科学,形象思维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文化热”。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了刘欣大的《科学家与形象思维》和沈大德、吴廷嘉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辩证逻辑的一对范畴》两篇文章之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刘欣大的文章《科学家与形象思维》论述了一个观点,科学家也同样离不开形象思维,这就把形象思维的适用范畴由艺术推向了科学。文章在结尾部分提出,“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公开发表一年半以来,被诸多原因阻断了十多年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又活跃起来了,很多同志热心探讨形象思维的特征,从多方面阐述形象思维的功能,但仍然囿于文艺领域。”[9]107于是,作者呼吁“希望哲学家、心理学家、脑和神经系统研究工作者、作家、艺术家、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工作者通力协作”[9]108。研究思维的方法,不应该仅是哲学上的理论思辨,还应该包括实验、分析和系统的方法。直到今天的认知美学领域,审美思维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1]程光炜.“85文化热”三十年[J].文艺争鸣,2015(10):3.
[2]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座谈会纪要[J].诗刊,1978(1):2.
[3]孟伟哉.形象思维二题[M]//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形象思维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33-58.
[4]蔡 仪.批判反形象思维论[M]//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形象思维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25-32.
[5]王文生,郭绍虞.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M]//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形象思维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108-117.
[6]王朝闻.艺创作有特殊规律[M]//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形象思维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59-797.
[7]唐 弢.谈“诗美”——谈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M]//四川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形象思维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59-797.
[8]祝志满.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美学发展的思考.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2):154.
[9]刘欣大.科学家与形象思维 [J].中国社会科学,1989(3):97-108.
(责任编辑 伯 灵 校对 伊人凤)
The Discussion of “Image Thinking” in New Period and its History Significance
AN Jing
(School of Literature,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Propagandalized by The Renmin Daily,The Poetry Club and The People′s Literature Editorial Board,and Mao Zedong′s Letter to Chen Yi on Poem published in Renmin Daily and Guangming Daily on the date of 31st in December of 1977,the discussion of “image thinking” In New Period formally began.This time of “Image Thinking ” discussion rectificated the name of literature and art,reversed the social atmosphere initiatively,and opened the way of literature theory study,aesthetics popularity and the culture study.
New Period;image thinking;history significance
2017-03-0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11);中央民族大学2015年度校级自主科研项目(2015MDQN18);中央民族大学文艺青年创新团队“经典阐释与当代文艺学建设”阶段性成果
安 静(1982-),女,山西代县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10.13888/j.cnki.jsie(ss).2017.03.001
I206.7
A
1672-9617(2017)03-028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