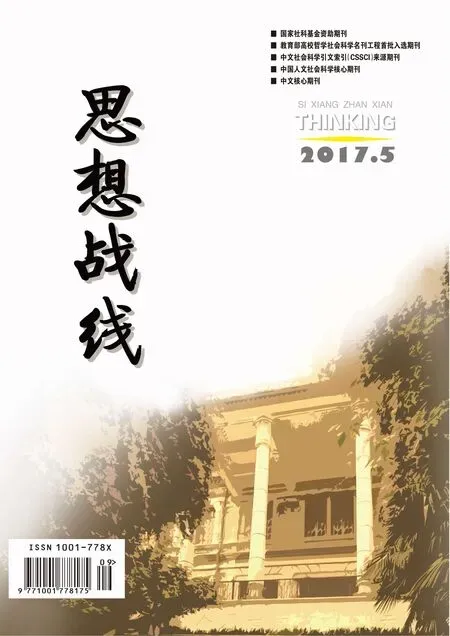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儿童正义问题
2017-04-11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儿童正义问题
亓光
儿童由于其特殊道德地位——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特殊性——决定了儿童正义既是社会正义的具体类型,又不同其他具体的社会正义类型。在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具体表象中,能力匮乏是其得以居于儿童正义问题核心的决定因素。在道德哲学谱系中,能力进路致力于解决此种匮乏而成为正义理论的重要流派,但一般性的能力进路难以解决儿童的能力匮乏问题,必须在扬弃能力进路的正义观的基础上,揭示儿童正义的实质——特殊的能力养成。为此,特殊的能力清单应让步于能力的特殊性,以客观位置性为角度,从儿童主体的维度、社会正义的维度、能力养成的维度来揭示和解释儿童正义所需的特殊能力的选择标准。
儿童正义;能力进路;社会正义;“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福祉与发展
儿童正义是一个重要的正义问题。在伦理学层面上,作为特殊人类群体的儿童是人类之爱的中心,即便是将这种爱作为一种严格道德律令,人们也会欣然接受。但是,正因为爱与儿童之间的关联性,加之“公正的言说所具有的特征,与爱的言说的特征形成最鲜明的对比”,*[法]保罗·利科:《爱与公正》,韩 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页。所以儿童正义问题鲜有阐述。然而,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儿童正义都具有相对完整的意涵与重要性,存在明确的中心议题和核心问题,而且具有总体性的现实责任感。本文拟在澄清儿童的道德地位与重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儿童正义的义界,以能力进路为中心切入儿童正义的核心问题,进而初步论证儿童正义所需的特殊能力的选择标准。
一、认真对待儿童
儿童正义是与儿童的特殊性及其道德地位密切相关的正义问题。西方学者伯鲁比曾悲观地指出:“假如我们能设想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组织中,像杰米(这里泛指良好的儿童生活并接受优质的教育——作者注)一样的公民被养育、支持与鼓励与尽可能地实现他们的人类潜能,即便如此,我们到底会出于什么原因而设法创建它呢?”*参见[美]玛莎·努斯鲍姆《正义的前沿》,朱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章引语。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儿童不具有特殊的人类特征与特定的道德地位,那么即便存在某些生理特征的差异性,也无法证明儿童正义作为一种特殊正义的正当性。因此,何谓儿童正义是一组命题的综合,即儿童的重要性、儿童的道德地位以及关于儿童的正义话语。
一方面,认真对待儿童就必须理解儿童的重要性。如何认识儿童,这是判断儿童居于何种道德地位的前提。一则,如果将儿童看作成年人的准备或长成阶段,那么在伦理学语境下,儿童就是成年人早期的概念符号。因而按照成人的道德标准,儿童只是一种未成熟的准备状态。其并不具备相对独立的道德地位。二则,如果将儿童作为儿童,即儿童是作为一个在特定时期实际存在的自我主体范畴,尽管儿童必然要长大成人,但其存在意义是当下的而非只是为了他(她)的未来,那么儿童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道德地位。否定“儿童-成年”是“过程-结果”的逻辑关系并非意在割裂二者,而是揭示任何道德评价都需要尊重语境与评价本身,不能为了实现正义标准的一致性而忽略儿童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理解儿童正义以及什么是发生在儿童身上的不正义,应该理解对待儿童的正义(或不正义)会如何波及他(她)的余生,而不是相反。
具体到正义问题,儿童之所以具有特殊重要性,最初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横亘在成人生活中的爱与正义之间的伦理界限对儿童则难以成立。近代以降,正义逐渐成为一个在道德主义范式内被严格限定的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它主要甚至只涉及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普遍追求的一般价值或共同遵循的理性原则,且是建立在偏好博弈与契约理性之上的正义制度、原则与规范。与此不同,契约性议题在儿童问题上非但不是核心问题,甚至被其质疑的爱之正义以及由爱而产生的幸福反而是儿童正义的核心要义。首先,儿童正义的存在以其自身为归宿。古典德性论者强调,儿童通过教育在身心和道德感等方面获得成人所需要的正义德性。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儿童对于正义问题的认识是以培育成人世界的正义理性与正义感为目的的。然而,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意味着任何附加于儿童的德性、制度与行为标准,都是“社会分工-标准化”这一工具理性的结果。但是,“儿童-成人”的过程本应是多元诉求与多种可能的。儿童潜能的实现并不存在标准化的合理性,因而可能性是儿童的主体价值,追求精神和物质的富裕生活只是这一价值的部分外化。其次,儿童正义的基础是承认儿童的非独立性。一般而言,正义是德性或理性的主体间关系的理想状态。在传统伦理话语中,儿童因其非独立性而不属此列。但事实上,这种非独立性正是儿童的主体性及儿童正义的合法性所在。其将成人对儿童的关爱、儿童的幸福感与儿童的成长目标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最后,儿童正义的内容取决于儿童生活的多维性。儿童生活中的信息数量庞大而复杂,而近代以来社会正义论的经验基础却是理想类型化的产物。二者根本上是无法调和的。只有立足于儿童生活的多维性,才能从整体上了解儿童正义的完整性与动态性。如果当代社会正义论可以涵盖儿童正义,那么其必然要充分接受这些维度的差异性,而相关维度的正义解释经充分概念化才构成了儿童正义的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认真对待儿童必须正确认识儿童道德地位的特殊性。儿童的主体重要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而是在道德意义上的重要性,即判断儿童的道德地位是确定儿童正义的前提要件。儿童的生活不是一种个体生活,而是一种基于公共关怀的社会生活。亚里士多德的总体正义观虽然正确地发现了正义的总体性与复义性,但却在这种总体性中排除了儿童这个群体。自由主义者则直接用权利观解释儿童的道德地位,认为实证性的儿童正义是借助个体基本权利的诉求而建立起来的。但是,自由主义者对基本权利的建构并不是为了阐明儿童正义,而是试图吞噬它的存在。基本权利的建构无法充分说明儿童的正义。
在很大程度上,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径路不仅遭受这种一般性的困难(即它的建构是不确定的),还要遭受特殊的困难(即它不能为那些不完全的义务奠定基础),而这些义务的履行在儿童的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的……那些鼓励尊重儿童权利的人并不是对儿童讲话,而是对那些会以自己的行为影响儿童的人讲话;他们有理由优先选择义务的修辞而不是权利的修辞。这既是因为义务修辞的范围更广,也是因为它更加直接地对相关的听众讲话。*[英]奥诺拉·奥尼尔:《理性的建构:康德实践哲学探究》,林 晖,吴树博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9页、第261页。
因此,所应转变之处在于将权利框进儿童的主体特征边界内。衡量儿童的道德地位,应同时强调儿童的主体特征既不同于成年人,也不同于一般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在规范伦理学中,无论何种认识进路,儿童都会与成人相区别,因而产生了儿童较为特殊的以爱与关怀为基础的道德地位判定。但是,这种判定是混同于其他限制行为能力人道德地位的判定。例如,在能力进路的分析中,儿童就往往与残疾人等量齐观,并由此为他们设计了彼此相似的伦理规范。这本身就是一个认识偏差。我们不妨将儿童的指向极端化,以婴儿、新生儿甚至胎儿为标准,这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表现出儿童主体特征的特别之处。一方面,儿童的自我决定性较低,特别是对于伤害性后果的判断与规避的自我能力较低。另一方面,儿童的自觉抵御性较低。尤其是对既存或先天的不利因素缺乏抵制能力。这两点并不同于生理性的不健全或精神性的不健全,且是可逆或可变的。其本质是自我意识的阶段性不健全。正是这种不健全,决定了儿童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主体。正因为如此,生物性的功能和能力的特征决定了儿童的道德地位,并意味着要严肃对待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
在此基础上,认真对待儿童的中心问题,就是以儿童-成人的差异性来观察儿童正义所直接关系到的作为基本实质性善的儿童福祉。在这里,儿童-成人差异性的影响就必然体现在儿童福祉的正义标准上,即任何儿童福祉都应该是以儿童的内在需要为首要条件。在儿童福祉问题出现时——主要是贫困、不平等问题——要充分考虑儿童的幼稚性、脆弱性与依赖性是普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分析儿童福祉的正义性就离不开一般福祉的正义性。由于能力进路充分解释了现实福祉的正义性,因此其也就自然会置入到儿童正义问题的视域中。
二、理解儿童正义的前提:能力进路及其修正
众所周知,功利主义成为近代以来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主流范式。功利主义以模块化的方式试图归纳正义概念的共性要素。其中,密尔的“六类说”最为著名,由此奠定了正义转向分配正义、总体正义转向特殊正义的基础。在这里,基于效用、资源、制度等思考路径的差异性,实际上来自于关注点及其优先性排序的认识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罗尔斯正是发现了功利主义轻视分配问题,才在揭示出“功利主义并不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基础上,*[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进而批判性地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阿马蒂亚·森精确地指出,功利主义发现了正义与优势的评价与配置关系,而罗尔斯则解释了优势是因人而异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因人而异的相对优势如何放置在同样的指标体系中加以评价而得出正义与否的结论。由此,阿马蒂亚·森才提出了能力——即人有实现其重视之事的能力——是检验优势正义的一套指标体系。*参见[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 磊,李 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项目管理系统:根据科研项目的特点,对项目申报、立项、实施、验收过程中所需财务信息的归集、整理、提取和分析进行科学全面的设计。采用传统的办法,难以及时有效地掌握最新的科研情况,而且每次查询统计工作量浩大,通过本系统对科研项目实现项目分级、分类管理,使各级领导不但可以对所承接的各类项目及取得的成果一目了然,也能对未来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预测。
儿童-成人的差异性是儿童具有特殊道德地位的原因。它体现在依法律的完全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区分而产生的能力匮乏。这一现象的实质在于,人们往往重视儿童的法定地位的特殊性,而忽视其道德地位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匮乏决定了这种特殊性,产生了一种不正义的状态;而如何消除或者减少此种匮乏则是一种道德改良,是恢复正义的基本理路。在当代道德哲学谱系中,能力进路明确主张:“人性尊严应得到尊重,这就要求公民在各个主要领域内都发展出最低限以上的能力,而具体所定的最低限应当是充裕的。”*[美]玛莎·努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田 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6页。能力进路因致力于解决由匮乏而造成的不正义状态而独树一帜,成为正义理论的重要流派。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一般性的能力进路能否解决儿童的基本能力匮乏问题。“在基本能力的延展和塑造过程中,母亲的营养和孕期的经历都有其作用。在此意义上,即便是孩子出生之后,我们也总是在面对已由环境形塑的幼年期的内在能力,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潜能。”*[美]玛莎·努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田 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由此可见,能力进路的正义观是否适用、能解释并改造所有因匮乏造成的不正义状态,才是理解儿童正义的重要前提。
首先,应承认能力进路是理解儿童正义问题的基础性论证。能力进路是平等主义正义论的重要基石。相对于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形式性,平等主义正义论特别强调基本善的实质性。它突出了所有的理性人作为目标概念的平等性,强调作为目标概念的善体现在对人们生活的平等评价之中,而这种平等评价必须具有明确的指向和决定人际间比较的现实性。这就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就是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福祉和能力。不过,无论是经验性的能力路径还是先验性的能力路径,能力作为一种基本实质性的善,是考量人们生活是否平等的总体性把握。
甚而言之,只要人们认为我们能够通过这种准则对人的生活的平等状况加以总体评价,以及能够依据基本实质性善的方式在不同人的生活质量之间进行一般性比较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的话,我们就可以对诸如益处或获得益处的途径设定某些整合性的平等准则,而这些益处就包括了福祉、资源与能力等。*Thomas Christiano. A Foundation for Egalitarianism. Egalitarianism: New Essays on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Equal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这种哲学性的描述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感。正如努斯鲍姆所言:“它们都包含着生物……与某一具支配性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和能力的严重不对称。”*[美]玛莎·努斯鲍姆:《正义的前沿》,朱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而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指出,权力仍属于简单计算的客体对象,而能力则着眼于人类生活,是一种基本的正义视角,其所关注的是纠正那些专注于手段的方法,从而将注意力放在实现合理的目的的机会与实质自由上。*[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 磊,李 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作为实质性自由的能力是复杂的。个体的才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个人才能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发展环境的结合,能否创造出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机会,才是它的基本要素。如今,这种现实感使得能力路径在直接关涉与具体的人相关的正义问题时成为了十分重要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学理性基础正是能力路径。由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解决以贫困为代表的不正义问题时,能力路径逐渐成为政府设计制度、制定政策的首要依据。
其次,基于儿童-成人差异性的特殊匮乏性,需要扬弃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阿马蒂亚·森较早地提出了可行能力论,而努斯鲍姆则在可行能力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内在的可行能力、综合的可行能力与人类的核心能力为基础的能力门槛论,由此构成了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这一进路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能力“可以以种种方式转换成运作。如果一个社会只是赋予民众以充分的能力,但民众却从未将能力转化为运作”,*[美]玛莎·努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田 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6页。我们就不能称这是一个好的社会。相比之下,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可行能力是一种正义方法的内在逻辑。而努斯鲍姆的能力门槛则是这一内在逻辑外化后的具体对象,并最终为如何认识和界定福祉概念提供一种有效路径。在这里,通过能力进路,人们的福祉是由一些作为人性本质的能力所界定的。对此,就如努斯鲍姆所言,人类至少需要具有十种能力:生活,身体完整,身体健康,有感觉、想象力与思想,情感,实践理性,相互联合,关怀动物与植物,游戏以及控制个人环境。正因为它们与对福祉的客观考量有关,所以能力进路对儿童福祉问题的考察十分有吸引力。*Alexander Bagattini, The Nature of Children’s Well-being: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Springer, 2015. p.175但是,即便上述能力内容具体化了,甚至考虑了残疾人等能力缺陷主体的特殊性,这依然不能证明其真正考虑到了儿童-成人的差异性带来的儿童能力选项上的特殊匮乏性。我们认为,儿童-成人的差异性意味着,一方面,虽然儿童是一个缺乏道德自主的主体,但儿童阶段却是获得道德自主性的必然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能力匮乏不是绝对的、固定的,而是相对的、变动的。另一方面,儿童获得道德自主性的过程是迅速的,因此这个阶段的能力匮乏既存在多种可能来源,又会产生直接而长久的不良影响。因此,能力进路虽然提出了儿童正义的核心是能力平等的问题,但是却并未能真正建立与儿童相适应的规范理论。事实上,能力进路的基础是假设在正义出现问题时,主体能够做出自主性的决断,而且这种决断是一贯的。然而,儿童恰恰就缺乏此种一贯的决断性。这就导致能力进路并不能充分运用到儿童,也就难以解释儿童正义的问题。*Colin M.Macleod. Primary Good, Capabilities and Children. Measuring Justice-Primary Good and Capacit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174~192.由此可见,安排符合儿童正义的能力内容是扬弃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能力进路的关键。这就必须考察儿童的精神、生理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因素及儿童对其吸收后出现的自我后果,并将符合儿童的道德自主性养成和选择的能力作为儿童正义的构成要件。
最后,考量面向儿童正义的能力进路的基本判断。厘清上述两个方面问题后,主要问题已经转向了实现将符合儿童的道德自主性养成和选择的能力作为儿童正义的构成要件的方式。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考量面向儿童正义的能力进路的基本判断。一方面,应考虑儿童的特殊匮乏性所决定的能力主体的差异性和变动性。这是面向儿童正义的能力进路在主体维度上的扬弃与重构。努斯鲍姆在涉及儿童生活的正义问题论争中,确认了儿童在主体上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能力框架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而“在能力进路下强调主体性,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指明儿童所应承担的最大限度的决断性要与儿童的实际或潜在的理性能力与理性选择(或判断)形式的能力直接保持一致。”*Rosalind Dixon, Martha Nussbaum. Children’s Rights and a Capacities Approach: The Question of Special Priority, Chicago Public Law and Legal Theory Working Paper, no.384.这一标准不但有助于解决儿童年龄段判定分歧造成的能力内容碎片化,而且在总体意义上,对未成年人的能力内容的判定和选择也具有启示性。另一方面,面向儿童正义的能力进路所设计的变动性不是任意模糊的,而是与人在特定阶段的不同程度上的自身才能、既得业绩与环境条件等因素直接相关。而能力进路的不确定性之所以并不会造成儿童正义的虚无化,关键在于其能力门槛作为实现目标的确定性。
具体而言,能力扩展或能力演进的过程是从tn时期的儿童已具备的内在的功能集合中开始的。资源交往的过程受到制度、规范、文化等限制方式或许可方式的影响。这就塑造了儿童的各项功能和能力的新集合的形式,而这些功能和能力是具有跨期特性的。因此,资源或限制性、自身的有限性机遇以及具备的才能催生了儿童的能力集合。从多维能力集合角度看,在tn+1时期将决定获取新功能的朝向。如果对此连续性时间周期加以观察,那么会发现这一动态过程将受到回馈环路的影响。儿童在情感认知上的进步体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中,他们所作的决断及其主体性受生活经验和模仿行为的塑造。*Jérme Ballet, Mario Biggeri, Flavio Comin. Children’s Agency and the Capacity Approach: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ldren and the Capacity Approach,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34.
总之,儿童正义问题的根本在于特殊的能力养成。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下位概念,儿童正义指向以儿童-成人的差异性为特征的儿童福祉与道德自主的增益过程,通过特定的能力内容在阶段性变动与长远性稳定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能力或功能的完善,而逐步实现充分的社会福祉与道德自主的能力养成。
三、儿童正义:特殊的能力养成
一般人认为,假如能力匮乏是一种无力支配的能力状态,那么其必然是恶的。而这种恶是非正义的,因此必须要克服。在这里,儿童正义是普遍理性的能力养成的特殊阶段。我们认为,这就偏离了特殊的能力养成的内在需要。为此,应避免按照社会正义标准对人进行抽象性的重建,而从特定个体的具体尺度和属性出发,对其进行分别计量和对待。能力进路的积极性,也正是因为它在人与人的差异性对于正义的影响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对主体的多样化需要与能力的多元化模型的相互关联与综合,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抽象的制度建构主义与正义的纯粹社会理论之间的割裂。问题的关键由此变成了能力匮乏成为制约实现正义的关键问题。从具体内容来看,阿马蒂亚·森陈述了诸如年龄、性别、肢体、疾病、物理环境、社会气候、人际关系等造成的能力匮乏,旨在证明可行能力与实质自由的一致性,证明能力匮乏将使一个人无法从事其认为有实际价值的事。然而,能力匮乏并非必然的恶,“未成年人无力支配其自身,即无力自己追求适合于他自己的目的,通常都是基于某种缺失。这种缺失可能是不自然的和不正常的……也可能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比如在小孩子那里,此时,这种缺失并不是一种恶,而仅仅只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匮乏”。*[法]耶夫·西蒙:《权威的性质与功能》,吴 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1~12页。可见,能力匮乏本身也存在差别,并非一般的恶。而儿童的能力匮乏并非是恶,反而是自然的善。如果将这种能力匮乏简单划入一般意义上的恶,也就无法从完善能力的角度理解儿童正义。
如果上文的论证是成立的,那么提出一个能力清单,并不会直接有助于明确特殊的能力内容及其养成。一般的能力清单特殊化处理的实际效果是为既存的优绩统治理论下的能力不平等进行正义性辩护,即将儿童的特殊性从能力清单中排除,而代之以其他道德情感的关怀,使之成为正义无涉的论题。其实质是“存在于内在能力之中的不平等应该通过承诺不平等的成就和不平等的地位及时地表达自我”。*[英]布莱恩·巴利:《社会正义论》,曹海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4页。为了扬弃这种狭隘的能力进路及能力清单,应将经验性的清单纳入原则性的特殊性标准的构想中,即位置客观性。对此,阿马蒂亚·森指出:
位置客观性是指从某个特定位置观察结果的客观性。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不因人的变化而变化,而与所处位置相关的观察及其可观察性,也就是我们从一个给定的位置上所能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客观评价的对象是任何占据某个给定的观察位置的正常人都能确定的事物……观察的内容可以因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但不同的人从同一位置进行观察却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 磊,李 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在很大程度上,这既是努斯鲍姆认定阿马蒂亚·森没有充分重视具体的能力内容的误解之源,也是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论更加贴近儿童正义问题的实质——特殊的能力养成——的可能性所在。
假设位置客观性的预设是合理的,那么面向特殊的能力养成应该成为儿童正义的核心与目标。位置客观性应包含主体维度、社会正义维度与能力发展维度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从儿童主体维度看,特殊的能力养成只有关注儿童本身,且以儿童的视角为评价标准,才可能实现能力进路下的儿童正义。对于儿童,首要之处在于,其所要得到的能力养成是以其特有的福祉及其发展为目标的。这些目标本身不是具体而明确的。不同的国家、种族、宗教以及财富、智识等方面的差异,都是造成上述目标难以明确的原因。因此,站在儿童的主体性角度,就必须将有待养成的能力,放置于特定能力匮乏所导致的不正义现象的考察中。换言之,真正将儿童作为正义主体,意味着由儿童的能力匮乏造成的不正义,不是从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应具有的普遍能力及其终极标准出发,对上述匮乏加以改造,而是将前者作为后者所产生的后果。努斯鲍姆曾经强调,之所以动物正义、残障人正义、儿童正义都应服从于一种普遍的能力清单,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尊严是普遍适用于有感知生物的基本道德观念。但是问题在于,感知生物的尊严生活的内涵是模糊的,而儿童正义的内涵是明确的。感知生物的尊严生活所能影响到的正义范围也是有限的,而儿童正义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感知生物的尊严生活只能描述一种正义的状态,而儿童正义则是一种不断实现的正义过程。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保障对儿童自身的关注,凸出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实际,就必须进一步强调尊重儿童的自身视角。当然,这并不是一味接受儿童的需求、判断与选择,而是从他们的需求、判断与选择中发现某些特定的可行机会,以此来推进特殊的能力养成。进而言之,承认和尊重儿童的视角,并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认为儿童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具有完全的自主决断力,而是承认儿童在其年龄阶段会产生与相应阶段相符合的个人观点。这就需要通过承认和尊重儿童视角的方式,将这些观点有机会表达出来,并且将其作为制度性正义考量的价值要素加以对待。*David Archard, Marit Skivenes. Balancing a Child’s Best Interests and a Child’s View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Rights, 2009,17(1) .
第二,从社会正义的维度看,特殊的能力养成应与社会正义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可以在实践中得以验证、改变与重塑,并且能够得到与社会正义相关的评价方式的客观考量。正是立足于社会正义的价值性,阿马蒂亚·森才提炼出来可行能力的方法论意义,即这样一种研究正义问题的方法不仅能在理论上成立,而且在实际中也能得到应用,即便它不能明确地列举出绝对公正社会的要求。这种方法包含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各个理智而中立的判断者,可以对先验主义的公正社会是什么样的持有不同的合理看法。*[印]阿马蒂亚·森:《正义的理念》,王 磊、李 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由此可见,坚持从能力进路分析儿童正义问题,既不是一个儿童需要的特殊正义状态,也不是一个完备的能力正义状态,而是一种底线判断。它并不试图解决所有的分配难题。它只要具体规定一种相对充裕的社会最低限。*[美]玛莎·努斯鲍姆:《寻求有尊严的生活》,田 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页。这一进路是在社会正义的语境中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并通过这种社会正义的批判性审思,对不断变化、革新抑或重现的儿童正义问题加以解决。如果说社会正义是一种动态的合理性评价体系,那么,在它的视域下,经过特殊的能力养成而存续的儿童正义问题,一方面表明,任何能力清单都必须根据社会正义需要的变化而设计、调整、修改与重新设计;*参见Colette McAuley, Wendy Rose, Child Well-being: Understanding Children’s Lives.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2010.另一方面指明,能力清单始终处于偏离正义的可能性与危险性。*参见Gottfried Schweiger, Gumter Graf.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Child Pover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特别是要警惕以幸福为核心的正义标准。这一标准往往会被功利主义者算计,而偏离特殊的能力养成和尊重儿童主体特性的正轨。
第三,从能力本身的维度看,特殊的能力养成,须是一种在儿童的各个主体范围和多元的社会正义标准下可以反复配置的能力集合。对此,资源主义者的激烈批评不但对能力进路的儿童正义提出了挑战,甚至对于能力正义的一般理论也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最明显的一条就是,能力无法配置,也就谈不上正义的配置。在这里,努斯鲍姆专门指出:
从狭义经济学或自利意义上的‘获利’来讲,这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将由此(正义的配置)获利,它仅仅是出于我们对正义和爱他人的依恋,我们感到我们的生活跟他们的生活相互交织,感到我们跟他们分享目标。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在人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形成社会的问题上给出一个有缺陷的故事。正是我们接受了那种信息,并把它深深地容纳到我们自己的自我理解当中,一切才变得难以解决。*[美]玛莎·努斯鲍姆:《正义的前沿》,朱慧玲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5页。
为此,努斯鲍姆极力主张,明确的能力清单应提供一种新的正义配置。虽然她的能力清单未能充分考虑到儿童的主体特性,但确实已经清楚地证明,能力不论特殊与否都应被配给,儿童能力的特殊性及其特殊的福祉与发展之间保持着因果关系,进而从侧面证明了可以根据社会正义的标准,以儿童所需要的特殊福祉和发展为对象,进行能力的配置。在此基础上,这种配置因其对象的现实性而具有反复实现的可能。较之于罗尔斯对基本善的可分配性的分析,努斯鲍姆的能力清单的可行性更高。当然,从能力本身出发,就必然会面对在特殊能力的养成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后果与消极后果。而如何权衡利弊,也对所应考量的不同能力养成结果的儿童正义的具体语境提出了更为复杂的要求。*Gottfried Schweiger, Gumter Graf, 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Justice and Child Pover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66.
四、结 语
儿童正义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儿童,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儿童正义概念。只有从儿童的非独立性的正当性,建构其上的非权利性道德地位与儿童-成人的差异性的正义标准角度出发,儿童正义才能从自由主义正义话语的思维限制中解放出来。超越权利本位的正义话语,需要从学理上清算功利主义道德哲学的影响。为此,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的能力进路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反思,确认了能力进路是分析解决儿童正义的适当基础与合理框架。但是,基于儿童-成人差异性的特殊匮乏性的存在与显现,表明阿马蒂亚·森-努斯鲍姆能力进路所预设的前提条件、核心论证的依据以及基本逻辑推演,都是在模糊甚至吞噬上述差异性的前提下,才能自我证成。解决这一悖论,就有必要寻找提供一种面向儿童正义本质的能力进路方案。作为社会正义的子类型,儿童正义是以儿童-成人的差异性为核心的儿童福祉与道德自主的增益过程与结果。在儿童的特定能力内容的阶段性变动与长远性稳定的相互关系中所产生的能力或功能的完善,是实现充分的社会福祉与道德自主的能力养成,即儿童正义的关键。正因为这种动态性的存在,传统能力清单等模型工具的分析效力必然不断衰退。在位置客观性的基本条件下,将经验性清单纳入原则性标准的构想中,是合乎儿童正义所欲实现的特殊能力养成的可行之法。换言之,这种特殊的能力养成,就是要从主体维度,注重确立面向儿童本身且以儿童为视角的特殊标准;在社会正义的总体建构中,强调特殊的能力养成是社会正义现实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能力集合的反复配置中,将儿童的各个主体范围及其多元化的社会正义标准包裹进来。
(责任编辑 张振伟)
Justice fo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QI Guang
The special moral status of children or the particularity caused b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determines that although justice for children is a specific type of social justice, i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specific types of social justice. Of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lack of capabilities is the decisive factor at the core of the issue of justice for children. In moral philosophy, capability approach, known as the Sen & Nussbaum approa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chool of justice theory for its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the lack of such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general capability approach can hardly be us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children’s lack of capabil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useless part of justice in capability approach to reveal the true nature of justice for children——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 capabilities. To do that, the list of capabilities should give way to particularity of capabilities. The selection criteria for special capabilities required by justice for children should be revealed and interpreted objectively from three aspects: children as subjects, social justice and cultivation of capabilities.
justice for children, capability approach, social justic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ldren and adults, well-being and development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公正话语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13CZZ002)。
亓 光,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徐州,221116)。
B089
:A
:1001-778X(2017)05-009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