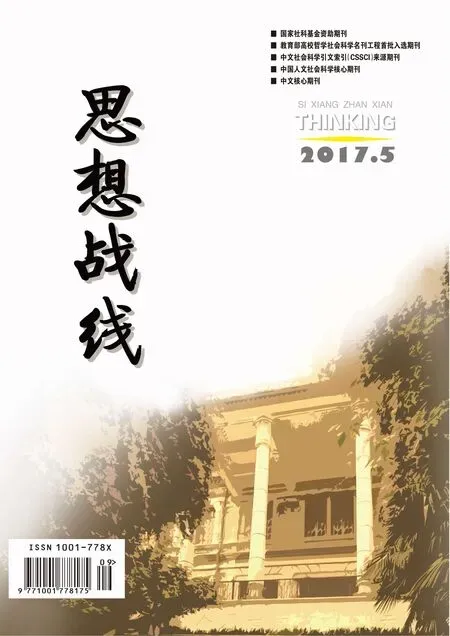“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2017-04-11
“亨廷顿之忧”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
周平
亨廷顿在其最后著作《我们是谁?》中,看到苏联解体、英国“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时,不禁为美国是否会出现同样的情况而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作为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的要害——民族国家合法性根本上来自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为保障民族认同国家而构建的制度机制之所以会引出国家认同问题,甚至导致国家认同危机,是因为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遇到了“多族化”问题。正是这样的“多族化”现象,侵蚀了曾经屡试不爽的那些实现和保障国家认同的制度机制,成为了国家认同危机的温床。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完整地演绎了“多族化”引起国家认同问题,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的逻辑,从而触发了“亨廷顿之忧”。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也无法置身事外,只有把巩固国家认同的内容纳入到民族政策的政治标的,并以此来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方能规避“亨廷顿之忧”。
亨廷顿之忧;国家特性;多族化;认同危机;国家解体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以对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慧眼独具的见解而著称。然而,他晚年时却将目光转向美国自身,聚焦于美国的国家认同/国家特性问题,并在对美国的国家认同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之后,出版了人生的最后著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该著作提出了一个看似平淡却蕴涵着震撼性的问题——“我们是谁?”。在对此问题的追问中,他看到了美国的国家认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下降。而这与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直接相关。他针对英国、美国和苏联的现实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这三国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会,它们的政府相对说来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认是合法的,它们的人民作为英国人(British)、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有很强的国民身份意识。”可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不复存在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联合王国的联合不那么强了”,“有了分崩离析之势”,“有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历史”。不仅如此,美利坚合众国也可能在2025年“成了另一国家或几个国家”。*[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页。而这一切,都是由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造成的。亨廷顿为此而深深地忧虑!诚然,亨廷顿的忧虑是针对特定的国家而发出的,但这样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亨廷顿之忧”也具有普遍性,它对民族国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示: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严重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导致民族国家解体。民族国家的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亨廷顿之忧”直击民族国家要害
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亨廷顿的论述是从“还挂国旗吗”的提问开始的——亨廷顿把这看作是具有“重要性”的问题。该设问的背景有两个,远一些的是苏联解体,近一些的则是美国的“9·11”事件。在这样背景下提出上述问题后,亨廷顿通过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挖掘到了美国的国家认同/国家特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事实,并意识到这对国家的统一和巩固构成严重的威胁。亨廷顿的忧虑也就来自于此。不过,通观全书就会发现,“亨廷顿之忧”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国家面对严峻挑战和危险而产生的情绪宣泄,而是对民族国家进行全面审视基础上形成的一针见血的见解,击中了民族国家的要害。
曾经,民族国家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冷落的问题。由于缺乏研究以及对民族国家的不了解,民族国家常常被界定为“单一民族国家”。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民族或族群构成单一的国家,所以民族国家又常常被否定。由于对民族国家缺乏了解和正视,政治学、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学的许多研究无法合理地推进,甚至还导致了许多理论误判。针对这样的现实,笔者于2009年和2010年先后发表了“对民族国家的再认识”和“民族国家与国族建设”等一批研究成果,*这两篇论文分别发表于《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4期、《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对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随后,民族国家受到的关注度便不断提高,民族国家这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现象也被广泛接受。尤其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性质得到了普遍的肯定。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界对民族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和论述大量涌现,出现了诸多的民族国家定义。可是,其中的许多定义、分析和论述,仅停留于民族国家的表象,只抓住了民族国家的某种类型、某一方面或某个特定阶段的特征,而没有抓住民族国家的本质,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往往模糊、不全面甚至是以偏概全,过分强调自己国家的特殊性,因而未能真正把握民族国家的本质,影响了进一步推论得出的结论的准确性。
诚然,民族国家是今天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国家形态。而且,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或自我标榜的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但是,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人类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态,有其形成和演变的规律。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民族”与“国家”结合的产物,并且以“民族”(nation)来命名,自然具有突出的“民族”属性。但是,对民族国家的民族属性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民族是社会群体形式,国家是政治形式,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并非简单的“等同”,而是一种有机的结合,即国家有了民族的内涵,民族有了国家的形式。今天的民族国家具有多样性,相互间的差异性很大,不可一概而论。但是,各个民族国家不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具有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并且,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和法律单元,因而深受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及其规则的影响和制约。
纵观人类国家发展的历史,国家不过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政治形式,当然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最为持久和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但是,它本身也处于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并且处于不同文明中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形式。民族国家是在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然后才推广到全世界。而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西欧绝非偶然,而是与“民族”的形成直接相关。罗马帝国对欧洲的统治及其推行的罗马化,对欧洲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促成了文化的同质化。恩格斯就曾指出:“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4页。这种状况到了中世纪末期才逐渐改变。中世纪末期,王朝逐渐兴起。各种王朝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整合方式,逐渐把国内居民整合成为一个个的整体,即后来民族主义者所称的“民族”。因此,黑格尔指出:“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转引自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霍布斯鲍姆也认为:“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当这些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渐萌生和觉醒以后,王朝并不代表也不保护整个民族利益的症结就不可避免地被意识到了。于是,觉醒的民族便与王朝处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在此背景下,各种以维护民族的每个成员权利为基点的观点和理论应运而生,并在唤醒全民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而还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打倒专制君主,摧毁王朝国家才能构建起近代民族国家。”*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朝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最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为新兴的民族所接受和认可的新形态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这便是民族国家。
首先出现于西欧的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既为国家增添了民族的内涵,从而为国家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又使民族具有了国家的形式,披上了国家的外衣。由于国家与民族相得益彰,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式便具有了巨大的活力,产生了巨大效应进而形成示范作用。于是,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式纷纷被其他国家采纳、效仿,最终遍及全球,成为普遍性的国家形态。随着民族国家的普遍化和广泛化,民族国家间的差异性也变得十分突出。从总体上看,欧美最早出现的民族国家,是在一种大体一致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国内的人口性质和构建的方式基本一致,是原生型的民族国家。后来那些因为学习和接受欧美民族国家制度而构建起来的民族国家,属于模仿型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其实质在于,“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实现的。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又由一系列制度化的机制来实现和保障。首先,民族国家确认民族的每个成员/国民都拥有作为人的权利,而这样的权利是平等的;其次,民族国家在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系列有利于民族的成员即国民行使权利的机制,并使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运行以此为基础;再次,民族国家通过体现平等、公正价值的制度安排,维护国民的权利。经由这样一套逐渐建立起来的完整的制度体系,民族国家实现了民族对国家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制度机制。
这样一套制度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应对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来的。首先,它将王朝国家末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构建的国家主权机制继承下来,并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完整的领土、主权制度,以保证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权利。其次,通过国内的一套权利机制,来维护和保障民族的成员即国民享有平等权利,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再次,通过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来组织国家政权、规范政府行为,实现了国家的制度化、政府的制式化、治理的法治化。总之,这样一套制度通过对民族成员即国民的权利的保障,实现了国民对本国领土、主权的认可和忠诚,把政治中的争斗纳入到制度规范的渠道之中,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使国家的组织方式、各种政治力量的争斗方式、外部的互动方式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使民族国家与以往的国家形态区别开来,实现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民族国家的构建,开启了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
作为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都是指向“国家”的。民族国家的所有制度安排的核心是对国民-公民的权利的保障。因此,公民权利成为了民族国家制度设置的基点和支点。民族国家以此来实现作为民族成员的公民与国家的一致和同一,保障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在此基点之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是有关于政党的、有关于政府组织和运行的。这样一套制度机制,并不排斥甚至保障由公民组成的政党之间的竞争或争斗。政党在为掌握政权、组织政府而努力的过程中,也相互竞争、争斗。但是,这些争斗只针对政府,而不针对国家本身。当然,政党、政权本身也有一个是否得到公民的认同的问题,即也有合法性问题。如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或政权可以更迭,但这并不影响国家的合法性,不涉及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不影响或危及国家的存续。
民族国家通过“认同”而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同一,从而也就把“认同”凸显为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环节。根据政治学家对“认同”的研究,“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民族国家内的居民对国家的一种心理取向,核心在于确认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同一性”。*政治认同的研究,首先是针对国家的,即国家认同。但随着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政府认同、政党认同、民族认同等问题也受到关注,并形成了相应的研究,进而产生了相关的概念、理论和逻辑。虽然,这些研究与国家认同的研究紧密相关,但又具有明显的区别,不能将它们混同和混淆。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具有根本的意义。国家构建的意义、国家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等,都与国家认同的状况直接相关。国家认同成为了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或者说,国家的合法性源于民族对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制度机制无疑具有巨大的优势,但也引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对于国家来说,当民众、国民认同它、接受它的时候,它就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有了存续的理由。国家也因此而稳定、巩固,或者说,具有稳定、巩固的基础;反之,国家存续的理由就会丧失,就会受到社会力量的冲击,招致各种形式的反对,从而使国家面临危机,甚至分崩离析。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的认同出现了问题,即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那么,影响国家存续的严重问题就会不断涌现。如果国家认同受到了挑战,国家认同下降到了一定的程度,国家就有解体或瓦解的危险。这样的情形表明,民族国家的头上总是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认同及其程度,就成为民族国家这种制度机制的要害所在,也可以是它的“命门”。
从亨廷顿在《我们是谁?》一书中的论述来看,“亨廷顿之忧”就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之上的。在亨廷顿看来,民族国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认同下降,从而使“国家特性面临挑战”,民族国家就具有解体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剑就会坠落。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之忧”抓住了民族国家的要害,直击民族国家的“命门”。
三、“多族化”为认同危机提供了温床
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机制。那么,为了协调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关系和实现民族与国家有机结合的民族国家体制,为什么会出现认同危机,并危及民族国家自身的统一和巩固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首先关注国家认同问题的政治学家,当数鲁恂·W.派伊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派伊在1966年出版的《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中就指出,政治发展会面临国家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在政治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六大危机中,“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危机是由认同感的获得引发的”,即国家认同危机。这是由于新兴的民族国家与传统的认同方式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在大多数新国家中,传统的认同方式都是从部族或种姓集团转到族群和语言集团的,而这种方式是与更大的国家认同感相抵触的。”*[美]鲁恂·W.派伊:《政治发展面面观》,任 晓,王 元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页。于是,便产生认同危机。
在阿尔蒙德看来:“对政治共同体的支持问题常常被称为‘国家的认同意识’问题。”在新兴国家中,“当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时,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就可能成为首要的问题,并造成重大的政治危机。于是,全国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即它能否名正言顺地使人们服从,就成为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主义运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页、第39页。阿尔蒙德用“集体忠诚冲突”*参见[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9页。来指称这种现象,算是点到了认同问题的要害。
派伊、阿尔蒙德所说的“新国家”或“新兴国家”,是那些第二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大都效仿西方的民族国家体制,努力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这也构成了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然而,这些向往民族国家制度的国家,却并不具备最早采取民族国家体制的那些国家的人口条件,国内存在着众多的族类群体,以及相应的准国家单位。它们是将不同的历史文化群体整合为一个整体——nation——而构建民族国家的。用阿尔蒙德的话来说,“新兴国家是从一些种族的、政治的和地域的准国家单位中产生的”。*[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8~39页。但是,这些国家将国内的多个族类群体整合为nation并促成了民族国家的构建以后,各个族类群体之间的差异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这些族类群体将会长期存在。这些国家的国族(nation)是一个具有复杂的结构的多元复合体,“多族化”成为此类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这些组成国族的族类群体,在有的国家被界定为“部族”,在有的国家被界定为“族群”,在有的国家则被界定为“民族”。由于国内存在着多个族类群体或民族,这些国家也常常被认定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人类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首先出现于欧洲,随后逐渐拓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在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形成以后,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构成单元。而多民族国家则是根据国家内的民族构成而确定的国家类型。由于依据的标准不同,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对子。尤其是中国,往往用“多民族国家”来指称这样的国家。
20世纪中叶,民族国家的“多族化”现象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常常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现象。但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样的现象也出现于西方国家,而且还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全球化的必然性的后果。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人口成规模地、频繁地、快速地在国家间移动成为了趋势。近年来中东的战乱,又进一步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在移民普遍化、规模化的条件下,曾经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大量增加,那些人口曾经单一或均质化程度很高的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大批来自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口。目前,这样的现象还呈增强之势。西方国家的移民在规模增大尤其是族裔增多以后,以各自母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来维系情感的需求随之上升,以此来加强相互间的联系从而去争取更多的利益也成为有效的手段而常常被使用。“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41页。总之,“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王希恩:《全球化中的民族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于是,西方国家便出现了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群体现象——“聚众成族”。在此情况下,西方那些原生型的民族国家的“多族化”就逐渐形成并日渐突出。
在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问题与“多族化”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相关。派伊、阿尔蒙德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就是在“多族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是“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之间的冲突”。而欧美国家的认同危机,更是“多族化”的直接政治后果。美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具有突出的文化多样性。但是,美国并没有把国内的族类群体界定为民族,拒绝承认各种族类群体的集体权利,“只有在‘美国公民’的身份下才可以拥有政治权利,任何族群不得以族群身份享受独有的政治权利”。这就“成功地回避了对‘国家’(nation)以外的任何‘民族’的认可”,“所以在美国,只有种族问题和‘族裔’(ethnic)问题,以及相应的族裔政策,而没有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任一鸣:《美国和前苏联民族政策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国际观察》2013年第2期。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核心的美国主流文化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其他文化背景的人移入美国后都融入了美利坚民族。因此,“在美国通常只承认有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层面上的美利坚民族,而将其内部的各次级群体称为ethnic group,即族群。”*蒋立松:《略论“族群”概念的西方文化背景》,《黑龙江民族丛刊》2002年第1期。美国也因此而被誉为“民族的熔炉”。但是,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加和“聚众成族”现象日益普遍,“多族化”现象日渐凸显并逐渐瓦解了“民族熔炉”,导致了美国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问题。在此过程中,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的目的是族裔文化的保留和发展,以此来获得少数民族族裔(也包括法裔居民)对国家的认同”,*洪 霞:《加拿大多元文化与威尔·金里卡的民族国家构建思想》,《英国研究》(第1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但结果并不理想。早在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时候,亨廷顿就指出:“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 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页。“多族化”基础上形成的多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对国家认同形成侵蚀和解体性影响。
民族国家以一个统一的国族为主体和支撑。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都是建立在维护民族的成员即国民的权利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多族化”,意味着一个国家内存在着多个活跃的族群或民族,国族的同质性被差异性所取代。因此,随着“多民族”的巩固和凸显,民族国家内国民所属的族群或民族的意义也逐渐突出起来。而国民间群体或民族差异的突出,又进一步激发起族群或民族的利益诉求,以及相关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生成——多元文化主义、差异政治理论等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甚至还会导致维护族群或民族利益的集体行动。而各种巩固族群或民族意识,要求维护族群或民族利益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国民的群体差异性。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长期以来屡试不爽的维护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国家——的机制就被从根本上动摇了,功能也随之弱化。随着这些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就会削弱和流失。事实就是这样,“政治认同并不是固定的……相反,它们具有高度的可变性和社会建构性。”*[英]胡安·J.林茨等:《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孙 龙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6页。一旦有导致民族或族群自我意识激升的事件出现,某个或某些民族或族群的国家认同就可能整体崩塌,国家认同危机形成的风险就陡然增加,甚至直接导致国家认同危机。而民族国家内不认同国家的群体或集团,往往就会成为一种难以驯服的力量,会不时掀起冲击现代国家体系的分裂行动。
在“多族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是否出现认同危机,以及认同危机所能达到的程度,与各个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直接相关。民族国家内的族群意识或民族意识的表现多种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相对他者而“自觉为我”*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的梁启超,就曾将民族意识的内涵界定为:对他自觉为我。《梁任公近著》(第1辑)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43页。的意识。一个民族国家内的各个族群或民族的自我意识愈强,为本族群或民族争取权利的冲动也会走强,形成“集体忠诚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因此而增大。如果民族国家内某些民族或族群的人们,虽然生活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却不把该国当作自己的国家,民族国家维持国家认同的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在族群或民族意识走强的过程中,各种为各个族群或民族争取权利的理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在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就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亨廷顿就明确指出:“多文化论和多样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出现,损害了美国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尚存的中心内容,即文化核心和‘美国信念’的合法地位”,进而使美国面临解体的威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 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第16页。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具有潜在分裂作用”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使多民族的美国巴尔干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就有面临解体的危险”。*[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25页、第118页、第126页。
民族国家越来越普遍的“多族化”,为国家认同问题或国家认同危机的萌生提供了土壤。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形成和广泛化,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机会就大大增加,并对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民族国家如若不能有效应对这样的挑战,任由各种有可能促成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的因素自由生长,各种割断悬挂达摩克利斯之剑细绳的力量也会越来越强,民族国家就面临着解体的危机。这正是亨廷顿所忧虑的。
四、苏联解体触发了“亨廷顿的忧虑”
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重大事件。一个庞大的国家,顷刻间瓦解、灰飞烟灭。如此一个重大事件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民族因素无疑十分重要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签署最后一道总统令——辞去苏联总统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职务,将武装部队和“核按钮”的控制权移交给叶利钦——的讲话,也点明了这一点。他说:“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共和国拥有主权;同时主张保留联盟国家,保持国家的完整性。但是,事态却是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的,肢解和分裂国家的方针占了上风” 。真正造成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是在“多族化”基础上生长起来并无法摆脱的国家认同危机。这样的国家认同危机在特定的条件下爆发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因此而坠落,摧毁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把民族国家的认同问题以一种十分粗暴的方式凸显出来了。
俄国十月革命推翻的沙皇俄国,在以军事征服进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把数量众多的族类群体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但并没有将其当作“民族”来看待。它们是“具有自己语言文化和自治传统的少数族群”,却“具有反抗沙皇政府压迫和恢复独立的愿望”。*马 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革命党便以此为突破口而对其进行政治动员:“承认具有自己语言文化和自治传统的少数族群为现代政治意义的‘民族’(nation,nationality)并允诺中央政权被推翻后这些少数族群享有‘独立’或‘自治’权利。”*马 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布尔什维克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列宁、斯大林为了发动沙皇统治下的各少数族群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宣布他们都是‘民族’并应当享有‘民族自决权’,可以自由地脱离俄国并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由于如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各地以‘民族’为单元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自治政府’就如雨后春笋那样遍地出现。新生的布尔什维克中央政府没有力量在军事上进行镇压,而只能与它们妥协,在政权建构上给予各‘民族’很大的权力”。*马 戎:《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读萨尼教授(Ronald G.Suny)的〈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因此,苏俄在建立伊始,便面临着一个“多族化”的现实,成为了“多民族国家”。这也成为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为“集体忠诚的冲突”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在承认各个历史文化群体的民族地位的基础上,列宁“不顾卢森堡、布哈林等人的反对,坚决主张俄国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原则。列宁明确表示:“‘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9页。民族自决权原则赋予了各个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从而把民族国家内各个民族群体的政治自主权和独立性推到了极致。民族国家的“多族化”问题也因此而走向了极端,为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巩固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为苏联的解体埋下祸根——最早脱离联盟的加盟共和国就是援引民族自治权的理论和原则来表达分离的政治诉求的。*对苏联解体有过专门研究的左凤荣就指出:“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那么就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它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苏联宪法。戈尔巴乔夫也不敢放弃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发展之时,他强调的仍是要遵循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原则,这当然无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1922年成立的苏联,创造了“一种多民族成分的民族国家的国际联盟”*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载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然而,该联盟仍然以一个国家的形态出现,“在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国家”。*郝时远:《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载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这个特殊的民族国家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中,又建立了按民族划分的行政单位和行政实体,最终建立了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这样的做法再辅之以强制性的民族迁徙,就基本上实现了各个民族与地域的统一。此外,1924年、1936年、1977年宪法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如此等等,就构建起了一种“具有苏联特色”的“多族化”制度体制。因此,苏联自建立之日起就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困境”——既想要按照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来组织国家,又面临着“多族化”的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复杂的族际关系和族际矛盾。
苏联“多族化”的制度体制,为基于“多族化”而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因素的形成和强化提供了温床。但是,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又不容许这些因素自由生长。为了消除对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形成侵蚀和解构的因素,实现对局面的有效控制,苏联采取了多种严厉和有效的措施。
首先,也是最重要和最为有效的是,虽然采取了联邦制的国家形式,却在事实上实行了单一制。在涉及国家权力总体分配的国家体制问题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随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然而,虽然“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没有具体细则,苏共实际上只是做做样子,本没打算实行”。*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其次,对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自治区等加强控制。“苏维埃联盟能够维系70年,依靠的主要手段是苏联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即强大的行政命令体制。苏共并没有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经济空间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对于那些试图挑战这种控制的民族及其精英,一概采取强制措施,一是进行政治清洗,一是实施强制性的民族迁徙。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以叛国罪和国家安全为由把11个少数民族强行迁往异地他乡,不分男女老少,还是党员干部,一律分散居住,强行管制。”*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最后,在硬性政治控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情况下,苏联开始构建统一的国族——“苏联人民”。1936年苏共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便否认国内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朝着构建统一国族的方向发力。20世纪60年代,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就宣布:“在苏联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即苏联人民。”*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但是,苏联的国族构建并不成功。“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直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消除民族差别,构建单一化的‘苏联民族’实践一直在进行,只是这个‘苏联民族’的内涵是‘俄罗斯化’而已。”*郝时远:《苏联多民族国家模式中的国家与民族》,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3页。
按民族划分区域并实行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以“俄罗斯化”为特征的国族构建的失败,反过来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首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才是苏联人。在此情况下,政治控制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性的和唯一的手段。在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内,这样的手段固然是强大、有力和有效的,但过于单一且缺乏弹性和韧性,当然也没有替代性。这样的手段一旦失效,严重的后果就难以避免。
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为此严重后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戈尔巴乔夫1985年担任苏共总书记后,摈弃斯大林主义政治体制的遗产,试图建立所谓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从根本上触动了长期形成并行之有效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和控制。党内的权力斗争,又给中央的集权体制以沉重的打击,使形势雪上加霜。在此条件下,压抑已久、酝酿已久的民族力量终于等来了喷发的突破口。“这一政治体制改革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剪断了维系苏联存在的最后纽带,中央权威下降,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展。在选举的气氛下,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为了自己在本共和国的威信,大力向中央争主权,认同本民族的民族主义。”“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于是,“随着改革的开展,在公开性、民主化等口号的推动下,引发了原先潜藏着的民族矛盾和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演变成为一股要求民族分立的浪潮”。*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96页。最终,“随着苏共的削弱和解散,不再有对民族分离主义施加威慑的力量,联盟中央被架空,联盟国家便走向了解体”*左凤荣:《民族政策与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民族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轰然坠落。
苏联从建立到解体的过程,把民族国家从“多族化”到国家认同危机,再到国家认同危机爆发最终导致民族国家解体的逻辑,完整地演绎了一遍。“苏联不复存在了”的事实,引起了亨廷顿高度的警觉,进而发出了“亨廷顿之忧”。
五、中国该如何对待亨廷顿发出的警示
在“亨廷顿之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之时,中国对此问题的反应却显得迟疑和犹豫,并且意见还不统一。虽然有不少学者在苏联解体后对我国的民族问题的治理进行了反思,在亨廷顿发出警示后,对中国族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忧心忡忡,但很多人却不以为然,抱持“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态度。他们不仅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因民族问题而导致的认同危机,而且还努力传播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和价值,提出了以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的多种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甚至把蕴涵个别民族利益诉求的观点意识形态化,并以激昂的情绪加以传播。
可是,在此问题上的“驼鸟心态”并不符合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逻辑,也不符合民族国家认同危机生成的现实逻辑。中国自秦统一后,王朝国家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这是一种以王朝及王朝的统治为核心或基本形式的国家政治体系。文化或文明成为将王朝统治下的人口联结为统一的共同体的基本力量。因此,中国的传统国家形态常常被称为“文化国家”或“文明国家”。王朝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周边的政权产生了极大影响,其他族类群体建立的政权往往以内附、归附、依附等方式而融入其中。因此,王朝国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众多的族类群体。但是,这些族类群体既没有民族的称谓,也没有凝聚为完整的整体,更没有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享有集体权利。只是在“民族”概念于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后,尤其是在此后的民族构建中,这些群体才被构建成为民族。*关于中国20世纪的民族构建问题,可参阅笔者的《中国民族构建的二重结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
辛亥革命推翻最后一个王朝之后,古老的中国开启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此过程中,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被构建了起来,并对中国的民族国家制度体制形成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这一进程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这是一种与王朝国家具有本质区别并取代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中华民族国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已经由传统的文化或文明型国家转变为现代政治国家,是国家形态的巨大转型。当然,政治中国取代文化中国后,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中华民族国家以中华民族的构建为基础。但是,中国的民族构建是二重性的。在中华民族构建的同时,以众多少数民族的构建为基本内涵的“各民族”的构建也随之推进——苏俄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对此发挥了重要影响。因此,中华民族国家构建完成以后,作为国族支撑着国家的中华民族,就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中华民族不是直接由公民构成的民族,而是由多个民族群体构成的民族,是“民族的民族”。*参见笔者的《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2015年第4期。而且,中国存在着多个民族的事实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国家因此而被界定为“多民族国家”。如此一种突出的“多族化”的现实和倾向,为国家认同问题的酝酿和萌生提供了土壤和温床。
诚然,国家认同问题并没有立即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族际关系得到了很好的调整,族际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少。这样的状况与两个方面的事实直接相关:一是“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关于中国民族政策的“民族主义”取向,可参阅笔者的《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少数民族的感恩和回报心态抑制了民族意识的增长;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政策,以及体现这种思想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延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任何主张少数民族民族意识的思想和行动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但是,此种情形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发生了改变。逐渐恢复和落实的民族政策,在给少数民族带来了多项实实在在利益的同时,也激发起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以“利益给予”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其政策红利的形成与政策受益者的感恩和回报心态直接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政策的受益者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感恩的心情会渐次减弱并最终消失,政策的红利也会逐步消失。不仅如此,如果原来的政策激起了受益者对政策的强烈期待的话,还会导致“狄德罗效应”,*狄德罗效应是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发现的。其基本的涵义是,一个人在没有得到某种东西时心里是很平稳的,而一旦得到了却又想要更多。此种现象十分常见也十分普遍。这样一种“愈得愈不足效应”,就被称为“狄德罗效应”。进而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产生催化作用。事实上,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和趋于旺盛,已成为现代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的意识却逐渐淡漠,从而导致了中华民族的虚拟化。为了维护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国家的国族——中华民族——的巩固,对中国的民族和民族问题有着十分深刻和透彻了解的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命题,通过肯定各民族的“多元”存在而肯定中华民族的“一体”,从而再次凸显了中华民族。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命题是在香港提出后才“出口转内销”的。
在“多族化”基础上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认同”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近年来,强调“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以及族性张扬的观点逐渐增多,并日益意识形态化。各种体现少数民族权利要求的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否定中华民族的观点也一再出现并日渐走强。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可参阅笔者的《中华民族: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4期。直接支撑着中华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对中华民族采取不承认和否定的态度,本身就是国家认同出现问题的一种表现。这表明中国的国家认同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时代,支撑各个族类群体特殊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性或分殊性显而易见,这样的差异也屡屡被当作把各个族类群体界定为“民族”的“事实依据”。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代化快速推进,不仅对传统社会形成解体,而且推动着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迅速地转型。于是,那些使各种族类群体成为“民族”的事实依据正在快速地改变并日渐式微,各个“民族”间的统一性则日渐增多和突出,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快速地推进。在这样的条件下,维护各个民族特殊利益的要求,更多是民族意识走强的表现,甚至就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委婉表达。
现实的情况表明,今天中国的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状况,以及在民族意识引导下的争取自身权利的实际行动等,与“亨廷顿之忧”中所料的那些削弱国家认同的情形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事实上,通过否定中华民族的存在的方式,曲折反映出来的国家认同的下降已经出现并且仍在走强。固然,今天中国的国家认同问题表现得并不突出和尖锐,族际关系中的矛盾处于可控的范围,族际关系总体良好,但“亨廷顿之忧”中所分析的那些现象也在不断增多,民族国家具有朝着亨廷顿警示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在此问题上闭目塞听并自我陶醉,必须高度重视“亨廷顿之忧”发出的警示!
中国是时候采取必要措施来巩固国家认同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探索巩固国家认同的有效措施,应该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中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这并不是出于审慎的未雨绸缪,更不是杞人忧天。试想一下,在苏联解体之前,谁会预料到如此强大的国家会出现这样的悲剧性后果呢?在亨廷顿把美国面临解体的危险陡然凸显在世人面临之前,谁又会对如此强大的国家产生可能解体的怀疑呢?“历史是充满意外的”。*[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页。当前中国在族际关系上的各种表现已经表明,亨廷顿发出的警示并非与中国无关。在可能萌生国家认同危机的因素业已存在并渐显凸显的条件下,采取有效措施来巩固国家认同的基础,才能防止民族国家滑向危险的边缘!
中国为了应对“多族化”基础上形成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但是,该政策体系的政治标的中,并没有包含以增强国家认同来支撑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的内涵。从“亨廷顿之忧”所发出的警示来看,相关政策必须更有整体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要把巩固和提升国家认同纳入相关政策的政治标的之中,才能有效地应对中国可能出现的问题。发出警示的亨廷顿本人,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是加强国家认同构建,筑牢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亨廷顿分析了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以后,指出:应对的“办法就是重新振作国民身份和国家特性意识,振奋国家的目标感,以及国民共有的文化价值观”([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1页),其中最为根本的是,重塑同质性的“核心文化”(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经历了苏联的解体的季什科夫,*瓦·阿·季什科夫(1941-),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苏联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美洲研究室主任,1992年应叶利钦总统之邀而担任俄罗斯民族事务部第一任部长,现任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季什科夫在总结苏联解体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认识:“在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里,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宣传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珍惜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В.А.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2页)。这种具有突出的殊途同归意味的结论,点明了“亨廷顿之忧”的破局之钥之所在。这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的经验和借鉴。今天,中国的国家决策层也十分强调国家认同。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华民族思想,以及随后提出的“五个认同”,*2015年8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其基本的指向都是强调国家认同,或通过中华民族认同来增加国家认同。这为中国国家认同的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引。据此对相关政策进行校准和重塑,应该是我国民族政策建设的圭臬。
六、几点启示
在写作《我们是谁?》时,亨廷顿并不讳言,自己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的。虽然他在分析和论述问题时总是难掩饱满的热情,但他“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前言。以便得出理性的结论。作为一名功力深厚并提出影响当今时代的诸多命题的政治学大家,他对美国会否分裂的忧虑,并不是某种情绪的宣泄,更非杞人之忧,而是“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后得出的理性的结论——揭示了民族国家的“多族化”现象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危机与民族国家体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后得出的结论。当然,这是一种民族国家运行过程中蕴涵着的本质联系,将其从各种具体现象的掩盖下揭示出来,就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
“亨廷顿之忧”唤起了对民族国家制度机制的关注。民族国家出现至今已近4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迅速遍及全球并促成了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完善也过去半个世纪了。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以及整个世界的民族国家化,使世人对民族国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民族国家不过是国家形态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民族与国家相结合的国家形态。这样的结合是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机制来实现和维系的。民族国家通过完整的制度机制的构建,实现了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但是,民族国家并非一成不变,而且不是国家的终极形态。一旦保障公民认同国家的机制遭到破坏,民族国家出现认同危机,民族国家就难以避免解体的厄运。
早先民族国家的人口都是均质化的。均质化的人口构成的“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结合在一起,才形成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普及和发展,“多族化”现象不可避免。因此,最早民族国家结构中那种“一”和“一”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具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多”的内涵。正是这样一种与国家结合的“民族”内的多样性的文化和群体现象,对民族国家制度体系中实现和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机制形成了侵蚀,进而影响到民族国家赖以存在的国家认同。在这样的条件下,若要在国族构成多样化的基础上维持和巩固国家认同,就必须在多样性的群体中构建和增强共同性,使国家保持强大的同化能力。建立强大的国族文化,尤其是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是达此目标的不二之选。
民族国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制度机制,这些机制在发展中日渐复杂。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国家如果由于认同危机而解体,那些完善的制度机制也将随之毁灭。政治共同体是国家制度机制的基础。因此,国家问题研究在关注或聚焦制度机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或忽略民族国家的其他属性和侧面。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实体,既有政治形式的属性,也有政治共同体的属性和政治地理空间单位的属性;既是政治形式,也是政治共同体,还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是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国家问题研究在关注某一方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方面,否则,就无法在所关注的那个方面的研究中得出合理的结论。
(责任编辑 张 健)
“Huntington’s Worry” Sounded a Stern Warning
ZHOU Ping
In his last workWho Are We? ,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saw the Soviet Union in disintegration and Britain in danger of falling apart. He could not help showing deep concern about whether the same thing would hap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its special connotations, Hungtington’s worry gets to the core of the nation-state as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to guarantee national identity, i.e. the legitimacy of a nation-state is fundamentally derived from the people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tate. His worry thus has issued a strong warning to nation-states.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to guarante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nation-state, may lead to problem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and even cause the crisis of national identity because of the multi-ethnic problem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state. It is the multi-ethnic phenomenon that has eroded those longstanding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the realiz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has become the hotbed of identity crisis. How the Soviet Union went from establishment to disintegration has fully illustrated the problems about national identity caused by multi nationalities. The logic that serious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split of the country has thus triggered “Huntington’s Worry”. As a nation state, China has to face this reality, too. Only by integrating the objectives of strengthening national identity into the political goals of the national policies and correspondingly adjusting and reshaping the relevant policies can we free ourselves from “Huntington’s Worry”.
Huntington’s Worry, national identity, multi-ethnic, identity crisis, state disintegration
周 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
D08
:A
:1001-778X(2017)05-00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