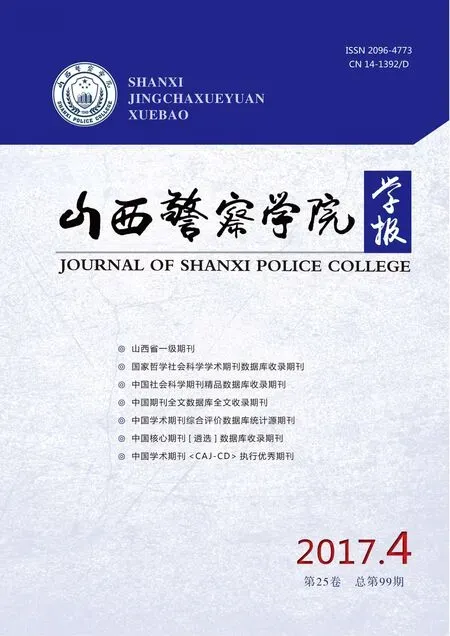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从实体角度出发
2017-04-11张雪丹
□张雪丹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法学研究】
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从实体角度出发
□张雪丹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我国现行法律中针对行政追偿制度的相关规定近乎空白,使行政追偿在实务中几乎不具有可操造作性,严重制约了追偿制度作用的发挥,这也导致构建该制度的目的无法实现。实体问题是一个制度的根基,因此以追偿金额、追偿主体、追偿条件等几个实体问题为出发点来探讨行政追偿制度的完善就十分必要。
行政追偿;追偿金额;追偿主体;追偿主观条件
2016年,政府信息公开了一起吉林省四平监狱违法不作为的国家赔偿案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热议,学界也由此针对行政追偿制度再一次掀起了热烈的讨论。简要案情:赔偿请求人滕德刚因犯盗窃、抢劫罪于1996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在四平监狱服刑,在服刑过程当中,因与其他三名服刑人员发生冲突而将该三人殴打致重伤,案件移交至法院后,滕德刚起诉监狱违法不作为,要求予以国家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四平监狱劳动现场存在安全问题,监狱干警监管措施不到位,故根据本案具体情况,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确定由四平监狱承担30%的监管不作为责任,决定由四平监狱向赔偿请求人滕德刚支付国家赔偿款总计人民币136519.11元。
对于以上案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国家赔偿之后的行政追偿问题,也即:监狱在对赔偿请求人予以国家赔偿之后是否应向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如果进行追偿,又应当以谁为主体并且用何种标准来实施?
事实上,早在1994年公布实施的《国家赔偿法》中就已经规定了追偿制度,并且在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也保留了追偿制度的存在,该法第16条中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然而,除此以外,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追偿制度的标准、程序、执行等具体规定几乎为零,使该制度在实务中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导致追偿机关对于“追偿权”的行使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不用”,要么“过度滥用”。[1]
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目前从实体角度上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大方面的问题:
一、追偿金额标准参差不齐
追偿金额标准作为行政追偿制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追偿制度能否具有实际意义。而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统一的标准,而是将进一步细化标准的权力授权给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因而从实质意义上来讲,我国的追偿金额标准实行的是“地方”标准而非国家标准。这就会产生各地标准参差不齐的问题,导致各地所计算出的追偿金额差异悬殊的结果。以对重大过失追偿的最低数额为例,除未规定最低数额的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浙江省外,山西省的最低数额为 894元,甘肃省的最低数额为900元,内蒙古自治区的最低数额为940元,青海省的最低数额为1280元;但是,重庆市的最低数额则为6000元,安徽省为10581元,黑龙江省更是高达15000。[2]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就行政追偿金额设立统一的国家标准,取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细化标准权力的授权,真正实现公正公平原则。
总结其他国家针对追偿金额标准的立法经验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在立法中规定的追偿标准都是非常低的,*捷克赔偿法律规定: “除非劳动法有特别规定,除非过错系被追偿人故意,国家求偿额原则上不超过已赔偿额的六分之一,以 1000 克郎为最高额”; 俄罗斯联邦国家赔偿立法规定 “致害公务员赔偿数额不得超过其月工资的三分之一,法院确定其违法后,责成其交付该损害赔偿诉讼的诉讼费”; 加拿大赔偿立法规定 “公务员所承担的赔偿费用不能超过 250 加元”。也就是说追偿金额并不完全与国家赔偿相对应。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因为设置行政追偿制度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对公务人员进行警示和惩罚,并且对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导致国家赔偿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惩罚,如果惩罚力度过大,则会给被追偿人员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难免会使其他公务人员为了防止启动追偿制度,而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畏首畏尾、该处罚的不处罚,从全局上来看这反而不利于依法行政的实现。当然,追偿金额的标准也不能完全不设置下限,否则就无法起到其应有的惩罚作用。而究竟该如何设立具体的追偿标准?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金的确定均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国家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也以国家公布的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础来确定行政追偿金额。举例来讲,浙江省在其2017年3月1日新实施的《浙江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即采用了此种标准,该《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的追偿比例根据违法性质、损害后果以及被追偿人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追偿金额最高不超过国家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倍。作出追偿决定时国家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尚未公布的,以已公布的最近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准。
建议追偿标准的如此设立有两大方面的原因:
1.从法律制度层面上来看,追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制度其中的一部分,理论上对追偿金额的计算应当与国家赔偿金的计算基准保持一致性,否则赔偿金采用一种计算标准,而之后的追偿金却又采用另一种计算标准,这既会导致在同一法律制度内出现矛盾,也会增加追偿在实务中操作的难度。
2.从具体操作层面上看,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础更具有科学性。以往在实践中,赔偿义务机关通常是根据相关公务人员应承担的过错程度,在1%~100%之间去决定一个比例作为追偿比例,再以赔偿总额乘以追偿比例,计算得出被追偿人员应该承担的被追偿金额。例如,《四川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实施办法》(1999年公布)第14条中规定:因故意行为造成国家赔偿,国家赔偿费用在2万元以下的,应向责任者追偿20%以上直至全部国家赔偿费用;国家赔偿费用在2万元以上的,应向责任者追偿10%以上(不少于4000元)直至全部国家赔偿费用。*《四川省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实施办法》在1999年2月7日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布。这样的规定虽然能使追偿金额的计算标准具体化,但是如前所述,我国地方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样极易发生同案不同果的情况,有违公平正义的法律基本原则。
而由法律统一规定以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基础确定追偿金额,则会在最大限度上避免这个问题出现。看似这种追偿标准并未考虑到我国各地贫富不均的国情,其实恰恰相反:在国家赔偿金和追偿金额采用统一计算基准的前提下对于同一起国家赔偿案件,在平均工资较高的地区支付的赔偿金较高,由此而产生的追偿金额也会相应的高,反之追偿金额也会相应地较低。如此一来,追偿数额的确定一方面与赔偿金的数额保持了比例上的一致,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实现了追偿制度的惩戒作用;另一方面也不会使被追偿人背负过大的经济压力。
除此以外,还应当明确追偿金的支付方式。由于被追偿人的薪资收入具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对于追偿金的赔付既可以允许其一次性支付,也应当允许其分期支付,并且不应当因延期支付赔偿金而增加利息。同时,在确定被追偿人每月的支付数额时,应充分考虑到其收入水平和家庭情况,在为其保留必要的基本生活费用后,再确定出具体的月扣除额。
二、追偿主体不明确
《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粗略地规定了由侵权主体作为追偿主体,但是在实务中案件情况纷繁复杂,仅对追偿主体做如此概括性的规定,是造成追偿制度“启动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学界中对于追偿主体的确立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家赔偿费用一般都是由各级财政部门列支,因此理应由其作为追偿主体。赔偿义务主体在向财政部门提交支付赔偿申请的同时,也需要提交包括是否应向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追偿、追偿数额为多少的申请,并由财政部门一同审核。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由人民法院作为追偿主体。第三种观点主张可以设立专门的国家赔偿保险机制,其运作结构类似于现有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性待遇,由国家和公务人员各自承担一部分的投保比例,在发生国家赔偿事由时,由国家赔偿保险机制进行赔付,其中超出投保金额部分由该保险机制进行追偿。
但是,上述三种对追偿主体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首先,将人民法院设定为行政追偿主体会打破我国现在国家权力分配之间的平衡。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的目的之一在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并且在行政机关的不当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损害时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变更或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即人民法院的司法权与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界限。而行政追偿权属于行政权,如果再由人民法院作为追偿主体,会使人民法院同时具有了司法权与行政权。这样一来,人民法院既是行为者,又是行为的审判者,公平正义的法律基本原则该如何实现?其次,以国家财政部门为追偿主体虽然可以避免权力重叠的问题,并且实现追偿主体统一化,但是又会产生新的难题。我国的行政服务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由此而设立的行政部门也是数量繁多,例如教育部门、交通部门、食品部门等。不同的行政部门所要求公务人员具备的知识领域和专业技能之间的区别千差万别,但是并不能保证国家赔偿只会发生在那固定的一个或者几个行政领域当中。如果真的以财政部门为统一的追偿主体,这就要求财政部门中必须具有来自每个领域
的专业人才,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由缺乏专业人才的财政部门作为行政追偿主体就难以保证追偿制度的效率以及公正性的实现;同理,设立保险机制作为追偿主体也同样缺少上述的“专业人员”。除此以外,新制度的实施往往都伴随着失败的风险,而设立并在全国推广和适用一个全新的保险机制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巨大的消耗,一旦推行失败将造成不可估计的社会损失,进而影响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该设想也缺乏实际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在设立追偿主体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我国当下还并不具备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条件,而是需要根据实践经验,在现有法律规定由侵权主体作为追偿主体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地细化,在此仅举出几个较少被关注的内容作为例子来阐明观点,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对此问题的重视:
1.《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2款规定: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义务机关。那么其中一个行政机关在先行赔偿后,是向其他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追偿还是向该机关工作人员直接追偿?对此《国家赔偿法》中并没有规定。[3]
2.《国家赔偿法》第8条规定,经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也即复议机关只有在加重赔偿的情况下才成为赔偿义务机关。但是《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中,*《行政诉讼法》第26条第2款:经复议的案件,故意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却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对原行政决定无论是改变还是维持,都有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风险,这其实是增强了对复议机关的监督,使复议机关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其作出的每一次复议决定,从而减少行政权力滥用的几率。如果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这一立法精神对在该种情况下的追偿主体进行设立,复议机关维持或者部分减轻原决定,就表明该机关对原决定内容的全部认可或者部分认可,那么由此而造成的国家赔偿,复议机关也应当在其认可的范围内作为共同赔偿义务主体。这么一对比就可以发现,《国家赔偿法》第8条与《行政诉讼法》第26条之间所追求的目的是相矛盾的。
3.在1990年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国务院在1995年制定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都有过以下规定:行政机关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作为追偿对象,其追偿主体是该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责令有责任的行政机关支付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财政机关审核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的申请时,发现该赔偿义务机关因故意或者有重大过失造成国家赔偿的,或者超出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赔偿的,可以提请本级政府责令该赔偿义务机关自行承担部分或者全部国家赔偿费用。也就是说如果是由于行政机关自身而非其工作人员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了国家赔偿(例如:对赔偿数额计算错误、对不该赔偿的对象进行赔偿等),也应当依法对该机关进行追偿。但是《行政诉讼法》在2012年的修改中删除了这一内容,而目前《办法》中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中,也未见该项规定。这无疑是法律制度的一种退步,因为我国的行政机关除了代表国家为公众提供服务之外,还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由于行政机关自身原因而并非其公务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的国家赔偿时,如果因为行政机关的特殊身份就免除其赔偿责任,而统统由国家为其“买单”,这既是对行政机关的一种纵容,也会损害纳税人的利益。
三、追偿主观条件界定模糊
《国家赔偿法》第16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该条明确了行政追偿的主观条件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实际上也间接指明了并非所有由公务人员造成的国家赔偿都属于被追偿的范围之内,例如因公务人员的“一般过错”、情势变更、意外等。之所以法律对公务员因一般过失而造成的国家赔偿进行免责,是因为公权力的行使在实践当中往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是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的,这就意味着公权力行使的本身就存在着可能会导致侵害结果产生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苛求公务人员不犯一点错误是几乎不可能的,即便确实实现“零错误率”的目标,也可能会由于过度注重行政结果而忽略了对行政效率的要求。但是,也不能对这种致害风险全无管控,否则会造成另一个极端的后果,即助长越权、不作为、权力滥用等不良之风。但是除了该条概括性的规定之外,立法上对怎样认定何时为“故意”、何时为“重大过失”则并无进一步的解释,这就大大增加了追偿制度在实践中运用的复杂程度。其中,对于“故意”的认定相对较简单,可以借鉴刑法学中的概念对其进行把握和适用,而真正的难点就在于该如何对“重大过失”这一概念进行界定。
学界对于什么叫“重大过失”尚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重大过失就是一般人都能注意到并能避免发生的事情,但是行为人却没有注意到,也没能防止发生。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重大过失是指行政人员不但没有达到其职务所要求的特别标准,连一般人所应有的一般标准都没有达到。第三种观点认为重大过失是指一个行为极其明显的不合法律要求并有损于他人,即使是一个疏忽之人都能够加以避免,但是行政公务人员却未能避免。第四种观点认为,所谓重大过失是指显然欠缺普通人应有的注意而产生的过失和已经预见但轻率地认为能够避免而产生的过失。[4]
实际上,这四种观点都是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来做比较,但是这样又会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该怎样定义一般过失的具体内容?两者之间的区别又在何处?由此可知以上四种对“重大过失”的分析从本质上来看其实都是以概念来解释另一个概念,而并不能起到真正解决问题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追偿中的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的认定,也应当借鉴刑法学中在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过失程度时所考虑的两大因素: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认识要素涉及的是有关责任人是否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意志要素涉及的是有关责任人对这种危害是否持反对态度。”[5]其中,意志要素的作用在于将故意和过失区分开来。因为在意志要素的内容中,故意是追求或放任其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过失则是反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在过失程度上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的区别就在于认识要素的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一般过失是指公务人员在意志要素上是反对这种危害结果实现的前提下,却因为疏忽大意、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受其认知水平所限而导致其行为有侵害性,即“无心之失”;而重大过失则要求行为人已经意识到其行为具有危害性,属于“有心之失”。因而,要认定构成重大过失,就必须要证明该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存在的危害风险具有认知性,同时也要保证该行为人在意志上并非是出于追求或者放任某种危害结果的产生而作出此种行为,否则行为人将构成故意而非重大过失。另一方面,行为人对自身行为在客观上的注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重大过失与一般过失。例如,在同样的情形下, 自身注意能力强的公务人员肯定比注意能力较弱的公务人员过失程度大;公务人员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概率越容易预见或者避免的,其过失程度也就越大;公务人员因有意识地违反法规范或者组织规定而产生的过失肯定比因无意识而产生的过失程度要大。
四、结束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国追偿制度在以上三大实体问题上的欠缺,导致了追偿制度也在程序上的缺失与空白,这将在根本上导致追偿制度的内容无法启动,使其成为“休眠条款”。因此,我国立法应当对追偿制度予以足够的重视,尽快通过立法等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规定,从而真正地发挥出行政追偿制度所应有的监督作用。
[1]郝登建,万 军.论行政追偿执行难的原因及解决途径[J].法制在线,2009(4):12.
[2]谢祥为,叶 雨.国家追偿标准研究:以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规定为分析对象[J].江西社会科学,2006(12):165.
[3]武兴宽.行政追偿制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3:23.
[4]江必新,梁凤云,粱 清.国家责任与国家赔偿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678.
[5]吴光升.论国家赔偿费用追偿程序之完善[J].政法与法律,2014(3):94.
(责任编辑:申 巍)
TheMissingandImprovementofChineseAdministrativeCompensationSystem——In view of entity
ZHANG Xue-dan
(SchoolofLaw,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China)
There is almost blank provision about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our present laws, which makes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not to be operated in practice, severely restricts the playing of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causes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this system not to be realized. Entity is the base of a system, so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impr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system starting from compensation amounts, compensation subject and compensation conditions.
administrative compensation; compensation amounts; compensation subject; compensation subjective conditions
2017-05-25
张雪丹(1993-),女,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
DF74
A
1671-685X(2017)04-007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