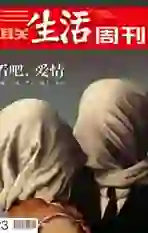荷兰,在自然中精雕细刻的人造风景
2017-04-11张海律
张海律
荷兰是一个几乎就没有自然风景却非常漂亮的智慧国家,它的精致,完全源自生活在海平面之下的低地人民,是千年来与江河湖海搏斗、妥协并最终巧妙运用的战果。
翻越过被西风夹杂海水“洗剪吹”过后的大草坡,我置身于一片绵延25公里的沙滩。在深秋凛冽的冷风中,泰瑟尔岛(Texel)西岸小镇德科赫(DeKoog)上演着一年一度的迎冬风筝节。时间已近黄昏,乌云密布的天空预告着又一场暴雨,北侧的两条金鱼鼓圆惊恐的大眼睛,分离扒开云层、“游”向地面;西侧的两只安全套,已疲软地塌陷在沙土之中;更远处的蝙蝠、蜜蜂和风火轮等等一个个大风筝,都正被主人收线而归。它们造型古怪,却又不悬挂任何商业标志,纯属爱好者图个高兴找乐恶搞。暴雨倾盆而至,我骑着自行车狼狈逃窜,天空中唯一不愿下来的无脸摄魂怪,在背后阴魂不散地追赶。
这块从森林渐变到盐沼再归于海滩的泰瑟尔沙丘国家公园,被北海环抱,与欧陆隔着半小时船程,算得上是荷兰难得一见的“自然风景”。
在我看来,荷兰是一个几乎没有自然风景却非常漂亮的智慧国家。城市和乡村有着清晰的界限,大片农田和牧场连接着相距不远的城市,人工运河与高速公路一道组成国家笔直的动脉。乡村为城市提供农产品,让城市专注于工业和服务业。当游客面对沟渠交错的风车村、溪流蜿蜒的羊角村,赞美回归自然之乐趣时,可能不容易意识到,这番随手一拍就能在朋友圈引来无数点赞的美景,全是经年累月而来的人造风景。
1
我是逆着“二战”最后阶段纳粹的败退路线,乘火车从德国衰退的鲁尔工业区进入荷兰东部的阿纳姆。这是1944年9月盟军失败的“市场花园行动”主战场,城郊欧斯特贝克的空降博物馆前,有着一块1994年立下的纪念碑——“海尔德兰省的居民们:50年前,英国和波兰空降部队士兵在这里浴血奋战,以期打通进入德国的道路,让战争早日结束,同时也给你们的城市和生命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但你们却从未埋怨。”我从外到内漫步在这段胜利迟迟没有到来的悲痛历史中,心里却纳闷着,低地国家一马平川,没有任何起伏山峦,怎么就能让盟军在付出近2万人死伤代价下,仅正面推进了45公里昵?是住房、沟渠成为作战经验丰富的德军的有效屏障吗?还是一辆虎式坦克能抵得过十辆盟军谢尔曼?又据信是盟军情报里没留意到下游有一个可避开德军装甲师的渡口?
事后诸葛亮,是属于军迷的乐趣,我更迷恋于馆里展出的那些还未被影视文学改编的故事。“市场花园行动”时,男孩鲍勃正好15岁,战火让他兴奋极了,大胆地从双方阵地的死人身上搜刮各种军装和武器,来年7月搬到鹿特丹后,有了丰富军品收藏的他,热衷于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着残酷的Cosplay游戏。另一则是爱情故事。1942年,两个16岁的波兰孩子约瑟夫(Josef)和伊米莉亚(Emilia)相遇了,他们与14万波兰人一道,被苏联红军抓去了西伯利亚,在那儿走散。后来逃到英格兰的约瑟夫在一份难民名单上看到身在德黑兰的伊米莉亚的名字,就立刻写信过去。这封信在炮火中折腾了一年才到达伊朗,几经周折,伊米莉亚也去到了英国,两人相爱了。加入波兰第一旅的约瑟夫,参与了“市场花园行动”的空降任务,两人再次失联。不过一年后,他们又一次意外重逢,随即决定马上结婚,如今还健康地生活在英格兰中部城市布拉德福德。
坦克装甲集群碾压过的土地,而今早已重新变回肥沃农田及在其间阡陌交通的沟渠水道。从抽水造田开始,荷兰人便同时挖掘运河,既作为灌溉排水工具,又发展成旅游名胜。在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莱顿这些或商或学的重要城市中,运河更兼具运输和防御的重要用途。而到了真正乡间,河道、小舟、鲜花、木屋、拱桥、绿草、家禽、炊烟,就一道组成游人最神往的田园牧歌画卷。
2
这其中,最为漂亮,以至于几乎沦为中国同胞又一个海外旅游“殖民地”的,当属De Wieden自然保护区内的羊角村(Giethoorn)。地下泥煤经过千百万年的渗水,形成了湖群,最早的拓荒者在10世纪洪水留下的沼泽里发现了羊角,于是这里就有了羊角村的名字。当然,如今面积不大的区域内,是只有羊角面包而没羊角的,人們渐渐拼凑出90公里长的宽窄运河,搭建起180座直通家门或公共区域的大小桥梁。这里对投资置业有着严格限制,因此村庄保持着2620人的居民人口,而每年前来的中国游客却高达15万到20万人。
我是在区域中心城市兹沃勒(Zwolle)住了一晚后,赶大清早来的羊角村,偏偏这一天还是我们国庆长假开始的第一天。可能因为到得实在太早,并没见到预想中大规模的“国庆仪仗队”,成为这一天第一个单车租客后,在只有树上鸟鸣和鸭子扑水的村子里转悠,却发现其实已有不少懂得享受的自助游同胞,要么“潜伏”在水上联排别墅,要么操控着平底电动船在狭窄河道深处神出鬼没。捎我前来并顺便探望姐姐的兹沃勒房东严(Yah)告诉我:“中午过后,你们中国人就该以自拍杆集团军的规模,乘着大批大巴前来了,村里人可喜欢他们了,毕竟带来好生意。”
严在土耳其费特希耶生活了好些年,回到家乡后,做着一份看护残障人士的全职工作,而他的太太高迪丽芙(Godelieve)则是一名颇有影响力的电视明星,是在节目里或派对上教人做菜的厨艺高手。他们家中收藏了许多把经典贝斯,在换过几波玩票性质的乐队后,严如今将风格定型为雷鬼铺底的尼德兰语摇滚。对于这个低地农业大国的国民来说,喜欢高山大海了,能有足够的钞票去心仪之地生活几年甚至大半辈子,想奶酪了乡愁了,又可以随时回来。至于如今欧陆难民带来的麻烦问题,还没在荷兰东北部的城镇体现,不过右翼政党越来越得势也是事实。不像谨慎到不敢谈半句政治的邻居德国人,严虽然也反对右派,但还是坦承自己更担心难民威胁。“夏天还好,现在天凉了,他们该要暖气房子和厚衣服了,Winter is coming。”他念叨起《权力的游戏》里最被人熟知的这句台词。

3
即便凛冬已至,即便荷兰的天空总是阴晴不定,说翻脸就翻脸,但天气转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火车站旁的运河边就热闹起来了,红灯区的姑娘们生意也好了起来,橱窗纷纷拉起了帘布,被互联网色情冲击的实体经济重又复苏。
以前在阿姆斯特丹住過数日,第二次过来,就只是解决一下饥饿的“西南民族胃”需求,毕竟这儿有着中国之外品质最高也最辣的川菜。顺便去打折的大卖场买件大衣,到阿贾克斯俱乐部主场看看如今没落到不成样的荷兰职业足球——座无虚席、鸦雀无声的90分钟,确是我看过的最沉闷的一场球赛,最后被在牙买加认识的荷兰妞放了鸽子,独自在影院看了一部恐际片。
乘着火车失望离开,半小时后,就在一片公共设施和工业建筑的景观中,驶入哈勒姆(Haarlem)城域范围。由于要下榻在一位城市规划设计师家中,为了有话题可聊,我开始查阅从阿姆斯特丹到哈勒姆的规划建设新闻和知识。于17世纪开始大规模发展起来的阿姆斯特丹,采用的是辐射状运河结构,建设从西向东,设计城内三条运河同时留足岸边住宅开发空间,外围的第四条有着防线功能,并管理冗余水资源。而哈勒姆城市则由南向北规划,与海岸和海岸沙丘保持着平行。
对我来说,任何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描述,都如同挂在事务所墙上的案子,或双年展大厅里的介绍文字,复杂如天书。而面对眼前社区水面上突兀而起的三栋异形建筑,闪现于脑海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住这种房子不招蚊子吗?似乎欧盟又有非常严格的、包括灭蚊剂在内的农药限令。见到房主罗纳德(Ronald)之后不久,我就抛出自己的疑问。答案很简单,频繁地抽走废水脏水并进行有效再循环,就不会滋生蚊虫。
罗纳德的家是一套独立的三层高大宅。即便屋里有着很多舒服的窝,他的狗儿老友还是总要趴在工作室的电脑下,那曾是罗纳德妻子进行设计工作的地方。在我重新启动那台电脑打印一张球票时,73岁的老头子陷入了回忆。妻子两年前去世了,而这房间里的东西除了时不时掸一掸灰尘外,就再没动过。
1943年,罗纳德生于荷兰东北部,在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之前,他父亲被迫在纳粹空军基地从事制造和测试工作,经常故意“动手脚”。“冷战”期间,所有荷兰青年都必须服兵役,罗纳德就子承父业,为北约战斗机做地面导航。退役后回到校园,去代尔夫特(Delft)理工大学攻读建筑规划,也是在这个他最喜欢的城市里,认识了后来相濡以沫的妻子,并一道赶上了西欧经济腾飞、需要大量城建规划的忙碌好日子。罗纳德第一个独立承接的案子,是中部城市尼沃海恩(Nieuwegein)的市中心改建项目,在他的坚持下,一个围楼式的区域出现了,广场四散开来更可容纳2500户人家。罗纳德记得几年后去中国香港开会,对岸刚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深圳也来人取经,并羡慕嫉妒恨地表示:“你们的工作真爽啊!就对2500户负责,我得考虑好几百万户。”接着在哈勒姆的规划院工作了十来年后,罗纳德退休了。接着就参加各类非政府组织(NGO),到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过后的斯里兰卡Pottuvil、肯尼亚Nakuru火烈鸟保护基地和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外延社区,主持规划顾问。“这些都是英国殖民者留下来的地方,开展工作很艰难,英国佬就从来没怎么有过城镇规划的学问和传统。”他说。
次日清早起来,罗纳德带我看了整个社区,并上了一堂实景规划课。他的住宅花园,与其他几户人家一道,连着一片公共水域。在这个绝大部分国土低于海平面的国家,居民社区若低于周边填围城镇的高度,得保证至少6%的公共水域面积,以便在发生洪涝时,扩大地表水的容纳和排水能力,而加大的水泵功率,能把运河过来的水位再降低2米,和公共水体基本保持同等高度。大面积的绿地公园,则是从垃圾填埋场改建而来,全面铺上2米深的塑料体后进行植树种草,不过由于垃圾块自身会分解,因此有些步径已经出现了些许沉降起伏。我最先留意到的那些在水面正中央的倾斜房子,是比利时建筑团队1985年进行的公寓实验,后来还进一步成为国家级遗产。
4
1658年,殖民地新荷兰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在曼哈顿岛北部,照着南部前哨新阿姆斯特丹的模板,建起又一个哨点新哈勒姆。英国人把它夺去后,把整片岛区重命名为新约克(纽约),却只对新哈勒姆(Nieuw Haarlem)进行简单删减,成了后来非裔美国人最为集中的哈莱姆区(Harlem)。
虽说在哈勒姆住了两晚,但真正进老城区,也就只逛了圣巴沃大教堂(Sint Bavo)。因为从无信仰也懒得求知,以往进教堂,要么刷卡集邮式到此一游,要么只为避暑避雨,偏偏这次碰上一位主动愿意义务讲解的老太太,不但完全不为宣教,还在介绍一只金鸟雕塑时,大概表明了荷兰人对信仰的态度:“新教到来后,教会用这种啄自身肉以喂养幼鸟的神物,来替代耶稣。我们荷兰人在16世纪开始转信新教,更多是一种对抗西班牙侵略者的情绪,是觉醒的民族意识,而非真正的宗教自觉,也因此,到了今天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不再信教。”当然,相对较弱的教会依然有着筹款能力,祭坛左前方有一个被称为面包长椅的福利分发点,过去是给穷人和寡妇发面包,现在则把宗教节庆筹措的款项用于照顾中东和北非难民。断断续续的难听声音,从教堂上方那座荷兰最大管风琴传来,从亨德尔到莫扎特,都曾受教会之邀,演奏过这部名琴,而此刻把玩它的,则是阿姆斯特丹合唱团过来练习的孩子,下手没轻没重的。
这天是10月3日,南边一点的城市莱顿(Leiden)迎来了热闹的解围纪念日。1574年,被西班牙侵略军围城5个月后,莱顿最终解围。为嘉奖勇敢的该城民众,王室让市民们选择建一所大学或豁免某些税收。市民认为免税令可被撤销,大学却能延续百年,所以选了后者,从此荷兰拥有了一座学术声誉响当当的莱顿大学,建造了全球第一间低温物理实验室,洛伦兹和彼得·塞曼发现了塞曼效应,威廉·埃因托芬发明了心电图,爱因斯坦讲学时写下了玻色子统计分布的手稿。不过,也有外人开玩笑,“就是因为没选择免税,所以你们荷兰人现在变得如此抠门”。确实,除了众所周知各付各的“去荷兰”(Go Dutch,AA制)之外,参观博物馆和收费景区时,学生证、记者证、军人证都是很难被承认的,而想要找到免费沙发住宿的难度,也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
莱顿解围纪念日,渐渐变成秋凉之后的第一个狂欢节。火车站旁的大广场直接搬来了主题公园游乐设施,被跳楼机绑牢的姑娘们,高分贝尖叫着向桥面砸下;来到顶端过山车,蓄势向站台俯冲而去;斑马、布老虎和塑料鸭子,在各个角落被一支支气枪击毙。音乐节般的舞台,顺着运河,一个个在城中其他角落排开,仿古罗马建筑的廊桥上,翘臀的性感妞儿在唱着乡谣《可爱的家乡阿拉巴马》。雨又下大了,曲拐的巷道深处,醉醺醺的男女在强劲的电音拍子中淋浴狂舞,不过他们手里可没随时可供发泄的玻璃瓶子——在这个妓女和大麻都合法化的国家,是不允许拎着酒瓶在街上走的。
5
为保持中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和充足空间,即便留有王室,但荷兰并没有多么规模恢宏的宫殿。大量奇思妙想的现代公共建筑,集中于重要港口城市鹿特丹以及国外其他城市,而古老名城则保持了与过往几乎同样的相貌。譬如几乎从未离开过代尔夫特的肖像画大师维米尔,偶也以他独门的光影技艺,描绘过这座城市。如今拿着画作,比对过去,运河、小舟、广场、倾斜的老教堂、陶瓷工艺品店,都还原封不动地搁在那儿,只是眼前画面里多出了间错驶过的汽车,以及密密麻麻停放的自行车,而深秋的运河,不知怎的,也铺满了绿藻。
中国香港二代移民库克(Kwok)带我在运河边转悠,碰到一个遛猪的奇怪家伙后,被电视台记者抓过去采访。因为同时作为土生土长的代尔夫特本地人,他就以流利的尼德兰语讲述了对这座城市稀奇古怪事物的热爱。
当音轨转为英语夹杂着一丁点粤语和普通话时,库克就飙着他的宝马Coupe,跟我说着酷炫的人生观:“第一代移民拼死赚钱,第二代省吃俭用攒钱和经商,第三代开始吸毒乱交,第四代就糟蹋钱搞艺术,接下来的后代又得开始重新打拼赚钱,成了海外华人一种绕不过的有趣循环。很幸运,我今年42岁,却把这四代人生都经历了个遍。”他生在荷兰,回香港学过咏春拳,甚至去过北京给部队进行武术指导。不过因为天性叛逆、吃喝嫖赌抽,书没读完就辍学了。后来自己办起“糟蹋钱”的现代舞团,又以第一代人的吃苦和第二代人的精明,投资各种房产,“我从不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那就不是能生财的投资了”。于是我也跟着花钱,住进他的“投资”里。
这些年,作为自有舞团品牌的艺术总监,他开始在泰国龟岛组织沙滩现代舞,通过脸书召集并短期培训有兴趣的各国网友。“怎么说呢?我和其他华人移民不一样,他们省吃俭用赚钱养家,然后留下一大笔财产后,撒手人寰,而我想要Live Rich,DiePoor。”从跑车中开门出来,我才注意到这个荷兰籍香港人的个头竟然如此之小,却不知哪里积蓄来的气,能让他从一位咏春导师变成舞蹈老师。
6
“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这些口号似乎更适用于荷兰人,且在他们的“斗水”历史上几乎差点就被证实是正确无比的。在千年的与水争地过程中,他们真正获取了家园,以至于谚语都不得不赞美这些造物主一一“上帝创造了世界,荷兰人创造了尼德兰。”
填海造地与抽水干拓(Polder),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所带来的土地,纷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UNESCO),这其中风景颜值最高的,是鹿特丹以东、莱克河与诺德河交汇处的小孩堤防(Kinderdijk)。
我在秋高气爽的一天来到这里,19座风车安静地守在水道两侧,从入口堤坝看去,疯长的野草遮住了大半胖乎乎的椭圆躯体,螺旋桨状的叶片如同巨大的飞去来器凝滞在蓝天之中。河水清澈如镜,倒影中的风车也就成了一个个独守怜影的自恋狂。偶有人迹,扒开深草,走过木桥,爬上不知是否还有功效的塔顶,开始认真检查着什么。如此这番融洽和谐,哪能想象会变成怎样洪峰奔涌的可怖场面。
可偏偏关于小孩堤防名字来历的历史故事,就是关于斗洪水的。千年以来,随着地下泥煤渗水和土质变化,低于海平面的阿尔布拉瑟沃德(Alblasserwaard)圩田,一直受到外海和河流来水的威胁,不可能再依赖自然排水和风干。14世纪中期,高低错落的两块蓄水库区建了起来,却也无法应对大一点的水患。1421年的圣伊丽莎白洪水退去后,有人去堤坝之间看看,是否可能挽回点什么损失。远处漂来一个木制摇篮,稍近一些的时候,人们看到有只猫辛苦地跳来跳去,试图在波纹之中保持摇篮平衡,到眼前时候,里面原来是一个熟睡到什么都不知道的婴儿。从此堤防有了小孩之名(Kinderdijk),而最初一批靠自然风力抽水的风车,也开始陆续建起,如今还留着其中两座。从1738到1740的两年间,17座可以靠单人操作的新型风车又立了起来。
先筑起的8座砖石结构风车,位于低水库区(Nederwaard),减轻了重量的后8座木制八边形风车则应对高水库区(Overwaard),却也会引发火险,以至于在1981年还烧倒了一座,并在后来重建。19世纪以来,越来越先进和高效的蒸汽、柴油和电力,渐渐取代了以往操作复杂的风车水泵,现今,依然有人在操作这些大风车,却更多是作为文化遗产保存的一种不太实用的技能,毕竟,随风向操控这些最长可达30米叶片的难度,不亚于在海上驾驶帆船。
狭长水道的拐弯处,隐藏着一座可能是小孩堤防最古老的Blokweer风车,由于历史资料缺乏,人们只能大概估算它建于1500年。它的大肚腩里如今是一间精致的起居室,里面并没如Hoek家风车那样反映旧时生活印迹的博物,只是在梁柱顶端的电视里循环播放着风车运转知识视频。相貌出众的母女两人,在午后透进来的丁达尔光柱里,忙碌着编织手艺活,不过她们表示,自家并不是真正生活在这里。屋外,穿着典型荷兰大木拖鞋的叔侄两人正在劈柴烧火。他们沉默寡言,以至于我始终没弄明白,虽然这架风车和周围田地的产權属于这家人,但在这个游客罕至的角落里,他们的穿着和劳动,究竟是为展现传统的活态表演,还是某种返璞归真并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
再有人定胜天的信念,再有让其他国家仰慕的高尖科技和生活质量,荷兰人还是没能真的彻底征服自然。1953、1993和1995年,都发生了倾国之力应对的严重水灾。这让他们在城建规划和筑坝工程中开始了一些新的思考,在以往“与水争地”的思维中,也渐渐产生“还地于河”的新观念。无论如何,这个自己作为上帝建造家园的智慧国度,始终会保持着最漂亮的“人造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