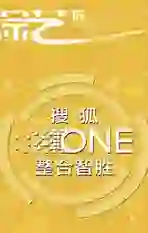人类学纪录片的两种类型及其对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的启示
2017-04-11王凌雨
王凌雨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发展如火如荼。纪录片行业里面有一个鲜为人知但是异常值得尊重的老前辈——人类学纪录片,人类学纪录片在文化保存方面和真实性方面完美地诠释了纪录片的实质和内核。影像的真实是最动人的力量,也担当着使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世留存和传播的重要使命。人类学纪录片的独特价值对中国纪录片行业重新审视自己,树立行业自信起到无可比拟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人类学纪录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和发展过程中,不同的职业或学术人群,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功能和价值,存在着差异较大的看法;这些观念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学影片在内容与形态方面的类型化分野,目前中国的人类学纪录片可以大体分为两种类型——学术型人类学纪录片和大众型人类学纪录片。
学术型人类学纪录片的特征及其独特价值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人类学者的看法。
在人类学者看来,人类学影片的主要作用,首先是作为人类学研究的“科学资料”,其次是用于与人类学相关的课程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纪录片作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影视成果,主要应被视为一种“可靠的科学资料”,而不是具有美学属性的艺术作品;当“科学”和“美学”这两种性质发生矛盾时,应当尊重科学而牺牲美学。这种由影像和声音构成的“资料”的作用或曰功能,除了用于不同文化传统间的“对话”和彼此“分享”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将我们正在变化着的生活方式的种种特征保存下来,留传给后世。”([美]保罗·霍金斯《影视人类学原理》[M]. 伊利诺伊州荧加哥阿尔丹公司,1975.)
在中国纪录片的诸多类型和种类之中,在文化保存方面,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的表现最为抢眼,也最能突出纪录片的巨大价值和意义。20世纪初以来持续不断的世界和中国影视人类学实践的认识与实践成果表明,用人类学纪录片这种影像的方式纪录和保存工业化之前人类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对于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的传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在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发展史的1950——1960年代左右,诞生过具有标杆性质的的21部民族志影片,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學纪录片,这批影片有:《黎族》《凉山彝族》《佤族》《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人》《苦聪人》《独龙族》《西藏的农奴制度》《景颇族》《新疆夏合勒克乡的农奴制》《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鄂伦春族》《大瑶山瑶族》《赫哲族的渔猎生活》《丽江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人》《方排寨苗族》《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婚姻》《苗族的节日》《苗族的舞蹈》《苗族的工艺美术》。这批影片在当时被命名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为“民纪片”。“民纪片”是规模庞大、耗时长久、有组织有计划的“国家行为”,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独此一家的。因此,当这批影片后来被送到国外展播时,在国际社会的反响是用“震惊”二字来形容的。基于这一前提性认识,这批至今还是鲜为人知的纪录片作品,在学术界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中国人类学界公认,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上,这批影片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在我国纪录片的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生活在文化变迁急剧加速、文化传统快速消失的20世纪,人类学者最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同质化正在和即将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呼吁将现存的、多样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尽可能及时和完整地纪录下来,以作为人类生存和人类文化未来发展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中,可以说人类学纪录片为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人类学研究凭借的传统“科学资料”,主要由文字、图片和实物构成,这些资料无论从信息的鲜活、生动、易于感知,还是信息的完整性(即“全息性)方面来看,都无法与以影像和声音为介质的人类学纪录片相比——由此体现出人类学纪录片的独特价值。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内容一样,人类学纪录片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人类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种繁衍、组织规则、宗教信仰、社会结构、文化模式等,都在其视野之中。但后者在对这些信息的纪录和再现方面,却比人类学传统的笔录方式要优越得多。譬如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中,相对传统的笔录方式而言,人类学纪录片不仅能够用短得多的时间纪录下更多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的生动性、拟真性、可信度与可重复再现性,无疑要比抽象的文字符号强得多。
大众型人类学纪录片的特征及其独特价值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影视从业者的看法。
在如弗拉哈迪、格里尔逊等影视媒体的从业者看来,人类学影片的功能与价值,绝不应该是仅供科研之用的“资料”,它们应该能够被用于服务“大众”这个规模最大化的社会人群。将人类学纪录片视为完全剥离了艺术美学性质的“科学资料”,这仅仅是人类学者的看法,影视界对此片种的功能认识却要宽泛得多。后者认为,除了作为“供研究用的资料”和“人类学课程的教学片”之外,人类学纪录片还可以是以“大众”这个最广大的社会人群为传播对象、供视听媒体播放的影片。正是由于被统称为“大众”的受众(读者)人群的极大扩展,以及这一人群中个体间的知识与趣好的极度参差,使得这类人类学纪录片中的“科学”与“美学”这一对矛盾的性质,有可能由截然对立转为相依共存。
在具备人类学纪录片在内容方面的“真实”——即真实的人物、场景和事件——这一内核的前提下,大众型人类学纪录片不绝对排斥“主观”与“虚构”,从而使这类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艺术化的内容结构与形态特征。这种人类学纪录片的性质,与英国纪录电影运动的领导者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对纪录片摄制原则的阐释相近:“在现实中挖掘素材,并从熟悉素材的过程中自然形成故事,通过生活细节的并列,创造出对生活的阐释,有明确的创造意图。”格里尔逊认为,他的老师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等作品,就是这类纪录片的典范之作。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BBC)出品的系列纪录片《失落的文明》(Lost Civilization)以及《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等,更是依据“历史真实”加入了大量人物扮演和场景复原等艺术化与故事化的成分,籍此赢得了大量的电视受众。
大众型人类学纪录片的价值在于,它比“资料型”或“教材型”的人类学纪录片,拥有更大的受众人群;亦因为如此,这种纪录片对于完成其先天承担的任务——文化的“对话”、“分享”和“传承”,具有效率与效益最大化的优势。事实上,从《北方的纳努克》以来,大众型人类学影片的作品层出不穷、数量庞大,对人类学知识的社会普及和不同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共享,作出了巨大贡献。如1930年代英国“纪录电影运动”制作的这类紀录片,数量就超过了400部;这些纪录片作品中的《漂网渔船》(Drifters,1929)、《锡兰之歌》(The Song of Ceylon,1934)、《彼特与波特》(Pett and Pott,1934)、《夜邮》(Night Mail,1936)、《煤矿工人》(Coal Face,1936)等,就凭借大众化电影媒体作为传播平台,以其多样化的人类学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性结构方式,对于当时的大英帝国(包括其海外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物产等信息,向本国及国外民众“广而告之”,不仅形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而且对处于欧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英国的国内外贸易发展,和今天被称为“软实力”的国家形象的提升,都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浩瀚无边,拥有海量的资源,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纪录片创作者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是纪录片创作和产业发展的丰厚土壤。在纪录片领域,很多获得国际国内大奖的纪录片很多都是人类学纪录片或者具有人类学性质的纪录片,例如《神鹿啊,我们的神鹿》《最后的山神》《沙与海》《山洞里的村庄》《三节草》《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藏北人家》《普吉和他的情人们》《八廓南街16号》《蜕变(阿卡人)》《神圣的鼓手》《隆务河畔的鼓声》《仲巴·昂仁》《祖先留下的规矩》《端午节》《虎日——小凉山民间戒毒的人类学实践》《犴达罕》等。
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之路,应该充分意识到纪录片的历史使命和文化担当。鉴于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下半叶变迁的加速,许多传统文化体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濒于解体甚至湮灭的严酷现实,建立在扎实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基础之上的人类学纪录片,具有对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即时影像保存的巨大意义。对于中国未来纪录片的发展,不论是片种类型、创作理念还是创作方法,以及题材选择等角度都会提供新鲜血液和别具一格的借鉴,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对于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之路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