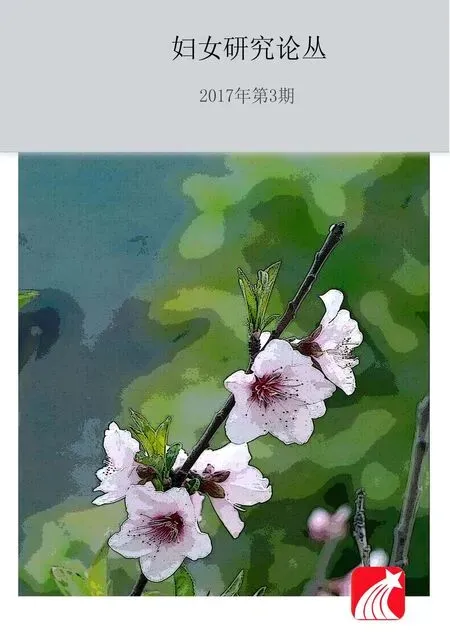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基于Hypatia杂志2014-2016年研究的综述
2017-04-05李蕊
李 蕊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基于Hypatia杂志2014-2016年研究的综述
李 蕊
(清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Hypatia;女性主义认识论;认识论不公;女性主义哲学
Hypatia杂志是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杂志,它面向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前沿研究。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具体体现在三个领域:认识论领域、具体领域中的女性声音和对女性主义哲学经典的重新解读。通过对杂志近期论文的综述,我们可以获知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这不仅为我们近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新方向,同时也能为我们优化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Hypatia杂志是著名的女性主义哲学杂志,也是美国主要哲学杂志之一。它面向女性主义哲学中的前沿研究,在1985年创立之初就成为扩大和改善女性主义哲学的催化剂,女性主义从中重新发现与继承女性哲学家传统。它不仅关注女性自身的问题,同时更以女性的角度提出对各个领域和各种问题的理解。通过对杂志近期论文的综述,可以获知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新趋势,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新方向,同时也能为我们提供方法论方面的指导。本文将通过三个主题——认识论领域、女性在具体实践领域的声音和对经典的重新解读来评述当代女性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一、认识论不公和对认识论公正的追求
认识论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女性主义哲学一直对它保持高度关注。在认识论领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科学、哲学等以“理性”为标准的领域中,女性处于不被认可的边缘地位。而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在认识论中所处于的劣势地位,也分别从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识方法进行了剖析,以此提出针对性的方法。同时,她们也对知识的表达和交流工具——语言进行了研究。
“认识论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近年来不断出现在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中,这个热词出自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的著作《认识论不公:认知中的权力和伦理》[1](P 1)。弗里克认为,认知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权力发挥着重大作用。她定义了一种“身份权力”,它依赖于被包含在社会权力运作中的身份的共享性社会设想性概念,直接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或者客体的认知能力相联系。接着她分辨了两种认知不公:证明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和解释不公(hermaneutical injustice)[1](P 1)。当听者对说者降低了信任,就发生了证明不公;而当一个人理解自身的社会经验时,集体的解释资源预先地将他放置在不公正的劣势地位,解释不公就发生了。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警察因为一个人是黑人而不相信他[1](PP 4)。后者的典型例子是,一个人遭受了性侵,但是她所处的文化中缺乏批判性概念,这样她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她自身的经验,更不必说和别人以可理解的方式进行交流,即“情境性解释不公”:“在解释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社会经验不能得到恰当的概念化并且被错误理解,甚至这些群体自身也是如此;或者这些群体在想要传递内容时,却因为自身的表达方式被不恰当地理解而不被看作是理性的”[1](P 4)。
在认识论中,女性首先遭受的不公就包含了证明不公——无法作为认知主体。杰弗里·霍尔兹曼(Geoffrey S.Holtzman)认为,与其他学科中的女性所取得的进步相比,哲学领域中的女性进步稍显逊色。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与哲学教授以及同事持有不同意见,女性在哲学课堂中对于不同意见更为敏感,等等,这些偏见无形中为女性对哲学和其他认知领域的参与设置了更多的障碍。而如果哲学将女性排除出去,就意味着它不公平地将一些个体(经验)排除出去,并且拒绝她们对哲学作出贡献,而依赖于纳入更为丰富的人类经验和视角的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必受影响。同时,仅仅关注哲学中稀少的女性数量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为什么哲学中一种非人性的态度和个体感知维持着这个学科中(失衡的)性别构成,这种研究对于哲学进步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2](PP 293-312)。
但是,在将女性纳入主体地位以后,女性主义也要警惕另一种不公正——认知对象化。丽贝卡·图维尔(Rebecca Tuvel)以女性主义关于环境变化的知识为例阐述了这个问题。在环境变化这个学科领域中,认识论具有非常明显的性别色彩:女性被看作对于适应环境变化具有更完美的知识,更能够处理并且能够超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图维尔认为这种做法具有将女性在认识论上对象化的风险:女性虽然积极地分享她们的知识,但是仅仅被看作知识的来源,尤其是对于第三世界的女性而言,她们有可能被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倾向所利用,她们的知识在压迫的背景下被获取,或者只是为了政策的需要。女性更多地作为知识的来源,更少地被看作参与讨论的知识主体;女性的知识被看作“来源”,而非参与性的“声音和角度”[3](PP 319-336)。
米兰达·弗里克认为证明不公出自可信性的缺乏,艾玛伦·戴维斯(Emmalon Davis)则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狭隘,并提出了补充,即证据不公也可能出自可信性的过度。如“亚洲人擅长数学”“女性善于照顾孩子”“黑人能歌善舞”等,这些人因为偏见性的刻板印象而被看作拥有某些方面的知识,一种关于群体的印象被施与所有个体,或者个体的某些特征成为整个群体的代表。个体仅仅被看作信息来源,而非积极性的信息传播者:这些个体所想要表述的任何内容都被禁止或者被忽视——这种积极性的角色设定和以偏见方式膨胀的可信性评估都对边缘化的知者进行了认知压迫和剥削[4](PP 485-501)。同样地,跨性别女性也遭受了同样的刻板印象威胁。拉切尔·麦金农(Rachel Mckinnon)认为刻板印象威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关注与性别之间的关联,并且目前这种关联仅仅局限于这种威胁和顺性女性(cisgender women)*Cisgender指个体对自身性别(gender)的理解与其生理性征(sex)相一致。它与Transgender 相对,后者指对自身的性别理解与生理性别不一致。目前有四个词语与之相关:cisgender female、cisgender women、cisgender male 、cisgender men。前两者意思相近,后两者意思相近。此解释参考维基百科。及其经验之间。这种研究将跨性别女性所经历的刻板印象威胁以及归因模糊(attributional ambiguity)*归因模糊是心理学术语,指受到歧视的群体在理解反馈时所面临的困难。如被歧视的一个主体在他人否定性的反馈时,他无法辨明这种歧视出自于他们自身还是他们的行为;而在他收到肯定性的反馈时,他更多地将它归因于同情,而非自己的能力以及成就。排除出去,跨性别女性因此受到了男性以及顺性女性的双重性的刻板印象威胁。她期待我们可以获得对这种威胁及其恶果的更深入的理解[5](PP 857-872)。
与知识的产生相伴随的是知识的表述和传播,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的使用。而语言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超出了描述的范围,更多地发挥着语用角色——语效和语力作用。丽贝卡·库克拉(Rebecca Kukla)考察了性别如何塑造言语的语用学,而一种言语不公在这种考察中凸显出来。言说作为一种社会合作行为,充满了复杂的权力关系和实际的偶然性。当处于劣势地位的成员系统性地无法产生一种他们本有权力去完成的具体的话语行为,尤其是当他们的愿望实际上产生了一种不同的言语行为,这种行为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主体性更具妥协性,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为言语不公的受害者[6](PP 440-457)。如一个女主管在对员工发号施令的时候,她的话语所产生的效果就不如男主管,而这种言语不公又进一步地恶化了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斯蒂芬妮·茱莉亚·卡普斯塔(Stephanie Julia Kapusta)则关注性别词汇的使用对跨性别者的伤害。如当下“女性”隐含着成为女性的规则,它的使用削减了跨性别者的自尊,限制了他们对自身性别的定义方面的话语资源,并且导致对他们最大程度的侵略性的心理伤害。这导致了或者至少一些跨性别女性被排除在外,或者它们暗中滋养了女性内部的分级,尤其使跨性别女性被边缘化。因而我们需要在道德上或者政治背景下挑战这些性别词汇:我们可以假定“女性”这个词语具有暂时性和可修订性,而不是具有固定的不可改变的含义,性别词汇使用的道德争议性则成为一种引起这种修订的催化剂[7](PP 502-519)。
而女性主义对于认知公正的追求包含了努力将自身纳入知识主体、警惕认知对象化、保持真诚和开放的认知态度、社会各方创造良好的知识环境等。戴维斯提议,不仅倾听者要提高自身的认知和道德素质,也要求听者能够改善他们的认知环境,还要求边缘化的主体在抗争中保持自我意识的同时,也能够容纳对处于优势地位但积极争取证据公正的人[4](PP 485-501)。图维尔强调保持双方公平合作交流的同时,也对压迫保持敏感;警惕认知主体寻求知识的动机,并且持续地分析这些人在压迫中可能具有的同谋角色[3](PP 319-336)。杰克·孔(Jack M.C.Kwong)认为,认知不公能够通过“开放性思想”这个理智特性得到重构,尤其是某些不公出于人们在某些方面的封闭思想[8](PP 337-351)。同时,凯伦·阿诺德(Karen Frost-Arnold)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观点:欺骗在某些情况下对认识论是有益的——如果这种背叛扩展了真实网络,从而能够将那些被压迫的主体纳入进来,那么这种背叛就是有益的[9](PP 790-807)。
在女性主义分析中,知识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知识,更代表了一种真理、规范和标准,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在认知不公的分析中,“刻板印象”“身份偏见”等一再地出现,与认知不公正紧密联系。正如弗里克所理解的,纠正这些不公不仅仅需要认知方面的努力,更需要伦理上的努力,需要集体性的社会政治上的改变,因为归根结底,女性所遭受的认知不公并非出自认知的缺乏或者认知方法的不足,而更多来自于对女性作为“认知主体”能力的怀疑和轻视。在提倡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平等、更具有交流性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下,女性更需要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更可能被听到、被认可。
二、具体领域中的女性声音
在Hypatia创刊25周年的纪念刊中,学者们关注并设想了女性主义哲学的未来。其中,雅丽萨·施林普夫(Alexa Schriempf)提议女性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关注残障人的体验,把残障看作一种与种族、阶级、性别、性等相同的分析维度,通过残障的体验来理解世界和分析社会生活[10](PP 927-934)。可喜的是,女性主义近几年的发展趋势体现出了对残障人士的关怀。除此之外,女性主义也对儿童等一样处于弱势或者边缘地位的群体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表现出了特别的敏感性和共通性,因而也给予了特别关注。
Hypatia杂志在2015年用整整一期集中探讨了残障问题,其中关注的问题有“残障”的定义、对规定“残障”和“正常”的标准的质疑和考察、残障人的个人自主性、对残障人的参政以及私人性生活的关注、残障与关怀、残障与变性和酷儿之间的联系,等等。玛格丽特·希尔德里克(Margrit Shildrick)考察了规定正常人和非正常人的界限,她质疑将残障人看作非正常人的、有关于身体完整性和自然身体的设定。通过论证所有身体的模糊性——即我们的身体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她消解了所谓的身体完整性以及例外主义的设定,这就消解了残障人的“非正常人”的性质[11](PP 13-29)。同样地,劳拉·戴维(Laura Davy)的论证也将残障人纳入个体自主性的范围:自主性作为个人的必要特征,这种特征只能通过相互支持、拥护和相互实现的关系得以体现,残障人也因此被纳入道德和政治理论中[12](PP 132-148)。罗拉·贝克(Laura Back)提议将关怀施与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定位为平等和相互依赖的,并且将残障人的公民资格放置到中心地位[13](PP 115-131)。凯瑟琳·米尔斯(Catherine Mills)思考胎儿因为肢体残障缺失而被终止妊娠的案例,最终她论证说,这种终止与因为胎儿性别而被终止妊娠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大家通常设想的那样大[14](PP 82-96)。亚力克山大·巴里尔(Alexandre Baril)则关注了残障研究中对“变性”的排除,以及规定“深度”和“普通”整形之间差别的预设[15](PP 30-48)。
劳拉·维尔德曼·凯恩(Laura Wildemann Kane)关注政治中的“儿童”概念。通常的政治哲学将儿童看作静态的,处于智力、身体和道德能力都未充分发展的缺乏状态。凯恩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贬低了人类的某些普遍特征——依赖性和成长,并且错误地将这些特征仅仅看作儿童的特征。这就导致对儿童和被看作完满发展的成人的严格区分,并且它限制了儿童的发展能力和有序进行的道德发展。凯恩提议我们将依赖看作普遍的人类条件,从而儿童和成人就形成了某种关系,即鼓励儿童以及成人的道德感的成长和发展[16](PP 156-170)。
校园欺凌不断地出现在近期的新闻中,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女性主义则对此进行了哲学反思和女性主义分析。阻止欺凌通常有两种方法:零容忍政策和生态学干涉。提姆·约翰斯顿(Tim R.Johnston)使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分析了每种方法的效率,论证说生态学干涉是比较好的方法。欺凌形成的原因非常复杂,因而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诱惑或者威胁性的惩罚得以阻止,而只能通过如同欺凌的起因那样复杂的关系、环境、文化和情绪相互交织的网络。她提出用“肯定”作为生态学解决方法的认知上和伦理上的规范,即我们学着去创造、参与和修复个体之间肯定性的反馈循环,这种肯定性的反馈循环是我们关心他人的重要方式[17](PP 403-417)。
日益严重的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问题也引起了女性主义学者的关注,而其中环境变化中的性别维度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海蒂·格拉斯维克(Heidi Grasswick)通过研究获取恰当的信任的复杂性来强调我们在环境变化中的负责任的行动。我们一般依赖具有绝对权威的机构来获取环境变化的信息,但是这些机构的可信性依赖于它们满足竞争性利益的能力,这就对普通人的信任提出了挑战。女性主义情境主义观点的引入,对于我们在知识产生中处于什么位置、这种位置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对此进行批判性反思提供了洞见[18](PP 541-557)。凯尔·波伊斯·怀特(Kyle Powys Whyte)重申文化价值和身份塑造出人们对于共同利益中所承担的责任的不同回应,而由此更加突出了公共伦理和关于自满的哲学论证[19](PP 599-616)。奥斯特里达·内曼尼丝(Astrida Neimanis)与雷切尔·沃克尔(Rachel Loewen)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关于主体的形而上学,即将我们看作“环境性主体”(weathering body):我们并不是环境的掌控者,也不只是处于环境之中,而是我们自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本身就充满了环境行为,也一起改变着世界的环境[20](PP 558-575)。霍利·巴克(Holly Jean Buck)、安德里亚·甘蒙(Andrea R.Gammon)等将性别带入到地质学中,以此研究了环境变化中的性别维度。如男性通过技术性解决方案将全球环境变化看作“确定的”,而这极有可能恶化而非减弱环境伤害和人类痛苦[21](PP 651-669)。
由于母乳喂养的好处广为人知,鼓励母亲母乳喂养已经成为公共健康推进工作的一个目标,这在当前的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通过引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观点,即我们都对他人负有责任,罗宾·李(Robyn Lee)论证说:喂养饥饿儿童的道德义务必须从满足母亲的需要来同时考虑,尤其是在当下缺乏对母乳喂养的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喂养需要在更广泛的关于饥饿的政治背景中得到理解,通过提升母亲的社会、经济、情感等需要来得以实现,比如提倡共同担负食物准备、家务劳动、照顾儿童等责任,为母亲提供更便利的健康设施,延长离职时间,在其工作处提供更好的母乳喂养设施,提供高质量的日托,等等[22](PP 259-274)。这些措施对于中国的母乳喂养问题的推行和解决具有参考性。
丹妮拉·库塔斯(Daniela Cutas)和安娜·司马雅多(Anna Smajdor)考察了一项与母性有关的新技术——体外衍生生殖细胞技术,即使用胚胎干细胞或者诱导性多能干细胞来生成卵子,从而避免借用他人卵子或者使用自己因为年长而不健全的卵子。它不仅对当前的生殖医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已经将新的讨论维度带入了这个领域:绝经后的母性得以重新产生,它是否加强了狭隘的基因生殖论证和鼓励女性不惜任何代价来生育与之有基因关系的后代的鼓励性生殖文化[23](PP 386-402)?
就世界范围来看,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过多承担是普遍性的。出于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公地位,女性也对促进家庭内部的公正进行研究。西瑞·卡迪尔(Serene J.Khader)认为发展伦理(Development Ethics)将降低家庭内部的性别不公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应当提供互补性-兼容性论证。因为贬低女性劳动的家长制和不公平的性别模式使得男性推卸掉应当承担的互补性的责任,而这阻碍了女性获得平等和福利[24](PP 352-369)。波琳·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 Kleingeld)和乔尔·安德森(Joel Anderson)批判了通常的观点,即一个家庭是否公正与一个家庭是否有爱的模式相冲突,她们提倡将公正看作家庭价值,从而建立以公正为导向的关爱性家庭概念[25](PP 320-336)。
女性在这些具体领域中的声音不仅关涉女性自身,同时也关涉可以联合起来一起争取公平的群体。这些不同的声音不仅代表着需要被正名和重视的领域;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对传统的知识、伦理、政治理论等基础观点进行了质疑和修正。在这样的质疑和考察中,通常的认识论、社会学、科学技术等表面上的公正客观性显现出权力、社会力量和处于不同位置的个体的参与和运作;也正是在这样的显露下,每个个体,包括各个性别、阶级、种族、年龄、身体状况的人都应该参与并承担起认知责任和伦理责任,为了使共同生存的世界变得更好而付出自己的行动。
三、对女性主义哲学经典的重新解读
在女性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玛丽·沃夫斯通克拉夫特、西蒙·德·波伏瓦、苏珊·奥金、朱迪斯·巴特勒等著作因为新颖的观点和有力的论证成为女性主义哲学的经典作品。对于这些著作的重新解读不仅对于厘清她们的思想非常重要,更能从她们的思想中汲取新的观点和内容,与当代问题的结合使她们的作品呈现出新的色彩。
波伏瓦的《模糊伦理学》[26]《第二性》[27]在发表后近70年中一直被不断地引用和解读。斯蒂芬妮·里维拉·贝鲁兹(Stephanie Rivera Berruz)认为《第二性》为作为“他者”的女性的生活体验作出论证,但因为波伏瓦的论证依赖于种族和性别压迫之间的对比,这种压迫通过黑人白人的二元对立得以理解,因而这个框架的结果就是种族和性别范畴的十字路口的身份无法被感知。她发掘波伏瓦著作的空白,使有色女性遭受的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得以显现。正是因为《第二性》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具有权威性,所以女性主义要负责任地使用它,就必须处理这个缺点[28](PP 319-333)。伊恩·莎莉文(Ian M.Sullivan)则将波伏瓦的思想与儒家角色伦理相结合,借助波伏瓦关于模糊性的论证来重新建构个体的关系性角色。儒家伦理认为个体始于与他人的依赖关系,并且通过加强和扩展这种关系而得以完善为独特的个体。莎莉文澄清,儒家思想中的个体并非社会关系的总和或者各种角色的核心自我,而是如同波伏瓦的模糊性概念所认为的,个体既承担社会角色,同时也是独特个体。这种重构有助于个体更多地注意到伦理以及政治层面的家长制统治以及个体教化过程中的压迫。它有助于将儒家角色伦理发展为人类繁盛的现代愿景,适应女性主义转变的需要[29](PP 620-635)。里奥尔·莱维(Lior Levy)关注波伏瓦独一无二地将儿童看作一种哲学现象学的思想。在《模糊伦理学》和《第二性》中,波伏瓦考察了儿童和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考虑这种关系在主体发展之中的作用。莱维注意到波伏瓦前后期思想的转变:前期将儿童看作缺乏道德自由、并不具有充分统治权的个体,而后期认为儿童如同成人一样自由。而当儿童并不完全拥有或者实践自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处在不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位置,而是因为各种社会制度阻碍了他们。后期立场对于将儿童看作自由场地的现象学论证是非常有用的,它成为重新思考人类存在的短暂性和生命期限中人类主体本质的哲学现象学的重要来源[30](PP 140-155)。
Hypatia杂志在2016年第3期特别设立了一个专栏来讨论苏珊·奥金的《公平、性别和家庭》[31]。如同鲁斯·阿贝(Ruth Abbey)所说:“有关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和公正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生活中其他领域的应用依然被很多现代思想家所忽略”[32](PP 636-637),这凸显出重新解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布鲁克·阿克力(Brooke A.Ackerly)对奥金的“家庭”概念进行了澄清:这里的“家庭”并不指称具体的家庭,性别不公在社会中以复杂的和强制性的方式与其他形式的不公一起发挥作用[33](PP 638-650)。麦克乐·弗格森(Michaele L.Ferguson)同意阿克力的观点,她提议将奥金划入激进女性主义阵列,因为奥金关注性别不公的根本原因:不公并非来自具体的实际的家庭,而是出自传统的家庭理念、私人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同时她指出奥金的论证具有局限性:不必要地采用了更为狭隘的家庭概念,高估了经济脆弱性对女性在离婚后走出婚姻的影响[34](PP 687-703)。
正因为性别不公正出自于所有的基础性结构的制度,因此性别公正,如妇女、儿童的权益就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努力,而更需要能使重叠交织的压迫的政治得以转变的性别政治。南希·希尔施曼(Nancy J.Hirschmann)也否定奥金解决性别不公的一个措施:雇主将男性工资分成两份,其中一份给予家庭主妇。这个措施实际上破坏了奥金的整体论证,分开的支票使得劳动的性别分工得到保留和维持,女性不平等的地位也得到保留和维持。她提倡婚前协议(preup)——它能够使男性认识到女性所放弃的东西,并且能使他们认识到女性没有酬劳的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和对婚姻所做出的贡献;而女性由此获得她们为共有财产所做出的贡献的社会和经济认知[35](PP 651-667)。
伊丽莎白·博蒙特(Elizabeth Beaumont)疑惑的问题是:当很多法律和政治都赞同性别平等原则的时候,在现代怎么还有如此之多的性别不公存在?她通过考察苏珊·奥金对虚假的性别公正的批判、对内隐的偏见的研究提出了法律之中的“隐形之手”,如法律在报酬和升职上的内隐性的性别歧视等。隐藏的性别倾向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个人行为形成、合法化并且掩盖了广泛的不公[36](PP 668-686)。
朱迪斯·巴特勒的“操演”以及“规则”“颠覆”“自由”等概念[37][38][39]也依然是学者关心的话题。针对一些女性主义认为巴特勒提供了一个并不充分的主体论证的观点,劳伦·思维恩·巴托尔德(Lauren Swayne Barthold)诉诸于伽达默尔的现象学为巴特勒进行了辩护。在巴托尔德看来,巴特勒对主体的社会历史性的强调类似于伽达默尔对知识的历史性质的强调,前者赋予“重复”的意义近似后者的“游戏”概念。巴特勒没有给我们提供评估这种“表演”的方法,但巴托尔德认为伽达默尔的“节日庆祝”可以被用作评估的标准:如同节日庆祝一样,胜利、统治或者将个体分离或者排除并不是充满活力的集体的目标,成功的操演也应该包含更多的人参与并保证活动的持续进行,为了促进更加包容性的集体,真正的身份应该滋养归属感[40](PP 808-823)。这种成功的标准脱离了个人的体验,而是被放置到交互主体性层面或者集体层面。阿兰特·卡拉德米尔(Aret Karademir)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在世”“向死的存在”“真”“焦虑”等观点用于解读巴特勒关于个体自由和边缘化的观点。在巴特勒看来,强制性的规则决定了什么是可理解的以及什么是适于居住和可思考的,我们的自由因此被社会文化网络限制。如同海德格尔的“焦虑”让主体从对世界的规则的习以为常中惊醒过来,从而摆脱“成为社会自动性”(social automaton),自主性地去选择成为自身,这种新的自主性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方式来攻击社会历史的固化的和具体化的规则,巴特勒的不符合规则的边缘主体对于社会来说正是“引起焦虑的实践”(anxiety-engendering practice),而无法彻底颠覆规则的(正常)主体借此看到规则是可以不同的或者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实现了自己的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自由依赖于那些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产生“焦虑”。这也就呼吁一个彻底民主的社会,它成为少数群体不断争辩与挑战社会规则的场地[41](PP 824-839)。桑那·卡尔胡(Sanna Karhu)追溯了巴特勒的“暴力”概念起源。这个概念出自于《性别麻烦》,她在书中对莫妮卡·维蒂格关于性征二分法是一种言语暴力进行解读,发展出了“性别暴力”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军事暴力以及非暴力的伦理[42](PP 827-843)。
四、总结与展望
Hypatia杂志是以古希腊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希帕蒂亚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位著名的女哲学家为了真理惨死在教徒手下。自创立之初,Hypatia杂志就一直将增进女性主义哲学和哲学多元化作为核心目标,它服务于广泛的女性研究群体、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家和对女性主义提出的哲学问题感兴趣的所有人。作为美国哲学核心期刊之一,它为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这对于哲学以及女性哲学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今,“它已经成为女性主义哲学的首要发布平台,成为其他哲学和性别研究以及女性研究期刊的模范”[43](PP 267-268)。
近期女性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趋势。首先,认识论不公以及对于这种不公的探究和纠正依然是重要话题。这是由认识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当前女性在哲学中依然受到不公待遇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知识代表权威和真理,代表了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女性所表述的事物是否成为知识,意味着它们是否能够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而在当前,女性在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劣势地位依然明显,不论在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上,还是在表述话语的被正视程度上,都呈现出“人微言轻”的势态。女性最初争取平等的选举权到如今女性关注各个领域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要成为社会共识,从而促使社会将这种公平正义付诸实践,依然需要女性为这种知识作出解释和辩护,也就从根本上需要女性成为知识的拥有者和表述者。从波伏瓦对女性在知识领域中的“他者”身份的关注,到弗里克对认识论不公的直接表述,再到从性别刻板印象以及语言使用等角度的分析,对认识论不公的分析更为具体和明确。女性争取对知识的公平参与任重而道远,对认识论不公的分析和纠正依然是未来女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
其次,女性主义哲学不断将性别维度引入新的具体领域,这不但扩展了女性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围,同时也对女性主义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和方法进行审视和扩展。在工业发展、男性统治与遭到贬低和破坏的自然的对比中,女性被隐喻为遭受损害的大地母亲,女性主义哲学对于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南希·图安娜(Nancy Tuana)和克里斯·科莫(Chris J.Cuomo)认为,虽然过去的环境研究关注了性别角色和性别劳动分工在环境变化中的影响和回应中的不同方式,但是性别公正视角在主流环境公正理论和政策中依然处于边缘化地位。她们因此用整整一期“环境变化”来澄清这个问题,关注性别与草根阶层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工作以及更高层次的国际协商与政策制订的关联,从而呼应“促进联合国框架公约以及京都协议中的性别平衡与女性参与”[44](PP 533-540)。理解环境变化中的性别维度,这种维度与社会及环境公正之间的关系,这促发女性主义哲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而女性主义哲学关于残障以及儿童的研究,对于传统哲学以及政治和伦理层面上的“主体”“依赖性”都提出了挑战。我们可以期待女性主义哲学对于传统问题(如环境及残障)以及社会热点问题(如校园欺凌)的继续关注,这种积极性和扩展性的参与对于女性主义哲学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为女性参与到正统的科学、哲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契机。
再次,直面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在当今民族、种族、经济、宗教等因素纵横交织的女性主义内部,尤其在第三波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冲击下,女性主义在应当选择何种解放道路方面面临着迷茫和选择的压力。笔者相信女性主义应该遵从面对并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策略——即使“女性”的含义是模糊的,“主体”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但在当下,女性作为“他者”的事实依然成立,在家庭、社会中一样面临着或显性或隐性的不公正,对不公的实际分析以及针对性的解决依然是必要的。即使作为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巴特勒也同样诉诸颠覆规则的边缘行为。而这种边缘行为,并非是无意识的,而是女性出于自主性的对压迫和不适的反抗,是女性主义所需要的“自我解放”。这种解放,出自积极性的意识觉醒和实际行动,需要“法律、主体意识、社会的多维度解放”[45](PP 530-546)。
对女性主义哲学发展趋势的把握,不仅为我们了解世界女性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提供全面性视野,我们也可以在这种新发展与自身情况的结合中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借鉴。第一,在儒家伦理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碰撞中澄清思想。近期的学者们不断地注意到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学的关系。凯利·艾普利(Kelly M.Epley)支持李成阳(Chengyang Li)的观点,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性。对于学者们将儒家的“礼(仪)”看作两种伦理相互区别的原因,艾普利认为关怀伦理恰恰需要采用业已被认知的“礼(仪)”来保证其顺利进行[46](PP 881-896)。李成阳则澄清了关于这两者关系的讨论的政治维度[47](PP 897-903)。这种讨论有助于澄清和继承儒家思想。第二,在东西方思想交融中寻求对实际问题的把握和解决。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实际,女性正处于传统儒家思想和现代问题的交错裹挟之中,这就使得我们面临的不公正和西方学者所关注的不公正不同。如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更多提倡女性扮演“贤妻慈母”的角色,而在当前市场经济情况中,女性需要处理更为严重的工作和家庭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求职时更易遭受隐性或显性的不公正待遇;当前的“二孩”政策也对女性和社会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克莱因盖尔德和安德森将公正引入家庭的观点[25](PP 320-336),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但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对西方学者“法律”和“公正”等的观点并不能生搬硬套,“孝道”“家和”等传统文化依然为我们所秉承。正如上文所说,中国女性在吸收西方学者理论和观点的同时,要强调和立足于我们的实际情况,面对和解决我们的具体问题。第三,在近期杂志中,只有一篇关注中国女性的文章。通过对女性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的分析,王奕轩认为户口和性别或者单一性地、或者依次性地、或者共同性地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的就业[48](PP 862-880)。中国女性整体境况并没有得到哲学层面很好的关注。在未来,我们需要努力发出中国女性的声音,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循环中不断地追求和参与“公正”。
[1]M.Fricker.EpistemicInjustice:PowerAndTheEthicsofKnowin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G.S.Holtzman.Rejecting Beliefs,or Rejecting Believers? On the Importance and Exclusion of Women in Philosophy[J].Hypatia,2016,31(2).
[3]R.Tuvel.Sourcing Women’s Ecological Knowledge:The Worry of Epistemic Objectification[J].Hypatia,2015,30(2).
[4]E.Davis.Typecasts,Tokens,and Spokespersons:A Case for Credibility Excess as Testimonial Injustice[J].Hypatia,2016,31(3).
[5]R.Mckinnon.Stereotype Threat and Attributional Ambiguity for Trans Women[J].Hypatia,2014,29(4).
[6]R.Kukla.Performative Force,Convention,and Discursive Injustice[J].Hypatia,2014,29(2).
[7]S.J.Kapusta.Misgendering and Its Moral Contestability[J].Hypatia,2016,31(3).
[8]J.M.C.Kwong.Epistemic Injustice and Open-Mindedness[J].Hypatia,2015,30(2).
[9]K.Frost-Arnold.Imposters,Tricksters,and Trustworthiness as an Epistemic Virtue[J].Hypatia,2014,29(4).
[10]K.Intemann,E.S.Lee.et al..What Lies Ahead:Envisioning New Futures for Feminist Philosophy[J].Hypatia,2010,25(4).
[11]M.Shildrick.“Why Should Our Bodies End at the Skin?”:Embodiment,Boundaries,and Somatechnics[J].Hypatia,2015,30(1).
[12]L.Davy.Philosophical Inclusive Design: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the Limit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in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y[J].Hypatia,2015,30(1).
[13]L.Back.Private Dependence,Public Personhood:Rethinking“Nested Obligations”[J].Hypatia,2015,30(1).
[14]C.Mills.The Case of the Missing Hand:Gender,Disability,and Bodily Norms in Selective Termination[J].Hypatia,2015,30(1).
[15]A.Baril.Needing to Acquire a Physical Impairment/Disability:(Re)Think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rans and Disability Studies through Transability[J].Hypatia,2015,30(1).
[16]L.W.Kane.Childhood,Growth,and Dependency in Liberal Political Philosophy[J].Hypatia,2016,31(1).
[17]R.Johnston.Affirmation and Care:A Feminist Account of Bullying and Bullying Prevention[J].Hypatia,2015,30(2).
[18]H.Grasswick.Climate Change Science and Responsible Trust:A Situated Approach[J].Hypatia,2014,29(3).
[19]K.P.Whyte.Indigenous Women,Climate Change Impacts,and Collective Action[J].Hypatia,2014,29(3).
[20]A.Neimanis,RL Walker.Weathering:Climate Change and the“Thick Time”of Transcorporeality[J].Hypatia,2014,29(3).
[21]J.Buck,AR Gammon,CJ Preston.Gender and Geoengineering[J].Hypatia,2014,29(3).
[22]R.Lee.Feeding the Hungry Other:Levinas,Breastfeeding,and the Politics of Hunger[J].Hypatia,2016,31(2).
[23]Cutas,A Smajdor.Postmenopausal Motherhood Reloaded:Advanced Age and in Virto derived Gametes[J].Hypatia,2015,30(2).
[24]S.J.Khader.Development Ethics,Gender Complementarianism,and Intrahousehold Inequality[J].Hypatia,2015,30(2).
[25]P.Kleingeld,J.Anderson.Justice as a Family Value:How a Commitment to Fairness is Compatible with Love[J].Hypatia,2014,29(2).
[26]S.D.Beauvoir.TheEthicsofAmbiguity[M].New York:Citadel Press,2000.
[27]S.D.Beauvoir.TheSecondSex[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7.
[28]S.R.Berruz.At the Crossroads:Latina Identity and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J].Hypatia,2016,31(2).
[29]I.M.Sullivan.Simone de Beauvoir and Confucian Role Ethics:Role-Relational Ambiguity and Confucian Mystification[J].Hypatia,2016,31(3).
[30]L.Levy.Thinking with Beauvoir on the Freedom of the Child[J].Hypatia,2016,31(1).
[31]S.Okin.Justice,Gender,andtheFamily[M].New York:Basic Books,1989.
[32]R.Abbey.Susan Okin’s Justice,Gender,and the Family:Twenty-Five Years Later[J].Hypatia,2016,31(3).
[33]B.A.Ackerly.Raising One Eyebrow and Re-Envisioning Justice,Gender,and the Family[J].Hypatia,2016,31(3).
[34]M.L.Ferguson.Vulnerability by Marriage:Okin’s Radical Feminist Critique of Structural Gender Inequality[J].Hypatia,2016,31(3).
[35]J.Hirschmann.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Split Paycheck[J]Hypatia,2016,31(3).
[36]E.Beaumont.Gender Justice v.The“Invisible Hand”of Gender Bias in Law and Society[J].Hypatia,2016,31(3).
[37]J.Butler.BodiesThatMatter:OnTheDiscursiveLimitsofSex[M].New York:Routledge.1993.
[38]J.Butler.GenderTrouble:FeminismandTheSubversionofIdentity[M].New York:Routledge.1999.
[39]J.Butler.UndoingGender[M].New York:Routledge.2004.
[40]L.S.Barthold.True Identities:From Performativity to Festival[J].Hypatia,2014,29(4).
[41]A.Karademir.Butler and Heidegger:On the Relation between Freedom and Marginalization[J].Hypatia,2014,29(4).
[42]S.Karhu.Judith Butler’s Critique of Violence and the Legacy of Monique Wittig[J].Hypatia,2016,31(4).
[43]S.J.Scholz,S.Wilcox.Editors’ Introduction[J].Hypatia,2014,29(2).
[44]N.Tuana,C.J.Cuomo.Climate Change——Editor’s Introduction[J].Hypatia,2014,29(3).
[45]D.Coole.Emancipation as a Three-Dimensional Proces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J].Hypatia,2015,30(3).
[46]K.M.Epley.Care Ethics and Confucianism:Caring through Li[J].Hypatia,2015,30(4).
[47]Chengyang Li.Confucian Ethics and Care Ethics: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a Scholarly Debate[J].Hypatia,2015,30(4).
[48]Yixuan Wang.The Mystery Revealed——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Black Box:An Analysis of Female Migrant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n Urban China[J].Hypatia,2015,30(4).
责任编辑:绘山
New Development in Feminist Philosophy:A Review of Recent Three Years’ Research Published inHypatia
LI Rui
(School of Marxism,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Hypatia;feminist epistemology;epistemic injustice;feminist philosophy
As the most famous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Hypatiacovers almost all the cutting edge research in feminist theory.The new trend in feminist philosophy is embodied in three areas: Feminist Epistemology,specific fields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 of Feminist theory.A review of the recent papers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could provide us an opportunity to ac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developments.It is very helpful for us to identify new directions for our further research and improve our research methods.
李蕊(1986-),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性别与社会公正。
B089
A
1004-2563(2017)03-01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