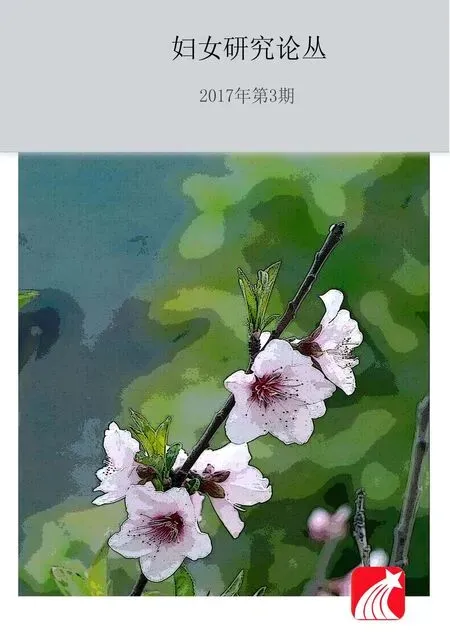从社会活动家到战争协助者*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的中国战场慰问
2017-04-05童晓薇
童晓薇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深圳 518060)
从社会活动家到战争协助者*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的中国战场慰问
童晓薇
(深圳大学 外国语学院,深圳 518060)
日本;女作家;战场慰问;战争协助者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诸多女作家响应日本军方的要求,奔赴中国各地战场慰问劳军,回国后提交战地报告,四处巡回演讲,在宣扬日本的侵略国策、激励日本民众投身战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助者。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文化界对她们的战争协助行为缺乏必要的反思,对她们的责任追究被消解于对其女性身份的强调中,从而割断了对她们从走在时代前列的社会活动家到战争协助者的反思。今天我们应该在反思的前提下,在战争协助者的框架内重新审视她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一面历史之镜。
一、侵华战争期间女作家战争协助状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号召整个文化界为战争国策服务,于1938年组建了一支由作家、诗人、画家等组成的“笔部队”,开赴中国战场慰问劳军,宣扬日本侵略“国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以“集结全日本文学者的力量,确立彰显皇国传统与理想之日本文学,辅佐皇道文化之宣扬”[1](P 88)为目的,组建了“文学报国会”,建立了一支规模更为庞大的帝国宣传部队,成员一度多达四千余人。参加宣传部队的作家有的亲自从军打仗,有的奔赴亚洲各个战区慰问劳军,有的则在后方进行精神支援,生产了大量反映战争的文学。
对这支帝国宣传部队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学者樱本富雄等人对这支部队的组建背景、经过、成员和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梳理[2]。高崎隆治从作家的战地报告、纪实文学入手,深入研究了文人与战争、军队的关系。国内学者王向远等人则对“笔部队”的存在进行了揭露,指出笔部队的作家文人担当了侵略战争的谋士和鼓吹手,他们“炮制”了数量庞大的战争文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侵华“国策”的施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3]。
在这支庞大的宣传部队中,活跃着很多女作家。1938年武汉会战中派遣的第一批“笔部队”中就有两位女性:林芙美子和吉屋信子。她们随军赴中国汉口视察劳军,被称为“笔部队”中的“两点红”。王向远等也特意提到她们,尤其是对林芙美子在战争中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批判。但实际上,武汉之行并不是她们二人第一次到中国战场劳军慰问。侵华战争期间,接受日本军部委托到中国各地战场劳军慰问的女作家也远不止她们二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吉屋信子就曾作为《主妇之友》的特派员到达中国华北战场和上海;同年林芙美子也去了战火中的上海与南京战场;1941年佐多稻子和林芙美子去了中国东北战场;同年真杉静枝、円地文子、长谷川时雨等女作家同赴中国广东战场劳军;1942年佐多稻子与真杉静枝到达中国华中战场最前线……。而更多的女作家则活跃在本土后方。1933年1月长谷川时雨协同岡本佳乃子、平林泰子、佐多稻子、林芙美子、野上弥生子、真杉静枝、吉屋信子、森茉莉、与谢野晶子、平塚雷鳥等女作家组织“闪耀”会,创办宣传册《闪耀》。这份原本旨在谋求女性进步发展的杂志,在侵华战争爆发后大变身,成为宣扬日本侵略国策的一个重要阵地。1939年“闪耀会”成立了协助战争的“闪耀部队”,与军方积极配合,除了从军奔赴亚洲各战场外,女作家们还主持参与面向军人遗属、伤残官兵等的慰问活动,并特意企划出版了三册集女作家、画家之全力完成的《闪耀慰问文集》作为给陆军、海军前线士兵的新年礼物。她们利用女性、作家、母亲、妻子等多重身份,利用女性文学特有的感性与细腻,在侵华战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支强有力的宣传队伍。
战后,日本文化界曾展开对作家战争责任的揭发和追究,希望严惩战争期间负有重大且直接责任、将日本文学引向堕落的领导者,以期唤起全体作家的反省。但这场反思和责任追究运动很快流变于“责任追究者的资格追究”问题而不了了之。而在政治思想界进行的战争责任追究,也只是把这些作家划分到“一般国民”的道义责任的追究。正如王向远所指出的,战后日本文化界对作家战争责任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追究,绝大多数文人对自己应负的战争责任缺乏严肃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导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对这支帝国宣传部队的漠视与失语[3]。
其中女作家们更是长期被作为战争受害者来看待。战争是男性发动的,是男性权力相争的结果,女性都是身不由己,她们与广大日本妇女一样都是受害者。这种观点不仅是战后日本文化界的普遍共识,也是在战争期间“大显身手”的一些女作家在战后逃避责任的托辞。吉屋信子在战后便避重就轻,强调自己的无力、无能和无奈,把战争协助问题消解成自己与林芙美子之间争强好胜的个人问题[4](P 150)。佐多稻子在1984年被追问到自己的战争协助问题时,给出的解释依然是含混不清的:“过去‘反对战争’的话是难以启齿的。(中略)如果从‘女性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立场来看战争中女性的行为的话,多数女性是不自觉被动员到战争中去发挥作用的。……现实生活中,是会被各种事情卷进去的。”[4](P 102)
佐多稻子等人的“身不由己”说放在普通人身上没有问题,但作为女作家开脱罪责的借口却是很难成立的。也早有批评家指出,吉屋信子等人在战后塑造的自己于战争中的形象都是被动的、非当事人性质的、矮化的与缺乏客观性的[4](PP 150-151)。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作家们都是自愿或者说相当情愿地接受军部的邀请奔赴中国各地战场的。1938年日本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确立“国论统一”“举国体制”,开启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效法“一战”时期德国的做法,将征用、派遣文化人随军或赴战场考察作为战时国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作家而言,率先顺应国策积极响应的不是女作家,而是男作家。由新闻社和杂志社派遣到中国战场打头阵的是吉川英治和林房雄等人,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7-8月,他们随军去了中国大陆。男作家在战争中的“先行”,为女作家提供了示范的同时,也激发了她们的斗志。作为一群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谋取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正是她们一直孜孜以求的事业。
早在1911年,一群女作家就集结一起创办了一份面向女性的《青鞜》杂志,平塚雷鳥在创刊号上写下了一段可谓惊世骇俗的话:
初始,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
现在,女性是月亮,是依靠他人生存,依赖他人的光发光的
如病人脸般苍白的月亮。
终有一天,女性将重新成为太阳,
成为真正的人[5](P 33)。
由此掀起了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序幕。女作家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她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学历者,蔑视传统的“良妻贤母”思想,要求享有与男性平等的人权,主张提高女性地位,让女性走出家庭,发挥女性特有的天赋与才能。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个人生活上,她们都大胆挑战传统世俗道德,一度被称作“新女性”。作为女性中的精英,她们既有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诉求,又有一种高度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侵华战争爆发后,她们和其他诸多女性社会活动家一样,将参与、协助战时体制作为提高女性地位、争取女性权益的绝好时机,在致力于男女共同协作的立场上积极投身于协助战争的运动中。换言之,正是因为长期被排斥在“男性权力”之外,她们急于接近“权力”中心,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归属感。“知识女性第一次听到政府当局将自己提升到代表国家的地位上非常感动,为女性地位以及女性意见能反映在政治上的时代的到来而喜悦”[6](PP 114-115)。另一方面,能被军部或各大杂志社、新闻社看中的作家都已具有相当名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近代日本,女性写作虽然十分活跃,却没有得到主流文坛的足够认可,能够跻身名作家行列,与男性并肩为国效力,对女作家来说恐怕已是巨大的光环。因此,她们都是抱着热切的心情期待着中国战地之行。林芙美子出发前表达她迫切的心情说道:“我想去。自费也想去”,在得知第一批“笔部队”里有自己和吉屋信子两个女性时,喜出望外,鼓励自己一定“努力完成使命”[7](PP 224-225)。
同时由于女作家对男权社会的挑战从未逾越天皇制,对天赋皇权的精神构造本身没有提出质疑,战争爆发后,她们曾唾弃的“良妻贤母”成为她们进击社会、建构战时女性与男性的社会角色分工的切入点。那就是重新强调女性的“母性”和“妻性”,在国家层面上解读“母性”的意义,通过母性的发扬将家族-国家相连,让女性重新成为太阳。日本天皇的皇神是母神天照大神,天照大神与天皇自古形成了母亲-儿子关系的母性原理深植于日本人精神意识内层。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外表现出男性化军事国家态势”[4](P 55),在深层给予支持的正是来源于天皇制母性原理的精神动力。一方面,政府向广大妇女鼓吹圣战,宣扬战时国策,要求日本的母亲、妻子、女儿都应为圣战而奉献。1938年,应军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设置厚生省,连续颁布《母子保护法》《保健法》等一系列法令,加强对女性对母亲的保护,以多生多产,确保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包括女作家在内的女性活动家们从内部进一步阐释母性与国家的结合。早在1930年,高群逸枝、平塚雷鳥等原《女人艺术》系的“新女性”们创刊《妇人杂志》,提出“否定强权主义”“清算男性”“女性新生”三大口号,明确女性排除一切强权、清算男性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母性抬头”。高群逸枝说:“母性意味着弱小、温柔的时代必须过去,今天,母性才是最果敢、最顽强的。”[8](P 142)通过对母性力量的强调,阐发女性特有的“天赋”,瓦解家庭-社会中男性的主体地位,将女性推到社会舞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37年侵华战争爆发后,女作家纷纷奔赴中国战场慰问劳军,尝试通过发挥母性、将女性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
二、女作家的中国战场慰问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诸多女作家到中国各地前线慰问劳军。除了个别自主前往外,她们一般肩负媒体特派员或从军作家身份,有经费支持,有军官陪同,回国后应要求发表相关从军记和战地报告,并四处汇报讲演。
1937年8月,吉屋信子作为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大的妇女杂志《主妇之友》的皇军慰问特派员奔赴中国华北战场。当月25日,她从羽田机场出发到达天津,在拜访了日本驻天津司令部后,吉屋信子参观了被日军轰炸得满目疮痍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市政府,慰问了天津日本陆军卫戍医院的伤残官兵,并去了战火中的北平与通州。1938年8月,吉屋信子再次作为《主妇之友》特派员前往中苏边境的张鼓峰战场视察劳军,参加了张鼓峰阵亡士兵遗体运送仪式。回国后随即参加第一批“笔部队”,加入“海军班”,以从军作家的身份奔赴中国上海、武汉战场,视察并慰问了武汉会战中的日军将士。
吉屋信子的从军记和战地报告主要发表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女性杂志《主妇之友》上,如《去到战火中的华北现场》(1937年10月)、《战火中的上海冒死行》(1937年11月)、《汉口攻略战从军记》(1938年11月)。1937年10月20日与22日,吉屋信子分别在东京和大阪做了两场汇报讲演。讲演会由《主妇之友》主办,听众只限女性。会上,吉屋信子用非常接地气的语气向听众们讲述了自己战场慰问的经历,听众发出26次笑声。“笑点”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吉屋信子对中国话的体会,她说:“爱这个字,‘支那’语和日本语的发音和文字都一样。不爱这个词在‘支那’语中就直接写成‘不爱’(笑声)。……因爱这个字,我就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国民,而且是邻国,‘支那’为什么就不爱日本呢?(笑声)……希望‘支那’能早日停止‘不爱’,成为我们的亲善国,让战争早日结束。(鼓掌)”[9](P 214)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并对南京及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大屠杀。当月,林芙美子作为《每日新闻》的特派员奔赴上海与南京。在南京光华门前,她举着日本军旗留影以庆祝日本军队攻陷南京。1938年8月,她参加“笔部队”陆军班飞往上海,随即脱离陆军班开始单独行动,乘坐海军飞机飞往南京,乘船去到江西九江,参观九江前线并慰问了九江兵站医院后返回南京休整。10月17日,她再次飞往九江,乘坐小型运输船到达湖北武穴,从武穴与当地日军快速部队一起行军数日进入战火中的汉口。林芙美子作为第一位进入汉口前线的女作家在日本国内引起极大轰动。当年10月29日的《朝日新闻》上刊登文章《笔部队的女丈夫 率先进入汉口 勇士也惊叹的林芙美子女士》称:
林氏的勇敢与谦虚让全体将士尊敬和感激。她行进在尘土大雨中,风餐露宿,乘坐的车随时有可能压到地雷。林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军的。……虽然她晚了一天入城,但也是文人中第一位进入汉口的。林氏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10](P 48)。
30日,《朝日新闻》晨刊刊登林芙美子发自汉口的纪事,三行大大的标题:女子我一人/热泪入汉口城 林芙美子记/艰苦亦如梦/美丽城镇 堂堂之皇军[7](P 237)。
高崎隆治明确指出: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作为女作家协助战争的起点,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11](PV)。正是在她们的激励下,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加入到中国战场慰问的队伍。林芙美子发表的从军记和战地报告主要有书信体的《战线》(1938年12月朝日新闻社)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1939年《妇人公论》新年特别号)。林芙美子脱离陆军班单独行动,曾遭到同行男作家的不满。虽然与她同行的日军部队不是作战部队,但孑身一人,没有了作为陆军班随军作家的待遇,并且一路行进战地十分艰苦,还有遭遇流弹的危险。她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打算不得而知,但她作为一名女性和女作家的“野心”是可见一斑的。在《北岸部队》中她说:“我想作为一名日本的女性,把日本军队战斗的样子深深烙印在我的生涯之眼上。……即便被炮弹击中,我都无所谓。热爱国家的激情,与我而言,是一个大大的青春。”[7](P 46)
1941年,佐多稻子作为朝日新闻社组织的小说家慰问部队的一员到中国东北战场慰问。1942年5月初至6月下旬,她和真杉静枝以新潮社《日出》杂志特派员身份再次奔赴中国各地战场。5月8日她们乘飞机飞往上海,11日到达南京慰问总司令部、视察战场,参观了汉口、杭州、上海等地的军事据点、陆军医院,还顺便去了苏州和鸦雀岭,甚至到了当阳与宜昌对岸的最前线馒头山[4](PP 222-223)。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为切断武汉周围与中原的交通,发动了“宜昌作战”,并于1940年6月攻陷宜昌。宜昌沦陷后,国民党军队几次反攻未果,退距三峡入口处石碑防守,凭借长江天险与日军对持三年之久,其间长江两岸发生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佐多稻子一行进入宜昌后,看到街头空无一人,扬子江边也没有任何中国人居住的痕迹,“惟有夕阳空虚地洒在江面上”[12](P 60)。她们听到了宜昌对岸馒头山阵地的交火声,深切体会到了战争最前线的紧张和不安感。
1942年5月19日佐多稻子与真杉静枝回到南京去了杭州。此时正是浙赣会战的紧张时期。5月中旬,日军对国民党第三战区发动进攻,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反击。5月20日,佐多稻子与真杉静枝在军方安排下搭乘军用飞机飞越钱塘江盘旋在浙江上空,在空中视察了燃烧中的东阳(金华)。《日出》杂志打出大标题称她们开创了女作家乘坐军用飞机在空中视察交战中的战场的先河。日本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轰动一时,两人回国后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她们的战地慰问报告大都发表在新潮社月刊《日出》上,如佐多稻子的《最前线的人们》、《华中战场的士兵们》,真杉静枝的《在死城——浙东作战从军》,等等。1942年6月26日始,在军部授意下,《都新闻》召集佐多稻子、真杉静枝、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等人举行了八次座谈会,听取她们战场慰问的感想。佐多稻子第一个发言,借用在宜昌最前线时一位军官称赞她们“作为一个女性能到距离重庆最近的地方是完全可以大大骄傲的”的话来表达自己对去到中国战场的喜悦以及对发挥女性力量的迫切心愿[4](P 219)。
在吉屋信子等人的影响下,女作家的战地慰问视察蔚然成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佐多稻子、真杉静枝等人为首的更多女作家奔赴南洋各地战场。与被征用的送往东南亚各地的男作家不同,女作家并非被强制的,她们之所以甘冒危险应军部要求去到南方,“是因为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有中国战场的慰问经历”[11](Pvi)。女作家们的战场慰问是日本军方为实现战时的举国体制、扩大侵略的一个重要策略,目的是利用女作家的女性+作家的双重特质,安抚前线士兵,给士兵鼓气,通过她们的叙事让国内更多女性看到战场上日本军人的英武和艰辛,看到“敌人”的残忍和野蛮,从而激发女性的妻性、母性,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良妻贤母”的框架下,投身于支持、协助战争的运动中。在慰问过程中,她们受到了军方的各种优待,所到之处都有军官随行。佐多稻子和真杉静枝更是乘坐当时日本最大的道格拉斯飞机从羽田机场飞往上海的。这在燃料缺乏的战时是相当奢侈的做法。用高崎隆治的话说,在那个时代,乘坐这样大型民用飞机从东京飞到上海,只有将军级的军人或超高级军人家属才有可能做到[11](PP 98-99)。可以说,女作家们的战场慰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与军方的“共犯”关系。
三、女作家战地报告的特点及影响
当时日本军方期待的作家的战争报告课题主要有这样几项内容:(1)前线、日本军的状况;(2)战况、皇军的胜利、优越性宣传、煽动对敌国的报复;(3)当地人的欢迎、打消他们的反抗;(4)恢复和平、强调友好与共荣以美化战争目的[4](P 146)。最终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女作家的“讲述”宣扬战争思想,将后方与前线连接一体,巩固战争体制。女作家们的战地报告基本在此框架下完成。虽然她们到了不同的战场,且性格迥异,写作风格千差万别,提交的报告各有侧重,但她们的战场讲述表现出的诸多共性使她们的战场慰问形成了一个整体,极大地满足了军方的要求,在“使战争正当化、向军队传递慰问与感谢之意、向女性读者传达战场情况、将前线与后方融合一体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4](P 145)。
首先,她们都相信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正义的,是“圣战”,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贫穷和灾难、谋求与日本的共同繁荣而发动的。因此,尽管她们目睹了残酷血腥的战场、伤痕累累的士兵、空寂无人的城镇,体会到了日本士兵远离故土穿梭于异国的枪林弹雨中的寂寞和悲怆,却都没有进一步思考这场战争的性质,质问发动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也就是说,自始至终都缺乏“侵略战争”的视点。这对奉命出征的她们来说,也是不能逾越的政治前提。另一方面,能作为女性代表进入“男性话语权力”空间为国效力所营造的巨大光环,也使她们毫不怀疑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报告中,她们无一例外地奉日本军队为正义之师,为日本军队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当吉屋信子在北平为攻城日军与宋哲元部队的交火歌颂“民族的荣光”,佐多稻子在浙江热泪盈眶地目送夕照下进军在“敌区道路”上的“我日本军队”,林芙美子进入汉口高喊“日本的母亲哟、妻子哟、兄弟姐妹、恋人哟,现在,你们的人,以骑虎之势向汉口大进军!”[7](P 237)时,她们的心情应该是一样的。在侵略视点缺失前提下展开的战地观察其主题必定过于简单,视线过于单一且居高临下,缺少多维观察和思考。面对中国平民遭受的苦难,她们虽然同情甚至于心不忍,但都没有把中国人的苦难与战争本质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怀疑日本军队的正义性。1937年8月27日,吉屋信子一行进入天津。当年7月底日军对天津市区以及周边地区实施了反复轰炸,造成大量房屋被毁和燃烧,2000余人在轰炸中身亡,10万余难民无家可归。距离大轰炸仅一个月时间,吉屋信子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看到,但她在战地报告中却这样写道:“无论哪处被空炸的地方,都是有军事上正当之理由才实习的,其证据就是,我军准确无比的爆击没有伤到良民房屋的一片砖瓦。”[9](P 28)站在被日军炮弹炸得面目全非的南开大学校园里,吉屋信子感到阵阵冷意。作为知识分子,她尊重知识,尊重大学,也曾反问过自己:如果是日本的帝国大学被炸成这样,自己还能如此笃定地站在这里吗?片刻犹疑之后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即日军轰炸南开、轰炸天津都是迫于无奈的正义之举,张伯苓应该看到日本的诚意[9](P 25)。
1942年佐多稻子和真杉静枝在杭州乘坐军用飞机盘旋在浙江上空,起飞不久她看到了下面残破的钱塘江大桥。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主持修建大桥的茅以升奉命炸掉了这所竣工通车仅两个月的大桥。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佐多稻子却避重就轻地说道:“蒋介石造的这个铁路,在战祸中被毁,三分之一坍塌落入河中。但是,现在被我军修复了……。”[13](PP 34-35)同样,在宜昌,真杉静枝惊讶在这样的内地,还有如此繁华的城市。“这个都市,……作为四川省所产物资的贸易市场,战前非常兴旺。现在在我军驻扎部队本部的努力下,正在逐步恢复秩序。”[14](P 76)大桥因何而炸,宜昌的兴旺是被谁破坏又是如何破坏的,佐多稻子们不愿进一步追问和思考。她们强调日军在中国大陆上的建设性和开拓性,为日军的行为进行辩护。在钱塘江大桥边的萧山义桥镇,佐多稻子看到这个曾充满生机的小镇已如鬼城,房屋倒塌,有的屋里还有遗弃的尸体,但她并未在意。她对义桥镇的描写好比一组人物照的拍摄,主题是为突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日本将士仍保持的人情之美,在对日军将士的人情美的强调与称赞中,“敌国”平民遭受的损失被虚化,日军的暴行淡出画面。
对战争“正义性”的坚信不疑导致她们对战争本身的思考非常有限,并且在有限中增添了不少天真的成分。在祈愿战争早日结束、和平早日到来时,她们都认为一切取决于中国人。中国人要摆脱悲惨的命运,最好的做法就是尽快向日本投降,由日本来建立一个和平共存的社会[9](P 93)。也就是吉屋信子在讲演中提到的“爱”与“不爱”的问题。
其次,她们赞叹日本兵的英勇,把日本将士的英勇渲染成武士道精神,在“圣战”的框架下对前线战士的“斗魂”“友情”和“男人气魄”大写特写,将士兵们的牺牲与祖国、家乡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他们的神圣和正义。用一种浪漫主义情怀去虚化战争的残忍。在女作家集结的宣传杂志《闪耀》1937年10月号上,著名作家岡本佳乃子特意题写了一篇名为《寄予我军战士的话》的文章,用相当煽情的语言写道:
日本男子成为出征军人将士之际,我感觉他们俨然是神。
全身发光。万众光芒汇集一起,向那唐土之野庄严进发。
此刻,那迎着日本的秋风飘动着鬓毛准备出征的战马,也散发着神的光芒。
……[4](P 182)
这篇文章得到了平塚雷鳥的高度评价,认为岡本佳乃子的文章道出了所有后方日本女性的共同心声,“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皇军将士敬奉天皇之命,超越生死,已是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宗教的绝对境地[4](P 183)。
这种在天皇制框架下将士兵“神格化”的浪漫主义在女作家们的报告中得到延续。在宜昌看到山丘上站岗的日军哨兵,真杉静枝对这样一个战场上再普通不过的场面如此写道:“看到那夹着枪,一个人融入于蓝天之中,听着遥远异乡的风声四处守望的(哨兵)的样子,我突然有种神圣感。”[14](P 70)吉屋信子在参观南开大学时,一位伍长向她津津乐道自己在战场上如何杀中国人,她却被他胡子拉碴、黝黑瘦削的脸吸引住了,想起来日本战国时期的“武神”,便形容这位伍长说:“是战场的勇士……很像加藤清正。”[9](P 24)林芙美子在行军汉口的路上作诗说:
我热爱士兵
一个命运
在转瞬之间
呼呼飞过
在战场上的士兵头上
生命、生活、生涯
灿烂间玉碎
有时那般的壮烈
士兵们
超越那样的命运
超越命运的感伤
日复一日前行
默默地,对战场的“绝对”充满自信
我热爱士兵
吹走所有的姑息之念
鲜血洒在荒凉的土地上
洋溢着对民族之爱的青春
肩扛旗帜默默进军[7](PP 172-173)
对将士的记叙是女作家战地报告的重点。相比部队的运作、战斗的状况,她们更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她们充分调用其敏感、细腻、多情的特质观察士兵的容颜,倾听他们的声音,表现他们的坚韧、辛劳,强调他们的温情、慈爱、绅士,在神格化士兵精神的同时,用母亲、妻子的眼光审视他们,将他们还原成普通的父亲、丈夫、儿子。通过“母性”与“妻性”,在情感与精神层面上将前线与后方联系在一起,激发起日本国内广大妇女的共鸣。这是男作家战地报告难以企及的。同时,她们从自己的见闻出发,反复敬告国内女性要发挥女性的作用,与前方男子共同努力。林芙美子在汉口从军归国后的演讲中便特别强调:这次从军我最深切感觉到的是前线的士兵们对“爱”的饥渴,母亲的爱,孩子的爱,尤其是故国女性的爱,……特别希望日本的年轻女性们,能更接近战区,在只有女性能做到的照顾慰问伤病及其他领域积极发挥作用,在这个国家的重大时期燃烧爱国热情[7](P 239)。佐多稻子也在报告中多次提及:“一想到我们女性的伴侣——这么多的男子在战场上超出我们想象的辛劳,就觉得‘内地’的困苦太过温和。牵挂战地的艰辛,在后方努力,这种‘觉悟’应该已经刻在我们女性心中,成为我们每日的动力。”[13](P 58)
第三,她们通过对中国士兵和中国平民的漠视或他者化,增强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主体性。同时,她们采用仰视和俯视的双重视角审视日本人和中国人,面对日本人和日本兵时,她们的视角是仰视的,并且充满想象力,与讲述“支那人”和“支那兵”时采用的俯视视角的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行进在扬子江北岸的林芙美子感叹日本每个士兵都挂念着故乡,经常思念故乡直到堂堂正正、壮烈无比地战死,他们是好丈夫、好父亲、好哥哥、好弟弟。但看到同样也应该是丈夫、父亲、兄弟的中国士兵和中国士兵的尸体,她只觉得非常不舒服[7](PP 165-166),拒绝对中国士兵身份的多重认知,只是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在各地战区医院里工作的日本女护士,女作家们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和称赞,在护士们切实的报国行为面前抬不起头,感到自身的渺小[9](P 31)。在“敌国”女性面前,她们的态度则变得十分微妙。在汉口俘虏收容所里,佐多稻子见到了一位被俘的中国女军医。这位军医被俘时怀有8个月身孕,狱中生产后百天婴儿身亡。面对这位经历了丈夫战死、孩子夭折的中国女性所经历的苦难,佐多稻子没有尝试从女性的立场上解读她大大咧咧表象后的深层心理,更没有由此想象战争带给女性的灾难,反用几近挖苦的语气调侃她“没有母性”[13](PP 71-74)。如果说女作家在男性中心的国家中还处于弱者地位的话,在中国女性面前她变成了凌驾于“弱者”之上的“强者”。
报告中,她们有意无意地设置了日本兵和中国兵之间的二元对立:
日本兵(日本人)=清洁、善良、仁义、勇敢、友爱
支那兵(支那人)=肮脏、凶残、不仁、懦弱、冷漠
以此突出日本军队对中国战争的光荣和正义。1937年8月27日,吉屋信子一行乘“天津丸”从大连绕道塘沽进入天津,下船后一个“外国人”与“支那”黄包车夫发生争执,并对车夫施以暴力。此时,一个“日本旅客中的男人”伸出双手站在“支那”车夫面前保护他,这个“日本人”愤慨而立,“那个似乎不把‘支那人’当人的‘外国人’也因他的气势退缩了”[9](P 8)。可以看到,吉屋信子所说的外国人并不包括日本人,只指黄发碧眼的洋人。在她看来,在华北,洋人是外国人,日本人和“支那”人是一国人,洋人欺负“支那”人,日本人保护“支那”人,日本人是强者,“支那”人是弱者。由此她兴奋地喊道:“高喊抗日主义、追随英美主义来巩固主权的蒋介石啊,我告诉您,您也来看看这个场面!”[9](P 8)
1937年7月华北通州保安队起义,对日军发动袭击,并发生了针对通州的日本居留民的袭击,造成约200名日本平民的死亡*据高崎隆治《戦場の女流作家たち》的调查,死亡的日本平民只有数十人,多数是居留在通州的朝鲜人。。“通州事件”自爆发初始就成为日本方面激化国内对中国的仇恨以扩大侵略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今天仍有一些右翼分子“企图以强调通州事件日本居留民的死亡来消解进而抹杀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5]。吉屋信子的华北战地报告用很大的篇幅记叙了自己在通州的所见所闻,详细描述了血迹斑斑的现场,并不断发出悲叹和咒骂。任何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居留民妇女和儿童的死激发了吉屋信子的悲愤。但她的视线始终只停留在遇难的日本平民身上,丝毫没有追寻一下中国平民的身影,更没有追问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被日军炸毁的天津市政府大楼前,吉屋信子看到仍悬挂着的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的匾额,非常不屑,认为中国人对日本居留民的残杀是对“礼义廉耻”的嘲讽,但她站在已成断壁残垣的南开大学图书馆前时,却没有质疑过日军的行为是否也与“礼义廉耻”相去甚远。在虚化“敌国”和“敌国”平民遭受的苦难的同时突出日本平民的悲惨,视线的不对等加上强烈的情感叙事,吉屋信子的战场报告激发了日本国内不明真相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女性的愤慨之情,有效煽动了对“敌国”的报复之心,而这也正符合日本军方利用这一事件增强国内民众“同仇敌忾”之心从而扩大对华侵略的策略。
四、反思与展望
1941年“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后,打着推进女性文学的旗号,次年日本文学界又组建了日本女流文学者会,其目的还是利用女作家的力量,通过有组织的行为,让更多女性参与到支持协助战争的运动中来。其成员中多数人都有丰富的战场慰问经验,如吉屋信子、宇野千代、园地文子、佐多稻子、林芙美子、真杉静枝、岗田祯子等人。“文学报国会”最大的“功绩”就是组织召开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1942年11月3日至10日、1943年25日至27日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女流文学者会的诸多成员抛头露面大声呼吁“大东亚精神”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尤其是在第二次大会上,女作家们一律以上身和服外褂、下身裤子的防空服打扮出现在众人面前。女性防空服是战时诞生的新鲜事物,为方便妇女行动,配合时局,将生活战场化,在一切意义上把女性拉入战争,1943年开始了从上至下的妇女服装改良运动[16](PP 64-71)。女作家们率先穿上这套“战服”,正是为了表达对战争的全力支持以及坚决站在战争攻防第一线的决心。
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诸多作家沦为战争协助者,与那个不正常的时代有关。平野谦曾说:“昭和十三年攻击汉口之际,依照内阁情报部的依托,数十名作家、批评家分成陆军班、海军班从军,仍是件划时代的事情。……‘政治与文学’的露骨勾连,通过‘笔部队’的结成展示了一种强制力,……视察国内各地工厂、农村,然后写文章汇报或到处讲演,作为各班军报道员被强制征用到遥远异国战场,逐渐成为汉口从军以来文人的生活状态。……明治以来内部积蓄的反世俗的文学精神被完全粉碎,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非文学时代。”[17](P 264)在这样一个时代难免随波逐流、做出有违理性和良知的选择,但这不是逃避责任、拒绝反思的借口。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女性生活在军国主义国家权力下面的被打压,被强迫协助战争而卷入生产战中”[18](P 220),那么女性与战争的真实状况就会被隐藏在历史尘烟中,无法为当今提供一面历史之镜。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诸多女作家为追求自我价值,建立社会空间中的身份,积极响应军国政府的战争国策,在战争的“男性”特质上寻求“女性”特征,发挥作家的天赋与力量,用文字的方式在女性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助者,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日本兴起,一些批评家在对女作家与战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主义强加给女性的战争责任和义务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深刻反思了女作家的战争协助行为,提出“受害者+加害者”认识是考察近代女性“战争文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视点,主张在国家-国民-战争的话语体系中讨论女作家在“受害者+加害者”的双重身份下的战争话语和战争体验[4](PP 150-151)。
总体而言,对“战争文学”的研究,其视点应该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只基于一方的历史认识,仅根据作家的记叙和回忆来讨论人与战争,而忽略被侵略方的历史认知与战争体验,其研究都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中国研究者视点的加入有助于使这项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立体和公正的道路。同时,今后的研究不仅应该将她们放置于反战传统断裂的研究课题中,在基于“受害者+加害者”的视点上,在国家-国民-女性-战争的话语空间中继续展开,还要在“受害者+加害者”的双重视点下,建立对她们的共性认识基础上考察她们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结合她们战时其他文本,梳理她们的战争语言与文学语言,倾听她们个人的声音,深入她们的内心世界,了解她们的心路历程,对其“受害者”与“加害者”身份的转换进行客观、丰富且人性化的解读。
[1][日]岡野幸江.女たちの記憶―「近代」の解体と女性文学[M].东京:双文社,2008.
[2][日]桜木富雄.文化人たちの大東亜戦争[M].东京:青木書店,1993.
[3]王向远.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4][日]岡野幸江.女たちの戦争責任[M].东京:東京堂,2004.
[5][日]中野久夫.大正的日本人[M].东京:鹈鹄出版社,1982.
[6][日]若桑みどり.戦争がつくる女性像[M].东京:筑摩书房,1995.
[7][日]林芙美子.北岸部队{M}.东京:中公文库,2002.
[8][日]永畑道子.フェミニズム繚乱[M].东京:社会评论社,1990.
[9][日]長谷川啓.戦時下の女性文学1吉屋信子——戦禍の北支上海を行く[M].东京:ゆまに書房,2002.
[10][日]荒井とみよ.中国戦線はどう描かれたか[M].东京:岩波書店,2007.
[11][日]高崎隆治.戦場の女流作家たち[M].东京:論創社,1995.
[12][日]佐多稲子.時にたつ[M].东京:河出書房新社,1982.
[13][日]長谷川啓.戦時下の女性文学5窪川稲子——続女性の言葉[M].东京:ゆまに書房,2002.
[14][日]長谷川啓.戦時下の女性文学14真杉静枝——帰休三日間[M].东京:ゆまに書房,2004.
[15]耿寒星.国际法视野下的通州事件研究[J].文史杂志,2015(4).
[16][中]秋山洋子.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日]渡边澄子.日本近代女性文学论[M].东京:世界思想社,1998.
[18][日]铃木裕子.フェミニズムと戦争[M].东京:マルジュ社,1997.
责任编辑:含章
From Social Activists to War Cooperators: Japanese Women Writers’ Visits to Frontline Japanese Invaders in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Japanese Invasion
TONG Xiao-w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518060,China)
Japan;women writers;visit to frontline Japanese soldiers;war cooperators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China,Japanese women writers answered the call of the army to visit Japanese soldiers in the frontline in China.After their visits they prepared reports about what they saw in China and traveled across Japan to disseminate their reports so as to promote Japanese policy on invasion in China and encourage more Japanese to join the war.After the war,their war cooperative behaviour didn’t receive necessary attention from their literary counterparts,who emphasized their female identity and did not hold them responsible for their behaviours and failed to connect their social activism from acting as avante-guard in society to war cooperators.Our reflections today will help re-anchor an analysis of these women writers’ behaviours to the effect of them as promotors of war as a mirror in history.
童晓薇(1970-),女,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日本女性文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从社会活动家到战争帮凶——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女作家群研究”(项目编号:16YJA752014)的阶段性成果。
I313.065
A
1004-2563(2017)03-006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