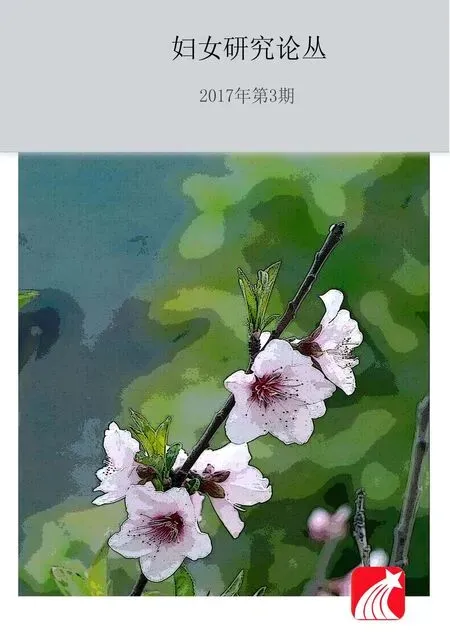罗普《东欧女豪杰》的女性设计与政治想象
2017-04-05张新璐
张新璐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罗普《东欧女豪杰》的女性设计与政治想象
张新璐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互文;女性主体;家国;启蒙
文章以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为参照,考辨出小说《东欧女豪杰》的主人公苏菲亚的生成寄寓了作者罗普对新女性的想象与设计。作者探讨了女性主体的养成——教育、女性的自我认同、女性与家、国之间的复杂关联。罗普的女性设计从属于他的政治想象。苏菲亚的变形以及她所置身的小说世界,已经背离了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的历史语境,寄托了作者罗普更为强烈的启蒙意图。
一、前言
在晚清的西学风潮中,批茶女士、罗兰夫人、苏菲亚等来自西方的女性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批茶女士以文学之笔——《汤姆叔叔的小屋》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先驱,罗兰夫人被送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苏菲亚也捐躯于俄国虚无党的暗杀活动。她们作为新女性的楷模,积极参与着晚清新女性的想象与建构。作为当时在思想界流行的女性之一,苏菲亚最早出现在小说《东欧女豪杰》中,作者罗普以文学想象的方式形构了这一女杰形象。从1902年1月开始,《东欧女豪杰》在《新小说》上连载,到次年6月成刊为五回的未竟小说。随后,又涌现出一批有关苏菲亚事迹的传记文本:1903年6月,任克的《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在《浙江潮》上刊载;1904年,金天翮的《自由血》单辟一个章节介绍苏菲亚的生平。到了1907年,廖仲恺在《民报》上再次为苏菲亚作传——《苏菲亚传》。与小说的虚构色彩不同,这些传记更加真实地再现了苏菲亚的生平经历。苏菲亚凭借着小说与传记两种不同的文体,在晚清流传开来。
在《东欧女豪杰》的已有研究中,王德威将小说纳入侠义公案小说系统,认为苏菲亚的形构,将中国古代的侠女风范转化为现代革命美德,她与晏德烈吻合古典侠骨柔情的浪漫情侣形象,两人之间的情感再次推演了英雄与儿女之间的复杂纠葛。这篇小说接续、再造了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开启了女革命家的近代叙事[1](P 184)。1904年,《女娲石》与《女狱花》两部小说问世,女主人公都以暗杀为革命志业。到了1911年,小说《六月霜》以秋瑾就义为蓝本,作者静观子对女革命家的想象,即使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作底,可具体的情节设置再度与《东欧女豪杰》形成互文。而胡缨的解读,从苏菲亚的两个传记文本入手,考察任克、廖仲恺两人传记策略的不同以及对苏菲亚死亡场景的处理。在解读小说文本时,她抓住了《东欧女豪杰》与历史语境里中国新女性的关联。小说框架叙述的支撑者华明卿,则仿写了晚清女医生康爱德的收养、留学经历。苏菲亚的小照与易装,与晚清女革命家秋瑾的女扮男装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作者罗普假借的女性作者身份——“岭南羽衣女士”,正是晚清红十字会的先驱张竹君的笔名。这些在晚清烜赫一时的新女性,都是文本内外召唤出的苏菲亚的中国姐妹[2](PP 125-171)。这些解读,或将《东欧女豪杰》放在纵向的文学谱系中来考察,或还原到小说文本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横向的对比与勾勒。
但是,这些解读似乎都忽略了苏菲亚的小说文本与三个传记文本之间的隐秘关联。这些文本都来源于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此书梳理了俄国虚无党发生与形成的历史。罗普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他跟随烟山专太郎学习现代欧洲史,受到老师的著作启发[1](P 185)。三篇传记也都翻译自同一个源文本,《自由血》是最完整的译作,《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与《苏菲亚传》则是节译。前两个传记文本,含纳在1903年苏报案所引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潮中。这一时期鼓吹俄国虚无党的文章,大都依据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翻译或改写而成。1902年,《近世无政府主义》由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刊印后,引起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成为排满革命话语的来源。但是,廖仲恺发表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的《苏菲亚传》,和他同期一系列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则归属为《民报》所宣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和共和主义、民粹主义一起,成为该刊物宣扬的三大思潮。此时,部分同盟会成员非常认同无政府主义暗杀、暴动的革命手段。与传记文本所指向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革命意图不同,《东欧女豪杰》的发表刊物《新小说》,是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力主新民与改良群治。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阵营,对无政府主义与虚无党的介绍,则试图用俄国虚无党的暴力暗杀活动威吓清朝统治者实现政治改良[3](PP 20-36)。那么,作者罗普将怎样处理苏菲亚所牵扯的历史事实,与其所承载的政治意图之间的缝隙?他将动用哪些文学策略来重构苏菲亚这位来自东欧的女豪杰?其中又寄寓着他对新女性怎样的想象与设计?罗普的女性设计与他的政治想象之间,又将有着何种关联?
二、两个文本与新女性的生成
以《近世无政府主义》中苏菲亚的人生经历为参照,叙述者罗普忠实地追述了苏菲亚显赫的贵族家世,他将苏菲亚改写成家中独女,把她的出生拉回到中国的语境中,赋予其浓重的传奇色彩。苏菲亚诞生之际,“白鹤舞庭,幽香满室”,她的成长自然不同凡人,她“秀慧无伦”,二岁识字、五岁吟诗[4](PP 4-21)。历史中的苏菲亚断断续续地读了小学和中学,而罗普却忽略了苏菲亚的小学经历,让她从“寻常中学”读起。八岁时,苏菲亚随母亲去格里米亚,也没有暂停她的教育,而是去读中学,她能够“过目不忘”“闻一知十”,毕业后升入“高等中学”。当苏菲亚回京读“女子大学”时,被父亲强制退学,但是罗普却让她用自学的方式,继续成长。苏菲亚躲在朋友家里,“自己念书”,母亲相助其学费,她还是“从容独学”。苏菲亚托人在国外买遮尾舍威忌与笃罗尧甫等人的禁书,“潜心熟读,大为所感”[4](PP 21-22)。在罗普的设想中,苏菲亚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最终却是在超群的自学能力中真正成长了起来。从此她以救世自任,投入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中。罗普为什么要赋予苏菲亚如此完整的教育经历,又一再强调她的自学成才,并为她平添家中独女的身份呢?
罗普并非凭空虚构苏菲亚的成长经历,而是借用了另一个文本: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1902年10月),该传记比小说《东欧女豪杰》早一个月发表。梁启超将罗兰夫人的个性养成,归结为“彼以绝世天才,富于理解力、想象力,故于规则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以常倍蓰焉”[5](P 1)。她的兄弟姐妹六人,悉数夭折,她也是家中独女。即使后来苏菲亚投身革命,也处处可见罗兰夫人的影子。她像罗兰夫人一样成为党魁,与济格士奇组建革命团,会长是济格士奇,但一切章程、运动的策划却在苏菲亚的掌控中;她入狱时,像罗兰夫人一样,趁机“做学问”“研究哲理”“做小说”[4](PP 58-66)。罗普在想象苏菲亚这位女豪杰时,总是时不时地借用罗兰夫人的人生经历。两人成长最重要的途径都是通过教育,从事的政治活动、陷入低谷时的心境也极其相似。作者罗普曾借莪弥之口,点出这群来自东欧的虚无党女性们决意去巴黎,“更欲一上那罗兰夫人的坟墓,凭吊一番,以表我们景仰的真心”[4](P 15)。罗兰夫人就是她们敬仰的楷模。她在小说中仅有的一次出现,连同与苏菲亚人生经历的相仿,就意味着罗普对苏菲亚这样的新女性的理解,更接近梁启超对新女性的设想。所以,罗普在形构苏菲亚时,大体遵循了烟山专太郎为她勾勒的人生轨迹,但主要依据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想象成篇。
小说中另一位女性华明卿,借用了梁启超的另一篇女性传记,即《记江西康女士》(1897年3月)中康爱德的人生经历[2](PP 140-147)。梁启超仅有的两篇女性传记,都被罗普征用,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梁启超与罗普的关系,非同一般。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万木草堂讲学时,两人都是他的嫡传弟子[6](P 214),戊戌政变后,罗普比梁启超早一年到日本,他充当了梁启超的日文老师。在切磋日文的过程中,两人撰写出风靡一时的日语入门读物《和文汉读法》(1988年)[7](PP 171-172)。1902年,两人一起翻译了儒勒·凡尔纳(Jules Gabriel Verne)的小说《两年假期》,译为《十五小豪杰》[8](PP 321-324)。两人私交甚密,一起撰写、翻译了多种著作。梁启超为“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作传后不久,罗普再写“东欧女豪杰”,与之呼应,也就自然而然。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探讨了传主个性的养成、女性主体的情感以及对公私领域的越界,寄寓着他对新女性的想象与设计,也与他这一时期的女性言论互为指涉。在晚清的女学运动中,梁启超的女性论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最大。作为好友,罗普自然很熟悉梁启超的思想理念,也会有所认同。当罗普再次想象苏菲亚这位来自东欧的女豪杰时,自然会借用梁启超的某些女性思想与言论。或许,在罗普看来,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已经为新女性们预设了普泛性的成长途径——教育。但罗普对女性教育的处理,比梁启超更为现实。他将苏菲亚的辍学,归结为父亲“性情顽固、守旧异常”,他“听了俗人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话,信以为然”,而且也不能接受苏菲亚与同学之间的往来言谈,认为“好为诡异”[4](P 22)。苏菲亚的父亲依旧秉持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念,不能接受新学。而苏菲亚的辍学,正是晚清女学通常会遭遇的挫折,它针锋相对并试图改变的正是传统女性观念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力。这种改写,就表征出了晚清女学思潮的现实处境。苏菲亚的自学,也表明罗普似乎为现实中的晚清女性指出了一条抗争传统观念的有效途径。罗普对苏菲亚教育经历的改写与虚构,仿写了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但也是一次强有力的互文,两者构成互文性文本,都积极迎合了晚清的女性解放潮流,成为塑造新女性的典范性文本。
三、女性与“家”“国”
在一波三折的教育过程中,苏菲亚成长为一位胸怀远大理想的女性主体,她立志救世,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她与济格士奇组建革命团时,四处演说。她前去乌拉山的矿工大会演讲时,装扮成贫家女子;转至佐露州之际,又扮作传教的姑娘。演说时的易装,这个细节并不符合日文中苏菲亚的生平纪事。在日文中,1871年,彼女发愿游说,她亲为田舍小学教师。1972年,巡至乌拉山中,屡被饥渴所迫,备尝辛酸。又转至芝韦尔州,以教师的身份游说,她正直而又热心,得到了劳动者的同情[9](PP 254-255)。书中只有简单的事实罗列,没有更为详尽的细节描写。但是,易装又确实是苏菲亚四处演说时极有可能采取的手段。该书在第三章就提及察科威革命团到民间游说时,有诸种易装手段:“或变身为劳动者、小杂货商,或一男一女诈为夫妇营一小商店,或为织工、木工、其他工民入诸种工场,或为马匹商、町村书记、小学教师”[9](P 101)。所以,罗普对苏菲亚易装的想象,并不是凭空虚构,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
在罗普的设想中,一位身处社会中上层的贵族小姐,将自己的“华装丽服”“簪饰”脱去,换上“不新不旧”的衣服,装扮成底层的“贫家女”,或改装为“穿黑色斜纹绒的摇曳长衣”、头戴“圆阔平冠”、脸盖“乌染线纱织成的密网”“压着绿色玻璃造成的眼镜”的“女教士”[4](P 22)。这里的绿眼镜是虚无党员的标志性配饰。在“1860年代及70年代,虚无党员服装统一,着粗罗纱之衣,穿长靴,戴青眼镜”[9](P 215)。罗普参考了虚无党员的男性化装扮,借用了最明显的标识青(绿)眼镜,但是这个标识却被面纱遮挡。面纱是女性特有的装饰,表征着女性的性别。这样,青(绿)眼镜指涉的男性性别,就被最大程度地淡化。这意味着罗普始终都在强调苏菲亚的女性身份。这两次易装,苏菲亚本人也有所回应。前一次,她非常认同自己的装扮所代表的新身份,“自觉有趣”,就拍了一幅小照,相赠朋友。莪弥等人看到小照后,议论之余,也互相传看。明卿就认为“菲亚妹的天生丽质,越扮得质朴,越显得名贵”[4](P 23)。在她看来,苏菲亚农家女的装扮并没有妨碍她与生俱来的气质,这种气质来源于她贵族阶层的教养,她的易装也就没有损害她的真实身份。而“小照”,在晚清非常盛行,它实际上为新女性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生动的视觉资源[2](P 129)。明卿的评论,作为对小照的回应,实际上认可了苏菲亚身份的流动。后一次,她“揽镜自照”,暗想“母亲在路上碰见了我,也认不出来哩,看着不禁自笑了一会”。这里的“镜子”与“母亲”,在雅克·拉康(Ja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中有着重要的意味。镜像期理论说明了“自我如何在认同的过程中成形”,也就是“自我”是“人认同自己的镜像产生的结果”。婴儿在镜中认出自己后,会需要身边的成人,即“大他者”的代表,通常“母亲是第一个占据幼儿大他者位置的人”,希望她能“核对、认可这个形象”[10](PP 193-224)。苏菲亚就像拉康所言的婴儿,先在镜中进行了自我认同,转而就假想了母亲的眼光,请求母亲的确认。只不过,她认同并需要确认的自我,已经是“女教士”这个新身份[2](PP 138-139)。苏菲亚在不断构建身份的过程中,掌握了某种主动性,召唤出一个有着历史能动者的自我,而来自女性同胞们的回应,意味着一个新的女性主体已经得到了女性群体的认同与肯定。
罗普调用了镜子与小照,让女性主体来完成自我认同。这里的自我,在不断地改装中具有了不同的身份。身份的流动打破了阶级的壁垒,却没有改变女性的性别认同。这是女性对自我的真正认同,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体得以生成。而罗普对新女性的理解似乎不同于梁启超。罗兰夫人作为苏菲亚的模仿对象,她的越界以抹除自己的性别认同为代价。她投身革命,即进入政治领域这个公共空间时,就是雌雄同体的模糊性别。公共领域一直是分属于男性的活动空间,男女内外有别,女性只能被禁锢在家庭这个私人领域中,承担母职与妻职。然而苏菲亚却可以带着自己的生理性别安稳地越界,以女人的身份进入到公共领域中。这就对传统的性别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就有了些许革新的意味。
但是,对于苏菲亚的性别认同和身份流动,男性世界的态度是暧昧不明的。苏菲亚易装后,被街上的巡捕一眼认出。他贪恋苏菲亚的容色,曾经凝望失神,跌倒在沟渠里[4](P 34)。巡捕,这个男权世界秩序的维持者,他似乎并不认同她的身份流动,而是认可她的女性特质。他的凝视,发生在大街这个外在于家庭的公共空间中。由凝视而导致的跌倒,让这个来自公共空间的认可出现了狼狈的结局。代表男性世界的巡捕,无法处理女性的越界与性别,面对着她对传统性政治的冲击,非常惊慌失措。作者借这处虚拟中的凝视,似乎泄漏了他心中些许的焦虑。苏菲亚的革新,似乎也让他感到非常棘手。作者连同文本中的男权世界,恐怕都没有做好苏菲亚对传统性别秩序的冲击,以及由此可能造成失范的心理准备。
苏菲亚越界后获得了话语权,也就掌握了公共领域的某种权利。在演讲中,她从生活力的角度,肯定了工人们联合罢工的言论,抨击了贵族制这一导致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她转而宣扬人人生来平等。她认为平民要联合起来,组成团体,缔造一个公平的世界。她将这个“大大的团体”界定为“大公局”,可以由此设定公价,购买贵族的土地,让贵族的财产变为大众共有。但是,随后她就将“一国人的大公局”定义为“政府”,并给出平民与大公局关系的一套说辞:由于“大家不管事”,导致大公局变成了“大私局”,“如今各位且向那里着想就是了”[4](P 31),换言之,平民没有政治权利意识,导致政府的性质改变,但平民还是要为政府着想,以政府的利益为出发点。她已经在宣扬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与此相一致,她也在多种公开场合反对激烈的斗争手段。认为联合罢工是“拿着鸡蛋儿去打那石头”,“不过是一时的岔气,到底行不去的”;籍没贵族的土地,“却未免太过激烈了”,她对同党姐妹常说,“现在总要到处游说,提倡风气,别要急激从事”[4](P 24)。这就与历史事实形成了断裂。
在日文中,苏菲亚组建察科威革命团时的宗旨非常明确:(一)扑灭国家,(二)破坏文明,(三)辅助全世界自由团体联结成“全世界自由民的组织”。他们在民间进行大游说时,通常改变身份,亲近下民,“告诉彼等无智无学的民众,各自的境遇最为悲酸,煽动彼等对政府的憎恶之情”[9](P 101)。从虚无党革命运动的三阶段,即撰写革命文学、游说煽动、暗杀恐怖来考量,该团的活动属于第二时期。他们此时采取的斗争手段宣传演说比较平和,但是他们的主张却非常激进。他们要摧毁沙皇统治下的专制国家,也要破坏一切文明,他们要追求与缔造真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在该团的革命理念中,他们首当其冲要破坏的,正是国家和政府。小说中苏菲亚宣扬的以“大公局”为核心的政治理念,已经违背了该团横扫一切文明与制度的宗旨,不仅没有了激进革命的意味,反而变得相当温和,用赎买的方式平稳地改变政府的性质。政府本身并未受到冲击,依旧执行着政治统治的职能。对政府与国家而言,苏菲亚就不再具有破坏力。她对家庭而言,也是如此。日文中的苏菲亚与虚无党人相交,被父亲禁止后,她“脱家匿朋友宅”,母亲“密送”她学费[9](P 254)。面对苏菲亚离家这样简短的历史事实,罗普想象填充了一些有意思的细节。面对父亲的禁令,她先是“力为解说”,试图以辩解的方式,征得父亲的同意,父亲“仍是不依”。当她抗拒不了父亲的威权,“再没有办法,只得和他母亲商量,暂时躲在朋友的家里,自己念书”[4](P 22)。离家是和母亲协商的结果,并不是自作主张。而且,也只是“暂时”躲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并没有断然与家庭决裂。后来“喜得母亲欣然答应,又张罗了好些学费,给他携去”[4](P 22)。她最终离家和前去求学,都获得了母亲所代表的父母威权的许可。史实中的“离家”,意味着她对父亲所代表的家庭父权制度的抗拒与颠覆,但是,罗普设计她向父亲“辩解”,与母亲“商量”,让“离家”这一决绝的行动变得和缓起来。而离家这一史实所具有的反叛父权的革命意味,也被巧妙地消解掉了。
在对女性与家、国关系的想象中,罗普完全扭曲了真实的虚无党女性。历史中的她们以暴力革命、暗杀恐怖著称,苏菲亚成功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更是让她声名大振。这些女性信奉的虚无主义,要“废止家族、财产、国家及法律”,也就“否认了国家与社会,无视家族与宗教”,这是一种彻底的“否认主义”与“破坏主义”[9](PP 4-5)。在这种全新的革命中,她们解放的不仅仅是人民大众,更是她们自己。女性历来深受父权制国家的宰制,被禁锢在父权压迫、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纵横交错的罗网中。虚无党女性信奉的破坏主义,对国家与文明的摧毁,意味着女性对国家的彻底逾越与拒绝。在她们看来,这是对现存制度与社会的一种彻底的解构,这似乎可能会给女性解放带来某种契机。但是,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却是“一种否定强权,特别是国家强权和家庭强权的社会理想主义”[11](P 11),是一种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她们崇尚的极端自由与绝对平等,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并不可能真正实现,更遑论女性的解放。而女性真正的解放,是要根本改变女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结构关系的改变”,即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11](P 29)。晚清无政府主义者何震,谈及女性解放问题时,就认为“有志之妇女”,应该有“废灭政府之心”,废灭政府的根本目的,在于“行根本改革,使人人平等”。总之,“实行共产,妇女斯可解放也”[12](PP 98-107)。
小说中的苏菲亚,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中的虚无党女杰,她不再具有任何破坏力,宣扬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她已经被罗普改造为一位遵奉国家主义的改革者。她从事的演说,变成了单纯的启蒙: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与权利,反叛贵族制的封建专制政体。革命的目标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建设。她不像梁启超传记中的罗兰夫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操,直接宣称爱国,她的国家主义情感暗含在她的言论中。实际上,苏菲亚和罗兰夫人成为极为相似的女性,两人都反对封建专制。前者崇尚共和政治,后者则宣扬“大公局”式的政府,其实都是民族国家的不同范式。她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追求,以及她们自觉的国民意识与责任,成为晚清以罗普、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新女性想象与设计中最重要的面向。
四、小说的政治意图
罗普重构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试图将她改造成像罗兰夫人一样的女性。历史中这两位女性信奉的理念——无政府主义与民族国家是如此不同。罗普为什么要选择苏菲亚来宣扬与其格不入的政治信念?他的新女性设计与政治想象之间,又有着何种关联?
罗普赋予苏菲亚的国家主义情怀,实际上遵从了小说宣传广告中的整体构思。在作者的设想中,“东欧女豪杰”原指“威拉、苏菲亚、叶些”三位女性,他将以女性架构起历史叙事。同时,这些女性被定性为“爱国美人”。他之所以选择东欧女豪杰,因为“盖爱国美人之多,未有及俄罗斯者也”[13](P 33),即俄罗斯的女豪杰最多。更重要的是,她们信奉“自由”,反叛“专制”,甚至不惜流血牺牲。“以求易将来之幸福,至今未成,而其志不衰”[13](P 13),这种战斗不息的精神最让人钦佩。小说的意图就在于“中国爱国之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也”[13](P 43),作者寄望东欧女豪杰能够激起读者的爱国热情。这就意味着作者的新女性想象,并不指向女性自身的解放,而是为了爱国情操的孕育。女性作为弱者,似乎她们对强权的抗争,对国家的热爱,更能激励广大的民众。充斥在《东欧女豪杰》构思中的政治意图,实际上严格遵从了《新小说》的办刊宗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起爱国精神。”[13](P 41)此文即《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署名为“新小说报社”,通篇的叙述者自称为“本社同人”[13](P 41)。这就意味着罗普的小说不再是单纯的个人创作,而是浸染着浓重的群体色彩。在这一期的创刊号上,罗普同时译述了侦探小说《离魂病》。刊载在《新小说》上的《东欧女豪杰》,除了小说正文外,还夹带着谈虎客(韩文举)的批注。韩文举也是康有为的嫡传弟子,他在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担任主笔,极力鼓吹民族主义[6](P 214)。罗普、韩文举等,成为集结在《新小说》的创办者梁启超身边的同路人。他们认同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也积极响应着梁启超此时大力宣扬的小说界革命,以创作、翻译、评注等方式予以支持。
具体到小说《东欧女豪杰》牵涉的历史语境——俄国无政府主义,他们也应该能够达成一定的共识。罗普没有专门针对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评论,但他同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政党论》中阐述了立宪政治的理念。他认为“政党者,立宪政治之产物,而与专制制度不能相容者也”,政党是“人民政治思想的表记”,反对专制,就要先对人民进行政党思想的启蒙[14]。由此可以推测,罗普应该不会认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梁启超却多次撰文评论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甚至最早引入了“无政府”一词[15](PP 27-28)。在《论俄罗斯虚无党》中,他将虚无党钟情的暗杀手段,与革命惯用的暴动手段相比较,解析出暗杀手段的必要性。他直言“虚无党之手段,吾所钦佩。若其主义,则吾所不能赞同”[16](P 30)。在他看来,无政府的宗旨违背了“人道”与“天性”,该党秉持的“共产均富主义”,已被生计学者驳倒。虚无党的争点在“生计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16](P 30)。梁启超的言论似乎启发了罗普,小说中的苏菲亚就是从工人的生活力,也就是生计问题,引出了她的“大公局”理论。她隔天再度演说时,作者就在“大公局”的指称后,加了“(债)”。与罗普隐晦的呼应相比,韩文举的眉批就直白得多:“虚无党是主张共产主义,全从柏拉图得共和思想生出来,今日却是行不得的。”[4](PP 30-31)团聚在梁启超身边的这群友人,并不认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罗普却选择该党的历史演义成小说,希望对民众进行一次爱国主义的启蒙。爱国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是如此格格不入。那么,他将怎样围绕主人公苏菲亚来设置人物,搭建起小说世界,完成他的写作意图?
华明卿最先出场,作者将她的身份界定为:我国中“被时势造出来的人”[4](P 7)。她成为晚清新女性的代表。莪弥等留学瑞士的俄国学生,迫于政府的压力,将被遣散。她借机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制度。华明卿以中国的时局相回应,认为两国都是野蛮政府,戏言“天生成一对大虎国”[4](P 13)。莪弥接过话茬,宣称了虚无党的宗旨。这让明卿深深地被震动到,她辗转难眠。在她的意识流动中,充斥着启蒙的论调。她直陈出说教的对象:中国的广大民众。即“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姐妹,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4](P 16)。“甘做外人的奴隶,忍受异族的凭陵,视国耻如鸿毛,弃人权若敝屣,屈首民贼,摇尾势家,重受压抑而不辞,不知自由为何物。”[4](P 16)她深知中国的现实处境,国民深受国权与阶级的压迫,却没有国家意识和平等、自由的政治观念。在对国民性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后,她反问道:“倘使若我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能不愧死么?”[4](P 16)华明卿的意识流,再次回应了小说的意图:寄望虚无党女杰能够唤醒国民,激发民众的国民意识与爱国情操。韩文举也在此批注,点明“此是著书本意”[4](P 16)。华明卿成为启蒙意图的重要承担者。她的人物功能,就不仅仅是框架结构的导引,而是牵出了中国的本土语境。华明卿作为中国的新女性,她为民众树立了榜样。她能被启蒙,中国的众多读者也应该有此觉悟和意识,她成为作者的启蒙意图在文本内外实现的重要中介。
华明卿退出叙述主线后,作者围绕苏菲亚入狱事件,设置了众多人物为营救她四处奔走,晏德烈成为营救事件的核心人物。在烟山专太郎的著作中,晏德烈和苏菲亚一起参加了弑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前后被捕身亡。两人的确相爱,但晏德烈是有妇之夫,他早已娶妻生子,妻子是位产婆[9](PP 269-275)。罗普却将两人的关系和情感变得非常简单、纯洁,晏德烈成为苏菲亚青梅竹马的恋人。但是,作者也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他的教育经历。
日文中,作者只简短提及晏德烈的两次辍学:1868年,入哇台斯萨大学,由于不稳妥的举止,教授让他离校。再入法科大学,他参加示威运动而被退学[9](P 162)。罗普却精心设计了第一次退学时晏德烈与教习针锋相对的场景。这所大学被限定为:由权贵创办的“最专制、最守旧、最能养成柔声下气、奴颜婢膝、真正凉血泪的人才”[4](P 42)的大学堂。教习向学生宣讲君权神授,爱国就是爱君主。晏德烈对此进行了驳斥,他将专制制度的成因追溯为初民没有合群意识,君主和贵族凭借强权欺压平民。到了18世纪,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理念深入人心,世界掀起了革命的风潮。平民组织成民党,向政府宣战,各国相继建立“立宪制度”。在晏德烈看来,立宪制度虽然有益平民,政府也占了很大的便宜。现在的各国君主,都应该乐意“用着这个计策,和平民讲和”[4](P 46)。晏德烈的反驳,更像是苏菲亚的工厂演说。两人话语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只不过苏菲亚演说的落脚点在“大公局”,如果不仔细分辨,似乎倒真有点像虚无党宣扬的共产主义。晏德烈却义正辞严地宣扬起立宪制度,这自然是罗普《政党论》中宣扬的政治理念,但也是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所达成的政治共识。此时,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中,已经完成政治理念的转向:由激进革命转向温和改良,他更为推崇立宪制[17](PP 269-275)。可是,历史中的晏德烈却是非常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扭曲似乎要造成文本的断裂,罗普却巧妙利用了晏德烈的学生生涯,他此时尚未加入察科威革命团,那么,罗普就能直截了当地借他之口,宣扬立宪。而不需要像处理苏菲亚的演说那样,要经过一番伪装,含蓄而又委婉。两人的启蒙意图最终都得以完成。继晏德烈出场的苏鲁业、赫子连,作为苏菲亚的营救者出现在小说结构中,两人都是被启蒙者。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变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
小说中的华明卿、苏菲亚、晏德烈,共同完成了作者的启蒙意图。他/她们的演说,成为作者意图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这也是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的主导范式——政治小说的一大特点,即“政治小说的演说调”[7](PP 216-217)。演说,也是罗普再造虚无党历史之际,力图表现的“虚无党之精神”,韩文举的总批就如此和盘托出[4](P 36)。演说还成为构建人物关系的关节点。华明卿听说了苏菲亚的事迹,见过她的小照,最渴慕的却是苏菲亚的“言论风采”[4](P 23);晏德烈作为苏菲亚的天生佳偶,他接过了身陷囹圄的苏菲亚无法再继续的演说任务。他/她们之间,凭借演说,彼此进行认同。但各自演说的内容有着细微的差别,华明卿要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感,未加入革命团时的晏德烈要宣扬立宪,苏菲亚宣传的政治理念,已经严重背离了俄国虚无党的无政府主义,成为改良主义的传声筒。《东欧女豪杰》中的演说调,对于它的创作语境《新小说》以及晚清文坛的“小说界革命”而言,就不仅仅是小说外在形式的仿同,而是内容上的真正呼应。依附于演说的启蒙意图,规约了小说的人物设置与架构。文本内启蒙意图的实现,势必影响到文本外的世界:文本的旅行以及读者的接受反应。广大的中国读者们,才是作者启蒙意图的最终意指对象。
五、结语
罗普《东欧女豪杰》,来源于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但苏菲亚的形构,更重要的是借鉴了梁启超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仿写了女性主体养成的重要途径——教育。罗普借易装,想象女性在公私领域间的越界,赋予苏菲亚的自我认同。易装所代表的性别认同,很难说是罗普有意为之的革新,或许只是一种巧合,小说整体构思中的“爱国美人”,已经为女豪杰们定了性。苏菲亚,在浓厚的群体色彩和作者的理念先行中,成为新旧杂糅的女性主体。罗普的女性设计,实际上从属于他的政治想象。无政府主义,此时正以它的破坏手段风靡中国。罗普并不认可虚无党女杰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却认为她们的反抗精神最能警戒当政者,也是对民众最好的激励。围绕着苏菲亚的小说世界,放置在小说的创作语境,即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中,无疑将成为新的小说理念——政治小说的一次成功的演绎。
[1][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胡缨著,龙瑜成、彭珊珊译,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3]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4]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A].中国近代小说大系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瓜分惨祸预言记等[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5]梁启超.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A].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冯自由.革命逸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7]夏晓虹.觉世与醒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M].北京:中华书局,2006.
[8][美]韩南著,王秋桂等译.韩南中国小说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日]烟山专太郎.近世无政府主义[M].东京: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2.
[10][英]狄伦·伊凡斯著,刘纪蕙等译.拉冈精神分析词汇[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
[11][美]阿里克德里夫著,孙宜学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葛懋春.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13]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4]罗普.政党论[J].新民丛报,1903,(25).
[15][韩]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梁启超.论俄罗斯虚无党[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日]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含章
The Design of Females and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Luo Pu’sAnEasternEuropeanHeroine
ZHANG Xin-lu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intertextuality;female subjectivity;family and nation;enlightenment
This paper compares LUO Pu’sAnEasternEuropeanHeroinewith Yan Shan Zhuan Tai Lang’sModernAnarchismand Liang Qichao’sTheBiographyofModernHeroineMadameRoland, and finds similarly that the depiction of Sophia,the leading character in the former expresses the author,LUO Pu’s imagination and design of new modern female’s experiences,especially in their search of education,identity and their complex relationships with the family and the nation.LUO Pu’s portrait of Sophia follows his political concep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Sophia and the fictional world she is situated in,both of which are detach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anarchical context of Russian nihilists,reveals the author’s strong enlightenment intention.
张新璐(1985-),女,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
I206.5
A
1004-2563(2017)03-005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