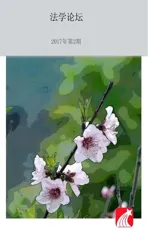利益法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适用
2017-04-05石聚航
石聚航
(南昌大学 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利益法学立场下刑法目的解释的适用
石聚航
(南昌大学 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面对刑法规范供给的不足,刑法解释需要重视利益分析及其基础上的目的解释方法。刑法解释不是认知教义学上的理解,而是表达意义上的论证,利益法学与目的解释之间具有学术上的内在关联,后者是前者在解释论上的延伸。目的解释的内在危险不在目的解释本身,而在解释者解释的过程缺乏利益判断的类型化思维。利益法学立场下的刑法目的解释适用需要妥善处理案件事实对刑法规范的型构意义,目的解释与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关系以及利益类型化的判断。强调利益分析接受构成要件类型化的限定,是目的解释应当坚持的基本准则。
利益法学;目的解释;实质解释;构成要件类型化
刑法解释是将“文本中的刑法”转变为“行动中的刑法”之中介与桥梁,在这个过程中,案件事实始终是刑法解释所要面临以及意图解决的对象。但是,刑法立法一旦完毕,文本就形成了相对固定性的系统,文本语义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在所难免。概念法学及形式法学所秉承的依据逻辑演绎藉此明确刑法规范内涵的观点,在处理并不复杂的一般案件时,通常不会有太大争议。但是,一旦刑法用语的边缘语义呈现,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是否具有涵摄关系就不太容易判断。况且刑法规范本质上乃价值判断之产物,构成要件中空白罪状的大幅增加以及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判断,都远非概念法学所能解决。在“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或曰供不应求具有不可避免性”*付立庆:《刑罚积极主义立场下的刑法适用解释》,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4期。时,实质判断就不可避免,规范背后所隐喻的目的及其利益诉求成为刑法解释中的重要参量。
一、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实践困境
一般而言,在奉行成文法的国度中,刑法规范供给不足似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刑法规范供给不足可以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1)基于刑法用语自身的模糊性而形成的规范适用不确定。立法为了尽可能使得刑法用语具有包容性,以避免刑法立法频繁修改而影响其稳定性和权威性,通常会采取具有一定模糊性的用语来周延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形。典型的如刑法中的兜底条款,《刑法》第225条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规定就是如此,这种情形实际上是刑法用语的不明确性所导致的。在解释论上为避免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的危险,就需要结合非法经营罪的罪质来框定“其他经营行为”的范围。(2)刑法用语相对性导致的解释标准和幅度的差异。刑法用语具有相对性,同一法典中出现的同一用语比比皆是,但是其含义却不尽完全相同。例如,人们显然不能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暴力”与抢劫罪中的“暴力”作相同的解释。因此,轻罪与重罪中的同一用语解释标准和幅度不仅要受到罪质的限定,也需要通过观察刑罚轻重的程度来反向理解构成要件要素。(3)刑法用语的保守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加剧了刑法规范供给的不足。以文字为载体的刑法一旦形成之后,其基本语义或核心语义就固定了。当社会发生变化后,就会使得原本清晰的刑法用语范围开始出现模糊,诸多边缘语义甚至具有分歧性的语义开始进入解释者的视野。刑法文本的固定性与社会变化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刑法规范似乎永远无法应对未来的事情。刑法立法在本质上是保守性的知识系统,它是依据过去而来处理未来的可能预见的事情。但问题是,在转型幅度如此之大的当下中国,未来案件的处理经常会挑战人们的已有认识。我国刑法立法历来的基本策略是先粗后细,成熟一个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这种通过“实验→纠错→实验→纠错”的立法逻辑,永远是步社会发展之后尘。因此,刑法供给不足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刑法成文法主义或成文法运动与近代启蒙运动的关于理性的认知有关。在将法律从宗教与神学中解放出来后,人的价值得到空前的高涨与尊重。以建构主义为导向成为了立法的主要指南,人们总是试图通过严密规则的建构来涵盖整个社会中的事实,使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都能找到适用的规则。“法律研究者唯一的目的就是揭开法律领域中不可思议的神秘,并揭示法律之逻辑有机体的纤细的血管。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借助逻辑思维就完成了这样的任务——最精美的辩证法作品,人类洞察力的真正奇迹,十九世纪智慧的丰碑,就像经院哲学家一样,仍然会受到久远后世的赞美,并将促使人们去模仿。”*[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逻辑的建构力图使立法的产品成为艺术品以至于能流芳百世为后人永远传颂。在法典完成之后,人们基于对法典理性的无限忠诚,诸多法学概念的诞生直接服务于法典的理解和适用。“概念法学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名,抛弃自然法学的主张,仅仅承认实在法,认为成文法典一旦制定出来即可自给自足,足以解决各种纠纷。法官只需根据适当的逻辑推理, 就可以从现有的由概念构成的法律条文得出正确的判决,无需考虑法律的目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和社会的实际需要。”*杜江、邹国勇:《德国“利益法学”思潮述评》,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6期。如此,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时常被唯概念化或唯形式化的理论隔断。概念法学无法从社会事实中寻找到发展和完善自身的营养,人们对于法律规范的理解是完全通过概念的建构来实现的,即便概念适用会存在误差,但那也是司法适用者不完全遵守概念思维的结果,即耶林所讽刺的“概念不能容许与现实世界接触。”*[德]鲁道夫·冯·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如此的刑法解释,即便在程式上如何精巧,恐怕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实际上,刑法“解释所凭借者,通常能够并非明文化法律所为规范,而是透过社会通念,以法律逻辑的方式来诠释。”*柯耀程:《通识刑法》,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5页。概念法学推向极致恰恰是对概念的伤害,因为当刑法解释失去了社会观念作为参量时,概念实际上已经被抽为一个空壳,完全没有任何意义。这倒不是贬低概念或形式对于刑法解释的意义,而是对纯粹的概念演绎多有微词。概念法学的任务“只是从现象上认识法律,对实在法规范进行加工整理、综合分析,决不允许超越这个界限。从概念法学所主张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概念法学脱离社会实际,它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方法坚持伦理和价值虚无主义的观点,并假定法律是无缺陷的,通过适当的逻辑分析,便能从现行的实在法制度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满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吕世伦、孙文凯:《赫克的利益法学》,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6期。同情地理解概念法学,其基本初衷或者是基于对司法的不信任,中世纪以来的司法擅断足以让法治发展蒙羞,通过概念思维来限制司法权并且保障立法的成果不被司法篡改。但是在疑难案件面前,这种初衷经常大打折扣。
实际上,尽管立法者殚精竭虑地试图限制司法者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对刑法的解释权力,但司法裁判中法律职业群体无时无刻不在解释着法律。仅仅通过立法就试图解决所有案件的时代从来没有也绝不可能存在。微观上,刑法适用或刑法解释的主体就是审理案件的裁判者。刑法规范是一般性的、类型化的规定,它所面向的是基于已然案件的共同特性而抽象出的规则。换言之,由部分案件归纳出来的刑法规则由于在归纳基础上的不完整性,也一定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的案件。继而产生的问题是,司法者究竟应当如何解释刑法规范?如前所述,这已经不是概念法学统领的时代,概念也仅仅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工具,如同政策、经验、认知等因素一样,共同构成了人们理解刑法规范的参量。刑法规范也不再是封闭的系统,刑法规范的适用只有在各种知识因素交叉理解、交互认定和检验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出符合规范目的的正当性结论。
除却概念法学之外,刑法解释的方法亦有多种,型构、制约与影响刑法规范的因素也极其复杂。但所有方法及因素的运用都围绕着一个最基本的目标,即“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的相互印证”。以案件解决为中心的刑法解释,表明刑法解释的实践面向。这种面向具体而言:(1)在首肯刑法规范所隐含的一般公正的同时,尤其关注个案的具体性、非典型性与特殊性。以个案为出发点,在类型化的刑法规范与个案之间建构合理的解释规则与解释方法。这种意义上的刑法解释可称之为司法刑法解释学。*刘远教授曾经提出司法刑法学的观点。笔者认为,如果司法刑法学的提法成立,那么其核心命题则应当是司法刑法解释学。具体有关司法刑法学的主张参见刘远:《司法刑法学的视域与范式》,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4期。(2)以司法为核心的刑法解释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甚至与现实主义思潮具有某种思想的关联,在“英美法系的法律思想中,法官更是被视为法律制度的中心。”*[美]罗杰·科特维尔:《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法官是刑事司法运作的主导者和案件终极结论的判断者,这既是司法本原的含义,也符合现代司法的基本原理。既然如此,司法的面向就不应当仅仅是立法或法学家们所罗织的概念及其演绎,真正需要他(她)虑及的问题是如何过滤各种因素,并采取何种方法来论证自身的判决结论,并且对于裁判者而言,通常还要考虑案件裁判结论之后不仅仅对当事人具有怎样的影响,对于公众及裁判者个人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刑法解释中,“法官的核心工作是一种个人的工作,即法官以个人的最大努力来决定案件,法院内部的机制必须促进而不是抑制这种个人的作用。”*[澳]安东尼奥·拉默:《法官的角色与作用》,陈鹂译,载《人民司法》1999年第11期。当然,主张个体性的理解,仅仅是从解释主体的角度而言,但并不意味着解释者可以随意对刑法进行解释。批评规范外因素作为刑法解释依据的人们,通常会指责包括目的、利益、政策等原因极易导致刑法解释突破法治的底线。不容否认,在个案解释中,的确会出现裁判者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情形,但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解释本身,而毋宁是解释者歪曲解释或不善于解释的恶果。况且,常态下的刑法解释,解释者也需要顾虑到法律职业群体关于具体问题的认知。因为,现代司法作为一种职业,司法的操守对于裁判者个人的生涯及其职业评价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因此,常态下的法官解释,也不能过于忧虑甚至夸张上述因素对刑法解释的负面影响。
真正需要虑及以及提防的是,解释的过程或程序。任何一种解释都是一种实验性的结论,它需要接受各方知识的检验甚至挑战。在刑法解释中,解释的思维的路径是如何形成的,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例如,在考虑利益是刑法解释的要素时,显然不能一概地认为凡是侵犯了利益,造成了损害的,就可以解释为犯罪。解释刑法的基本底线仍然是类型化的刑法规则,疑难的问题只是对于类型化中的构成要件要素是否能够将一些外在受到利益损害的行为解释进去。例如,组织同性之间提供性服务的行为,是否属于组织卖淫罪中的“卖淫”?财产性利益是否能够解释为财产,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的干股能否解释为财物,性贿赂是否属于贿赂犯罪的对象,等等。在上述问题的解释中,解释者显然不能够笼统地以直觉上有危害就将之犯罪化。解释者不仅需要仔细甄别在危害行为中,究竟哪些利益受到了损失,以及损害是否可以为刑法的类型化涵摄,甚至还要考虑到如此解释是否便于司法操作等等问题。“法律是一门社会之学,法官在裁判时,如果面临复杂的利益取舍、困难的权利安排,单靠法律知识往往不敷适用,还必须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社会经验和良好的衡平感觉,才能作出合理而公正的裁判。”*刘风景:《裁判的法理》,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法律本质上是利益博弈之规则体现,刑法解释自然需要返璞归真,详尽地考虑利益究竟在解释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及其在解释中如何操作,并在此基础上探求解释的适用方法。
二、从认知意义上转向表达意义上的刑法解释
解释者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其目的就是认知法律的含义及其意义。而问题在于,认知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仅仅是理解,认知意义上的刑法解释在本质上是机械的注释,既无法从体系上总体把握刑法,更罔顾挖掘与拓展刑法用语在具体案件适用中的可能含义,从而掣肘了刑法发展的内在动力。正如黑克(赫克)所言,“旧(概念法学,笔者注)理论所持的一种很确定的观点,我们可称之为认知教义( Erkenntn isdogma)。它将法官限制于一种理解性的活动。法官必须认识法律规范并将案件事实逻辑地涵摄于规范。他必须根据认知逻辑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但不应进行评价,更不能自己创造规范。这种活动的典型称谓是‘运用概念计算’。计算是一种纯粹的认知,不含任何情感因素。因此,法官被看成是一台将事实投入其中就能给出判决的机器,所据虽然不是机械学的规则,却也是同样客观的逻辑规则。至于判决在生活中是否正确,法官无须考虑,因此也无须负责。”*[德]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傅广宇译,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6期。刑法规范背后的目的及其利益考量在认知层面上基于方法论选择的偏差而被遮蔽了。刑法用语的含义只有在案件裁判中才可能得以明确,无法为案件裁判提供信息的刑法规范徒成具文。刑法规范的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上述认知教义的思维而造成的。
表达意义上的刑法解释注重刑法用语的流变性与弹变性,在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交互认定的过程中,以明确刑法用语的边缘含义,增强刑法用语的弹力。与此同时,表达意义上的刑法解释由于照应裁判者的能动性,可以有效地处理刑法规范稳定性与社会变化之间的融通。“有关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之间的协调性问题,从某个方面来看,变成了一个在规则与自由裁量权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在根据确定的规则(或至多根据从严密确定的前提所作出的严格推论)执行法律与根据多少受到训练的有经验的司法人员的直觉进行司法之间进行调适的问题。”*[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显然,表达意义上的刑法解释肯定裁判者的能动性,因此,作为表达意义上的刑法解释,关照规范背后的利益诉求,这种利益诉求在解释方法上与目的解释具有内在的关联。
利益的保护及其衡量在刑法层面上都被凝练为刑法的规范目的。刑法规范的用语表述及其解释都需要以目的作为解释的指南,目的是刑法解释的导向与航标。一般认为,“目的论解释,是指根据刑法规范的目的,阐明刑法条文含义的解释方法;质言之,是根据保护法益及其内容解释刑法。任何解释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论解释;当不同的解释方法得出多种结论或者不能得出妥当结论时,就必须以目的论解释为最高准则(当然应受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页。台湾学者林书楷认为:“所谓目的解释(TEeleologische Auslegung),主要系基于法律规范之目的而为之法律解释,其主要是确认‘规范的当代目的’,目的论解释可以说是刑法解释中最重要的一种解释方法。由于刑法系以保护法益为其主要目的的,因此所谓‘目的解释’其实就是一种以法益为导向的解释方法。”*林书楷:《刑法总则》,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39页。尽管学界也不乏对目的解释的质疑之声,但问题是,古典意义上的严格解释在近代也发生了一些松动。例如,古典的罪刑法定原则严格禁止习惯或习惯法作为法,其主要理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的基本要旨相互矛盾,容易导致刑法用语的不明确性。但是时至今日,“在采成文法国家对于行为之处罚,虽唯成文之刑法是赖,然而对于处罚前提之构成要件要素与违法性之认定,实不能不顾虑习惯或习惯法所承认之事实,惟是,习惯虽不得成为刑法直接渊源,但仍可成为刑法内容之一部分。”*蔡墩铭:《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9页。刑法用语的实质判断实乃刑法解释无法避免之情形,因此,在实质化的语境中,尽管人们否定将习惯或习惯法直接作为解释的法源,但另一方面又无法否定习惯法对于刑法用语解释的补充作用。习惯法的运用照应了刑法的目的解释,却未必会导致刑法适用的过度扩张。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基于“抢婚”的风俗习惯在“抢婚”过程中出现的致人轻伤情形,尽管符合《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却并不因此而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在“抢婚案”中,目的解释的解释可采取两个路径:(1)在违法性认识阶段做出判断,即从习惯法的角度排除刑法一般规范的适用。刑法规定故意伤害罪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伤害,“抢婚”的行为如若也认定为犯罪,势必会是对民族地区风俗的否定,由此可能引发更大的不正义。因此,明确刑法规范的目的在违法性判断阶段的意义,在“抢婚案”中可以收缩刑法处罚的范围。(2)在责任判断中,也可以否定行为构成犯罪。易言之,“抢婚”者只是基于民族风俗的认可而实施的行为,行为人对于被害人并没有充足意图侵害或过失侵害的心理状态。可见,基于利益分析而具体化为目的解释的方法在解释的过程中根据案件的具体不同,可以在违法性或有责性阶段作出判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规范的目的仅仅具有指引性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只要发生了利益损害,解释者就一定将行为解释为犯罪。学者们认为的目的解释有可能滑向任意解释或类推解释的危险,根本上并不是目的解释自身的问题,问题是在如何理解目的解释,当认真对待目的解释时,目的解释也未必就会突破法治的底线而成为危险性的解释方法。
实际上,目的从来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任何一种解释方法中。因为,“人类行为服从‘目的律’的支配,创制法律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解释法律也同样是一种合目的的行为;相对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或确定,对法律解释目的的考虑具有前置性——法律解释方法的基本含义之一就是达到解释目的的可行路径。”*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考夫曼甚至认为,在最近的时代,特别是在法律资讯的领域中,一种新的逻辑发展出来,此种逻辑称之为“模糊逻辑”,一种具有模糊、不清楚、不明确轮廓的逻辑,人们借此来把握不确定法律概念。它并非仅仅提供一个正确的解决途径,相反的,是存在着许多正确的,亦即“适当的”,可以交互选择采用的解决途径。*参见[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第2版),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5-46页。人类追求案件处理的妥当性,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原动力。
换言之,只有肯定裁判者拥有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时,才能承认目的解释在案件裁决中的功能。“规则的内涵是在官方知识(刑法规范)与经验知识(法官个人的经验判断)不断融合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下来的。从西方国家的实践看,对法官个人经验知识的尊重和认可既可以实现个案的公正,也有助于保持规则内涵的开放性,并进而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哈耶克认为:“人们最初使用‘自由裁量权’这个术语时,是指法官解释法律的一种权力,即法官从整个有效地法律规则体系的精神中,发现其间所蕴含的各种含义,或在必要的时候,将那种先前并未得到法院明确陈述或先前并未得到立法者明确规定的原则做一般性规则加以表述。”*[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9页。如果对目的进行界定的话,就不难发现,目的解释所谓之目的并非是裁判者随意的解释,而是融通一般刑法规范与个案特殊性之间不适应的解释方法。重视目的解释思维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强调的是目的解释仍然要受之于刑法体系以及自蕴育在刑法规则中的基本精神。目的解释不曾宣示过要突破刑法的体系限制与刑法精神的制约,继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便是如何寻找到论证目的解释之思路和检验目的解释结论之方法。
三、刑法目的解释的具体适用
(一)案件事实在解释论上对刑法规范的反制影响
“在刑法解释、适用的程序中,必须对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交互地分析处理,一方面使抽象的法律规范经由解释成为具体化的构成要件,另一方面,要将具体的案例事实经由结构化成为类型化的案情;二者的比较点就是事物的本质、规范的目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的彼此对应。”*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任何解释,包括目的解释都要面临上述的问题,即如何寻找到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的用语之间的相互映射。案件适用的基本程序如下:先确定刑法规范A的含义,然后在此刑法规范的指引下去适用案件,当案件事实能被刑法规范涵摄时,则适用A;如果不能够被A所涵摄,亦即刑法规范适用出现障碍时,则面临着两条路径:(1)再选择其他刑法规范或者(2)再以案件事实逆向推导重新解释刑法规范。上述思路(1)(2)的结合可谓三段论和三段论倒置的综合运用。
三段论的司法逻辑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解释者恪守对刑法规范的忠诚,其内在的政治哲学是权力分立。但三段论同样存在问题,三段论适用的前提是人们对于刑法规范的理解首先是确定的,毫无争议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才可能确定某一刑法规范究竟是否能够涵摄规范事实。但实际的问题却是,在刑法用语较为抽象时,大前提的确定较为困难,因此才会出现前文所说的规范供给不足的问题。由此看来,案件事实并非完全是孤立的、静态地作为小前提存在的,它同时也会对大前提形成解释上的影响。日本学者加藤一郎认为:“自由法学不可能也不可以抛弃三段论法,只是运用中有其不同的地方。三段论法把法规下面的事实包容在内,然后由上向下进行演绎的逻辑推理。而自由法学,从下面的事实出发向上归纳为法,是在事实上面赋予法来得出结论。”*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实现案件事实与类型化刑法规范之间的契合性,是刑法解释的任务和宗旨,所谓疑难案件,实质上就是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断裂的情况。例如,对于伤害助势的行为如何认定。所谓伤害助势行为是指行为人并不实施伤害的实行行为,只是在现场造势的行为。伤害助势行为是否能够认定为伤害罪的共犯行为,就需要在利益衡量的视野下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从案件事实逆向归纳刑法规范类型的可能蕴意。《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规范目的是保护任何人免受他人的不法侵害,因此,需要分析助势行为在本质上是否对他人健康构成一定的伤害。但问题是,助势行为并不直接作用于被害人,因此衡量法益侵害的标准自然不能考虑助势行为对被害人的直接作用力,而应考虑助势行为对实行者产生的原因力是否具有现实性。换言之,如果承认助势者对实行者具有现实的加工行为,则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共犯,反之则不能够认定为共犯。行为人单纯地嚷叫“打得好”、“真刺激”等话语不应当认定为对实行行为具有原因的促使力量。但是,如果叫嚷他人快把对方“打残废”、“别耽误时间,快上”的,应当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帮助犯。*参见周光权:《刑法各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助势者尽管没有叫嚷上述内容,但是对实行者声称“尽管打,警察来了我给放哨”等行为,则亦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刑的帮助犯。由此可见,在理解构成伤害与否时,对伤害的界定不可能仅仅从《刑法》第234条的规范出发,基于经验的认知而判断何种行为是否具有伤害性。换言之,在上述认定伤害的思路中,案件的具体事实本身已经被纳入到解释者的视野之中。正如考夫曼所说:“理解经常是主观与客观并存,理解是从‘理解地平线’处罚,该理解不是消极地从认知中形成,而是需创设,其在‘包摄’时,不是仅将事件置于法律之下,完全不顾事件过程,而是在所谓‘法律适用’上扮演积极形成之角色。”*[德]阿图尔·考夫曼:《法律哲学》(第2版),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需要注意的是,在包摄案件事实对刑法规范理解时,对于内涵较为确定的刑法用语则不能作出扩张性的解释,否则有可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例如,在对于交通肇事逃逸中“逃逸”的界定中,有学者认为,由于行为人先前的肇事行为使他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产生了作为义务,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当然能够成为法定刑升格的根据。所以,应当以不救助被害人(不作为)为核心理解和认定逃逸。例如,发生交通肇事后,行为人虽然仍在原地,但不救助受伤者的,应当认定为逃逸。*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强调从“不救助被害人”为角度来解释逃逸的规范目的之方向是可取的。例如,行为人尽管逃离现场,但是通知朋友或亲属、或者拨打救助电话救助被害人的,则不能够认定为逃逸。但是,如果将肇事后仍然留在原地但不救助的行为也认定为逃逸,则其实并不符合规范的保护目的。例如,行为人自认为被害人的伤势比较严重已经来不及救助了,而没有采取救助措施(实际上如果行为人及时救助,被害人就不会死亡),等待公安机关的到来而自首的行为,势必也将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从而适用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这无法令人接受。实际上,逃逸之所以作为加重处罚的事由,所评价的是“基于逃跑而不救助被害人”的情形,上述观点的问题在对规范目的解释由于只是抓住了规范目的的一个要素,而出现扩大解释的情形,从而造成案件事实反包摄刑法规范过程中的不当解释。
(二)在符合国民预测可能性下规范地解释刑法
任何一种解释都需要考虑解释结论是否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之解释不可拘泥于各个用语之原本意义。解释适用之际,该用语与其他规定之关系或与法律制定时之各种情况等皆应列入考量。因此,乃容许扩充用语原来意义之扩张解释的存在。唯扩张解释亦应就其适用过程中设定界限,例如将用语文义之可能范围作为界限,以不超过一般国民预测。换言之,不论类推方式或者采行扩张解释之方式,只要属于有害国民预测可能性质刑罚法规的适用,最后,终将被认定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黄朝义:《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之解释》,载林山田等:《刑法七十七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一)》,元照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12页。目的解释同样如此,一般的国民预测反映了居于社会主导的价值规范,刑法无外乎就是这种规范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因此,目的解释也需要考虑解释结论是否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强调国民预测可能性,并不是刑法解释必须要符合所谓的民意,而是说解释的结论需要考虑当下的社会文化和人们对于某项解释结论的可接受性程度。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教授认为:“是否属于在一般国民认识到该用语之时,能够客观地预测到的范围之内的解释这一标准(客观性预测可能性)更为合理。”*[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易言之,国民预测性尽管在内容上可能是具有弹性的范畴,甚至是模糊的,但仍然是具有客观性的。之所以国民预测可能性具有客观性,源于构成国民预测可能性内容与基础的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具有相当的恒定性。例如,当将拐卖成年男子也解释为拐卖妇女时,必然会冲击人们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但是当财产性利益也解释为受贿罪的行为对象时,尽管在语义上突破了刑法用语上的“财物”的范围,但人们仍然可以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同样是可以换算的,甚至价值可能高于财物,财产性利益和财物一样,也具有可计量性,并不会为司法的认定带来诸多的困难。故这种解释不能认定为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将舆论直接等同于国民预测,并进而将舆论认为危害严重的行为就当然地被解释为犯罪。例如,性贿赂的问题,学界关于性贿赂的问题历来存在否定与肯定的观点。大体看来,否定的观点是,性贿赂无论如何也不能够理解为财物,性贿赂的本质是将人作为商品,不能够为受贿罪的财物所涵摄。但是如果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则无疑会得出肯定的结论。肯定说中有学者认为,在国家工作人员包养“情人”,其花费由请托人负担时,“因为包养‘情人’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请托人为该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资金后,往往会让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谋取利益,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因此,这种情况亦应以受贿罪定罪处罚,事实上这种情况往往社会危害性更大。”*张成法:《受贿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7页。的确,在普通公众眼中,对于收受性贿赂的官员危害程度的认知会比一般的财物性受贿危害程度要大。但问题是,在目的解释中,利益需要经过刑法规范的过滤才可能转化为指导刑法解释的指南。确定某一种利益是否为刑法所保护,需要在规范的类型中加以考虑。不能笼统地认为危害发生就应当被解释为犯罪,这种观点和逻辑不是实质解释的观点,而是规范外的任意解释。人们对实质解释所认为的可能导致内在的危险多是采取上述的思维,其实是对实质解释的误解,是对案件事实的泛实质化的理解。正如日本学者木村龟二教授指出:“实质违法性系对立于形式违法性,并非将其修正与变更,而应是具有补充及确认其内容之任务。”*[日]川端博:《刑法总论二十五讲》,甘添贵监译,余振华译,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24页。换言之,实质解释本身也是在刑法类型化和体系化视野下作出的解释。有学者所说的“在实质论者这里,文义、历史、体系充其量只是法律解释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它们都受目的的统领,是在目的的统领之下发挥各自的功能”,*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实际上是对目的解释及实质解释有失公允的评价。“在法律解释实践中,各种解释方法的效用尽管不能相提并论,但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哪一种解释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各种解释方法总是相互为用,我们很难说哪一种方法总是处于独立主导的地位,而不具有辅助意义,哪一种方法(如果能构成一种方法的话)则完全处于辅助地位。”*张志铭:《法律解释的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刑法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各种解释方法之间并没有位阶的顺序排列,“在实务上,的确应该根据规范保护目的、具体情境来权衡各种解释理由,形成具体的协调规则,以限制法官恣意解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目的解释始终绝对地具有优位性。”*周光权:《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即便主张目的解释决定论者,也并非认为文义等因素应当被统领于目的解释之中,张明楷教授认为“由于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故文理解释也具有决定性。不过,目的解释的决定性与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具有不同的含义。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在于:所有的刑法解释,都要从法条的文理开始,而且不能超出刑法文言可能具有的含义;凡是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解释,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即使符合刑法条文的目的,也不能被采纳。目的解释的决定性在于:在对一个法条可以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时,只能采纳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可见,目的解释仍然是在规范类型化下的解释操作。既然刑法受贿罪的对象是财物,则将人作为商品的“性贿赂”完全超出财物自身的含义。“将非财产利益纳入刑法,势必修改这种认定犯罪的标准,这样使受贿罪和财物大小的关联性丧失,能否得到公众的认同,是一个问题。”*周光权:《刑法各论》(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刑法解释之目的是在个案中适用刑法规范,如果解释的结论反而无法导致规范的适用,那解释方法的有效性则不免大打折扣。唯有在类型化指导下的目的解释才可能确定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并进而为构成要件的实质化判断提供可操作性的标准。
(三)通过利益类型化的判断强化目的解释的操作性
日本学者加藤一郎指出:“利益衡量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结论,存在着平衡被破坏的可能,同时,也造成思考过程的浪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必要把实质利益衡量的类似情况汇集成为一种类型的构成。这样,不是依据法规形式来加以分类,而是尝试依据实质性利益衡量来加以分类,这是创建新的法解释学所不可缺少的。”*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利益类型化的具体优势在于:(1)可以明确何种利益为刑法所保护,以至于为刑法判断设置相应的边界。类型化的利益表明并非所有利益都是被刑法所保护的,重要的与人的价值有关联的法益才可以成为刑法保护之对象。(2)类型化的利益可以为刑法解释提供个别化指导,进而为构成要件的判断指明标向,个罪之间的区分得以明示。(3)更为重要的是,类型化的利益能够在规范的范围内为刑法的评价设定制约并在个案的规范应用中充足刑法用语的实体与内涵。既避免了刑法评价的思维错乱,也厘定了刑法解释的应然指向。例如,行为人在妇女人数众多的公众场合裸露生殖器官,是否能够认定为猥亵,就需要结合刑法处罚猥亵行为的内在规范目的。《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罪之宗旨在于保障他人免受被强制的性侵害权利。行为人上述行为虽然有伤现场妇女之性羞耻心和性道德,但因此种行为并未采取强制之措施,也未具体化地侵害个体的性权利。因此,不能够将上述行为解释为本罪。
问题在于,既是利益类型化,则类型化一定面临着不彻底、不具体之情状。犯罪侵害利益有时表现为复杂化,理论上有谓复杂客体的范畴。所谓“复杂客体,实质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的客体包括两个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复杂客体为解释犯罪之实质也提供了标准,例如在抢劫罪中,行为人只要造成了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或者劫取了财物,就应认定为犯罪既遂。这种分析逻辑,有利于剖解抢劫罪的内在行为构造。但是,笔者认为,复杂客体的提法应当慎重,并有节制地运用该范畴。复杂客体容易导致对犯罪的理解过于宽泛,甚至导致危害认定标准的模糊。以绑架罪为例,通说认为,绑架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健康、生命权利及私人财产所有权。既是复杂客体,则其解释逻辑应当与前述的抢劫罪逻辑一样;但是在绑架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时,通说又认为,应当以绑架行为是否达到实际控制人质,并将其置于之实际支配之下为标准。*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77页。由此可见,同样是复杂客体,但是在抢劫罪和绑架罪的解释中,复杂客体对犯罪形态的认定却是两种不同的逻辑,难免自相矛盾。
此外,在复杂客体或者侵害多重法益的情况下,因构成要件的法定化而决定了法益的类型性。因此,突破法益类型性的制约而作出的解释也值得商榷。例如,在关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诈骗罪的关系时,有学者认为,“由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保护法益为诚实交易秩序,并不以造成他人财产损失为要件,故对于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必须再次判断其是否符合更重的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即使认为造成了他人财产损失的行为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也不妨碍认定该行为符合财产犯罪的构成要件。”*张明楷:《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单纯从利益受损角度出发,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确既对消费者的财产造成了侵害,也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但能否就此如上述观点一样,认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诈骗罪之间就一定存在竞合问题呢?对此,显然不能从纯粹的损失事实入手,还需要具体考虑个罪的类型化规定。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理由为,如果承认二者之间是存在法条关系,按照上述观点则应当适用重法优于轻法。但问题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数额标准是5万,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是3000元至1万元以上。如果生产、销售的数额达到5万元,则按照《刑法》第140条的规定,其最高法定刑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按照《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规定,应当适用数额巨大的量刑幅度,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此,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中就被诈骗罪彻底架空了。如果将这种逻辑推向极致,则凡是含有欺骗或虚假成分的行为,都可能在与诈骗罪比较的过程中因诈骗罪处刑较重而选择重法。这样的分析逻辑不禁令人质疑,刑法干脆直接规定诈骗罪就可以了,为何还要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岂非多此一举?构成要件是刑法立法类型化的产物,刑法立法以及刑法适用追求的是刑法用语的精确性,刑法解释必须接受类型化的制约。“刑法之适用对于人民之权益影响甚大,故只能为正确允当之适用,绝不可有误用之情事发生。”*蔡墩铭:《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自序第1页。维持刑法解释的适当之依据,就是须在解释者心中时刻谨记类型化思维是刑法解释不能走出的背景。正如台湾学者所言:“优胜的利益本并非评价之标准(而是评价之客体),它仍须借助其他适格之评价标准,方能判断其是否值得法律加以保护。”*高金桂:《利益衡量与刑法之犯罪判断》,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32页。如果说刑法解释需要树立在案件事实与刑法规范之间来回往返的解释理念,那么在解释方法上是利益分析与构成要件类型化交互认定的产物,这是解释刑法基本准则,更是对刑法明确性映射的法治要义的坚守。
[责任编辑:谭 静]
Subject: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urpose of Criminal Law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 Law
Author & unit:SHI Juhang
(Law school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China)
In the face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criminal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iminal law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analysis and the basis of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Interpretation of criminal law is not a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doctrine, but the expre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argument, the interests of the law and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ic, the latter is an extens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l risk is not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itself, bu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ck of interes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ype of thinking. The purpose of the criminal law in the interests of law interpretation is applicable to the need to properly handle the case facts to the criminal code of the constitutive significance,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national predic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the type of judgment. The limitation of the type of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 of the interest analysis is emphasized, which is the basic principle to be persisted.
the interests of law; the purpose of interpretation; substantive interpretation;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typifies
2016-12-2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法社会化研究”(11BFX109)的阶段性成果。
石聚航(1980-),男,河北邯郸人,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D924.1
A
1009-8003(2017)02-006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