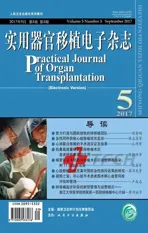心脏移植术后并发症及研究现状
2017-04-02李雨琪张海波孟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北京100029
李雨琪,张海波,孟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外科,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 北京 100029)
心脏移植是终末期心脏病的首选治疗方式,提高了患者的存活率及生活质量[1]。然而,供体的短缺限制了心脏移植手术的大量开展,并使得机械循环支持数量有所增加。据统计66 000个心脏移植病例的注册表,每年有近3 000个新病例登记,国际心肺移植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ISHLT)指出,移植术后1年、5年生存率分别为83%、72%,有较明显提高,因近年在患者选择、外科技巧、供体保存以及术后管理、免疫抑制方案和相关并发症预防等方面的改进,使得患者存活率有所提高,生活质量较前改善。但仍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威胁患者术后的长期生存。
1 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
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是心脏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症,是患者术后30天内死亡的主要原因,病死率近40%,近些年发生率轻度升高,可能与大量使用边缘供体相关[2-3]。起初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定义,使得不同心脏移植中心报道的PGD结果差距较大,发生率为2.3%~33.0%,病死率为14%~83%[4]。2014年4月,ISHLT关于心脏移植术后PGD的定义、诊断和治疗发布了指南[5]。原发移植物功能障碍定义为心脏移植术后24小时内发生的原因不明的单一左心室、右心室或者双心室衰竭,而排除了已知继发因素如超急性排斥反应、肺动脉高压、手术并发症等。原发性移植物左室功能不全(left ventricular graft dysfunction, PGD-LV)根据超声心动图、血流动力学和药物或者循环支持进一步分为轻、中、重三个等级。此共识的资料来源于47个移植中心,包括了9 901例心脏移植患者,其中733例(7.4%)发生了PGD,其30天病死率为30%,1年病死率为35%。主要的死亡原因包括多器官功能衰竭(占70%)、原发移植物衰竭(占20%)、脓毒症(占10%)[6]。目前多种致死因素已被明确,脑死亡因素使移植物心肌功能减退[7]、β受体的敏感性减低[8]。2013年,小鼠实验研究发现,脑死亡加剧了移植术后心肌缺血/缺血再灌注损伤,降低了移植小鼠的存活率。进一步受体小鼠的靶向补体抑制剂改善了脑死亡所加剧的缺血/再灌注损伤[9]。而2016年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中一个单中心经验研究发现,脑死亡时间越长,发展为PGD的发生率越小[5],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证实。急性缺血 /再灌注损伤(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IRI)及心肌顿抑与心肌保护不足有关,已经被证实是原发移植物衰竭的主要因素。总缺血时间超过4小时仍是影响1年生存率的主要因素。有动物实验研究发现,长时间低温储存的供体再灌注时,对心钠素(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ANP)的管理显著改善了左室功能,但对室颤的发生无明显意义。由此,可以利用ANP提高供心左室功能,从而减少心脏移植后移植物衰竭的发生率[10]。
治疗移植物衰竭的目标是在保证足够容量负荷前提下减少右心室前后负荷。严密监测血压以保证冠脉及重要脏器的灌注。通常给予患者强心药物(米力农或者多巴胺联合多巴酚丁胺)以及血管扩张剂(如硝普钠或者硝酸甘油)[11]。应用左西孟旦治疗心脏移植术后原发移植物衰竭安全有效,减少了机械循环的治疗[12]。前列腺素以及吸入性NO可以减小肺血管阻力,基本不影响血压,可以用于治疗血压临界的患者[13]。西地那非是一种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以用来治疗移植术后右心功能不全。右心功能不全是原发性移植物功能衰竭(primary graft failure, PGF)的最常见原因,这些患者通常有较高的右房压(>20 mmHg,1 mmHg=0.133 kPa),较低的肺毛细血管楔压(<10 mmHg)以及低心输出量和低血压[14-15]。术前测量患者的肺血管阻力以及跨肺压差并监测对于预防该并发症的发生有很大作用。应用机械辅助循环支持(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 MCS)是治疗重度PGD患者唯一有效的方法,能够保证终末器官灌注,预防多器官功能衰竭,减轻心室负荷,避免血管活性药物过度应用,从而恢复移植物功能,77%的患者能够好转,成功撤除MCS[16]。ISHLT指南建议主动脉内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n pump, IABP)应该作为药物治疗后无效的第一选择,因其创伤小,通过增加冠脉供血和左室功能而有效的应用[17]。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及心室辅助装置(ventricular assist device,VAD)应该作为后续手段。ECMO治疗重度PGD效果良好,患者1年后存活率无异于未患PGD的患者[3]。有研究发现,重度PGD应用静脉-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比应用VAD的装置相关并发症、病死率要低,移植物恢复率高[16]。
心脏移植术后通过RADIAL评分能够较好的预测PGD的发生发展,利于预防和早期治疗这一并发症(R:右房压≥10 mm Hg,A:受体年龄≥60岁,D:糖尿病,I:强心药支持,A:供体年龄≥30岁,L:缺血时间≥240分钟)[18]。日本单中心研究发现[19],供体应用高剂量强心药物、受体既往脑卒中病史是心脏移植术后发生PGD有意义的预测因素。因此优化受体移植前条件,预防脑卒中,并通过仔细评估供受体匹配度,使边缘供体危险因素数量最小化,以减少移植术后出现PGD的发生。高敏肌钙蛋白 T(high-sensitivity-troponin-T,HSTNT)大于2 000 ng/L和体外循环时间延长是PGDLV的独立预测因素。由于体外循环时间受术中血流动力学等手术相关因素影响较大,因此监测心脏移植术后患者HS-TNT有益于早期发现PGD-LV[20]。另外,检测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 PCT)、B型尿钠肽(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等指标简单易行,还可以检测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白细胞介素 -6(interleukin-6,IL-6)等[5],这些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术后患者的功能状态,对患者PGD的发生发展给予提示,从而更好的预防与及时治疗。
2 移植物血管病变
心脏移植物血管病(cardiac allograft vasculopathy,CAV)是心脏移植术后最重要的心源性死亡原因[21],它可能是慢性排斥的一种临床表现,尸检研究发现CAV综合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中心性内膜增厚、纤维化,血栓形成,以及炎症反应[22-23]。可以导致冠脉管腔狭窄或闭塞致使心肌缺血。ISHLT登记信息上显示,CAV在术后第1年、第5年、 第 8年 发 病 率 约 为 8%、32%、40%[24]。CAV危险因素包括: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不匹配,免疫抑制的类型, 抗体介导性排斥反应,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吸烟,糖尿病,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供体脑死亡,供体年龄、性别、缺血/再灌注损伤等[25]。这些因素会增加局部炎性反应、加快冠脉狭窄进程[23,26]。
由于移植物去神经化,缺血症状不明显,并且常规冠脉造影结果低估了病变的程度,这对于CAV的诊断常常受到限制[27]。2010年ISHLT指南[28]:冠脉造影Ⅰ级推荐,缺点:心外膜血管评估受限,早期病变、弥漫病变检测不敏感,射线照射,造影剂肾病。大多数的移植中心常规行冠脉造影检测CAV病变程度及进展。然而,传统的冠脉造影经常遗漏或者低估CAV。一项研究发现冠脉造影的阳性发现率仅为44%[29]。而血管内超声(intravascular ultrasound, IVUS)诊断了近50%移植术后患者冠造正常的患者有CAV[30-31]。因此,一些移植中心认为术后1个月、12个月应该常规行IVUS来明确高危人群的未来心血管事件[32]。还有一些移植中心应用无创检查来帮助诊断CAV[33]。多巴酚丁胺负荷超声心动图是常用的手段,与冠脉造影相比,敏感度约为80%,而相比于IVUS,其特异性为88%。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有较高的阴性预测价值,可用于严重CAV的检测。多层螺旋CT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86%和99%;但是这种检查方法不适用于移植术后患者,因为这些患者通常有较高的静息心率,可能影响成像效果。此外,对比剂的使用及放射性可能会增加肾功能损害或者导致肿瘤发生,因此,在大部分移植中心CT不是常用的检查方法[26,34]。冠脉造影仍是大部分移植中心诊断CAV的标准。ISHLT指南未将光学相干断层成像术(optional coherence tomography, OCT)列入推荐,而目前有研究发现,OCT通过增加了对斑块形态学及血管壁结构的评估,优于传统的冠脉造影[35]。分层纤维化斑块是最普遍的斑块组成形式,与非致命性移植物冠脉血管病变进展(nonfatal CAV progression, NFCP)密切相关。通过OCT检测出的分层纤维化斑块和亮斑被认定是用来预测NFCP的重要预后标志物。因此,在花费不成问题并且有OCT检查设备的前提下,建议进行OCT检查以评估心脏移植物血管病变并指导治疗。
为了防治CAV,一些预防性用药包括他汀类药物[36],可以减缓 CAV 的进展,改善生存率[37-38];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ve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 ACEI)可以改善微血管内皮功能,激活内皮素,促进斑块消退[39-40];还有钙通道阻滞剂,可能延缓CAV的进展[41]。一些免疫抑制剂如西罗莫司、雷帕霉素可能也会减慢CAV的进展[42];某些特定的感染,如CMV感染可能与CAV发生相关。更昔洛韦可能减慢CAV发展,然而缺乏有效的CMV预防用药可能加速管腔狭窄的进展[43-45]。
CAV的再血管化治疗不影响长期生存率,可能仅用来缓解症状[46]。大部分移植中心选择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来治疗有症状患者[47],冠脉搭桥术因较高的死亡风险很少施行。对于CAV的治疗,再移植手术是唯一明确的治疗手段[48-49]。
目前,他汀和肝素诱导低密度脂蛋白体外血浆分离置换法成为CAV新的治疗方法[50]。纤维蛋白肽B β15~42提高微脉管系统并减少缺血/再灌注损伤[25]。近期关于脂质纳米粒子携带化疗药物治疗兔子心脏移植后冠脉病变的相关实验研究[51]为将来临床治疗CAV提供了新方向。基质金属蛋白酶 -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9, MMP-9)在心脏移植物内明显高表达,且与炎症因子分泌、免疫细胞浸润、纤维化及心脏移植排斥程度呈正相关,因此,血清MMP-9可作为CAV早期病理变化及诊断的预测指标。研究证明,通过应用MMP-9抑制剂降低MMP-9水平及活性,可抑制心室重构、抗炎、改善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预防心血管事件发生、抑制心脏移植后排斥反应等,这些均有利于心脏移植后防治CAV的发生发展,为该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新靶点。改善心脏移植的远期疗效[52]。
3 感 染
感染是移植术后的主要并发症[53-54],造成1年内的病死率近20%,并且是存活移植患者余生最主要的发病及致死因素[55]。众多病因中,由于应用免疫抑制剂所致的机会性感染最为突出。术后6个月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呼吸机支持、心室辅助装置、供体CMV阳性、OKT3诱导治疗[56]。多中心分析发现,移植术后感染的主要部位在肺部,因为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患者常免疫低下,各种感染源如原虫、真菌、细菌、病毒,均可能造成感染,其中病死率最高的是真菌感染。
移植后第1个月,大部分感染是院内相关感染,多为细菌感染,如导管性、手术相关及机械通气相关感染。术后第2个月,机会性感染流行,特别是CMV感染,弓形虫病,查加斯病,曲霉病,卡式肺孢子虫肺炎。术后第6个月开始,随着免疫抑制剂应用的减少,与免疫健全的患者类似,社区获得性感染更常见,但是较易发展为严重感染。CMV感染是实体器官移植后患者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不仅表现在感染综合征方面,而且表现于排斥反应、移植物血管病变,机会性双重感染方面。移植患者术后6个月内容易感染CMV,患者临床表现差别较大(从轻微发热症状到致命的多器官功能衰竭)[57-58]。CMV感染是急性、慢性移植物排斥的独立危险因素[58]。普通的预防性抗病毒药物包括高剂量阿昔洛韦、免疫球蛋白、更昔洛韦,一些指南和综述推荐伐昔洛韦作为预防用药的选择。因为静脉应用免疫球蛋白花费大,并且治疗的有效性差于更昔洛韦。口服阿昔洛韦已有不少研究证实有效[59],但是供体血清阳性/受体阴性的患者其药效欠佳。伐昔洛韦是能减少CMV感染和排斥反应的新型用药。预防性应用伐昔洛韦可减少CMV发病率,从22%降至2%。高剂量伐昔洛韦(8 g/d)被证明有效[60],但是38%的患者由于发生神经系统并发症而被迫中断。应用伐昔洛韦3 g/d的剂量CMV发病率为6%[61]。应用伐昔洛韦1 g/d足以预防移植术后CMV感染,减少了患者花费及药物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62]。
在移植前所有患者都应该注射肺炎球菌疫苗及流感疫苗。术后不久即应预防性应用抗肺孢子虫、抗单纯疱疹病毒、抗口腔念珠菌及低剂量伐昔洛韦预防CMV等药物治疗。脓毒症的临床表现因人而异,往往由轻度或非典型症状到重度难治性休克。因此,需要高水平的监测以助于早诊断,并在感染早期进行治疗。常用治疗手段是应用广谱抗菌药物,可以联合抗病毒或抗真菌制剂。除此之外,医生应根据感染程度考虑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
4 排斥反应
移植排斥反应根据急性程度可以分为超急性、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根据机制可分为细胞免疫排斥和体液免疫排斥。超急性排斥是由已存在的抗移植物抗体所介导,可在移植后数分钟到数小时即发生,引起移植物脉管快速闭塞导致衰竭,但目前在血液配型及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配型等技术下很少发生。
急性排斥又可以分为细胞介导和体液免疫介导两类。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一般在术后1周内或数年内发生。细胞排斥反应主要是由T淋巴细胞介导。目前,急性排斥反应仍没有敏感的血清标志物,心肌活检仍是诊断的金标准[63-64]。在大部分移植中心需要至少术后1年内定期进行心肌活检。因为在排斥反应期间,患者可以无临床表现。活检可根据ISHLT修订的标准评分:0级:无排斥反应;1R级,轻度:间质性与/或血管周浸润,有1处心肌细胞损害;2R级,中度:2处以上心肌细胞损害;3R级,重度:多处心肌损害弥漫浸润,可有或无水肿、出血、血管炎。
急性体液排斥反应及慢性排斥反应主要表现为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ntibody mediated rejection,AMR),多引起移植物功能不全[65]。目前,已发现AMR的危险因素包括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on antibody, PRA)水平升高、CMV感染阳性、术前机械辅助支持、T细胞配型阳性、二次移植、经产妇以及莫罗单抗CD3治疗史[66-67]。ISHLT指出应从临床、组织病理学、免疫病理学及血清学4个方面来诊断AMR,然而有超过半数的移植中心根据心功能不全和活检未发现细胞浸润来诊断。临床方面主要包括移植物功能不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等,早期发生AMR与之较密切。随着对AMR认知的提高,晚期发病率也在提高。抗体反应激活补体系统,是AMR的主要病理机制。补体和免疫球蛋白在移植物微血管沉积,会引起内皮细胞激活、细胞因子释放、巨噬细胞浸润,增加血管渗透性,形成微血管血栓,诱发炎性反应过程。血管内皮是首先接触抗体诱发AMR的主要场所[66]。抗体和补体反应诱导细胞内信号转导,引起内皮活化,表现为内皮细胞(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增大肿胀,而成为表面抗原决定簇的结合点。随后因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归巢及单核细胞的聚集发生的炎性反应使白细胞穿过内皮细胞浸润到血管壁,引起相应组织损害。免疫球蛋白在AMR的诊断中缺乏特异性和敏感性,因为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种类丰富,且在体外容易与抗原解离、并在体内快速降解。补体沉积是AMR的必要条件,有实验提出C3d和C4d是诊断AMR的一条标准[68]。供者特异性抗体(donor specific antibodies, DSAs)与细胞排斥、AMR及CAV的发生关系密切。研究发现,在C4d和C3d阳性的活检标本中,约95%可发现DSAs;而C4d+C3d+常提示与移植物功能和病死率紧密相关,约84%的双阳性病例发生移植物功能不全[68-69]。
急性排斥反应患者应住院进行基本评估,包括心脏彩超及血液检查。而发生急性心衰或者血流动力学改变的患者应收入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治疗并行右心导管检查。予强心、升压、利尿及抗心律失常等药物对症治疗。AMR的基础治疗包括静脉大剂量激素冲击、静脉应用丙球蛋白、血浆置换、光分离置换法等。利妥昔单抗可以用来减小排斥复发风险[66]。
急性全身细胞排斥反应不论分级均需应用大剂量激素冲击。根据ISHLT指南,在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或激素治疗12~24小时仍无改善时,需加用抗T细胞抗体进一步治疗[38]。
5 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不全是心脏移植术后常见并发症,通常移植术后1年内是肾功能损伤的急速恶化期,1年后肾功能缓慢下降[70]。严重急性肾损伤是心脏移植术后1年患者死亡的预测因子,可以通过肾小球滤过率及一些评分系统评价分层,如RIFLE、AKIN、KDIGO[71]。慢性肾功能不全是环孢素和他克莫司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72],在第1年内影响超过25%的患者,术后5年16%的患者患有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221 μmol/L,需要透析或肾脏移植)。术后10年30%的患者发生肾脏衰竭,占10年病死率的8%[73]。主要机制与入球小动脉的收缩及肾小管间质纤维化有关[74]。患者术前应通过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或肌酐清除率评估肾功能,出现异常时需进一步评估,包括蛋白尿、肾动脉疾病,行肾脏超声检查,以排除肾脏固有疾病。2016年ISHLT指南指出[38],肾小球滤过滤低于30 ml /(min·1.73 m2)考虑为不可逆肾功能不全,为心脏移植的禁忌证(Ⅱa级推荐,C类证据)。术后早期诱导治疗,以延迟这环孢素和他克莫司的启用,并且密切监测控制药物浓度,避免应用其他肾毒性药物来保护肾功能。与环孢素相比,他克莫司较少发生慢性肾功能损伤,其优势在于他克莫司谷浓度与总暴露关系可靠,可降低血压,减少肾血管收缩,增强免疫抑制。目前明确的移植术后急性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大的体表面积、高血压、吸烟病史、术中少尿[75]。慢性肾功能不全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女性、移植前或移植术后早期发生肾功能损害[76]。移植前需特别注意上述危险因素,以期患者良好的预后。
儿童心脏移植人群中,术后急性肾损伤普遍常见,回顾分析66例行心脏移植的患儿资料发现[77],73%的患儿发生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与其他儿童心脏手术一样,较低基线水平的肌酐清除率(estimated creatinine clearance,eCCl)的患儿不易发生AKI。这里定义AKI为术后7天内测量的最高血肌酐水平较基线eCCl水平下降25%,根据修订后的RIFLE标准。移植前通气治疗及高水平的eCCl基线是AKI的独立危险因素。移植前强心药的使用减少了发生AKI的风险。AKI患儿通气持续时间及重症监护时间有所延长。因此建议,评估新的免疫抑制策略以减少或者尽可能延缓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 CNI)的使用,监测控制药物浓度,从而减少AKI的发生。
近年报道,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hemolytic uremic syndrome,HUS)多与细菌感染相关,以贫血、低血小板血症、肾功能损伤三联征为特征。与应用CNI密切相关,特别是他克莫司。肾脏移植受体中已有很多报道,成人心脏移植中也有相关报道[78-79],2016年首次报道了儿童心脏移植受体发生他克莫司相关HUS的个案[80],研究指出,他克莫司相关HUS的机制尚未明确,肾移植受体较为多见,移植物活检发现微血栓形成,血栓形成的原因尚不清楚,相关假说指出他克莫司可能通过干扰血栓素A2和前列腺素PGI2的平衡从而影响凝血级联反应。也可能诱导内皮损伤,释放血管性血友病多聚体和血小板聚集因子从而导致功能不全。而长期应用CNI致相关肾毒性,损伤间质和纤维化可表现为迟发的HUS[81]。虽然HUS这一并发症并不常见,但这项报道提醒着我们,当发现应用他克莫司的移植患者有贫血、血小板减少症、肾功能损伤时,及时考虑他克莫司相关HUS,并予以重视。
6 恶性肿瘤
心脏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使患者生存率升高,免疫抑制方案相关问题一直是焦点,给患者带来不同的预后,免疫抑制不足会造成排斥反应,免疫抑制过度会发生感染,恶性肿瘤,慢性肾脏疾病。恶性肿瘤是移植患者晚期死亡的一个主要因素,3年以后约占死亡因素的1/4[38]。主要原因是免疫抑制治疗期间预防用药剂量的增加。预防和治疗排斥反应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强度与其产生的不良反应及术后恶性肿瘤的发生成正比。据ISHLT指南,心脏移植患者术后1年恶性肿瘤的累计患病率为2.9%,10年为31.9%[38]。恶性肿瘤是慢性排斥反应的结果,最常见的是皮肤癌(占42%~50%),紫外线照射是最主要的致病因素,头颈部位占70%,鳞状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移植受体患鳞状细胞癌的概率是常人的65~250倍,患基底细胞癌是常人的10倍。移植术后淋巴增生病变是移植术后第二常见的恶性肿瘤,尤其以B细胞型为著,多发生于术后1年内,总发病率在5年内约为3%,EB病毒感染与其发病相关[82]。儿童最常见的移植后恶性肿瘤是淋巴瘤,10年发生率为8%[83]。其他常见肿瘤(乳腺癌、宫颈癌、肺癌、结肠癌、前列腺癌等)的发病率与普通人群相似,肺癌是最常见的实体器官癌,一项单中心研究发现,在长久吸烟的老年男性中,肺癌发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84]。高龄、男性、白种人、先前存在恶性肿瘤、免疫抑制治及致癌病毒感染等是移植术后患恶性肿瘤的高危因素[85]。防治恶性肿瘤的策略是严密的术前监测,控制免疫抑制药物浓度在最低有效水平,预防病毒感染如CMV、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避免太阳暴晒,定期系统地体检和检测。新型免疫抑制剂(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向抑制剂)的应用,使CNI和糖皮质激素的用量最小化,改变了传统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糖皮质激素+环孢素(CSA)/他克莫司(Tac)+ 咪唑硫嘌呤(AZA)/麦考酚酸酯(MMF)。治疗方法通常是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密切随访排斥反应。
7 神经系统
脑血管意外在心脏移植手术中的发病率高于常规心脏手术,其中缺血性脑卒中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发生率>13%)高于颅内出血(2.5%)。除了围术期高血压、糖尿病、吸烟、卒中史等常规危险因素[86],术前左室辅助、IABP、术中转机时间、术后肝功能衰竭也是心脏移植术后早期神经系统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87]。而且有研究发现,在扩张性心肌病及瓣膜病的患者中,移植术后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率更高[88],提示对病心的操作或切除可能会增加术中脑卒中风险。颅外动脉粥样硬化如颈动脉狭窄超过50%,是脑卒中发生的一个常见病理机制。心源性脑栓塞也是脑卒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其中心房颤动占主要地位。已有研究报道,心脏移植术后早期房颤的发病率很高,而且超过一半的患者发生于术后前2周内。此外,腔隙性脑梗在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病中约占25%。然而脑出血的发生多与凝血功能紊乱、体外循环(cardiopulmonary bypass,CPB)压力过高、过度灌注及不可控的高血压相关。已研究发现脑卒中在心脏移植术后有显著的发病率及病死率[89],约占术后早期死亡病例的7%,并且是影响远期生存最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与1年存活率相关[90]。
8 结 论
心脏移植仍然是终末期心衰患者的最佳治疗手段。尽管术后结果能得到改善,但其术后管理具有挑战性,这些患者有一系列严重并发症(可能与免疫抑制治疗及同种异体排斥有关),还可能合并感染(非典型临床表现)及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等。对显著影响患者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移植物相关和非移植物相关的症状高度警惕、早期诊断并予适当的干预是移植术后患者的长期生存的关键。详尽的系统评价及严密的管理能使这些并发症的影响最小化,并且最终改善移植术后的生存质量。